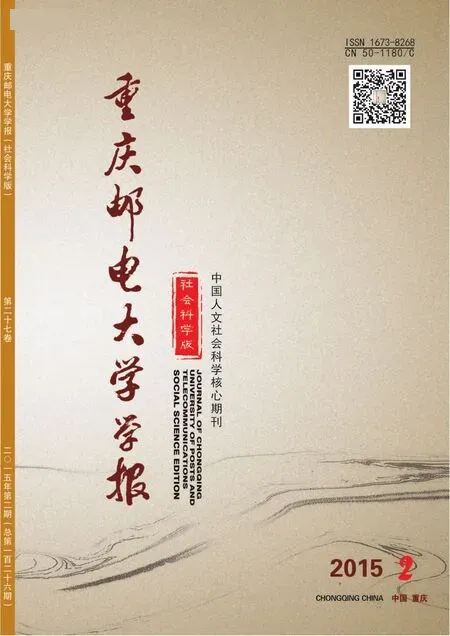新目录学派志:英国文学考据的兴起与没落*
2015-02-21史敬轩
史敬轩
(重庆邮电大学 外国语学院,重庆400065)
一
沃特·威尔逊·格雷格(Walter Wilson Greg)进入剑桥三一学院时,罗素正担任该学院研究员。虽然格雷格主修中世纪与现代语言,但他对罗素的数学却兴味盎然,在《变量微积分》一书中,尝试用数学逻辑解决文学问题。罗素曾言:“在特定问题上,它(分析哲学)因此可以取得确定的答案,从而具有科学而非哲学的特征……我无疑相信,通过这些方法,许多老问题可以完全解决。”[1]这句话无疑印证了格雷格的梦想:“所有或差不多所有的文本问题都可以求助于目录学手段得以解决。”[2]
新目录派(new bibliography)这个名字易招致误解,不过罗素在中国的好友梁启超评价乾嘉学派时曾说:“多尊重古书,其辨伪程序,常用客观的细密检查”[3],其中对王念孙、引之父子十分赞赏,点出了目录学派工作的实质。英国的目录学到格雷格达至鼎盛,1908 年格雷格取得了新目录派的第一个里程碑式的胜利,他通过研究帕维尔四开本(据认为是莎士比亚戏剧1600 年、1608 年和1619 年的三个伪本)的首页,证明前两个版本并未出现当时的印刷特点和手段,由此认定三个不同时期的文献实际都出自1619 年。也就是在同一年,格雷格的论敌、试图用系统方法论为文学谋得科学地位的约翰·彻顿·柯林斯不堪羞辱,投水而死。
“格柯论战”是新目录派发展道路上的一场重要论战。格雷格说新目录派“并不只是图书目录的编纂”[4]40,他和学长罗纳德·布朗里斯·迈凯洛在大英博物馆书籍部管理员波拉德的建议下组成了“马隆”①Edmond Malone(1741-1812)曾对蒲伯写于1725 年的《莎士比亚作品集》进行过编订。学会,这三人后被称作“新目录派三杰”②莫顿文学教授弗兰克·帕西·威尔森(1889-1963)在为英国目录派协会所著的《莎士比亚和“新目录派”:1892-1942 年的目录学协会》一书中称三人为“a happy band of brothers”。。马隆会和“剑桥使徒会”相比,显得太过于默默无闻,因为使徒会彼此介绍入会的都是获得奖学金资助的学生,比如诗人丁尼生、目录派元老肯博(John Mitchell Kemble)等都曾是使徒会成员。格雷格家境殷实,显然不需要靠奖学金去读书。丁尼生曾讽刺柯林斯是“文学秀发上的一只虱子”[5],这么说不无道理,因为,有一个事实恐怕不得不考虑在内,那就是文学当时在大学的地位的确无法与罗素的数学哲学平起平坐,今天恐怕亦是如此。
文学,特别是英国文学能够进入大学课堂实在是十分晚近的事情。16 世纪下半叶,伊丽莎白女王的大主教马修·帕克吁请女王应该重视盎格鲁 萨克森语古书的研究工作,从而支持英国教会脱离罗马教廷的正当要求。这种呼吁反映出襁褓中的英伦民族意识,因为,嗣后兴起的文艺复兴作者们收藏古手抄本的热潮,导致了目录派首个重要作品的产生:内尔·科尔的《含盎格鲁萨克森手稿之目录》。这一浪潮也推动牛津在1795 年设立了盎格鲁 萨克森教授职位。即便如此,牛津也已远超剑桥,剑桥最终开始有文学学位是在《英语研究评论》(简称RES)创办的次年——盎格鲁 萨克森文学已经在文学史中独立成章了③参见A.W.Ward.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English Literature,Vol.1. Londo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08。。
而迈凯洛于1925 年创立《英语研究评论》,就是为了在英国文学和语言上“侧重历史性治学成果而非解读式批评”[6]。其实这也正是牛津的柯林斯所致力为之的。他认为过去对文学的理解太多印象性而不够严谨,《英语文学研究》一书,打算系统和科学性地“对戏剧家罗伯特·格林尼的文本做最终敲定”[7],但格雷格随后对该书中的不准确之处,诸如省略、错字、不实信息、标点等毫不留情地详加指责④参见W.W.Greg. Review of J. Churton Collins ed. The Plays and Poems of Robert Greene. Modern Language Review,1905(i):238-251。。这显然引起了柯林斯的不满,他反过来抨击格雷格对田园诗和田园剧“难以理解”、“一塌糊涂”,并说“评论家的任务应该既要评价不足也要揭露错误”[8]。结果他自投罗网,格雷格随即回应:“我由衷同意柯林斯教授的看法,批评家有责任向公众揭露一本书的错讹与不足。”[9]后来,一位好友致信格雷格婉劝他对朋友应笔下留情⑤参见现藏于剑桥三一学院格雷格书信之MSS 42。。其实二人并非立场不同的死敌,相反,二人同是新目录派的先锋人物,唯一的不同就在于柯林斯对文学文本准确性的要求要胜过格雷格所认为的文本本源的要求。换言之,需要“一套体系,可以使得英国文学大略……更加精确,更加专业化,更科学化”[4]40。
而科学正是新目录派塑造英国文学民族性的一杆大纛旗。“文学研究大多是个品味问题……因为,那些数据说穿了不过是大多之类所谓有关文学的八卦和闲聊而已。”[10]此话不无道理,因为如果没有准确的文本,任何对作者或者文本的所谓解读都可以妄称权威,这显然不足以使得文学成为有价值的学科。所以,新目录派认为,要想使得文学的地位更巩固,“精确的阅读和传抄文献显然是十分必要的”[4]39。
二
人们通常认为,印在书上的东西一定是对的,换言之,“印刷书籍能够给予印出来的文字和思想以牢固经久的形式,能够通过大量发行在页面上文字组织形式一致的相同拷贝来传播这一客观化了的语言实体”[11]。但梅鷟(1483-1553)在《南雍志·经籍考》下篇《梓刻本末》中指出:“……两经钦依修补,然板既从乱,每为刷印匠窃去刻他书以取利,故旋补旋亡。”同时期一个威尼斯修道士也指责印刷出现的三宗罪:文本讹误众多,文献内容不道德,愚人也可获得书籍。从印刷《圣经》导致释经歧义而造成的宗教分裂这点来说,教会的激烈态度可以理解。不过,印刷错讹或许正是有意为之,帕克等人翻译印行古艾尔弗雷克的《有关复活节牺牲的布道词》在有关圣餐礼的描述上与古英语原稿有诸多出入,因此,在对耶稣血肉化作圣餐酒与面包的阐释上与罗马的解释完全不同①参见Theodore H.Leinbaugh.Ælfric’s Sermo de Sacrificio in Die Pascae:Anglican Polemic in the Sixteenth and Seventeenth Centuries.Anglo-Saxon Scholarship,the First Three Centuries.Kalamazoo:Western Michigan University Press,1978。。这或许说出了一个我们未曾想过的问题,这也成为日后追求科学权威的新目录派始终无法逾越的障碍。
新目录派的潜台词正是印刷术的发展所带来的语言的规范化,“民族主义的发展要归功于法律和语言的稳定”[12]。1557 年,英国王室颁发特许状,书业公会成员或有特许状的人才有印刷书籍的权利,原因就是严格限制印刷工的“盗版”行为。不过这个“盗版”并不是新目录派和今天我们所认为的未经作者许可的印刷,而是指侵犯出版商利益的盗印。不久,莎士比亚第一对开本得以出版,但此时并没有作者这个概念,著作权只属于出版商,书业公会的垄断导致英格兰和苏格兰两个民族出版商之间的一场诉讼,由此,1709 年的《安妮法案》才将版权赋予了写书人——作者。英格兰人的“莎士比亚”由此产生,但新目录派似乎忘记了1709 年以前的事:如果莎士比亚是英格兰(English)的,那么从一开始他就应该属于英格兰。这正是格雷格和罗素的另一相同之处,二人都有一种将复杂事物归一的强烈渴望,用牛津学者贝特森的话来说,就是“作者这个字眼从字面上就该认可为是定论”[13],因为“对文本的固定赋予了作者以信任感”[14],作者成为了文本意义的终极决定者。这种“想当然”的意识延续至今,使得文学批评者们对于以印刷形式存在的文本的“研究样式和排版的视觉语言漠不关心”[15]。“说经者期于得经意而已,前人转注不皆合于经者,则择其合经者从之,其皆不合,则以己意逆经意而参之他经,证以成训。”[16]当本经作者的权威性被置于毋庸置疑的高度,就必然会产生王念孙所说的“礼仪生则生伪匿之本”[17]的乱象:任何人都可以假托圣贤而自命权威,目录派们同样要面对这样一个纠结的问题:或者认为莎士比亚是神化了的伟大戏剧创作者,或者必须辨别那些神秘作者的手到底是谁的。
格雷格选择了前者,他希望用科学来神化莎士比亚,或者说英国文学,从而提升新目录派的地位。2013 年是他为英国目录协会所作的《何为新目录派》讲座一百周年。在这次讲座上,他首次将新目录学定义为“文学文本传播物质的科学”[18]。在这篇讲稿中,包括名词和形容词形式,格雷格使用“科学”这个词前后有28 次之多——科学的力量似乎可以使英国文学的英国性确定而不容置疑,但这同样也导致了新目录派的内讧。
格雷格如此急于为新目录派谋求科学的头衔,未必就不应该,新目录派的另一位干将——彼得·亚历山大是位数学家。亚历山大的一个重要成就即分析次要情节的逻辑连贯性,辨别出Taming of a Shrew 是莎士比亚剧作的伪本。《驯悍记》有两个版本,情节也多有出入,其中一本中间冠词为a,而另一个则是the②亚历山大之前塞缪尔·西克森曾认为,The Taming of A Shrew 系出自The Taming of The Shrew 的赝本,但无实据。参见Peter Alexander,The Taming of the Shrew,The 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1926-09-16 和The Original Ending of The Taming of the Shrew,Shakespeare Quarterly,1969,20(1):111-116。。这似乎应该归咎于印刷工的疏忽,但这个疏忽却影响重大。在“印刷业的发展推动了民族语言的规范化”[19]的情况下,新目录派对于使得英语语文得以明晰民族身份是有功绩的。1921 年,迈凯洛在国王学院执教的时候就说过:“对于本学科的文本批评来说,确需涉及概略描述我们的语言和文学的历史沿革,其旨非为纪念我们的前人,而为批评其方法,评价其陈述”[20],以使它“引领我们走出了迷雾,走出泥泽,走出了混沌……”[21]毋庸置疑,仓颉造字而鬼夜哭,蔡侯纸出而天下从,图书的相对稳定特征使得书面语言能够以更久远和明晰的形式将民族意识和特性加以塑造和保存。
所以,当1815 年托克林出版专著认为古英语抄稿《贝奥武甫》源自古丹麦语的时候③参见Richard C. Payne. The Rediscovery of Old English Poetry. Anglo-Saxon Scholarship,the first Three Centuries.Kalamazoo:Western Michigan University Press,1978。,目录派显然看出了其中的不祥之兆。1837 年,肯博出版了他的现代英文译本以及研究专著——《肯博的贝奥武甫》,该书四次再版,是英国古书考据史上的巨著。不过他的成就却招来了本派同行的一场骂战,除了肯博为人刻薄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的德国人身份,虽然他试图转移矛盾到牛津和剑桥之间,但一个叫赖特(Cyril Ernest Wright)的学者一针见血地指出:“(肯博的贝奥武甫)给我们的不是盎格鲁萨克森的,而是德意志萨克森的!”[22]这一点影响了格雷格乃至整个目录学的发展:德国人在同年先于英国人成立了新莎士比亚研究会,海峡对面的学者们却对此表现冷漠。格雷格在1925 年曾经说过:“我唯一希望的就是‘告诫’外国人不要碰莎士比亚批评。”[23]科学本无国界,格雷格似乎忘记了这一点。
迈凯洛也曾说过新目录派也许永远无法与科学比肩而立:“我们时刻感觉到缺乏其他学科所定义的可控实验,诚然,我们时时处于一种分析者对其试剂的纯洁性毫无把握的情况下。”[24]尽管明知如此,但他们却始终不承认莎士比亚在写完他的剧本后曾做过修改,他们更乐意相信莎士比亚所有的剧本都是一气呵成的。格雷格认定莎翁在创作的时候必定留意要印刷出版,所以剧本才写了那么长。因此莎翁“与其说是个剧作家,不如说是个写书人”[4]57。这种想法有些荒谬,但考虑到对印刷图书的过分信赖却也不奇怪,这就是为什么兰姆公开宣称《李尔王》上不了戏台的因由①查理斯·兰姆曾说过该剧“is essentially impossible to be represented on the stage”,而更适合在书斋中品味,见其1811 年文“On the Tragedies of Shakespeare,Considered with Reference to Their Fitness for Stage Representation”. The Romantics on Shakespeare. ed. Bate. Harmondsworth:Penguin,1992:123-124。。
三
1930 年,格雷格荣任英国目录学协会主席,在就职演说中发表豪情壮志:“有一天,(新目录学)或成为公认的一场意义非凡的文学批评运动。”[25]英国人向来不好吹嘘,仅仅两年后,他就已经按明确类别辨析了整整70 份手稿。此后,他孜孜矻矻,见微知著,刊载文章150 篇,著书10册,总共辑录了各种原始文献资料125 份之多。1932 年,新目录派如日中天:格雷格获牛津荣誉文学博士学位,目录学协会的注册会员史无前例地达到了1 150 人,身为秘书长又荣膺协会金牌的迈凯洛在这一年成为了英国科学院院士。
实际上,即使撇开对开本,由于没有任何手稿遗存,要想寻根溯源,格雷格就必须更进一步。威尔森就曾提醒格雷格要“重点推敲印刷文本背后的手抄稿”[26],当足以认识到印刷不够可靠的时候,就必须寻觅印刷的来源出处。多佛·威尔森是波拉德的养子,他率先认为莎士比亚的全部印刷对开本或四开本都是印刷排字工在没有剧作者监督下的任意篡改,威尔森的剑桥版《新莎士比亚》依然是如今广为遵循的权威版本,对于新目录派来说,威尔森最有名的成就是《仲夏夜之梦》中有关疯子、恋人、诗人中的分行错误。手抄稿研究对于新目录派来说具有转折意义,如果新目录派单纯停留在印刷书籍的考量上,那么在维护英国文学的地位上必然处于十分尴尬的境地。因为,当卡克斯顿印行世界上第一本英语书时,是在佛兰德斯,而不是在英国本土,这本叫《特洛伊历史回眸》的书甚至都算不上英语文学作品。
不过,格雷格主要参校的仅是乡村舞台表演的提词本,这些故纸对于新目录派来说却不可小觑。古腾堡之前的作者或许“对于把名字加于一部作品之上几无兴趣,而印刷者则需要找出,或已经找到他们所印作品的真实作者——亦即作品并不是印刷者的创作”[27]。所以,只有假设这些小册子的作者是真实可信的,才能推证莎士比亚是“神圣的英国人”,这成为了新目录派后期论战的一个潘多拉魔盒。
当新目录派本能地认为作者在直觉上写下来的通常就是他已确定了的内容的时候,这显然会与新目录派就手写稿的认识相冲突:一方面他们对莎翁戏剧中的俚俗语汇和忌讳使用上存在矛盾,觉得莎翁不可能整段修改其戏剧作品;另一方面又不否认作者可能会另起炉灶。早在20 世纪20 年代,新目录派成员奥布莱特,一个真正的潘多拉就注意到伊丽莎白戏剧改编修订或许远比人们想象的要频繁得多。她认为印刷剧本,台词前面的名字可能并不是格雷格以为的抄写的原作者名字,有可能是乡村舞台表演的提词人为了方便记忆才写上的演员名字。为此格雷格写了评论加以回应,他嘲笑小姑娘幼稚,演员不按作者要求自作主张这种烦心事,居然也值得大惊小怪。而奥布莱特也毫不示弱地高调回应②“格奥论战”可参见E.M.Albright.Dramatic Publication in Engla nd 1580-1640.New York:Modern Language Society of America,1927,以及RES 在1928 年第4 期发表的Albright.Dramatic Publication in England,1580 1640:A Reply 和Greg.Review of Albright,Dramatic Publication 以及Reply to Albright 两篇论文。。事实上,格雷格已经很清楚文学文本考据不大可能像科学那样做到一锤定音。他在自己的笔记和个人抄稿《温莎风流娘儿们》的编本中记录了很多奥布莱特的批评和观点,可见对她看法的重视。同时,在私人信件中谈到自己的见解时,也自嘲地写满了“荒唐”、“胡唚”、“垃圾”、“臆测之作”、“这完全不可能”等用语——在回应奥布莱特时,他流露悔意,早没有了当年笔诛柯林斯的戾气。
不过,“格奥论战”并不意味着新目录派就此改弦更张了,恰恰相反,当一个新西兰人来到剑桥的时候,此人的《剑桥出版社1696-1712》迅即引起一片哗然。唐纳德·麦肯锡于1966 年出版的这本书,被认为是新目录派自开山以来最振奋人心和能够继承三杰所确立的传统的扛鼎之作,但该书也意外地摧毁了新目录学的基石,即梅鷟所提出的假设以可靠的排字工将一个固定完整的字版传播于“交流圈”①罗伯特·达恩顿的交流圈概念(communication circuit)指的是从作者到出版者、印刷者、贩运者、书商和读者形成的一个关键要素运行的封闭模式(参见Robert Darnton. The Literary Underground of the Old Regime. Harvard Uni. Press,1982:22)。中的前提是不存在的。由剑桥的出版历史可知,书肆一般会同时运作几个固定字版,即“板既从乱”,消解了新目录派版本甄别的逻辑链条。这立刻引起了正统目录学者的自卫,他们认为数百年前的剑桥社不过是个乡村小作坊,不足以代表伦敦更权威的印刷行。麦肯锡随即对此进行了辩驳,并提供旁证材料,不过他没有进一步运用18 世纪的手稿去质证莎翁对开本和四开本的物质分析。相反,他全面描绘了格雷格所定名的《威尼斯商人》的排字工B 的草就工作。和波拉德1909 年出版的《莎士比亚对开本和四开本》相比,麦肯锡并没有带着一种穷根溯源的想法去寻找英格兰的“莎士比亚”,而是用一种更宽容和开放的态度分析文本的物质世界。达恩顿在2009 年《书的案例:过去、现在与未来》中说,“19 世纪格雷格创建了新目录派,20 世纪麦肯锡则使之臻于完善”[28]29,非本土的麦肯锡“威胁到了那些老卫道士…… 他在他们的游戏中打败了他们的顶尖好手”[28]136。
这正是新目录派学者们最缺乏的东西:一种世界性的态度。新目录派始终没有达到几乎是同一时期的乾嘉学者的成就,乾嘉学者一直都没有脱离六经皆史,将圣人仅作为哲史学家来看待的基本方针。王念孙总结出古书致误六十余例,为书籍的校勘辨伪建立了完善的工具体系②梁启超语王念孙“订正俗本九百余条”,传王念孙举“古书致误之由,凡得六十二例,其中就《淮南子》正文、注文中误、脱、增、删、移、改的严重情况抽出来的实例有四十四例,就《淮南子》韵语中误、脱、增、删、移、改的严重情况抽出来的实例有十八例”(参见洪湛侯:《中国文献学要籍解题》,杭州大学出版社1997 版,第102 页),但在王书中,仅见“以上六十四事略举其端,以见例,其余则遽数之不能终也”(参见《读书杂志》下册,淮南内篇第二十二,第63 页)。。相比新目录派则明显疏漏,急于通过科学维护伊丽莎白戏剧表演的权威标准,新目录派的方法始终不成体系,“由于实例和所需解释证据总是两不搭界,他(格雷格)要想历数例证数目困难重重”[4]42。
但新目录派绝非一无是处,正如迈凯洛所言:“(至少)我们这些发现是真正的发现,不单是观点类的东西,而是经得起证明的,没有任何后来调查可以动摇的东西,这就是属于目录学研究的魅力所在。”[29]新目录派所做的去伪存真工作,曾被盛赞为是“向19 世纪主观印象主义发出的《独立宣言》”[30],这么说不免言过其实,不过也道出了文学民族化的初衷。到1950 年罗素获诺贝尔文学奖的时候,目录学已经成为英国众多大学英语系博士专业的入学资格要求。研究生们在学习英语语言学和其他专业技能的同时,要学会“识别格式、核对签名、发现删节(包含错误或可能有违碍字句的书页)、明辨字号、追踪水印、分析插图及鉴别装帧”[31]。同年,因其对“英国文学所作的贡献”,格雷格被敕封爵士位。而数学家罗素的文学奖获辞则是:“表彰其在捍卫博爱理想与思想自由方面的丰富而重要的作品。”
新目录派缺乏博爱精神,它只爱英伦民族。早在20 世纪60 年代后伴随法兰西“五月革命”的风潮,从苏联形式主义汲取养分的结构主义大纛开始迅速横扫西方世界,布拉格学派和法兰克福学派所掀起的狂飙沿着语言学、符号学、社会学的路线演进,纵贯了法国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美国西马影响下的文化唯物主义和解构主义等批判运动。相形之下,英伦岛上的新目录派则落落寡合,再没有类似肯博或是柯林斯这样的人来打算挑起一场绅士们的决斗了。新目录派最终没能掀起一场“意义非凡的文学批评运动”。
[1]RUSSELL B. A History of Western Philosophy[M].New York:Simon & Schuster,1945:834.
[2]GREG W W. Bibliography-A Retrospect[M]//FRANCIS F C. The Bibliographical Society 1892 1942:Studies in Retrospect.London:The Bibliographical Society,1945:29.
[3]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M]. 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276.
[4]MAGUIRE L.Shakespearean Suspect Texts:the“Bad”Quartos and Their Contexts[M].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6.
[5]CHARTERIS E. The Life and Letters of Sir Edmund Gosse[M].London:Heinemann,1931:197.
[6]BABINGTON D,AHDERON V,LEPAN D,et al. The Broadview Guide to Writing[M]. 5th ed. Buffalo:Broadview Press,2010:407.
[7]COLLINS J C.Plays and Poems of Robert Green:Vol I[M].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05:vii.
[8]COLLINS J C. The Hybrid-Academic[N]. The Tribune,1906-04-20.
[9]GREG W W.Greg’s Reply[N].The Tribune,1906-04-26.
[10]FREEMAN E A. Literature and Language[J]. The Contemporary Review,1887(52):562-563.
[11]KERNAN A. Printing Technology,Letters and Samuel Johnson[M]. 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7:53.
[12]JOHNS A.The Nature of the Book:Print and Knowledge in the Making[M]. Chicago:Chicago University Press,1998:11.
[13]BATESON F W.The Application of Thought to an Eighteenth-Century Text[M]//WELLEK R,RIBEIRO A.Evidence in Literary Scholarship:Essays in Memory of James Marshall Osborn.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9:323.
[14]戴维·芬克尔斯坦,阿里斯泰尔·麦克利瑞.书史导论[M].何朝晖,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42.
[15]MCKENZIE D E.Typography and Meaning:The Case of William Congreve[M]//MCDONALD P,SUAREZ M F.Making Meaning:Printers of the Mind and Other Essays.Amherst: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2002:236.
[16]王引之.经义述闻:第32 卷[M].南京:凤凰出版社,2000:1.
[17]王念孙.读书杂志[M].北京:中国书店,1985:241.
[18]GREG W W. What is Bibliography[J]. Library,1913,12(1):48.
[19]BRYSON B. Mother Tongue:the Sto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M].London:Penguin Books,2009:127.
[20]MCKERROW R B. A Note on the Teaching of English Language and Literature[M].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21:31.
[21]A LBRIGHT E M. Dramatic Publication in England,1580 1640:A Reply[J].Review of English Studies,1928(4):201.
[22]WRIGHT C E. Anglo-Saxon Scholars and Literature[J].Gentleman’s Magazine,1834(9):259.
[23]KELLNER L.Review of Kellner[M]//Restoring Shakespeare:A Critical Analysis of the Misreadings in Shakespeare’s Works.New York:Biblo and Tannen Publishers,1969:476-477.
[24]MCKERROW R B.Review of Pollard ed.Shakespeare’s Hand in the Play of Sir Thomas More[J].Library,1923(4):239.
[25]GREG W W.The Present Position of Bibliography[J].Library,1930(3):251.
[26]GREG W W. Review of Fredson Bowers,“On Editing Shakespeare”[J].Shakespeare Quarterly,1956(7):101.
[27]FEBVRE L,MARTIN H J. L’Apparition du Livre[M]//The Coming of the Book:The Impact of Printing,1450 1800.GERARD D,trans.London:NLB (National Library Board),1976:261.
[28]DARNTON R. The Case for Books:Past,Present,and Future[M].New York:Perseus Books Group,2009.
[29]MCKERROW R.An Introduction to Bibliography for Literary Students[M].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28:5.
[30]Review of W. W. Greg:Principles of Emendation in Shakespeare[J].Life and Letters,1928(I):526.
[31]DARNTON R. The Heresies of Bibliography[J].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2003,50(9):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