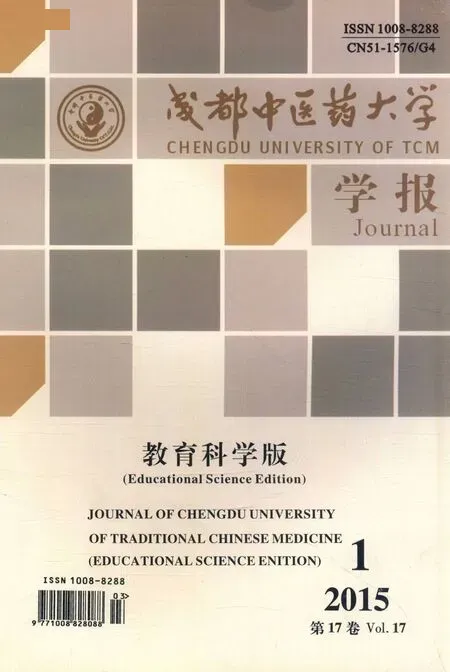医疗暴力背景下对医学生职业价值观教育的反思
2015-02-21张喜彬
张喜彬
(辽宁中医药大学社会科学部,辽宁 沈阳 100847)
一、医疗暴力现象的消极影响
医疗暴力,是指在医疗活动中发生的,由于患者及其家属对医疗行为或医疗效果不满意而对医护人员实施的语言侮辱、人身攻击或对医院财产进行恶意破坏的行为。据卫生部统计资料显示[1],2006年全国医疗暴力事件共发生10248件,到2010年陡增至17243件。医疗暴力现象在全国范围内呈现出逐年扩大的趋势,加上媒体缺乏客观公允的报道,使得“白衣天使”被妖魔化。2013年10月25日,温岭杀医案1死2伤的悲惨结局更是把医患关系再次推到风口浪尖。
近年来频频爆发的医疗暴力事件无疑会对医学生的职业价值观产生重大的影响。职业价值观是指价值观在职业选择上的集中表现,职业价值观教育的目的是提高从业人员的理性思维,培养从业人员正确的职业价值观念、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然而,国内高校对于大学生的职业生涯教育严重滞后。据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儿童研究所所长孙宏艳介绍[2],中国高中生的职业生涯教育已全面落后于美国和日本。职业生涯教育虽然在我国已经发展了十几年,但是仍然停留在建议和倡导阶段。近几年普通高校才刚刚开设职业生涯规划的课程,作为医学院校的大学生更是欠缺有关职业生涯的教育。因此,医学生对于职业的陌生感和困惑感都是制约其职业发展的重要屏障。
医疗暴力现象充分表明医生在当今社会已经是一个高危职业。当职业安全都成为一个严重的问题时,作为医学院校的大学生其职业价值观难免不受此影响。职业安全问题甚至变成了一些学生选择逃避学业和职业的理由和借口。一方面,高校毕业生“就业难”的大环境给医学生毕业的职业选择带来挑战。医学院校本科生毕业进入高层次医院工作的几率越来越小已是业内一个不争的事实,社会环境客观要求医学生的学历必须有一个提升。因此,从本科生到研究生学习的压力陡增,使得医学生对未来职业既充满了期待又多了一些无奈。另一方面,医疗工作本身的风险性也已成为影响医学生职业价值观良性发展的重要因素。救死扶伤的确是医生的天职,但是医学不是万能的。在现阶段,医学技术的发展并不能治愈所有的疾病。然而,在患者看来,当疾病得不到治愈,生命得不到挽救的时候,一切责任都归咎于医生的失职。这显然是不符合逻辑的。患者一旦认为权利受到侵害,轻者在医院闹事、辱骂、指责,重者则对医务工作者拳脚相向,甚至殴打致死。医疗暴力的发生不仅给医务人员造成身体和心理的巨大创伤,更为严重的是可能使即将从事医学事业的医学生对其职业价值产生怀疑。
二、医学生职业价值观教育的两个维度
医疗暴力现象固然有医疗制度不完善方面的原因,但就医学生职业教育而言,应着重强化医学生职业价值观教育的两个维度,即工具理性维度和价值理性维度。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思想是由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马克斯·韦伯提出的。二者在“应然”状态上相互依存,但是在“实然”状态下却有着明显的区别。
工具理性,又叫技术理性,是指一种以科学技术为核心的思维方式,也可称为绝对的理性主义[3]。工具理性的特征是关注手段的适用性和有效性,即追求最佳方案和最佳手段。因此,对于医学生而言,实现职业理想的先决条件就是最大程度地掌握医学技术。掌握的医学技术越高超,职业平台就会越好,职业发展也会越好。然而,工具理性的过度膨胀导致人的物化和价值理性的失落[4]。工具理性主张效用至上,这就使得人们把功利性的目的和实用性的效果当作衡量社会行为合理性和工作成就的唯一标准。工具理性的遮蔽使得价值理性缺失,进而导致终极关怀的缺乏、理想的缺位,甚至道德的沦丧。韦伯用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冲突和悖论揭示了资本主义出现危机的根源,可是今天社会的医疗暴力现象何尝不是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矛盾冲突酿成的恶果。因为,医学绝不仅仅是一项技术,“医学即人学,医学是科学性与人文性相结合的科学,人文、人道是医学的基本特征。”[5]
“医者,生人之术”,如何“使人生”,不仅需要医学技术,更主要的是用仁爱之情灌注于患者的救治上,所谓“医乃仁术”,“仁爱”应成为医德的“元德”,也就是“仁爱”应是医学职业精神的轴心,这也是医学本身的性质和特点决定的。[6]这就需要价值理性思维。所谓价值理性,其实质是人的生命理性,它涵盖了人自身发展过程中的道德、理想和情感等因素。相对于工具理性而言,人的价值理性的特征是关注合理性和终极关怀性。正如康德在《实践理性批判》中所说,“在整个宇宙中,人所希冀和所能控制的一切东西都能够单纯用作手段;只有人类,以及一切有理性的被造物,才是一个自在的目的。”[7]医学生的职业价值观教育应区别于其他专业,突出对生命的终极关切,这样才能更加有的放矢。然而,在现阶段的医学教育中,重技术轻职业精神的做法普遍存在。这对于医学生而言势必是一种致命性的误导,一味地重视医学技术,势必导致医疗实践中的过度医疗、伤害性医疗和防御性医疗。诚然,医学职业需要医学生掌握过硬的医学技术知识,但是更为重要的是培养医学生体认“关怀生命”的医学本性,这正如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所言,“全部教育的关键在于选择完美的教育内容和尽可能使学生之思不误入歧途,而是导向事物的本源”[8]。
在医学生职业价值观教育中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不应被割裂,而应该走向融合。工具理性是基础,而价值理性是方向。没有过硬的医学技术,医学生的职业理想是不可能实现的;没有悬壶济世的终极关切,医学生的职业发展势必误入歧途。因此,只有将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思维相融合,才能保证人的全面发展,避免走向异化。在马克思的视野中,“人类的异化”首先就是“劳动的异化”,“在资本主义的条件下,劳动对于工人来说成为了外在的东西,也就是说,不属于他的本质的东西。工人在自己的生活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不是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个人力量和个人意志,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折磨,精神遭受摧残。劳动不是满足生活本身的需要,而只是满足生活以外的需要(获取金钱)的一种手段。”[9]医学是一个悬壶济世的伟大事业,而绝不应该沦为赚钱的简单工具。
三、医学生社会责任感的重塑
医疗暴力背后隐藏着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博弈。而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凡是可以量化的东西必定可以用货币获取,于是工具理性在这场博弈中大获全胜。由于政府对卫生投入不足,医院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已经成为自负盈亏的经济实体,其自身运营成本和发展建设费用最主要来源自医疗服务创收。因此,在利益的驱使下医院逐渐背离了公益性,医务人员利己主义膨胀而社会责任感淡化。
医疗暴力现象反映的是当下医患关系的剑拔弩张。患方普遍认为负担了昂贵的医疗费用就应当“被治愈”,医院一旦治愈不好,就应当进行赔偿。这样的逻辑看似顺理成章,但是健康本身并不能作为商品随意被购买。一些医院的过度治疗、伤害性治疗也的的确确客观存在,究其原因不过是为了经济效益。就这样医患关系逐渐被商品交换的金钱关系所替代,医患关系陷入恶性循环。当患者付出了金钱却交换不到“商品”时,他们往往会争取社会舆论的关注和政府部门的重视,维护他们认为应得的权益。一旦维权无门,无助压抑的情绪便爆发出愤怒的火焰,企图和医务人员一起同归于尽。价值理性的凋零导致整个医学行业技术至上、金钱至上,责任感和温情变得一文不值。最终导致医患冲突不断,医疗暴力愈演愈烈。
工具理性把人际关系量化为金钱关系,这种思维是诱发医疗暴力的毒瘤。因为它不可避免地漠视了人的情感和精神价值,这已经背离了医学是对于生命的关切这一本性。医方把患方当成经济创收的“工具”,而患方把医方当作治病救命的“工具”。这就不可避免地走向功利主义,医患双方为了各自的目的而变成“工具”,失去了应有的自由和尊严。而康德则认为,“每个有理性的东西都必须服从这样的规律,不论是谁在任何时候都不应该把自己和他人仅仅当做工具,而应该永远看作自身就是目的。”[10]所以,在康德看来,只有到达“目的王国”,才能够真正凸显主体的自由本性和价值尊严,才能够完成利益主体向价值主体的转换。因此,价值理性需要回归,这是对医学生职业价值观教育的关键。
工具理性的统治地位注定了人们沦为“物”的奴隶。或许,最坏的历史情况并非是工人阶级受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剥削与奴役,而是工具理性把满足人的需求当作是第一要务并且凌驾于文化理性之上推崇庸俗的经济决定论。[11]如果医生把患者仅仅当作“工具”,那么医学的神圣性崇高性也就荡然无存了。失去了患者的信任,医生的尊严亦会随之消失。孙思邈在《大医精诚》上说,“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妍媸,怨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亦不得瞻前顾后,自虑吉凶,护惜身命。见彼苦恼,若己有之,深心凄怆,勿避崄巇、昼夜、寒暑、饥渴、疲劳,一心赴救,无作功夫形迹之心。如此可为苍生大医,反此则是含灵巨贼。”作为医学生必须谨记医学对生命的关切,这是医学职业价值观的核心。
社会责任感的重塑是弥合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重要环节。在医疗实践中,工具理性解决的是“如何做”的问题,这属于技术范畴;而价值理性解决的是“该不该做”的问题,这属于精神价值范畴。两者同样重要,缺一不可。对医学生而言,工具理性是一个技术问题,掌握精湛的医学技术知识是从事医学职业的前提条件;价值理性是一个伦理问题,确保医疗技术合情合理公平正义是从事医学职业的重要保障。没有价值理性的考虑,医疗实践注定走向冷漠无情,从业人员在创造财富的同时也沦为挣钱的“工具”,甚至还会付出遭遇医疗暴力的代价。因此,在医学生职业价值观的教育中,积极培育和践行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使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相融合,是克服医疗暴力消极影响的重要途径。
[1] 欧阳晨雨.医疗暴力面面观[J].政府法制,2014(4):6~9.
[2] 向楠.职业生涯教育应该成为中国学生的必修课[N].中国青年报,2013-3-28(07).
[3] 王炳楠.实践理性论[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152~155.
[4] 王彩云,等.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及其方法论意义[J].济南大学学报(社科版),2014(2):48~53.
[5] 王小玲,等.医学人文学概论[M].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2:2.
[6] 储全根,等.论医学职业精神及其在当下医学生教育中的塑成[J].中医教育,2014(2):11 ~14.
[7] 康德.实践理性批判[M].广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79~80.
[8] 雅斯贝尔斯.什么是教育[M].上海:三联书店,1991:4.
[9]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43~44.
[10] 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原理[M].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53.
[11] 刘磊,等.论工具理性对道德力的侵蚀[J].中北大学学报(社科版),2008(2):80~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