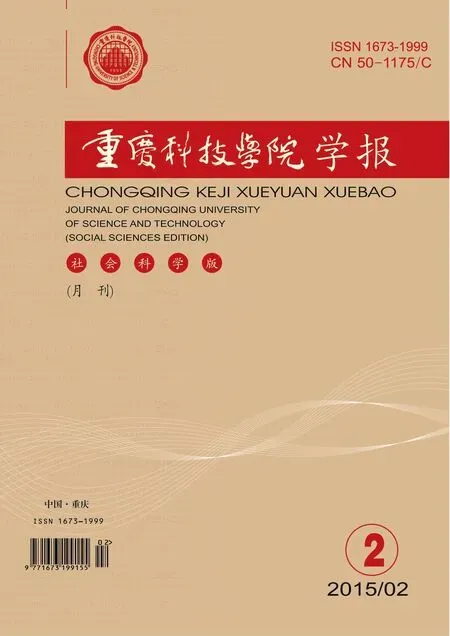从厦航“黑名单”案看民事关系的合宪控制
2015-02-21李晓萍
李晓萍
2008年曾经被厦门航空公司列入“黑名单”的范后军,状告厦门航空公司侵犯其人格尊严权和名誉权。法院一审判决认定,厦门航空公司的一系列行为不构成对范后军人格权的侵犯,驳回了范后军的全部诉讼请求[1]。民法学界对此案颇为关注。一些法律专家认为,厦航自行拟定“黑名单”,于法无据,侵权显然;法院的判决,扼杀了范后军主张人格尊严、主张平等、主张自由的正当诉求。于是,又引出了如何通过对民法概括条款的解释实现民事关系的合宪控制的议题。
近年来,民事领域频频出现“激活宪法”的案件,民事诉讼中的原告动辄以宪法平等权、人格尊严权被侵犯而提起诉讼,民事法官已经不能回避对宪法基本权的考量。
一、民事关系与宪法基本权的私法效力
传统理论认为,民法调整私人之间的水平关系,宪法调整国家与公民之间的垂直关系,两者间泾渭分明,井水不犯河水。随着时代的发展,基本权的侵害源头已不限于国家,拥有优势地位的企业团体可能以压倒性的实力妨碍他人基本权的实现。在这种特定情形下,民法的地位平等、意志自由的基本预设已不复存在。随着“福利国家”“社会国家”的兴起,民法的社会功能不断被扩大,“宪法归宪法,民法归民法”的观念已有修正之必要。“民法理论试图在自身内部来回应新的社会情势对民法规范提出的挑战的时候,为获得价值共识的支撑,往往诉诸于宪法上的价值判断来对民法上的一般条款进行价值补充。”[2]某些私法上的主体,因为其所拥有的实力和资源,可以对其他私人产生实际上的强制力,从而妨害他人的基本权利的实现。这为宪法基本权的效力扩至民事关系领域,提供了现实基础。
关于涉及宪法基本权的私法效力问题,大致有三种主张[3]:(1)直接效力说。认为宪法是最高规范,不论在公法领域还是私法领域均可直接适用。因此,民事主体可以直接援引宪法对其他私人行使请求权,宪法可以作为民事案件的诉讼标的。(2)间接效力说。认为基本权的保障仍属于对公权力主张的权利,但私人间的权利侵害亦有通过私法“概括条款”予以救济的情形,如涉及违反公共秩序、善良风俗等情况时。此时并非由于“私人行为违反宪法”,而是基于该私人行为显然与宪法基本权保障的意旨相违背,通过私法一般条款规定,间接适用宪法。(3)无效力说。认为宪法的基本权保障是为限制国家公权力所设,私人间的权利侵害应交由法律解决。
历史地看,宪法的出现确实是为了对抗来自国家的侵害,私人是宪法保护对象而非拘束对象。但是,面对社会上层出不穷的私人侵害,民事法院还不能意识到基本权保护义务的功能和合宪性解释原则的运用,那么其中的问题恐怕就不只是“落伍”而已了[4]。
二、宪法基本权私法效力的展开
(一)宪法基本权私法效力的规范宣示
我国《宪法》的“序言”规定:“全国各族人民、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并且负有维护宪法尊严、保证宪法实施的职责。”在“总纲”和其他部分中也采用了“禁止任何组织或个人”,规范的对象直指社会组织和公民个人。因此,有学者认为宪法可直接适用于私人关系,在司法中应理直气壮地适用宪法。笔者认为,从宪法上的宣示并不能当然地推导出私人之间的基本权请求权。在我国法院直接适用宪法,还存在着难以逾越的制度障碍。
(二)法院直接适用宪法的制度障碍
我国宪法的实施有赖于立法机关将抽象的宪法基本权转化或解释为具体的法律权利。司法机关和法官通过将具体的法律适用到案件中,是间接适用宪法。如果承认宪法可以在司法中直接适用,则必然会导致司法对法律的违宪审查。由此可能出现“假普通诉讼之名,行宪法诉讼之实”的情形,从而出现法院与全国人大常委会“篡夺释宪权”的违宪嫌疑。宪法赋予全国人大常委会的那种解释权,是一个“排他性的专属解释权”。我国宪法中直接针对个人的条款虽然很多,但“这反映出中国立宪理念上的误区,把宪法中保护公民权利的条款大量用于对抗公民个人,这是对宪法的误用”[5]。
(三)法院对宪法基本权的保护义务
宪法基本权私人效力的“直接效力说”,在我国已无运作可能。当然,“直接效力说”与“间接效力说”对于宪法规范对象是公权力这一点均无疑议,包括立法、行政、司法在内的国家机关,负有保护公民基本权的义务。同时,基本权利亦是一种“价值体系”或“价值标准”,是国家公权力追求的目标。从基本权利中萃取出客观价值判断并投射至所有法律领域,是所有公权力机关行使职权时应遵循的准绳。法院作为国家公权力之分支,也是宪法基本权的直接约束对象,对宪法基本权保障负有保护义务。这要求法院在做出司法裁判以及采取强制执行措施时,必须对基本权利予以尊重。就民事法官而言,鉴于基本权作为法律秩序的价值规范与解释原理,可以透过对民法概括条款或者开放的法律概念等转介条款的解释于个案中实现基本权的价值判断,间接达成宪法所揭示的基本权保障目的。
因此,笔者认为宪法基本权在我国法构造上存在二元论:司法机关在尊重立法专属的释宪权的前提下,对基本权有直接的保护义务;基本权对作为司法行为对象的私人主体,则只有间接效力。换言之,宪法基本权对私人关系的影响是一种“事实上”的效力而非法律上的效力,民事关系的基本权保障及合宪控制是国家机关(法院)的义务,私人对此只享有宪法基本权规定适用在国家机关上的“反射利益”。
三、合宪性解释与民事关系合宪控制的操作
民事概括条款的存在为宪法价值导入民事关系提供了技术上的可行性,但民事关系的合宪控制对于法院来说无疑是“带着脚镣跳舞”。法院的义务在于:既要在依法审判的架构下满足司法行为对基本权的保护义务,又不能逾越对基本权的尊重义务。
(一)合宪性解释之运用
合宪性解释是法律解释的一种。我国的法院没有违宪审查权。但是,“在基于普通法律个案的法律解释和法律三段论思维中,合宪性解释应该是法官作为公权力主体承担宪法义务的基本方式”[6]。
一般认为,合宪性解释包含合宪性的考虑和宪法取向的考虑[7]。也就是说,规范存在多种解释的可能性时,司法者不应采取违宪结果的解释方式;司法者应采取最能实现宪法基本权要求的解释方式。在我国现行宪法框架下,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集立法权、宪法监督权于一身,法律尤其是宪法性法律本身包含对宪法内涵的界定,它对于法院具有硬性的约束力。因此,法院的“合宪性解释”不仅要参照宪法条文,还需要参照法律尤其是宪法性法律,尊重立法对宪法具体化的优先权。就考虑 “宪法取向”而言,则要求法官在处理民事案件时将对宪法基本权的保障纳入概括条款考量,将基本权价值和存在于概括条款的社会价值做一番“调和”,经过基本权的投射,形成民事行为的新界限,从而对诸如合同的有效性、是否构成侵权行为责任等情形进行认定。
(二)法律权利冲突背后的基本权冲突与利益衡量
在我国法规范结构上,基本权利所规范的事项与法律权利所规范的事项是高度重合的,解决冲突应首先适用具体的普通法律。这时基本权利处于静态,无须上升至基本权利规范层次[8]。如果法院认为法律符合基本权规范的要求,权利冲突自然在普通法律领域就可以得到解决。但是在有些情形下,冲突的解决需要依据宪法的规定来考量。法官在解释和适用民事概括条款填补法律漏洞时,根据合宪性解释的原则,具有考虑基本权利的义务。如果不履行该义务,就可能造成对私人基本权的保护不足。具体个案中的“法益衡量”,按照德国著名法学家卡尔·拉伦茨的说法,应该根据有关法益的“重要性”来进行“权利”或法益的“衡量”[9]。同时,考虑到民事领域毕竟不是基本权的主战场,基本权跟民法概括条款的调和必须保持合理的限度。比例原则的运用尤其在关涉意思自治的合同关系中,应根据当事人之间地位的平等性和意思自治之干预性因素等,形成宽严相济的审查密度。
四、厦航“黑名单”案的合宪性分析
在厦航“黑名单”案中,范后军在“调解意见书”中承诺了 “今后自愿在有子女前放弃选择乘坐厦门航空公司航班的权利”,而从意见书的形成过程来看,法院认为,难以看出达成该调解意见书非基于双方的真实意愿,因此在厦航确认范后军女儿出生的事实前的拒载,未侵犯其人格尊严权。至于此后的拒载,法院认为,公共航空运输企业如果认为旅客的运输要求可能构成对航空安全的影响,有权基于合理的判断拒绝承运,而厦航的判断具有一定合理性。
对于在确认范后军女儿出生的事实前的拒载,可以从契约自由与基本权(此处指出行自由权)限制角度来考量其合法性。我国《合同法》规定了从事公共运输的承运人不得拒绝旅客、托运人通常、合理的运输要求。鉴于从事公共运输的承运人的优势地位,上述规定被视为是承运人的强制缔约责任。可见,相比承运人订立合同的自由而言,法律对旅客的出行自由赋予了更高的位阶效力。由于双方地位不对等,这里就应采取严格的比例原则来审查。
“调解意见书”的签订是双方为了解决劳动纠纷,即使范后军是“自愿”的,从必要性而言,厦航在有其他手段确保飞行安全的情况下,要求范后军在有子女之前放弃选择乘坐厦航航班的权利,也难以通过“最小侵害原则”检验。要求范后军离开福州,在有子女之前放弃选择乘坐厦航航班的权利,这样即便能达到确保飞行安全的目的,手段亦过于沉重。可以通过对民法“禁止权利滥用”原则的解释,认定“放弃选择乘坐厦航航班的权利”的协定为无效约定。
对范后军女儿出生后厦航的拒载行为,法院是从“公共安全”的角度加以权衡。我国《航空法》规定:“公共航空运输企业应当以保证飞行安全和航班正常,提供良好服务为准则。”“公共航空运输企业不得运输拒绝接受安全检查的旅客。”航空公司为了确保飞行安全可以采取一定的安全限制措施,拒载拒绝安检的旅客。按前述“法益衡量”原则,公共安全较个人自由有较高之位阶,个人自由在一定情况下应该受到限制。实践中,关键在于如何准确判断本应受到保护的个人自由是否会影响公共安全。在本案中,如果原告“可能存在安全危险”只是厦航的主观怀疑或猜测,那厦航就违反了“最小侵害原则”,构成对范后军出行自由的侵害。
五、结语
近年来,拒载事件常见于媒体,航空公司如何规范行使拒载权的问题亦成为舆论焦点之一。公众已经察觉到,航空公司动辄以保障安全为由下 “逐客令”的行为是对自身乘机权益的侵害。法院在尊重航空公司采取安全限制措施的同时,有义务考量基本权保障,以满足公众防止航空公司滥用职权的期待。民事法官应该牢记宪法赋予公民的基本权利,通过合宪性解释、利益衡量,在个案裁决中保护宪法赋予公民的基本权利,从而间接达成宪法所揭示的基本权保障目的。
[1]王丽英.厦航“黑名单”案原告败诉,法院发司法建议[EB/OL].(2009-11-10).http://www.chinacourt.org/article/detail/2009/11/id/381288.shtml.
[2]薛军.“民法-宪法”关系的演变与民法的转型[J].中国法学,2010(1).
[3]初宿正典.人权保障理论之新展开[J].萧淑芬,译.月旦法学,2006(6).
[4]王耀霆.私法关系的合宪控制:间接影响说的再构成[D].台北:国立政治大学法律学研究所硕士论文,2008:21.
[5]蔡定剑.中国宪法实施的私法化之路[J].中国社会科学,2004(2).
[6]张翔.两种宪法案件:从合宪性解释看宪法对司法的可能影响[J].中国法学,2008(3).
[7]林更盛.法学方法在劳动法上的可能运用[J].东海大学法学研究,2005(23).
[8]徐振东.基本权利冲突认识的几个误区[J].法商研究,2007(6).
[9]卡尔·拉伦茨.法学方法论[M].陈爱娥,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2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