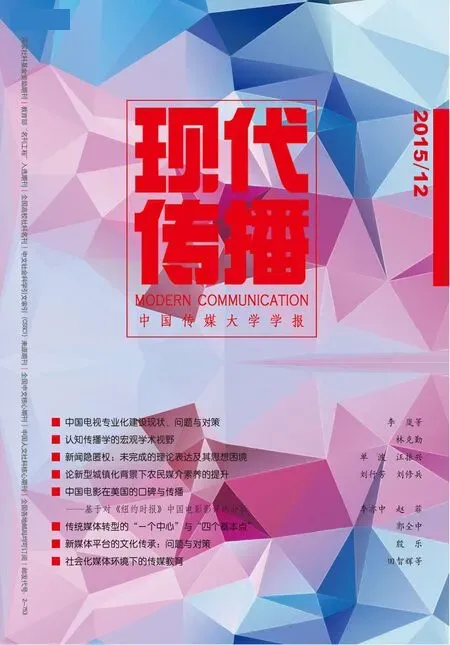中日动漫产业发展环境比较研究
2015-02-20李海丽
■ 李海丽 姜 滨
中日动漫产业发展环境比较研究
■ 李海丽姜 滨
改革开放后,因政治关系的缓和与文化的同源性,中国动漫在艺术表现上最直接的借鉴对象是邻国日本,且广泛表现在题材、风格、内容等诸多分野。而产业运营上,因手冢治虫在上世纪60年代创造的以电视动画为主的产业运营模式在70年代渐趋成熟,更给当时刚起步的中国动漫产业以关键性的影响。数十年来,中日动漫产业虽然在各自不同的环境中呈现出不同的发展轨迹,但从形式上来看,中国动漫尚未完全摆脱模仿的尴尬。作为文化载体,中国动漫应辨识不同环境中所秉承的文化思路,形成具有明确自身特色的发展风格。
一、本土特质形成不同的文化环境
国际政治格局改变、现代科技的发展以及本土政治环境的更迭使中日两国产生了不同的文化环境,传统、现代文化以及本土与外来文化在这一期间的相互博弈与相互渗透也直接影响着文化创意产业的运营取向与发展定位。
中日两国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之间的关系嬗变,最为关键的时期均是二战以后的三十年间。二战后,美国统治日本,为防止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大力打压日本以武士道为代表的传统文化思想,强力灌输西方的现代文化存在形态。进入50年代后期,日本经济获得了飞跃性的发展,在物质日渐富足的背后,美国在文化、思想、道德观等方面直接、强制性的影响,以及因败战而产生的自卑心理使大部分日本民众无条件地视西方文化为先进文化。西化的结果,是道德生活、伦理意识的崩坏、价值规范的错位、传统人间关系的荒废等社会现象的出现。①另一方面,在这样的环境背景中,艺术创作者们的本土文化归属意识开始被强烈唤醒。以手冢治虫为代表的动漫作家将民族文化意识融入到作品表现中,看似西方痕迹明显的现代、未来生活情境的设定中,包含的是日本传统文化中的道德观、价值观与审美意识。表现在产业模式上,虽借鉴美国的产业链理念,却与美国不同,走出了以漫画试水市场,通过电视形成规模性、持续性的长期传播态势,穿插以电影形成的品牌提升“三者合一”的日本动漫产业运营模式。
二战后结束内战、新中国建国伊始的三十年,对中国而言却是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正面冲突的时期。封闭式政治局限的环境,文化冲突被导引到了本土的传统与现代的内部层面上。上世纪60年代,文革前,是中国动漫最为荣光的阶段,题材、形象及艺术手法均有明确的本土化归属意识,也奠定了中国动漫的风格基础。
1979年改革开放政策实行,随着思想的解放,本土文化开始迎接新的发展契机。模仿与借鉴成为了一时的盛行风气,而动画加工大潮更是清洗了中国曾经完整独立的动画语言与制作体系。1983年在尝试复归传统文化形式之作《天书奇谭》的默默无闻后,中国动漫制作明显地剥离了传统文化所代表的过去,聚焦于代表着先进的外来文化载体。最为集中的表现之作是1999年的《宝莲灯》,虽然在题材上代表着传统,但其制作过程、发行方式等无一不在商业模式、技术手段上显出“文化经济”的外来特征,且两者尚未以兼容的态势完成融合与统一。反而其矛盾性致使中国动画陷入了题材自卑的“失语”泥沼,从“用别人的话讲自己的故事”迅速转移到了“用别人的话讲别人故事”的创作误区。“从本土性的表象脱蜕到意识残缺,中国动漫就在这种渐渐失去自我的过程中开始失去了本色性特征。”②
二、人才培养机制迥异造成不同的人才发展环境
是要“加工者”还是要“创作者”,这一培养目的在不同的领域大略都会指向后者,但在现实中,不同状况会导引出不同的结果。中日动漫人才的培养状况,也同样存在着这两种目的的对立与共生。
中国动漫最应该审视自身培养理念存在的问题。大学、职业院校、公司的分层次培养,是日本数十年来一直践行的培养理念并已成熟地体系化。职业院校培养技师型人才、大学培养创造型人才、公司培养综合性人才,三者形成了各自的培养目标并且具有完全的独立性,业界与学校的接轨也仅限于考察、交流学习和有限制地合作。因学生在专业知识不扎实的情况下过早涉身业界,会使学生学习的方向发生转移,容易滋养浮躁求成的学习态度,不利于专业文化素养、专业创造能力的形成与提高。因而,日本学校虽也存在“产学研”三合一的机构设置,但重在让学生试炼能力而非利益攫取。这种清晰的分层次、定位培养不混淆目的的体系在日本已经承续数十年未变。
而中国动漫人才培养起步较晚,且培养部门在产品出现大量需求缺口的前提下在近年呈几何数字“暴涨”,实则并未达到相应的师资、设备等培养水平:2000年初中国具有动漫学科的4年制大学不过数所;2004年以后激增;截至2009年开设动漫专业的本专科院校1279所。大多数新增设的动漫学科是原来美术学科新挂的看板,教师也大多为原来的美术教师,真正具有动漫制作经验的教师少之又少。因而,中国动漫专业学生一般具有美术基础强及3DCG软件操作能力佳(因无专业教师,使用3DCG自动生成软件来制作作品能力逐渐增强)的特征,却严重缺乏剧本写作、角色设计等创作能力,更莫论产业必需的制片人、制作进行管理者的专向能力。“日本的制作外注流向中国,结果,中国动漫制作人才大量流向相关企业,且只承接海外企业如规定动画稿件加工等片面制作任务。使中国动漫教育呈现出整体制作乃至于创作型人才缺失的状况。”③而这样的“危害”是显而易见的。
其次就培养方式而言,日本注重自“原始”而来的过程培养与整体培养,而中国注重自“现代”而生成的技术培养。“原点”开始的教育理念,始终贯彻日本动漫创造型人才培养的全过程。大学教学前半期以动漫的基础美术表现、创造能力训练为主,制作技术以“逐格拍摄”的手绘二维动画为核心进行,后半期则开始进行“分流-合作”训练,即脚本创作、角色设计、作曲和剪辑等各种动漫人才的专向培养,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进行团队合作训练。而专门培养技师型人才的职业院校则从制作载体角度加大培养力度,分类电脑软件使用程度明显加强,并时刻注意本行业先进技术的更迭状况,主要是培养能够在某个专向上表现合格的技术工人。
中国在动漫培养上尚未根据培养人才性质的不同而形成明确的动漫人才培养定位,大学、职业院校、基地的培养方式基本无二,最为薄弱的都是在创作能力的培养环节。尽管教育的本意是培养“创作者”,但实际上是“加工者”居多。而由于高端创意人才奇缺,导致我国动漫自主品牌研发能力弱,原创精品匮乏。
三、政策环境的两面
对于中国与日本而言,同样将动漫产业视为文化创意产业的支柱,是国家“软实力”的呈现载体。两国各自纷纷出台各种制作、播出、发行等的扶持政策,以适应产业自身日新月异的发展需求以及获得更多的经济、文化回馈。而如何在中国特色的国情下处理政治、艺术与产业之间的关系,是中国目前的重要课题。
规则与自肃,是政策的两个层次。中日政府对于动漫产业的政策核心点也是围绕这两个层次展开。上世纪50年代,由于动漫内容、题材的无序性,色情、暴力等特质成为日本动漫发行的眼目。意识到其危害的孩子们的自治体和父母们联合发动了面对问题动漫的抵制运动,即有名的“恶书流放”④运动,也正是这次大规模的抗议活动直接催生了日本动漫严格的分级制度。时至今日,日本动漫制作分级意识已成为行业细则,也已经达到了制作者、发行机构自肃的程度。另外,在影视制作公司与电视台以及其他推广媒介之间,还存在着一个定位为“监督与服务”,即协调两方关系的中介性团体,在监督两方利益配给的基础上力争使两方互利互赢,并借此推进整个动漫市场有序化的良性运作。
相比较而言,因国情不同,中国对于动漫制作尚处于规制阶段。完善产业运营机制,创造良好的社会发展环境是促进中国动漫这一文化资本壮大的基本保障。尽管国家出台了很多旨在保护国有动漫的相关政策,但实际上需要的不仅仅是针对播出平台的,更需要的是如何结合国情现状完善或改革现有产播机制,引导内容与题材的健康、平衡发展,并在此基础上形成有利于我国动漫产业形成和发展的环境。对于中国动漫而言,处于何种阶段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制定明朗的行业规则、严格贯彻明晰的行业制度。
日本动漫产业发展至今,从单纯的盈利量产到文化实力的形成,历经数十年,而中国的动漫产业其实还处在初步发展阶段。在这个阶段,文化环境的营造是根本,不论是人才培养还是政策施行都应该以提升文化归属意识的文化导引为主旨。而且,我们必须意识到的是:我们可以暂时成为异文化商品的生产车间,但绝不能成为没有自我思想的机器群;我们可以成为异文化资本的发展媒介,但绝不能成为其成长的温床。而这一切都源自于对本民族文化与传统的传承。
注释:
① [日]俊藤浩滋、山根贞男:《日本电影传记》,讲谈社,东京,1999年版,第67页。
② 姜滨:《中国制造与中国动漫产业》,《声屏世界》,2012年第6期。
③ [日]青崎智行:《创意产业在中国》,翔泳社,东京,第8页。
④ 随着日本各地儿童保护法案的陆续出台,上世纪50年代,日本各地开始以各种青少年保护协会、监护人联合会的名义发起对色情、暴力漫画书的声讨运动:在城市各处设立“恶书追放”白色邮筒,收集大量有问题作品后进行审核并逐一交涉处理。
(作者李海丽系江西师范大学传播学院讲师;姜滨系江西师范大学传播学院副教授)
【责任编辑:张国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