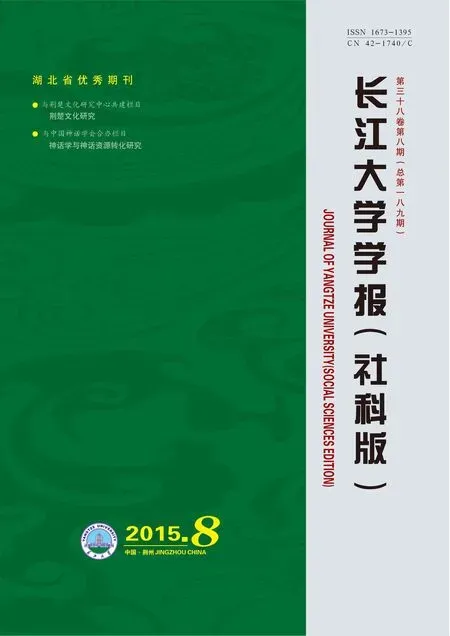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国民公德问题管窥
2015-02-20纪宁
纪宁
(青海师范大学 人文学院,青海 西宁 810000)
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国民公德问题管窥
纪宁
(青海师范大学 人文学院,青海 西宁 810000)
国民公德意识的缺失,是在中国迈入近代社会之后,逐渐引起人们重视的社会问题;也是中西方文化强烈碰撞后,引起人们广泛讨论的学术命题。讨论国民公德意识,不仅可以更好地促进中国近代史研究,亦且将为中国近代史研究者理解西方文化对于我国既有文化模式的冲击,提供全新的观察视角。
国民;公德问题;近代史
中国近代史研究具有超越纯粹学术研究的社会意义和文化价值。它以中国人在近代社会所经受的苦难历史作为研究对象,为我们了解中西方何以在千年的历史进程中走上不同的道路,提供了答案。我们虽然习惯于将1840年爆发的鸦片战争,视为中国近代和古代的切分点,但中国近代史上所发生的一切,却是诸多因素在长期发酵和历史沉淀后的产物。其基因中,既有西方列强的入侵,也有中国文化自身的缺陷和制度的滞后。国民公德意识是我们从西方借鉴过来的概念,其内涵如何界定,以及其与近代史研究的学理依据,是需要我们首先加以厘清的问题。同时,我们必须认识到,作为学术概念的国民公德意识虽然是后发的,但并不意味着我国传统社会中就没有涉及国民公德意识的相关内容。因此,我们还需要从历史中去钩沉相关内容,通过对比,以进一步确证,传统文化中哪些元素与国民公德具有学理层面的对称性。只有解决了前述两个问题,我们才能真正回到国民公德问题在近代史研究中的地位和意义的讨论上来。
一
古人云:“无乎不在谓之道,自其所得之谓德。道者,人之所共由。德者,人之所自得也。”[1](P243)中国传统文化将道视为宇宙的本源,认为道存在于万事万物之中,又渗透到各种事物的发展演变进程中,并使其获得存续发展的终极意义,而事物只有遵从道的内在诉求,才能展现其价值,当此之时,此一事物便具有了德;同样的情况也适用于人。当我们将道视为人类所共同认可的行为准则时,就会进一步意识到,德是维系道之本源和事物自身存在的根本性力量。当人的行为准则能够按照德的准则不断前进,或者说自觉地归摄于德的领属时,道与德就在内在的逻辑构成层面上获得了统一。因此,我们在通常意义上所说的“道德,一方面是指人们一种社会性的行为准则,一方面又是个人的一种心理或内在的品质。道德准则内化为道德品质,道德品质外化为道德准则。换言之,道德,既是社会群体的行为标准,又是个体的心理素质。前者可称为群体道德,即公德。后者可称为个体道德,即私德”[2]。由此可见,所谓公德,涵盖了公民在社交活动和日常生活中,所应遵守的职业道德、公共道德和家庭伦理道德;而所谓私德,则是强调个人的综合素养,即品质和操行。后者即我们在生活中所说的社会公德,亦即独立自主的个体在公共生活中所应遵循的道德准则。学术界近来趋向于将公德概念明晰化,称其为国民公德。国民公德是指具有独立行为能力的个体,在日常生活中需要遵从的道德准则。国民公德渗透于前述公德与私德两个层面之中:一方面,国民公德是全体国民都需要接受的道德准则,并应成为个体在其私生活和社交活动中所应遵从的行为准则;另一方面,国民公德还需要上升至国家意识形态层面,并通过法律、法规和教育的方式加以强化,以使其成为提高全体国民道德素质的制度保障。
在中国伟大的改革开放事业不断深化,且已取得良好的发展成果的前在条件下,在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环境场域中,我国当代国民在思想观念以及道德形态上,仍部分地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复杂性。[3]由是言之,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无法规避有关国民公德转型和塑造问题的相关讨论。它始终是当代中国社会在走向现代化国家的历史进程中,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问题。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核心命题之一,便是探讨中国社会是如何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这一命题,既关涉到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诸多层面,也与民众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我国传统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是以儒家文化为核心所构建的道德体系,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伦理秩序,深刻影响并渗透于传统社会的各个领域;但传统社会的道德观念与现代社会所提倡的道德评价标准之间,存在着不相一致的地方。其差异,不仅引发了我们对传统文化的反思,也对我们理解中国人的日常行为方式,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因此,基于中国近代史视角开展国民公德问题研究,就显得十分迫切而必要,因为这一研究,能使我们充分了解中国近代社会是如何新陈代谢的,并在中西方文化的碰撞中,不断地加深其反思。
二
鸦片战争爆发后,中国社会旋即被抛入世界历史的漩涡之中。上至帝王将相,下至黎民百姓,人们的思想观念,经受着前所未有的冲击。一方面,封建帝王的政治制度依旧延续着,并以政治的强制力和科举制度等形式,持续地发挥其影响力。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开始放眼看世界,其认识世界的方式,正在悄然地发生着变化。在这一过程中,中国传统社会文化语境的变迁,使得其既有的文化模式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冲击;随之而来的,则是人们有关日常生活伦理秩序、行为准则和评价标准的改变。
作为现代社会重要表征之一的国民公德意识,正是在这一时期开始逐渐萌芽,并逐渐受到中国人关注的。在中国近代,最早从事中国国民整体公徳水平与西方人之实际公共道德水平比较分析的著名学者是郭嵩焘。郭嵩焘认为,西方人在其具体的社会实践生活的开展过程中,不仅与中国儒家一样,具有比较明显的仁爱道德取向,而且西方人所讲求的博爱思想,比中国儒家所讲求的爱有差等,具有更为广泛的普世意义;中国人所言的义,往往具有更多的道德层面的虚化成分,因而近代中国人在实际生活畛域中,重义轻利者往往比较少见,而见利忘义者则比比皆是,与之相反,西方人则大抵重利而不轻义,而这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出了中西方不同的道德分野。[4]郭嵩焘认为,中国国民沿袭自封建王朝时期的礼制,以及根深蒂固的国民等级制度,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不同等级的国民个体之间的正常人际交往,引致了中国封建社会在信息渠道层面的高度封闭;相较而言,西方国家的国民之间的社会人际交往,则带有更多的开放宽松的人际氛围特征,因而其彼此之间的人际关系,也就显得更加融洽和谐。[5]郭嵩焘所列举的如上事实,至少能够说明,在社会公德执行力层面,近代中国国民是比不上同一时期的西方公民的。郭嵩焘是通过实际的社会实践调查活动而最终得到上述结论的。他所得出的这一结论,毫无疑问,给当时坚持认为中国的礼仪道德约束与实践水平,远胜于西人之上的迂腐的封建社会的卫道士们,狠狠地当头泼了一盆冷水。
而久负盛名的西方传教士史密斯,则将缺乏基本的社会公德意识,认作当时中国人的一种基本性格。他是基于当时中国人所有的一些具体的国民社会实践行为,来给出上述结论的,如道路损坏却没有人去修理,等等。在他眼中,当时中国的基层民众所关心的,只是如何使自己的切身利益不遭受不必要的外在损失,却往往不会去充分考量,其自身单纯性的社会活动,会导致怎样的社会效应,以及其是否会对社会公共财产以及公共安全,造成一定程度的损害,因此之故,马车夫和肩扛夫会在人车奔行的道路中间随意装卸货物,农夫则将树木任意横倒在道路上,屠夫、理发匠、小商贩、木匠、泥水匠、修理工以及其他数目不清的工匠则肆意混迹于大街小巷之中,妇女将被褥晾晒在街衢两侧,布匹染色工将工作成果晾晒在窗棂上,面馆师傅将面条随意地晾晒在街道两旁。[6]凡此种种,不一而足。由此,史密斯进一步指出,当时的中国人相对地比较缺乏诚信的道德品性。与此同时,为了使自己的观点论述更具有一般性意义层次上的可信性和说服力,史密斯还有针对性地引述了一些中国历代流传的历史文献典籍,并对其中的有关文本表述,做出了基于历史视角的分析阐释。
三
中国国民公德意识,是随着中国社会从传统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过渡期间发展起来的,具有明显而强烈的前现代特征,并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和制约。自中国近代历史时期开端以来,国内主要从事历史研究的学者和思想领袖们,不仅清晰而详尽地揭示了中国公民缺失社会公德意识的种种表现,而且还系统完备地揭示了中国近代缺乏社会公德意识的原因。近代学人对这一问题所持有的有代表性的分析,大抵将其归结为封建专制统治严酷摧残的结果。
近代思想家严复指出:西方国家的公民之所以拥有比较充分的社会公共道德意识,就在于西方国家的公民个体往往都拥有比较充分的自由和平等之政治权力,而中国人之缺乏基本的社会公德之心的主要缘由,就在于其饱受封建专制统治制度的统治与控制之苦;拥有充分的自由与平等权利的西方国家公民,往往不能将社会公共性的管理实务视作自有性的事务,而相较之下,中国古代的历朝封建统治者,则往往将国民视作没有任何人权的奴隶,他们不但不鼓励国民关照国家有关的社会政治与综合性事务的发展走向,甚至还会想方设法地阻碍国民获得关照国事前进之走向的机会与可能性。[7]严复认为,这样的现实境况,养成了中国历代国民只顾自身切实利益,而不与周旁的外在客观的物质性与环境性现实世界进行有效关联的行为模式。[7]
近代著名思想家、学界文化大儒梁启超曾经指出,数千年民贼(封建时代的国家统治者)以国家为私有财产,为保护其私产,其采用“训”、“舌”、“役”、“监”之术使民愚,遂养成了国民“苟私”、“恶直”、“崇虚”、“耽逸”的品性,此即愚民统治的直接结果之客观体现。梁启超还用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论原理,阐释了近代中国国民社会公共性道德意识与理念缺失原因之所在。梁启超认为,生息于专制政体之中,只有诈伪、卑屈之人才能保全和有所作为,而那些刚直的人则往往被淘汰,由此使得卑诈之种代代相传,恶劣品性根深蒂固。君武先生也曾经谈到,源于中国古典政治统治制度的原在传统沿袭规律,家姓王朝统治者往往将国家视为自己的财产,久而久之,基层国民便往往无法厘清国家与朝廷之相互制约关系,无法厘清国家与国民之相互关系,因此之故,国民倾向于将国家视作皇帝的私有产业,对国家的命运福祉漠不关心,即使国家领土遭受外国侵略者的不法侵占时,他们依然会躺在鼓里睡大觉,悠然自乐。唯此,中国封建统治制度所造成的国民整体性社会公共道德意识的缺失,也就在情理之中了。明白了这一点,对于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国民公德问题,我们便有了一个清晰的认识。
[1]管仲.管子[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3.
[2]魏英敏.关于国民公德建构的思考[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2).
[3]陈永森.中国近现代史上的国民公德问题研究[J].江西社会科学,2002(4).
[4]桑兵.辛亥南北议和与国民会议[J].史学月刊,2015(4).
[5]黄俊华.聚焦学术热点,推动史学创新——“中国近代史研究热点问题与理论前沿学术研讨会”综述[J].史学月刊,2015(4).
[6]赵庆云.略论十七年间的中国近现代历史调查[J].中共党史研究,2014(12).
[7]刘文楠.南京国民政府的国家政权建设——史学界对1932-1937年民国政治史的研究述评[J].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14(6).
责任编辑 韩玺吾 E-mail:shekeban@163.com
On the National Morality in Chinese Modern History Research
JiNing
(HumanitiesCollege,QinghaiNormalUniversity,Xining810000)
The awareness of national ethics is a social problem that has gradually aroused attention in the Chinese society after entering the modern society,and it is also an academic proposition which has caused wide discussion after the strong impact of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As a starting point,it will promote the study of modern history,especially for the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modern times,which provides a new perspective on the impact of western culture.
national;social morality;the modern history
2015-06-16
青海省社会科学规划2010年度项目(10051)
纪宁(1963-),男,河北饶阳人,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史及中国民族史研究。
K25
A
1673-1395 (2015)08-009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