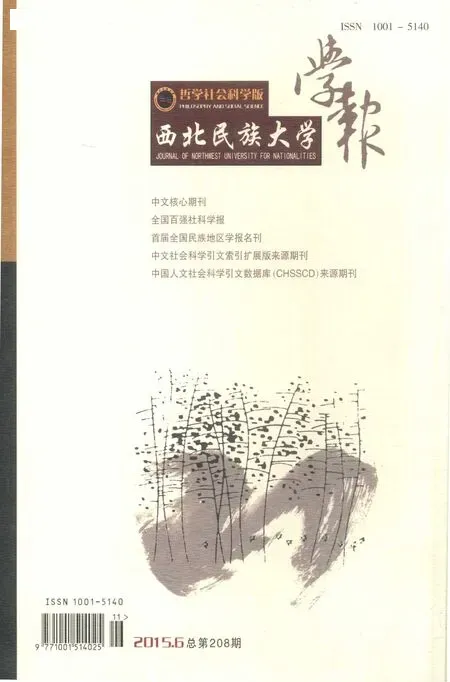元代“以儒饰商”现象探析
2015-02-20张瑞霞葛昊福
张瑞霞,葛昊福
(兰州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甘肃 兰州730000)
受传统重义轻利观念的影响,处于四民之末的商人不仅地位低下,而且常常受歧视。唐代“工商杂类,不得预于士伍”[1]的规定就是商人不受主流社会认同的重要体现。蒙元时期,统治者受儒家文化影响并不深刻,对经商行为持开放态度,对商业和商人采取了保护措施。商人群体扩大,他们的地位也较先前朝代有了一定的提高。彼时,儒学正统地位被颠覆,处于边缘化。儒学的边缘化造成士人仕进困难,但客观上也促使择业多样化,一些儒士为谋生计转而从商。部分商人由于仍受传统观念的影响,则多与士人结交,导致“以儒饰商”现象的出现。关于这一现象,王秀丽曾提及元朝士商亲融①王秀丽《元代江南地区的士商亲融关系》,《历史教学》2004年第5期;《海商与元代东南社会》,《华南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5期等。的关系,但未作深一层的探究,笔者欲在此基础上,就元朝“以儒饰商”出现背景、主要类型以及相关活动和影响作进一步探讨。
一、“以儒饰商”出现的背景
汉族王朝历来实行“重农抑商”政策,商业被视为末业,直到宋朝这种局面才有所改观。时人郑玉道言:“古有四民,曰士,曰农,曰工,曰商……此四者,皆百姓之本业”[2],承认商业的本业地位,这表明一部分士大夫已经意识到商业的重要性,他们对商人的态度也有所转变。元朝统一后,各区域之间的壁垒被打破,相互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这为商业贸易的发展提供了便利。朝廷对商人给予优待和照顾,地方官吏保护商旅安全,“湖广江湖间盗贼出没,剽取商旅货财,哈剌哈孙发兵剿杀,水陆之途始皆无梗”[3],政府法令还规定“商旅所至,官给饮食,遣兵防卫”[4]以及“州郡失盗不获者,以官物偿之。”[5]甚至还享有一些“持玺书,佩虎符,乘驿马”[6]的特权,这些待遇在前朝是无法想象的。受此扶持,一大批商人活跃起来,有些家财至万贯,声名远赫。如吴江巨富沈万山,“富甲天下”[7];四明人夏荣达,原是个赤贫者,经商数年后,“泉余于库,粟余于廪。”[8]
元朝是一个多元文化并存的朝代,儒学从汉以来所确立的独霸地位不复存在,日渐处于边缘化的境地。加之科举时行时废,士人入仕困难,为了谋生他们“或习刀笔以为吏胥,或执仆役以事官僚,或作技巧鬻贩以为工匠商贾”[9],弃文从商便成为他们的一种选择。元朝重商政策的实行和商人物质财富的殷实,为儒士经商提供了一种环境,而儒士境遇的改变则迫使他们中的很多人转入商人行业。
元朝很多文人不再对商人持一种否定蔑视的态度,程钜夫就对河南商人姚仲实颇为认可,认为历史上剧孟、郭解、白圭及猗顿都不如他,“剧孟、郭解辈事甚义而不轨于道,白圭、猗顿术可富而不闻其能散。孰若长者一介之士,名动万乘,声流四方,称于后世。岂不以好义而轨于道,积而能散也欤!乌乎,贤哉!”[10]称赞他既会聚财又能散财。泉州海商朱道山,以宝货往来海上,王彝认为他“务有信义,故凡海内外之为商者,皆推焉以为师。”[11]还有以儒转商的鲍孝子,杨维桢给予他“鲍孝之转化,吾知其仁矣”[12]的赞赏。文人士大夫此时表现出更多的是对商人所从事职业的一种礼赞。杨维桢和他的弟子袁华,不仅否定了商业是末业,“胸蹯万卷不疗饥,孰谓工商为末艺”[13],而且还对传统四民的次序作了修改,“古者四民各有所处,士处闲燕,工处官府,商处市进,农处田野”[14],更是认为商业是兼备四德“曰仁、曰智、曰勇、曰断”[15]的高尚职业。王结也肯定了商人在生活中的作用,“城郭之民,类多工商,工作器用,商通货财,亦人生必用之事,而民食其中。”[16]从中可以看出,元代文人对商人及其所从事职业的认识较之以往已有很大改观,给予了一定的认可,这更加坚定了儒士们从商的决心和信念。
基于以上分析笔者认为,元朝儒士经商原因不外乎以下几点:一是人们对“商”之观念的变化,使儒士能从容于商;二是仕途的艰难迫使一些儒士转而从商;三是商人的成功诱惑着儒士从商。这与余英时[17]认为明清大批儒士“弃儒就贾”的原因基本一致,两者明显不同的是元朝由于儒学的边缘化和政府实行的重商政策,才出现了“士”与“商”亲融的可能。
但传统儒家重义轻利的观念,如孔子“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18],孟子“何必言利”[19]等思想深入人心,在道德深处已构成了对商人的否定。社会“无商不奸”的言论,更伤害了商人的自尊心,他们对自身的身份仍未完全认可。商人们即使家财万贯,仍觉得经商不体面,而对“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士人仍心存羡慕。
二、元代“以儒饰商”的类型
“以儒饰商”的实质就是商人虽然承认了自己的身份,但并未从根本上认可自己。虽然在元朝商人所处的环境已有了很大的改观,但儒家文化中重义轻利的传统常常使商人感到自己经商谋利的某种不体面和自卑,为弥补心态的平衡,商人欲以“儒”来装饰。
第一,儒士经商多为时势所迫。如山东邹平鲍兴曾以读书问学为务,“至正间,随父宦游浙上,值兵变,潛难于淞,则诡名氏,逐时以事转货。”[20]还有吉水商人萧雷龙,从小嗜学不厌,长而业成,宋社已屋无所试,后及元统一后,到处游学寻求仕进,中间也曾担任过一些职务,但都未能心满意足,“遂绝意于仕进……乃折节治货”[21],从“折节”可看出其从商之勉强。更多儒士则将经商作为谋生的手段。至元中,桐庐县人谢翱,“所居产薪若炭,率秋暮载之杭易米,卒岁少裕。”[22]李和,钱塘贫士,“国初时尚在,鬻故书为业,尤精于碑刻。”[23]元杂剧中也有一些弃儒从商者,如《来生债》中的李孝先,“习儒不遂,去而为贾”[24];《冻苏秦》里的王长者,“幼习儒业,颇识诗书,后从商贾”[25]等。元朝“明经射策,贡举进身之法皆废,(儒士)又不能治生,农工处市井中,遂商贾为业。”[26]弃儒从商亦不失为文人士子的一条出路。但也有一些儒士是自愿从商,如河南人姚仲实,为官已经10多年,慨然曰:“‘剥下以事上,非我志也’,弃官而还……东至于海,西踰于昆仑,南极交广,北抵穷髪,舟车所通,货宝毕来,可废居以为富。行之十年,累赀巨万。”[27]青州高仁“日诵千言,长习律令”,打算进入仕途,后叹曰:“为吏受赇,获罪辱先;守廉奉公,塱食弗给。”亦毅然放弃从仕而选择了从商。清河张文盛,“自力于学读书,通大义,工草隶,尤邃于医务,蓄方药以济人,卓犖有康世志。”后因“时事浸殊,太息曰:‘是不足展吾志矣。’乃弃其所学,从计然之术,研得其精”,成为元代有名的富商。综上可知,儒士经商又分为被迫经商和自愿经商两种,前者迫于时势不得不经商谋生,后者则主动放弃仕途投身商业。
第二,商人致富后多与文人结交,或为其子弟供养求学。如新喻商人周孟辉,不仅与儒士梁寅有较好交情,还广泛结交四方才俊,同时还效仿古圣贤之行为。“其也致远以服贾、懋迁以赡生,而因获友四方之才俊,观圣贤之遗迹,是皆古名人之所尝为。”[28]金溪商人王善,早年读书很有天赋,但值父丧后为振家业,废学而从商。“自叹早废学,力迪其子经术,筑精舍一区,聘硕士居之,朝夕策厉,若斯须不忘去者。俄俾从师两千里外,膏粱之馈,络绎道途,曾不以为烦。及见长子经,有《礼》经连领乡荐,喜曰:‘有子能通经,吾虽废学,政复何憾?’”[29]从中可窥出他弃学虽有遗憾,但寄望子弟能通儒,这种对儒情结已深深扎根其内心。吉水萧雷龙经商成功后,除自己积极学习,著述“有文集若干卷”[30]外,还出资建屋藏书,保存其他文人的著作,“积世藏书颇多,乡之贤达,若忠简胡公、闻节杨公、文忠周公之属,凡十余人,其所著书共数百卷。恐其废不传,构竹林精舍,发旧藏共庋之”。他对子孙的教育也非常注重,其二子皆从儒,长子来复,顺州儒学正;次子来有,某州儒学录;其中一孙洵,是乡先生刘岳申的高弟,专通群经,以善古文辞名,在明朝被应诏为虞部主事[31]。定海富商夏荣达,①参阅王秀丽老师《元代江南地区的士商亲融关系》一文,文中提夏荣达为夏荣发,笔者查阅相关史料发现,并未有这一叫法,“君讳荣达,字仲贤,姓夏氏”可能为其笔误所致。读书虽不多,“然雅敬贤士夫而听其话言,子若孙必延名师儒以教。”[32]具体并未提及具体名师,但看其子琛的孝行,“屡尝刲股,己母”[33],可知其受儒家孝文化的影响。元杂剧《老生儿》中的刘从善,虽做了一辈子商人,但他对侄子刘引孙的教育,“我知道那读书的志气豪,为官的度量小……读书的把白衣换做紫袍,则这的将来量较。可不做官的比那做客的粧幺,有一日功名成就人争羡”[34],从中仍可看出他对士人身份的羡慕和向往,极力劝说侄儿从文。
由上可知,元朝虽然对商的观念有所改观,但多数从商者仍为被迫所为,尤其具有一些文化背景者,在内心深处儒仍为他们心有所属和向往之,具体从他们一生的作为可表露。
三、“以儒饰商”的活动
在中国传统观念中,一提到商人人们往往就会想到贪欲、唯利是图,常与“奸”字联系在一起,似乎商人眼中只有利益。但上述提及的两类商人,他们的行为却不同于传统的一般商人。
其一,散财济贫。商人在致富后并未为富不仁,而是多方施财帮助贫困人士,富商姚仲实耳目之所及,力之所至,缓急患难,知无不为,“谓人莫悲于死无以葬,买雍庄地十余顷为义茔,以藏之。岁将冬,地且冻,预为竁以备之;人莫病于男女失其时,贫不能婚嫁者,资以助之;人莫不幸于失身为奴,赎而齐民者数十家。饥则为食于路,以饷饿者;寒则置席于狱,以藉囚者。”[35]对弱势群体的关照无微不至,甚至还有一套“积而不散,祸之招也”的散财观,这与商人张天祥的“积弗散,不有天灾,必有人祸”[36]观念一致。说明这类商人已经深刻意识到致富后也要兼济别人,让周围的人尤其是贫困者能够得到一丝温暖,这样才是保持富有的长久之道。
其二,赈灾救荒。灾后大批饥民嗷嗷待哺,国家无足够的钱财甚至不可能如此迅速送达济灾物品,而商人生活在饥民之中,看到饥民饱受饥荒的惨状,很多都积极主动拿出钱财、粮食投入赈济,上海商人唐煜,“至顺庚午,郡大水,出粟五千斛于官以赈。”[37]济南商人张信,“壬辰岁饥,出粟赈贷,乡人赖以全活”[38]。对于灾民来说,商人给予他们的救济往往是最及时最有效的。历来赈灾中商人都是一个活跃的阶层,但是在传统社会中,商人仍处于“尴尬”的角色。这与政府对商人的态度有关,尤其是入粟补官政策,陷商人于“不义”之中,但一些商人赈灾并不出于此目的,如嘉兴项冠,至元二十年,境内饥,输粟数万赈之,活者无算,“闻而旌之,授以将仕郎少府丞,力辞不拜。”[39]商人王德秀,弃科举业,于经子传记百家之书无不读,而尤喜陶朱丹圭之术,研精其奥。以赀雄州里,好施不倦,“丙午、丁未,岁大饥,倒廪出粟赈之,全活不可胜计。时募民入粟拜爵,君不自言”[40],从“不自言”。可看出,“入粟拜爵”是对他赈济行为的一种讽刺。
其三,助乡帮族。有强大的经济为后盾,商人对生活困窘的乡邻和宗亲往往给予帮助,改善他们的生活境况。如集庆路上元县的秦士龙,喜赒人之急,“乡邻有假货弗能偿者,不责也。”[41]武州张林,“舅氏及继母妹老无依,养葬并如此,育姻旧子女孤贫者凡三人,俾习善艺嫁娶焉。”[42]萧雷龙,“天雨雪,族里有弗炊者,载薪粲巡户周之。”[43]他们全面照顾乡邻和族人的日常生活,这也可从侧面了解儒家宗法制对这些商人影响之深。
同时,商人还捐赠佛寺,如吴人张天祥,“佛老家营大土木,亦乐予之赀。”[44]资助士人如元杂剧《裴度还带》[45]里的王员外,资助苏秦去应试。商人在闲暇之余的生活,尤其是晚年甚是恬淡,江西吉水商人王善,“悠然自放山水间,举觞属客,抚髀高歌,遗落世事,或饮至一石不乱”[46],这样的生活是多么的惬意。
此外,商人培育的后代也多行一些正义之事,如张彦明其父治生商贾,曾给予乡人贫穷者帮助,“乡里贫不给者,出有余以周惠之。称贷而不能偿者,悉毁其券”,及发廪赈饥“兵荒民乏食,发私廪起饿殍,赖以全活者不可胜计”。他幼习儒,以科举进士之路,废改习吏,仍不间断读书,并为其家乡捐赠书籍,“还家,买书八万卷以归,以万卷送济南府学,以作养学者。”[47]
四、“以儒饰商”的影响
从上述商人的行为可以看到他们身上闪耀着儒家文化提倡的美德,尤其是“仁”和“义”。“仁”“义”是儒家文化对伦理道德的要求,在一定程度上也揭示了儒家精神的内涵。
关于“仁”含有广狭两义。广义即“仁者,人也”,狭义即指爱人之心。上述商人极具有仁爱之心,他们广施钱财,用以帮助乡邻和宗族,如商人萧雷龙,在雨雪天,载薪餐,挨家挨户给族里揭不开锅的贫困者送食物[48]。他们的救助不仅局限于熟人,对陌生人也不排斥,正如陆文圭对商人榕傑的评价“孰饥而啼,予粟汝哺”[49],他们对身边的一切,都怀有一颗仁爱之心,充分体现了仁者爱人的内涵。
“义”作为一种道德准则,在儒家“重义轻利”的观念下,商人因求利的性质一直被儒家士人瞧不起。但在以儒“饰商”形象中得到了改观,如集庆路上元县秦士龙,偶与江淮间一巨商做买卖,巨商遗其槖金,他“拾而藏之以俟,日且墓……即举而归之”[50],后巨商请以其三分之一为报,他拒而不纳。元杂剧《东堂老》[51]中的东堂老李实,并未贪得无厌,趁扬州奴不思进取、挥霍浪费之机,霸占其家产,相反他是不负朋友重托,暗中帮助扬州奴重整家业,最终当众将巨额家产全部归还。在他们身上,明显体现了比利更重要的儒家“信义”观。
元朝儒学虽然处于边缘化的困境,但并不代表儒家文化不受重视。相反,儒家文化深深影响着元朝,包括商人他们身上明显闪耀着儒家“仁义”伦理美德。“以儒饰商”现象的出现表明了商人对儒士生活的向往,同时也表明儒家所倡导的道德体系在元朝得到了延续,它仍然在约束着绝大多数人的行为。儒士经商、商人慕儒从总体上提升了商人阶层的文化素质和道德修养,从而净化其“利益至上”的风气,这群人的出现及其所作所为显示了儒家文化对他们的影响,提升了商人群体的整体形象,这有助于打破世人对商人固有的偏见。
另外,在元朝由于入仕比较困难,士人开始转向务实经商谋生,而巨商富贾则多与士子文人结交。这使双方有了更多的了解,尤其是士人对商人的认识为士商观念的渗透提供了可能,客观上有利于士商界线淡化的趋势,这似乎是明朝后期士商互动的先声。
总之,虽然以儒饰商带来的影响是较大的,但是仍无法掩饰商人饰儒的初衷与动机。致富后,商人从事各种公益、慈善活动,意在使自己的经商活动变成一种有社会意义的行为,希望通过“义举”来补偿末业的“俗贱”,来追求社会对其价值的认可,正是基于这样的状况才产生了“以儒饰商”的现象。
“以儒饰商”现象是在元朝儒学边缘化和政府实行重商政策的双重影响下出现的,一部分儒士经商,但在传统儒家重义轻利观念的影响下,商人为获得心态的平衡也多与士人结交,同时注重培养子孙后代习儒,商人多少受到儒家文化的熏陶,从事多种公益性的慈善活动。此一群体的出现及其所作所为表明儒家所倡导的价值体系仍然植根于人们的心中,影响和制约着人的行为。即便是元朝,儒家的地位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但儒家文化仍然顽强地被保留了下来。当然,该群体的作为扭转了世人对商人的传统偏见,同时商人与文人的结交有利于士商观念的渗透,客观上促进了士商的融合,为明朝后期士商互动奠定了基础。
[1][宋]刘昫.旧唐书[Z].北京:中华书局,1975.2089.
[2][宋]郑玉道.琴堂谕俗编[Z].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2.294.
[3][4][5][6][9][38][明]宋濂.元史[Z].北京:中华书局,1976.3292,278,37,505,2017,3990.
[7][清]倪师孟,沈彤.乾隆吴江县志[Z].陈纕等修.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302.
[8][32][33][元]戴良.九灵山房集[Z].四部丛刊初编本.73,75,75.
[10][27][35][元]程钜夫.雪楼集[C].台北:国立中央图书馆影印,1970.312,310,310.
[11][明]王彝.王常宗集[C].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2.434.
[12][15][20][41][50]李修生.全元文[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169,169,169,508,508.
[13][明]袁华.耕学斋诗集[C].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2.314.
[14][36][44][元]杨维桢.东维子集[Z].四部丛刊初编本.154,141,141.
[16][元]王结.文忠集[C].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2.253.
[17]余英时.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M].南宁:广西师范出版社,2004.305.
[18]杨伯峻译注.论语[M].北京:中华书局,2006.42.
[19]杨伯峻译注.孟子译注[Z].北京:中华书局,1960.1.
[21][29][30][31][43][46][48][明]宋濂.宋学士文集[C].四部丛刊初编本.42,25,43,43,43,26,43.
[22][宋]邓牧.伯牙琴[Z].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2.511.
[23][元]杨瑀.山居新语[Z].南京:江苏广陵古籍刻印本,1984.8.
[24][25][34][51][明]臧晋叔.元曲选[C].北京:中华书局,1958.294,437,376,206.
[26][47][元]胡祇遹.紫山大全集[C].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2.294,269.
[28][元]梁寅.梁石门集[C].台北:新文丰出版社,1985.669.
[37][清]谈起行,叶承.乾隆上海县志[Z].李文耀修.南京:凤凰出版社,2014.436.
[39][清]嵇曾筠等.浙江通志[Z].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3243.
[40][49][元]陆文圭.墙多类稿[M].台北:台湾新文丰出版,1985.599,600.
[42][元]王逢.梧溪集[C].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2.806.
[45]隋树森.元曲选外编[Z].北京:中华书局,1959.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