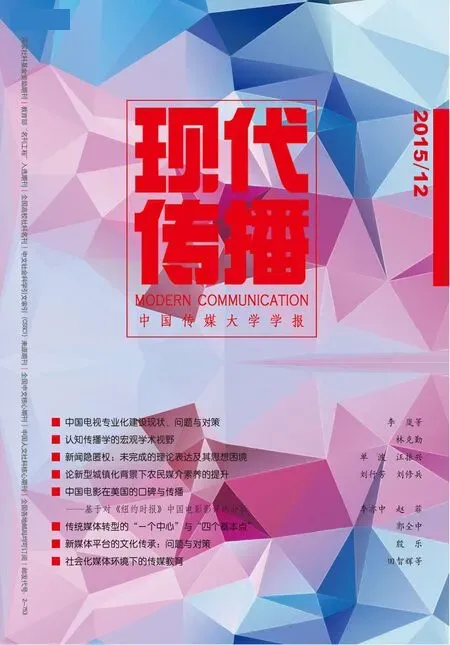激发公众同情:新记《大公报》与 20世纪30年代的赈灾运动*
2015-02-20郭恩强
■ 郭恩强
激发公众同情:新记《大公报》与20世纪30年代的赈灾运动*
■ 郭恩强
近年来,在有关中国近现代社会问题的研究上,很多学者关注了20世纪20、30年代大众媒体与公众情感(特别是公众同情)的关系。基于上述研究基础,本文探讨了20世纪30年代以新记《大公报》为代表的大众媒体在赈灾运动中激发公众同情的历史过程。研究发现,与以往强调大众媒体是利用非实在的公众情绪进行政治参与或追求商业利益的结论不同,赈灾运动中,以《大公报》为代表的大众报刊,通过对娱乐赈灾修辞和民族主义话语的运用,以及讲述现实中普通个体的捐助故事,来激发公众同情。在这一过程中,参与的公众获得了情感满足与升华,大众媒体则通过激发的公众情感获得了新闻行业的象征性权威和话语资源。
赈灾运动;公众同情;新记《大公报》
一、引言
20世纪前半叶,人类社会的剧烈变动,给人们在生活与情感上带来前所未有的强烈冲击,使群体性的情感体验变得频繁而丰富。这引发了学者从社会运动角度研究情感的兴趣。随着研究的逐渐深入,学者们试图在宏观历史背景下观察现代情感在社会进程中所起到的作用,并开始重视探究群体情感氛围与群体行动两者之间的关系。①
近年来,在有关中国的社会议题上,很多学者开始探讨一些重大社会事件、社会运动过程中情感氛围对于事件或运动本身的影响。如汉学家裴宜理(Elizabeth J.Perry)探讨了中共革命的成功 “不仅需要有益的外部结构条件,还需要在一部分领导者和其追随者身上实施大量的情感工作”,中国的案例“阐明了情感能量如何可能(或不可能)有助于实现革命宏图。”②在这些研究中,如何通过媒体激发大众情感从而在社会运动中采取行动,也往往成为作者考虑的重要因素。如顾德曼(Bryna Goodman)对民国一桩著名自杀案的研究,③林郁沁(Eugenia Lean)对民国施剑翘案的研究④,皆是此类研究的典型代表。前者认为在20世纪20年代,报纸通过组织公众对现代情感进行讨论,构建现代主体性,并且通过讨论创造了有理性的公众。而后者详细考察了在20世纪30年代发生的施剑翘一案中,大众化商业媒体和文化机构是如何利用戏剧化炒作和渲染激起公众同情,并揭示出公众同情既勇于批评时弊又容易被操纵的特殊社会批判功能。⑤大众媒体在制造这一公众同情的过程中具有中心地位。媒体提供了公共空间和平台,使得传统中不能发声的群体参与其中,展现个体性的现代自我,如即使是作为情感的消费者。
仔细分析上述研究,无论是理性主体公众的建构,还是情感主体公众的塑造,其逻辑归宿都落在对中国公众情感性政治参与与批判的强调,落在了“大众媒体的煽情炒作如何有效地动员或询唤了一个对不断集权化的政权表达强烈批评的现代公众”⑥的问题上。换言之,以往的研究虽然关注了中国大众媒体参与政治角色的一面,并对各种大众媒体形式(如新闻报道与评论、戏剧文本、电影等)之于大众情感的影响进行了考察,但如果以媒介中心的视角进行分析,则问题还有进一步讨论的空间。比如,在中国语境下的不同历史时期,媒体在一些大型的社会性事件中制造公众情感的方式是否与上述突显“轰动性”特征的案件有所不同?如有不同,媒体与公众情感的塑造又是通过何种机制实现的?除了媒体大众造就了所谓“一种批判性的、畅所欲言的实体存在—‘公众同情’”⑦式的情感性消费者,是否还有其他的情感性需求?与之相关,媒体自身除了通过市场炒作的方式追求商业利益外,是否还存在着其他方面的利益诉求,而这又如何表现?等等。本文拟通过《大公报》在20世纪30年代对几次大型赈灾运动报道的考察,尝试对上述问题进行初步回应。
二、娱乐赈灾与“平等国民”:激发公众同情的话语策略
早在19世纪70年代,以《申报》为代表的新式大众报刊的出现就与中国民间社会义赈的流行紧密相关。甚至可以说,正是因为晚清大众媒体介入到救灾之中,才使得义赈成为可能,使得救灾“近代化”得以成立。新式大众报刊改变了传统中国人的交往方式与信息传播方式,在此后的历次灾害赈济中,民众捐助都是由大众报纸组织。20世纪30年代前后,精英商业报纸新记《大公报》发起过几次有影响的赈灾运动。有研究者统计,在新记《大公报》发展初期,该报发起有关捐款救灾的运动将近二十次,⑧真正有影响的赈灾运动是20世纪30年代前后发生的几次。
对于“为民请命”这种传统中国的政治母题与意象,新记《大公报》一开始就是重视的,甚至计划列为重点经营的领域。⑨但从后来的反应看,应者寥寥,没有形成反响。从1928年的两次赈灾开始,《大公报》在赈灾模式上不断变换花样,运用多样的手段,使媒体成为了能够联结城市捐助个体和社会各参与机构的中介化结点。自从晚清由国家主导的赈济模式逐渐崩塌后,多样化的民间赈灾模式就不断被创造出来。其中在晚清媒体提倡的“娱乐助赈”,成为各时期赈灾运动中大众媒体调动公众情感与行动采用最多的手段。通过演戏、映影、游艺、说书,甚至“花界选秀”等易于调动情绪的娱乐形式筹募钱财,是大众报刊既积极组织又乐于展示的方式。1928年《大公报》发起的赈灾运动,就联合娱乐界如电影公司等参与赈灾活动。⑩同时,大众媒体采取的娱乐赈灾与社会名流相结合的方式,也使其与社会上层和其他各界建立了联系,获得了社会资源与职业资本。在1929年2月发起的“平津慈善演艺会”活动中,《大公报》不仅在显要位置刊登广告,还罗列了包括河北省主席、国府委员、外国公使等政界、军界、商界、银行界在内的各界名流四十余人的“台衔”。在这次以“平津市郊贫民众多,际此春冬之交生活尤为凄惨”,“恳请中外慈善大家发起慈善演艺会”的赈济活动中,《大公报》承诺演艺会的开销由该报“捐助”,而售票收入则救济贫民。(11)20世纪 30年代,尽管国民党在政治领域的新闻审查逐步加强,但在以“国家审查制度和泛滥的媒体商业主义为特点的时代,它的媒体和娱乐文化才可能作为一个‘江湖’的空间而发挥作用”。(12)这种状况也在社会领域为媒体提供了诸多可作为的空间。因而,像参与娱乐赈灾这种社会性议题,无论对媒体还是上层精英而言,都是风险极低并能获得社会声誉的活动,尽管这可能要付出被城市公众消费的代价。
但从《大公报》1929年公布的赈灾收支结果看,这种诉诸上层文化娱乐路线的策略并不十分有效,名流并没有实际参与捐助活动,尽管《大公报》借这些社会名流的头衔“展示”了其拥有的社会政治资源。(13)这一状况在1930年5月赈济陕西大旱的“陕灾”运动以及1931年8月下旬的“南方大水”赈灾活动中得到改善。此时的《大公报》有关娱乐赈灾的话语策略发生了逆转,由原来主要诉诸上层各界变为呼吁中下阶层,由提倡娱乐赈灾变为反对之。1931年的“南方水灾”,《大公报》认为“平津两市,盛行奢风”,号召人们“牺牲短期之享乐”,以救济灾胞。(14)在“救灾日”运动中,该报呼吁在救灾日,无论公私机关、家庭学校,都应该“停止娱乐”。(15)针对国民党中宣部发出的“告全国书”的呼吁,《大公报》认为“政府既正义在握”就应该“禁止一切奢靡享乐之事”和“不必要之消耗”,如各地跳舞、赛马、赛狗赌博等都应严禁。(16)上海、北平等城市的跳舞娱乐被《大公报》贬斥为“自利自私”,(17)而对程砚秋、梅兰芳等梨园名家的捐赠和“演义务戏”则大加赞赏。(18)《大公报》对城市大众娱乐所持的激烈言辞,对京剧名家的赞赏褒扬,背后隐含着该报诉诸中国传统公共伦理合法性的话语策略。
除了通过关注大城市现代式“娱乐”话题,诉诸公共伦理的话语策略以激发公众的同情外,《大公报》也尝试在赈灾运动中引申出更为丰富的政治与社会意义。在《大公报》的评论、新闻报道甚至副刊的话语修辞中,赈灾运动不仅是社会的,也是政治与军事的;不仅是物质的,也是精神的。在续刊号上,《大公报》希望通过“代灾民呼吁”,以便“普遍的宣传”民众“民国主人翁”地位,对“军阀官僚已泯灭之良知”施加影响。(19)民众赈灾是对军阀们“减灭好杀喜乱的恶根性”,显现“天良未泯”的一种救赎方式。(20)在社会意义上,《大公报》也试图以弥合各阶层社会差异的言说方式强调新的时代精神。赈灾运动可以成为展示“人类应有之同情”,获得“精神上报酬之代价”的良机。(21)通过赈灾运动,可以扫除“暴戾冷酷”的社会风气,重拾“同胞相爱之美德”和“人类爱”。(22)
20世纪30年代中国社会流行的民族主义情绪氛围,也为大众报刊发起的赈灾运动提供了话语契机,成为调动公众情感的合法性资源。在这一背景下,赈灾不仅是个体的,也是民族的,是“中国人心之不死”的表现,也是“提高地位,不愧为平等国民”,团结起来“收回租界”“打倒不平等条约”的演练。(23)《大公报》认为救灾与救国融为一体,救天灾与御外辱根本为一。在此一语境中,爱国群体“团结互助”“人道精神”的民族主义又与上文提及的个体奢侈享乐对立起来。《大公报》建构的民族主义话语修辞,既是时代潮流,也使得此种策略激发的公众同情作为一种政治力量能够获得官方的认可。国民党就试图利用此时的灾难话题增强民族主义和国家的凝聚力。国民党中宣部曾在1931年的“南方大水”赈济运动中发布“告全国书”,号召国民对受灾同胞“发同情之心,共节无谓之虚糜”,“拥护中央,力图挽救”。对国民党这一充满民族主义情感的言辞,《大公报》不仅加以引用,还强调这是“披肝沥胆之至论”。(24)可见,民族主义话语与赈灾话语的勾连,是《大公报》与国民党官方都能共享的激发公众同情的话语方式。
三、讲述老百姓的故事:建构想象的情感共同体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理解公众不能仅仅从制度和社会的层面,还必须从它的规范能力(normative capacities)去分析。公众除了以一般理解的实体形态存在外,更多时候应理解为一种“想象性的权威”。(25)按此思路,大众媒体无疑可以成为塑造这种“想象性”公众的联结性空间。
对于20世纪30年代的新闻业和读者而言,“读者来信”这种形式通常是使双方感觉到彼此存在的维系纽带。换句话说,报纸刊登读者来信或信息一方面是以“公共机构”属性的姿态展示,另一方面也能使自己触摸到读者的“脉搏”,感受真实读者群的存在。(26)在20世纪30年代前后媒体发起参与的赈灾运动中,《大公报》通过大量刊登个体性的故事,来激发公众的同情心,从而使“媒体-读者”想象性的关系联结不仅变成了实体,并且可以相互循环转化。
1928年6月底,《大公报》第一次发起“救灾”话题后,在该年11月底到12月底发起的“贫民的呼号”特刊中,尝试整版刊登受灾家庭人数、地址、受灾情况。这种形式在1930年的陕西赈灾捐款运动中,换之以整版刊登捐款者的姓名与捐款额。通过鼓励民众到报馆现场捐款,刊登捐款者名单和数额,讲授捐款者故事等形式,城市公众不仅可以通过阅读报刊触发不同个体之间的情感共鸣和想象性互动,还能实地感受由想象而行动的情感氛围。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通过大众媒体将日常生活变为奇观,在消费文化中形成的大众群体,能够结成一个消费社会事件的新都市群体。他们不仅观看故事,有时还会在媒体激发的情绪下采取行动。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就大众媒体发展的状况而言,此时的媒体“已经大大拓展了它们眼界,并呈现出一些前所未有的新特性,诸如追求轰动效应和鼓动感伤主义以迎合大众。”(27)大众媒体追求轰动效应一般采用具有“感伤主义”特质的新闻故事。而这其中,“小市民和日常生活的新闻故事,最为有效地,以比较含混,强烈和具体的方式,提出和表达了当时的道德议题。”(28)自然灾难之中普通受灾者与救济者的故事,无疑是反映具有“道德议题”特征的“小市民和日常生活的新闻故事”典型。
对赈灾运动中捐款与受捐民众个体经历、故事情节的渲染,强化了大众报刊作为一种公众情感激发与行动中介性空间的影响。赈灾中,无论城乡男女老幼还是富有与贫穷者,往往因报刊而“遇见”他人,想象与感受他人遭遇,甚至到受灾之地接触他人,接之再将这种感受与情感通过报纸传递给不同空间的他人,使之往复交往、互动与行动。在赈灾运动过程中,大众报刊力图使社会界限清晰的阶级、地域、年龄、性别等角色准则与情感界限变得模糊。此种角色与情感既包含了捐助个体彼此间的信任、给予与感激,也包括了充满商业消费色彩的娱乐体验与妇女参与。通过阅读各色人等捐款的感人故事,公众的“恻隐之心”被极大激发,上至达官贵人、社会名流,下至老少妇孺、贩夫走卒,甚至于赌徒、歌妓,都积极参与、慷慨解囊。在诸多故事的叙述框架中,《大公报》主要强调人的善良本性和读者的自发行为,而该报只是“借文字功用,诉诸社会同情心”,捐“一角”与捐“万元千元”在价值上是相等的。(29)在这样的基调下,编者在故事主人公的选择上作了精心安排,力求在平凡与显赫的人物身上都挖掘出普遍的情感。面对一幅幅带有强烈故事性甚至传奇性,由残酷现实中各色人等交织而成的感人场面,公众的情感没有理由无动于衷,漠然视之。
已有的研究表明,情感与个体行动的动力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柯林斯(Randall Collins)从人际互动的角度指出,人际互动之中促成人们交往的根本动力就在于情感能量(emotional energies),它包含个体在情境中所动员的感情、感觉和感触的种类与水平。(30)在赈灾运动的情境中,读者公众个体被激发的感情、感觉与感触无疑是立体丰富的。同时,与行动中夹杂着理性计算的情感不同,赈灾行动中的人们还有追逐情感满足与情感升华的一面。
那么,大众媒体激发读者公众产生情感能量,并进一步促使其产生行动的心理机制过程是怎样的呢?在整个赈灾运动过程中,《大公报》的故事报道模式首先激发了公众同情,将原本匿名的公众通过朝圣般的捐款现场变得可见,将原本分散的各种地位、职业、地方的读者通过捐款名单和故事的集体阅读、谈论得以“制造”。正是在一天天的新闻故事阅读中,公众的同情转化为行动,促发人们前往报馆捐款。在行善的名义下读者在报馆见到了为捐款而拥挤的同胞,也见到了以前只能想象的报纸编者。在这种集体仪式性的情感氛围中,是报纸将自己与其他流动人群联结与凝聚起来。对城市普通大众而言,对着纸面品评亲属、朋友、工友的捐款数目,甚至感慨于社会名流捐献的什物或巨款,可能是最直接的情绪性反应。他们渴望成为报纸故事中充满善良人性的主人公,希望自己的名字和其他人一样被印刷在整版的充满着密密麻麻名字和捐款数额的报纸上。在说服自我的感受上,重要的是自己名字已经和不同地位、不同职业、不同地域的人同列在一起,尽管数目不同甚至悬殊,但在以行善为名的人性光辉上,自己并不会觉得逊色,因为可以和“皇帝”、名流、富商等人做出同样的举动。(31)如此公众的情感行动正如有的学者所言,“现代中国的公众并不一定是指实在的、恒定的空间,而更多时候是被‘呼唤’和询唤出来的”。(32)而承担这种询唤角色的恰恰是当时的大众媒体。
《大公报》在组织赈灾运动过程中,逐渐意识到这种刊登行善者感人故事的情感动员力量。1930年5月发起的“宣传周”结束之后,该报将读者来信择要以“可贵的同情心”为题连续刊登,认为公众同情心是此次募捐运动的“无价收获”。(33)马可夫斯基(Barry Markovsky)和劳勒(Edward Lawler)曾指出,情感是种粘合剂,它将社会结构联结在一起。(34)《大公报》在赈灾运动中准确把握到了情感的这种网络联结作用,呼吁公众利用各种关系广为宣传和劝捐,(35)从而将公众想象的情感共同体建筑于实体的现实网络关系之中。
四、共享职业伦理:新闻界对诉诸情感模式的反应
根据林郁沁的归纳,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已经是“大众媒体的时代”。随着城市人口的增长和识字率的提高,大众媒体在中心城市及边远地方的扩张,以及媒体形式的多样化和娱乐业的繁荣,区域性事件能够迅速地转变为广泛流传的传奇并在全国范围内激起城市及近郊社群公众的同情。(36)与此直接相关的是,在现代灾难赈济中,一般都要以大众媒体为中介结点。赈灾组织经由报刊联结,将其成立情况、会议决定、行动及筹款、放赈等信息加以公开与透明化,以构建公众信任。而大众媒体则“凭借发表耸人听闻的社会新闻或社会事件,既增加销售,也增加与扩大了参与性读者相连的象征性资本。”(37)《大公报》正是在20世纪30年代前后的几次大型赈灾运动中,增加了自己的象征性资本。对《大公报》而言,发起赈灾运动激发的公众情感所产生的影响,不仅引发了公众的同情与行动,同时也重塑了自身甚至新闻界的形象。
在赈灾运动初期,《大公报》对新闻界同行虽没有直接发出呼吁,但却强调了报纸在运动中所能起到的鼓动作用,号召其他各界各业参与运动。尽管没有直接的证据表明平津新闻业加入1930年赈灾行动,是直接或间接受到了《大公报》的影响。但毋庸置疑的是,该报所发起并营造的捐款赈灾热潮与社会情绪,几乎波及了平津社会的各个机构和阶层,新闻同行很难置之不理。在《大公报》陕赈“宣传周”结束后,天津《商报》馆也举行“宣传周”并举办义务戏;继之天津《庸报》馆动议组织“救灾十人团”;辽宁的《东三省民报》《新民晚报》也仿行天津报界;哈尔滨《国际协报》也举行赈灾“宣传周”。(38)北平报界在后期也举行“宣传周”,以几家报馆为一组,顺序继起举行三周,有十家新闻机构参与。(39)北方新闻界对“宣传周”的热衷,是对《大公报》此前诉诸公众情感的宣传模式的仿效。
在1931年发起的南方水灾捐款运动中,《大公报》也采取类似的策略,初期倡设“救灾日”,希望“公私各界,政商机关,家庭,学校”等择定一日捐款赈灾或服务灾民。《大公报》提倡“救灾日”的第二天就有报纸作了响应。沈阳的《东三省民报》《新民晚报》公开表示效仿《大公报》的做法,与该报同一天举行“救灾日”运动。(40)北平报界也组织了“北平中外记者水灾筹赈大会”,计划开展记者自办的游艺会,将售票收入捐赠灾区。甚至有报纸坦诚,其参与赈灾活动是对《大公报》赈灾模式的“步其后尘,拾人牙慧”。《东三省民报》在社论中辩解,捐款方法上只要“最稳妥,最有效,最敏捷”“用力少而成功快,不但实际有效,并且唤起同情”,那他们就绝不会因为别人已经用过,或者不是自己发起而放弃使用。正确的态度是“感谢他们对于我们的指引”,而且“既然采了天津同业(大公报)的办法,更不惜用他们的言语”。(41)
用《大公报》用过的“办法”和“言语”修辞,也就认同了其激发公众情感的操作模式和伦理要求。那些采用此法来积极响应赈灾运动的社会各界、机关个人,无疑要加以褒扬。对那些积极响应的新闻同行,《大公报》不仅在评论中再次诉诸情感策略,讲述“因劳成疾”“几于以身殉赈”的同业故事,还将其倡导的新闻价值观与新闻界现状相勾连,认为“关内外同业的努力”对“自来中国报界,偏重政治,漠视社会事业”的狭隘新闻观起到了纠偏作用,由此号召“全国各处同业一致跃起”,致力于赈灾的社会事业。(42)而对赈灾持冷漠、消极,甚至“唱反调”的举动,《大公报》则直接批评或冷嘲热讽,如对募款期间北平跳舞场问题的贬斥,对官方救灾“散漫无能力”的指责,以及在陕西赈灾中对上海各界“不响应”的抱怨。(43)在一篇发自上海的“特讯”中,该报记者描绘了水灾声中上海社会的百态。在作者笔下,上海在全国一片赈灾声中俨然成了“罪恶之都”,充满了堕落、色情和腐朽的味道。(44)
林郁沁对施剑翘事件的研究表明,20世纪30年代大众媒体所创造的“集体同情成为了一种新的、影响深刻的道德和政治权威”,并且“更广泛地说,这个新的公众群体代表了一种正义”。(45)当赈灾的集体同情成为权威或代表了正义,那么作为此种正义代言人的大众报刊就划定了本行业的职业伦理规范,如果同行不正视此种规范,那就代表了“非正义”或丧失了职业合法性。面对赈灾议题,新闻界在或选择参与卷入以迎合公众情感,或选择漠视议题以冒着可能丧失职业伦理风险的权衡下,《大公报》实际上已经为新闻行业设置了不得不参与的议程。
值得指出的是,也有报刊对《大公报》在赈灾运动中诉诸的激发公众情感的操作方式提出挑战。有上海刊物对《大公报》只刊登了逊清皇帝溥仪捐款的“特有的新闻”,对其他报纸同行都刊登的皇妃“闹离异”的“普遍的新闻”却“不见一字登载”的做法提出质疑,并反问“这件事,是不是算做‘新闻’?”并要《大公报》“有以交代”。(46)将名流离异看成是新闻界会广泛发表的“普遍的新闻”,而将其赈灾捐款看成是只有某些媒体才刊登的“特殊的新闻”,可见上海的小报并不认同《大公报》所划定的新闻价值观和职业伦理,而是将侧重都市大众娱乐性的事件作为普遍的新闻价值观和伦理标准。
新闻界对赈灾活动由只展示公众情感的中介性空间,转变为积极参与到宣示自身情感与立场的活动进程中,是20世纪30年代大众媒体对诉诸公众情感模式,激发公众同情的新闻范式的认同、共享和一次大规模演练。赈灾运动作为当时大众商业媒体关注的热点话题,通过新闻行业内部对相关议题的交流互动,形成了翟利泽(Barbie Zelizer)所说的 “阐释共同体”。(47)新闻同行参与或不参与赈灾活动,已然被《大公报》塑造成当时新闻界是否能够代表正义的职业伦理界限。
五、结论
现在回到本文开头提出的一系列问题,与顾德曼和林郁沁探讨的民国时期一些“轰动性”的社会事件类似的是,20世纪30年代由大众媒体发起的赈灾运动,公众情绪也是被“询唤”和调动起来的,期间也往往和城市大众文化、消费主义纠缠,因此这种公众情绪也同样具有易被操纵的特点。但不同的是,大众媒体发起的赈灾运动规模更大,各阶层参与的人数也更多,运动具有时空上的扩展性和持续性。更为突出的是,大众已经由林郁沁笔下非实在的、隐匿的人群,变为可见的、“社会实体存在”的公众。(48)正是有如此的区别,以《大公报》为代表的大众媒体面对实际采取捐助行动的公众,采用了真人秀式的故事模式机制制造公众情绪。这些故事比之顾德曼描绘的拥有一定知识水平的“闺秀”或林郁沁笔下带有社会背景的“女侠”形象,更为多元、立体,跨越各种社会特征,因此也更有情感普遍性的意义。在此意义上形成的公众情绪,既有大众文化的消费特质(如娱乐赈灾),又具有现代城市陌生人群之间渴望形成互动关系的情感交换仪式特征。
同时,就作为大众媒体的《大公报》自身而言,通过炒作与调动公众同情固然有其追求商业利益的考量,但定位为严肃报纸的《大公报》也必然有其追求职业认同与行业权威的自我想象。煽情炒作的故事模式表面上与其严肃报纸的定位相冲突,但当这种冲突被涉及公益的赈灾议题冲淡和遮蔽后,看似“非理性”的公众情绪及其行动就转换为新闻行业的象征权威和话语资源,从而为其积累职业资本,这一点从《大公报》设定的赈灾议题对同行的影响中可以看出来。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在晚清义赈兴起前,江南社会已有着深厚的慈善传统,但其主导观念是浓厚的行善必得福报的思想。通过对《大公报》的赈灾案例分析可以看出,20世纪30年代的大众媒体赈灾,在话语修辞上已经摒弃了中国传统社会因果循环的福报观念,代之以民族主义和“同胞”“义务”“公德”“爱群”“合群保国”“爱国保种”这一类词汇,来激发公众的赈灾爱心与情绪。这反映了近代以来大众媒体所推崇的民族国家观念与国民党提倡的官方意识形态的合流,他们与中国城市公众的日常生活交互渗透、相互影响。
注释:
①(30)淡卫军:《发现情感之旅——情感社会学的当前概貌》,载苏国勋主编:《社会理论(第5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176、173、178页。
② 裴宜理:《重访中国革命:以情感的模式》,《中国学术》,2001年第4辑。
③ 顾德曼:《向公众呼吁:1920年代中国报纸对情感的展示和评判》,《近代中国妇女史研究》(台湾),2006年第14期。
④ 参见林郁沁:《施剑翘复仇案:民国时期公众同情的兴起与影响》,陈湘静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
⑤ 李文冰:《公众同情与“情感”公众:大众传媒时代一种新的社会批判力量》,《中国出版》,2014年第15期。
⑥⑦(12)(25)(27)(32)(36)(45)(48)参见林郁沁:《施剑翘复仇案:民国时期公众同情的兴起与影响》,陈湘静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0、223、83-84、8、27、7-8、26-29、225、7-8页。
⑧ 吴廷俊:《新记大公报史稿》,武汉出版社1994年版,第205页。
⑨ 《本报致全国慈善团体书》,《大公报》,1926年9月1日,第6版。
⑩ 《为救济四乡难民敬告电影界》,《大公报》,1928年7月3日,第9版。
(11)《本社主办平津慈善演艺会》,《大公报》,1929年2月8日,第2版。另见2月9日、10日、15日第2版的类似广告及19日3版的报道。
(13)《本社主办慈善演艺会会计报告》,《大公报》,1929年4月3日,第2版。
(14)《平津各界与救灾》,《大公报》,1931年8月22日,第2版。
(15)《本报发起“救灾日”运动》,《大公报》,1931年8月26日,第2版。
(16)《读中宣部告全国书》,《大公报》,1931年8月27日,第2版。
(17)《本社救灾日之辞》,《大公报》,1931年9月1日,第2版。
(18)《本社救灾日各方同情声》,《大公报》,1931年9月1日,第4版。
(19)《本报致全国慈善团体书》,《大公报》,1926年9月1日,第6版。
(20)《善机已动诸君努力》,《大公报》,1930年5月17日,第3版。
(21)《陕灾宣传周之精神》,《大公报》,1930年5月16日,第2版。
(22)《赈灾责任宜由全国共负之》,《大公报》,1930年6月4日,第2版。
(23)《本报代募陕赈第五日情形》,《大公报》,1930年5月17日,第4版。
(24)《读中宣部告全国书》,《大公报》,1931年8月27日,第2版。
(26)在笔者获得的文献中,读者与编者通过文字相互结识并相约见面的案例很多。如《大公报》主编副刊“小公园”的何心冷就经常有读者相约会面或对其形象进行想象。
(28)顾德曼:《向公众呼吁:1920年代中国报纸对情感的展示和评判》,《近代中国妇女史研究》(台湾),2006年第14期。
(29)《本报代募陕灾赈款第一日情形》,《大公报》,1930年5月13日,第3版。
(31)对于阅读产生意义的问题探讨,可参见[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吴叡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31-32页。书中对读者阅读产生“民族国家”“共同体”意识的精彩论述。另外,[美]林·亨特:《人权的发明:一部历史》,沈占春译,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20-48页,也对“阅读小说”所产生的“想象平等”的意义进行了探讨。
(33)《可贵的同情心》,《大公报》,1930年5月20日,第4版。
(34)B.Markovsky&E.Lawler,A New Theory of Group Solidarity,Advance in Group Process,No.11,1994,pp.113-138.
(35)《陕灾宣传周之精神》,《大公报》,1930年5月16日,第2版。
(37)顾德曼:《向公众呼吁:1920年代中国报纸对情感的展示和评判》,《近代中国妇女史研究》(台湾),2006年第14期。
(38)(42)《赈灾责任宜由全国共负之》,《大公报》,1930年6月4日,第2版。
(39)《北平报界宣传陕灾今日起举行宣传周》,《大公报》,1930年6月14日,第4版。
(40)《沈阳民新两报救灾日与本报同日举行》,《大公报》,1931年8月28日,第4版。
(41)《本社救灾日各方同情声:东三省民报救灾日》,《大公报》,1931年9月1日,第4版。
(43)分别见:《大灾中北平跳舞场问题》,《大公报》,1931年9月3日,第2版;《赈务太缓慢官民速努力》,《大公报》,1931年9月9日,第3版;《上海奈何不响应陕赈》,《大公报》,1930年6月23日,第2版。
(44)《水灾声中之上海》,《大公报》,1931年8月31日,第5版。
(46)《天津大公报与傅浩然》,《时时周报》,1931年2卷35期,第2-3页。
(47)Zelizer,B.,Journalists as Interpretive Communities,Critical Studies in Mass Communication,No.10,1993,pp.219-237.
(作者系华东政法大学科学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法学在站博士后)
【责任编辑:张毓强】
*本文系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资助项目“新记大公报与中国新闻界集体记忆研究”(项目编号:2015M570354)、华东政法大学重点学科传播学资助项目“中国近现代新闻传播思想研究”(项目编号:CBX2015)的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