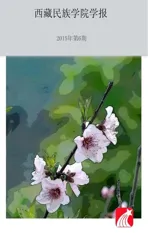从思维模式转向看智顗实相诠释学的建立
2015-02-20杨胜利
杨胜利
(西藏民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陕西咸阳 712082)
从思维模式转向看智顗实相诠释学的建立
杨胜利
(西藏民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陕西咸阳712082)
龙树以双边遮遣的中道思想提出不执空以否定有、不执有以排斥空的空有相摄的二谛理论。天台宗实际创始人智顗大师上承龙树,师事慧思,通过思维模式的转向,对龙树的二谛进行了创造性诠释。他认为空、假、中相即一体,涵容互摄,当体全是,从而构建起“一心三观”的方法论、“一心三谛”的本体论和“一念三千”的解脱论实相诠释学体系,不仅解决了般若中观学无限否定而导致“顽空”的矛盾,而且也会通了当时摄论师和地论师关于心、意、识之争。
智顗;三一;一心三观;一念三千;诸法实相
从人类认识来看,实际上存在着两个视域,即主体自身的视域和特定的历史视域。当认识主体进入历史时,认识主体的视域与历史的视域构成了一个更为广阔的视域,它包容了历史和现代的整体视域,这就是伽达默尔所谓的“视域融合”。“在历史和现代的整体视域中所获得的理解更具有普遍性意义,一切特殊的东西都在整体中被重新审视,特殊视域中所包含的不真的前判断将根据这种更全面的视域被修正。”[1](P343)“理解最后所达到的,就是获得以视域融合为标志的新视域。”[1](P343-344)天台智顗大师,正是通过视域融合对前贤时哲的料检科判,以思维模式的转向,重新诠释佛教之实相理论体系,从而建立起自己圆融无碍的佛教哲学。
一、困境与科判
佛教的根本宗旨是引导众生修行成佛,但由于众生对现象界的遍计执性而妄执我法两有。为了消解众生的这一执著心理,佛陀从说法开始便以“缘起性空”为其根本指导思想,教导人们不可执著世法,而要祛除一切计执之心,显现宇宙实相。实相是指宇宙间万事万物的真实性相,它的内涵就是空,是超言绝待的,“是与各别事物的自相不同的概念,它是在自相上显示的共性即空相。”[2](P121)实相并非客观的实体,“是从缘起现象上作出的价值判断。”[3](P666)它是大乘佛教的根本法印,《大智度论》云:“三世诸佛,皆以诸法实相为师。”《华严经》云:“唯佛与佛能究竟诸法实相。”所以,实相是佛教哲学诠释的根本对象。
大乘中观派在论说般若性空时,常常以中道实相来论述,认为一切现象,从俗谛看是有,从真谛看是空;既要看到假有,又要看到真空,同时还要不著两边,即是中道。《中论》云:“众因缘生法,我说即是无,亦为是假名,亦是中道义。”中道代表着一种非有非无双遮两边的思维方式,因为它是超出名字言语的,对它的把握只能靠般若智慧去观照。为了破除人们在不执著空有之后而执著中,中观学派只能通过不断的否定对其消解,《中论》又说道:“不生亦不灭,不常亦不断,不一亦不异,不来亦不出。”因为在中观学派看来,众生对事物的认识无外乎生灭、常断、一异、来出这四对范畴,只有对其双边遮遣,才能彰显中道实相。“诸法实相者,心行言语断,无生亦无灭,寂灭如涅槃。一切实非实,亦实亦非实,非实非非实,是名诸佛法。”[4](P24)“从因缘品来,分别推求诸法,有亦无,无亦无,有无亦无,非有非无亦无,是名诸法实相。”[4](P36)从这些引述可以看出,中观学派就是通过这种不断的否定方式防止人们执著于任何表述,虽然实相是超言语的,但为了表述仍不得不借助语言文字,这种表述只是权宜之计,只有真正懂得了第一义谛的真实性相,才能证得寂静涅槃。所以,龙树对实相的理解基本上是一个对“有”、“无”、“即有即无”、“非有非无”、“非非有非非无”的无尽破执过程,从而造成了业报轮回主体难以成立的理论困境。“一味地从破的立场来理解方便缘起法,而不适时地分析其存在的价值,最终一定会置自身于‘顽空’之地,自然就不利于佛教事业在现实世界的生存发展。”[5](P5)
阿赖耶识实相说认为外在事物都是人之微细心识——阿赖耶识所转变出来的幻象,只有阿赖耶识本身才是真实的存在,其他事物都没有真实的本质。它是一切染净种子的承载者,其中受无明熏习而生虚妄分别的是染法种子,依托清净法界而生的是清净种子,它同时也是业报轮回的主体。众生只有通过方便缘起法渐进修行,转识成智,转无明为清净,证得实相,得涅槃解脱。但问题在于,阿赖耶识实相论虽然为业报轮回找到了主体,对流转的生灭法作出了积极的说明,却使出世间法陷入由经验层面来决定的局面,导致众生成佛的必然性缺少内在的依据。因为,出世净心的产生主要依靠“正闻熏习”,这让众生成佛必须依靠外缘,成佛具有很大的偶然性。为了解决这一矛盾,如来藏实相论树立起一个具足无量功德的如来藏自性清净心,它是世间、出世间一切法的归依。“摩诃衍者,总说有两种。云何为二?一者法,二者义。所言法者,谓众生心,是心则摄一切世间法出世间法,依于此心显示摩诃衍义。何以故?是心真如相,即示摩诃衍体故;是心生灭因缘相,能示摩诃衍自体相用故。”[6](575)此心能开出真如和生灭二门,“真如门”即指如来藏自性清净心本具一切清净出世间法,不需要后天渐修;“生灭门”是用来解释世间万象如何产生的。“依一心法,有二种门。云何为二?一者心真如门,二者生灭门。是二种门皆各总摄一切法,此义云何?以是二门不相离故。”[6](P576)虽然如来藏实相论为众生成佛找到了内在依据,但由于如来藏自性清净心是一切法的根源,而且本为自性清净,那么在清净心中怎么能生起染法?如来藏自性清净心摄含真如心能够说明出世间法,但如来藏自性清净心和无明的关系则很难调和。所以,如来藏实相论与阿赖耶识实相论比较起来看,它解决了人成佛的内在必然依据,但对自性清净心如何产生生灭法则又陷入了理论困境。
关于实相问题,到了南北朝时期成为成实师、三论师、摄论师和地论师们争论不休的话题,而且愈演愈烈。摄论师为了解决众生成佛的必然性,又在阿赖耶识上增加了第九识阿摩罗识,代表众生的自性清净心,这就成为第八识阿赖耶识为妄心,第九识阿摩罗识为真心,为众生成佛的必然性提供形上依据。而地论师把阿赖耶识看成是如来藏自性清净心的一种变体。“依如来藏固有生灭心,所谓不生不灭与生灭和合非一非异,名为阿梨耶识。”[6](P576)如果说中观学派在探求诸法实相的过程中陷入无限否定的困境,那么,阿赖耶识实相论和如来藏实相论则在众生心识之外重新寻找解脱的依归,又陷入了无明与法性之间难以调和的矛盾。这些争论,如果从佛教发展方面来看,自然是不利的,因为它影响着众生对佛教的信仰。但从思想史发展来看,却是一次整合、创新的好时机,尤其是随着政治上统一趋势的出现,佛教思想上的统一融合,也是大势所趋。
智顗就是在上述理论困境中着手创建他的圆融哲学体系。首先他对当时地论师和摄论师的论说都进行了审视、批判和料简。他说:
“若从地师则心具一切法;若从摄师则缘具一切法,此两师各据一边。若法性生一切法者,法性非心非缘。非心故而心生一切法者,非缘故亦应缘生一切法,何得独言法性是真妄依持耶?若言法性非依持,黎耶是依持,离法性外别有黎耶依持,则不关法性。若法性不离黎耶,黎耶依持即是法性依持,何得独言黎耶是依持,又违经。经言:非内非外亦非中间,亦不常自有。又违龙树。龙树云:诸法不自生,亦不从他生,不共不无因。”[7](P54)
在这里,智顗对真如缘起论和阿赖耶识缘起论进行了科判。他认为,如果法性是一切法的依持,那么法性就不是先天之真如心和后天熏习而成的阿赖耶识,也就谈不上真如法性为一切法的依持。如果法性不是依持而阿赖耶识是依持的话,在法性之外还有一阿赖耶识依持,导致法性和阿赖耶识之关系难以协调的悖论。吕澂说:“那时期佛学的一般趋势都带着折中意味。”[8](P325)为了解决如来藏清净心、阿赖耶识和真心之间的矛盾,智顗以“三一”相即的思维模式予以调和,把心、意、识三者看成相即一体,即众生的“一念心”。他说:“对境觉知异乎木石名为心;次心筹量名为意;了了别知名为识。”[7](P14)这是从心、意、识三者功能上来说,各各有别,但从法性来看,则非三非一,非一非三。
“心中非有意亦非不有意,心中非有识亦非不有识。意中非有心亦非不有心,意中非有识亦非不有识。识中非有意亦非不有意,识中非有心亦非不有心。心意识非一故立三名,非三故说一性。若知名非名则性亦非性,非名故不三,非性故不一。非三故不散,非一故非合。不合故不空,不散故不有。非有故不常,非空故不断。若不见常断终不见一异,若观意者则摄心识。一切法亦而。若破意无明则坏,余使皆去。故诸法虽多,但举意以明三昧。”[7](P14)
智顗对当时关于实相争论的检视,是以思维方式的转变来融合沟通的。这里的“非一故立三名,非三故说一性”等表述,就是其“三一”思维模式的表现,其核心即是相即互具,正是通过这一思维模式,智顗把当时的如来藏清净心、真心和阿赖耶识融合起来,心中有意识,意中有心识,识中有心意,虽然三者各各有别、有名,但从法性来看,其实是一,三者相即不离,从而把众生解脱成佛的理论依据重新拉回到众生心,而这众生心既不是阿赖耶识染净心,也不是如来藏清净心,而是众生的“一念无明法性心”,通过对“一念无明法性心”的重新诠解,将大乘佛教最高境界“烦恼即菩提”、“生死即涅槃”这一不二法门又拉回了人间,重新树立起众生成佛的自信。在智顗的实相诠释学体系建立的过程中,正是以“三一”相即的思维模式,将三观、三谛、三智建立在众生“一念心”的基础上,三谛、三观、三智、乃至三千大千世界都在众生的“一念心”中顿然呈现,圆融无碍。
二、内在与转向
智顗会通了如来藏清净心、真心、阿赖耶识之间的矛盾与冲突,接下来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融合涅槃学和般若学。他当时所面临的是般若学地位下降、涅槃学地位上升这样一个局面。而他又对龙树的般若中观学又非常看重,曾说:“稽首龙树师,令速得开晓。”[7](585)为了解决二者的矛盾,智顗选择《妙法莲华经》(以下简称《法华经》)作为自己思想体系建立的诠释文本。这是因为《法华经》能够很好地将《般若经》和《涅槃经》融合起来。“此经所说要义在于开示佛教的究竟处、真实处,就和相传为佛最后所说的《涅槃经》会沟通。还有,《法华》的根本思想是性空说,说明宇宙间一切现象都没有实在的、可以把握的自体,这样又和《般若经》相融摄了。”[8](P325)基于这种原因,智顗极力推崇《法华经》,认为《法华经》最为究竟。“今经不尔。絓是法门纲目,大小观法十力无畏,种种规矩皆所不论,为前经已说故。但论如来布教之原始,中间取与,渐顿适时,大事因缘究竟终讫。”[9](P800)所以,选择《法华经》既不违自己归命龙树之初衷,也与当时佛教界的佛学思潮相统一。这样,智顗以《法华经》为自己著书立说的文本,以“会三归一”思想为主导,以思维模式转变的方式重新对龙树《中论·观谛品》中“三是偈”诠释,认为空、假、中三谛相即不离,一即三,三即一,非一非三,非三非一,通过“一心三观”悟入“一心三智”,从而体认“一心三谛”,空、假、中三谛举一即三,全三是一,三谛在一心中呈现,圆融无碍,从而证得诸法实相。
《中论·观四谛品》中“三是偈”是:“众因缘说法,我说即是无,亦为是假名,亦是中道义。”[4](P33)智顗根据自己的“三一”相即互具思维模式,认为这一偈则是说三谛的,即空谛假谛中道第一义谛。“空观闻于真谛,假观闻于俗谛,中观闻于中道第一义谛。”[10](P22)他认为自己是与龙树意同。“非离空有外别有中道,故言不异,遍一切处故言不尽,此亦与龙树意同。《中论》云:因缘所生法即空即假即中,因缘所生法即空者,此非断无也,即假者不二也,即中者不异也,因缘所生法者,即遍一切处也。”[9](682)但许多人通过文献和语言分析,认为智顗违背了龙树原有的精神,因为在《中论》还有这样一句话:“诸佛依二谛,为众生说法:一以世俗谛,二第一义谛。若人不能知,分别于二谛,则于深佛法,不知真实意。若不依俗谛,不得第一义。不得第一义,则不得涅槃。”[4](P32-33)这里只讲了二谛即俗谛和第一义谛,而并非智顗说的三谛。牟宗三对此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解读这四句话的关键在于“亦为是假名”一语,对它的解读不同,将会有两种解释。一种是:此偈中虽然含有“空假中”三字,但仍是二谛。“亦为是假名”此语是说空的,即“空亦复空”,空也是假名,是防执实有空;而中道则是空“离有无二边见”的。所以,假与中皆是对空的补充说明,都不具有实体义。所以是俗谛和第一义谛。第二种解释是就四句一气读,连三即。众因缘生法,我说他们就是空,同时他们亦就是假名有,同时这亦就是中道义。这样一连读的话,“空假中皆是对缘起性空讲的,空即于缘起无性而为空,非永远停在分解说的空义一面而不融于缘起;缘起即于空无自性而为缘起,非永远停在分解说的幻有一面而不融于空。分解说的前二谛是方便,归于一实谛即第三中道是圆实。即三而一,即一而三,圆融无碍。”[11](P75-77)这正是智顗的讲法。牟宗三进一步指出,无论是二谛还是三谛,都与义无违,并无冲突。而且智顗也有七种二谛说,说三说二皆可。
诚如牟宗三所言,无论是讲二谛还是讲三谛都无违龙树《中论》之原意。但是,智顗并不是照着龙树等人讲,而是接着讲。如果说龙树是以荡相遣执之否定的思维方式论说二谛的话,那么,智顗讲三谛则是以“三一”相即互具的思维方式论说三谛之理,与别教不同。他说:
“即中即假即空,不一不异,无三无一。二乘但一即,别教但二即,圆具三即。三即真实相也。《释论》云:何等是实相?谓菩萨入于一相,知无量相;知无量相又入一相。二乘但入于一相,不能知无量相。别教虽入一相,又入无量相,不能更入一相。利根菩萨即空故入一相,即假故知无量相,即中故更入一相。如此菩萨深求智度大海,一心即三,是真实相体也。”[9](P781)
在智顗看来,二乘偏重于说空,能入一相而不能知无量相;别教知空、知假,虽能入一相并且知无量相,但不能更入一相。圆教则以“三一”相即的思维方式观照空、假、中三谛,举一则具三,能够即空即假即中,即入一相,又知无量相,还能更入一相。在这里,智顗讲三谛于一心中得,同时将三谛与实相联系起来,知道了一心即三之理,即可证得真实相体。他又说:“别三谛者,开彼俗为两谛,对真为中,中理而已。”“圆三谛者,非但中道具足佛法,真俗亦然,三谛圆融,一三三一。”[9](P705)别教说三谛,是将其俗谛开为真俗二谛,把真谛看成为中道谛,此中道谛只是理,而不是法,所以就不具备诸法。而圆教不仅仅中道具足佛法,而且真俗二谛亦具足佛法,因为它们相即一体,圆融无碍,一三三一相即不离。所以,别教之三谛是隔历三谛,而圆教之三谛则为圆融三谛。“分别者,但法有粗妙。若‘隔历三谛’粗法也,‘圆融三谛’妙法也。”[9](P682)智顗认为对三谛的看法有粗法、妙法之别,也是别教和圆教之异,别教看三谛是一一相隔,将空、假、中各隔别对待,而圆教则是一一相即,即空即假即中,体一互融,一心三谛。三谛圆融的结果则是一实谛。“三谛具足,只在一心。分别相貌,如次第说。若论道理,只在一心,即空即假即中。”[7](P84-85)
智顗对其“三一”思维方式的表述有多种,如果从肯定的方面讲,则是一即三、三即一、一三三一相即不离;从否定的方面讲则是三非三亦复非一。他认为,非三非一为本,而三而一为迹。因为诸法实相是超言绝待的,说三说一只是权,目的是开权显实,只有证得了诸法实相,则言语道断,心行处灭,迹权皆废。这一思维特征实现了般若中观学思维方式的转向,避免了大乘中观派重空可能导致的“恶趣空”困境,因为此一模式在讲空时,空亦具中、假,当讲假时,假亦具空、中,当讲中时,中亦具空、假,通过相即互具化解了对任何一谛的偏执。智顗说:“若谓即空即假即中者,虽三而一虽一而三,不相妨碍。三种皆空者,言思道断故;三种皆假者,但有名字故;三种皆中者,即是实相故。但以空为名,即具假中,悟空即悟假中,余亦如是。”[7](P7)悟一谛则余二谛相即并得,如三点伊(∴),一不相混,三不相离,举一而得三。陈英善说:“我们知道‘空’、‘假’、‘即空即假即中’三个概念皆在陈述缘起的道理,然而于所面对问题不一,所以表达缘起实相的方式也就有所不同。约略来说,‘空’所面对的对象,是因缘法,故以‘空’来表达因缘法,亦以‘空’来破除对因缘法之自性执。当‘空’的概念提出后,则形成了‘因缘法’——‘空’之二概念,即‘假’(有)与‘空’二概念。为了避免把‘空’与‘假’对立化(或对‘空’之偏执,或对‘假’之偏执),因而以‘中’来化解之。因此,‘中’所面对的是‘空’、‘假’之问题,故以‘中’来化解之。当‘中’之概念形成时,所面对的问题——‘空’、‘假’、‘中’三个概念的问题,为了避免对‘中’之执著(即视‘中’为自性),因而以‘即空即假即中’来化解之,以连结‘空’、‘假’、‘中’三者之关系,是彼此相即不离,故以‘即空即假即中’表之,此不单可以遮除对‘中’之偏执,亦可遮除对‘空’、‘假’之偏执。”[12](P144)所以,这一思维模式就避免了对空、假、中任何一边的偏执。
智顗之所以强调三谛之理,是因为谛含有真理、审实之义,明白了三谛之理,也就证得了诸法实相。世界的本质纯一实相,实相之外无任何别相。“实相者,即经之正体也。如是实相,即空假中。”“一实谛即空即假即中,无异无二,故名一实谛。”[9](P781)实谛即实相,实相有种种名,都是方便假设,“实相之体只是一法。佛说种种名,亦名妙有真善、妙色实际毕竟空、如如涅槃虚空佛性、如来藏中实理心、非有非无中道第一义谛、微妙寂灭等。无量异名悉是实相之别号,实相亦是诸名之异号耳。惑者迷滞,执名异解。”[9](P782)实相是毕竟空,是超言绝虑的,这些名字只是假名施设,决不可执为实有。但为了让众生明白诸法实相之理,才以种种方便假设明实相之理。三谛不等于实相,实相也不等于三谛,空、假、中三谛只是实相的三种表现。实相是体,三谛是用;三谛是权,实相是实;三谛是迹,实相是本。只有当证得诸法实相,则“莲成华落”,权迹皆废。而智顗正是通过“三一”相即的思维方式将体用、权实、迹本关系表述出来,最后“会三归一”皆入一实相。如何证得诸法实相呢?智顗继续通过“三一”相即互具思维模式建立“一心三观”、“一心三智”,以“一心三观”悟入“一心三智”,照三谛圆融之理,证诸法实相。
在智顗看来,一心三观、一心三智、一心三谛其实就是认识实相过程中的能观、所观、观成三个方面,所发为三观、观成为三智、所照为三谛,三者相即不离,三观、三智、三谛都是建立在众生的“一念心”之上,在一心中得。但别教是对顿根之人而说,是次第观,次第证,是方便说,尚不究竟。而他所立之圆教则是“一心三观”,无须次第,一心中全然呈现。“观心释者,观心先空次假后中,次第观心也;观心即空即假即中者,圆妙观心也。”“观心释者,观因缘所生心,先空次假后中皆偏觉也;观心即空即假即中是圆觉也。”[10](P4)一心中刹那间同时观察空、假、中三谛,三者三而一,一而三。
三观、三谛、三智三者各自本身不仅相即一体,而且三者之间也是三一一三相即不二,都在众生的一念心中呈现。
“若一法一切法,即是因缘所生法,是为假名,假观也;若一切法即一法,我说即是空,空观也;若非一非一切者,即是中道观。一空一切空,无假中而不空,总空观也。一假一切假,无空中而不假,总假观也。一中一切中,无空假而不中,总中观也,即《中论》所说不可思议一心三观。历一切法亦如是。若因缘所生一切法者,即方便随情道种权智;若一切法一法,我说即是空,即随智一切智;若非一非一切,亦名中道义者,即非权非实一切种智。例上,一权一切权,一实一切实,一切非权非实,遍历一切,是不思议三智也。”[7](P55)
三谛、三观、三智在一心中相即一体,交融不分,互相观照,一空一切空,不假不中谓之空;一假一切假,不空不中谓之假;一中一切中,不空不假谓之中,观假即观空中,观空即观假中,观中即观空假,一心三观、一心三智而达三谛圆融,而此三者圆融统一于一念心。“在一心中,即一而论三,即三而论一。”[10](P886)“只约无明一念心,此心具三谛;体达一观,此观具三观。”[7](P84)因此,在智顗“三一”思维模式下,三观、三谛、三智圆融无碍,相即一体,而为一心之呈现。
心是成佛的根本条件。因此,智顗通过“三一”相即模式调和了当时佛教界关于心、意、识的关系问题,他认为三者三而一,一而三,非一非三,非三非一,相即不离,互为一体——“一念心”。而此心能天堂,能地狱;能造五阴,能造名字。他说:
“《释论》云:三界无别法,唯是一心作。心能地狱,心能天堂;心能凡夫,心能贤圣。”[9](P685)
“若依《华严》云:心如工画师,画种种五阴。界内界外一切世间中,莫不从心造。”[7](P52)
“《毗婆沙》云:心能为一切法作名字。若无心,则无一切名字。当知世、出世名字,悉从心起。”[9](P685)
心不仅是解脱成佛的关键,而且也能造世间一切法。智顗引述这么多关于心用之表述,一方面是想将当时众生成佛解脱的依据转向众生自身,而不是向外索求;另一方面,也为他的“一心三观”、“一心三智”、“一心三谛”找到一个基点,而通过“一念心”去体认中道实相或诸法实相。智顗之“一念心”既是认识的起点,又是认识的终点,既是能观又是所观,认识主体、认识对象、认识的结果都在“一念心”中实现。所以,他说:“心即实相。”众生的“一念心”就是心的刹那活动去观照本心,观照实相,明白了心和实相相即一体之理,则可解脱成佛。
但他的实相诠释学并未到此结束,如果这样的话,他所说的心识活动就容易让人产生执为实有之偏颇。所以,他又以“三一”思维模式中的否定模式对其否定。“复次,此三非三亦复非一。非三非一为本,而三而一为迹。皆言语道断,心行处灭,不思议一也。”[10](P129)他所要达到的境界是言语道断,心行处灭的“不思议境界”。所以,他对心又进行了重新审视。
“心如幻焰,但有名字,名之为心。适言其有,不见色质;适言其无,复起虑想。不可以有无思度故,故名心为妙。”“心本无名,亦无无名。心名不生,亦复不灭。”[9](P685)
因此,心也不可执为实有,既无名,又无无名,不生不灭,是谓不思议妙心。而由心所证之实相,也是不可言说的。“诸法寂灭相,不可以言宣,是无谛义也。”“一谛尚无诸谛安有,一一皆不可说。可说为粗,不可说为妙。不可说亦不可说是妙。是妙亦妙言语道断故。”[9](P705)前面的所有言语施设都是权,是迹,当明白诸法实相之理,权迹皆废,言语皆断,进入不思议之境。诚如《法华经》所言:“如实相不颠倒,不动不退不转,如虚空无所有性,一切语言道断,不生不出不起,无名无相实无所有,无量无边无碍无障,但以因缘有,从颠倒生故,说常乐观如是法相。”
可以权且的说,智顗通过“三一”思维模式的肯定与否定,以《法华经》中“方便通经”和“会三归一”为原则,将三观、三谛、三智归于众生“一念心”,通过此心既完成了他“一心三观”的认识论,也构建起了他的“三谛圆融”本体论实相诠释学。但作为大乘佛教,实现众生脱离苦海,获得解脱,才是根本宗旨,认识论、本体论都是为其解脱论服务的,因此智顗又将诸法实相原理应用于三千大千世界,通过“一念三千”为众生超凡成圣提供理论支持。
三、融合与超越
如果说“一心三观”、“圆融三谛”是智顗的认识论和本体论,那么,“一念三千”则是为众生超凡入圣而构建的解脱论,是实相学说在止观中的实践。
“一念三千”中的“一念”就是“一念心”;“三千”就是三千世间,指整个世界,是“一念”的对象。三千世间是智顗依据《大智度论》的“三种世间”、《华严经》的“十法界”、《法华经》的“十如是”而对整个世界和各别事物从纵横、内外方面做的精细分析。三种世间是对众生的构成、构成因素以及所处环境做的一个由内而外的描述,是每一众生必须面对的现实世界。智顗对三种世间并无多大发挥性的解释,而超越性的解释在于对十法界提出的“十界互具”思想和“十如是”的“翻转三读”。
十法界是指由于众生的迷误不同,从而导致诸法的分界各各不同,即地狱、饿鬼、畜生、修罗、人、天、声闻、缘觉、菩萨、佛,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六凡四圣”。之所以有如此的分界,关键在于迷误所致,迷则在六凡位,悟则在四圣位。根据智顗的“性具实相说”,“阐提断修善尽,但性善在。佛断修恶尽,但性恶在。”[10](P882)佛与阐提之人都性具善恶,但阐提之人虽修善尽,但具性善;佛虽修恶尽,但性恶在。正由于他们性具善恶,所以,佛才能度化众生,而阐提之人也能成佛。“阐提不断性德之善,遇缘善发。佛亦不断性恶,机缘所激慈力所熏,入阿鼻同一切恶事化众生。”[10](P883)阐提之人不断性德之善,若遇机缘,则善性可发,有成佛之潜在可能性;而佛则由于不断性恶,受机缘慈力之所激所熏,则可度化一切众生。这一思想不仅是对竺道生“一切众生悉有佛性”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也为众生成佛提供了平等的机会。由于十界性具善恶,所以,智顗提出“十界互具”,即每一界皆具其他九界,举一界即九界。“即”是相即不离之意,而“互具”也有相即一体之意,所以,“互具”是“相即”思维模式在佛性思想中的进一步展开。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三一”思维模式的特征在于相即一体,“即”是关键词。智顗曾对他的“三一”相即思维模式做过比喻,他说:“如摩醯首罗面上三目,虽是三目,而是一面。”[7](P25)摩醯首罗面上三目是圆伊(∴)之三点,此三点相即不离,而且互为观照。知礼在《十不二门指要钞》中又对“即”字做了进一步的详细说明,“当宗学者,因此语故,迷名夫旨;用彼格此,陷坠本宗。良由不穷‘即’字之义故也。应知今家明‘即’,永异诸师。以非二物相合,及非背面翻转,直须当体全是,方名为即。”[13](P617)知礼认为,虽然它宗也使用“即”字,但并没有真正认识“即”字的真正含义。他认为,“即”不是两物的相合,也不是一物的两面翻转,直须当体全是,成佛之道也是如此,不是烦恼之外另有菩提可证,无明之外另有法性可求,而直须当体在一念心中明白二者相即不离之义。智顗曾说:“对无明称法性,法性显则无明转变为明,无明破则无无明,对谁复论法性耶?”[7](P82-83)无明即法性,烦恼即菩提,法性、菩提是针对无明、烦恼而言,无明、烦恼破,则法性、菩提就无所对称,成佛或者证得诸法实相的关键就在于须破心中的无明,别无外求,只在自身的“一念心”。从此一思路而来的“性具善恶”也是一样,对恶称善,当修善尽则无复称恶,以此意而言,互具、相即正是智顗“三一”思维模式特征的不同表述。“一法界具九法界,名体广;九法界即佛法界,名位高;十法界即空、即假、即中,名用长。即一而论三,即三而论一,非各异,亦非横亦非一,故称妙也。”[9](P692)十界是区别众生的别相,但从体上来说,都属于智顗所立的中道实相,或者是诸法实相,无论是体、是位、还是用,都是诸法实相在诸法界的展开,是权,是三,而最后都归结于一,归结于实,这正是“会三归一”、“三一”相即思维模式下的逻辑构建。
如果说十法界是从个别相而言的话,那么个别相还有自己的性、相、体、用等,这就是智顗所说的“以十如约十法界”的“十如是”。智顗对“十如是”的解读是承慧思和《法华经》的思想而来,《法华经》所谓“十如是”是:“唯佛与佛能究竟诸法实相,所谓诸法如是相、如是性、如是体、如是力、如是作、如是因、如是缘、如是果、如是报、如是本末究竟等。”但是,智顗以“三一”思维模式结合空、假、中三谛对此进行“翻转三读”。《法华经》只说“十如是”,而他解读成“是相如”、“如是相”、“相如是”。他说:
“依义读文,凡有三转。一云是相如是性如,乃至报如。二云如是相如是性,乃至如是报。三云相如是性如是,乃至报如是。若皆称如者,如名不异,即空义也。若作如是相如是性者,点空相性,名字施设,逦迤不同,即假义也。若作相如是者,如于中道实相之是,即中义也。分别令异解故,明空假中;得意为言,空即假中。约如名空,一空一切空;点如名相,一假一切假;就是论中,一中一切中。非一二三而一二三,不纵不横名为实相。唯佛与佛究竟此法,是十法摄一切法。”[9](P693)
智顗将十如是“翻转三读”,显示了空、假、中三谛之义,“是相如”等显空义;“如是相”等是显假义;“相如是”等显中义,三者“非一二三而一二三”。从别相来看,是一二三,从实相来看非一二三,三即一,一即三,三者最后都归于一实相,而“唯佛与佛究竟此法”。
三种世间、十法界、十如是和三谛之理如何统一?智顗再次以“三一”相即思维模式,通过“一念心”将其“会三归一”。首先,他从事、理、因果、依正等方面看“一念心”与十界、十如、三谛和三种世间的关系,他说:“于一念心不约十界,收事不遍;不约三谛,摄理不周;不语十如,因果不备;无三世间,依正不尽。”[7](P294)所以,“一念心”只有约十界、三谛、三世间,语十如,才能理事周遍,无所不备,三千世间即在众生的“一念心”。
“夫一心具十法界,一法界又具十法界、百法界。一界具三十种世间,百法界即具三千种世间。此三千在一念心,若无心而已,介尔有心,即具三千。”[7](P54)
在智顗的实相诠释学体系中,是将认识的对象和认识的主体合而为一的,也就是将心之能所合一,心所观之境是三千世界,而三千世界就在众生心中所具,心的发动就是“一念心”,就在这刹那一念之间能所合一,心即具三千世间,而果则是达到一种“不思议境”。另外,此心和一切法的关系不是心生一切法,也不是心含一切法,它们之间是相即不离的一体关系。
“若从一心生一切法者,则此是纵;若心一时含一切法者,此即是横。纵亦不可,横亦不可,只心是一切法,一切法是心故。非纵非横,非一非异,玄妙深绝,非识所识,非言所言,所以称为不可思议境。”[7](P54)
如果心生一切法,则是纵;如果心含一切法,则是横,纵横都不可以。只能是心是一切法,一切法是心,心和一切法是相即不离之关系,非一非异。“一念三千”这种对心物的认识,“摆脱了佛教传统的各类缘起论和心物相合的认识论的规范。”[2](P34)智顗将诸法、实相和心相即一体来看待,心即实相,而诸法则是实相的显现,心与诸法也是相即一体,非一非异。结合前面智顗所引《释论》之“心能地狱,心能天堂;心能凡夫,心能贤圣。”“一念心”中即具佛界,又具众生界,成佛解脱的关键就是这“一念无明法性心”的启动,如果识得诸法实相之理,则贤圣天堂;如果永处迷误,则凡夫地狱。至此,智顗既为众生成佛既找到了所依之体,也为成佛指明了方向。
综上,智顗通过视域的融合和思维模式的转向而构建起来的实相诠释学,不仅会通了涅槃学与般若学的矛盾,也融合了摄论师与地论师之争;不仅建立起了“一心三观”、“圆融三谛”的本体论实相学,而且也构建起了“一念三千”的解脱论,为众生成佛指明了方向。在这一思维模式构建下的实相学,使“一念无明法性心”得到了很好的解读,无明即法性,法性即无明,二者相即不离。它们的分界只在众生的“一念心”,当此“一念心”明识诸法实相之理,则无无明,而法性也不可复论。“对无明称法性,法性显则无明转变为明,无明破则无无明,对谁复论法性耶?”[7](P83)此又与《华严经》所说之“心、佛及众生,是三无差别”相契合,其实相诠释学的圆融会通特色彻底得以彰显。
[1]潘德荣.西方诠释学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
[2]潘桂明.智顗评传[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6.
[3]方立天.中国佛教哲学要义[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4]高楠顺次郎,小野玄妙等.大正藏(卷三十)[M].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3.
[5]张刚.智顗实相论研究[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10. [6]高楠顺次郎,小野玄妙等.大正藏(卷三十二)[M].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3.
[7]高楠顺次郎,小野玄妙等.大正藏(卷四十六)[M].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3.
[8]吕澂.中国佛学源流略讲[M].北京:中华书局,1979.
[9]高楠顺次郎,小野玄妙等.大正藏(卷三十三)[M].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3.
[10]高楠顺次郎,小野玄妙等.大正藏(卷三十四)[M].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3.
[11]牟宗三.佛性与般若[M].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0.
[12]转引自张刚.智顗实相论研究[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10.
[13]转引自牟宗三.佛性与般若[M].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0.
[责任编辑乔根锁]
[校对康桂芳]
D823
A
1003-8388(2015)06-0106-08
2015-09-20
杨胜利(1976-),男,陕西渭南人,现为西藏民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在读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先秦儒家文化和西藏宗教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