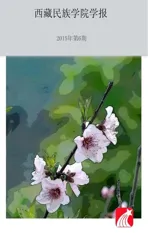《麦克马洪线》摘译(五)
2015-02-20梁俊艳张云
梁俊艳 译,张云 校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历史研究所 北京 100101)
《麦克马洪线》摘译(五)
梁俊艳译,张云校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历史研究所北京100101)
本文根据大量英文原始档案资料,叙述并分析了西姆拉会议中“麦克马洪线”产生的前因后果,认为印度政府为“麦克马洪线”的合法性所作的辩解是站不住脚的。文中将中国和西藏并举等这类西方学者普遍使用的错误提法,并不代表译者及本刊的观点,请读者明辨。
西姆拉会议;第二次签订的西姆拉条约;麦克马洪线
二十六、麦克马洪线[1]
即便中国人签了字,西姆拉条约也不可能为阿萨姆喜马拉雅的英国边界问题提供最终解决方案。的确,从理论上而言,内外藏的划分的确可以令中国领土不再与部族山区发生直接接壤,但并不能保证今后西藏人不会在中国的支持下宣称对该地区拥有权利和影响,虽然自1910年以来印度政府就认为该地区处于英国的势力范围之内。1910年以来,由于阿波尔远征军及其他探险活动,印度政府对于阿萨姆喜马拉雅地区边界的具体位置有了相当清楚的了解。现在除了保证将中国影响力排除在外藏之外,还需要通过签订条约划定这条边界线,而这样一份文件也正是印度总督哈定和英国全权代表麦克马洪希望通过西姆拉会议获得的成果之一。除了上述原因,印度政府决定不与中国政府讨论阿萨姆边界问题,因而便有充分理由保证不将划定麦克马洪线放在西姆拉会议日程上。看起来,似乎将西姆拉会议会场作为英藏代表直接讨论边界问题的场所——没有中方代表的参与——显得更为明智,如果天赐良机,其谈判结果或许会通过最终的三方协议获得确认(也许会通过间接方式)。正如我们所见,通过3月24日和25日的换文,麦克马洪获得西藏代表同意边界线的划定,也就是后来著名的麦克马洪线,再通过巧妙地使用一些红色墨水,便延长了西姆拉条约所附地图上的大西藏边界范围。麦克马洪竭力地争取中国代表承认他所绘制的这条线。
自20世纪50年代中印关系恶化以来,印度官员始终认为,麦克马洪线的附件仅仅是“将该地区自然的、传统的、民族的、行政的边界线变得正式化而已”。[2]正如印方声明所言,阿萨姆喜马拉雅地区的部族地区,在公元8世纪,《瑜伽尼往世书》创作之际,就已处于印度人的管理之下了。自那时起,直至现在,该地区始终处于印度管辖之下。一位印度作家指出:
直至麦克马洪线的整个部族地区,始终都处于阿洪王朝的持续统治下,阿洪王朝之后便是英国人继续管理该地区。在英国人管理期间,从一开始,部族地区先是在政治代理人或毗邻地区的副专员的司法管辖之下……全世界没有哪一条边界线像中印边界一样依据传统、条约和管理而确立,不存在任何争议。[3]
不幸的是,无论多么符合现代印度外交的需要,我们都很难说上述言论对阿萨姆喜马拉雅山地部族区域治理历史的理解是正确的。在1910年初,中国人占领拉萨之际,西藏政府的权力以直接和间接的方式延伸到达旺地区,直至阿萨姆平原地区的边缘。在当时,除了察隅河谷(又译作洛希特河)之外,英国人对阿萨姆喜马拉雅地区的渗透是非常肤浅的。不少英国人和其他欧洲旅行家都曾前往察隅河谷,他们在察隅河谷瓦弄附近看到了西藏边界的标志;即便是在察隅河谷之上,也不能说当时的米什米部族以任何合法的方式归属于英国的主权之下。在1914年3月24日和25日的英藏换文中所确定、地图中所标注的麦克马洪线,并非古老的印度边界线,而是一条全新的边界线,英国人将其设计出来之后,用以替换沿着山脚的老外线。这条边界线并非基于古老的传统,而是1911年初威廉逊被阿波尔部族人杀害后,英国人积极的调查工作产生的结果。
作为一条印度边界线,麦克马洪线起源于1910年10月23日敏托勋爵的一份电报,相关情况已有所述及。在这种情况下,由于中国人对察隅河沿岸的米什米地区产生兴趣的证据已为众人所知,敏托建议,通过向北推进外线,在英国和中国领土之间“获得缓冲区”;他建议,新的边界线应遵循阿萨姆喜马拉雅山脉山脊的一般界限,从达旺地区东部边缘延伸至伊洛瓦底江-萨尔温江分水岭。1910年,印度政府仍将达旺地区视作纯粹的西藏领土,从达旺直至山脚下的领土都是如此,因而不建议由于新边界线的缘故而将其纳入英属印度领土范围内。1910年的建议实际上非常模糊。除了察隅河谷之外,关于阿萨姆喜马拉雅山脉的地理信息还十分贫乏。除了察隅河谷,英国官员仅仅渗透到外线以北的山区里几英里、为数不多的几个小地方。在这种情况下,英国本土政府认为自己没有能力对敏托的建议作出判断,因而这些问题暂被搁置了。
1911年9月21日,在威廉逊被谋杀一事充分影响了印度边疆政策之后,哈定勋爵再次提出敏托勋爵的建议,在阿萨姆划定一条新的印藏边界,以此作为自己的“松散的政治控制”政策。尽管克鲁勋爵对“松散的政治控制”政策包含的意义怀有一定质疑,但依然同意,这种类型的新边界似乎是很有必要的。故也被确定为阿波尔远征军及其相关探险活动,米里使团和米什米使团的目标之一,以便通过这些远征活动与探险考察确定一条最适合的线作为新的边界线,并令中国人尽可能地远离印度平原,也尽可能与西藏人占领该地区的事实相互妥协与调和。截止1913年底,印度政府已拥有足够多的信息,足以详细具体地描述出这条边界线。当然,还有不少没有探索到的地方,但阿萨姆喜马拉雅山脉山脊已不再像1910年那样,对印度外交部门而言是一片未知区域。
正如许多印度观察家在中印争端过程中指出的那样,新边界线划定的明显原则是流入阿萨姆和流入西藏的河流之间的分水岭。不幸的是,阿萨姆喜马拉雅山脉本身的特征尤其不适于始终用分水岭概念来划分其边界。阿萨姆喜马拉雅山脉被亚洲的大河之一雅鲁藏布江-布拉马普特拉河从中切断,从距离印度河河源不远的雅鲁藏布江源头发端,这条河流经数千英里确定无疑属于西藏的领土。印度平原和中亚之间的真正分水岭就位于雅鲁藏布江及其支流以北;若遵循这条线为边界,则拉萨、日喀则、江孜以及中部西藏的绝大多数城镇都将划入印度范围内。随着在阿萨姆喜马拉雅山脉地区的探险活动的增加,人们发现雅鲁藏布江-布拉马普特拉河绝不是唯一的一条横跨新边界线的河流。在最东部,即缅甸和西藏交界处,塔伦河上游,是伊洛瓦底江的恩梅开江分支的一个支流,流经西藏人居住的一个地区。位于瓦弄以北、历史悠久的察隅河(亦作洛希特河),流经西藏察隅地区之后就变成了察隅河。在阿萨姆喜马拉雅山脉的雅鲁藏布江-布拉马普特拉河以西,探险家发现苏班西里河及其支流察隅河的源头也确定无疑位于西藏领土内,而从西藏流经达旺地区北部直至东部不丹的娘江河也是如此。因此,现在的情况十分清楚,如果新的边界线不会导致英国吞并西藏大片领土,那就不得不横穿至少六条主要河流。因此,这条边界线的最终形式——麦克马洪线,实际上并没有遵循印度—中亚的主要分水岭,而是沿着发源于喜马拉雅山脉最高峰北麓的几条主要大河的一系列河谷分水岭划定的。在这条边界线的好几段组成部分中,麦克马洪爵士及其顾问不得不在两条或更多的分水岭界限中做决定。详细界定麦克马洪线是不可避免的:与其说这条边界线清晰地遵循了传统以及人种学、民族学,不如说是英国人一系列决定产生的结果。
在选定一条令人满意的新边界线的过程中,印度政府在达旺地区面临的困难尤为突出。正如上文提到的,西藏领土在达旺地区被认为从山脉山脊向南延伸至山脚、位于乌达古里以北几英里的地方。在1910年10月23日敏托的建议以及1911年9月21日哈定的建议中,二人都认为不应再修订英属印度和达旺地区之间的边界线。他们一定认为,如果修订这条边界线,势必导致英国吞并西藏领土,而这一点恰与1907年英俄协定中的规定相冲突。然而,达旺地区并没有被忽略。因为这是一处将喜马拉雅山脉屏障一分为二的突出地区,而其处于西藏的控制之下(由此也处于中国的潜在控制下)。作为英国防御链上的一个弱点,达旺要远比其西面的春丕谷重要得多。因此,截止1912年6月,印度总参谋部决定,尽管存在1907年英俄协定的限制,印度政府必须对达旺地区采取一些措施。印度总参谋部指出:划定关于达旺地区的边界线要求我们深思熟虑。当前的边界(已经划定的)[4]是在达旺以南,从乌达古里附近沿着山脚向西直到不丹边界以南,由此,米里地区和不丹之间被插入了一个危险的楔形地带。一条相对容易通行、使用较多的贸易路线从北到南横穿这片楔形地带,中国人可以利用这条路线给不丹施加影响或压力,而我们却无法从侧翼抵达这片突出地带,正如我们在春丕谷的情况那样。因而,我们必须修订这条边界线,一条理想的边界线将从山上东经93度、北纬28度20分的地方出发,到错那宗以北的不丹边界,这是一条东西走向的直线,位于不丹北部边界领土内。这似乎是一处非常便利的分水岭。[5]
印度总参谋部在建议中提到的边界线修订范围,不仅暗示着英国将占领达旺和门巴人居住的达旺以南,而且包括西藏行政中心错那宗。当印度政府意识到有必要占领达旺地区的部分领土后,他们显然认为只有选定一条更靠南的边界线才能满足其需求。在1913年10月28日的备忘录中,麦克马洪指出,印度政府必须遵守达旺地区的山脚边界线,他还附上了在皇家地理学会所绘地图基础上绘成的草图。皇家地理学会绘制的这幅地图的名称为《西藏及周边地区》,1906年编辑,比例尺为1:3800000,在整个西姆拉会议期间被使用,标注出各种各样的边界线,标明英国边界线是从不丹向东延伸,经由德旺吉里和乌达古里北部,直至完全经过达旺地区,过了达旺之后突然向北延伸,与苏班西里河谷以西、后来称为的麦克马洪线相互衔接。[6]到了1913年11月中旬,一条更为激进的边界线被确定了。现在,印度政府劝说哈定勋爵接受的新边界线穿越色拉山口,距离达旺寺以南只有几英里。[7]这种情况一直维持到1914年2月。1914年1月22日,在亨利·麦克马洪爵士致函亚瑟·赫泽尔爵士的一幅草图中,标明了这条位于阿萨姆喜马拉雅山脉的新边界线,这是在与伦钦夏扎讨论的过程中形成的,当时的色拉山边界线仍然是标注出来的。[8]然而,在另一幅地图中,即1914年2月19日麦克马洪寄给赫泽尔的那幅地图,边界线略显向北延伸,遵循着麦克马洪线的最终划定,将达旺寺的所有地区都囊括在英属印度的领土范围内。[9]
以上边界线出现这种变化的准确原因,我们还不得而知。1914年前三个月期间,英藏关于麦克马洪线谈判的备忘录似乎并没有保存在印度事务部和英国外交部的档案中;有理由认为,这些备忘录实际上从来没有寄到伦敦。将达旺寺囊括在英国领土范围内最有可能的解释或许是,1913年末,麦克马洪从贝利和莫希德处获得了关于达旺地区的最新准确信息;此二人在刚刚沿着雅鲁藏布江探险的归途中经过了达旺地区,他们在1913年11月26日抵达西姆拉后,向麦克马洪报告了相关情况。[10]贝利在报告中提出,达旺寺在管理色拉山以南的门巴族中发挥着关键作用;麦克马洪经过一番深思熟虑之后,很可能认为:如果英国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控制达旺寺的僧人,那么今后英国在色拉山以南的治理将会容易许多。[11]此外,麦克马洪似乎还希望,通过向北拓展英国边界,西藏和阿萨姆之间经由达旺的古老商贸路线就会再次复兴。[12]从贝利的报告中,麦克马洪很可能得出这样的结论:若听任达旺寺僧人自行其是而不加干涉,他们很可能会想尽办法阻挠途经达旺经商的商人。
达旺地区以东,这条新边界线的其中一段经过了苏班西里河(也就是西藏的杂日河)及其支流察隅河。米里使团访问该地区的目的之一就在于此;但苏班西里河支流卡姆拉上游居住的部族百姓的敌对态度,迫使科尔伍德及其率领的部下在还未抵达西藏最南端之前就不得不原路折返。在这偏远的地区,从西藏一侧抵达过苏班西里河上游的贝利和莫希德二人,可以提供第一手的可靠信息。他们提到,在苏班西里河,或曰杂日河,马及墩标志着西藏人占领的最南端,从马及墩往南,则是珞巴人居住的地区。然而,他们发现西藏人习惯于每隔12年就沿着马及墩南部的苏班西里河进行朝圣,同时还要用盐巴和其他物品重重贿赂珞巴族商人,以此劝阻他们不要屠杀虔诚的朝圣者。[13]在贝利的建议下,麦克马洪似乎将新边界线确定在马及墩以南,但同时意识到这些小的调整必须符合西藏人的宗教情感。
苏班西里河以东是雅鲁藏布江—布拉马普特拉河这条大河从喜马拉雅山脉中穿过的地方。在这里划定一条令人满意的边界线存在几个困难的抉择。第一,在雅鲁藏布江—布拉马普特拉河的支流锡约尔河上游,居住着一些信仰佛教的人,他们似乎处于西藏大贵族拉鲁家族的封建统治下,给工布地区的西藏政府缴纳赋税。第二,很难沿着雅鲁藏布江—布拉马普特拉河自身,在阿波尔和西藏人定居处、或受西藏人影响地区之间绘制一条清晰明确的分界线。比起最南端的西藏村庄,这里的阿波尔村庄向更上游的地方一直延伸到一处地方,不丹人在19世纪曾向这里移民;直到1913年,这里的定居者还认为自己是不丹仲萨本洛的臣民。阿波尔和西藏人、门巴人(一个术语,专用来概括来自达旺地区和东部不丹的人)的关系始终都不太平。过去发生的战争常常给距离老外线以北不远的阿波尔村庄强加各种义务,例如,迫使他们向波密和工布的西藏政府缴纳各种贡赋等。1912年和1913年,由于英国调查队和探险队的缘故,这里的情况日益清楚:直至科博,底杭河谷(或香河)主要居住着阿波尔人,他们在很多情况下与西藏人存在某种关联,但在文化上和语言上并不能归类为西藏人。从科博以北到聂拉姆河和金珠曲汇入雅鲁藏布江-香河之地,有时又被称作白玛科钦,是多民族杂居之地,其中藏族和门巴人占绝大多数。在聂拉姆-金珠曲河以北,居住着绝大多数藏族人,但阿波尔人(或珞巴人)会时不时回到这里经商。然而,位于白玛科钦的藏族和门巴族村庄,都是最近才迁居来的,时间不超过一百年,他们迁居此处都是以阿波尔人为代价的。根据获得的所有信息,邓达斯和内维尔在1913年10月提出两条穿越底杭河谷的可行边界线。[14]其中一条边界线包括白玛科钦在内,沿着北部的纳姆拉和最近发现的海拔25000英尺高的南迦巴瓦峰划定。这条边界线将大批西藏人和门巴人划入英国领土界内,但英国政府的正当理由是,白玛科钦曾一度属于阿波尔。另一条边界线越过香河向南,位于科博村和孟库村。这条边界线排除了阿波尔属于少数群体的地方,很可能更容易治理。印度政府决定采纳这条边界线。
底杭河谷以东是迪邦河谷,1912年和1913年,米什米使团的分支曾沿着察隅河谷来过这个地方。[15]在迪邦河谷上游,在德赖河,安得拉河,永雅河等支流附近,西藏人曾于20世纪最初10年来此定居过。他们似乎在寻找一处圣地,一位西藏先知曾预言这处圣地是一座完全用玻璃做成的山。这些西藏定居者和当地的米什米人部族发生了冲突。1913年,他们发现当地人对自己过于抵制,于是,除了太老或病得太厉害不能行走者之外,其余绝大多数藏族人都返回了西藏。因此,在迪邦河谷上游的这条边界线不存在真正的问题,这条线应遵循迪邦河及其支流与向北流入西藏的河流之间的分水岭。
迪邦河以东的察隅河,在阿波尔远征军抵达之前,是英国人对阿萨姆喜马拉雅山脉地区了解最多的一处地方。不同于阿萨姆边界的其他部分,中国人十分清楚自己在察隅河上的具体边界。1910年,中国人在叶普河竖立了边界标志,1912年,他们再次设立界柱。他们还表明,自己的边界与察隅河北岸、德赖河汇入察隅河之处接壤。据此,1913年11月,陈贻范提出,中国宣称的边界从德赖河-察隅河交汇处,向东穿越迪邦河谷,直至雅鲁藏布江-香河,而这里也正是英国人决定其边界所在之处。[16]诸如威廉逊和贝利等英国官员,始终倾向于这种观点,即叶普河是察隅河上的一处较为公正的边界点,它正好是米什米人和西藏人居住地的分界线。然而,1913年,邓达斯根据自己在米什米使团的经验指出,这个分界点也有几处弊端。[17]首先,中国人在叶普河标注了边界标志,这说明中国人在德赖河-察隅河交汇处的边界点没有任何问题。若基于此,中国人或西藏人在德赖河汇入察隅之处的叶普河附近设置哨岗,则该哨岗会位于米什米地区深处,且横跨从萨地亚到英国设置在叶普河附近的曼尼克莱边界哨岗之间的道路。仅仅这一事实就足以表明:整个边界线都应北移,这样就能把整个德赖河谷掌握在英国人手中。在这种情况下,也可以把整个边界线推到察隅河边。第一,这样就能从德赖河上游的格雷山口获得一个较为容易的分水岭边界线。第二,就在叶普河以北,沿着迪曲和萨尔梯河,经由塔洛克山口从察隅直至缅甸北部的康提垄地区。中国人已经从云南一侧渗透到康提垄地区,如果他们返回西藏,必然也会尝试从这里划界,趁现在还有机会关闭这扇特殊之门,可谓审慎之举。邓达斯辩解道:中国人在叶普河的边界点并没有他的前任威廉逊认为的那样合理。他这样写道:“中国人仅仅去了一次曼尼克莱,在那里插下了他们的旗帜,这并不等同于边界线,也不证明我们不能在多曲以北的地方宣誓主权。”我们暂且忽略中国人前往叶普河拜访的次数是三次而非一次,邓达斯继续表示,尽管意义重大的米什米人的定居止于叶普河以南,但西藏人的定居直到卡浩村才真正开始,即迪曲河汇入察隅河之处。在二者之间,只有四处西藏民居(瓦弄和提奈各有一处,董有两处)位于米什米人习惯于放牧的地方。邓达斯说,的确,一些西藏人常常被米什米人雇来放牧。叶普河,多曲,迪曲之间的地区是真正的“汤姆·梯特勒的土地”(查尔斯·狄更斯著作,又名《富乐园》—译者)。邓达斯建议,这条新的边界线应沿着分水岭向东,从格雷山口沿着多曲北部至察隅河,在卡浩村(邓达斯认为这是最靠南面的一个西藏村庄)南边越过察隅河,随后向东沿着克里提河和迪曲之间的山脊进入塔洛克山口。印度政府更希望将塔洛克山口这条路线纳入康提垄,因而对该建议稍作修改,将卡浩村纳入英国领土,然后令这条边界线从察隅河沿着迪曲以北直至塔洛克山口。[18]
1914年2月,在西藏人最终接受新边界线之前,这条建议中越过察隅河的边界线因为英国人在该地的行政管理而得到进一步确定。[19]1914年1月1日,邓达斯的助理、负责米什米部族地区的奥卡拉汉,带领39名廓尔喀人组成的护卫队,从萨地亚出发,沿着察隅河游历。2月初,他抵达叶普河,看到了中国满清王朝在1910年和1912年初在当地所立的界标,同时也看到1912年6月中华民国官员在米什米使团从曼尼克莱撤离后重新竖立的界标。奥卡拉汉将自己能找到的界标全部连根拔起,并带到上游的卡浩村埋在地下。他为自己的行为所找的正当理由是:
如果我们允许这些界标继续存在下去,今后就可能会被误解为我们默认了中国人和西藏人对这些领土的主权,而通过我拔除这些界标,并将其弃之于卡浩村,我们便不承认任何人在此处的主权。[20]
奥卡拉汉从卡浩村继续前往日马,受到了当地西藏政府的热情欢迎。当地政府询问西姆拉会议进展如何,并向他保证,他们认为西藏利益在英国人手中是安全的。他没有发现能证明中国人在察隅有丝毫影响的证据。就在奥卡拉汉拔除中国人的界标之际,有证据表明,印度政府当时还没有下定决心将这些界标移到无疑属于西藏人定居处的卡浩村以北。然而,奥卡拉汉的行为得到了阿萨姆行政专员阿奇戴尔·厄尔爵士的授权,因而一劳永逸地解决了该问题。[21]卡浩村由此变成了英国领土,边界线从迪曲以北直接穿过。
察隅以东是英属缅甸。如果新边界线麦克马洪线的东侧仍然悬而未决,那么,这处与西藏间未划定的边界也不容忽视。有必要在位于新的西藏-印度-缅甸三方交界点的塔洛克山口,与萨尔温江-伊洛瓦底江分水岭上(英国人宣称该分水岭是英国与云南省的边界线)的伊苏拉齐山口之间建立某种联系。[22]这就出现了塔伦河的问题。塔伦河是伊洛瓦底江的恩梅开江分支的一个小支流,起源于西藏附近的卓瓦镇和门贡镇。塔伦河的最上游部分显然住着一些西藏人,其流经路线途经门贡镇和阿墩子两地,将察隅、波密、工布和云南连接起来。因此,塔伦河沿线可谓真正的分水岭边界线,可以令英国侵入到毫无疑问属于西藏的领土;此外,这一点也正是西姆拉条约所附地图上的内外藏边界线的源头和起点。在1912-1913年冬天,普理查德上尉和沃特菲尔德上尉来到塔伦河谷探险,由此极大地丰富了普理查德和贝利在1911-1912年间获得的信息。[23]这次探险令普理查德失去了性命,但也表明英国理想的边界线是一条在北纬27度40分的地方穿越塔伦河的边界线。塔伦河分界线以北的居民从未给康提垄酋长纳过税,他们认为自己是西藏臣民。军事部门也认为,对于塔伦河谷以北的军事防御,英国不应承担任何责任。印度政府接受了普理查德和沃特菲尔德的建议,并将其体现在麦克马洪线中。[24]
一旦印度政府决定详细地划定这条阿萨姆喜马拉雅地区长达850多英里的新边界线,就不得不令西藏代表接受这样一个建议:英国实际吞并了被达赖喇嘛视为自己领土范围内的2000多平方英里的土地。1914年1月和3月间,当西姆拉会议在德里举行之际,查尔斯·贝尔和伦钦夏扎通过一番谈判达成了上述协议。双方谈判结果便是1914年3月24日和25日的英藏秘密换文。换文的文本第一次被公布是在1929年。通过这些换文,我们就能大致了解谈判期间究竟发生了什么。[25]不幸的是,印度政府认为与伦敦沟通贝尔—伦钦夏扎谈判备忘录似乎并不恰当;而现今的印度政府也不大可能在今后公开这些文献,因为它们和现代中印边界争端之间的关系过于密切。[26]
自1911年印度政府获得的关于阿萨姆喜马拉雅山脉的地理信息,体现在一幅地图中,这幅地图比例尺为8英里:1英寸,共有两页,名为“印度东北边疆,临时”。在这幅虽然远远不够完美、但却是当时所能获得的最好的地图上,这条新的边界线,即麦克马洪线,被绘制在上面。[27]现在,印度政府必须说服伦钦夏扎接受这条边界线。由于缺乏备忘录,我们很难说清当时印度政府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但得出一些基本的结论是有可能的。
第一,伦钦夏扎很可能把麦克马洪线视作一笔更大买卖中的一部分,至少后来西藏人是这样辩解的。西藏代表同意与英国人划定这条符合印度政府喜好的边界线。英国人则保证划定一条更符合达赖喇嘛喜好的中藏边界线,没有英国人的帮助,西藏政府永远不会得到这样一条边界线。这样一笔交易,如果真的发生过,无论是直接还是间接,都充分解释了麦克马洪不愿和中国人在划定内外藏边界线时作出让步的原因。如果是这样,那么,是麦克马洪线导致了西姆拉会议的失败;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西姆拉会议反过来又成为阿萨姆喜马拉雅地区安全问题最终解决方案麦克马洪线失败的原因之一。
第二,从目前公布的极少数文献资料可知,伦钦夏扎的确没有无条件地放弃西藏在麦克马洪线以南的领土主权和权利。在达旺地区,他保留了他所认为的收税权,尽管试图通过以下术语伪装:“西藏政府现在征收某些税费……从门巴人和珞巴人出售的物品中”。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香河和察隅河谷。伦钦夏扎似乎坚持认为,锡约尔河上游的拉鲁家族的家产无论如何不能受到影响。最后,在苏班西里河上游,西藏朝圣香客还将和往常一样,不得受到英国人干涉。对于这些条件,麦克马洪似乎都已经同意了——这是对1914年3月24日麦克马洪向伦钦夏扎发去的照会所做的最符合逻辑的解释。他还向西藏人保证,如果觉得因为麦克马洪线而遭受了任何损失或困难,他们有权与查尔斯·贝尔就此问题重开谈判。因此,从某种意义来看,麦克马洪线具有临时性和实验性的特点。正如麦克马洪本人在信中向哈定和克鲁拐弯抹角地作出的解释:
拉萨的西藏政府已经充分考虑了这一边界问题,同意西藏全权代表承认现在这条印度和西藏之间划定的正确边界线。在我们针对双方边界进行谈判的整个过程中,他们尽可能表现出合理、公正的态度。要不是鉴于西藏政府和我们或许在将来修订这条边界线的任何地方时需要更详细的情况,我们毫无疑问会对西藏人的利益表现出同样的态度,但这种义务等内容并没有在协议中提到。[28]
基于这一分析,麦克马洪线便包含了相当奇怪的宪法含义。诸如达旺地区、香河上游、锡约尔河谷以及叶普河和卡浩村之间的察隅河等地方,都被划定到英属印度帝国的领土范围之内了。然而,这些地方并没有成为英国统治下的领土。实际上,这些地方更像是英国的保护地,正如不丹那样,具有一定的内部自治权。然而,不丹是一个拥有自己权利的政治体。不丹人自我管理这一政治体。而像达旺这样的地方,即便对外国政府负责,也无论如何都不是由大英帝国任命的官员来治理管辖的。由此,人们可以辩解说,西藏的部分领土如达旺等,已经处于英国利益范围之内,而此处的麦克马洪线,与其说是一条国际边界线,不如说是印度政府无法容忍除了西藏之外的任何国家的影响力(例如中国)出现在这条边界线以南;而即便是西藏的影响力,也只能在不带有侵略性的情况下才被印度政府接受。从这一观点来看,这也是西藏人有可能接受的唯一解释,麦克马洪也在很大程度上遵守着“松散的政治控制”这一政策。例如,在察隅河谷,克鲁勋爵已经接受了这一原则,认为有必要设置一个英国哨岗,但英国军队不得驻守在中国人曾经竖立过界标的叶普河以北。
如我们所见,麦克马洪线边界实际上涉及将西藏领土名义上转让给印度政府。由于这场交易发生的时刻正值英国、西藏、中国代表讨论西姆拉条约的签名事宜,而西姆拉条约则有可能宣布西藏处于中国的宗主权之下,并构成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因此,麦克马洪得出结论,最好还是征求中国人在一定程度上同意这条边界线。然而,阿萨姆喜马拉雅边界并不在西姆拉会议的议事日程上;英国人又不希望与中国人讨论他们认为与之无关的事宜。所以,要想获得中国代表批准一则他们一无所知的协约(3月24日和25日的英藏换文),而且英国代表并没有向中方代表正式提及该协约是何主题,这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但麦克马洪决定尝试一次。他使用的工具便是一幅草图,比例尺为1:3,800,000,在整个西姆拉会议上,他都不断地将边界绘制在这幅地图上。在这幅地图上,麦克马洪标出了他认为的内外藏正式分界线。“大”西藏的边界线,也就是即将被划分的这个区域,用红线标注出来。内外藏之间的边界线,也就是中国和自治西藏之间的边界线,用蓝线标注出来。由于在理论上,西姆拉会议只关注中藏边界问题,麦克马洪草图上的红线并不总是围绕着“大”西藏而定。这条线从最西北部的喀拉喀什河突兀地发端,到东南方向的达旺地区则戛然而止。从喀拉喀什河到伊苏拉齐山口上的缅藏中三地交界点,这条红线把西藏从中国分离开来;从伊苏拉齐山口到达旺地区,红线又把西藏从英属印度区分开来。如果中国人同意了地图上标明的内外藏划分界限,那么,他们将会发现自己也接受了麦克马洪线;当然,除非他们能及时地发现麦克马洪线的目的是什么,从而提出移除伊苏拉齐山口—达旺地区之间的红线。和那些在当前中印边界争端中为印度辩护的普通印度外交官一样,陈贻范很可能也不擅长查看地图,他似乎并没有觉察出麦克马洪所耍的手腕;抑或,即便他真的发现了什么问题,也慑于英国代表团的压倒性优势而不敢抗议。正如预期的那样,他在1914年4月27日,在画有麦克马洪线的地图上进行了草签,这是中国人永远无法忘却的行为。
人们或许会问:为什么明明有机会,印度政府却没有争取划定整个西藏的边界?划界时为什么要留下达旺地区和喀拉喀什河之间的这块地区?红线之所以终止在达旺地区和喀拉喀什河边,主要有以下因素。第一,正如我们已经提到,印度政府并不希望再发起一轮关于划定尼藏和缅藏边界的谈判。尼藏边界和缅藏边界的划定都不会令人满意。其划定都需要准备大量的原始资料以供讨论,而如果不邀请相关国家的代表参与谈判,划定这两处边界都将是空谈。麦克马洪自然不愿意邀请尼泊尔和不丹参与到西姆拉会议中来,而1890年条约已经规定了锡—藏边界,因而也不必在西姆拉会议中再讨论这一话题。对于尼泊尔以西的大片印藏边界,只存在一些小问题上的争端,如什布奇山口附近地区,以及沿着现在的东旁遮普、喜马偕尔邦、北方邦等边界上的小争端,以及沿着西藏—拉达克边界上的小争端,如在库尔纳克、尼苏和碟木绰克等地。无疑,和伦钦夏扎详细讨论这些话题,可能不但会消耗掉大量时间,而且还一无所获。[29]此外,额外延长麦克马洪地图上的红线,必然会把英藏边界和中藏边界一样带到西姆拉会议议程上,而一旦会议开始讨论英国边界,阿萨姆喜马拉雅地区的麦克马洪线就不可能不引起注意。
近些年来,对于中国代表在西姆拉会议期间针对麦克马洪线以南提出的特殊领土主权声明的事实,竟然没有得到回应,这的确令人感到吃惊。1914年1月12日,当陈贻范阐明中方观点时曾提出,赵尔丰在1911年就将察隅的部分山地部族纳入了满清王朝的保护之下,而察隅的某些山地部族似乎覆盖了阿波尔人、米里人和米什米人的居住区。[30]在西姆拉会议的不同阶段,每当陈贻范在草图上画出他对内外藏边界线的理解时,中国边界线总是从察隅河的叶普河支流所在地瓦弄以南开始,向西与察隅河-德赖河交汇点的察隅河接壤,随后向西北穿过迪邦河谷,在麦克马洪线稍南端与底杭河-香河交汇。[31]从底杭河-香河开始,陈贻范所绘制的边界线继续向西北直达西藏江达,中国代表团坚持认为江达是位于中藏边界线上的一个镇。当陈贻范将内外藏边界线从江达后撤到萨尔温江(中国称为怒江)时,可以说他放弃了中国对阿萨姆喜马拉雅地区的所有主权声明。然而,西姆拉会议并没有接受陈贻范作出的这一让步,由此,中国人又重返他们先前声称的江达边界线,该边界线包含了阿萨姆部族山区。那么,既然西姆拉条约所附地图上的麦克马洪线与陈贻范本人所表达的边界线相冲突,陈贻范为什么还要在西姆拉条约所附地图上草签呢?可能有两个原因。第一,陈贻范一定意识到他的行为会遭到自己政府的斥责,因而他草签的内容是什么并不重要。第二,鉴于他同意草签之前面临的巨大道德压力,他极有可能没有过多考虑西姆拉条约所附地图上标注出西藏边界红线的小小附加物,而这条红线后来竟成为著名的麦克马洪线。
毫无疑问,在征求中国代表同意其边界线的过程中,麦克马洪并没有采取明确坦率、直截了当的方式。如果中国代表真的在西姆拉条约上签字,他们必然发现很难否认阿萨姆喜马拉雅地区印藏边界的划定在某种程度上具有一定合法性。然而,中国代表并没有正式签字,截止1929年,当3月24日-25日的英藏换文首次公之于众时——如果不是在更早时候公布的话——中国政府一定发现自己成为英国骗局的牺牲品,这也就充分解释了为什么中国人痛恨“非法的”麦克马洪线的原因。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中国人似乎从来没有搞清楚,麦克马洪事实上也在试图哄骗中方代表接受拉达克最东北部的大片领土之地位发生的变化,即现在众所周知的阿克赛钦。20世纪50年代,当中国人提出对阿克赛钦拥有主权时,他们似乎没有意识到,正是西姆拉条约所附的那幅地图暗示着中国人接受了麦克马洪线,同样也暗示着英国人(由此导致印度)接受西藏(由此导致中国)至少拥有阿克赛钦的部分领土。
1899年3月,克劳德·麦克唐纳爵士给清朝总理衙门提交了一份照会,承认了中国对阿克赛钦部分领土拥有的权利。[32]中国人从来没有正式回复过这份照会,但在20世纪最初10年间,英国人认为自己受到了这份照会的约束。随着俄国人越来越有可能占领新疆,贫瘠荒芜、渺无人烟的阿克赛钦高原获得了英国战略家的青睐。他们认为,作为潜在的俄国领土和从喀喇昆仑山脉通往印度平原的山口间的缓冲区,该地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因此,印度政府认为应当针对阿克赛钦采取一些措施。根据1899年的照会,很难说阿克赛钦是属于英国的领土。那么,为什么不把这片土地变成西藏人的呢?无论如何,这是1907年印度外交部门的路易斯·戴恩爵士的看法。[33]1912年,新疆局势更加严峻,哈定勋爵敦促:在英国承认俄国人保护或吞并新疆作为重新调整喀什噶里亚—克什米尔边界的先决条件的过程中,阿克赛钦务必不可落入俄国人的手中。西姆拉会议为达到这一目的提供了绝好的机会。麦克马洪一定是看到了这种可能性。在他的地图上,这条红线向西北方向直指阿克赛钦侧翼的喀拉喀什河北岸。由于红线被定义为“西藏的边界线”,而西藏又位于红线以南,因而便得出结论:至少阿克赛钦的部分领土是属于西藏的。这一观点很难用语言来表达。或许,通过地图最容易理解其含义。第20幅地图表明了西姆拉条约所附图上的红线。第22幅地图标明1899年-1947年间阿克赛钦边界发生的浮动变化。第21幅地图则标明西姆拉条约所附地图上的红线最西端末端遵循着当前印度宣称的阿克赛钦地区部分边界线。[34]
印度政府积极捍卫了麦克马洪线的有效性,主要基于以下三点理由[35]:第一,可以认为,这条特殊的边界线的确是传统上确立的印藏边界线,时间可以追溯到远古。本书前文已阐述了这一说法的弱点,此处毋庸赘述。第二,1914年3月24日和25日的英藏换文是国际法中合法有效的协议。这种观点几乎没有什么说服力。通过1906年中英条约,英国承认中国有权管理西藏的外交关系,也承认英国人只能通过中国政府与西藏政府进行谈判,因而这一点超出了拉萨条约和贸易协定的范围。西姆拉会议之所以召开,就是为了搞清楚英藏关系的本质能否获得修订;而当英藏双方交换了关于麦克马洪线的换文时,西姆拉会议并没能产生各方一致同意的草约,更不必说各方签字盖章的正式协议。毫无疑问,1914年3月,英国根本没有条约权与西藏代表签署双方协议。第三,无论3月24日和25日换文的有效期如何,麦克马洪线得到了中方代表陈贻范的确认,4月27日,陈贻范在西姆拉草约及其所附地图上进行了草签(initialled)。印度观察家及其拥趸者,例如奥拉夫·卡罗爵士,继续指出,尽管陈贻范称自己草签了地图,但他实际上是正式签署了地图。[36]原始地图就是证据。但这是真正利用语义学搞的恶作剧。草签是一个技术术语,只有外交官才理解其含义;从外交的角度讲,陈贻范的确是草签了条约。他对西姆拉草约和所附地图的草签行为,很快遭到了中国政府的驳斥和否认,正如陈贻范警告麦克马洪的那样。很难从国际法上看出这些文件的有效性。印度政府自然对西姆拉条约不抱任何幻想,在西姆拉会议结束后不久写给查尔斯·贝尔的信中,印度政府指出,“中国政府没有在西姆拉条约上签字,俄国政府也没有承认西姆拉条约,因此,到目前为止,这个条约是无效的。”[37]中国代表从未签字,而俄国人又不接受,由此可推测西姆拉条约始终是无效的。
萨佐诺夫始终了解麦克马洪线谈判的一般性质,但必然不会有人告诉他该谈判还涉及割让西藏领土。尽管情况颇为复杂,又具有一定误导性,而且近些年的言论也有互相矛盾之处,但和春丕谷一样,直至1914年,色拉山以北的达旺地区都是西藏领土这一点确信无疑;达旺地区由西藏官员错那宗本治理,向达赖喇嘛政府的财政部门纳税。色拉山以南地区虽然没那么清晰,但即便如此,西藏在该地的主权领属仍然十分有力。通过麦克马洪线纳入到英属印度的达旺领土要比春丕谷的面积大得多。若吞并达旺地区的消息公之于众,萨佐诺夫必然不会接受,正如他反对英国重新占领春丕谷。因此,印度政府占领达旺地区的行为,无疑完全忽略了1907年的英俄协定。格雷和克鲁不可能完全了解阿萨姆喜马拉雅地区真正发生了什么。他们似乎没有机会研究贝尔和伦钦夏扎关于达旺地区的谈判备忘录,也无法详细地了解西藏在麦克马洪线以南的影响力达到了什么程度。正如我们所见,自阿波尔远征以来,印度政府很少公开阿萨姆喜马拉雅地区发生的情况。议会成员也无法弄清楚,英国究竟是打算扩张领土,还是仅仅巩固现有领土。如果有关达旺地区的真相在1914年被公之于众,那么,格雷完全有可能将相关情况向萨佐诺夫和盘托出,由此强化俄国在阿富汗和其他地区的立场。在这种情况下,伦敦甚至极有可能决定将达旺地区置于大英帝国领土范围之外。
从西藏人那里获取麦克马洪线之后,麦克马洪自然迫切地想看到这条边界线不再仅仅是一种抽象的制图表达。在他的《最终备忘录》中,麦克马洪敦促印度政府采取措施开通阿萨姆部族山区的贸易路线,即穿越达旺地区直达底杭河—香河与察隅河谷的贸易路线。或许,他有些怀疑这条商贸线路是否能给英属印度带来巨大的商业利润,但他必然知晓这些商贸线路会给英国官员制造机会,令其沿着麦克马洪线拜访那些偏远地区,同时确保在阿波尔地区设置“商贸”站点的既定政策会得到更广泛的实施。麦克马洪认为,在不久的将来,亟须一位英国官员前往达旺地区,以确保达旺纳入英国势力范围后出现的情况不会有损英国的利益。有关达旺,还有很多需要学习了解的地方。印度政府必须和统治该地的达旺寺建立联系;必须采取措施将门巴人及其东部的非佛教徒部族之间的冲突和矛盾降到最低。当然,麦克马洪并没有建议将达旺地区直接纳入英国统辖之下,这必然会违背3月24日和25日的英藏互换照会以及印度事务部宣称的“松散的政治控制”政策之基本精神。麦克马洪所要求的不过是派遣一位“在部族地区有治理经验的”英国官员,携带“一位对西藏事务有丰富经验的本地助手和一位本地的医生助理”,对达旺地区进行一次试探性的访问,以便为将来的政策制定等提供基础。当麦克马洪提出这一要求时,印度政府实际上已经根据以上原则进行了实践,但麦克马洪却特意没有在他的《最终备忘录》中提及。
在1913-1914年的寒冬,东北边疆西段政务官内维尔上尉率领令人生畏的1000余人组成的队伍,深入达旺地区和苏班西里河谷之间的阿卡山区。在1914年3月底,与达夫拉部族发生武装冲突之后,内维尔及其同伴、医生肯尼迪上尉一起前往达旺地区。3月23日,他们抵达德让宗。4月1日,抵达达旺镇,并与掌管当地政府的西藏官员,两位错那宗宗本会面。内维尔确信,达旺地区,至少“色拉山以北地区”属于西藏政府,位于错那管辖范围内。色拉山以南,除了森格宗村之外,都在拉萨哲蚌寺的子寺、拥有500多名僧人的达旺寺的统辖范围内。达旺僧俗官员怀疑内维尔之行标志着英国人对阿萨姆喜马拉雅部分地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此之前,该地区始终未曾引起印度政府的真正关注。1913年,莫希德和贝利成为拜访达旺地区的第一批欧洲人。西藏官员似乎十分迫切地想和这些新来的英国人讨论政治事宜。但除了礼貌性的问候之外,内维尔拒绝讨论政治问题。尽管此时至少在理论上达旺地区已经属于英国一周多,但内维尔并没有试图通知达旺地区和错那宗政府这一事实。事实上,直到20世纪30年代之前,没有一个印度政府官员提到英国占领了达旺地区。返回印度之后,内维尔敦促印度政府在达旺设立长期性的英国代表,但他的观点甚至都没有被正式传递给西姆拉。[38]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印度政府并不打算考虑扩大自己在偏远边界地区的责任。[39]因此,在麦克马洪线诞生之后,印度政府并没有立即采取任何行动向伦钦夏扎及西藏政府表明,他们认为达旺地区虽理论上属于英国,但实际上仍是西藏政府领土的观点是错误的。英国的不作为也同样被拉萨理解为:西藏政府在阿萨姆喜马拉雅的某些地区也拥有领土主权。
中方拒绝承认麦克马洪线这一事实,已在国民党时代的中国地图中得到明确体现;而中方拒不承认麦克马洪线并非由于这条边界线涉及英国吞并西藏(从而也就是中国的)大片领土,而是由于中方坚信英国政府和西藏政府根本没有讨论麦克马洪线的权利。无论麦克马洪线经过哪些地方,只要在西姆拉会议上发现了其条约基础,中国政府就自然拒绝接受。这一点也正是尼赫鲁先生及其顾问似乎始终未能理解的,而他们本应更加理解这一点。作为一条边界线,一旦麦克马洪暗示的意思不存在,这条1914年的边界线也就备受诟病。印度政府吞并达旺地区很可能是个错误。从过去多年试图获得西藏的合作这一点来看,如果麦克马洪线保留在色拉山这条边界线,会产生更好的效果。将边界线从叶普河向北推进到察隅河上的迪曲,也是非常糟糕的建议。毕竟,中国人在满清时代和中华民国期间都声明对叶普河边界线拥有主权,他们还在叶普河设立了边界标志,等于公开宣布了中国的主权范围界限;麦克马洪对于这一点拒不承认,也不做评价,或许太过愚蠢。奥卡拉汉将中国人竖立在叶普河的边界标志拔除的行为,很难说是态度友好的行为。从某种角度来看,这其实也是愚不可及的行为,因为这相当于毁掉了中国人认为他们的边界线最北抵达过老外线的证据。沿着麦克马洪线的其他地方,例如在苏班西里河,在香河—底杭河(或雅鲁藏布江—布拉马普特拉河),迪邦河和塔伦河等,英国人在选择其边界线时都表现出一定的克制。
一旦认为非佛教徒山地部族,如米什米人,阿波尔人,米里人,阿卡人,达夫拉人等等都不是西藏人,从法律等任何重要的角度来看,也从未是西藏臣民,那么,除了达旺地区和察隅河之外,麦克马洪线就为西藏领土和非西藏人居住处提供了一条合理的边界线。不可避免的是,麦克马洪线以南居住着一些西藏人,正如在锡约尔河上游和香河河谷,一些非藏族族群生活在麦克马洪线以北、雅鲁藏布江上的白玛科钦。在实践中,几乎不可能设计出一条完美的民族边界线。如果真正尝试解决英中边界争端,或者,如果阿萨姆边界问题被提交由他人仲裁,那么,除了达旺地区和察隅河之外,结果很有可能是和麦克马洪线非常相似的一条边界线。值得一提的是,麦克马洪线本质上还是一条民族划分线,将西藏人和非西藏人分开。只有在偏离了民族划分原则的达旺地区和察隅河地区,出于战略考虑的原因,这条边界线遵循了当地的地理特征。除了这两个地区,麦克马洪线背后的争论实际上并非围绕传统的印度边界是否遵循了喜马拉雅山脊原则,而是非藏族或非佛教徒的阿萨姆山区部族,若不在西藏主权统治之下,就应被合并到印度帝国。
当前的印度政府没有能看到这一点,或者说拒绝看到这一点。印度政府重申:阿萨姆喜马拉雅地区的传统边界线也是遵循喜马拉雅山脉分水岭的边界线。印度政府宣称,麦克马洪线是一条分水岭边界线。实际上,分水岭原则根本没有在1914年3月24日和25日的英藏换文中提过。该原则只出现在1890年锡金—西藏条约里的中印边界条约语言中,而且只有很短的一段边界是根据两条河系之间的分水岭划分的,但这并没有试图在整个喜马拉雅边界上创造出一条分水岭边界线原则。[40]正如我们所见,麦克马洪线并没有遵循流入孟加拉湾和阿拉伯海,以及流入中亚沙漠、中国和东南亚的河流之间的分水岭。我们对麦克马洪线作出的唯一大体上的地理学描述只能是这样:这是一条或多或少遵循了阿萨姆喜马拉雅山脉最高峰走向的边界线,这些最高山峰则通过分水岭连在一起。然而,这一描述是绝对不够全面的。不少最高峰,例如雅鲁藏布江上的南迦巴瓦峰,就位于麦克马洪线以北。分水岭所遵循的一切都是可以避免的。正如我们所见,印度政府不得不在若干有可能的分水岭体系中作出选择。有时候,麦克马洪线完全偏离了分水岭概念,而是穿越了一条主要河流,诸如娘江河,苏班西里河,香河—底杭河,察隅河和塔伦河等。此处的分水岭,与其说是一条普遍的制定边界线的原则,不如说是一个将居住在山谷里的人们区分开来的简便方法。
[注释及参考文献]
[1]节译自《麦克马洪线》原书(The Mcmahon Line:A Study in the Relations between India,China and Tibet,1904-1914,by⁃Alastair Lamb,London:Routledge&Kegan Paul,Toronto: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1966)第530-566页。
[2]《白皮书,二》,第40页,尼赫鲁致函周恩来,1959年9月26日。
[3]戈帕拉查里,《中印边界问题》,《国际研究》,V,nos.1-2,1963年7月-10月,第42页。也可参见查克拉瓦蒂著:《印度对华政策》,布鲁明顿,印第安纳,1962年,第137页。
[4]19世纪70年代,格兰汉姆少校曾提出划分山脚边界线的建议。参见《阿萨姆喜马拉雅边界问题的背景》。
[5]PEF 1910/14,第3057/12号文件,印度总参谋部关于东北边界的备忘录,1912年6月1日。
[6]PEF 1913/18,第4692/13号文件,麦克马洪备忘录,1913年10月28日。
[7]PEF 1913/18,第4790/13号文件,总督致函印度事务大臣,1913年11月21日。
[8]PEF 1913/19,第461/14号文件,麦克马洪致函赫泽尔,1914年1月22日。
[9]PEF 1913/19,第893/14号文件,麦克马洪致函赫泽尔,1914年2月19日。
[10]FO 535/16,第449号文件,总督致函印度事务大臣,1913年11月26日。
[11]贝利,《报告》,如前所引,第13-14页。
[12]《备忘录》。
[13]贝利,《报告》,如前所引,第10-12页。也可参见本书第十七章《阿萨姆喜马拉雅边界问题的背景》。
[14]FO 535/16,第422号文件,阿萨姆致函印度,1913年10月17日。也可参见贝利:《报告》,如前所引。
[15]贝利:《报告》,如前所引;贝利:《无护照西藏行》,如前所引;冈特著:《米什米探险调查分队报告,1912-1913》,参见伯拉德著:《印度调查报告,四》,加尔各答,1914年。
[16]FO 371/1613,第53461号文件,印度事务部致函英国外交部,1913年11月24日。
[17]FO 535/16,第422号文件,阿萨姆致函印度,1913年9月17日。
[18]PEF 1913/18,第4790/13号文件,总督致函印度事务大臣,1913年11月21日。
[19]PEF 1913/28,第1918/14号文件,奥卡拉汉旅行日记,1914年3月7日。
[20]PEF 1913/28,第1918/14号文件,奥卡拉汉旅行日记,1914年3月7日。
[21]里德:《阿萨姆边界》,如前所引,第250页。
[22]在威廉逊死后的阿萨姆喜马拉雅山脉地区探险期间,英国人开始将塔洛克山口(或曰迪普山口)视作英国领土的固定地点之一,印度的布拉马普特拉河系和缅甸的伊洛瓦底江流域之间分水岭的标志。然而,英国同时也将塔洛克山口或迪普山口视作从西藏通往缅甸最西北部的一个潜在入口处,如果中国人企图再次利用这个地方,印度政府就决心利用这个入口处拒绝中国人。印度政府下定这一决心的结果,便是令麦克马洪线沿着迪曲以北而行。这同样意味着,麦克马洪线实际上并没有沿着塔洛克山口或迪普山口的最高峰通过,而是遵循了向北几英里处的山脊。在1960年10月1日的中缅边界协定中,迪普山口被接受为真正的边界线,也是该边界线最西端的一个点(但中国人拒不承认这意味着迪普山口或塔洛克山口是中印缅三国交界处的一个点,当然,这原本意味着中国政府承认麦克马洪线的一部分为中印边界线)。对于新划定的中缅边界线设在塔洛克山口或迪普山口的决定,印度政府提出了若干次抗议。中国政府轻易驳回了这些抗议。参见《白皮书,五》,第20页,1960年12月30日印度政府备忘录。
[23]普理查德和沃特菲尔德合著:《1912-1913年东北边界……旅行报告》,西姆拉,1913年。也可参见,贝利:《中国,西藏,阿萨姆》,如前所引;普理查德:《从密支那经恩梅开江和康提垄到萨地亚》,《地理学期刊》,XLIII,1914年。
[24]PEF 1913/18,第4790/13号文件,总督致函印度事务大臣,1913年11月21日。
[25]这些换文第一次公开发表是1929年的《艾奇逊条约集》。至少这是一种普遍看法。然而,约翰·阿迪斯先生告诉我,1929年的《艾奇逊条约集》有两个版本,其中一个版本包含麦克马洪线换文和西姆拉条约的文本内容,另一个版本则不包含。阿迪斯先生认为,这些文本是1929年之后被插入《艾奇逊条约集》的,新版本的《艾奇逊条约集》替换了那些原来不包含这些文本内容的老版本《艾奇逊条约集》。阿迪斯先生在哈佛大学看到的一本1929年原版的《艾奇逊条约集》,不仅省略了麦克马洪线换文和西姆拉条约的文本,而且声明西姆拉会议没有产生有效的协约。修改后的版本,即在绝大多数英语图书馆中收藏的版本,则明显地暗示:麦克马洪线换文和7月的西姆拉协约,是符合国际法的协议。阿迪斯先生在他所著的《中印边界问题》一书中详细讨论了这一问题,该著作仅在1963年2月的哈佛大学国际问题中心中私下流传过。我非常感激阿迪斯先生寄来这本引人入胜的著作,同时还允许我在这里引用他的作品。
[26]我在英国外交部和印度事务部档案中找到的唯一记述麦克马洪线谈判的文献资料,便是麦克马洪1914年3月28日所写的备忘录。后来,他把这份备忘录合并到他的著作《备忘录》一书中。参见FO 535/17,第91号文件。这份文件对于贝尔和伦钦夏扎讨论期间真正发生的事件几乎没有任何记载。
[27]还有一个更早一些的地图版本,名为《印度东北边疆》,临时问题,印度总参谋部,SDO,第741号文件,早于现在英国外交部地图室馆藏的麦克马洪线地图,第17144号文件。这份文件日期为:1913年8月分第一页和第二页,1913年9月则分第三页和第四页(与麦克马洪线无关,包括东部西藏),而麦克马洪线地图标注的日期为1914年2月。
[28]FO 535/17,第91号文件,麦克马洪备忘录,1914年3月28日。
[29]在双方交换了关于麦克马洪线的照会之后,贝尔和伦钦夏扎似乎对印藏边界的其他部分做了一些讨论。参见印度外交部:《印度政府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关于边界问题的官方报告》,新德里,1961年,第84页。
[30]《中藏边界问题》中,北京,1940年,第17-18页。
[31]FO 371/1613,第53461号文件,印度事务部致函英国外交部,1913年11月24日;PEF 1913/18,第4768/13,麦克马洪备忘录,1913年11月6日;FO 371/1929,第6603号文件,印度事务部致函英国外交部,1914年2月12日。
[32]这份照会的文本,连同这段历史及结果,可以参见兰姆所著《中印边界》一书,如前所引。
[33]PEF 1912/82,第1227/07号文件,戴恩致函里奇,1907年4月3日。
[34]上述这些观点,以及这些地图中的第一部分草图,在兰姆参加1964年香港大学举办的亚洲历史大会上提交的名为《拉达克边界划定问题研究》的论文中有所提及。
[35]例如,参见K.K.Rao所著:《中印边界问题与国际法》,《国际比较法季刊》,1962年4月;格林:《中印边界争端的法律问题》,《中国季刊》,第三期,1960年7-9月。
[36]卡罗爵士:《中印问题》,《皇家中亚期刊》,1963年7-10月;卡罗爵士:《中印边界争端》,《亚洲评论》,1963年4月。
[37]FO 535/18,第44号文件。
[38]里德:《阿萨姆边疆》,如前所引,第283-287页;PEF 1913/28,第3461/14号文件,内维尔致函阿萨姆,1914年6月21日,附上访问达旺日记。
[39]在1914年的前九个月期间,阿萨姆政府数次建议在阿萨姆喜马拉雅地区沿着新划定的麦克马洪线积极采取行动。除了内维尔对达旺地区的想法之外,邓达斯也提出计划,将底杭河—香河一带的哨岗向前推进到Karko地区,计划沿着察隅河直至萨地亚的一条马路上的曼尼克赖建立一个哨岗。然而,1914年11月12日,哈定通知阿萨姆政府,他“已经决定不再根据你的建议采取任何措施,直至这场大战过去。”PEF 1913/28,第4745/14号文件,印度致函阿萨姆,1914年11月12日,印度事务部备忘录,1914年12月7日。
[40]1846和1847年克什米尔边界委员会中的英国成员似乎认为,分水岭原则在划分山区边界时颇有价值,但必须承认,在制造一条分水岭边界线——即今天著名的中印边界西段——的过程中,他们并没有获得多大成功。参见BC⁃CA,第81页。
[责任编辑陈立明]
[校对梁成秀]
D823
A
1003-8388(2015)06-0037-12
2015-10-28
梁俊艳(1978-),女,新疆阜康人,现为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清代西藏历史,西藏近现代史,西藏与英国关系史。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特别委托项目子课题“《麦克马洪线》的翻译”(项目号:XZ1219)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