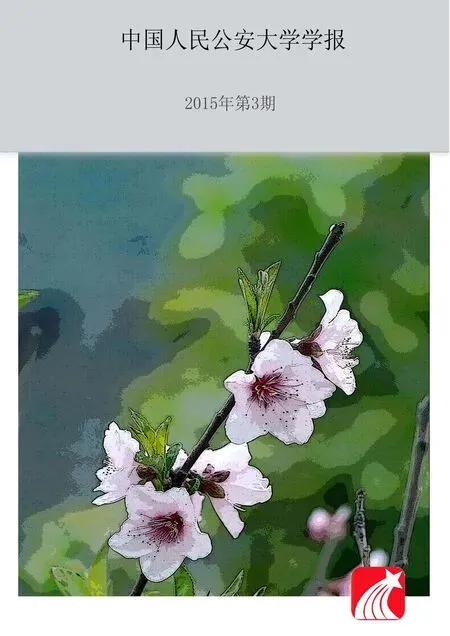基于SAFE模型框架的危机谈判阶段性策略分析
2015-02-17于洋
于 洋
(广东警官学院警务指挥战术系, 广东广州 510230)
基于SAFE模型框架的危机谈判阶段性策略分析
于洋
(广东警官学院警务指挥战术系, 广东广州510230)
摘要危机谈判作为警务执法单位在处置应急事件中唯一的非武力手段,历经近半个世纪的发展,目前已经成为各国执法单位在危机事件处置中的首选方案。危机谈判模型的发展长期以来引领且主导警务谈判的发展方向。以目前国际警界主流的SAFE谈判模型框架为理论基点与基本分析工具,尝试分析危机谈判不同情势下的阶段性谈判策略,期望利用SAFE框架构建从情绪控制——良好关系搭建——实质性要求分析与解决方案设计的实用性谈判模型,从而为国内危机谈判专业的发展提供有益借鉴。
关键词危机谈判; 谈判模型; 阶段性策略
0引言
从二战结束至20世纪70年代前夕,国际社会在应对劫持、绑架、恐怖活动等诸多危机事件中主流的理念与处置方法几近趋同:以暴制暴的处置手段成为了主导[1]。在历经包括1972年“慕尼黑人质惨案”以及1976年“法航班机事件”等一系列重大人员伤亡案例后,各国警队开始认真思考更加有效和通过和平方式处理危机事件的方法,由此执法成本较低的危机谈判应运而生*在回顾危机谈判在全球警界发展历程中,“慕尼黑”劫持人质事件应该是最具代表的事件之一:1972年在西德慕尼黑奥运会上发生了巴勒斯坦“黑九月”成员在奥运村内劫持以色列运动员及教练员的恶性劫持人质事件。该事件发生后持续了16小时。当恐怖分子的要求被拒绝后,警方以武力强攻的方式解救人质。令人遗憾的是,该事件以10名恐怖分子、全部11名人质和1名警察死亡而告终。。美国联邦调查学院(FBI Academy)设立了全球范围内最早的危机干预小组Crisis Intervention Team(简称CIT),随后法国、英国、澳大利亚、以色列以及中国香港警务处等执法单位纷纷成立专业的危机谈判机构,在随后近半个世纪的多项危机事件处置中,警方谈判小组在有效赢得时间、收集情报,确保当事人安全乃至最终通过和平方式解决争端等多项功能中发挥出重大作用,由此谈判成为了危机事件处置不可或缺的重要手段[2]。
危机谈判在近半个世纪的发展过程中,学界中众多学者也力图通过心理学以及行为科学等领域的科学研究推动实战的发展前行。其中谈判模型的发展在引领警务危机谈判工作中备受瞩目,目前国际警界主流的危机谈判模型可归纳为:
(1)“原则型谈判”模型(Principled Negotiation)
“原则型谈判”模型由哈佛大学荣誉教授Fisher在上世纪80年代最先提出,是商务谈判早期发展的重要模型之一,同时在上世纪80年代早期被引入巴以冲突的戴维营谈判之中。“原则型谈判”模型专注基于利益基础而主导的问题解决方式,强调双方利益的最大化。模型设定初始谈判架构,双方在谈判前应充分了解谈判原则与框架,在谈判过程中利用已有原则对于当前问题进行方案的制定与修正。
(2)“行为阶梯影响模型”理论(Behavioral Influence Stairway Model)
“行为阶梯影响模型”理论(简称BISM模型)最早由FBI著名谈判专家Noesner 在上世纪90年代初提出,后由Vecchi等专家在随后的近20年中年得以完善,该理论借鉴美国联邦调查局(FBI)以及美国纽约警察局(NYPD)谈判组在多次重要的劫持人质以及反恐谈判中的经验推导得出[3]。BISM模型理论强调危机谈判发展的阶梯式推进程序,通过积极聆听—同理共情—提供支持—施加影响—行为改变的有效框架,推进由心理发展以及言语沟通而导致的重要性行为改变。BISM是目前美国各城市警署谈判组较为普及的危机谈判模型之一。
(3)“SAFE”模型理论(S.A.F.E. Model of Crisis Negotiation)
SAFE 谈判模型最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由美国华盛顿谈判专家Hammer 与 Rogan 共同提出(Hammer, 1997, 1999; Rogan, 1999; Rogan, Hammer,& Van Zandt, 1997)。作为华盛顿地区著名的谈判专家,Hammer 在长达十余年的警务危机谈判过程中探索出与事件谈判进程中影响危机升级与危机指数下降相关度最高的四项基本因素:自尊与情面(Face);情绪与情感(Emotion);关系(Relationship);实质性要求(Substantive Demands)*SAFE模型命名最初由Face,Emotion,Relatinship与Substantive Demands 4项因素的英文首字母命名,即为FIRE。但由于此缩写与英文Fire(开火、射击)同义,为避免引起歧义,故使用Attunement一词替换Relationship, 同样代表协调性关系之意,由此定义为SAFE模型。。通过对于四项重要因素在不同类型谈判以及不同谈判阶段的状态分析,从而进行针对性策略的制定与修正。
SAFE谈判模型设计基点在于融合行为科学研究成果于危机事件谈判实践之中[2],在更加关注解决实质性要求的基础上提出了依据不同条件而设计的针对性策略。SAFE 谈判模型在将近20年的实践发展中不断完善,在理论发展的同时不断通过危机谈判实战而进行印证与运用,在众多复杂的劫持人质乃至恐怖主义谈判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目前已经成为全美乃至世界范围内最主流的危机谈判模型之一[4]。
1基于SAFE模型架构的阶段性策略分析
在研究FBI谈判组,美国洛杉矶警察局(LAPD)谈判组以及香港警务处谈判小组(PNC)多年的谈判实践及训练经验,Hammer与Vecchi等专家认为在危机事件谈判发展过程中,谈判通常会呈现出初期发展—高原期—尾声阶段三大发展阶段[5],如图1所示,各发展阶段应根据危机指标与当事人情绪状态制定不同的谈判目标与策略选择。
在危机谈判发展的初期阶段,由于情报有限,现场情况复杂,劫匪、人质处于极度紧张状态等诸多因素,危机指标通常高企,谈判组的目标在于有效缓解当事人情绪,帮助其恢复平静心态,在此阶段着重处理模型中自尊(Face)与情绪(Emotion)要素;而随着谈判的介入,通过谈判技巧的使用与警方整体策略的实施,可以有效缓解多方的紧张状态,搭建沟通平台,使得劫匪进入相对理性的沟通轨道,在高原期谈判组需将重点放在良好的合作性关系(Attunement)的建立与巩固上;进入尾声阶段,基于前期信任与合作性关系的不断发展,危机指标会持续下降,双方重点都应置于实质性要求(Substantive Demands)的处理与条件的交换,从而形成双方得益的解决方案。而如果通过武力方式解决危机,则危机指标无疑会短时内高企,且其危机的状态由于相对缺乏回旋而难于控制。而整个SAFE模型的运行过程应遵循识别(Identify)—匹配(Match)—转化(Shift)的基本程序,即首先应识别谈判对象的情绪状态处于事件发展的何种阶段,由此采取相对匹配的模型策略。在一个阶段发展到已经实现阶段性目标时,逐步进行转化,将谈判引入下一个更趋近于和平解决的阶段。

图1 危机谈判发展趋势与SAFE模型策略分析
1.1 自尊、情绪型框架的阶段性策略
1.1.1自尊型框架的阶段策略
自尊(Face)一词在不同学科领域定义广泛,在危机谈判领域中各国执法单位通常采用由心理学专家Goffman提出的司法心理学解释:在特殊关系中个人有效维护自身正面的社会价值(Noesner & Webster, 1997; Rogan, 1997)。通俗来讲,自尊就是个体希望得到的对于自己的正面社会评价与良好形象。在谈判介入危机事件的初段,谈判对象通常处于自尊框架之中,即碍于情面而不愿与警方接触,同时由于自尊在谈判实践中还通常表现为自我认同(Individual Identity)与社会认同(Social group identity)两个方面,由此有效地树立当事人的个体价值认同与维护其社会价值认同是SAFE模型中处理自尊的有效策略选择。
SAFE模型在经过多年分析美国联邦调查局(FBI)HOBAS(人质谈判统计数据库)的基础上总结出谈判对象在对话过程中四类最主要的自尊框架内的反应,以及警方谈判组有效应对的策略方法[6],如表1所示。

表1 自尊行为反应与应对策略
1.1.2情绪型框架的阶段性策略
众多研究表明,行为在危机情况下更易于受到包括情感在内的非理性因素支配。有效处理如愤怒、绝望、内疚、激动等众多负面情绪被认为是危机谈判在初段发展的首要目标。在谈判小组介入的初段,双方由于陌生或时间短暂,几乎难以建立信任,谈判对象在非信任的前提下更无法接受警方的建议,由此谈判员唯一可以做的就是表示对于事件的关注,对于当事人的关怀,逐渐引导负面情绪的转化,从而为下一步的沟通建立基础[4]。
危机事件中的当事人通常是在长期被忽视与缺乏有效聆听者的前提下而产生通过极端方式解决问题的非理性意识。由此,积极聆听式的谈判策略与沟通方式是SAFE模型在谈判发展初段以及高原期重要的缓解负面情绪以及帮助当事人回归理性的策略选择,通过体现关心与理解的积极聆听式沟通技巧,逐步建立双方互信,在理性的前提下给予当事人解决问题的最佳建议,当前各国执法单位普遍使用的主流聆听技巧包括[7]:
开放式问题(OQ):通过询问个人基本情况、背景信息等开放式问题(你从哪里来、怎么称呼您)收集更多情报信息,在全面了解当事人背景的情况下进行针对性沟通。
标签情绪(EL):像贴标签一样,使用婉转言语为当事人目前的不良情绪做出表示,使其明白谈判员可以理解其目前的心情与处境,从而建立信任。
重言复述(Mirroring):通过重复对方的话语来表示对于对方问题的关心与关切,有效表示警方愿意倾听与解决问题的诚意。
微量鼓励(ME):给与适当的鼓励,帮助当事人恢复理性,建立重新振作的勇气与信心。
1.2 关系型框架的阶段性策略
关系(Relationship/Attunement)通常指人或事物之间某种性质的联系或相互作用与影响的状态(J.P. Folger, M.S. Poole,2009)。正如谈判专家Hammer指出:“危机事件中谈判双方相互作用的行为或言语表现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相互关系的影响——即对于对方行为的评价或亲疏远近的关系”。由此,关系的发展成为了未来谈判走向与发展的重要决定性因素之一。从本质上讲,危机事件谈判也正是发展和利用了一种相对“临时性”(谈判双方在绝大多数情况下相互都不认识)且有效的合作框架关系才得以通过和平方式解决问题。
1.2.1合作关系的言语性策略
在SAFE模型框架用于全球危机谈判发展的几十年内,各国谈判专家已经总结出若干行之有效的合作性谈判言语策略(McMains,2006):
继续利用积极聆听的谈判技巧,如微量鼓励、知情解意等,在前期信任的基础上不断缩短心理距离,拉近相互关系。
将谈判话题逐步转向面向未来发展的可能性方面,而非停留在容易延续目前负面情绪的话题之中,从而给予双方更多的参与讨论与设计解决方案的机会与可能。
继续表达对于谈判对象的关心与情绪状态的关注,甚至表达对于谈判对象所关注的人或事物(如谈判对象需要会见自己的亲属或利害关系人等)的关注,从而让对方感受到警方愿意帮助其解决实际问题的意愿与诚意。
尽可能寻找与谈判对象相似或相同的经历,如相同的病痛经历、从业经历、情感经历、家庭状况等,从而使得双方更容易建立同理心,获得认同而进一步强化合作框架。
1.2.2合作关系的行为性强化
(1)谈判员的肢体语言。谈判员(特别是近距离的面对面谈判中)肢体动作的表现所传递的合作性意愿对于建立互信与构建良好的合作关系至关重要。保持一定的安全距离,避免给与对方压迫感。同时应注意展示双手,防止对方猜疑警方的攻击行为。在此基础上尽可能展现亲和性动作与自信的姿态,逐步缩短双方的心理距离。
(2)谈判现场控制与基本要求的实现。谈判初段中可适当展示警力,其目的是为了降低谈判对象使用武力对抗或企图强行逃脱的心理预期。在谈判的中期,应尽可能减少着装警察出现的次数,创造安静与平和的对话环境,帮助其恢复理性,引导谈判对象倾诉、甚至情绪宣泄。在此过程中应尽量满足谈判对象如饮水、饮食、取暖等基本生理需要,展示警方的诚意,强化合作关系。
(3)第三方中介人使用(Third-Party Intermediaries)。危机谈判中合作关系的建立并非一定直接地通过谈判双方开展。谈判过程中当事人通常会向警方提出需要会见家人、亲属、朋友、利害关系人甚至媒体记者、相关领导等第三方关系人。利用第三方中介人帮助建立谈判双方的合作关系已经成为目前谈判专业领域的通用方法。警方通常会寻找与谈判对象关系良好(评估关系人在现场不会引起当事人的不良情绪)的第三方中介人介入谈判,且通话前应进行全面的安排与过滤,如话题的内容、情绪控制的方法、意外发生时的撤离方式等。
2SAFE模型的实质性要求框架分析
危机事件的谈判在经历了自尊与情绪阶段、合作关系阶段后,危机指标逐步降低并趋于平缓,谈判对象在情绪的宣泄后通常会进入理性考虑现实问题或当前危机状态有效解决的思考通道。在SAFE模型的预期中,谈判工作也随之向实质性要求(Substantive Demands)解决框架转移并试图在帮助当事人有效解决实质性要求的前提下促使双方达成可以接受的可选方案,从而通过和平方式结束现实危机。
2.1 实质性要求的类型分析
2.1.1生理性要求与心理性需求
上世纪70年代早期FBI谈判专家Roloff 与Jordan等人将危机谈判中谈判对象所提要求分为生理性要求与心理性要求两大类别。生理性要求主要包括警方所提供的如饮水、饮食、取暖休息等基本的人体生理日常需要,且通常认为这些要求的实现可有效建立双方信任,搭建良好的合作性问题解决框架。心理性需求主要指为挽回当前危机状态而满足谈判对象心理上慰藉的要求,包括与家人沟通、挽回颜面以及获得谅解等等,且心理性需求通常被认为是最难实现也是危机事件得以和平解决的最重要因素。
2.1.2实质性要求与非实质性要求(要求本身与内在需要的关系)
在危机谈判进展的过程中,谈判对象会在不定时提出若干种不同的要求,而要求的实质性与非实质性的区别我们通常以诉求言语表达形式与诉求的内在利益为区分点。以劫匪在车内劫持人质为例,劫匪可能会提出需要大量现金与一件防弹衣,此时警方应考虑劫匪的真实意图与利益所在:劫匪在封闭空间内几乎没有使用现金的可能,而同时又需要一件防弹衣,那么综合考虑此时劫匪现实利益所在应是对于自身安全的迫切考量。由此提供安全保障,如减少着装警察的出现、避免距离压迫感、明确警方在非危急时刻不会采取武力等谈判策略,可以切实满足谈判对象的真实需求,而并非通过提供现金来满足安全需要。
2.1.3可满足性要求与非满足性要求
从警方的执法工作机制与策略选择分析,谈判对象所提要求通常可分为可满足性与非满足性要求。可满足性要求主要指在法律与工作职责允许的框架之内,谈判员可以实现的要求,如生理需要、会见家人、传达诉求等有利于谈判向和平解决方向发展的要求。而非满足性要求通常指违反法律,如提供武器、提供车辆逃逸等要求,或提供酒精饮品等违反职责规定或法庭举证阶段中容易引起严重法律责任的要求。当然可满足与非满足要求间并无绝对界限,如要求会见媒体、会见领导等要求应依据是否有利于谈判发展的原则具体考量与分析。
2.2 实质性要求处理的阶段性策略
2.2.1实质性要求的价值权衡
在实质性要求处理的过程中,要求能否满足,何时满足以及满足到怎样的程度是警方在谈判后期遇到的最大挑战,实质性条件交换的效果在众多危机谈判中可以影响和左右事件结果。而在所有考量过程中,价值的权衡是首先需要作出的重要决定。在法律允许框架中(除去如提供武器、弹药、伤害人质等法律明文规定不可以采取的行动外),哪些条件可以满足、哪些可以通过谈判而进行条件交换,从警方视角分析,警方满足此条件(如会见媒体)所带来的正面效应应大于其可能产生的负面作用,且负面后果是警方可控范畴之内的。如帮助谈判对象会见媒体可以取得释放两名人质的回报,基于生命价值优于其他价值的权衡,那此项条件交换的价值就明显有利于事件的和平解决。
2.2.2实质性要求的接受与回应
谈判组在接到谈判对象提出的实质性要求时,通常我们不建议谈判员立即做出是否可以满足的即时回应,特别对于一些难于实现的要求(如提供车辆离开、提供酒精类饮品时)。如果谈判即时回应可以实现,期限将至时警方又无法履行承诺,使得双方信任破裂;如果即时否决谈判对象要求,则双方无法实现交换,使得谈判陷入僵局。在现实危机谈判中,谈判员首先会详细记录要求的全部内容,如要求细节、实现时间、交换条件等等,承诺在尽可能快的时间向上级请示,争取最大限度的满足。与此同时,现场指挥部会即刻启动实质性条件的分析程序,依据价值权衡以及对于事件的利弊分析等因素,确定实质性要求是否可以实现,若无法在现场实现,后台指挥部应依据现有谈判成果以及警方资源,制定后续谈判策略乃至由此非实现要求所导致的备选行动方案,确保谈判在警方控制范围内的良性发展。
2.2.3实质性要求的交换与执行
实质性要求在经过现场指挥部分析与价值权衡后,若可以满足谈判对象,则进入实质性要求的处理与执行要求阶段。在要求执行前,应形成相对完备的执行方案(执行人员、执行的方式、紧急方案等),所有参与实质性要求交换的现场部门应熟悉执行流程、如有异议应及时提出并加以完善,确保在条件交换过程中各部门的配合顺畅。在完成基本桌面推演后,如果现场地形条件允许,可以选择相似空间条件进行实地模拟执行,从而对于方案进行最后完善。
执行方案确定后应与谈判对象协商,在双方同意后方可执行。在方案执行过程中,现场指挥部对于各参与单位进行现场监控与调度,同时谈判组应时时保持与各行动单位的通讯联络,在掌握执行进度的前提下便于与谈判对象的沟通,避免引起不必要的猜疑与误会。意外情况发生时,立即停止原方案执行,依据紧急方案快速撤离,最大限度确保现场人员安全。
参考文献
[1]Roberts A R. An overview of crisis theory and crisis intervention. In A. R. Roberts (Ed.), Crisis intervention handbook (2nd ed.). New York7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0.
[2]Vecchi G M. Hostage/barricade management: A hidden conflict within law enforcement[J]. FBI Law Enforcement Bulletin,2002, 71(5): 1-14.
[3]Gregory M. Vecchi, Vincent B. Van Hasselt, Stephen J. Romano. Crisis (hostage) negotiation: current strategies and issues inhigh-risk conflict resolution[J]. Aggression and Violent Behavior,2005,10(5): 533-551.
[4]Amy Grubb. Modern day hostage (crisis) negotiation:The evolution of an art form within the policing arena. Aggression and Violent Behavior,2010,15(5):341-348.
[5]Rosenbluh E S. Police crisis intervention: A dilemma in the aftermath of Columbine High School. Journal of Police Crisis Negotiations, 2011,1(1): 39-46.
[6]Romano S J. Personal communication. Crisis Negotiation Unit, Critical Incident Response Group. Quantico[J]. FBI Academy, VA, 2002.
[7]Sharp A G. The importance of role-playing in training. Law and Order: The Magazine for Police Management, 2010,48(6): 97-100.
[8]张明刚,何睿,于洋.危机谈判实务[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14.
[9]王大伟,张榕榕. 欧美危机警务谈判[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7.
(责任编辑陈小明)
作者简介于洋(1981—),男,辽宁沈阳人,副教授。研究方向为危机谈判,警察战术,危机管理。
基金项目2013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警务危机谈判机制建构研究”(13CFX041);2012年公安部理论与软科学课题“基于谈判主导的人质事件现场处置模式研究”(2012LLYJGDST048)的阶段性成果。
中图分类号D91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