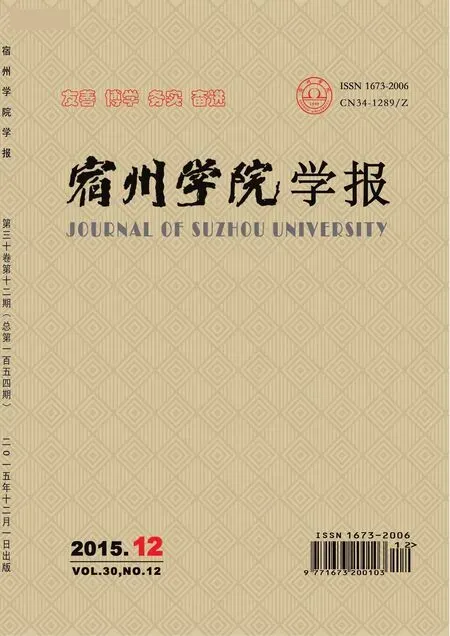从接受美学看意识流小说在中国大陆的译介
2015-02-15丁惠
丁 惠
安徽农业大学外国语学院,安徽合肥,230036
从接受美学看意识流小说在中国大陆的译介
丁 惠
安徽农业大学外国语学院,安徽合肥,230036
自进入中国大陆伊始,意识流小说因其自身特点和读者接受等因素经历了一个较为曲折复杂的译介过程,这其中,尤以读者因素的影响作用为最大。接受美学肯定读者因素在文学作品接受过程中的主要地位,因此能够作为理论基础以研究意识流小说在中国大陆的接受过程,将在阐述其源起与特点的同时,从历时的角度梳理其译介史,重点分析在译介过程中读者因素对译介的影响和译者因双重身份采取的翻译策略。研究结果表明:读者因素不但左右了意识流小说在中国大陆的接受程度,也影响着译者的翻译策略选择。
意识流小说;译介;接受美学;中国大陆
意识流小说作为欧洲现代主义文学的先锋,其还原心理意识过程、以人物内心独白串联情节等非理性元素,给读者阅读带来较大困难,这也为它在中国大陆的译介带来重重障碍。从接受美学的视角探讨读者因素对意识流小说译介过程的影响,将会给该类小说在中国大陆的译介研究开拓新的思路。
1 意识流小说的源起与特点
“意识流”的概念最早由美国心理学家威廉·詹姆斯提出,他认为人的意识有很大一部分是无逻辑和非理性的,意识的活动是一种流,以“思想流”“意识流”等方式进行,而人过去和现在的意识交织在一起,重新组织人的时间感。法国哲学家柏格森肯定了这种时间感,强调过去的经验对现在产生的影响以及两者的有机统一,提出了心理时间的概念。奥地利心理学家弗洛伊德发展了詹姆斯关于非理性、无意识的观点,肯定了潜意识的存在。
意识流小说的诞生与现代哲学和现代心理学密不可分。欧美一些作家深感过去单一的写实主义的小说创作方法已不足以表现现代社会和现代人的复杂性,为了能“原原本本地展示人物精神活动的真实过程”[1],以恰当表现复杂人性,需要一种全新的文学形式。意识流概念的出现恰好与他们的文学主张相契合,其小说的写作手法就是在这种精神探索中形成的。意识流小说在20世纪初兴起于欧美,与传统小说对客观世界写实的创作手法截然不同,它以临摹人物复杂的主观心理和情感变化为主要表现方式。
意识流小说整体不是按照时间顺序或按情节之间的逻辑联系而形成的单一、直线的结构,而是一种立体、多维的结构网络。故事和情节的衔接随人的意识流动和自由联想来组织,不受时间、空间或逻辑关系的限制,小说的时间常常是过去、现在、将来交叉或重叠,空间跳跃、多变。情节上常以一件事为中心,通过自由联想使人的思维意识不断发散又收回,以此循环反复。意识流小说用人物“内聚焦”的叙事方式展示人物的意识流动,最常用的技巧主要有内心独白、自由联想、蒙太奇、时空跳跃、旁白等。其中以内心独白、自由联想和蒙太奇这些技巧最能挑战读者的阅读习惯。内心独白有时不用“他想”“她感到”等提示词,而是将人物的意识直接呈现给读者;自由联想的手法展示了人物意识流动的非理性和无序性;蒙太奇的表现方式把不同时间和空间中的事件和场景拼接在一起,超越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意识流小说杰出的代表作家有爱尔兰的乔伊斯、法国的普鲁斯特、英国的伍尔芙和美国的福克纳等,他们创作了《尤利西斯》《追忆逝水年华》《达罗卫夫人》《喧哗与骚动》等一大批优秀的小说。然而他们的作品在问世之初因过于颠覆传统的小说创作手段在读者和评论界一度遭到冷遇,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意识流小说的创作和译介数量增多,这类小说才逐渐得到认可并广为流传,且在世界范围内拥有了较大的读者群。
2 接受美学与译介研究
接受美学即接受理论,是西方当代文学批评理论中的一种,它受现象学和哲学诠释学影响,诞生于20世纪60年代后期的德国,属于康斯坦茨大学的一个文艺批评学派,以姚斯和伊瑟尔为代表人物。接受美学主张在研究文学和文学史时,必须将重点放在对读者接受过程的研究方面,因为文学作品的意义理解和生成只有经过读者的参与才能完成,姚斯认为:“一部文学作品的历史生命如果没有接受者的积极参与是不可思议的。”[2]伊瑟尔认为文本意义是“不确定”的,是一个开放的“召唤性结构”,需要读者在阅读时填补其中空白,即一种“借助经验和想象对作品中空白和模糊点的充实”[3],而读者的“期待视野”(读者的世界观、个体经验、审美层次和文化知识等因素综合作用而成)导致读者对文本产生“偏见”,“偏见”与文本相互作用,即读者过去和现在的观念在互相交流,达到“视野融合”,形成新的视野,在这一过程中也就完成了理解。
接受美学打破了作者中心论和文本中心论占主导的传统的文学批评范式,推崇读者在文学研究中的中心地位,在这一点上,恰好有助于解释外来文学的译介过程。首先,翻译文本的意义本身也是不确定的,需要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将意义具体化以实现译文的存在价值,而在理解过程中,译者兼具双重身份,既是原作的读者,也是译作的解释者,译者自身期待视野的作用必然影响译文的解读。其次,读者的个人审美经验和受社会历史影响形成的价值观念等也影响外来文学在译入语文学系统的译介过程。
接受美学在开辟了文学研究新领域的同时,也拓展了译介学研究的视野。然而,该理论过分夸大读者的作用,强调读者的主体性是作品产生效果的决定性因素,有一定的不合理性。这里不谈它的片面性,仅借助它对读者因素的肯定方面来探讨接受美学对意识流小说译介过程的解释性。
3 接受美学视域下意识流小说在中国大陆的译介过程
从接受美学的视域来看文学翻译,译者是译介活动的主体,决定原文文本和翻译策略的选择,而读者的作用同样重要,因为读者因素直接干预了译介的整个过程。
3.1 读者因素影响译介的过程
意识流小说在中国的译介过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它受到了来自意识形态、历史条件、文学传统、文化语境等综合因素的制约。它在中国的译介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20世纪20年代至1949年,第二阶段为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至今。
第一阶段,最早被译介进中国大陆的意识流作家为普鲁斯特,对他的介绍在郑振铎所著的1927年4月出版的《文学大纲》(下册)上略有提及[4]。1929年8月,《小说月报》介绍了乔伊斯的《尤利西斯》迥异于传统的手法和伍尔芙的作品特点,其后的三四十年代,中国文坛对意识流文学的译介采取了包容的态度,作为推介西方现代文艺重要舞台的《西洋文学》《现代》《文艺月刊》等报刊杂志对意识流的译介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伍尔芙的短篇小说《墙上一点痕迹》和她的意识流诗学得到译介,乔伊斯和福克纳的小说创新手法分别得到评价。此外,1935年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出版了《今日欧美小说之动向》,也基本涵括了欧美意识流代表作家创作的大致情况[4]。最值得一提的是1931年出版的《欧洲文学史纲》、1946年出版的《法国文学史》(下册)和1947年翻译出版的《英国文学史》,这些文学史的书籍评价了意识流文学的历史地位,普及了代表作家的作品和意识流手法。然而,由于意识流作品独特的表现手法和“内向”的表现内容不符合当时旧中国寻求解放和民主的大时代背景,背离于中国读者一贯的现实主义审美传统,所以其接受、欣赏的范围也只局限在特定的文学和学术圈内,即使是翻译意识流小说作品,也重在向读者引荐“意识流”的哲学与心理学因素方面,突出“意识流”及其代表作家所具有的现代性。这个时期对“意识流”的译介倾向于帮助读者了解当时的现代思想,如对福克纳的译介是出于他的作品属于新崛起的美国文学的考虑,而美国文学所表现出的摆脱旧束缚的特质能够为当时寻求革新和进步的中国文学所学习。同时,当时的文坛对意识流作品的译介还存在批判的倾向,如批判乔伊斯的作品是颓废消极的,是没落的市民阶层文学,与当时引进的苏联社会主义文学的写作方法形成鲜明对比,因为后者更能揭露社会矛盾,反映社会现实。这些人为操纵、将读者接受因素考虑在内的译介活动反映了“中国现代文学注重实际的现代译介观”[5]。
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由于意识形态限制,新中国的文学系统认为欧美现代派文学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物,在思想上是悲观颓废的,不符合当时民众参与新社会、建设新社会的普遍精神需求,由此以意识流为首的西方现代派作品被“打入冷宫”。此后,苏联社会主义阵营的现实主义文学作品占据了翻译文学的主流位置,到1978年现代派文学重新踏入国门,这三十年间意识流文学的译介是一个断层。
第二阶段的译介始自1979年的“新时期”,政治环境的相对宽松和文艺活动的重获自由使得意识流小说在中国大陆的译介获得新生。仅从1979年到1983年,福克纳、乔伊斯和伍尔芙等意识流文学大师的中、短篇小说作品在《外国文艺》《美国文学丛刊》等文学期刊上相继被翻译出来。1983年后,以上三位作家的作品翻译全集面世,其中包括他们的代表作和重要作品: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和《八月之光》,伍尔芙的《夜与日》和《到灯塔去》,乔伊斯的《尤利西斯》。1989年,另一位意识流巨匠普鲁斯特的长篇巨制《追忆逝水年华》也翻译出来。另外,乔伊斯、伍尔芙和福克纳三位作家的文学评论也相继翻译出版,中国读者可以借此对西方最优秀的意识流文学作品有一个全面的认识。其后,对欧美现代主义文学的翻译热潮愈演愈烈,较早被译介过来的意识流小说也逐渐为读者熟悉。
然而实际上,新时期开始时,中国读者对意识流文学译介的态度是微妙而复杂的。意识流小说诞生之初的身份就是传统现实主义的反叛者,它重心理描述、轻故事情节的创作手法与中国读者的传统审美观念和经验相异。首先,中国的古典小说自魏晋南北朝的志人志怪小说到明清小说都是以情节为中心。其次,20世纪的现代小说和建国后的社会主义题材等小说也多以情节取胜,中国读者习惯了在阅读小说之前对它有“故事情节”上的审美期待,这种阅读经验和审美模式显然对意识流小说奇特的象征手法、交错的时空顺序、跳跃的自由联想和大段的内心独白有阅读障碍甚至排斥心理。因此,如何使意识流文学译介顺畅并被读者顺利接受,这是摆在译者面前的一大问题。
3.2 译者的双重身份影响翻译策略的选择
接受美学认为在翻译的理解和表达过程中,译者既是原文的读者又是译文的作者。在理解原作时,文本的文学特点和译者自身的“期待视野”、审美习惯、本民族诗学传统等因素会影响译者对作品的解读;在创作译文时,译者不仅要表达出原文的意义和内涵,还要将目的语读者的因素考虑在内,对读者的需求、审美层次和接受水平进行预判,进而选择相应的翻译策略对原文再创造。总之,在译介时,“读者意识应贯穿翻译的全过程”[6],这一点,在《尤利西斯》和《喧哗与骚动》的翻译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再如著名学者李文俊对福克纳《喧哗与骚动》的翻译。《喧哗与骚动》一书最大的文体特点是由四位不同的人物对女主人公凯蒂的一生进行了多重视角的叙述,原著最后一部分采用全知全能的视角全方位描述了康普生家族的经历。这种多视角叙事的层次复杂,线索繁多,尤其是凯蒂的小弟班吉是一名白痴,福克纳将他的语言处理为单纯、模糊和原始的表达效果,这些特点对中国读者来说也是一种阅读挑战。为降低阅读困难程度,帮助读者理解和欣赏,李文俊特意撰写了长篇前言,细致剖析了原著的艺术风格和特点,着重介绍了福克纳在书中使用的意识流技巧。此外,他还在译本中用了400多条注释,其中,介绍人物的70多条,介绍背景的80余条,提示情节和时空转换的多达260条,并用不同的字体印刷[7]。
由此可见,在译者解读并翻译文本时,不仅要深入了解原文文本含义、语言风格、文化内涵、原著作者和历史背景等,还应充分考虑读者的民族文化心理、诗学传统、接受能力、审美经验和阅读习惯等,如此才能实现读者与译文文本的视野融合,达到文学译介的最佳效果。
4 结束语
在接受美学的视域中,“艺术作品只有对于欣赏者才有意义,只有对于欣赏者来说,艺术作品才能存在”[8],以接受美学的翻译观来看,读者的期待视野、审美心理和审美经验等因素对意识流小说在中国大陆的译介产生了很大影响。读者因素不但左右着意识流小说在中国大陆的接受程度,也干预了译者的翻译策略选择。因此,考察读者的接受史,既是在梳理作家、原著、译文、译者和读者的关系史,又是在还原翻译文学的译介史,这会对外来文学在我国文学系统的接受研究产生极为重要的意义。
[1]李维屏.意识流语体的变异与表意功能[J].外国语,1994(4):63-69
[2]Hans Robert Jauss.Toward An Aesthetics of Reception[M].Trans Timothy Bahti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82:19
[3]朱立元.接受美学导论[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4:14
[4]吴锡民.“意识流”流入中国现代文坛论[J].外国文学研究,2002(4):110-115
[5]郭恋东,杨蓉蓉.论“意识流”在中国现代文坛的译介[J].山东社会科学, 2013(7):101-105
[6]刘凤梅.从接受美学视角论翻译[J].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2005(2):23-26
[7]查明建.意识流小说在新时期的译介及其“影响源文本”意义[J]. 中国比较文学,1999(4):59-72
[8]周来祥,戴孝军.走向读者:接受美学的理论渊源及其独特贡献[J]. 贵州社会科学,2011(8):4-16
(责任编辑:李力)
2015-08-07
安徽农业大学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接受美学视域下意识流小说在中国大陆的译介研究”(2014ZS30)。
丁惠(1982-),女,安徽宿州人,硕士,讲师,主要研究方向:翻译理论与实践、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H315.9
:A
:1673-2006(2015)12-0083-04
10.3969/j.issn.1673-2006.2015.12.0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