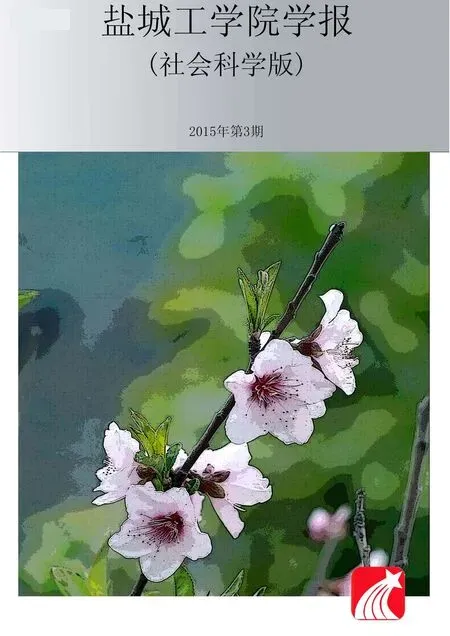李贺诗歌接受史上的“第一读者”与“第二读者”
2015-02-14魏琼琼
魏琼琼
(厦门大学 中文系,福建 厦门 361005)
李贺诗歌接受史上的“第一读者”与“第二读者”
魏琼琼
(厦门大学 中文系,福建 厦门 361005)
唐代著名诗人李贺,以“诗鬼”闻名后世。在考察李贺诗歌历代接受史的基础上,运用接受美学中的“第一读者”的观点,以及近来学界提出的“第二读者”的概念,分析、阐述李贺诗歌接受史。认定杜牧、严羽分别为李贺的第一、第二读者,根据历代诗评家对李贺诗歌的论述,具体阐述杜牧、严羽之评论对李贺诗歌的传播与接受的重要影响与作用。
李贺;第一读者;第二读者
李贺,字长吉,唐宗室郑王之后。李贺在世仅仅二十七年,在其短暂的生命中,其诗歌创作始于唐德宗贞元二十年(804),终于宪宗元和十一年(816),前后总共不过十三年时间,却留下让后人评论不已的诗歌。袁行霈先生《中国文学史》以“幽奇冷艳”[1]来概括李贺的诗风。
李贺在文坛上活跃时间较短,其交游面不广,与其往来的文人也不多。他像一颗黑夜中划破夜空的流星,给人无限遐想,并在人们的深深叹息中戛然而逝。而他的诗作却如同一颗耀眼的明珠,在李贺去世之后一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闪耀着熠熠夺目的光辉。在中国文学史上,很难找到像李贺这样的具有独特命运的诗人,这也是他诗歌独特风格的起点所在。
从晚唐至宋,再到金元,再到明清,直至近代,李贺接受了来自不同文人褒贬不一的评价。清代文学家龚自珍在他的《书汤海秋集》中对李贺其人其诗进行了恰当的论述:“人以诗名,诗尤以人名。唐大家若李、杜、韩及昌谷、玉溪;及宋元眉山、涪陵、遗山,当代吴娄东,皆诗与人为一,人外无诗,诗外无人,其面目也完”[2]347。龚自珍把李贺作为诗与人合一的典范,对李贺其人其诗的历史地位作了准确的定位。
一、杜牧——李贺诗歌评论的真正开端
1.杜牧对李贺的评论
从晚唐以来,诗评家们对李贺其人其诗的评价褒贬不一,差距甚大。最早对李贺的诗歌进行评价的有沈亚之、杜牧、李商隐等人。他们对李贺诗歌基本上持褒扬的态度。杜牧在《李贺集序》中给予其诗歌高度评价:“云烟绵联,不足为其态也;水之迢迢,不足为其情也;春之盎盎,不足为其和也;秋之明洁,不足为其格也;风樯阵马,不足为其勇也;瓦棺篆鼎,不足为其古也;时花美女,不足为其色也;荒国陊殿,梗莽丘垄,不足为其恨怨悲愁也;鲸呿鳌掷,牛鬼蛇神,不足为其虚荒诞幻也”[2]7。连用九个比喻句对其诗歌进行了概括,尽管有些说法遭到后人的质疑。然而,“时花美女,不足为其色也;牛鬼蛇神,不足为其虚荒诞幻也。”这两句却恰到好处地概括了李贺诗歌“艳丽”、“怪”、“奇”的风格。
虽然杜牧对李贺的诗歌大加赞赏,但是在创作时他却从未明显表露出对李贺诗的模仿。尽管如此,还是可以在他的诗歌中看到李贺的影子。杜牧的一首为官妓张好好所写的五言诗《张好好诗》,具有十分浓郁的伤感色彩。其中有几句:“聘之碧瑶佩,载以紫云车。洞闭水声远,月高蟾影孤”[3]。远处(越来越远)水“声”的意象并不平常,其背后微微显示了李贺的《金铜仙人辞汉歌》中的结尾。在李贺那首诗中,金铜仙人被带到东都洛阳,将离长安(渭城)越来越远,将要被迫为新主人服务,它感到十分的失落和沮丧:“携盘独出月荒凉,渭城已远波声小”[4]。月光的寂寞与远处熟悉的水声相配,张好好的命运和金铜仙人的命运都是身不由己的,都是被迫选择的失落与伤感。因此,“与其说是两首诗在字面上的相似,不如说是内在精神意蕴的相似。因此,杜牧虽从未模仿过李贺,但李贺诗中精彩的段落不时地回到他的脑海,有时还带着原始文本的强烈意味”[5]。
2.后世诗评家对杜牧评论的接受
杜牧之后的许多文人在对李贺其人其诗的接受上显然受到了杜牧的影响。
首先在李贺诗歌风格的评价上,多认同杜牧所说的“艳丽”的诗风。
历代诗评中,涉及到李贺诗歌“艳”“丽”风格论述的很多。刘勰在《文心雕龙·定势篇》说:“是以模经为式者,自入典雅之懿;效骚命篇者,必归艳逸”[6]。刘勰论述了“艳逸”的来源是“效骚”,十分显然,学习屈原《离骚》所表现的“艳”,被李贺诗歌十分恰当地表现出来。在杜牧之前,李贺生前故交沈亚之在《送李胶秀才诗序》中提到李贺诗风:“余故友李贺,善择南北朝乐府故词。其赋亦多怨郁凄艳之巧,诚以盖古排今,使词者莫得偶矣,惜乎其终亦不备声弦唱”[2]6。其中的“怨郁凄艳”四字都指出李贺诗歌的一个侧面。这是李贺诗风最早的评论。但从后世来看,显然,在他之后,杜牧的评价为更多人所接受。
“时花美女,不足为其色也。……”上述引用杜牧的九个比喻句在后世被许多文人原文征引,足以见出杜牧评论的重要性。皮日休在《皮子文薮》中说:“有与李贺同时,有刘枣强焉。先生姓刘氏,名言吏,不详其乡里。所有歌诗千首,其美丽恢瞻,自贺外世莫得比”[2]13。皮日休没有正面论述李贺诗风,而是借同时代的刘枣强与李贺进行对比,从侧面肯定李贺“艳”的诗风。张读在《宜宣志》中也说:“稚而能文,尤善乐府词句,意新语丽,当时工于词者,莫敢与贺齿,由是名闻天下”[2]14。在此,张读提出李贺诗的“意新语丽”,并提出李贺有盛名的原因以及其诗歌地位。齐己在其《读李贺歌集》中有两句:“玄珠与虹玉,璀璨李贺抱”[2]15。此二句,虽未直接说到李贺,到却道出李贺诗歌风格的“艳”。
至宋代,韦居安在《梅涧诗话》中有:“李长吉有《染丝上春机》、《美人梳头歌》,婉丽精切,自成一家机杼”[2]72。韦居安既肯定了李贺诗的“婉丽”,又十分明确地点出李贺诗“自成一家机杼”。可见,文人们已经把“艳”作为李贺诗歌特色的重要组成部分。刘辰翁在《笺注评点李长吉歌诗》中,也多次提及“艳”。例如在评论李贺《唐儿歌》的“浓笑画空作唐字”时说“艳语荡人”[2]57。
当然,也有对李贺艳丽诗风的贬抑之辞出现,宋薛季宣在《李长吉诗集序》中,针对一些文人对李贺诗歌“艳”的贬损观点给予驳斥:“其诗著矣,上世或讥以伤艳,走窃谓不然,世固有若轻而甚重者,长吉诗是也。他人之诗,不失之粗,则失之俗,要不可谓诗人之诗,长吉无是病也。其轻扬纤丽,盖能自成一家,如金玉锦绣,辉焕白日”[2]34。用“轻扬纤丽”来表达对李贺的欣赏。
至明代,胡震亨在《唐音癸签》评价长吉:“长吉天才奇旷,又深于南北朝乐府古词,故能镂剔异藻,成此变声”[2]124。胡震亨在此不仅探寻李贺诗“艳”的来源,并附和晚唐沈亚之的观点。
至清代,学者贺裳则另立高论,一反前人关于李贺诗风“艳”“奇”的说法。在其《载酒园诗话又编》称李贺诗“奇不入诞,丽不入纤”[2]272。并进一步指出李贺诗不是历代评论家说的“奇丽”,并举诗歌为证:“长吉诗艳,尤情深语秀。如《江潭苑》:‘十骑簇芙蓉,宫衣小队红。练香薰宋鹊,寻箭踏庐龙。旗湿金玲重,霜干玉鐙空。今朝画眉早,不待景阳钟。’虽崔汴州曷能过乎?”[2]272指明李贺诗的特点重在情感性及内蕴的深挚,“‘情深语秀’在其艺术感染力和语言美感两个方面深化诗歌美的韵致”[7]。清代袁枚也十分欣赏李贺的诗风,并认为李贺“一集中不特艳体宜收,即险体亦宜收”[2]326。
翁方纲在《石洲诗话》中对李贺的推崇更甚:“李长吉惊才绝艳,……此真天地奇彩,未易一泄者也”[2]342。接着翁方纲又论述这种“绝艳”的由来:“李长吉词调蕴藻,故自怨发”[2]342。翁方纲对李贺如此高度的称赞,标新立异,为文坛增色不少。方扶南有《方扶南批本李长吉诗集》,在评价李贺诗《美人梳头歌》时说:“不著一字,尽得风流,使温李为之,浓艳应十倍加。然为人羡,不能使人思,不如此画无尽意也。从来艳体,亦当以此居第一流”[2]294。他将李贺的“艳体”推到了“第一流”的地位,达到了“不著一字,尽得风流”的高妙境界。
第二,杜牧说的“牛鬼蛇神,不足为其虚荒诞幻也”,这种说法不仅指明其诗歌风格的“怪、奇”的风格,“牛鬼蛇神”一说更是被后代所引用。 钱钟书在《谈艺录》说:“自杜牧之作《李昌谷诗序》,有‘牛鬼蛇神’之说,宋景文论长吉有‘鬼才’之目,说诗诸家,言及长吉,胸腹间亦若有鬼胎”[8]45。杜牧首先把李贺同“鬼” 联系在一起。五代齐己在其诗《酬湘幕徐员外见寄》有二句:“诗同李贺精通鬼,文拟刘柯妙乳禅”[2]15。这里所提到的李贺诗“精通鬼”,无论是说诗歌内容,还是说诗歌技巧的高超,都是对杜牧说法的进一步发展;之后,宋人宋祁在《朝野遗事》中首先提出“太白仙才,长吉鬼才”[2]17的说法。而后钱易在《南部新书》中继而提出了“李白为天才绝,白居易为人才绝,李贺为鬼才绝”[2]21的观点。明代高柄在《唐诗总汇》中就从诗风的角度阐明了李贺诗歌“鬼怪”的特征,并引用了杜牧关于“牛鬼蛇神”的理论:“与夫李贺、卢仝之鬼怪,孟郊、贾岛之饥寒。此晚唐之变也”[2]98。陶望龄在《徐文长传》中提及李贺:“谓为诸生时,提学副使薛公应旗阅所试论异之,置第一,判牍尾曰:‘句句鬼语,李长吉之流也’”[2]119。他判断徐渭的文章为“第一”的尺度是“句句鬼语”,并说是“李长吉之流”, 可以从此处看出当时文人对李长吉诗歌的推崇。
清代,关于李贺诗歌“鬼”的风格的论述比之前更近一步,甚至达到从一种诗歌风格到一种审美境界的高度。胡宇泰在《李长吉总评》中提出:“贺只言片语,必新必奇,而实皆有据。案有原委,虽诘曲幽奥,而意绪可寻,昔陶明通博极群书,耻一事不知,曰:‘与为顽仙,宁为鬼才’。鬼才岂易言哉!”[2]245这里,陶望龄借用陶渊明“顽仙”、“鬼才”的说法,来表明李贺诗歌所达到的境界是一般修养程度的人难以企及的。崔季韫则指出:“宋景公诸公在馆中评唐人诗,曰:‘李白仙才,长吉鬼才。’而杜牧之乃有牛蛇之喻。不知鬼者,不其幽然无声,居于窈冥,或谓之死,或谓之生耳,非遂其真鬼也。若是,则《玄怪》、《树萱录》,具得先长吉矣。”[2]246胡宇泰与崔季韫二人都从自身角度论述对李长吉诗歌的总体感受,发表自己的意见,表达不同以往的真知灼见。他们的评论虽三言两语,但语意精炼,恰当确切。
朱轼对李贺诗歌“鬼”的风格推崇至极,在其《笺注李昌谷诗集序》中有一段话,表明他对李长吉诗的态度:“胜于太白,第思仙灵也,鬼幻也,未有幻而不灵者,而灵不必幻,则鬼幻矣。且人亦不知鬼之为鬼乎!……”[2]280这段文字十分长,可以分为以下几部分:第一,“鬼尚”。李贺诗歌在灵、幻方面超过了李白,是一种介于神、鬼之间的境界。第二,“鬼工”。对李贺那些超出意象表层、出神入化的作诗技巧,作肯定和称赞。第三,“鬼通”。认为李贺诗歌,上通之于神。第四,“鬼胎”。指出了李贺诗歌“鬼”的风格的源流所在,这种风格是师承中国古典文学的源流的。第五,“精神迎鬼”。要以聚精会神的态度来解读李长吉的诗歌[7]183-184。可以说,朱轼的评论,是李贺诗歌接受史上关于“鬼”的风格的最为全面的概述。他对李贺诗歌“鬼”的风格的评价超出了之前所有评价的局限,认为这种风格是李贺诗歌艺术达到至高境界的所在,是必须得到世人肯定和学习的一种诗歌创作方法。对于现代理解李贺诗歌也具有极大价值。
至今,很多学者对李贺这种诗歌风格给予肯定,并作出新的解读。大多学者把“鬼才”作为一种固定的评价来接受。钱钟书在《谈艺录》中肯定了杜牧以及后代许多诗评者关于“鬼才”“鬼诗”的说法。“牧之序昌谷诗,自‘风樯阵马’以至‘牛鬼蛇神’数语,模写长吉诗境,皆贴切无溢美之词”[8]47。袁行霈先生在其《中国诗歌艺术研究》中则肯定李贺这种诗歌风格是在学习前人基础上的创新,高度评价李贺在中国诗歌史上的贡献:“元白、韩孟、韦柳都不过是从风格上做了局部的调整,李贺则是全新的创造,他做了非圣人也非仙人所作的工作,难怪被称为鬼才了”[9]。
在中国诗歌发展历程中,对李贺“鬼诗”、“鬼才”的评论一直没有停止,这种论断直接影响着对李贺诗歌在古典诗歌史上的评价及定位,不仅是李贺接受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历代评论者们对李贺褒贬争论的重点所在。
综上观点,不论是对李贺“艳”“鬼”诗风的定评,还是关于长吉“鬼才”的说法,都从晚唐杜牧之评敷衍而来。因此,可以把杜牧作为李长吉诗歌接受的第一读者。所谓接受史上的“第一读者”,“是指以其独到的见解和精辟的阐释,为作家作品开创接受史、奠定接受基础、甚至指引接受方向的那位特殊读者;从此,这位‘第一读者’的理解和阐释,便受到一代又一代读者的重视,并在一代又一代的接受之链上被充实和丰富。一部作品的历史意义就在这一接受过程中得以确定,作品的审美价值也就在这一接受过程中得以证实”[10]。以此来看李贺诗歌接受史,杜牧关于李贺诗歌“骚之苗裔”“牛鬼蛇神”等等的定评,的确对后世诗评家有巨大影响。后代文人在杜牧评论的基础上,不断地对李贺诗歌做出不同的评断,并对杜牧的观点进行不断的充实与补充。
二、严羽——李贺诗歌评论的转折
在杜牧之后,并不是所有人都认同杜牧观点,“第一读者”的观点不是绝对不变的,也不是永久正确的。李贺诗歌从晚唐至近现代,经历了褒贬不一的接受历程,这中间存在一个“第二读者”,关于“第二读者”的概念,学界暂无确切定义,“第二读者”对“第一读者”的观点提出修改,有时“第二读者”的观点甚至会改变文学家的地位以及文学史接受的方向。
严羽在《沧浪诗话》中对李贺的评论有转折性的意味:“贺诗乃李白乐府中出,瑰奇谲怪则似之,秀逸天拔则不及也;贺以词为主,而失于少理,各得其一偏。故曰:‘文质彬彬,然后君子’”[2]46。在此,严羽批评了贺诗“少理”的缺陷。杜牧也说贺诗“理虽不及,词或过之”并非是指责批评,“其中所蕴含的更多是对李贺英年早逝的伤感和慨叹,更应该看成是包括杜牧在内的读者群对李贺的一种期许,希望出现一个更为成熟更为完善的李贺。李贺在中晚唐所受到的一致赞誉和宽容期许,是李白、杜甫这样伟大的人物所未能达到的”[11]。
严羽又说:“王介甫只知巧语之为诗……李义山诗只知有金玉龙凤,杜牧之诗只知有绮罗脂粉,李长吉诗只知有花草蜂蝶,而不知世间一切皆诗也”[2]46。“而不知世间一切皆诗”的观点,严羽站在一个更为宏大的位置上,以一种较为积极的态度,力求诗歌更加完美。并且最早提出了“长吉体”这一说法。他说:“以人而论,则有苏、李体、曹、刘体、李长吉、李商隐体”。这是现存的李贺研究资料中所见到最早的关于“长吉体”的记录,它并未对长吉体进行具体的概括,但是在某种意义上,长吉体指的就是李贺创作本身,是对诗人李贺及其诗歌的归纳。晚唐时代,李商隐的诗歌就具有浓郁的长吉诗歌特色。并且李商隐作《李贺小传》,他的诗歌在很多方面都效仿李贺。其《效长吉》是唯一一首明确标出为效仿李贺之作。因此,李商隐的诗歌并没有明确提出“长吉体”的诗歌体式。严羽可谓是自晚唐以来第一个对李贺诗歌提出不同观点之人。
严羽又说:“人言太白仙才,长吉鬼才。不然,太白天仙之词,长吉鬼仙之词耳。”在此,严羽对“鬼仙”的说法提出质疑,提出不同的看法。他还说:“玉川之怪,长吉之瑰诡,天地间自欠此体不得”[2]47。严羽认为长吉这种“瑰诡”的风格是天地间独一无二的艺术珍品,可见,他对长吉体诗歌是充分肯定和褒扬的。
1.“长吉体”的提出,对后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长吉体经过他的标举,就具有了诗歌宗派的意义,产生的社会影响更加广泛。李贺在元代大受欢迎,很可能就与严羽等人的大力称扬有关”[12]。自严羽之后,文人们纷纷效仿李贺诗歌,并在各自的著述中提及。刘辰翁在其《笺注评点李长吉歌诗·总评》曰:“旧看长吉诗,固喜其才,亦厌其涩。落笔细读,方知作者用心,料他人观到此也,是前年长吉犹无知己也。以杜牧之郑重为叙,直取二三歌诗而止。谓其理不及骚,未也,亦未必知骚也。骚之荒忽,则过之矣。更欲仆《骚》,亦非也。千年长吉,余甫知之耳。读之难读如此,而作者常呕心,何也?樊川反复称道形容,非不极至,独惜理不及骚,不知贺所长正在理外,如惠施‘坚白’,特以不近人情而听者惑焉。是为辩。若眼前语、众人意,则不待长吉能之,此长吉所自成一家欤?”[2]57刘辰翁也提出“长吉自成一家”之说法。宋代著名爱国诗人文天祥也提及长吉体:“予友云屋萧君焘夫,五年前善作李长吉体,后又学陶。自从予游,又学选,今则骎骎颜谢间风致”[2]72。提到了萧焘夫曾善作李长吉体,可以判断在宋代,“长吉体”已经成为比较受人关注的一种诗体。
元代学者刘将孙在《刻李长吉诗序》中较为详细地叙述了元代长吉体的情况:“先君子须溪先生于评诸家诗最先长吉。盖乙亥避地山中,……自长吉而后及于诸家。……自是传本四出,近年乃无不知读长吉诗,效长吉体。……第每见举长吉诗教学者,谓其思深情浓,故语适称而非刻画,无情无思之辞,徒苦心出之者。若得其趣,动天地泣鬼神者,固如此”[2]80。在刘将孙的时代,文人们对李贺诗的热衷已经达到“无不知读长吉诗,效长吉体”的程度;又说“举长吉诗教学者”,可见长吉诗已经成为当时人普遍效仿的诗体。这足以证明长吉诗在元代的流行之广,以及李贺在当时的影响之大。元代的文质、杨维桢是学李贺的集大成者。清人顾嗣立在其《元诗选》中说到“长吉体”:“文质学古,甬东人,隐居吴之娄江,学行卓然,词采奇放,好为长吉体。酒酣长歌,声若金石。常与铁崖夜行,有挑梅花灯者,铁崖命赋一诗,立就,为铁崖所称”[2]292。
明代涉及长吉体的不多,谭元春、李维桢有简单论述。清代翁方纲在其《石洲诗话》中说:“惟孟东野、李长吉、贾浪仙、卢玉川四家,倚仗笔力,自树旗帜。”[2]341列出诗歌风格各异的四家,也是对长吉体的褒扬与肯定。张采田在其《李义山诗辨正》中则把长吉体扩展成为长吉派,视角新颖独特:“余阅《才调集》卷末载无名氏诗数篇,皆仿长吉派者也。……始知长吉一派,真不易及,非具玉溪生之才,不能强学邯郸之步也。”[2]414并进一步论述了长吉诗一直为人们所热爱的原因:“长吉诗派佳处,首在哀感顽艳动人。其次炼字调句,奇诡波峭,故能独有千古。”王闿运在《湘绮楼说诗》中也论述了长吉体:“钞孟诗六叶,又看中唐后诸家,同李贺者不少,盖风气自开一派。”[2]352肯定了自晚唐李贺诗歌流传以来,学者对他的效仿一直不断,进而形成自成一体的诗歌体式,或者诗歌流派。
因此,自宋代严羽以来,长吉体在中国诗歌史上就成为一种事实。李贺的诗歌,对后人来说是独一无二的,他给人一种全新的视野和诗歌创作观念,“长吉体”这一说法更是对李贺诗歌艺术价值与生命力的最高肯定和褒扬。
2.在具体的诗歌创作上,后世许多文人有意识地效仿长吉诗歌
从宋至清,许多文人在诗歌风格上有意识地向长吉诗风靠近。宋代,长吉诗风引起文人的重视,但是仍有许多反对长吉体的呼声,因此,这一代对长吉体的重视十分一般。宋代著名词人秦观有一首拟李贺的诗《秋兴九首(其四)拟李贺》,说明他对李贺诗的重视。范成大有《夜宴曲效李贺》,可以十分明显地看出李贺诗歌的影子。周密是较多学习李贺的文人,他有《拟长吉十二月乐辞并闰月》,这首诗与李贺本人的《河南府试十二月乐词并闰月》有许多相似之处。可见,周密对李贺的诗歌是十分认同的。宋末诗人谢翱受李贺诗歌影响较深,他学李贺诗的成就很高,杨慎对其十分赞赏,称他为“宋末诗人之冠”,“学李贺诗歌,入其室而不蹈其语”,他学李贺不仅是形似,更是神似,“绝妙可传,郊、岛不能过也”[2]105。
元代是李贺极受推崇的时期,元代学习、追随李贺风格的文人也是历代中最多的时期。明代胡应麟有“宋初诸子多祖乐天;元末诗人竟师长吉”[2]219的观点。于石的《续金铜仙人辞汉歌》同李贺的《金铜仙人辞汉歌》在诗歌的语气、风格、意境等方面都有较多契合点。马祖常有《上京效李长吉》。刘诜有《天上谣戏效李长吉》,其中的游天、俯瞰等的视野与意境,颇具长吉意蕴。郭翼也有《和李长吉马诗九首》,同李贺的《马诗二十三首》相比,都是借助“马”这一意象,来表现自身的境况。吴景奎的《拟李长吉十二月乐辞》,将李贺诗歌作为范本,倾心学习。岑安卿在其诗《伤心行用李长吉韵》,在诗歌风格及意境上,都给人一种“鬼才”之感:“朔风动清吟,孤月流寒素。白发困青灯,红妆泣秋雨。罗扇沿网虫,宝鉴青鸾舞。白昼魍魉行,山昏鬼无语”[2]88。
元杨维桢是学李长吉诗的集大成者。同时代及后世的张天雨、何良俊、陈僅、钟秀等人都有关于杨维桢学习李贺的论述。张天雨《铁崖先生古乐府序》指出杨铁崖诗出李贺:“三百篇而下,不失比兴之旨,惟古乐府为近。今代善用吴才老韵书,以古语驾御之,李季和、杨廉夫遂称作者。廉夫又纵横其间,上法汉、魏而出入于少陵、二李之间,故其所作古乐府辞,隐然有旷世金石声,人之望而畏者,又时出龙鬼蛇神以眩荡一世之耳,斯亦奇矣”[2]92。何良俊在其《四友斋丛说》评论杨维桢,“元人最称杨铁崖,其才诚为过人,然不过学李长吉,其高者近李供奉,终非正脉”[2]109。虽然对何良俊不持欣赏的态度,但是肯定了李贺对杨维桢的影响。 第三,严羽对“鬼仙”说提出质疑,得到后世诗评家的认同。
严羽在其《沧浪诗话》中说:“人言太白仙才,长吉鬼才。不然,太白天仙之词,长吉鬼仙之词耳。”继严羽之后,明代的屠隆在其基础上,进一步把李贺列入“仙”的行列,并具体分析他们各自的区别:“人言太白仙才,长吉鬼才,非也。如长吉清虚飘渺,又加以奇瑰,政是仙才。人但知仙才清虚,不知神仙奇瑰。余读真诰诸上真诗,深奥玄远,与世间人口吻迥别。太白烟火仙人语,长吉语,后为上帝见召,故知其非鬼”[2]47。明代的王文禄也在其《诗的》中进一步论述“非鬼”的观点:“李长吉鬼才,非也,仙之奇才也。法《离骚》多惊人句,无烟火气,在太白之上。每携锦囊出游,采句投入囊中,晚归灯下炼集成章,是以奇也”[2]110。他认为李贺的诗超过李白,称赞李贺诗“仙之奇才”。明末的陆时雍更甚,把李贺称作“诗妖”,在其《诗镜总论》中:“妖怪惑人,藏其本相,异声异色,极伎俩以为之,照如法眼,自立破耳。然则李贺其妖乎?非妖何以惑人[13]83?由此可见,“在主流诗坛,推崇雅正诗歌的情况下,明代诗评家对李贺诗歌的评价都不高,大多持否定贬抑的态度,他们一致以盛唐诗歌的标准来批评李贺诗歌,李贺诗歌在明代受到自唐以来最为严厉的贬低和斥责,就连“诗鬼”的地步也难以保住,沦落到“诗妖”的地步”[13]。
元代的范椁在《乐府篇法》中直说“长吉虚妄,不可效为”[2]83。到清代,梁章钜则把李贺归为“无理取闹”一类,态度更为偏激。在其《退庵随笔》中:“唐诗自李、杜、韩、白四大家外,尚有李义山、杜樊川两集,亦须熟看,当时亦以李、杜并称。……长吉惊才绝艳,比太白更不可捉摸,后学且不必遽效之。今人但知学其奇句险语,何益于事!如‘石破天惊逗秋雨’句,虽奇险而无意义,赵瓯北所以讥其‘无理取闹’也”[2]352。梁赞同赵瓯北的观点,把李贺归入到他所不屑的一类。相比梁,乔松年在其《萝藦亭札记》中说:“李昌谷饾饤成文,无复义味,观其篇题当著议者,即无一句可采,则知其中无所得矣。昔人目为鬼仙,侪之太白,真是过誉,其才正当温歧之下耳。温有文藻,犹能以意驭之,李不能也”[2]355。认为李贺在温庭筠之下,可见他十分蔑视李贺。
因此,十分显然,在严羽之后,这些有关李贺的贬低评价有些是有十分道理的,有些则较为偏激,并带着个人的爱好来判定李贺诗歌。尽管如此,这些评论对认识、解读李贺也大有裨益。
纵观李贺诗歌接受史,从晚唐至近现代对李贺诗歌的接受呈现的总体形势是:晚唐以褒扬为主,宋代褒贬不一,金元时期总体上以褒扬为主,并出现了学习长吉体的高潮,明代总体上以贬抑李贺为主,至清代,文人们以较为客观公正的角度来评价李贺其人其诗,近现代承袭清代说法,认为李长吉诗歌有其独特的地位,长吉体是文学史上独一无二的,是自成一家的。
综上所述,作为李贺诗歌的第一读者,杜牧的观点对后世评诗家们产生不间断的影响,可见第一读者对诗人的评价是至关重要的,也影响了后世对李贺其人其诗的接受。而至宋代,严羽作为第二读者,对杜牧的观点提出了修正意见,其观点在后世被许多文人认同、追随,并形成不同的观点群体。但总观之,杜牧同严羽的评论不是完全对立的,杜牧总体上以褒扬为主,严羽则是站在较为客观、公正的立场上来评价李贺诗歌。因此,关于李贺诗歌的评论,文学史上并未形成两股相互对立的评论群体,而是在延续杜牧、严羽诗歌评论的基础上,后世诗评家不断地丰富完善前人的观点,提出自己的意见。对李贺诗歌的这种接受史态势使得李贺诗歌在后世一直受到褒贬不一的评价,而这恰恰是较为最为真实的接受史。也是因为如此,才使得李贺在历代的传播呈现出不同的形象,李贺其人其诗也被世人不断地认识与解读,在这一过程中,文学家李贺也得到不断地成长。
[1] 袁行霈.中国文学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320.
[2] 吴企明.李贺研究资料汇编[Z].北京:中华书局,1994.
[3] 何锡光校注.樊川文集校注[M].上册.成都:四川出版集团 巴蜀书社,2007:61.
[4] 陈允吉,吴海勇.李贺诗选评[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116.
[5] [美]宇文所安,晚唐[M].贾晋华,钱彦,译.上海:三联书店,2011:180.
[6] 赵仲邑译注.文心雕龙译注[M].桂林:漓江出版社,1982:27.
[7] 胡淑娟.历代诗评视野下的李贺批评[M].上海:学林出版社,2009:93.
[8] 钱钟书.谈艺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4.
[9] 袁行霈.中国诗歌艺术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310.
[10] 陈文忠.中国古典诗歌接受史研究[M].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1998:84.
[11] 陈友冰.李贺诗歌的历代接受现象及理论思考[J].中国文化研究,2004(1):74-86.
[12] 李德辉.李贺诗歌渊源及影响研究[M].南京:凤凰出版社,2010:213.
[13] 武春燕.李贺诗歌明清接受史研究[D].郑州:郑州大学,2011:1-57.
(责任编辑:李 军)
The Original Reader and the Second Reader in
Reception History of LiHe′s Poetry
WEI Qiongqiong
(College of Humanities,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Fujian 361005, China)
Li He,a famous poet in Tang Dynasty,known as the “ghost poetry”.On the basis of the reception history of Li He’s poetry,applying the viewpoints of “readers first” in reception aesthetics,and the concept of the Second Reader,which academic circles put forward recently,to analyze and interpret the reception history of LiHe’s poetry.The conclusion is that Du Mu is the Original Reader and Yan Yu is the Second Reader in Reception History of Li He’s Poetry.According to all evaluations from all previous dynasties about his poetry, discuss the important influence and role of Du Mu and Yan Yu’s comments on the spread and acception of LiHe’s poetry.
Li He’s poetry; the first reader; the second reader
10.16018/j.cnki.cn32-1499/c.201503015
2015-04-24
魏琼琼(1991-),女,河南新乡人,硕士生,研究方向:宋代文学。
I207.22
A
1671-5322(2015)03-0066-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