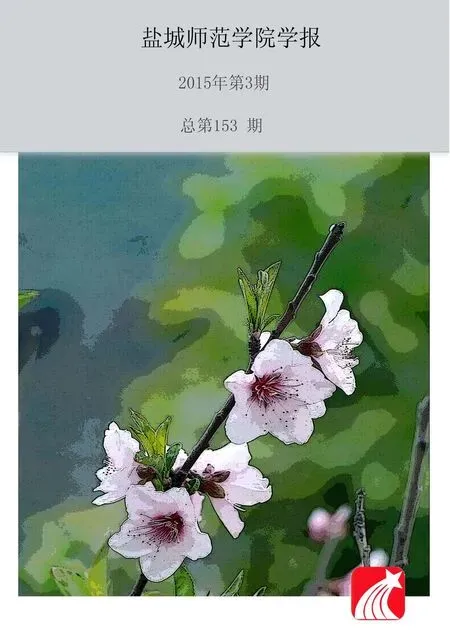唐代《诗经》文本研究的生态世界
2015-02-14李金坤
李金坤
(江苏大学 文法学院,江苏 镇江 212013)
唐代《诗经》文本研究的生态世界
李金坤
(江苏大学 文法学院,江苏 镇江 212013)
唐代《诗经》文本研究的状况大致表现为:其一,《诗经》学著作大多亡佚,存世者甚少。其二,研究内容主要集中于对《诗经》主旨、音义、典章与词汇的阐释,这与唐代科举需用《诗经》著作有密切关系。其三,《诗经》学著作中,既有对《毛诗传笺》内容的承传,又有对其解说的否定。另创新说,体现了独立思考的学术精神与时代特色。其四,《诗经》研究者中有不少人既是学者,又是老师,他们将自己的研究成果直接传授给学生,文脉赓续,形成优良的诗学传统。其五,孔颖达主撰的《毛诗正义》,具有里程碑式的杰出《诗经》学成果。《诗经》所开创的现实精神与比兴艺术优良文学传统,直接滋养了唐诗“丰神情韵”的思想与艺术精神。
唐代;《诗经》文本;研究生态;文学传统;唐诗;生态世界
唐代是继秦汉大一统局势以来的又一个南北统一的伟大时代,儒、释、道的兼容并包,生产力的迅猛发展,科举制度的兴盛与完善,诗歌创作的空前繁荣,这一系列的政治、经济、思潮、文化、文艺的新气象,使唐代的《诗经》文本整理与研究清晰地铭刻着自己独有的时代印记。由《诗经》所开创的现实精神与比兴艺术优良文学传统,直接滋养了唐诗“丰神情韵”的思想与艺术精神。
一
唐高祖李渊在灭隋立国之初,便立国子学、太学、郡县学,广置生员,尊崇儒教。唐太宗李世民则更是推而广之。在其任秦王时,即置文学馆,广延文士。登基之后,遂置弘文学馆,精选天下文儒之士,与虞世南、褚亮、姚思廉等大臣于政暇之际讲论五经大义,在国学立孔子庙堂,尊孔子为先圣,正式定孔子为儒教教主。鉴于当时流行的五经文本多有差异乃至舛误之现状,太宗即下诏颜师古等人考定五经文字,撰成《五经定本》,颁行于世。又因为经义纷纭,章句繁复,不便世人与举子们学习掌握,于是太宗又诏孔颖达诸人撰成《五经正义》一百八十卷(其中《毛诗正义》四十卷)。当时并未立即颁布施行,在孔颖达逝世后,高宗于永徽二年(公元651年),诏令中书、门下、国子三馆博士及弘文馆学士会集共同考订《五经正义》,最后又经于志宁、张行成、高季辅三位宰相亲自参加“增损”,直到永徽四年(公元653年)才正式颁行天下,永为定式。这是一部凝聚了君臣上下、众多大儒心血的不朽经学巨著。马宗霍评价说:“自《五经》定本出,而后经籍无异文。自《五经正义》出,而后经义无异说。每年明经,依此考试,天下士民,奉为圭臬。盖自汉以来,经学统一,未有若斯之专且久也。”[1]至中唐,由于中央集权被破坏,《五经正义》一统天下的局面亦随之打破,这就给经学的自由研究带来了生机。《新唐书·儒学传》云:“大历时,(啖)助、(赵)匡、(陆)质以《春秋》,施士匄以《诗》,仲子陵、袁彝、韦彤、韦茝以《礼》,蔡广成以《易》,强蒙以《论语》,皆自名其学,而士匄、子陵最卓异。”[2]4735这些学者都是在野派,与那些国子博士之类的科班者显然有别,个性鲜明,不带浓厚的政治色彩。至唐文宗李昂,雅好儒术,经学有所发展,注重校正经学文字,遂有《开成石经》之经学壮举。此时,成伯玙撰《毛诗指说》,实乃冲破《毛诗正义》束缚后学术自由的可喜新成果。中晚唐时期经学研究的自由精神,直接影响了宋代经学的变革与创新,开创之功,不可磨灭。
兹将唐代研究《诗经》文本之著作情况作一梳理,以见其概貌。*主要参考刘毓庆:《历代诗经著述考》(先秦--元代),中华书局2002年版;朱守亮编著:《十三经论著目录》(二)之《诗经论著目录》,洪叶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00年版;蒋见元、朱杰人:《诗经要籍解题》,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戴维:《诗经研究史》,湖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张启成:《诗经研究史论稿》,贵州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洪湛侯:《诗经学史》,中华书局2002年版;夏传才:《诗经研究史概要》,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汪祚民:《诗经文学阐释史》(先秦--隋唐),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陆德明《毛诗音义》三卷,存。全名为《经典释文·毛诗音义》,是解释毛诗音读、词义及文字异同的著作。陆德明在其《经典释文序录》中指出:“夫书音之作,作者多矣。前儒撰著,光乎篇籍,其来既久,诚无间然。但降圣以还,不免偏尚。质文详略,互有不同。汉魏迄今,遗文可见。或专出己意,或祖述旧音,各师成心,制作如面。加以楚夏声异,南北音殊,是非信其所闻,轻重因其所习。后学钻仰,罕逢指要。夫筌蹄所寄,唯在文言,差若毫厘,谬便千里……粤以癸卯之岁,承乏上庠,循省旧音,苦其太简,况微言久绝,大义愈乖,攻乎异端,竞生穿凿。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既职司其忧,宁可视成而已!遂因暇景,救其不逮,研精六籍,采摭九流,搜访异同,校之《苍》、《雅》,辄撰集《五典》、《孝经》、《论语》及《老》、《庄》、《尔雅》等音,合为三帙三十卷,号曰《经典释文》。”陆氏就撰著的原因、过程、意义等作了简明扼要的论述,具有纠谬厘正的积极意义。《四库全书总目》评《毛诗音义》曰:“今本经注通为一例,盖刊版不能备朱墨,又文句繁夥,不能如《本草》之作阴阳字,自宋以来,混而并之矣。所撰汉魏六朝音切凡二百三十余家,又兼载诸儒之训诂,证各本之异同。后来得以考见古音者,《注疏》以外,惟赖此书之存。真所谓残膏剩馥,沾濡无穷者也。”[3]160此著与孔颖达《毛诗正义》,堪称有唐《毛诗》研究专著中最为耀眼的双璧,代表了唐代《诗经》学的最高成就。二书最大的特点就在于保存了大量的佚书逸文。不同者,孔著擅长疏解诗旨,折中毛、郑;陆书重在诠释音读,罗列异文。合而观之,则唐以前《诗经》学之大要庶可了然于胸焉。
颜师古等厘正《毛诗定本》,佚。颜师古,名籀,字师古,以字行。《旧唐书·颜籀传》云:“太宗以经籍去圣久远,文字讹谬,令师古于秘书省考定《五经》,师古多所厘正。既成,奏之,太宗复遣诸儒重加详议。于时诸儒传习已久,皆共非之。师古辄引晋宋以来古本,随言晓答,援据详明,皆出其意表,诸儒莫不叹服。于是兼通直郎、散骑常侍,颁其所定之书于天下,令学者习焉。”[4]3788可见颜师古学殖丰厚,知识渊博,考证翔实,可信度高。
孔颖达等撰《毛诗正义》四十卷,又称《孔疏》,存。这是一部全面总结两汉至唐初《诗经》研究成果而具时代特色的官修著作。孔颖达自序云:“夫诗者,论功颂德之歌,止僻防邪之训,虽无为而自发,乃有益于生灵。六情静于中,百物荡于外,情缘物动,物感情牵。若政遇醇和,则欢娱披于朝野;时当惨黯,亦怨刺形于咏歌。作之者所以畅怀舒愤,闻之者足以塞违从正。发诸性情,谐于律吕,故曰:‘感天地,动鬼神,莫近于《诗》’。此乃《诗》之为用,其利大矣……其近代为《义疏》者,有全缓、何胤、舒瑗、刘轨思、刘丑、刘焯、刘炫等。然焯、炫并聪颖特达,文而又儒,擢秀干于一时,骋绝辔于千里。故诸儒之所揖让,日下之无双。其于所作疏内特为殊绝。今奉敇删定,故据以为本。然焯、炫等负恃才气,轻鄙先达,同其所异,异其所同,或应略而反详,或宜详而更略。准其绳墨,差忒未免。勘其会同,时有颠躓。今则削其所烦,增其所简,惟意存于曲直,非有心于爱憎。谨于朝散大夫行太学博士臣王德韶、征事郎守四门博士臣齐威等对共讨论,辨详得失。至十六年,又奉敕与前修疏人及给事郎守太学助教云骑尉臣赵乾叶、登仁郎守四门助教云骑尉臣贾普曜等对敕,使赵弘智覆更详正,凡为四十卷。庶以对扬圣范,垂训幼蒙,故序见其所见,载之于卷首云尔。”[5]自序对诗歌之形成、特质、作用与意义进行了颇为周全的阐释,理解极为深刻;对《毛诗正义》的编撰依据、过程、意义之交代甚为明晰,体现了作者非常谨严庄肃的著述精神。《四库全书总目》评云:“《毛诗正义》四十卷。汉毛亨传,郑玄笺,孔颖达疏……其书以刘焯《毛诗义疏》、刘炫《毛诗述义》为稿本,故能融贯群言,包罗古义,终唐之世,人无异词。”[3]77高度赞美了此著集思广益、独领风骚的学术价值与历史地位。《毛诗正义》作为一本法定的《诗经》读本,在《诗经》研究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它是自《毛诗郑笺》以来《诗经》学史上第二块重要的里程碑。它的出现,使《诗经》研究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值得一提的是,在唐代,日本、朝鲜等国曾派遣大批留学生来长安学习中国文化,临走时都带回许多中国文化典籍。《诗经》于此时传入各国。而《毛诗正义》是当时唯一的标准传本,日本民族文学的第一部和歌总集《万叶集》,在编撰体例、思想内容、表现形式、乃至某些艺术形象等方面,其学习、借鉴和继承《诗经》的迹象清晰可见。这与《毛诗正义》的流传当是分不开的。
在唐代初期,学诗、传诗者多有可见,其成就虽非突出,但在《诗经》学史上不能没有他们的记录。如下列几位便是如此。张士衡,瀛洲乐寿人,从刘轨思受《毛诗》、《周礼》,又从熊安生及刘焯受《礼记》,遍讲五经,刘轨思与刘焯皆是诗学大家。张士衡之诗学成就当亦自是可观,只是因为诸种原因,其诗学著作今已无从可知矣。李玄植,赵州人,受《三礼》于贾公彦,受《春秋左传》于王德昭,受《毛诗》于齐威。王德昭、齐威都是参与修撰《毛诗正义》的《诗经》学名家,故李玄植的《诗经》学成就较之其师来,想必也不会相差甚远。盖文懿,贝州宗城人,与冀州信都盖文达并称“二盖”,唐太宗时为国子博士。《旧唐书·儒学传》云:“文懿尝开讲《毛诗》发题,公卿咸卒,更相问难。文懿发扬风雅,甚得诗人之致”[4]4072。可见,其诗学成就当是较高的。
许叔牙撰《毛诗纂义》十卷,佚。许叔牙,字延基,润州句容人。少精于《毛诗》、《礼记》,尤善讽咏。官至太子洗马,兼崇贤馆学士。所撰《毛诗纂义》进皇太子,太子赐帛百段,兼令写本付司经局。御史大夫高智周尝谓人曰:“凡欲言《诗》者,必先读此书”。事见两《唐书·儒学》本传。王玄度撰《毛诗注》二十卷,佚。《册府元龟》卷六〇六曰:“王玄度为校书郎,贞观十六年十月,上其所注《尚书》、《毛诗》、《周易》,并《义决》三卷,与旧解尤别者一百九十余条,付学官详其可否。诸儒皆因习先师,讥其穿凿,玄随方应答,竟不肯屈。太宗欲广见闻,并纳之秘府。”此著之优劣得失已无从可知,但就其成书后诸儒的不同意见、作者的自我解释与坚定学术立场及其太宗帝的尊重学术的谨慎态度观之,王玄度的《毛诗注》当是一部自有特色的经学著作,否则,也不会引起皇帝的重视。刘迅撰《诗说三千言》,佚。《新唐书·刘子玄传》曰:“迅续《诗》、《书》、《春秋》、《礼》、《乐》五说。书成,语人曰:‘天下滔滔,知我者希。’终不以示人云。”[2]4596作者之言,一种知音罕觏、矜持自尊之况味溢于言表。《五经正义》在永徽四年颁行天下之后,对统一全国诗学的规范与利于士子的学习等方面,起到了许多积极的意义,但由于过多地强调了诗学的整体划一性,因此也就束缚了经学的发展。中唐时,因为中央集权制的被破坏,所以也就给经学的自由研究带来生机。至唐文宗,雅好儒术,又推动经学向前发展。中晚唐时期经学研究的自由开放的形势,给宋代经学研究的变革起到了很好的导夫先路的重要作用。诸如施士匄、成伯玙等,皆为典型的代表人物。
施士匄,吴人,以说《诗》最为著名,撰有《诗说》,又善《左氏春秋》,撰有《春秋传》,可惜此二著皆已亡佚。《昌黎文集·施先生墓铭》曰:“(施士匄)先生明《毛郑诗》,通《春秋左氏传》,善讲说,朝之贤士大夫从而执经考疑者,继往于门。太学生习《毛郑诗》、《春秋左氏传》者,皆其弟子……先生年六十九,在太学者十九年,由四门助教为太学助教,由助教为博士太学。”[6]施士匄较长时间执教于太学,讲说《诗经》与《左传》,著书立说,培育人材,为经学之传扬作出了重要贡献。从其所存的数条诗说材料观之,阐析《诗经》颇具自由评论之特征。施士匄善毛、郑《诗》,当时许多名人都听其讲解《诗经》。《唐语林》则记载刘禹锡同韩退之、柳子厚诣士匄听说《诗经》之事,曰:“《甘棠》之诗,‘勿拜,召伯所憩’,‘拜’言如人身之拜,小低屈也;上言‘勿剪’,终言‘勿拜’,明召伯渐远,人思不得见也。毛《注》‘拜犹伐’,非也。”[7]128-129敢破毛《注》,另立新说,体现了作者自由思想的学术态度。又如说《候人》“维鵜在梁”,施释曰:“梁,人取鱼之梁也。言鵜自合求鱼,不合于人梁上取鱼,譬之人自无善事,攘人之美者,如鵜在人之梁,毛《注》失之矣。”[7]127此则与《毛传》、郑《笺》不同。《毛传》说:“梁,水中之梁,鵜在梁,可谓不濡其翼乎?”郑《笺》说:“鵜在梁当濡其翼,而不濡者,非其常也,以喻小人在朝,亦非其常。”不管施说能否成立,但起码他释诗是建立在自己独立思考与钻研基础上,绝不恪守旧说,人云亦云。施士匄解诗,已渐脱略《毛诗》的牢笼,自出新意,但亦难免空疏浮泛之弊。对此,应作两面观。
成伯瑜(一作玙)撰《毛诗指说》一卷,存。熊克跋曰:“唐成伯瑜有《毛诗指说》一卷,《断章》二卷,载于本志。《崇文总目》谓《指说》略叙作诗大旨及师承次第。《断章》大抵取春秋赋诗断章之义,撷《诗》语汇而出之。克先世藏书,偶存《指说》。会分教京口,一日同官毗陵沈必预子顺见之,欲更访《断章》,合为一帙。盖久而未获,乃先刊《指说》于泮林,庶与四方好古之士共焉。乾道壬辰三月十九日建安熊克记。”《毛诗指说》是一部探讨《诗经》学基本理论问题的著作。全书共四章,第一章:兴述。论诗之功用、起源、兴衰及孔子删诗等问题。第二章:解说。一释诗义,二论国风排列次序,三论大小雅及正变,四论“四始”,五论“六义”,六论二南,七论诂、训、传、注,八论诗序,九论篇、章、什、句,十论《关雎》、《麟趾》,十一论《鹊巢》、《驺虞》。第三章:传受。列举齐、鲁、韩、毛四家诗传受源流。第四章:文体。讨论《诗经》章、句特点,最后论列《诗经》虚词。此书之出,打破了孔颖达《毛诗正义》之后一段颇为沉寂的局面,给唐代《诗经》学重又注入了新的活力。成氏论诗,从总体看,并未摆脱传、笺、序的束缚,是传统诗学的延续,但也提出了一些新的观点。其中最重要的是,认为诗序首句为子夏所传,以下为毛公所续。此说在唐代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到了疑古之风大盛的宋代,苏辙首先接受了成氏之说,在其《诗集传》中只取首句为序,以示“存古”。《四库全书》总目云:“颇似刘氏《文心雕龙》之体。盖说经之余论也。然定《诗序》首句为子夏所传,其下为毛苌所续,实伯玙此书发其端。”《毛诗指说》还辟专章讨论《诗经》句式与结构等问题,这也是一大贡献。在句式上,他指出《诗经》二言至八言不等之句式特征;在篇章上,他指出有“重章共述一事”者,如《采蘋》;有“一事而有数章”者,如《甘棠》;有各章开头相同而结尾不同者,如《东山》;也有各章开头不同而结尾相同者,如《汉广》。此外,成氏还专门讨论了《诗经》中的虚词,对十多种不同类型的虚词逐一举例加以说明,为《诗经》虚词研究开了个好头。
总之,《毛诗指说》虽然是一篇仅有六千余字论文式的著作,论述较粗,表述亦有所欠缺,也有不少因循守旧之处,但他的“鲁、殷为变颂”说,他对《诗序》写作时间的考证,他对魏晋南北朝时期《诗经》研究情况的论述,特别是他对《诗经》语助词与句式的论述等,都有一定的创新精神与文献参考价值。值得注意的是,“《毛诗指说》论《诗经》文体是对初唐《毛诗正义》有关论说的复述与改写,是地道的《诗经》文学阐释。他与孔疏作者前后呼应,共同代表了唐代文人对《诗经》的总体认识和看法……唐代《诗经》阐释是经学阐释与文学阐释的融通”[8]。由此观之,《毛诗指说》在《诗经》学史上当有一席之地。
成伯瑜撰《断章》二卷,佚。《崇文总目》云:“大抵取春秋赋诗断章之义,钞取诗语,汇而出之。”《玉海》注:“取春秋赋诗断章之义,钞诗语,汇而出之。凡百门,序云贞元十年撰。”程修己撰《毛诗草木虫鱼图》二十卷,佚。《新唐书·艺文志》云:“《毛诗草木虫鱼图》二十卷,开成中,文宗命集贤院修撰,并绘物象,大学士杨嗣复、学士张次宗上之。”据《唐朝名画录》载:“太和中,文宗好古重道,以晋明朝卫协画《毛诗》草木鸟兽虫鱼、古贤、君臣之象,不得其真,遂召程修己图之,皆据经定名,任意采掇。由是冠冕之制、生植之姿,远无不详,幽无不显矣。”鉴此,当可知是修己为之。《毛诗物象图》,佚。此即程修己所图之物象,盖《毛诗虫鱼草木图》为一编,其余则另为一编。令狐氏撰《毛诗音义》,佚。《经义考》曰:“王禹偁曰:‘顷年谪宦解梁,收得令狐补阙《毛诗音义》,其本乃会昌三年所写。’按:《小畜集》中有《还工部毕侍郎毛诗音义诗》,第言令狐补阙,不详其名。考《新唐书》,令狐氏止綯曾官左补阙,然历相位,元之不应仍以补阙称之也。”究竟令狐氏为何人,限于资料,现只能暂且阙疑也。
贾岛撰《二南密旨》一卷,存。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云:“《二南密旨》一卷,唐贾岛撰。凡十五门,恐亦依托。”《四库全书总目》曰:“此本端绪纷繁,纲目混淆。卷末忽总题一条云:‘以上十五门,不可妄传。’卷中又总题一条云:‘以上四十七门,略举大纲。’是于陈氏所云十五门外,增立四十七门,已与《书录解题》互异。且所谓四十七门、一十五门者,辗转推寻,数皆不合。亦不解其何故。而议论荒谬,词意拙俚,殆不可以名状。如以卢纶‘月照何年树,花逢几度春’句为大雅;以钱起‘好风能自至,明月不须期’句为小雅……皆有如呓语。其论总例物象一门,尤一字不通。岛为唐代名人,何至于此。此殆又伪本之重儓矣。”[3]1005贾岛著有《长江集》,事迹见《唐书·韩愈传》及《琅琊代醉编》三十。《新唐书·艺文志》著录有贾岛《诗格》一卷,《宋史·艺文志》著录有贾岛《诗格密旨》一卷,所指当即此书,但皆不入经部诗类。是书有《学海类编》、《诗学指南》、《逊敏堂丛书》、《丛书集成》等本。首论六义,次论风之所以、风骚之所由。再次论二雅大小正音及正变,由此而将古诗与《雅》之大、小、正、变相比合。再次论南北二宗,将诗分为南宗、北宗二派,例古今诗以明其体。又次论立格渊奥、论古今道贯一理。又次论篇目、论物象、论大意、论体裁,变言比兴之义,以明作诗之法。如言以“落花”为目者,言国中正风堕坏也;以“夏日”为目者,君暴也;以“贫居”为目者,君子守志也;诗言“舟楫”、“桥梁”者,比上宰,又比携进之人,亦皇道通达也;言“乱峰”、“乱云”、“寒云”者,喻佞臣得志也;言“白云”、“孤云”、“孤烟”者,喻贤人也;言“幽石”、“好石”者,喻君子之志也;言“黄叶”、“落叶”者,比小人也等。皆无关《诗》旨,故诸丛书多将其入于文词、诗学、文学之列,而不与经翼之部。至于何以不入经部,主要还在于《二南密旨》一书多侧重于对《诗经》作品进行文学性的阐释,无形中遮蔽了经学本然的精神内核。其实,就《二南密旨》对《诗经》的文学阐释而言,是颇具其学术价值与创新意义的。兹试举数例论之。如论大、小《雅》曰:“四方之风,一人之德,民无门以颂,故谓之《大雅》;诸侯之政,匡救善恶,退而歌之,谓之《小雅》”。(《论二雅大小正旨》)论大、小雅变者曰:“大、小雅变者,谓君不君,臣不臣,上行酷政,下进阿谀,诗人则变雅而讽刺之。言变者,即为景象移动比之。如《诗》云:‘日居月诸,胡迭而微’,此变《大雅》也……又《诗》云:‘绿衣黄裳’,此乃变《小雅》之体也”。(《论变大小雅》)论南北二宗曰:“宗者,总也。言宗则始南北二宗也。南宗一句含理,北宗二句显意。南宗例如《毛诗》‘林有朴樕,野有死鹿’。即今人为对,字字的确,上下各司其意……北宗例如《毛诗》‘我心匪石,不可卷也’。此体今人宗为十字句,对或不对”。(《论南北二宗例古今正体》)论引古证用物象曰:“四时物象节候者,诗家之血脉也,比讽君臣之化。《毛诗》云:‘殷其雷,在南山之阳。’比教令也;‘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此贤人它适之比也”。(《论引古证用物象》)从这些阐释例子可以看出,唐代《诗经》学所自然呈现出来的趋向于文学阐释的意味,具有时代特色。
张诉撰《毛诗别录》一卷,佚。《玉海》引《书目》云:“《毛诗别录》一卷,张诉撰,凡三十二篇。毛郑笺注,取其长者,述而广之。”蔡元鼎撰《辨类诗》,佚。《云霄县志·卓行传》曰:“蔡元鼎,字国宝。生于唐末,当五季衰乱,隐居不仕,以文章自豪。宋时屡徵不起,讲学大冒山麓,生徒至者千人,学者称蒙齐先生。时经学久荒,元鼎独辟性宗,不由师授,谓圣人道在《六经》,不讲明义蕴,亦糠秕耳。著《论孟讲义》、《大学解》、《中庸解》、《九经解》、《洪范会元》、《辨类诗》、《蒙齐诗文集》等。”《吉日诗图》一卷,佚名,佚。楼钥《吉日诗图跋》云:“此图古矣,意其出于唐人,是时六经未板行,本各不同,故沧浪录旧文,而以今本证之,前有壮士驱群丑而前以待王射,得‘悉率左右,以燕天子’之意。然御者当车中以执辔,主将居左,必择勇者为右,此画御者或在左,或在右,殊未晓也。”
综观唐代《诗经》学的研究状况,大致具有以下几个特点:(1)《诗经》学著作大多亡佚,存世者甚少。今可见者只有孔颖达的《毛诗正义》、陆德明的《毛诗音义》、成伯玙的《毛诗指说》、贾岛的《二南密旨》等四部。(2)研究内容主要集中于对《诗经》主旨、音义、典章与词汇的阐释,这与唐代科举需用《诗经》著作有密切关系,士子们需要统一规范而通俗易懂的教科书,故而对文本的阐释就显得十分重要而突出。(3)《诗经》学著作中,既有对《毛诗传笺》内容的承传,又有对其解说的否定,另创新说,体现了独立思考的学术精神与时代特色。(4)许多《诗经》研究者,本身既是学者,又是老师,将自己的研究成果直接传授给学生,薪火相传,文脉赓续,自然形成优良的诗学传统。(5)具有里程碑式的杰出《诗经》学成果。以孔颖达为首主撰的《毛诗正义》,在文本解读、经义阐析、六义论述等方面达到了时代的巅峰水平,成为《毛诗传笺》以来《诗经》学史上第二块重要的里程碑。
二
唐代尚无完整系统的《诗经》理论批评著作,人们零星的诗学理论观点,大多散见于他们的有关著作中。兹举数例观之。刘知几《史通》云:“夫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观乎《国风》,以察兴亡。是知文之为用,远矣大矣。若乃宣、僖善政,其美载于周诗;怀、襄不道,其恶存乎楚赋。读者不以吉甫、奚斯为谄,屈平、宋玉为谤者,何也?盖不虚美,不隐恶故也。”[9]此段论述突出了“不虚美,不隐恶”的实事求是的纪实精神,充分肯定了“观乎《国风》,以察兴亡”的《诗经》现实主义创作特征,从一位史学家的眼光中透视出文学创作奉行现实主义精神的重要性,这是颇为难能可贵的。皎然《诗式》云:“用事:诗人皆以佂古为用事,不必尽然也。今且于六义之中,略论比兴。取象曰比,取义曰兴。义即象下之意。凡禽鱼、草木、人物、名数,万象之中义类同者,尽入比兴,《关雎》即其义也。如陶公以‘孤云’比‘贫士’;鲍照以‘直’比‘朱丝’,以‘清’比‘玉壶’。时久呼比为用事,呼用事为比。如陆机《齐讴行》:‘鄙哉牛山叹,未及至人情。爽鸠苟已徂,吾子安得停?’此规谏之忠,是用事非比也。如康乐公《还旧园作》:‘偶与张邴合,久欲归东山。’此叙志之忠,是比非用事也。详味可知。”[10]作者结合《诗经》六义中的比兴问题,以魏晋时期著名诗人的作品为例,辨明了比兴与用事的区别,言之成理,甚为中肯。皎然《诗评》云:“或曰今人所以不及古人者,病于丽词。予曰不然。先正诗人,时有丽词。‘云从龙,风从虎。’非丽邪?‘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非丽邪?但古人后于语,先于意”。(《诗学指南》)此说通过古今“丽词”的对比,指出“今人所以不及古人”的根本原因,不在“病于丽词”,而在于有无真情实感,亦即有无像古人那样“后于语,先于意”。就其所举《小雅·采薇》“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而言,的确通过景物描写恰如其分地反映出服役士卒别离乡亲的难舍之痛与回归故乡的悲凉之绪,尽管语言很雅丽,但丝毫不影响诗人真实情感的抒发。真情出好诗,“哀怨起骚人”(李白《古风》五十九首其一),说的就是这个道理。白居易《文苑诗格》:“为诗有当面叙事,内隐一字。古语皆有此体。《毛诗》:‘纠纠葛屦,可以履霜。’此云不可以履霜,隐一‘不’字也”。(《诗学指南》)作者以《诗经》为例,指出了《诗经》“当面叙事,内隐一字”的叙事特点,真乃慧眼独具,令人叹赏!正是在这些有限的《诗经》评论话语中,我们深深感受到了《诗经》丰厚的蕴含与诱人的魅力。
唐代人对于《诗经》的深厚情感,在对它进行全面而深入研究的同时,还十分注重对它精神的继承与弘扬。初唐诗人陈子昂,针对晋宋以来诗歌创作出现的“文章道弊”(思想颓废)、“彩丽竞繁”(形式绮靡)与“风雅不作”(远离《诗经》现实主义精神与比兴传统)的严重现象,高举诗歌革新的旗帜,号召人们振作起来,努力继承“汉魏风骨”与“兴寄”优秀传统。所谓“汉魏风骨”,就是指健康的思想内容和活泼的艺术形式的融合统一;所谓“兴寄”,就是指“托物起兴”和“因物喻志”的表现手法。这些正是《诗经》精神的内核所在,是值得继承和发扬的优秀传统所在。陈子昂的这些思想与主张,主要体现在他的《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为唐代诗歌的健康发展吹响了第一支嘹亮的革新号角。而他的《修竹篇》和《感遇诗》等创作,则很好地实践了自己诗歌革新的主张,在客观上为唐代诗坛树立了一代新风,具有楷模之积极作用。而后的李白与杜甫,更高地举起诗歌革新的旗帜,身体力行,在自己的诗歌创作中努力体现《诗经》的现实主义创作精神与比兴传统。至于白居易与元稹等人开展的新乐府运动,则从理论上、实践上总结和发扬了陈子昂倡导“风雅比兴”的进步主张,大力弘扬《诗经》的“赋、比、兴”传统,促进了唐代诗歌创作更为繁荣昌盛局面的形成。晚唐的罗隐、皮日休、杜荀鹤等人,与陈子昂、李白、杜甫、白居易、元稹等人的诗歌理论主张与诗歌创作精神遥相呼应、一脉相承,以他们充满现实主义精神与比兴寄托手法的诗歌创作,使晚唐诗坛依然放射出耀人眼目的光辉。纵览唐代诗歌的发展脉络,可以这样说,《诗经》的现实精神与比兴传统是始终贯穿其中的一条生命红线。有此红线之贯穿维系,别具“丰神情韵”的唐代诗歌,方才有其源远流长的生命活水。
[1] 马宗霍.中国经学史[M].上海:上海书店,1984:94.
[2] 欧阳修,宋祁.新唐书[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3] 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M]//四部精要:10.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4] 刘昫.旧唐书[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5] 孔颖达.毛诗正义·自序[M]//四部精要:1.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261.
[6] 韩愈.昌黎文集·施先生墓铭[M]//四部精要:18.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162.
[7] 周勋初.唐语林校正[M].北京:中华书局,1987.
[8] 王祚民.诗经文学阐释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343-344.
[9] 刘知几.史通[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123.
[10] 皎然.诗式[M]//何文焕.历代诗话.北京:中华书局,1981:30.
〔责任编辑:王建霞〕
I206.2
A
1003-6873(2015)03-0064-06
2015-02-20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风骚诗脉与唐诗精神”(13FZW010)。
李金坤(1953-- ),江苏金坛人,江苏大学文法学院教授,博士,主要从事中国古典文学研究。
10.16401/j.cnki.ysxb.1003-6873.2015.03.0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