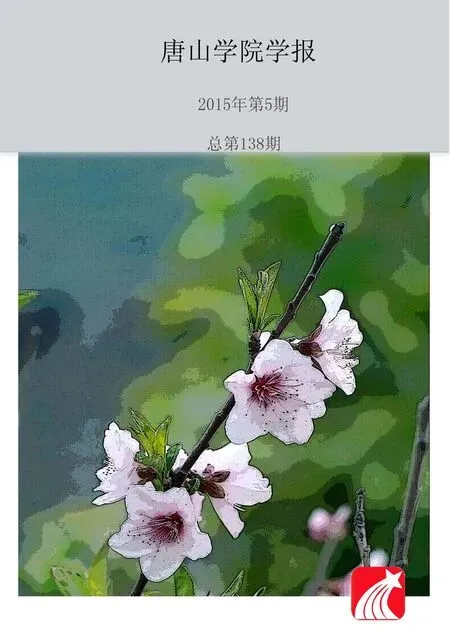理查德·沃尔海姆的“看进”和“看作”问题研究
2015-02-13赵树军
赵树军
(云南民族大学 职业技术学院,昆明 650031)
理查德·沃尔海姆的“看进”和“看作”问题研究
赵树军
(云南民族大学 职业技术学院,昆明 650031)
理查德·沃尔海姆受到达芬奇的启发,提出了“看进”理论,即一种旁观者能同时意识到绘画表面和绘画内容的绘画经验理论。之后,他的“看进”理论得到不断丰富、完善和发展。由此,他还提出了“看作”的观点。文章主要就“看进”的含义、特点、工作机理以及与“看作”的关系问题进行梳理和探讨。
看进;看作;双重性;理查德·沃尔海姆
一、沃尔海姆的“看进”含义
理查德·沃尔海姆(1923-2003年)是一位英国哲学家,曾致力于艺术和精神分析相互关系的研究,他在精神和情感方面,特别是与视觉绘画艺术相关方面,作出了创造性的贡献,提出了“双重性”、“看进”、“看作”、旁观者理论。沃尔海姆把“看进”当作一个“独特的感知类型”[1]46,它有着生物学基础,小孩子用它来认识世界。当旁观者面对一幅画并做出反应时,“看进”成为一个具有“双重性”的单一经验。这种单一的经验体现为,旁观者对画中形象的理解、吸收包括两个特点:他既能看到“被描绘的主体”,也能看到“被刻画过的表面”,例如,画笔的停顿、质地的密度、绘画的裂纹等等。沃尔海姆进一步认为:“一个单个经验的两个方面,它们不是两个经验。它们既不是我不知什么原因在大脑里即刻想到的两个分离的同时发生的经验,也不是在我犹豫之间产生的两个分离的可供选择的经验。”[1]46这个观点的两个方面是有区别的,又是不可分离的,它们体现在“双重性”概念中。他把“看进”的两个补充方面归结为:第一是认知方面,即旁观者识别到的画面里的某些事物;第二是轮廓方面,即旁观者对“被刻画过的表面”的意识。通过旁观者实现了两重性,正是这种对被描绘的主体和表面的同时意识,确保了画框内的场景既有深度又有平面性。除此之外,沃尔海姆的“看进”还有一种可能的含义,即“‘看进’的两方面,并不排除为了强调复杂经验中的一个方面而舍弃另一个方面的可能。在一个污染的墙壁上观看一个男孩,我可能集中于污染……或者,我也可能集中于男孩”[1]47。据此可知,在“看进”的实践中,因为旁观者目的任务、兴趣爱好的不同,他可能会把注意力集中于其中某一个方面,或者是画面里的某些事物,或者是“被刻画过的表面”,读者大可不必拘泥于“看进”的原初定义。
沃尔海姆的“看进”理论最早源于达芬奇,“画家创作了‘一个平坦的表面来展现一个物体,这个物体好像被当成了模型并同该平面分离开来’”,“当我们观看一幅绘画时,我们体验到的是‘一个展示了雕刻的平坦的表面’”[2]。沃尔海姆从中受到启发,将其发展成为自己的绘画理论,即一种旁观者能同时意识到绘画表面和绘画内容的绘画经验理论。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看进”理论在或赞扬或质疑中得以补充、丰富和发展。尽管有的学者的观点不免偏颇,但另一些学者提出的观点还是很客观的。例如,约翰·库尔维克认为,“看进”先于绘画而存在,是“我们生来具有的一种自然能力”[3]。这一点与沃尔海姆的观点(儿童生来就具有“看进”能力的生物学观点)如出一辙,只是表述不同而已。此外,约翰·库尔维克总结了“看进”的三个特征:①“‘看进’是旁观者面临绘画时产生的一个特征,但它不是绘画所独有的”[3]。比如,旁观者面临污染的墙壁、油状的水坑、云彩,以及其他类似的情形时同样能产生“看进”经验。同时,绘画有助于开发、培育这种有趣的感知能力。②旁观者面临绘画的经验特征包括视觉上意识到在画面前面的某些事物或在其后面的某些事物(在其他地方他可能称之为“对再现事物的一个视觉意识”)和对绘画表面本身的一种视觉意识。这一点,和沃尔海姆的“双重性”含义基本相同。③“轮廓意识和内容意识似乎以一个相当亲密的、互相感染的方式联系在一起”[4]。
如何理解“轮廓意识和内容意识似乎以一个相当亲密的、相互感染的方式联系在一起”呢?这涉及到轮廓意识、内容意识和感染性三者之间的关系问题。有的人只承认轮廓意识、内容意识,而不同意二者之间具有感染性的说法,有的人承认二者之间具有感染性,而否认轮廓意识、内容意识。沃尔海姆的“双重性”的定义当中,尽管只包含轮廓意识、内容意识,但是他也意识到轮廓意识、内容意识之间的关系,除了空间上具有可分离的特点外,二者具有感染性。比如,他认识到“看进”的重叠性“从现象上看,与经验或感知起源的表面或性质不相称”[4]。意即“看进”的“双重性”本来是指两个隔着一定距离的分离层,然而这个“双重性”却来自相同的一张绘画,也就是说,旁观者对绘画表面的感知的起源、旁观者对绘画内容的感知的起源均来自同一绘画。既然是两个分离的层面,为什么又会粘连在一起呢?尽管沃尔海姆认识到了这一点,但是,他并不能充分说明轮廓意识、内容意识二者之间的感染性特点,因此,他的“看进”的定义并不完整。
为了说明“艺术品即物理对象同时具有再现特征”,沃尔海姆曾引用霍夫曼的例子得出结论:“假如将黑色颜料应用于一个白色画布,颜料一定是在画布之上,但是我们仅需要说明的是黑色可能是在白色之上,或者可能是在白色之后,或者可能与白色处于同一水平。”[5]27换种说法,从“物理之维”看,绘画是在画布上,从“绘画之维”讲,黑色或者在白色之上,或者在白色之后,或者与白色相平行。在观看绘画时,我们可以同时意识到绘画的表面特征和绘画的再现内容,即既可以从“物理之维”来观看,又可以从“绘画之维”来观看。“物理之维”和“绘画之维”这两个视角并行不悖。“没有一般的理由可以否认我们在同一个时刻,既可以从物理上看到一幅绘画中一个因素是在另一个因素之上,又可以从绘画上看到这个因素是在另一个因素之后”[5]29。由此可知,“一个对象在绘画空间中是在一个位置,与它在物理空间中是在另外的一个位置并不矛盾”,“内容和画布分享的不是同一个空间”[3]。因此,在沃尔海姆看来,被感知的空间可以分为物理空间和绘画空间,即将轮廓方面和内容方面所在的空间分离开来,它们是可以兼容并存的。这样,他就达到了反驳贡布里希的目的。但与此同时,也产生了新的问题。这使得两者(绘画表面和内容)的密切联系变得疏远起来。绘画表面所在的空间和绘画内容所在的空间距离越远,则说明绘画表面和内容相互感染的可能性就越小。这就是说,沃尔海姆以牺牲两者的互相感染性为代价来换取满足两者的相容性。当然,反过来说,“两个空间的接近也明显威胁到内容经验的视觉性质”[3]。总之,这与沃尔海姆的目的相违背(一方面反对贡布里希的观点,即绘画表面的经验与它的内容经验是不相容的,另一方面,支持感染性)。那么,如何才能修正沃尔海姆的“看进”的定义呢,使它既能说明绘画表面的经验与它的内容经验的相容性,又能满足二者的感染性呢?
约翰·库尔维克从上帝的“天眼”得到了某种启示。推而广之,我们也可以从《西游记》中二郎神的“天眼”和人类的特异功能“天眼”中得到类似的启示。人类可以借助“天眼”,穿过地层发现矿藏,也可以穿过一个不透明的物体看到另一个不透明的物体。虽然“一个人永远不可能在一个给定的时间在一个给定的方向感知两个不透明的物体,但是无可否认,这样的经验是可以相容的”[3]。这就是说,一个人虽然不能穿越一个不透明的物体来观看另一个不透明物体,但是他可以具有把两个不透明物体看成交叉感染在一起的经验。而且有大量支持“双重性”的研究人员认为,“理解‘双重性’的最好方式是在一个给定的方向能够意识到多个不透明物体”[3]。
如果用“天眼”的原理来解释“看进”的话,我们可以得到另外一种关于沃尔海姆“看进”的定义方法,既可以避免重叠性与经验或感知起源的表面或性质的不相称性,又可以解释感染性。这个定义就是,“‘看进’是一种感知状态,在这种状态中,一个不透明物体位于另一个不透明物体之前,但是它们之中没有任何一个对象被另一个对象所遮掩住”[3]。在这种状态下,有两个互相感染的“重叠”,它们在某个方向上都把物体和特征置于感知者面前。如果我们把绘画表面看成不透明物体,同时也把绘画中的内容看成不透明物体的话,在我们“看进”时,这两个物体是以交叉感染的形态存在的,类似有彩色图案的玻璃球或有动物图案的古老化石,如此的话,轮廓性、绘画内容和二者之间的感染性就汇聚在一起,从而避免了沃尔海姆对“看进”定义的表述不周之处。
二、“看进”的工作原理
沃尔海姆对“看进”的工作原理作了进一步分析。他试图为“看进”寻找一种原始例证,因此,他设想“看进”源自梦、白日梦和幻觉,它们或者是“看进”的预期或者与“看进”相一致,但它们本身却不可能成为“看进”的例子。要实现“看进”的话,需要发展这种特殊的感知能力,即当旁观者观看一个事物时,不仅仅只是停留在眼睛“直接感知”到的东西,还能看到不在眼前的东西或者唤起某种感知经验。为了获得这种能力,达芬奇曾经鼓励有志青年画家观看潮湿玷污的墙壁、石头或破碎的颜色,从中识辨出战斗场景、暴力活动或神秘场景。但他们在欣赏时表现出了冷漠或犹豫不决。在这个过程中,一方面,他们是自由的,可以对所给的对象的一般特点进行把握;另一方面,他们可以进行选择,选择出对自己感兴趣的东西特别加以关注。其结果,或者是对某个局部给予了充分的关注,或者仅注意到大的轮廓。但无论如何,一个重要的事实是,他们与更进一步的视觉经验、观看战斗场景或背景是关键相关的,除了大的轮廓之外,“同对墙或石头的视觉意识相分离”[6]218。这一点很重要,是“看进”或“双重性”原理的最初萌芽。对墙或石头的视觉意识是一个层面,由此产生的视觉经验又是另一个层面,二者的分离才形成了“看进”的“双重性”效应。在这种情形下,这种更进一步的视觉经验会发生不同程度的变化或波动,或者非常小,或者非常强烈,这主要是因为“对这个视觉经验缺乏一个明确的规定,来消除对这个强烈程度的向上限定”[6]218。要消除旁观者的冷漠或控制视觉经验的强弱程度,这一点必须通过艺术家对物理媒介的调控来实现。
在实际的艺术鉴赏中,旁观者的视觉经验的产生不是无限任意的,必须受到艺术品的制约或艺术家有意识的引导。当艺术家改变或调整一个外在对象,并把这个对象呈现于旁观者之时,如果其他条件都满足的话,旁观者将获得经艺术家设计而期望产生的那类视觉经验,这是毋庸置疑的。艺术家主要通过线条和色彩的应用,来调整、控制视觉经验。其结果就是绘画再现。随着绘画性再现,旁观者原先疏忽的东西现在不得不注意起来。当绘画再现的历史重新展开之时,旁观者不停地接受邀请,放弃他的冷漠,不断接受艺术家的意欲产生的视觉经验,当达到对再现合适的观看程度之时,即符合“双重性”原理之时,旁观者产生的视觉经验和艺术家的意图的视觉经验趋于一致,艺术家就实现了绘画再现的目的,“假如旁观者尊重这种要求,艺术家现在就可以通过着手确立在眼前的事物的特征和在眼前的事物被看到的特征之间的复杂的对应和相似关系,来获得回报,这就是再现的快乐”[6]219。
三、“看作”的特点
将“看作”与“看进”比较,“看作”不是在直接感知之上的特殊的感知能力。“从某种程度上说,它就是直接感知的一个方面,或者直接感知的一个方面的发展。这个方面就是,当我直接感知某些呈现于感官的事物时,我对它的感知由一个概念来调节,或在感知它时,我把它包含于一个概念之下”[6]220。沃尔海姆在感知和概念之间建立了某种联系。把X看作f,即在对X的感知中,总有一些f,这个f是对X的判断,是概念,无论何时,我可以把X感知为f。问题的关键在于,在把X看作f中,是否把X看作f等同于旁观者对X的观看和他的判断它是f的结合。
在把X看作f中,一种观点是把X看作f等同于旁观者对X的观看和他的判断它是f的简单结合,另一种观点是把X看作f不等同于旁观者对X的观看和他的判断它是f的简单结合。第一种观点的提法是错误的。因为它把旁观者对X的观看这种感知和他的判断它是f分割开来,把他的判断它是f置于对X的观看这种感知之外。实际上,这种感知经验和概念是一体的,维特根斯坦就持这种观点,“当我把X看作f时,f渗透或融进了感知之中,概念不是被置于感知之外,这个概念表达了我对X的部分观点或猜测,而感知可能就是对这种观点在某种程度上的支持”[6]220。然而,他运用了再现的知觉转换的例子(鸭兔绘画),即把某些事物“看作”这个变为把它“看作”那个,他说明的是经验和概念不仅同时改变而且作为一个整体来改变,并未证明为什么感知经验和概念应该是一体的。鸭兔绘画与一般的绘画再现不可等量齐观,所以这个例子是不恰当的。
与第一种观点相比,第二种观点的提法比较科学。在把X看作f中,既然不把X看作f等同于旁观者对X的观看和他的判断它是f的简单结合,那么,在旁观者对X的观看这种感知和他的判断它是f之间的关系肯定是颇为复杂的。具体地说,这种复杂性表现为两种情形:①概念自然长入或补充到感知的方式中;②概念与感知综合为一体,概念扮演了认知角色。比如说,伴随着旁观者对X的感知,概念f在他的思想中立刻产生了,而且与对X的感知混杂在一起,进而形成了一个观念X是f,或者旁观者在对X的感知之前被告知X是f,结果他就真的把X看作了f,或者在观看X之前,旁观者有强烈地渴望要把X看作f,结果他如愿以偿,真的就把X看作了f,等等。
“看作”有三个特点。第一个特点,“‘看作’基本上是以对呈现给感官的视觉兴趣或好奇的形式来展示自己”[6]222。“视觉兴趣”,即对旁观者而言,对象曾是如何有兴趣,或现在是如何有兴趣,或将是如何有兴趣,而旁观者的“好奇”则分布在一个对象和它的匹配部分之间。并且旁观者不能把一个对象“看作”它或它的相匹配的部分永远不曾是某些事物。因此,当我们在观看一个对象的时候,一定有该对象的特点或与该对象一致的概念在同时起着调控作用,否则,我们就看不到这个对象了。第二个特点,假如把X看作f就是要实现旁观者对X的视觉好奇,他不仅可以想象X是f,而且可以作进一步想象:X是如何调适自身以便承担成为f的特征。在这个过程中,旁观者可以发现X中哪些部分是保持不变的,哪些部分发生了变化,而这一点正好与前面提到的局部化要求相吻合。第三个特点,在X和f的关系中,或者把X看作了f,或者X没被看作f。假如把X看作了f,这不等同于或超出了仅仅观看X并且同时判断X是f,把X看作f是关于X的一种特殊的视觉经验。相反,假如X不被相信是f,或者甚至相信X不是f,这也是一个很特殊的、相异于前者的视觉经验,其超出了观看X并且同时把X想象成f。现在,我们把X看作近似真实的f(counterfactual,在不同的条件下可能发生与现存事实相反),也就是说X可能变成f也可能变成与f相对的事实。假如把X看作f,我们可以意识到X的保持性特征f1,假如把X看作与f相对的事实,我们同样意识到X的保持性特征f2,而X的保持性特征f2必然不同于f1,属于f2特征对应的X的空间部分X2必然不同于属于f1特征对应的X的空间部分X1。换句话说,当我们试图将f的外表置于X之上时,保持把我们的感知X变成f的特征f1将必须从感知上掩饰起来,即f的外表遮住了f1特征对应的X的空间部分X1。或者将与f相对的外表置于X之上时,保持把我们的感知X变成与f相对的特征f2将必须从感知上掩饰起来,即与f相对的外表遮住了f2特征对应的X的空间部分X2。因此,在“看作”中“双重性”被排除了。在这里,X=X1+X2,f的外表与X1的大小相同,f相对的外表与X2的大小相同。
四、“看进”和“看作”的范围、共同感知问题
“看进”与“看作”相比,它的产生有不同的机理,即“‘看进’不是对眼前事物的视觉好奇。它是对一种特殊类型视觉经验的培育,在其成长的环境中这种经验抓住了一定的对象”[6]223。由此,“看进”产生了相异于“看作”的一系列特点。这种培育而来的经验跟普通的经验一样,分为一个事物的经验和一个事件状态的经验两种。甚至当观看一个事物的时候,也可以当成是在培育一个事件状态的经验。也就是说,有时可以把一个事件状态看成一个事物,一个事物的经验就相当于一个事件状态的经验。这是“看进”的第一个特点。而培育视觉经验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实现视觉经验与支持它的视觉意识相分离。由此产生了“看进”的第二个特点,即双重注意的可能性。正是由于对“看进”经验的培育,使得产生的视觉经验同视觉意识相分离,即旁观者对媒介的视觉意识同他从对象的再现中体验到的视觉经验之间发生分离,使得“双重性”成为可能,一方面,旁观者可以注意到媒介的存在,另一方面,他又可以注意到画面中的事件内容。而这种分离是“相对分离”,艺术家不会满足于一种经验漂浮在另一种经验之上,他还希望旁观者能从一种经验回到另一种经验,即从绘画中的事件状态回到绘画媒介表面来。至于如何在两种经验之间建立密切的关系,沃尔海姆未能给出明确的答案。“看进”的第三个特点是局部化的偶然性。要求局部化就必然要否定这种视觉经验同视觉意识的分离,显然这是不足取的。
沃尔海姆还提到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关于“看进”和“看作”的范围。这个问题与感知哲学、艺术哲学相关。我们可能会根据被感知对象的类型划分它们的所属范围,但是这不能作为一个普遍的规则。有一种特殊情况就是,当我们观看某些对象的某个时间段内,有时候属于“看进”,有时候又属于“看作”。比如我们可能经常会把天空中的一朵云作为“看作”的例子,我们可能把它看作一头大象或者一列火车等。然而,云朵不是固定不变的,有时候,我们会在云里看到一个女人或者一片广阔的田野或者一场激烈的战斗。如查尔斯·梅里庸(Charles Meyon,1821-1868,铜板画家)的“云彩拟人化研究”[1]57。因此,面对这样一个对象,它究竟是属于“看作”还是属于“看进”呢?我们很难对此做出确切的界定。这只能说明“看进”和“看作”可能享有共同的感知对象。
第二个问题是,“看进”“看作”之间有无共同感知。同一对象本身并未发生变化,但却既可以当成适合于“看进”的情形,又可以当成适合于“看作”的情形,二者似乎形成了一种竞争的趋势。比如说,贾斯珀·琼斯(Jasper Johns,美国当代艺术家)的《旗子》绘画。既可以把旁观者对《旗子》的感知看成“看进”,又可以把这种感知看成“看作”。绘画《旗子》向我们展示了一切细节,我们既可以注意到画布表面的色素,又可以注意到一面旗子,符合“双重性”原理,这种感知可以看成是“看进”。但是,这种再现又失去了作为再现的关键性要素:①每一种绘画再现了一个单一的特点,这些特点无论如何也构不成一个事件状态。虽然这些特点不是没有规则的,但这种情形在再现中是少见的。②把再现的画面大小削减到跟对象一样大小的轮廓。当然,这跟“看进”并不矛盾,我们也可以把它看成是在绘画中再现了一个作为整体的旗子,即旗子占据了整个画布。③对象(真实的旗子)和绘画享受了一些相同的特征:相同的维度、相同的色素、相同质地的纺织品、相同的设计手段和方案。因此,旁观者可能会把这三种再现方法同艺术品分离开来,在分离之后,产生了一种与绘画再现相竞争的趋势。这是因为当旁观者视觉意识到这些再现特征时,他知道是画家通过绘画《旗子》吸收、承担了一面旗子的这些特征。在旁观者把再现方法同艺术品分离开来之后,他逐渐变得视觉上意识不到这些再现特征,当这种转变到来之时,绘画的特征必须改变。他受到启发,看到的更倾向于是旗子的特征而不是作为绘画的旗子的特征,直到他把绘画再现“看作”了一面旗子。贾斯珀·琼斯的目的就是要产生一种模糊效果,究竟艺术的边界是什么,是一幅画还是一个具体的实物对象呢,这跟杜尚的《泉》、沃霍尔的《布里洛盒子》一样,是一个值得深思的美学哲学问题。还有一点需要提及,这里所说的贾斯珀·琼斯《旗子》的画面中是单个旗子的例子,而实际上他的《旗子》画群中还有大小旗子重叠在一起的情形,这正如同沃霍尔的重复的布里洛盒子、重复的罐头盒一样,作为波普艺术的代表,展示的是一种商业模式,表现的是美国当代社会人与人的冷漠、金钱至上的精神状态。
“看进”“看作”之间的关系,即在X中看到y与把X看作y之间,除了区别之外,它们之间有什么联系呢?为了找出这种联系,沃尔海姆提出了一种假设,即一个合适的感知所要求的是,当旁观者面临一个对y的感知,他是应该在再现中看到y,因此,他首先是“把再现‘看作’一个再现”[6]226,这意味着“看作”是先于“看进”存在的。因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看进’依赖于‘看作’,再现被‘看作’的事物永远与再现里看到的事物不是同样的。在X中看到y可能依赖于把X‘看作’y,但是,不会是因为它与可变化的y具有相同的价值”[6]226。
[1] Richard Wollheim. Painting as an art[M].London: Thames and Hudson,1987.
[2] Martin Kemp. Leonardo on painting[M].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1989:15-16.
[3] John Kulvicki. Heavenly Sight and the Nature of Seeing-in[J].The Journal of Aesthetics and Art Criticism,2009,67:387-397.
[4] Richard Wollheim. On picture representation[J].The Journal of Aesthetics and Art Criticism,1998,56(3):271-273.
[5] Richard Wollheim. On drawing an object[M]//On Art and the Mind. London:University of London,1965.
[6] Richard Wollheim. Art and its objects[M].2nd edn. Cambridge: Cambridge U.P.,1980.
(责任编校:李秀荣)
On Richard Wollheim’ “Seeing-in” and “Seeing-as”
ZHAO Shu-jun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College, Yunnan Nationalities University, Kunming 650031, China)
Richard Wollheim, inspired by Leonardo da Vinci, proposed the seeing-in theory, a empirical painting theory which argues that a spectator can simultaneously realize the surface and content of a painting. His seeing-in theory enriched, improved and developed. Later, he also proposed the concept of seeing-as. The author of this paper mainly discusses the meaning, features, working mechanism of seeing-in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eeing-in and seeing-as.
seeing-in; seeing-as;duality; Richard Wollheim
B83-02
A
1672-349X(2015)05-0030-04
10.16160/j.cnki.tsxyxb.2015.05.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