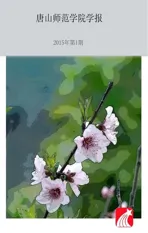庄子“坐忘”说与司马承祯的“坐忘”之关系探析
2015-02-13南京大学哲学系江苏南京210046
张 倩(南京大学 哲学系,江苏 南京 210046)
庄子“坐忘”说与司马承祯的“坐忘”之关系探析
张倩
(南京大学 哲学系,江苏 南京210046)
庄子是先秦道家代表人物,司马承祯是唐代道教代表人物,二者生活年代相隔千年,但庄子有“坐忘”说,司马承祯著有《坐忘论》,在历史上均产生深远影响,二者之间有什么异同及内在渊源关系,本文试图一探究竟。
庄子;司马承祯;坐忘
庄子是先秦道家的代表人物,吸取前人思想提出“坐忘”说。司马承祯是唐代道教代表人物,其最著名的学说是《坐忘论》。两人生活年代、成长背景、学说渊源均不相同,却同时选择以“坐忘”为其哲学思想的重要内容,本文试图对两者之间的异同一探究竟。
一、庄子及其“坐忘”说
庄子是我国战国时期一位著名的思想家,是先秦道家的集大成者。《史记》说:“庄子者,蒙人也,名周。周尝为蒙漆园吏,与梁惠王、齐宣王同时。其学无所不窥,然其要本归于老子之言。”[1]据考证,其生年大概在前375-前300间。庄子及其学派的学术结晶,便是《庄子》一书。自秦汉到宋代,人们一直认为此书是庄子本人的作品。自宋以来,一些学者就提出《庄子》内外杂篇的区分和真伪问题。经过学术界长期研究,一般认为,内篇乃庄子自著,是全书之核心,而外篇和杂篇大多出于庄子门人及后学之手。根据一般思想史的描述,庄子是老子思想的主要继承者和发展者,而庄子哲学更偏于处世之道。与老子相比,庄子的思想、生活状态更像一篇飘逸潇洒的散文。
关于著名的“坐忘”理论,在《大宗师》里面,庄子假借孔子与颜回的对话,谈及到这个问题:
颜回曰:“回益矣!”仲尼曰:“何谓也?’曰:“回忘仁义矣。”曰:“可矣,扰未也。”他日,复见,曰:“回益矣!”曰:“何谓也?’曰:“回忘礼乐矣!”曰:“可矣,扰未也。”他日,复见,曰:“回益矣!”曰:“何谓也?’曰:“回坐忘矣!”仲尼墩然,曰:“何谓坐忘?’颜回曰:“堕肢体,融聪明,离形去智,同于大道,此谓坐忘。”仲尼曰:“同则无好也,化则无常也。而果其贤乎?丘也请从而后也。”[2,p225]
这则寓言的核心,显然是一个“忘”字,“忘”即是达于安适状态的心境。从“忘仁义”到“忘礼乐”再到“坐忘”,层层递进。颜回前两次忘仁义忘礼乐仍是一种对某种具体东西的遗忘,第三次达到的“坐忘”显然是高于前两次,即达到不受形骸、智巧束缚的状态,忘掉自己,这就是坐忘高于礼乐仁义之忘的原因。仁义、礼乐均是人有知后发展得来,对人的自由发展却都有束缚,所以要忘掉仁义、礼乐,去除外界的藩离,去除了外在还要去除内在,即忘掉自我。这时外在藩离、内在自我都消失了,一切浑然一体,同于大通。在大通的境界里,没有好恶是非,一切都在流转,没有固定的界限,达到大通境界的人只要无心而任自化。
“坐忘”说的核心应是“离行去知,同于大道”,即超脱厉害计较、主客对立、分别妄执之心,认为这些东西妨碍自由心灵,妨碍灵台明觉,即心对道的体悟和回归[3]。徐复观先生说:“‘堕肢体’、‘离行’,实指的是摆脱由生理而来的欲望。‘黜聪明’、‘去知’,实指是摆脱普通所谓的知识活动。庄子的‘离行’,并不是根本否定欲望,而是不让欲望得到知识的推波助澜,以致溢出于各自性分之外。在性分之内的欲望,庄子即视为性分之自身,同样加以承认的。所以,在坐忘的境界中,以‘忘知’最为枢要。忘知,是忘掉分解性的、概念性的知识活动。”[2,p226]只有摆脱“形”和“知”的羁绊才能臻于明道,达到“天地有大美而不言”的境界。《大宗师》篇主要强调以道为宗、为师。那么,怎样才能得道呢?庄子提出“不以心损道,不以人助天”的修养原则,其生命体验的方式便是“坐忘”[4]。
二、司马承祯及其《坐忘论》
司马承祯,河南温县人,于唐太宗贞观二十年生于一个世代官宦之家,自幼好学,淹通诗书,薄于为吏,喜方外之游,师从潘师正,继承了潘师正的符箓、辟谷、导引、服饵等道术以及道教经典理论研究的宗旨,成为陶弘景正一法统的三传弟子。历经太宗、高宗、中宗、武后、睿宗、玄宗六朝,倍受统治者的赏识。他晚年久居天台山,唐玄宗多次迎请,后以天台山幽远,迎请不便,令他在王屋山自选形胜,特置阳台观以居之。卒于唐玄宗二十二年,享年八十九。司马承祯的著作较多,主要有《修真秘旨》《坐忘论》《天隐子》《太上升玄消灾护命妙经颂》《服气经义论》等。其中,《坐忘论》和《天隐子》是学术界研究其修道思想的代表著作。
对于道教的外丹方术,葛洪曾加以总结整理,成为他神仙道教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陶弘景早年曾受葛洪神仙养生之术的影响,对神仙方药也很擅长。魏晋隋唐以来,士大夫阶层掀起服食金丹丸散的风气,但这种炼丹服药,不但无效,甚至往往因此中毒身死。与此同时,斋戒符箓也兴盛不衰。司马承祯鉴于这种历史教训,对炼丹、符箓并不重视。在《坐忘论》中,他继承南北朝以来道体与心体、道性与心性、修道与修心等亦一亦二的宗教理论,以《老》、《庄》和其他道教经典为依据,并吸收儒家正心诚意和佛教止观、禅定等思想,提出自己的修炼方法,自称为“安心坐忘之法”,中心思想是守静去欲[5,p4]。这对道教在唐朝由外丹转为内丹,直接通过内力修炼成仙的思想起了重要的理论指导作用,并成为五代以至宋元道教内丹学的实践基础,对宋明理学的产生发展也有重要的影响。
司马承祯在《坐忘论》一开始就提出:“夫人之所贵者生。生之所贵者道。人之有道,若鱼之有水。”人之所贵重的是生命,而生命之中最贵重的即是道。人的“生”与“道”正像鱼和水一样紧密相连,所以要想获得长久的生命,首先要得道。得道的途径是“渐悟”,司马承祯告诫修道之士神仙可学,圣德可至,但必须积习而成,不遵循宗教修养的程序想达到现成结果,是不能成功的。他认为要得道,就必须修道,即按照他所说的“安心坐忘之法”的“七条修道阶次”依次完成。今归纳如下:
“敬信”。“信者,道之根;敬者,得之蒂。根深则道可长,蒂固则德可茂。”[6,p892]对修道要怀有敬仰尊重的心理,不能有半点怀疑的态度,真诚地信,才会有灵验。
“断缘”,即断除非必要的俗事缘分。“弃事则形不劳,无为则心自安,恬简日久,尘累日薄,迹弥远俗,心弥近道。至神至圣,孰不由此乎。”[6,p896]
“收心”。心为“一身之主,百神之帅”。“学道之初,要须安坐,收心离境,住无所有,不著一物,自入虚无,心乃合道。”[6,p894]心体本来是清净的,但是被外物所染,只有“收心离境,住无所有”,才能达到与道相合之自由自在的境界。这就要求人们既不受外物的诱惑,也不去追求外物,达到“心无所著”,以此达到心灵上的解脱。生命之道就是不断地去净化被污染的心。
“简事”,即修道之人不求分外不当事物。“酒肉”、“名位”、“金玉”等不是养生所必须的,一个人“任非当则伤于智力,务过分则弊于形神。身且不安,何能及道?”[6,p894]修炼生命之道,“莫若断简事物,知其闲要,较量轻重,识其去取。非要非重,皆应绝之”。
“真观”,即修道之人应善于观察事物,不致为外物所迷。“收心简事,日损有为,体静心闲,方可观妙。”[6,p897]也就是说,收心简事是真观的前提,真观是对简事的进一步发展。
“泰定”。“无心于定,而无所不定,故曰泰定。”[6,p896]到达泰定阶段时,人的智慧开始觉醒,此时做到“慧而不用”,才不至于伤“定”,然后就可以“深证常道”。
“得道”,即修道阶次的最后阶段,得道之后便“形随道通,与神合一”,称为“神人”,神人“神性虚融,体无变灭,形与道同,故无生死。”[6,p896]也就是长生不死,无所不能的神仙,这是生命修炼的终极目标。
在论述上面七个修行阶次后,司马承祯又在《坐忘枢翼》中综述了坐忘论的主旨。他指出:“若有心归至道,深生信慕”,则须先受三戒,即简缘、无欲和静心。总之,他认为修道之人无物无我,不生一念,内不觉其一身,外不知其宇宙,与道冥一,万虑皆遗,如此方能获得长生久视之道[5,p7]。这种修道思想吸取了佛教理论和传统儒家关于正心诚意的修养方法,再加入道教的思想,对当时社会及后世思想影响都很大。
三、“坐忘说”和《坐忘论》的渊源
“老庄”合称始于汉代,司马迁著《史记》也将庄子附于老子列传内,说明老庄关系密切。一般认为,庄子是老子思想的继承者,司马迁在《史记》中说:“其学无所不窥,然其要本归于老子之言。”老子思想核心是“道”,是万物的根本。庄子也是以“道”为出发点去观察万物的,他说:“夫道,渊乎其居也,谬乎其清也。”道无所不在。在体认大道方面,老子认为:“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7,p128]减损智欲有为才能照见大道,庄子的坐忘说也是这种修道理论的延伸。另外,庄子书中多以寓言形式阐述其思想,暗示性极广,给人们带来无尽的想象,更有利于其思想的传播。
道教与道家不同,但它的理论紧紧依托于道家,老子更多次被神化为道教神仙。隋唐时代的重玄学,以采用佛教的思辨方法和词旨发挥老庄哲学为特质,可称老庄哲学在佛学影响下的新发展或者道家、佛学融合的产物。“重玄”一词即出自老子“玄之又玄,众妙之门。”[7,p1]重玄学家们不仅重视“妙本”所具之理,更强调悟道证道之道。司马承祯是重玄学的代表人物之一,其《坐忘论》就是论述悟道证道阶次之书,经敬信、断缘、收心等最终得道。
四、“坐忘说”和《坐忘论》的异同
同为“坐忘”,说的都是保持心境的平和,去除欲望,最后达到得道的境界。“坐忘”说是庄子的修道理论,《坐忘论》是司马承祯的修道成仙理论。
庄子的“坐忘”是通过暂时与俗情世界绝缘,忘却知识、智力、礼乐、仁义,甚至人的形躯,达到精神的绝对自由。在《大宗师》里面,他描述一个真人,也就是真正的人,这个真人远离虚伪的生活,过着真实的生活:
何谓真人?古之真人,不逆寡,不雄成,不谟士。若然者,过而弗悔,当而不自得也若然者,登高不栗,入水不濡,入火不热。是知之能登假于道者也若此。[2,p227]
他强调真人的生活不是算计的,而是无心的,顺其自然,不为人事,真实的生活,与道通体,与天同性,与命同化。在庄子看来,除了用“坐忘”的修行方法来呈现真人的生活,还有一种重要的实践方法使“心斋”,“若一志,无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无听之以心,而听之以气。听止于耳,心止于符。气也者,虚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虚。虚者,心斋也。”[2,p186]以耳来感应,可能执定于耳闻,不如听之以心。以心来感应,期待与心境相符,尽管高了一个档次,但仍不如听之以气。因为气是虚而待物的,它没有任何欲望、坚持和偏见,通而为一,而耳和心则不同,只有某些东西是顺耳或者顺心的。所以,心志专一,以气来感应,全气才能致虚,致虚才能合于道妙。这就是“心斋”,空掉附在内心里的经验、成见、认知、情感、欲望与价值判断等,自虚其心,如气一般。
“心斋”是一种排除杂念和欲望的精神修养过程,“坐忘”是一种忘掉生理欲望与外在功名诱惑的状态,即通过“舍物”达到“得道”,是心境平和。“心斋”和“坐忘”二者相辅相成,构成庄子精神修养理论非常重要的环节。
“司马承祯所强调的‘心静’,并不完全是庄子所说的‘至人之用心若境’的心之虚静状态,而是静中有动,动中有静,即动而静,以一静应万动,入于动静不二法门。这种动静观念偏重于即动求静一面,便夸大了心的能动作用。心的作用能‘守静而不著空,不执著于‘动’、‘静’,如‘独避世而取安,离动而求定,劳于控制,乃有动静二心,滞于住守,是成取舍两病。’修道之心,亦不能执着于‘有’、‘空’,‘若执心住空,还是有所,非谓无所。’”[8,p360]任继愈先生认为,庄子所说的“至人之用心若境”的心之虚静状态,是一种完全顺应自然,空无杂物的状态。而司马承祯的《坐忘论》虽宗承庄子,而实际上受天太宗止观学影响尤深,如“无所着”的收心之要、观析烦恼等,与天台止观颇相一致。另一方面,庄子是道家思想代表人物,他强调通过“坐忘”的修行方法去体悟“大道”,达到真人状态,“与道合一”;司马承祯则是道教代表人物,道教修炼的最终目的是“得道”,即“身与道同”,到长生久视的神人状态。这是庄子“坐忘”说和司马承祯《坐忘论》根本不同之处。
五、“坐忘”理论对当时及后代社会的影响
庄子生活的战国中期,是一个思想与学术都异常活跃的时代,儒家、墨家、名家、阴阳家、道家、法家各宗各派均兴盛流行开来,庄子在这“百家争鸣”的时代对老子学说关注最多,甚至被视为老子哲学的继承者。但是,庄子跟老子不同,用牟宗三先生的话说,老子哲学是“实有形态的形而上学”,庄子哲学是“境界形态的形而上学”,他说“老子之道有客观性、实体性及实现性,庄子则纯成为主观之境界。故老子之道为实有形态,而庄子则纯为境界形态。”[9]相比老子哲学的沉寂,庄子哲学更为洒脱通透。庄子哲学的自由潇洒的基调,逐渐演变成一种著名的审美心胸理论,为后代的美学家所继承和发展,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
庄子洒脱不羁的形象在魏晋时期引起效仿高潮,魏晋玄学兴起,文人雅士纷纷注重玄谈,关注“神”的修养[10]。名教的伦理纲常被看作束缚人发展的桎梏,许多人纷纷倡导自然风尚,其中尤以阮籍、嵇康等为代表,他们崇奉历史上的不羁人物,尤甚推庄子的洁身自好。另外,作为在汉代以后和老子并称的先秦道家代表人物,庄子学说也是道教理论的根源,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道教理论多依托于道家思想。
隋唐时期是我国道教全面发展的繁荣时期,司马承祯的《坐忘论》是隋唐道教重玄学的代表作,远续庄子和老子的虚心坐忘之论,吸收儒家正心诚意和佛教止观、禅定等思想,对早期道教重服气炼形、符箓祈祷、丹鼎服饵以求长生之说进行了扬弃和提高,使隋唐重玄之风走出清谈,具体化为道教“气全则生存”的宗教实践活动。这一学说对后来宋代道教的内丹学以及宋代理学家影响极大,周敦颐“无欲故静”的“主静”说,朱熹“惩忿窒欲”的“居敬”说,程颢教人“定性”的主张,王夫之的《庄子解》“坐忘忘吾”说等心性修养都有影响[8,p362]。
在当代社会,科技日益发达,人们每天面对琳琅满目的物品,外在的东西无时无刻不充斥着人的内心,功名利禄如往常一样对人们有着极大的诱惑力,而人们在拼尽全力去追逐这些外在的东西时,很少有人有时间反观内心,把所有的精力花费在内心以外的地方。人们看到了社会的进步,却没有更多感受到生活的幸福,许多人在追问“幸福是什么”。如果有一天,人们可以静下来向自己的内心问问自己最需要什么,或许答案便明了了。庄子和司马承祯的坐忘理论也许对人们反观自身,重寻自由和幸福有一定的帮助。
[1] 司马迁.史记[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10.
[2] 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M].北京:中华书局,1983.
[3] 郭齐勇.中国哲学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4] 朱哲,刑晓雪.大宗师篇“真人说”要论[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 2013,33(6):156-157.
[5] 卿希泰.司马承祯的生平及其修道思想[J].宗教学研究, 2003(1):4-7.
[6] 坐忘论[A].道藏[C].北京.文物出版社,上海:上海书店,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
[7] 王弼注.楼宇烈校释.老子道德经注校释[M].北京:中华书局, 2008.
[8] 任继愈.中国道教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
[9] 牟宗三.才性与玄理[M].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10.
[10] 蒋朝君,田湖.道学中的“坐忘”思想及其意义[J].华侨大学学报,2013(4):70-71.
(责任编辑、校对:孙尚斌)
The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Zhuangzi’s Seating Forgetting and Sima Chengzhen’s Sitting in Oblivion
ZHANG Qian
(The Philosophy Department,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46, China)
Zhuangzi, who was the representative of pre-Qin Taoism and Sima Chengzhen, who was the representative personage of Tang Taoism, had a gap about one thousand years. Zhuangzi created the famous words of Seating Forgetting, and Sima Chengzhen wrote a book named Sitting in Oblivion. Both of them had a profound influence in history.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are analyzed between the two of them.
Zhuangzi; Sima Chengzhen; Seating Forgetting
B223
A
1009-9115(2015)01-0096-04
10.3969/j.issn.1009-9115.2015.01.025
2014-06-11
张倩(1993-),女,安徽宿州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现代新儒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