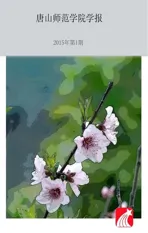崔浩与北魏经学
2015-02-13姚立伟扬州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江苏扬州225002
姚立伟(扬州大学 社会发展学院,江苏 扬州 225002)
崔浩与北魏经学
姚立伟
(扬州大学 社会发展学院,江苏 扬州225002)
崔浩与北魏经学关系紧密,其经学思想在太武帝时一度成为官方统治思想。通过对崔浩的经学著作、经学倾向与特点、经学地位、经学影响四个方面的梳理,来明确崔浩在北魏经学史上的地位。
崔浩;北魏;经学
崔浩是北魏历史上比较重要的一位人物,他担任司徒达19年之久,北魏前三朝重大军事、政治、文化决策他都多有参与。但关于能否认定崔浩“通儒硕学”,古今学者的观点差异较大。顾炎武在《日知录》卷一四“女巫”条借杜歧公的口表达了自己的观点,认为“道(太)武帝南平姑臧,东下山东,足为雄武之主,其时用事大臣崔浩、李顺、李孝伯等,多是谋猷之士,少有通儒硕学,所以郊祀上帝,六宫及女巫预焉”[1]。在顾炎武看来,崔浩算不上“通儒硕学”。宋代晁说之对崔浩的经学成就评价也不高,其《儒言·传势》讲“崔浩威福振宇内,其《五经》之注,学者尚之,至于勒为石经,逮夫……浩诛之后,无一人称道其说者,则前之所传者,非经也,势也”[2]。而明代胡应麟在《华阳博议》中则说“六经之学,广大闳深,历世名儒第专其一,有博于《易》者,有博于《书》者,有博于《诗》者,有博于《礼》者,有博于《春秋》者,有博于《尔雅》者。施、孟、梁、京诸人,博于《易》者也;伏、夏、周、刘诸人,博于《书》者也;齐、鲁、毛、韩诸人,博于《诗》者也;戴、曹、贺、贾诸人,博于《礼》者也;公、毂、邹、夹诸人,博于《春秋》者也;刘、郭、张、曹诸人,博于《尔雅》者也。若马融、郑玄、贾逵、王肃、刘炫、崔浩、颖达、德明数子,诸经并释,六籍兼该,义或未精,博斯称极”[3]。胡应麟将崔浩与马融、郑玄并举,认为他们都是能够“诸经并释,六籍兼该”“博斯称极”的“名儒”。顾氏仅从崔浩不能使太武帝郊祀全用汉礼而使“六宫及女巫预焉”来否定崔浩的经学成就,显然是欠公允的。而胡氏之说则比较恰当,崔浩治经称不上“第专”,其释经可能存在“义或未精”的不足,但可称为“博斯称极”的“通儒”。
一、崔浩的经学著作
崔浩的主要影响在明元帝、太武帝两朝政治的变化,使拓跋鲜卑的汉化过程加速,但其一切政治动向、社会行为无疑肇始于思想文化。崔浩家族为清河崔氏,中古山东高门士族,有很深的儒家文化渊源,其本传载崔浩本人“少好文学,博览经史。玄象阴阳,百家之言,无不关综,研精义理,时人莫及”[4,p807],家族传承、天资聪颖,造就了崔浩在北魏经学上的不凡成就,在北魏前期三个经学阵营①中,有魏晋经学倾向的派系便以崔浩为代表。
虽然崔浩“能为杂说,不长属文”[4,p812],其著书数量还是相当多的,《魏书》卷三五《崔浩传》载:“浩又上《五寅元历》,表曰:‘太宗即位元年,敕臣解《急就章》《孝经》《论语》《诗》《尚书》《春秋》《礼记》《周易》。三年成讫。……’”[4,p825]可见崔浩对儒学经典中的《周易》《尚书》《礼记》《春秋》《诗经》《论语》《孝经》都曾进行过注解,且三年完成,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崔浩儒学修养的深厚以及对儒家经典研究的深入。但是《隋书》卷三二《经籍志》载其著作仅四部:《周易》十卷、《急就章》二卷、《历术》一卷、《赋集》八十六卷。朱祖延所著《北魏佚书考》一书搜集崔浩著作有:《周易注》[5,p1-2]《汉纪音义》[5,p44-50]《女仪》[5,p72-73]《五行论》[5,p131]《食经》[5,p131-138]五部。综上,崔浩的经学著作到隋代还传世的不过《周易注》一部,随后此书也散佚了,仅留部分序文在《魏书》卷五二《张湛传》中:“浩注《易》,叙曰:‘国家西平河右,敦煌张湛、金城宗钦、武威段承根三人,皆儒者,并有俊才,见称于西州。每与余论《易》,余以《左氏传》卦解之,遂相劝为注。故因退朝之余暇,而为之解焉。’”[4,p1154]
二、崔浩的经学倾向与特点
崔浩的传世著作虽然不多,但从史书所载的片断大致可以了解到,崔浩的经学有魏晋经学倾向,但并未如两晋经学那样特别玄化,从其本传所载其“性不好《老》《庄》之书,每读不过数十行,辄弃之,曰:‘此矫诬之说,不近人情,必非老子所作。老聃习礼,仲尼所师,岂设败法文书,以乱先王之教。袁生所谓家人筐箧中物,不可扬于王庭也。’”[4,p812]可知。
基于其经学倾向,崔浩的经学有以下三个特点:
一是与郑玄相异。这与北朝时期的经学主流“尊郑”是不同的,《魏书》卷八四《儒林传》载:“(陈)奇所注《论语》,矫之传掌,未能行于世,其义多异郑玄,往往与司徒崔浩同。”[4,p1847-1848]陈奇与崔浩同属北魏初期有魏晋经学倾向的派系,于此可知崔浩经学特点之一为与郑玄“多异”。
二是用《春秋左氏传》立论。崔浩《周易注》序文中所说“每与余论《易》,余以《左氏传》卦解之”可见这一特点。崔浩好用《春秋左氏传》来论证其观点的合理性还体现在朝堂政争上。《魏书》卷三五《崔浩传》载:“初,姚兴死之前岁也,太史奏:荧惑在匏瓜星中,一夜忽然亡失,不知所在。或谓下入危亡之国,将为童谣妖言,而后行其灾祸。太宗闻之,大惊,乃召诸硕儒十数人,令与史官求其所诣。浩对曰:‘案《春秋左氏传》说神降于莘,其至之日,各以其物祭也。请以日辰推之,庚午之夕,辛未之朝,天有阴云,荧惑之亡,当在此二日之内。庚之与未,皆主于秦,辛为西夷。今姚兴据咸阳,是荧惑入秦矣。’”[4,p808-809]又载:“会闻刘裕死,太宗欲取洛阳、虎牢、滑台。浩曰:‘陛下不以刘裕欻起,纳其使贡,裕亦敬事陛下。不幸今死,乘丧伐之,虽得之不令。《春秋》:晋士丐帅师侵齐,闻齐侯卒,乃还。君子大其不伐丧,以为恩足以感孝子,义足以动诸侯。今国家亦未能一举而定江南,宜遣人吊祭,存其孤弱,恤其凶灾,布义风于天下,令德之事也。若此,则化被荆扬,南金象齿羽毛之珍,可不求而自至。裕新死,党与未离,兵临其境,必相率拒战,功不可必,不如缓之,待其恶稔。如其强臣争权,变难必起,然后命将扬威,可不劳士卒,而收淮北之地。’”[4,p813-814]
三是好用阴阳灾异谶纬之说。这一点在北魏初年的儒士中并不鲜见,《魏书》卷二四《燕凤传》载燕凤“博综经史,明习阴阳谶纬”[4,p609],《魏书》卷二四《许谦传》载许谦“少有文才,善天文图谶之学”[4,p610]。崔浩也是如此,其本传载:“三年,彗星出天津,入太微,经北斗,络紫微,犯天棓,八十余日,至汉而灭。太宗复召诸儒术士问之曰:‘今天下未一,四方岳峙,灾咎之应,将在何国?朕甚畏之,尽情以言,勿有所隐。’咸共推浩令对。浩曰:‘古人有言,夫灾异之生,由人而起。人无衅焉,妖不自作。故人失于下,则变见于上,天事恒象,百代不易。《汉书》载王莽篡位之前,彗星出入,正与今同。国家主尊臣卑,上下有序,民无异望。唯僭晋卑削,主弱臣强,累世陵迟,故桓玄逼夺,刘裕秉权。彗孛者,恶气之所生,是为僭晋将灭,刘裕篡之之应也。’诸人莫能易浩言,太宗深然之。五年,裕果废其主司马德文而自立。南镇上裕改元赦书。时太宗幸东南潟卤池射鸟,闻之,驿召浩,谓之曰:‘往年卿言彗星之占验矣,朕于今日始信天道。’”[4,p811-812]崔浩在此充分运用了阴阳灾异、天人感应学说。崔浩说服太武帝北伐蠕蠕时也用阴阳之说[4,p816]。
因为好用阴阳灾异学说,也造成了崔浩好观“星变”,其本传载:“浩明识天文,好观星变。常置金银铜铤于酢器中,令青,夜有所见即以铤画纸作字以记其异。”[4,p818]崔浩还通过观测天文来制定律令,即《五寅元历》,其本传载:“浩又上《五寅元历》,表曰:‘……复诏臣学天文、星历、《易》式、九宫,无不尽看。至今三十九年,昼夜无废。臣禀性弱劣,力不及健妇人,更无余能,是以专心思书,忘寝与食,至乃梦共鬼争义。遂得周公、孔子之要术,始知古人有虚有实,妄语者多,真正者少。自秦始皇烧书之后,经典绝灭。汉高祖以来,世人妄造历术者有十余家,皆不得天道之正,大误四千,小误甚多,不可言尽。臣愍其如此。今遭陛下太平之世,除伪从真,宜改误历,以从天道。是以臣前奏造历,今始成讫。谨以奏呈。唯恩省察,以臣历术宣示中书博士,然后施用。非但时人,天地鬼神知臣得正,可以益国家万世之名,过于三皇、五帝矣。’”[4,p825-826]可见崔浩制定律令的过程是一个“除伪从真”的过程,在崔浩心目中的真为“周公、孔子之要术”,并且在崔浩看来阴阳、灾异、星变、谶纬与儒家经典是相互影响的。
三、崔浩的经学地位
崔浩在北魏前期的经学地位是极为尊宠的,尤其是明元、太武两朝,“可以说在太武帝时期,儒学相对于北魏初期有了比较大的发展。在这个过程中,崔浩个人对经典的解释成了官方的意识形态”[6]。之所以能成为官方意识形态,大体有以下四个原因:
一是北魏明元帝深受崔浩的影响。崔浩本传载:“太宗初,拜博士祭酒,赐爵武城子,常授太宗经书。……太宗好阴阳术数,闻浩说《易》及《洪范》五行,善之,因命浩筮吉凶,参观天文,考定疑惑。”[4,p807]其对明元帝的影响还表现在明元帝也好引《春秋》,崔浩本传载:“太宗恒有微疾,怪异屡见,乃使中贵人密问于浩曰:‘《春秋》:星孛北斗,七国之君皆将有咎。今兹日蚀于胃昂,尽光赵代之分野,朕疾弥年,疗治无损,恐一旦奄忽,诸子并少,将如之何?其为我设图后之计。’”[4,p812]
二是崔浩所注《五经》被刻成石经,一度成为官方定本,且规模宏大。崔浩本传载:“著作令史太原闵湛、赵郡郄标素谄事浩,乃请立石铭,刊载《国书》,并勒所注《五经》。浩赞成之。恭宗善焉,遂营于天郊东三里,方百三十步,用功三百万乃讫。”[4,p825]《魏书》卷四八《高允传》亦载其事[4,p1069-1070]。
王志刚先生考证,认为“可初步判定崔浩石经石史数事:第一,石经石史的位置在天郊东三里,另据《南齐书》卷57《魏虏传》所载之‘城西三里,刻石写《五经》及其《国记》’,则其东距北魏国都平城亦为三里。第二,石经石史的规模‘方百三十步’,步是古时的长度单位,其制历代不一,秦至隋时1步为6尺。北魏时1尺约合今0.28米。一百三十步,合780尺,等于今天的218. 4米。可见,崔浩石经石史占地每边长218.4米,面积达到 47698.56平方米。第三,石经石史的创制,前后历时近两年半多,用功达三百万。这些都充分表明崔浩石经石史的显赫与独特:所处地理位置恰好位于北魏祭天之天郊和国都平城一线的中心点;占地面积空前绝后;所用人功之大前所未有”[7]。所刻石经字数为180万字左右,碑刻当在330枚左右。由此可见,崔浩石经的影响在当时是相当大的。
三是崔浩将经学研究与政治理想结合,成为儒家理想的忠诚践行者。崔浩笃信“周公、孔子之要术”,积极要求恢复五等爵制。其本传载:“天师寇谦之每与浩言,闻其论古治乱之迹,常自夜达旦,竦意敛容,无有懈倦。既而叹美之曰:‘斯言也惠,皆可底行,亦当今之皋繇也。但世人贵远贱近,不能深察之耳。’因谓浩曰:‘吾行道隐居,不营世务,忽受神中之诀,当兼修儒教,辅助泰平真君,继千载之绝统。而学不稽古,临事暗昧。卿为吾撰列王者治典,并论其大要。’浩乃著书二十余篇,上推太初,下尽秦汉变弊之迹,大旨先以复五等为本。”[4,p814-815]崔浩对儒家理想之诚,甚至使北魏道教领袖寇谦之要求“兼修儒教”,可见其感召力之强。
四是崔浩在推动儒家正统地位在北魏确立的过程中,积极打压佛教。崔浩本人“不信佛、道”②,其本传载:“浩非毁佛法,而妻郭氏敬好释典,时时读诵。浩怒,取而焚之,捐灰于厕中。……浩既不信佛、道,(崔)模深所归向,每虽粪土之中,礼拜形像。浩大笑之,云:‘持此头颅不净处跪是胡神也。’”[4,p826-827]基于此崔浩积极推动了太武帝灭佛事件的发生。
四、崔浩的经学影响
崔浩经学的承前启后作用明显。崔浩注《五经》本身就是对汉末以来“马、郑、王、贾”诸注的辩证总结,这是其承前之作用。崔浩的身份地位与个人好尚也影响了北魏中后期的经学发展,北魏中后期很多经学家都与之存在或亲或疏的关系。
一是与河西经学关系密切。正因为崔浩的重视、礼遇与帮助,自凉州东迁平城的河西经学家才得以立身安命、研究经典。《魏书》卷五二《张湛传》载:“司徒崔浩识而礼之。……湛至京师,家贫不粒,操尚无亏,浩常给其衣食。每岁赠浩诗颂,浩常报答。及浩被诛,湛惧,悉烧之。”[4,p1154]《魏书》卷五二《阴仲达传》载:“阴仲达,武威姑臧人。祖训,字处道,仕李暠为武威太守。父华,字季文,姑臧令。仲达少以文学知名。世祖平凉州,内徙代都。司徒崔浩启仲达与段承根云,二人俱凉土才华,同修国史。”[4,p1163]及崔浩被诛,河西经学家也多被牵连,受到严重打击,如河西著名经学家段承根与宗钦。《魏书》卷五二《段承根传》载:“浩诛,承根与宗钦等俱死。”[4,p1159]但河西经学家并未被一网打尽,到献文帝时还有影响,《魏书》卷六〇《程骏传》载:“太延五年,世祖平凉,迁于京师,为司徒崔浩所知。高宗践阼,拜著作佐郎;未几,迁著作郎。为任城王云郎中令,进箴于王,王纳而嘉之。……显祖屡引骏与论《易》《老》之义,顾谓群臣曰:‘朕与此人言,意甚开暢。’”[4,p1345]
二是专习郑玄、何休、服虔等人之注的汉代经学派系也与崔浩关系密切,如高允。虽然二人学术观点不同,但共事、问学多年。
三是与南来经学家也多有交往,如《魏书》卷三八《袁式传》载:“袁式,字季祖,陈郡阳夏人,汉司徒滂之后。父渊,司马昌明侍中。式在南,历武陵王遵谘议参军。与司马文思等归姚兴。泰常二年归国,为上客,赐爵阳夏子。与司徒崔浩一面,便尽国士之交。是时,朝仪典章,悉出于浩。浩以式博于古事,每所草创,恒顾访之。性长者,虽羁旅飘泊,而清贫守度,不失士节,时人甚敬重之,皆呼曰袁谘议。”[4,p880]《魏书》卷五五《刘芳传》载北魏后期著名的经学家刘芳“祖母,浩之姑也”[4,p1219],可能也受崔浩经学影响。
崔浩主要的影响对象还是秉持魏晋经学传统的经学家,如陈奇等,“其义多异郑玄,往往与司徒崔浩同”。但崔浩、陈奇这一魏晋经学的阵营由于不适应北朝经学潮流而消亡了。标志性事件就是“赞扶马郑”、执汉代经说的游雅与陈奇间的激烈冲突。《魏书》卷八四《儒林传》载游雅“因告京师后生不听(陈奇)传授”[4,p1847],最后将陈奇置于死地。陈奇死后,以崔浩为代表的魏晋经学阵营便趋于崩溃瓦解,在北魏经学史中所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小,北魏经学从第一阶段的兼收并蓄进入到了第二阶段以郑学为主③,也就是《隋书》卷七五《儒林传》所载的“河、洛《左传》则服子慎,《尚书》《周易》则郑康成”[8]的北朝经学“深芜”的典型阶段。
五、结语
崔浩积极推动儒学成为北魏官方意识形态,好说阴阳、灾异、天人感应、谶纬,我们似乎从崔浩身上看到了西汉大儒董仲舒的影子。崔浩笃信儒教,在日常生活中秉持儒教并与佛、道进行斗争,推动太武帝灭佛等行为,我们似乎又从崔浩身上看到了唐代中后期韩愈的影子,虽然其没有如韩愈提出“道统”学说这样的理论论争工具,但在维护儒教正统、努力排斥佛教在政治、文化生活中的渗透方面无疑是一致的。因此,可以说崔浩是经学史上一位承前启后的人物,崔浩的经学北魏经学乃至中国经学史发展上重要、不可忽略的一环。
[注释]
① 焦桂美的《南北朝经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346)中认为“从经学习尚上看,北魏前期经学至少存在三个阵营:一个是以梁祚,高允等为代表的,专习郑玄,何休,服虔等人之注的汉代经学派系;一个是以崔浩,陈奇,张吾贵等为代表的,以非难马(融)郑(玄),追求新异为特点的带有魏晋经学倾向的派系,还有一个是以迁徙者王肃等为代表的较为典型的南学派系。”
② 崔浩对道教的态度比较复杂,既称“不信佛,道”,又屡有道教的行为在其身上出现,如其本传载“初,浩父疾笃,浩乃剪爪截发,夜在庭中仰祷斗极,为父请命,求以身代,叩头流血,岁余不息,家人罕有知者”,如果这也还可视为儒家孝的体现的话,其后期与寇谦之交往,“既得归第,因欲修服食养性之术,而寇谦之有《神中录图新经》,浩因师之”却可佐证其有信道教的倾向。另外,崔浩善书以及清河崔氏与笃信天师道的范阳卢氏有密切的姻亲关系,这些侧面都佐证了崔浩信道教的可能性。因此陈寅恪先生在《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金明馆丛稿初编》,三联书店,2009: 16-17)一文中就认为以崔浩为代表的清河崔氏与范阳卢氏一样,为天师道世家。
③ 焦桂美在《南北朝经学史》(345-353)中的《北朝经学风尚之变迁》一节中将北朝经学划分为三个阶段:兼容并蓄——北朝前期的经学风尚;郑学为主——北朝中期的经学风尚;南学北渐——北朝后期的经学风尚。
[1] 顾炎武.日知录集释(全校本)[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6:864.
[2] 晁说之.儒言[M].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698册:508.
[3] 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382-383.
[4] 魏收.魏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5] 朱祖延.北魏佚书考[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
[6] 张轶.北魏郑玄易学研究[J].河南社会科学,2008(4):31.
[7] 王志刚.北魏崔浩石经石史考[J].史学史研究,2010(3):21.
[8] 魏征,令狐德棻.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1705.
(责任编辑、校对:郭静)
Cui Hao and the Northern Wei Dynasty’s Classics
YAO Li-wei
(College of Social Development, Yangzhou University, Yangzhou 225002, China)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ui Hao and the Northern Wei Dynasty Classics is close. Cui Hao’s classics ideology became the ruling ideology during Emperor Taiwu’s reign. The study is carried out in four aspects: Cui Hao’s classics books, the tendencie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he works, the position of the classics, and the influence of them. It is hoped to clarify the status of Cui Hao’s classics in Northern Wei.
Cui Hao; the Northern Wei Dynasty ; classics
K239.21
A
1009-9115(2015)01-0077-04
10.3969/j.issn.1009-9115.2015.01.020
2014-09-16
姚立伟(1986-),男,河北唐山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魏晋南北朝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