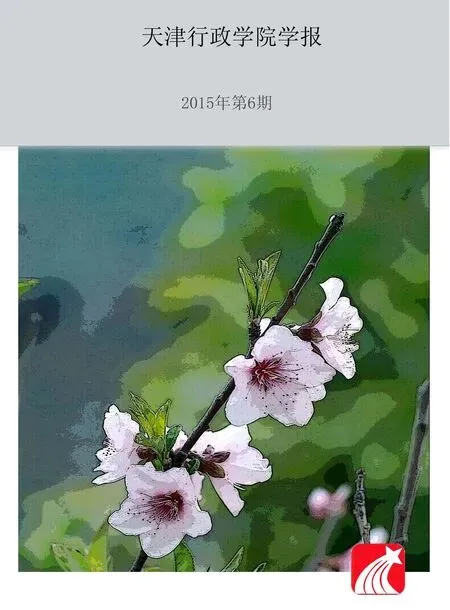监督制约“一把手”:政治生态建设的重点之域
2015-02-12赵园园
赵园园
(中共南通市委党校,江苏 南通 226007)
政治生态是党风、政风和社会风气的综合反映,也是影响人们价值取向和行为选择的重要因素。因此,在全面依法治国和全面从严治党不断成为强势话语的当前,重建政治生态逐渐演化成一个颇富学术增量的研究话题。综观已有研究,大致可见主要有两种理路:一是意识到“优化乃至重构党内政治生态,是我们党必须面对和要深入解决的一个关键问题,是全面从严治党内在的紧迫要求,是全体共产党员尤其是各级党员干部必须严肃担当的重大政治责任”[1];二是提出优化政治生态的政策性建议,如加强制度建设、重塑社会的政治伦理、建立公平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推进民主法治等。毫无疑问,对这些问题的关注,是研究政治生态议题的应有之义。
然而,任何事物都有重点。政治生态建设同样如此。在其复杂系统里,权力的监督与制约始终是关键。政治生态的优恶良善同权力运行状况密切相关。对权力进行有效的监督与制约,成为政治生态建设的核心问题。而在权力结构中“一把手”是“关键的少数”。虽然“一把手”并不是一个正规的文本称呼,但他们是公共政策的最后决策人和最终拍板人;监督制约“一把手”构成政治生态建设的重点内容。在这个意义上讲,从关注“一把手”的监督制约入手,能为分析政治生态问题提供一个新的切入点。
一、权力监督与制约:政治生态建设的核心问题
在政治生活中,权力具有巨大的吸引力。它是“在实现自己的目标时克服他人的阻力的能力”[2](p.279),或者是“一个人或许多人的行为使另一个或其他的许多人的行为发生改变的一种关系”[3](pp.697-698)。也就是说,权力具备较强的控制力、影响力和支配力。正因如此,权力成为人们竞相争夺的对象。对于一些人而言,掌控权力不仅意味着身份和地位,而且意味着以权谋私的可能。因而,权力一旦脱缰,就会对政治生态形成直接冲击乃至破坏。从这个意义上讲,对权力形成有效的监督制约,构成政治生态建设的重要议题。
政治生态是人们在分析政治问题时借鉴生态学理论而产生的一个概念,它为分析行动主体政治行为选择提供了一个新视角。“政治生态是指在一定社会中形成的政治环境,政治关系,政治行为模式,政治评价标准及其相互关系的总和,是政治环境之所以形成,政治关系之所以构建,政治行为之所以达成,政治评价标准之所以确立的内在机制和发生机理。”[4]作为一种存在物,权力是在政治生态环境中运行的。因此,政治生态对于权力的运行及其质态具有深层次影响。反之,权力的运行状况对政治生态建设也会发挥反作用:受到监督与制约的权力,能让人感觉到政治生态的风清气正,继而进一步产生维护和匡正政治生态的动力;而权力的肆意妄为是对政治生态造成破坏的最直接来源。
以对政治生态产生明显影响的腐败为例。腐败的本质是权力的滥用和异化。腐败之所以产生,从根本上讲就是公共权力被滥用而为私人或小团体谋利。“公共权力的存在,国家管理权的存在,人类社会生存所需,但如果这种权力高度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又没有适当的制约,那么公共权力就易于失去控制而被滥用。”[5]所以,孟德斯鸠早就告诉人们,“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6](p.154)。阿克顿勋爵更是断言,“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7](p.154)。既然权力具有如此之大的扩张性,且对政治生态产生直接影响,就必须对其进行监督和制约。由此可见,政治生态建设与权力监督制约之间具有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权力监督制约构成政治生态建设的核心议题。
二、监督制约“一把手”:权力规范运行与政治生态建设的共同所指
在权力监督与制约构成政治生态建设重要议题的情况下,如何对权力形成有效的监督与制约则成为关键。但是,由于权力系统本身的复杂性,不可能漫无边际地四处游离,而必须在最核心之处发力。从实践看,在目前的体制下“一把手”是这个核心所在。抓住了“一把手”这个“关键的少数”,就抓住了促进权力规范运行和政治生态建设的命脉。
在中国的政治体制中,“一把手”本来不是一个正规的称呼,在执政党的政策文件和国家法律中都未见“一把手”的表述。只是在现实生活中,它成为人们对一个单位或一个地区主要负责人的别称。由于“一把手”在领导班子中处于核心地位,拥有人财物的管理权、决策权、实施权、监督权和支配权,位高权重,其权力运行状况直接影响着一个地区或一个部门的事业兴衰。毋庸讳言,对“一把手”赋权,让其具备一定的决策权和拍板权,有其必要性。但是,在日常工作中,一些“一把手”堪称“一号人物”:说一不二、独断专行。对于这种情况,很多人称之为“一把手综合症”,言指一些人在担任“一把手”时因权力失去监督制约而产生的权力妄为现象。对此,一些人用“决策一言堂,用人一句话,花钱一支笔”来概括。一些“一把手”在提拔之前大多比较谨慎,但是随着岗位的变化,尤其是随着手中所掌握的权力给其带来的利益和诱惑,很多人逐渐逃离到权力规范运行之外,成为不受监督和制约的“异类”群体。
当“一把手综合症”演化成“一把手”腐败时,它对政治生态所产生的危害是其他腐败无法比拟的。第一,会滋生塌方式腐败,甚至引发政治危机。一个客观情形是“一把手”腐败并不是其个人单独或赤裸裸地实施腐败行为,而往往是借“加强领导”的名义,集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于一身,视监督与制约为儿戏。如果发现班子成员有不同意见,成为自己滥权揽权的障碍,便通过调整分工的名义大肆排挤或打击报复,以此实现加强自己权力、排除异己的目的。长此以往,就会在其部门或地区形成示范效应、连锁反应,其他干部会相互仿效;而一旦仿效成风,就会导致塌方式腐败。“一把手”失去监督制约引发的腐败,其结果便是裹挟、带坏一批干部,严重破坏所在地方、部门的政治生态。周永康案、苏荣案、李春城案、隋风富案等都是例证。第二,造成巨大损失,影响地区或部门发展。政治生态是一个地区或部门发展的基础,一旦遭受破坏,就意味着发展的基础受到了侵蚀。一些案例表明,患上综合症的“一把手”在一些重大决策上倾向于个人拍板,将重大问题决策权集中到个人手里,甚至采取“暗箱操作”的办法实现个人目的,从而使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流于形式。实际上,任何人都是有限理性的,都存在信息和知识盲区,不可能熟知所有情况。因此,当“一把手”大权独揽、依据个人判断作决策的时候难免出现失误;而一旦出现失误,就会产生巨大损失、影响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当前,因“拍脑袋”决策而导致的“人走政息”、决策失误等案例已经不绝于耳。第三,毒化社会风气,释放负面效应。患上“一把手”综合症的人,错误地将霸道当干练,将独断当能力,将高压当效率,习惯于用武断、高压手段推动工作,工作方法粗暴生硬,甚至以权压人。长此以往,不仅会破坏执政党群众工作的优良传统而且会直接损害干群关系,从而成为影响政治社会稳定的突出问题。
三、“一把手”监督难:制约政治生态重建的突出问题
“一把手”需要监督和制约,但是对其实施有效的监督制约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从总体上看,有三重因素阻碍着“一把手”的监督制约。
(一)主观世界发生动摇,一些“一把手”缺乏接受监督制约的思想意识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思想意识决定个人行为。理想缺失是最根本的缺失,信念滑坡是最危险的滑坡。人们常讲,一个人犯错误往往是一念之差。其实,这个“念”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念头,而是其理想信念和党性修养支配的人生观、价值观、权力观。在现代社会,一些“一把手”一边勤奋努力地工作,一边又毫不松懈地腐败堕落。其原因何在?从深层次上讲,还是其理想信念发生了动摇、出现了问题。在有些“一把手”的脑海里,只要经济建设搞上去了,其他方面“任性”一点没关系。于是,曾经牢牢守住的理想信念、党性修养在物欲横流和金钱美色的引诱下逐渐消退。在理想信念缺失的情况下,一些“一把手”看到有的商人一夜暴富,艳羡不已;看到同僚平步青云,心生嫉妒;看到别人处处潇洒,盲目追求。可想而知,在这种情况下,要其主动接受监督制约何其困难。一些查处的“一把手”在忏悔录中最多的反思就是:“根本上讲,还是放松了要求,失去了信仰,丢失了党性,不再以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有愧于党。”
理想信念和党性修养的不断丧失,带来的结果就是一些“一把手”对自身要求不高,廉洁意识差,遇事不讲原则,缺乏主动接受监督的意识。在他们看来,自以为是、自我中心、自高自大、脱离监督是能力的表现。在丧失监督意识的情况下,一些“一把手”几乎成了“一霸手”,他们认为公款吃喝玩乐、收受贿赂都是小事,把与商人的正常工作关系变成为私人关系甚至“哥们关系”,利用职权为其批工程、拉项目,逐渐被拉拢腐蚀,最终陷入严重违法违纪的泥潭。
(二)权力结构严重失衡——监督制约“一把手”的最大掣肘
对于身居重要岗位的“一把手”而言,可谓权力独大:既有用人的提名权、最后决定权,也有决策的再议权与否决权。简而言之,他们在重大决策、重大项目、干部提拔等重要事项上享有“一锤定音”的权力。从一些被查处的“一把手”的忏悔录中可见,权力过大、高度集中进而逃避监督、肆意弄权,是其共同的病灶。在权力高度集中且失去监督的情况下,“一把手”腐败便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权力意味着担当也意味着责任的承担,但在一些“一把手”那里,他们似乎只愿意享受权力,不愿意承担责任,理论预设上的权责对称遭遇了实践的阻滞:虽然在政策文本、法律规章等制度层面,均对权力职责的情况作了界定,但实际上很少付诸实践。在一些“一把手”眼里,追责似乎并不重要,自己离追责似乎很遥远。即使一些重大决策发生失误需要有人承担责任,一般也是由分管工作的副职承担责任,很少对“一把手”进行追责。即便要追究“一把手”的责任,也是“轻描淡写”、“一笔带过”。这种情况长期而来的结果便是“一把手”缺乏接受监督的意识,有的甚至把上级的监督认为是对自己的不信任、不放心,把同级的监督视为跟自己过不去、找别扭,把下级的监督视为让自己丢面子、失威信,甚至拒绝监督、反对监督、拖延阻挠监督。
(三)编织、运作腐败圈子,是一些“一把手”对监督制约体系、政治生态的最直接破坏
圈子腐败是破坏当前政治生态的一大直接因素,而在圈子腐败里“一把手”始终是重要推手。这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其主观意愿。在权力独大尤其是权力扩张的诱惑下,一些“一把手”逐渐痴迷权力,进而总想凭借权力的外衣谋取私利。但是,出于遮人耳目和逃避审查等多重因素的考量,他可能需要寻找其他人作为其滥权腐败的替身或“眼线”。在这种情况下,他便主动编织、运作圈子,以让圈子里的人替其谋利。于是,以“一把手”为核心、权力为纽带而逐渐形成的利益同盟、腐败圈子开始显现。二是外在环境的诱惑。权力具有吸附性和诱惑性,手握权力的“一把手”如同巨大的磁场,无形之中会对其身边人、亲戚、朋友、商人产生巨大的吸引力。于是,这个磁场逐渐演化成一个圈子。就客观而言,有时候并不是“一把手”自己有意编织、运作这个圈子,而是他在无形之中被自然裹挟进来;而一旦裹进圈子,则会成为人们吹捧、巴结、讨好乃至算计的对象。然而,不管是“一把手”因主观意愿而编织圈子,还是在外界因素的推动下裹进圈子,结果都是对政治生态的极大破坏。
四、监督制约“一把手”:探寻政治生态建设的有效突破口
从上述讨论可见,对“一把手”的权力进行监督与制约,构成政治生态建设的突破口。加强对“一把手”的监督制约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但以下四个方面是重点。
(一)构建分权制衡机制
如前所述,一些“一把手”之所以能逃离监督和制约,同权力高度集中且权责不对称的这种结构密切相关。“一种体制具备不具备抑制腐败的能力,或在多大程度上具备抑制腐败的能力,关键取决于这种体制中权力结构的功能分化与运行的整合。”[8]因此,分化权力结构、构建分权制衡机制对于“一把手”监督制约而言至为重要。
对权力进行监督和制约,本身就是基于权力分化的设想。权力分化既是现代公共事务日趋复杂对公共权力提出必然要求的结果,也是现代社会分工在政治生活领域的具体反映。权力分化的具体表现就是国家权力被分解为不同的职权,并由不同的人行使。从监督与制约的不同内涵看,监督是基于权力功能性的分权“即按照专业化的职能分工,将国家权力赋予一个对应的权力主体,通过其他主体或者由权力授予者本身对其予以监督。监督不仅应用于权力的横向功能性控权,也应用于纵向的权力安排,在这种权力配置方式下,权力主体在纵向授权后,需要对被授予者的权力行使情况进行监视、督察”[9]。制约则是基于权力运行过程的分权,把权力分解为不同的程序,由不同的机构行使,彼此相互制衡。尽管二者内涵略有差异,但本质都是一致的,即强调分权制衡。所以,“当政治学家们声言探寻科学合理的权力运行机制时,实际上他们所思考的是如何把公共权力置于有效的监督之下,或者使政治权力在精心设计出来的政治体制之中受到难以回避的制约”[10]。
对“一把手”进行有效监督制约,需要的正是分权和制衡。从理路看,这种分权包含两层含义:内部分权和外部制约。就内部分权而言,就是应该对权力实现分设,分化其行使过程。对此,可以根据集体领导和分工负责相结合的原则,厘清“一把手”权力的内容边界,强化“一把手”和班子成员间相互制衡。比如,明确“一把手”不直接分管人事、财务、工程建设、政府采购、产权交易、土地矿产等工作,改变“一把手”一把抓的状况。在办公会议题的确定上,不能只由“一把手”说了算,可以规定只要有一定数量的班子成员同时提出,就必须列入会议议题。还可探索建立副职对正职有不同意见可以直接向上级反映并能得到重视和受到保护的机制,通过扩大副职职权来制衡“一把手”的权力。就外部制约而言,要保障私权对公权的有效制约。“私权力是相对于公共权力而言的,是自律的社会组织和个人掌握和行使的治理私人事务的权力,它包括社会公共权力与财产权利。”[11]人类政治生活的经验表明,权利是权力的产生基础。“个人权利是公共权力正当性的根据,公共权力的行使也应当以扩展个人权利为目的。”[12]因此,要鼓励和引导公众参与,并为有效的媒体监督创造条件。
(二)加大对圈子腐败的治理力度
圈子腐败为“一把手”逃离监督制约、破坏政治生态提供了隐形外衣。从这个意义上讲,有效治理圈子腐败,是监督制约“一把手”、重建政治生态的基础性工程。
“一把手”为什么要编织圈子、挤入圈子?圈子为什么能运作起来?说到底,还是权力在作祟。因此,治理圈子腐败,重点还是在于约束权力。权力的约束首先来自权力的分设。这是对历史经验的借鉴和现实情况的反思。基于此,可以探索分权机制,使“一把手”的权力时刻处于制衡状态,防止权力集中造成拉帮结派。权力分设后,还需要明确权力的责任,特别是要明确“一把手”在人财物及重大事项决策中的责任。“一把手”之所以编织圈子,同其试图逃避监督直接相关,因此,应坚持权力运行的阳光化。让“一把手”在阳光下用权,进而促使隐性的权力能公开化,显性的权力能规范化,这样才能断掉“一把手”及其圈子肆意弄权的可能性想法和行为。尤其是要在阳光下,监督“一把手”的用人权、决策权和支配权,让其所有公务行为都处于阳光的环境中运行。
圈子本质上是一种利益联盟、利益均沾的腐败共同体,通过权力完成利益输送是其主要逻辑。从这个角度上讲,根治圈子腐败需要从制度层面优化利益结构,减少人们通过制度漏洞来谋取非法利益的空间和可能。所以,实施制度反腐、加强国家层面的反腐败立法都是需要深入推进的重要工作。
(三)锻造社会廉洁价值观
公众对权力运行情况的态度及行为取向,是对“一把手”进行监督制约的有力杠杆。当前的一个客观现实是,由于一些“一把手”肆意弄权贪赃枉法,在部门内部或所在地区成为“一霸手”对班子成员大肆打压,在单位外则对公众耍弄权术、耀武扬威。这些因素综合在一起,给人以“腐败无处不在”的假象,甚至释放出权力无所不能的信号。当这种情况超过一定程度的容忍度,以至于在心理上丧失对权力运行的警觉。这种情况反映的就是社会廉洁价值观的缺失。
廉洁价值观蕴含于廉洁文化的氛围之中。因此,要通过廉洁文化建设,让人们在廉洁文化的浸润中自觉形成抵制腐败的思想认识,并从内心深处认同廉洁行为,远离腐败行为,引导人们自觉抵制各种腐败行为。廉洁文化建设的当前重点是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引领,在全社会形成共同的理想信念、精神支柱和道德规范,筑牢权力监督、社会廉洁的“定海神针”。但是,不管采取何种方式,都要坚持通俗化、大众化的原则和方向,提升廉洁文化的亲和力、感染力,减少它与人们日常生活的距离,进而成为人们的自觉行动。
社会廉洁价值观的形成,不仅与教育密切相关,而且应注重“落地”。因此,可以从基层社会微观廉洁生态治理入手,将微观的基层单元治理好。比如,在社区治理中,强化基层群众自治中的自我监督功能,让居民从日常生活中锻造社会廉洁价值观。微生态建设好了,就好比畅通了江河支流,就会减少大江大河发生洪水泛滥悲剧的可能性。一些实践表明,这是完善社会廉洁生态系统自我修复功能的重要基础。
(四)抓住用人和决策腐败两大关键,重典治乱
“一把手”用权腐败破坏政治生态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用人和决策。其中,用人腐败是最大的政治腐败,直接损害党的公信力,影响党的执政能力。因此,监督制约“一把手”,必须重点惩治用人腐败问题,切实改变选人用人问题上少数人甚至一个人说了算、以所谓组织程序和组织手段屏蔽人民群众民主权利的做法,同时完善和加强法律追究,特别是向上追究,坚决打击用人腐败。这就要求在选人用人过程中严格执行相关法律法规,严明选人用人工作纪律,明确选人用人的程序和责任追求制度,形成一条完整的选人用人监督链,从制度上解决“一把手”在选人用人上“说了算”的问题。同时要营造风清气正的选人用人环境,尤其要通过监督检查,严厉处罚选人用人中存在的腐败问题,提高用人腐败成本。
决策腐败的危害越来越受到社会关注。“一把手”掌握着核心的资源和权力,是公共决策的最后拍板人。正因如此,决策腐败极易成为“一把手”权力腐败的重灾区。对于决策腐败,有人称之为“不落腰包的腐败”、“紫色腐败”、“决策失误”,这类腐败从表面上看似乎不是谋私,但实质上是一种间接谋私行为,具有谋取某种功利的强烈隐蔽性、随意性、盲目性和后发性。许多决策腐败在让“一把手”获得“功绩”的同时,滋生了大量的经济腐败和政治腐败。因此,能否根治决策腐败构成能否监督制约“一把手”的重中之重。对此,应通过采取专家咨询、第三方评估、社会听证、责任倒查等措施,建立健全一种程序严密、规则科学、相互制约、责任清晰的公共事务决策机制,促进科学决策、民主决策,其中重点要明确决策主体的责任。责任是权力的孪生物,“一把手”拥有决策拍板的权力,就要承担决策失误、腐败的责任。因此,要向那些“拍脑袋决策,拍胸膛保证,拍屁股走人”的“一把手”亮“红灯”;对那些“未竣工即拆除式”的胡乱决策者,则要加重处罚,以提高“决策腐败”的成本,降低决策腐败的发生概率。
[1]包心鉴.论优化党内政治生态[N].光明日报,2015-05-13.
[2][美]D.P.约翰逊.社会学理论[M].南开大学社会学系.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8.
[3]大不列颠百科全书(第14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
[4]戴长征.社会政治生态视角下的腐败与反腐败斗争[J].探索与争鸣,2013,(2).
[5]高新民.重构政治生态[N].学习时报,2015-04-01.
[6][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M].张雁深.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7][英]阿克顿.自由与权力[M].落亚峰.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8]汪玉凯.抑制腐败要注重从体制入手[J].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学报,2012,(2).
[9]陈国权,周鲁耀.制约与监督:两种不同的权力逻辑[J].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6).
[10]张康之.评政治学的权力制约思路[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0,(2).
[11]蒋永甫.乡村治理视阈中的农民土地财产权——一种私权力取向的研究路径[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2).
[12]叶传星.在私权利、公权力和社会权力的错落处——“黄碟案”的一个解读[J].法学家,2003,(3).
[责任编辑:张英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