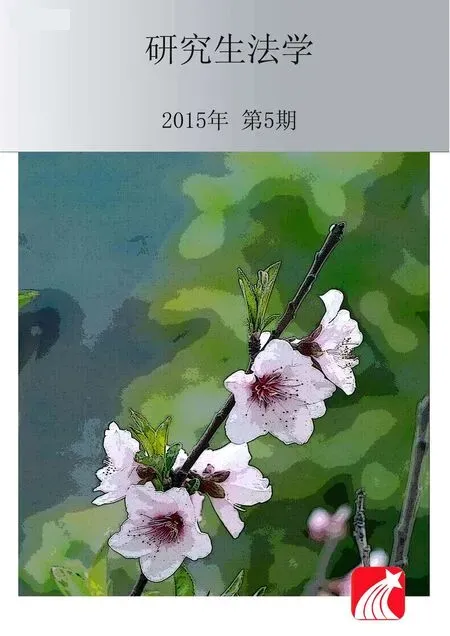从国际人权法视角看中国非法证据排除若干问题
2015-02-12马腾邱扬
马 腾 邱 扬
域外视野
从国际人权法视角看中国非法证据排除若干问题
马 腾*马腾,中国政法大学人权研究院人权法学专业2014级硕士研究生(100088)。邱 扬*邱扬,华东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军事法学专业2014级硕士研究生(200063)。
将非法证据明确加以排除,就斩断了在讯问和询问中施加暴力和强迫手段的必要性,这是从源头上根除刑讯逼供、暴力取证等酷刑行为的方法。从这个角度看,有必要以国际人权法的视角进行切入,对中国现有的非法证据排除若干问题加以分析,解读中国在此方面的立法进步和现存问题。
国际人权法 非法证据排除 刑讯逼供 人权保障
一、国际人权法与非法证据排除
(一)两项核心人权公约介绍
1948年,《世界人权宣言》将人权列入国际法范畴,此后联合国通过了大量的国际人权公约,构建了普遍性的国际人权标准。其中,有一些公约规定了特别重要的基本人权,这些公约构成了通常意义上的“核心人权公约”,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和《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以下简称《禁止酷刑公约》)就是其中重要的核心人权公约。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于1966年12月16日被联合国大会通过,并于1976年3月23日生效。《公约》下设人权事务委员会,负责接受各缔约国关于履行《公约》条款的国家报告,并负责作出针对各缔约国的结论性意见。这些结论性意见虽然不具有明确的法律效力,但它们在实际上往往起着指引各缔约国履行国际义务的作用。虽然中国尚未正式批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但已经于1998年签署该《公约》。而且,中国政府曾在不同场合多次表示,将在时机成熟时向全国人大提交批准该公约。因此,中国的立法、行政和司法等一系列措施都应当逐渐向该公约的要求靠拢。
《禁止酷刑公约》于1984年12月10日被联合国大会通过,并于1987年6月26日正式生效。与《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相类似,《禁止酷刑公约》下设禁止酷刑委员会,负责接受各缔约国关于履行《公约》条款的国家报告,并负责作出针对各缔约国的结论性意见。中国于1986年12月12日签署《禁止酷刑公约》,并于1988年10月4日批准该《公约》。同年11月3日,《公约》对中国生效。自1988年《公约》对中国生效以来,根据中国提交的国家报告,禁止酷刑委员会分别于1993年、1996年、2000年和2008年通过了4份针对中国的结论性意见。
(二)人权公约对非法证据排除的规定
非法证据排除通常是指:在司法诉讼中,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使用非法手段取得的证据不得在法庭审判中被采纳。当然,广义上的非法证据排除也涵盖了行政处罚等具体行政行为中对使用非法手段取得的证据的排除。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所述的并非仅限于证据的认定和对非法证据的排除,而是关照到了围绕非法证据排除为核心的其他相关问题,如刑事诉讼的程序、无罪推定的原则以及禁止强迫自证其罪的规定等。不详叙上述若干问题,就无法从更深程度把握有关原理和中国相关立法的缺陷。而且,国际人权法对于非法证据排除问题也不是孤立起来看待的,而是将其视作整体中的一部分来加以规范。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和《禁止酷刑公约》均对有关刑事检控、证据认定和罪名设置等问题进行了规定,这些规定直接或者间接地构成了非法证据排除若干问题的国际人权法规范。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4条第3款规定:“在判定对他提出的任何刑事指控时,人人完全平等地有资格享受以下的最低限度的保证:(a)迅速以一种他懂得的语言详细地告知对他提出的指控的性质和原因;(b)有相当时间和便利准备他的辩护并与他自己选择的律师联络;(c)受审时间不被无故拖延;(d)出席受审并亲自替自己辩护或经由他自己所选择所法律援助进行辩护;如果他没有法律援助,要通知他享有这种权利;在司法利益有此需要的案件中,为他指定法律援助,而在他没有足够能力偿付法律援助的案件中,不要他自己付费;(e)讯问或业已讯问对他不利的证人,并使对他有利的证人在与对他不利的证人相同的条件下出庭和受讯问;(f)如他不懂或不会说法庭上所用的语言,能免费获得译员的援助;(g)不被强迫作不利于他自己的证言或强迫承认犯罪。”这是对刑事审判最低限度保证和禁止强迫自证其罪的规定,这可以从根本上消灭非法证据滋生的土壤。
《禁止酷刑公约》第4条规定:“每一缔约国应保证,凡一切酷刑行为均应定为触犯刑法罪,该项规定也适用于施行酷刑的企图以及任何人合谋或参与酷刑的行为。”第15条规定:“每一缔约国应确保在任何诉讼程序中不得援引任何确属酷刑逼供作出的陈述为证据,但这类陈述可引作对被控施用酷刑逼供者起诉的证据。”这不仅明确规定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而且也规定了对刑讯逼供等非法行为的处罚。
除上述条款之外,人权事务委员会和禁止酷刑委员会还在一系列一般性意见、结论性意见和个人来文意见中表达了观点和主张。在下文中,笔者将对此加以详述。
二、行政法领域内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非法证据排除和强迫逼取供述等行为是紧密联系的。行政法领域内的强迫逼取供述的行为是指,在办案过程中,对违法行为人施以肉刑或变相肉刑,逼取违法行为人陈述的行为。其中,威胁是指以使被询问人的个人利益受到某种损害相恫吓,从而迫使其按照办案人员的要求进行陈述;引诱是指以满足被询问人的某种利益为饵,诱使其按照办案人员的愿望进行陈述。*参见杨鹏:“公安机关行政执法领域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研究”,载《湖北警官学院学报》2013年第8期,第28页。
(一)现有法律的规定
正如禁止酷刑委员会在2008年对中国所发布的结论性意见中所指出的那样:“2005年《治安管理处罚法》特别要求公安机关应当坚持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原则。尤其是,根据缔约国代表所言,‘这是第一次在国家法律中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Concluding Observations of the Committee against Torture CHINA, UN Committee against Torture,CAT/C/CHN/CO/4,Dec. 12, 2008,para.4.2005年发布的《治安管理处罚法》第79条规定:“公安机关及其人民警察对治安案件的调查,应当依法进行。严禁刑讯逼供或者采用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手段收集证据。以非法手段收集的证据不得作为处罚的根据。”2012年《治安管理处罚法》修订后,新第79条沿袭了原第79条的规定,未作变动。
本条第1款强调:“公安机关及其人民警察对治安案件的调查,应当依法进行。严禁刑讯逼供或者采用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手段收集证据。”本款规定了公安机关及其人民警察针对治安案件进行调查取证所必须遵守的要求,其中包括两层含义:第一,必须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来进行调查。第二,在收集证据的过程中,严禁采取刑讯逼供的方式或者采取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的手段。本条第2款强调:“以非法手段收集的证据不得作为处罚的根据。”本款是中国第一次明确出现非法证据排除的规定,对公安机关依法行使职权、保障公民不受刑讯逼供具有重要意义。然而,尽管中国《治安管理处罚法》规定了非法证据排除的原则,且也受到了禁止酷刑委员会的赞赏,但这并不意味着该法就能够完全杜绝治安案件中的刑讯逼供等行为的发生。
(二)存在的问题和分析
单独从国内法律规范体系来看,该法本身过度部门化,缺乏多元力量的监督和具体措施的落实。这虽然不是该法相对于《禁止酷刑公约》的缺漏之处,但它对于治安案件领域内的人权保障显然有消极的影响。而且,《治安管理处罚法》并未规定律师在治安案件处理中的作用,由于没有外在的第三种力量对警察的行为实施有效的监督,警察往往握有“一种不受任何约束的法外特权”,即使警察采用非法手段取证,但由于行政相对人处于一种“超级封闭”的情况下,往往根本没有能力来证明证据是警察通过非法手段收集的。*参见高军:“略论法治视野中的《治安管理处罚法》的不足”,载《理论与改革》2006年第2期,第134页。其实从立法背景和过程来看,《治安管理处罚法》是由公安部拟定草案后报送国务院,再由国务院提交到全国人大常委会进行审议的,换言之,这是一部或多或少体现着公安机关部门利益的法律。因此,对于该法第79条的贯彻落实,公安机关自身并没有太多积极性,当然也就不会积极将禁止刑讯逼供和非法证据排除的具体实施写入法律之中。
更重要的,从国际人权法的角度来看,该法的主要问题在于,它对酷刑行为的处罚方式违反了《禁止酷刑公约》的规定和委员会的意见。尽管从表面上看,《治安管理处罚法》第79条对刑讯逼供、体罚和虐待等行为采取了严格禁止的态度,但实际上其规定并不符合国际人权标准的要求。2005年《治安管理处罚法》第116条规定:“人民警察办理治安案件,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1)刑讯逼供、体罚、虐待、侮辱他人的;……办理治安案件的公安机关有前款所列行为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相应的行政处分。”这一条在2012年《治安管理处罚法》的修订中依旧未作变动。可见,对于刑讯逼供、体罚和虐待等行为,该条将其区分为“未构成犯罪”和“构成犯罪”两大类,只追究后者的刑事责任,而前者仅仅给予行政处分即可。然而,在这种分类之下,许多给被害人带来“剧烈疼痛或痛苦”的酷刑行为实际上很难受到刑事处罚,最多加以行政处分而已。*所谓“行政处分”,是指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对所属的国家工作人员违法失职行为尚不构成犯罪,依据法律、法规所规定的权限而给予的一种惩戒。行政处分种类有:警告、记过、记大过、降级、撤职、开除。很难想象,中国法律使用轻描淡写的行政处分方式来追究殴打虐待被害人的行为,这样的规定显然不符合禁止酷刑的国际人权标准。但是,《禁止酷刑公约》第4条则规定:“每一缔约国应保证,凡一切酷刑行为均应定为触犯刑法罪……”另外,禁止酷刑委员会在2008年对中国澳门特别行政区的结论性意见中表示:
委员会注意到澳门特区报告以及对问题的答复中说明的《刑法典》第234条(酷刑行为)和236条(严重酷刑行为)所规定的罪行之间的差别。委员会关切的是,这种区分可能导致形成一种观念,认为酷刑罪有重有轻,这不仅是一种错误的区分,而且可能会阻碍切实有效地对一切酷刑案提出起诉。澳门特区的《刑法典》应该完全根据《禁止酷刑公约》第1条和第4条界定酷刑,将其定为刑事罪。为此,委员会建议酷刑罪构成一项单独的罪行,但须按酷刑罪适用的相关加重情节处罚。*Concluding Observations of the Committee against Torture CHINA, UN Committee against Torture,CAT/C/CHN/CO/4,Dec. 12, 2008,para.5.
因此笔者认为,《治安管理处罚法》第116条的规定明显造成了实质上的“有罪不罚”和区别对待现象,不符合有关禁止酷刑的国际人权标准。*而且,由于1997年《刑法》将刑讯逼供罪的行为主体限缩为司法工作人员,且行为对象也仅仅包括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因此,如果在办理治安案件中出现暴力虐待等情况,行为人也只能依照故意伤害罪或故意杀人罪来定性。
(三)简要意见和建议
根据上述分析,笔者认为《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规定需要修改,将针对刑讯逼供、体罚、虐待等行为的惩处尽量剥离出行政处罚的范畴,对相关条款进行删减,并且相应地在刑事立法中体现出对一切酷刑行为的零容忍和刑事处罚。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遏制刑讯逼供等酷刑犯罪,阻断非法证据产生的源头。
三、刑事法领域内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与《治安管理处罚法》适用于治安违法行为不同,《刑事诉讼法》中有关非法证据排除的规定适用于刑事犯罪及审判领域。2012年3月14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了修改《刑事诉讼法》的决定,对我国现行的《刑事诉讼法》作了许多重大的修改,包括在总则中写入了“尊重和保障人权”条款,并在刑事法层面上首次确立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一)现有法律的规定
2012年最新的中国《刑事诉讼法》第50条规定:“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必须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够证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者无罪、犯罪情节轻重的各种证据。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方法收集证据,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这就第一次明文规定“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从而确立了禁止强迫自证其罪原则;第53条规定:“对一切案件的判处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没有被告人供述,证据确实、充分的,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这就改变了以往只重视口供的证明模式,并指出只有口供而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定罪处罚;第54条规定:“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应当予以排除。收集物证、书证不符合法定程序,可能严重影响司法公正的,应当予以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不能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的,对该证据应当予以排除。”这一条具体明确了对非法收集的口供、物证和书证等不同证据的不同处理方式,并要求对非法证据加以排除。总体而言,2012年新通过的《刑事诉讼法》在非法证据排除方面有诸多亮点。然而,该法在确有进步的同时,仍然存在一些需要改进和完善的地方,距离国际人权标准尚有一定距离。
(二)存在的问题和分析
1.禁止强迫自证其罪
在国际人权法上,《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对禁止强迫自证其罪原则有明确的规定。中国2012年《刑事诉讼法》第50条也规定了“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这意味着该原则在中国立法中得到了确立。但是,仔细考察《刑事诉讼法》的有关内容,不难发现一些尚未解决的问题。实质上,禁止强迫自证其罪原则在很大意义上被架空,这主要体现在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沉默权的不完全认可。
除了上述第50条之外,《刑事诉讼法》第118条还规定了这样的规则:“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的提问,应当如实回答。但是对与本案无关的问题,有拒绝回答的权利。”这意味着,法律一方面要求公安司法机关不得使用刑讯逼供和威胁、引诱、欺骗等方法逼迫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证有罪,但另一方面却没有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以沉默权来对抗公安司法机关的审讯。禁止强迫自证其罪是沉默权的基础,沉默权是禁止强迫自证其罪的核心内容。没有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保持沉默的权利,有关禁止强迫自证其罪规定的效用就大打折扣,其目的难以完全实现;离开了禁止强迫自证其罪原则,那么单纯的沉默权也没有法律上的意义和存在的基础。*参见包献荣:“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原则的制度渊源及在中国的贯彻”,载《湖北警官学院学报》2013年第4期,第138页。《刑事诉讼法》第118条的规定在实践中基本上架空了第50条的禁止强迫自证其罪原则,虽然第118条也声明“对与本案无关的问题,有拒绝回答的权利”,但在实践中,处于弱势地位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基本没有可能与公安司法机关论争究竟何种问题才“与本案无关”。而且,如果不能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以沉默权,那么在面对强大的公安司法机关重压之下,很难保障他们免于被迫自证有罪,公安司法机关可以通过讯问大量与案件有关的问题,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承受巨大的精神压力,使其心理防线彻底崩溃——这种讯问技巧在中国的实践中普遍存在。
对此,人权事务委员会在2007年对《公约》第14条所作出的一般性意见中指出:“(本项)保障有权不被强迫作不利于自己的证言或强迫承认犯罪。必须从没有来自刑侦当局为获得认罪而对被告作任何直接或间接的肉体或不当精神压力的角度来理解这项保障……”*CCPR General Comment No.32:Right to equality before courts and tribunals and to a fair trial (article 14),Human Rights Committee,CCPR/C/GC/32,Aug.23,2007,para.41.这一点在委员会对个人来文的评论中也得到了体现,例如在2000年的“Deolall v. Guyana”案中,委员会认为:
任何人不得被强迫自证其罪,必须从没有来自刑侦当局为获得认罪而对被告作任何直接或间接的肉体或不当精神压力的角度来理解……Deolall先生在警察的殴打下被迫作出了供述,即便这样的殴打是很轻微的,法院也不能对这样的供述加以任何采信,并且应当对被告人无罪释放。*Mrs. Deolall v.The Republic of Guyana,Communication No.912/2000,U.N.Doc.CCPR/C/82/D/912/2000(2005),para.5.1.
由此可见,委员会非常强调防止刑侦当局对相对人施加不当的精神压力,而中国司法实践中大量存在的为了获得认罪而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处于高度紧张和精神压力之中的做法显然与委员会的意见不符。倘若能够将《刑事诉讼法》第118条的“如实回答”义务删去,那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便可以凭借沉默权从容应对公安司法机关施加的不当精神压力。
另外,需要强调的是,关于证人是否享有禁止强迫自证其罪原则之保护的问题,学术界尚有一定争议。
《刑事诉讼法》第50条规定“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亦即从字面意义上理解,在中国法律中,禁止强迫自证其罪作为一项权利,仅仅由涉嫌有罪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享有,而证人仍然要对不利于自己的证言承担如实陈述的义务。初看起来,这对于证人而言是一项诉讼程序中的“危险”,然而仔细分析便可知,证人可能面对的此种“危险”在逻辑上是不存在的,因为在通常情况下,证人不太可能因为作证而引发对自己的刑事追究,也就不太可能面对所谓“不利于自己的证言”。如果出现“不利于自己的证言”,也只有一种可能,即证人本身也具有某一项犯罪的嫌疑,且作证行为可能引发对自己的刑事指控。有外国学者认为:“禁止自我归罪的根源在于英国的普通法,而现在则一般地属于公正审判的基本精神……该权利仅与被告有关。而在另一方面,证人可能不得拒绝作证。”*[奥]曼弗雷德·诺瓦克:《民权公约评注》,毕小青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260页。中国有学者便认为:“不被强迫自证其罪也适用于证人,在证言可能导致他自己有罪的情况下,证人可以引用不被强迫自证其罪的权利保护自己,拒绝透露有关事实。”*杨宇冠:《人权法——〈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93页。但当证人可能被认定有罪的情况确实发生时,该证人也已经在法律上转化为犯罪嫌疑人,那么其自然也享有了《刑事诉讼法》第50条所规定的免于被迫自证有罪的权利,因此所谓证人的该项权利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当然,也有观点对此表示反对,认为证人也应当享有此项权利。
笔者认为,证人显然不能享有免于被迫自证有罪的权利。笔者将论断建立在中国《刑法》《刑事诉讼法》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4条第3款的基础上。首先,正如前一段所分析的,在逻辑上通常不会出现证人因作证而使自己陷入刑事指控的情况;倘若出现上述情况,那么证人的身份已经变化为另一起案件中的犯罪嫌疑人,其权利在属性上也已经成为犯罪嫌疑人所享有的权利。其次,根据《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规定,在具体罗列权利时,第14条已经明确规定享有权利的前提是“在判定对他提出的任何刑事指控时”,而遭受刑事指控的人只能是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并不包括证人,因此《公约》文本并没有提供给证人以免于被迫自证有罪的权利。再次,在法律上证人具有作证的义务。《刑事诉讼法》第60条规定:“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人,都有作证的义务。”这表明公民只要知道案件的情况,就负有承担证人角色并如实作证的义务。《刑法》第305条规定:“在刑事诉讼中,证人、鉴定人、记录人、翻译人对与案件有重要关系的情节,故意作虚假证明、鉴定、记录、翻译,意图陷害他人或者隐匿罪证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可见,证人如果不能如实作证,就构成伪证罪,必须承担刑事责任。既然证人在法律上具有作证的义务,那么《刑事诉讼法》第50条的保护当然就不能覆盖到证人身上。最后,如果仔细分析人权事务委员会的一般性意见,不难发现,委员会并不认为《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4条第3款对证人提供了保护。委员会2007年关于第14条第3款g项的一般性意见全文如下:
第14条第3款g项保障有权不被强迫作不利于自己的证言或强迫承认犯罪。必须从没有来自刑侦当局为获得认罪而对被告作任何直接或间接的肉体或不当精神压力的角度来理解这项保障。当然,以违反《公约》第7条的方式对待被告以获取认罪,是不可接受的。国内法必须确保不得援引违反《公约》第7条取得的证词或口供作为证据,但这类材料可用作证明已经发生了该条所禁止的酷刑或其他待遇的证据。在这种情况下,应由国家证明被告的陈述是出于自愿。*CCPR General Comment No.32: Right to equality before courts and tribunals and to a fair trial (article 14), Human Rights Committee, CCPR/C/GC/32, Aug. 23, 2007, para.41.
由本段意见可以看出,人权事务委员会只在开头提及了“证言”,而后仅仅在强调不得违反第7条(禁止酷刑条款)时提及了“证词”,此外,委员会均只谈到不得强迫被告人认罪,而未提及关于证人证言的问题。笔者认为,采取这样的结构形式进行论述,意味着委员会对于“不被强迫作不利于自己的证言”的理解更偏向于“不被强迫”而不是“不利于自己”,即“不被强迫作不利于自己的证言”主要是指证人证言不能以“酷刑或残忍的、不人道的或侮辱性的待遇或刑罚”(第7条)的形式强迫获取,而不是指证人有权对不利于自己的证言保持沉默。这样的理解更契合委员会一般性意见的逻辑结构,也能够与中国《刑法》规定的暴力取证罪的要求相吻合。《刑法》第247条规定的就是刑讯逼供罪、暴力取证罪:“司法工作人员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实行刑讯逼供或者使用暴力逼取证人证言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致人伤残、死亡的,依照本法第234条、第232条的规定定罪从重处罚。”
2. 具体的证据排除规则
从国际人权法的角度来看,中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尚存在问题。这主要体现在两方面,第一是非法实物证据的排除还不充分,第二是非法证据排除的启动程序尚不合理。而且严格意义上说,后者在现有的国际人权法框架下也存在一些障碍和缺陷。
2012年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第54条规定:“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应当予以排除。收集物证、书证不符合法定程序,可能严重影响司法公正的,应当予以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不能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的,对该证据应当予以排除。在侦查、审查起诉、审判时发现有应当排除的证据的,应当依法予以排除,不得作为起诉意见、起诉决定和判决的依据。”此外,在国际层面上,也有关于非法证据排除的规定。《禁止酷刑公约》第15条规定:“每一缔约国应确保在任何诉讼程序中不得援引任何确属酷刑逼供作出的陈述为证据,但这类陈述可引作对被控施用酷刑逼供者起诉的证据。”中国作为《禁止酷刑公约》的缔约国,其履行公约的情况受到了禁止酷刑委员会的审议。2008年,委员会对中国政府的履约报告进行了审议,并作出了结论性意见。在意见中,委员会对中国的非法证据排除问题提出了关切:
虽然最高人民法院颁布了几项决定,防止将刑讯逼供取得的供词作为法庭证据,委员会对此表示赞赏,但是中国的《刑事诉讼法》仍然没有依照公约第15条的规定,明确禁止这种做法……缔约国应采取必要措施,在法律和实践中均确保,根据公约规定,任何诉讼程序中均不得援引以酷刑取得的口供作为证据,但在指控酷刑实施者时可援引为证据。缔约国应审查所有被告因逼供而被定罪的案件,以释放那些被错误定罪的人。*Concluding Observations of the Committee against Torture CHINA, UN Committee against Torture,CAT/C/CHN/CO/4,Dec. 12, 2008,para.11.
2012年,中国通过修订法律的方式,将委员会的意见进行了落实,但仍然存在对非法证据排除的一些障碍。
A. 条文的规定不利于非法实物证据的排除
第一方面,条文的规定不利于非法实物证据的排除。这一点虽然没有在国际人权公约框架下明确体现,但从国内法的角度来看,相关的立法过程所体现出来的徘徊,实在令人感到遗憾,所以笔者在此一并说明。
依据《刑事诉讼法》,中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采取了两分法:第一类是法律明确列举应当排除的非法证据,相当于法定必须排除的非法证据,包括采用刑讯方法获得的被告人口供,采用刑讯或威胁方法获得的证人证言和被害人陈述;第二类是可经补正或解释后再决定是否排除的非法证据,类似于自由裁量排除的非法证据,主要包括违反法定程序收集的物证和书证。其实,这样的两分法在立法过程中是有争议的,2011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发布的《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第17条规定:
增加一条,作为第53条:“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应当予以排除。违反法律规定收集物证、书证,严重影响司法公正的,对该证据应当予以排除。”*全国人大常委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第17条,2011年8月30日发布。
由此可见,草案中对于“严重影响司法公正”的“违反法律规定收集”的物证和书证,规定了绝对排除的处理方法。但是后来,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在其报告中却指出:
有的代表提出,对已经违反法律规定收集的物证、书证,还可以补正或者作出解释不妥。法律委员会经研究认为,这种情况可限于在收集物证、书证时,不符合法定程序的情形。建议将上述相关规定修改为:“收集物证、书证不符合法定程序,可能严重影响司法公正的,应当予以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不能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的,对该证据应当予以排除。”*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法律委员会:“关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草案)》修改意见的报告”,http://www.docin.com/p-1216845754.html,最后访问时间:2012年3月13日。
遗憾的是,最后通过的《刑事诉讼法》取消了2011年的草案规定,这样一来,中国法律对非法实物证据排除条件的规定就比较苛刻了,既要求“不符合法定程序,可能严重影响司法公正”,又要求“不能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可能严重影响司法公正”、“补正”、“合理解释”等属于比较模糊的表达,这就使得非法实物证据的排除显得异常艰难,学界甚至有人将中国非法实物证据排除规则戏称为“非法证据不排除规则”。*参见陈学权:“比较法视野下我国不被强迫自证其罪之解释”,载《比较法研究》2013年第5期,第40页。根据一些学者2013年1-8月的调研也印证了上述现状:
调研法院共计审理刑事案件17213件,其中提起申请排除非法证据的案件为124件,占全部案件的0.72%,法院决定启动证据合法性调查程序的案件为54件,占全部案件的0.31%,最终决定排除非法证据的案件为14件,占全部案件的0.08%;在申请排除非法证据的124件案件中,启动证据合法性调查程序的案件为54件,占43.55%;启动证据合法性调查程序的54件案件最终排除非法证据的有14件,占25.93%。*孙长永、王彪:“审判阶段非法证据排除问题实证考察”,载《现代法学》2014年第1期,第73页。
出现这样的情况,一方面是因为法院在司法实践中的地位中立性和司法严格性不足,另一方面是因为非法证据排除——尤其是非法实物证据排除——规则本身尚存不合理之处。
B. 制度的设计不利于启动非法证据排除程序
第二方面,制度的设计不利于启动非法证据排除程序,这是现实中绝少出现非法证据排除情况的一项重要原因。而且,目前的国际人权法规则在程序启动的设计上也存在缺陷,这也值得国际社会的进一步思考和改革。
程序的启动对于最后的法律效果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实践中,遭受刑讯逼供和威胁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往往难以提出有关的材料来启动非法证据排除程序。有一些案件,被告人在法庭上有刑讯抗辩,但当法官向其解释什么是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并明确指出申请启动证据合法性调查程序需要提供相关线索或者材料后,这些被告人均明确表示不申请启动证据合法性调查程序,表示认罪,并请求法院依法对其从轻处罚。*参见孙长永、王彪:“审判阶段非法证据排除问题实证考察”,载《现代法学》2014年第1期,第74页。
我们需要了解国内法中关于非法证据排除启动程序的规定。《刑事诉讼法》第56条规定:“当事人及其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有权申请人民法院对以非法方法收集的证据依法予以排除。申请排除以非法方法收集的证据的,应当提供相关线索或者材料。”第57条规定:“在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进行法庭调查的过程中,人民检察院应当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加以证明。”由此可见,对证据收集合法性的证明责任是由检察机关承担的,而如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要求排除非法证据,则首先应当提供相关的线索或材料。可以说,这样的规定相比2012年修订前而言,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步。可是问题在于,这样的程序设计尽管并没有把证据合法性的证明责任加之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但该程序的起点和启动的前提则仍然须由后者提供。如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没有能够提交出相关的线索或材料,那么非法证据排除程序就根本不会启动,也就难以实现保障人权的诉讼价值。当然,“相关线索或者材料”也是一项较模糊的表达,具体是否启动非法证据排除程序,主要是由法官进行裁量的。在“章某某受贿”一案中,章某某在开庭前提出其审判前的有罪供述是在被侦查机关刑讯逼供、诱供等情况下做出的违心供述,其向法庭提交了《冤案真相》、《审讯过程及我的心路历程》、《看守所日子》等书面材料,详细记载了何时、何地、何人对其刑讯逼供、诱供等具体情况,在庭审过程中,章某某又多次陈述侦查人员的上述行为,向法庭提出申请审查章某某在审判前的供述的合法性问题。由此,法庭启动了法庭调查程序,并根据章某某提供的线索,到宁波市鄞州区看守所提取到了章某某在2010年7月28日的体表检查登记表,该表载明章某某右上臂小面积的皮下游血,皮肤划伤2cm。*参见章国锡受贿案(法宝引证码:CLI.C.1334520),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2011]浙甬刑终字第288号(2012年7月18日),第12段。在这起案件中,《冤案真相》《审讯过程及我的心路历程》《看守所日子》等间接材料已经可以说服法官启动非法证据排除程序。而且作为刑讯逼供的重要线索,有关章某某受伤的医学检查结果却并不是启动非法证据排除程序的原因,相反该线索是在程序启动后的调查之中才被发现的。遗憾的是,其他案件中的被告人或许难以如此幸运,毕竟顺利启动该程序的案件比例依然很低,或许不少法官会认为这些间接材料都是被告人自己撰写的,并无非常明确的材料——诸如医学证明、伤情鉴定等——直接指向刑讯逼供行为,可能因此就没有对取证的合法性开展调查。
鉴于上述各方面情况,为了能够使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得到真正的落实,有学者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可以在此类案件中规定“刑讯逼供的推定规则”:
查证难已经成为遏止刑讯逼供的瓶颈……为了有效遏止刑讯逼供,可建议由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以司法解释的形式制定推定规则如下:有下列情形之一而且侦查人员不能提供充分反证的,应该推定有刑讯逼供:(1)犯罪嫌疑人在接受侦查讯问期间突然死亡的;(2)犯罪嫌疑人在侦查讯问期间形成非自造性身体损伤的;(3)侦查机关超期羁押犯罪嫌疑人而且没有按照法律规定通知犯罪嫌疑人的家属和单位也没有按照法律规定安排律师会见的。*何家弘:“‘喝开水死’应催生刑讯逼供的推定规则”,http://www.cssn.cn/fx/fx_xsfx_990/201503/t20150313_1545290.shtml,最后访问时间:2015年11月27日。
其实,关于非法证据排除程序的启动和证明问题,国际人权法上也有类似的规定。然而,笔者认为,目前的国际人权理论与实践尚存在进一步完善的空间。《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4条第3款规定:“在判定对他提出的任何刑事指控时,人人完全平等地有资格享受以下的最低限度的保证:……(g)不被强迫作不利于他自己的证言或强迫承认犯罪。”人权事务委员会2007年关于第14条第3款g项的一般性意见指出:“最后,第14条第3款g项保障有权不被强迫作不利于自己的证言或强迫承认犯罪……在这种情况下,应由国家证明被告的陈述是出于自愿。”*CCPR General Comment No.32:Right to equality before courts and tribunals and to a fair trial (article 14),Human Rights Committee,CCPR/C/GC/32,Aug.23 2007,para.41.而且,委员会在一些个人来文申诉中也表达了这样的观点,例如在2001年的“Singarasa v. Sri Lanka”案中,来文者Singarasa声称自己被斯里兰卡安全部队以“涉嫌与猛虎组织有关”的理由被逮捕,并遭受了酷刑,包括被推入水箱、在水下窒息以及拷打等,以此逼取供状。来文者指控斯里兰卡违反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4条第3款g项。对此,委员会发表了如下意见:
委员会认为,(禁止强迫自证其罪)这一原则包括了这样的隐含要求,即应当由控方证明供述的作出没有遭受胁迫……委员会还注意到,在本案中是由来文者承担证明责任的,即便如缔约国所辩称的那样,举证门槛“设置得很低”以及“仅仅是不自愿的可能性”就足以使法院的判决有利于来文者,但这仍然意味着由来文者承担证明责任。*Mr.Nallaratnam Singarasa v.Sri Lanka, Communication No.1033/2001,U.N.Doc.CCPR/C/81/D/1033/2001(2004),para.7.4.
可见,委员会也认为取证合法性的证明责任应当由国家承担,但这也并未能确定程序启动的责任主体。而在《禁止酷刑公约》体系下,禁止酷刑委员会对该问题作出了一定的解释。《禁止酷刑公约》第15条规定:“每一缔约国应确保在任何诉讼程序中不得援引任何确属酷刑逼供作出的陈述为证据,但这类陈述可引作对被控施用酷刑逼供者起诉的证据。”委员会在一些个人来文申诉中对这一条作出了解释,例如在2011年的“Gallastegi Sodupe v. Spain”案中,来文者声称自己因损害和破坏公共财物而被捕,并遭受了殴打和虐待。来文者要求控方通知家人其状况和下落,以及允许与律师进行私下交谈,但被拒绝,这剥夺了来文者与家人、律师或他信任的医生接触的权利。而且来文者在2003年1月29日提交Donostia-San Sebastián治安法院的书面陈述中指出,指定律师“一言不发,即使在我说遭到酷刑时”。然而,委员会在这起案件中对《禁止酷刑公约》第15条的解释却是这样的:“委员会认为来文者没有提供可以藉此断定他的认罪声明可能是在酷刑下作出的资料,例如应来文者要求出示的额外体检证明或证人的证词。委员会因此认定其收到的资料未显示存在违反《公约》第15条的情况。”*Mr. OskartzGallastegiSodupe v. Spain, Communication No. 453/2011, U.N. Doc. CAT/C/48/D/453/2011(2012), para.7.4.所以,禁止酷刑委员会的立场是与中国法律中的立场相一致的,即指控者必须提供一定的线索或材料。笔者认为,如果能够采纳何家弘教授的观点,采取特殊的推定规则——“侦查机关超期羁押犯罪嫌疑人而且没有按照法律规定通知犯罪嫌疑人的家属和单位也没有按照法律规定安排律师会见的”——那么本案就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揭示出可能存在的刑讯逼供,因为来文者GallastegiSodupe恰恰被拒绝会见家属和律师。推而广之,笔者认为,现存相应的国际人权标准和实践尚有空间进行类似的改革,而何家弘教授的观点不失为一条可以选择的道路。
再来看何家弘教授提出的推定规则,不难发现,在这样的规则之下,侦查起诉机关必须提出对推定事实的反证,即必须证明:(1)控告人没有死亡,或控告人虽然死亡,但其死亡并未发生在侦查讯问期间,或其死亡与侦查讯问行为没有因果关系;或者(2)控告人没有出现非自造性身体损伤,或控告人虽然出现非自造性身体损伤,但其损失并未发生在侦查讯问期间,或其损伤与侦查讯问行为没有因果关系;或者(3)没有出现超期羁押的情况,或已经按照法律规定通知了控告人的家属或单位。如果出现了死亡、损伤或未通知家属等情况,而侦查起诉机关又无法提出足以排除合理怀疑的上述反证,那么法官应当推定出现了刑讯逼供等酷刑行为,就必须启动非法证据排除程序。客观地说,如果侦查起诉机关能够严格依照法定程序行使职权,那么上述问题几乎不可能出现。对此,笔者查阅了2009年中国政府对禁止酷刑委员会结论性意见的回应,在回应中,政府不认同委员会的意见,声称中国的刑事保障措施较为完善,刑讯逼供在中国并非普遍现象。例如,中国政府表示:
中国对所有被拘留者均有系统的登记和审前拘留时长的记录……中国《刑事诉讼法》第96条明确规定,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后或采取强制措施(包括拘留)之日起,可以聘请律师为其提供法律咨询、代理申诉、控告……对于被拘留者,办案单位会告知其依法享有的权利,看守所和驻所检察官也会告知其享有的权利,看守所和驻所检察官通常会将被拘留者依法享有的权利在醒目位置予以公示……中国公安机关为保护看守所在押人员的合法权益,不断健全和完善监督机制,特别是外部监督机制。*Response by the Government of China to the Concluding Observations of the Committee against Torture,UN Committee against Torture, CAT/C/MAC/CO/4/Add.2,Dec.18,2009.
可见,依据政府的意见,中国的刑事程序和保障措施足以避免发生刑讯案件,倘若侦查起诉机关在实践中能够严格执行这些严密的程序规定,那么就几乎不可能发生上述死亡、损伤等情形,即便发生,侦查起诉机关也完全可以提出足以排除合理怀疑的反证,因为每一次重要的职权活动在理论上都会留下证据。因此,如果何家弘教授的观点能够得到采纳,那么在实践中就既不会冤枉侦查起诉机关,又能够在最大程度上杜绝刑讯逼供行为,何乐而不为呢?笔者认为,这样的推定规则也值得国际人权标准和实践所借鉴,这对于国际人权法的发展也具有重要的意义。
(三)简要意见和建议
根据上述分析,笔者认为,国内的《刑事诉讼法》在非法证据排除方面还有较大的修改空间。从实物证据排除角度来看,原《刑事诉讼法(草案)》中的内容值得借鉴;从相关程序启动条件来看,刑讯逼供的推定规则也是非常值得参考的一种立法选择,而后者对国际人权法本身的发展和完善也具有重要的价值。
结 论
从人权国际保护的视角来看,非法证据排除更多是一项刑事法领域的工作,因此相关行政法对刑讯逼供、体罚和虐待等问题的规定是不合适的,应当进行删减调整。而在刑事法领域内,禁止强迫自证其罪和具体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也需要在程序和实体上进行修改,一方面落实沉默权,另一方面在证据法上加强排除力度并进一步优化排除程序。在国内法逐步推进的过程中,国际人权法扮演着标杆的角色,同时它自身也需要不断完善和发展。
(实习编辑:赵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