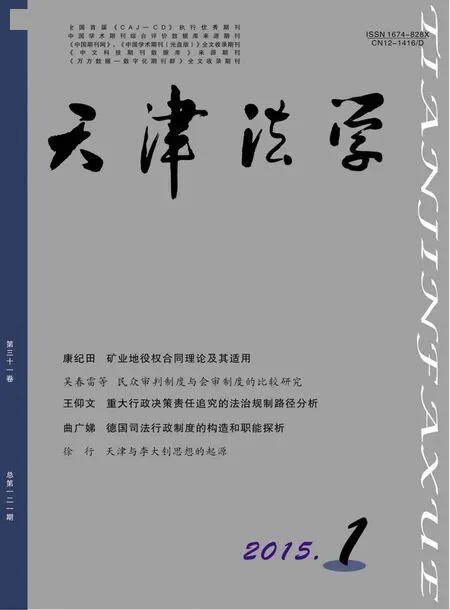论非讼法理在小额诉讼程序中的适用
2015-02-12孙永军
孙永军
(南京大学 法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3)
·立法建议·
论非讼法理在小额诉讼程序中的适用
孙永军
(南京大学 法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3)
关于小额诉讼,既有的研究多集中在小额诉讼程序的介绍比较、我国小额诉讼程序的建构、困境和问题等方面。对小额诉讼程序运作的程序理念及相应的制度设置方面的研究较为薄弱。利用小额诉讼程序解决纠纷的过程,很大程度上就是适用非讼法理的过程。它体现了程序相称原理,有利于纠纷的快速、简易解决,进而提升民众对司法的信任。我国在完善小额诉讼程序时应在当事人选择适用不公开审理主义、当事人的处分权受到限制、适用职权裁量法理、应允许法官裁量采用自由的证明程序等方面适用非讼法理。
小额诉讼;非讼法理;程序相称
小额纠纷经常发生在普通民众之间,与日常生活有密切关系。这些事件有押金、租金、工资请求、小金额的融资、消费借贷、零售商的价金请求、生活消费中的产品瑕疵、相邻关系中权利义务的划定、邻里之间的一般侵权等。这些事件的处理牵涉到如何设法提升人民日常生活品质的基本问题。如果采用正规的诉讼程序处理,必然出现诉讼程序繁琐、时间冗长、成本高昂等问题。这势必阻碍当事人对诉讼的使用。台湾大学邱联恭先生将小额诉讼事件解决的合理与否上升至法治社会能否建立的高度。他认为,如果发生在普通大众之间的小额诉讼不能得到合理解决,法治就很难在一个社会中生根发芽。不仅如此,它还是直接决定民众信赖司法与否的关键[1]。正因为如此,“为了保护当事人的诉诸司法的权利,保护当事人的系争外利益,世界上不少国家和地区根据程序相称原理,在其通常的民事诉讼程序外,设立了一种简易化、低成本、快速解决小额纠纷的程序,即小额诉讼程序。[2]”2012年我国修订民事诉讼法时也在第157条规定了小额诉讼程序。小额诉讼“不仅表现为小额诉讼的程序规则特殊,而且表现为小额诉讼的程序法理特殊。[3]”小额诉讼程序并不仅仅是相对于普通民事诉讼程序的简化,它更体现为传统辩论主义、处分权主义的修正、法院对诉讼程序进行控制权的加强。利用小额诉讼程序处理纠纷的过程,很大程度上就是适用非讼法理的过程。目前我国小额诉讼程序中非讼法理的适用虽然有所规定,但仍嫌不足。就小额诉讼制度的研究而言,我国小额诉讼制度规定之前,绝大多数研究集中在对国外或其它地区小额诉讼程序的介绍比较、我国小额诉讼程序的建构等方面。小额诉讼制度确立后的研究,多集中在对我国现行小额诉讼制度的困境分析和问题检讨方面。总之,学界对小额诉讼程序运作的程序理念及相应的制度设置方面的研究较为薄弱。基于以上考虑,本文就非讼法理在小额诉讼程序中的适用问题进行初步探讨,藉此为我国小额诉讼理论研究的拓展乃至制度的完善提供有益的参考。
一、非讼法理在小额诉讼程序中适用的理论基点
非讼法理是与诉讼法理相对应的程序理念。在大陆法系民事司法语境中,由法院处理的民事案件包括诉讼事件(案件)和非讼事件(案件)。诉讼事件是指当事人之间存在民事权利义务争议,需要法官通过判决化解纠纷的事件。非诉讼事件则是指当事人对案件所涉事项并无民事权利义务争议,通过诉讼的方式确定某种法律事实或行为状态,目的在于避免或预防纠纷发生的事件[4]。不同国家或地区关于非讼事件的范围规定得不尽一致。我国在立法上没有“非讼事件”的正式称谓,但从规定的实际情况看,也存在大量的非讼事件。适用特别程序审理的案件如宣告公民失踪案件、人民调解协议的司法确认案件、担保物权的实现案件和认定财产无主案件均属于非讼事件。此外,民法通则中规定的撤销监护案件,公司法规定的股东提起的公司解散命令案件、清算案件,《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中规定的共同海损案件等,从性质上讲也是非讼案件。“同属于民事案件,由于其性质不同,法院行使审判权的方式也有所区别,其结果便形成了支配审判程序进行的两大程序原理:诉讼程序原理与非讼程序原理。[5]”因此,传统大陆法系国家普遍实行诉讼程序法与非讼程序法(事件法)的立法区分,在处理诉讼事件时就采用民事诉讼程序,适用辩论主义、处分权主义、公开审理主义等程序法理,希望为当事人提供最为严密的程序保障。非讼事件则采用非讼程序处理,适用非讼法理。采取简易主义,迅速经济地做出裁判;借助法官的职权裁量,使案件的处理更加灵活。适用职权探知主义,法官可以有条件地超越当事人的请求或主张,贯彻一种缓和的或不彻底的处分权主义。这就是传统大陆法系国家民事诉讼中所谓程序法理的二元分离适用论。小额诉讼事件虽然涉及标的额较小,但也是典型的具有权利义务争议的诉讼事件,按照程序法理的二元分离适用论,理应贯彻诉讼法理,似乎没有适用非讼法理的必要及可能。但是这种见解当下有检讨的必要。
首先,程序法理的二元分离适用论对民事案件的划分过于绝对。在传统理论看来,民事事件分为民事诉讼事件和民事非讼事件。划分的基本标准就是当事人之间是否存在权利的对抗性。非讼事件,在形式上都是缺乏直接对抗性的案件。但是,如果我们对非讼事件进行仔细考察的的话,就会发现,尽管大多非讼事件不存在权利义务的直接对抗性,(如监护事件,包括监护人之选任、解任;离婚后亲权人的指定),但并不尽然。例如公司司法解散事件虽然属于非讼事件,但其与宣告公民失踪死亡明显不同。不同于宣告失踪死亡案件仅有申请人而无被告,我国的公司司法解散案件却两造具备,拥有10%以上股权的股东为原告,公司往往为被告,实务中还将其它股东列为共同原告或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其在诉讼构造上与典型的民事诉讼案件并无二致,诉讼的过程也极具对抗性。即使学者们又将非讼事件细分为民事非讼事件、家事非讼事件与商事非讼事件,这些细分后的非讼事件内部仍存在差异。同属于诉讼事件的案件之间亦是如此。如买卖合同纠纷案件与涉及人身关系的离婚诉讼事件存在不同是显而易见的。不同类型的诉讼事件在当事人之间的地位、纷争的基础、利益的诉求等方面存在差异,在处理时自然也应有所区别,把诉讼法理毫无区别地适用于这些诉讼事件,很显然并不妥当。不仅如此,程序法理的二元适用论也忽略了所谓诉讼事件与非讼之间存在流动性的事实。随着社会的发展,立法司法理念的转变,往往将原先属于诉讼案件的事件改为非讼事件,反之亦然。因此,程序法理的二元适用具有明显的形式主义色彩,有革新之必要。为了因应不同民事案件的特点,实现案件的最为妥当性解决,就需要超越程序法理的二元适用论,打破其藩篱,走向程序法理的交错适用论。即法院在处理民事案件时灵活而综合地运用各种相关的程序法理。就小额诉讼程序而言,法院就要适用尽量能促使案件简易、快速处理的非讼程序法理。
其次,程序法理的二元分离适用论忽视了程序保障的价值。一般而言,民事诉讼中所谓的程序保障指与民事诉讼的裁判结果有利害关系或者可能蒙受不利影响的人,都有权参加民事诉讼程序,并确保提出有利于自己的主张和证据以及反驳对方提出的主张和证据的机会。谷口安平将程序保障归纳为“参加命题”。在他看来,在民事诉讼中应保障具有利害关系的人作为诉讼的当事人直接进入程序,获得有利于自身的判决。即使在当事人实际上没有参加诉讼的场合,也应通过“通知”等方式保障其有参加的机会[6]。但程序保障并非仅仅保障当事人形式上参加诉讼这么简单。更为重要的是,当事人作为程序的主体,能够实质上影响裁判的形成,避免来自法院的突袭裁判。程序保障越充分,裁判结果就越应当受到尊重与肯定,越应当赋予裁判以既判力。相反,程序保障越少,裁判结果的正当性越低。程序法理的二元适用论机械地将民事事件分为诉讼事件和非讼事件,忽略了不同事件之间的差异和个性,必然出现对当事人程序保障关照不周的问题。为了体现程序保障的旨趣,就应打破程序法理分离适用的窠臼,摈弃“诉讼事件—诉讼法理”,“非讼程序—非讼法理”的机械操作。从更宽广的视野,将程序法理熔为一炉。正如廖中洪教授所指出的,程序保障不应当仅仅限于对于程序关系人参与程序,并提出攻击和防御方法上的保障,更应是尽可能根据诉讼案件的个性特征,适用有益于解决纠纷所需要的程序类型,有针对性地适用不同的诉讼法理或非讼法理,而不能不顾个案特征一概套用一种程序或适用一种程序法理[7]。
总之,为因应民事案件的多样化、流动化,提升程序保障的品质计,程序理念上就应从程序法理的二元适用论向程序法理交错适用论转变。在非讼程序中适时适式地适用诉讼法理,在诉讼程序中斟酌适用非讼法理。就小额诉讼程序而言,通过有选择地适用职权主义、裁量主义等非讼程序法理,以满足社会对司法救济迅速化、经济化和妥当化的现实需求。
非讼法理在小额诉讼程序中适用体现了程序相称原理。随着社会关系的复杂化、法律调整的范围也日渐广泛,涉及利益与价值也呈现多元化之势。不同的民事纠纷,产生的原因不同、表现形式不同、反映的利益诉求不同,对案件处理方式的要求也不尽相同。如果用一套相同的方式处理不同类型的案件,纠纷处理的妥当性就极成问题。为使不同类型的纠纷得到妥当的处理,实有必要依据纠纷的性质和特点设立不同类型的程序。“就是指程序的设计应当与案件的性质、争议事项的重要性、复杂程度、争议的金额等因素相适应,由此使案件得到适当地处理。[8]”从这个意义看,诉讼程序不应是一套冰冷、繁琐、僵硬的程序规则,而是奉当事人程序主体性为圭臬,为当事人提供灵活、通融、温暖服务的制度装置。重新组合诉讼法理与非讼法理的要素形成多元化的诉讼程序,以及在具体的诉讼程序中斟酌案件的特殊情况适当适用职权探知、职权裁量等非讼法理也正是我们所追求的。可以说,非讼法理在小额诉讼程序中的适用是对程序相称原理的直接注解。
非讼法理在小额诉讼程序中的适用有利于案件的简速解决。“小额诉讼程序本应适用诉讼法理,即应当贯彻辩论主义、直接言词原则、公开原则等基本原理。然而,小额诉讼程序完全贯彻这些原理,无法实现效率这一诉讼价值目标。[9]”而且,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当事人之间争议的小额化、普遍化正成为现代社会的趋势。自然,社会对纠纷处理的效率性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诉讼一旦从有产阶级的独占中解放出来,成为向一般民众提供的一种服务时,把诉讼成本置之于度外的制度运行就变得不可能了。[10]”人们的权利意识固然很强,但同时也更注重效率,考虑实现权利的成本。对于几乎没有任何精神利益的小额诉讼,当事人更不希望诉讼程序的过度繁琐、诉讼的拖延。人们对民事司法正义的追求不再仅仅满足于判决的实体正确性,时间、成本也成为考察正义是否实现的不可或缺的指标。从诉讼成本因素考虑,民事诉讼程序就不再是预先框定的僵硬的、不容通融的规定,法院和当事人只能被动地去适应,而是能够灵活组装的弹性装置。因此,现代民事司法在保护当事人系争的利益同时,也应对当事人因程序简化和避免使用繁琐的程序而导致的时间、人力、物力的节省等现实利益有所关照和保护。这意味着民事诉讼以当事人的利益为出发点,最大限度地尊重并维护当事人程序主体地位。这种重视诉讼效率的理念的贯彻,对国家而言,不仅现实地减轻了法院的负担,也实在地节约了国家的司法成本。它不应被作为法院应付当下诉讼激增的便宜之策,而应成为传统程序保障内涵的延伸和升华。因为,法院提供基本程序保障基础上,尽可能地快速处理纠纷,是对当事人诉讼争议之外利益的直接保护,它把传统形式主义的程序保障实在化了。非讼法理在小额诉讼程序中的适用为纠纷的简速解决提供了契机。反之,如果拘泥于形式上的程序保障,在审理小额事件时还完全适用辩论主义、处分权主义等程序法理,对当事人而言则相当不经济,也有违民事诉讼制度设立的旨趣。为了保护一个较小的利益,却耗费大量的时间、劳力,任何理智的当事人是不会进行这样诉讼的。为了迅速实现当事人的小额权利,法院就需要通过职权探知、职权进行、职权裁量等手段,尽量采用简化、灵活的程序进行处理。
二、非讼法理在小额诉讼程序中适用的保障
在小额诉讼程序中适用非讼法理有利于实现案件的简单快速解决。但是,当事人程序权利一定程度的缩减和法官职权的扩张也有损及当事人程序主体性的可能。藉此,在进行非讼法理适用操作的同时,就需要在程序上辅以相应的制约或保障措施。我们认为,当事人听审请求权的保障、程序选择权的保障十分重要。
听审请求权,又称公平听审权或听审权。是指法院在审理时,当事人享有的就案件的事实、程序及法律问题充分发表意见,并能够影响法院的审判程序及其审判结果的权利[11]。我国台湾学者沈冠伶认为,听审请求权保障,是程序保障中最重要的部分,它不仅是民事诉讼程序之基本原则,而且具有宪法的地位。法院处理民事案件所适用的程序,无论是诉讼程序还是非讼程序,都应秉承听审请求保障的要求。他同时认为,为了保障当事人的听审请求权,应当根据各不同程序之目的或案件类型,法律做出进一步的规定[12]。刘敏教授在论及小额诉讼程序中适用非讼法理过程中的程序保障问题时,进行了较为详细的分析。他认为,在适用非讼法理时应保障当事人的陈述权、证明权、到场权、辩论权、意见受尊重权等程序基本权。照此,在小额诉讼中,法院应当给当事人提出证据的机会,保障其证明权的实现;应当让当事人就案件事实和适用法律有发表意见的机会;案件的审理必须对当事人公开;当事人有到场权和阅卷权。因此,当事人的听审请求权是个复合性权利。从其内容来看,就是当事人的程序参与权,它不仅要保障当事人形式上能够参与诉讼的过程,更为重要的是它通过权利的细化,保障当事人参与的实质化。当事人在自己的权利受到影响的情况下,不仅享有“获得聆听”的权利,而且当事人能够通过自己的行为实质地影响到裁判的结果。
程序选择权,简而言之,是当事人享有的选择程序事项的权利,它是当事人程序主体性的要求。当事人的程序主体性要求民事诉讼程序制度的创设、构造、运行均应符合当事人的主体意愿。应允许作为程序主体的当事人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处分其实体利益和程序利益,选择符合其利益最大化的程序。不仅如此,程序选择权还可有效地补强当事人的诉权,对审判权的行使形成良好制约。在这样的制度框架中,非讼法理的适用才不至于成为法院强行为之的独角戏,其制约了审判权的恣意,实际上也为当事人与法院的理性沟通和交流提供了可能。尊重当事人的程序选择权,就意味着,为了案件的快速解决,即使是适用普通程序处理的案件,当事人也可变更为小额诉讼程序进行处理。譬如在我国,诉讼标的额在省、自治区、直辖市上年度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30%以上的可以合意选择适用小额诉讼程序审理。这种程序选择权属于相对的程序选择权,当事人的选择具有相对性,对程序的适用不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当事人的程序选择,尚需经法院的审查。这种选择权尽管最终需要经过法院的审查并同意才能够实现,但考虑到,一般情况下法院会尊重当事人的意愿,所以仍然具有重要价值。当事人选择非讼法理在小额诉讼程序的适用,意味着当事人自愿选择自己的辩论权、处分权受到限制。鉴于小额诉讼程序为了实现纠纷快速处理的目的,除了在程序规定上进行缩减外,往往还限制当事人上诉、诉的合并、反诉自认等方面的权利。所以,在当事人的案件本应适用普通程序却合意选择适用简易或小额诉讼程序时,法院必须要进行释明,如实告诉当事人适用这些程序的法律后果,使当事人的选择是其真实意思的表示。除了程序启动方面的选择外,在小额诉讼程序中也应保障当事人程序进行过程中的选择权。可以通过立法赋予当事人选择进行不公开审理的权利,允许当事人双方在离婚、商业秘密外的案件外选择不公开审理。在小额诉讼案件审理时,基于费用相当原理以及该类型案件对于达成迅速而经济裁判的强烈要求等因素的考虑,也应授予法院相当的裁量权,允许其视实际情况的需要,改用不公开审理的方式。在审理方式上也考虑赋予当事人选择不公开审理的程序选择权。
三、非讼法理在我国小额诉讼程序中适用的展开
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虽然在第162条规定了小额诉讼程序,但却将其放在第十三章简易程序中,并未将其作为与简易程序并列的独立诉讼程序对待。在程序法理上沿用的仍旧是简易程序的程序法理。因此,关于非讼法理在小额诉讼程序中适用的规定,我们只能从简易程序的有关规定中寻找。现行的规定主要包括《民事诉讼法》(后文简称《民诉法》)中简易程序部分的7个条文,以及《关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后文简称《规定》)的司法解释。在《民诉法》第158条中规定了当事人双方可以同时到人民法院请求解决纠纷的,法院可以根据情况决定予以当即审理或另定日期审理。第159条规定,法院在审理简单的民事案件时,可以用打电话、捎口信等简便方式随时传唤当事人、证人。这两条可以看作是立法授权法院斟酌采用职权裁量法理的规定。在《规定》中有关非讼法理适用的内容,也仅仅体现在第2条和第6条。其中第6条规定,案件受理后,法院可以采取打电话、捎口信、电子传真等方式随时传唤双方当事人、证人。这其实也不过是《民事诉讼法》第159条的重复和细化。较有新意的是《规定》中的第2条。依照该规定,法院本应适用第一审普通民事程序审理的案件,如果当事人各方自愿选择适用简易程序,法院斟酌后,可以适用简易程序进行审理。该条可以看作是法律授权当事人行使程序选择权、法院行使裁量权等适用非讼法理之情形。因此从立法的角度看,我国在小额诉讼程序中适用非讼法理的范围非常狭小。法院裁量或当事人合意选择实行不公开审理、书面审理、不适用严格证明等方面的规定付之阙如。
完善我国小额诉讼程序时,有必要规定下列非讼法理适用的情形:
(一)当事人双方选择不公开审理
如果在小额诉讼案件的审理中,当事人双方选择不公开审理或法院认为公开审理有损听审目的实现时可不公开审理。之所以如此建议,是因为我国现行法律虽然规定了法定不公开审理和裁量不公开审理两种情形,但这些不公开审理的案件主要集中在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离婚案件等特定类型的案件中,小额诉讼案件不属于以上不公开审理案件的范围。在这种情况下,赋予当事人双方选择不公开审理的权利或允许法官裁量不公开审理,不仅是对当事人程序选择权的尊重,也可以快速解决小额纠纷。对当事人的实体利益和程序利益也不会造成损害。
(二)当事人的处分权受到限制
小额诉讼涉及的金额较小,一般情况下案件事实也比较清楚,如果任由当事人像普通程序一样处分自己的实体权利和程序权利,不仅不能实现快速解决纠纷,对司法资源也是浪费,因此有必要限制其在起诉、提起反诉、上诉等方面的处分权。例如日本民事诉讼法虽然规定当事人可以选择适用小额诉讼程序,但其处分权是受限制的,根据其规定,虽然当事人可以提出异议,但不能够上诉。而且,该程序只能由同一原告在一年内的有限时间内使用(一年只能使用十次)。其还规定小额诉讼中不允许反诉。对于当事人上诉权的限制不同的国家或地区却有不同的规定。如美国大部分的州允许败诉的当事人提起上诉,也有的州不允许当事人就小额法庭的判决提出上诉。英国上诉要经过法官的许可。如果一方当事人败诉了,对法院的判决不服要上诉,要经过法官的许可。而法官许可上诉的条件也仅仅限于小额判决程序严重违法或在实体上适用法律错误等情形下。在限制当事人对小额裁判的上诉权方面,日本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则更为彻底,一概不允许当事人上诉。为了缓和这种绝对规定对当事人造成的可能损害,日本附设一个异议的救济程序。但这个程序也相当简单。当事人可以在接到判决书之日起二周的期间内,向做出该判决的法院提出异议,如果异议合法,诉讼恢复到口头辩论终结前的状态,然后按照普通程序进行审理和裁判[13]。我国对待当事人对小额裁判的上诉权问题上,可以借鉴日本的异议制度对上诉权进行限制。如果当事人对小额诉讼判决不服的,允许当事人向原审法院提出异议,由原审法院另行组成合议庭对该异议进行审理。审理后作出的判决为终局裁判,当事人即便仍有不服,也不得提起上诉。对处分权的限制还体现在如何限制原告适格问题上,也就是小额诉讼程序中原则上应将厂商排除在原告范围之外,原告只能由一般的当事人充当。如不在小额诉讼程序法中对原告的资格进行必要的限制,小额诉讼程序有可能被商家滥用作为其讨债之工具,有失设立小额诉讼程序制度之初衷。
(三)适用职权裁量法理
首先应允许受理案件的法官依照裁量决定以书面审理还是言词审理。如果法官依原告起诉时所提出的诉讼资料认为其陈述已经达到某种程度的心证,则不必进行言词辩论即可作出裁决。例如德国,法律就授权法官对于争议标的额在1200马克以下的案件,可以根据自由裁量决定程序进行的样式,而不必拘泥于普通程序的规定。法官通常的做法是,不开庭审理而以书面审理方式代之。在授权法官裁量书面审理的同时,在保护当事人之间有充分的攻击防御机会的前提下,就小额轻微事件的审理,是否开庭审理,也完全委诸于法官的职权裁量。甚至可以尝试采用周末法庭、假日法庭、夜间法庭等方式解决小额轻微事件,这种作法不仅不会对当事人的利益造成减损,反而能够方便快捷地解决当事人之间的争议。例如英国,法官在审理小额诉讼案件时可以采取其认为适当任何方式进行,审理既可以采用正式程序也可以非正式程序(包括书面审理)方式进行,甚至不需要当事人宣誓陈述他的案件事实,如果有需要,法官可以限制当事人交叉询问和证人作证的时间。其次,小额案件的审理,也未必完全受实体法律规范的拘束,应容许法官斟酌各种情况,依衡平之法理为裁判,扩大法官裁量的范围。小额事件多发生在市民的日常交往中,冲突的利益基础往往是私人利益,并不涉及重大的法律统一适用问题,因此纠纷解决方面的价值应优于规则之治的考虑。又因争议的数额较少,在纠纷解决中,更应追求简易经济之处理。为达该目的,完全可以引入与强行法不背之伦理、道德、社会规范作为处理之依据,不必拘泥于实体法的规定。在处理方式,也应优先考虑法院调解的适用,赋予法官斟酌情况强制调解与否的裁量权也未尝不可。
(四)应允许法官裁量采用自由的证明程序
自由证明是与严格证明相对应的概念。严格证明是指利用法定的证明方法并且经过法定的正式的证据调查程序所做出的证明。其他的证明为自由证明。自由证明的证据是否在法庭上出示、出示后用什么方式调查,由法院裁量。为追求小额诉讼案件的简易快速解决,应允许法官裁量采用自由证明的程序。在小额诉讼审理中,即使当事人提出要采用传唤证人或专家证人出庭作证这种证据调查方法,法官也可在“公正或适当”的情况下,仅仅采用证人或鉴定专家书面回答这种较为自由的证据调查方法。即使在当事人不在场的情况下,法官如果认为有必要,也可用电话询问等方式灵活地调查审核证据。在这种自由证明的审理程序中,同时也应考虑允许降低对案件事实的证明度。在通常的诉讼中,对事实的认定,法官的心证程度要达到高度盖然性的标准,才能认定某事实是真或是伪。在小额诉讼中,如果要达到与普通诉讼事件同样高的证明度,势必要花费相当的时间、精力、金钱去收集证据,进而增加当事人的诉讼成本。这与司法制度快速、廉价保护当事人权利的初衷背离。因此,即使没有达到高度盖然性的标准,只要法官对案件事实的心证达到一定的程度,即可认为事实已查清,法官就可以下判。唯有如此才能使小额诉讼当事人的权利获得真正的救济。
四、立法建议
依照上述分析,我国小额诉讼程序法制定时可以通过以下条款规定非讼法理的适用:
第 条 小额诉讼程序适用于金额不超过省、自治区、直辖市上年度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30%的给付金钱、有价证券等争议。应适用普通程序或简易程序的争议,如果当事人双方合意选择适用小额诉讼程序的,可以适用小额诉讼程序。法院认为适用小额诉讼程序不合适的,可以裁定适用简易程序或普通程序。
第 条 法院审理小额诉讼程序案件可以不公开审理,当事人选择公开审理的,应当公开审理
第 条 法院审理小额诉讼案件,可斟酌做出判决,但不得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
第 条 对于小额诉讼程序做出的判决,当事人不能提出上诉,但可以在接到判决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做出该判决的法院提出异议;如果异议成立,诉讼恢复到辩论终结前状态,并按照普通程序进行审理和判决,判决做出后为终局判决。
[1]邱联恭.司法之现代化与程序法[M].台北:三民书局,1992:277-288.
[2]刘敏.原理与制度:民事诉讼法修订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9:88.
[3]刘敏.论非讼法理在小额诉讼程序中的适用[J].清华法学,2011,(3).
[4]张艳丽.诉讼程序与制度前沿专论[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12:264.
[5]江伟.民事诉讼法学原理[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718.
[6](日)谷口安平.程序的正义与诉讼[M].王亚新、刘荣军,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12-15.
[7]廖中洪.中国民事诉讼程序制度研究[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4:327.
[8]刘敏.论我国民事诉讼修订的基本原理[J].法律科学,2006,(4).
[9]刘敏.论非讼法理在小额诉讼程序中的适用[J].清华法学,2011,(3).
[10](日)棚濑孝雄.纠纷的解决与审判制度[M].王亚新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249.
[11]刘敏.论民事诉讼当事人听审请求权[J].法律科学,2008,(6).
[12]沈冠伶.诉讼权保障与裁判外纷争处理[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10-11.
[13](日)中村英郎.新民事诉讼法讲义[M].陈刚,林剑锋,郭美松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303.
On the Application of Non-litigation Legal Theories in Small Claim s Procedure
SUN Yong-jun
(School of Law,Nanjing University,Nanjing 210093,China)
The currentstudy on the small claim litigation is concentrated to such aspects as introduction and comparison of small claim procedure,the construction of our small claim procedure,and the difficulties and problems of small claim litigation system.The study on procedural theory of small claim litigation operation and relative systematic design is comparativelyweak.The processofsolving disputes through small claim procedure is justa processofapplying non-contentious legal theory to a greatextent.Itembodies the principle of proceduralsymmetry,helps solve the disputes in fastand simpleway and enhances the public trustof judicature.When we improve the small claims procedure,the non-contentious legal theory should be applicable to such parties as follows:the party should choose hearing in private session,the limitation of depositing rightof litigants,application of official judgment doctrine,and permission of adopting free demonstration process by judges in their judgment.
small lawsuit;non-contentious legal theory;programmatch
D925.1
A
1674-828X(2015)01-0058-06
(责任编辑:郭 鹏)
2014-10-09
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课题“非讼法理在民事诉讼程序中的适用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12FXB010。
孙永军,南京农业大学法律系副教授,法学博士,现为南京大学法学院博士后研究人员,主要从事民事诉讼法及司法制度方面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