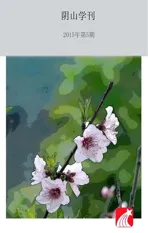米勒的中国缘
2015-02-12张伟
张 伟
米勒的中国缘
张 伟
一个艺术家,在异质文化中被接受、被认同的命运如何,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西方不亮东方亮,米勒的中国缘,就颇值得玩味。
我手头有两部欧洲美术史,一部堪称经典,是英国著名艺术史家贡布里希的《艺术的故事》;另一部颇具权威性,是《剑桥艺术史》。很遗憾,这两部煌煌巨著,都没有给米勒以我所预期的席位。
前者只在508页用一小段文字介绍了米勒的《拾穗者》,肯定了它的题材意义。学院派的观念,高贵的人才配进入高贵的画,普通工农之草根阶层,顶多在风俗画里充当群众演员。而人物画,乃贵族专属,就像当年上海租界里的那块牌子:“狗与华人不得入内。”米勒让衣衫褴褛的农妇,堂堂正正地走进了他的画作,坐正席,唱主角。
后者更加吝啬,正文只字不提,只在章节后附录的艺术家小传里,以区区100多个字的篇幅,介绍了米勒的生平,真正的叨陪末座了。这两部书,体量都很大。它们的作者,好像商量过了似的,把米勒挤兑到小角落里,这绝非偶然,而是以他们的标准作出的定评。
而在中国,米勒享有至尊的地位。西方油画被斥为封资俢、大毒草,我们几乎见不到的年代,米勒却获得了豁免权,出现在各类中文印刷品上,而且,中国读者一见如故,倍感亲切,极具亲和力。
乡土气息,苦难叙事,成为米勒与中国读者最大的契合点。
米勒说:“我生来就是个农民,到死了也是个农民。”在巴黎呆了一段时间后,他举家迁到枫丹白露的巴比松村,直到走完这一生。对自己的农民身份,他深以为自豪,并自觉自愿地以描绘农民的生活,表现他们的思想感情为己任。他在给朋友桑榭的信中写道:“无论如何,农民这题材是最适合于我的倾向的。你这个社会主义者也一定能赞成的吧!因为最能触动我的心的,是人味。”在米勒心中,那些贫寒的、辛苦的农民是“英雄形象”,他深表同情,更深怀敬意。他说:“(农民的)这些不幸,总是让我牵肠挂肚,以至我无心去寻找什么美景。因别人都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我也无意苟且偷安。”实际上,他自己也过着穷困潦倒的日子,也许正因此,他很容易走进农民的心灵世界。米勒的价值,包括他画作的商业价值,在他死后才被认可。据说,在一次拍卖会上,有个男人号啕大哭。原来,这人是个肉店卖肉的,米勒生前常去他店里赊账,他也常向米勒讨债。有一次,米勒实在拿不出钱来,说这样吧,你把我的画拿去两幅吧。这人不屑地说,哼!你那破画怎么能顶账。拂袖而去。现在看到米勒的画拍出高价,后悔不迭,痛哭失声。
米勒笔下的形象,单纯而简练,从而恰切地表现农民的简朴和纯洁。创作于1857年的《拾穗者》,描绘了农村一幕极其普通的场景,秋收时节,金色的田野一望无际,收割过的土地上,三个农妇正弯着腰捡拾遗落的麦穗。米勒没有着意刻画农妇们的容貌,弯腰的身姿更显突出,具有古典雕塑般的凝重的美。三个农妇有起有落,动作富有变化而不雷同。画面真实、亲切、美丽,汗滴禾下土,粒粒皆辛苦,是对劳动的致敬。手法简洁朴实,迷人的暖黄色调中,融入红、蓝头巾的沉稳、浓郁,构成和谐的三原色,丰富的色彩统一于柔和的调子。
米勒的画作,总是聚焦于农民的日常生活。收工了,吃饭了,昏暗的油灯下,女人缝缝补补,男人编筐编篓,婴儿在提篮里酣然入睡,透出浓郁的乡土生活气息。蹒跚学步的幼儿,正朝父亲走去;衣着笨拙的农民,躲在门板后等着麻雀进圈套;夫妻俩一起剪羊毛,男人捉住羊,女人娴熟地剃剪;冬天来了,劈砍木柴准备过冬。这一幅幅画面,只属于米勒,在那个时代,再也没有谁留下这样生动的劳作场景。
毛泽东时代的阶级意识、革命情结,也是中国读者与米勒结缘的共鸣点。即便文革结束以后,这种“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依然惯力不减。《拾穗者》背景深处那高高的麦垛,中国读者太熟悉了,那是谁家的?当然是地主家的,农妇只能在收割过的土地上捡拾聊以充饥的残羹冷炙。“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啊!贫与富,剥削与被剥削,尖锐的阶级对立,迅速点燃起仇恨的怒火,激发出反抗的斗志。那时候,就是这样解读的。牧羊女正值豆寇学龄,为生活所迫,不得不辍学,每天跟着一群羊转。女孩低头默然,本来是在做祷告,可在中国读者眼里,是可怜无助,是孤苦悲戚,是无声的呐喊。还有那个疲惫的中年农夫,脚下是贫瘠的土地,在艰辛的劳作之后,扶着锄柄稍事休息,从苦恹恹的表情,到弯腰弓背的体态,都是一种控诉。
事实的确如此,尽管米勒矢口否认他有煽动革命的创作动机,但他的多幅作品,在当时的法国社会,还是产生了这样的嫌疑,引起不大不小的震荡。
《拾穗者》在沙龙展出后,资产阶级舆论界十分警觉。有评论家著文称,这幅作品蕴有政治意图,画面上可以听见农民的抗议声。有人上纲上线说:“这三个拾穗者如此自命不凡,简直就像三个司命运的女神。”《费加罗报》上的一篇文章甚至耸人听闻地说:“这三个突出在阴霾的天空前的拾穗者后面,有民众暴动的刀枪和1793年的断头台。”这些字句,令我哑然失笑,似曾相识啊,这与极左思潮统驭下的中国,何其相似乃尔。看来,历史真的有相似的一面,经过启蒙运动洗礼的法国人尚且如此,中国发生文革,也就不难理解了,恐怕是必不可免。
有评论者说《扶锄者》不仅仅塑造了一个普通劳动者形象,而是“大地的呐喊”。还有人心怀叵测地给这个形象取了个“杜芒亚”的绰号。当时媒体曾有报道,一个叫杜芒亚的贫穷农民,杀死了雇佣他的地主一家。于是借题发挥,无端指责米勒在宣传社会主义,还危言耸听地说曾在某个社会主义者组织的俱乐部里见到过他。
米勒一生贫病交加,后来病情突然加重,在家里去世。据传说,在他弥留之际,家中园里一头被狗追逐的牡鹿,很可怜地被击中而死去。于是人们附会说,这是一种征兆,预示着这位伟大的农民画家,将要回归到大地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