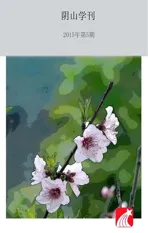扬抑屈原两世界
——试析元代少数民族散曲家对屈原的接受
2015-02-12曲钊志
曲 钊 志
(包头师范学院 文学院,内蒙古 包头 014030)
扬抑屈原两世界
——试析元代少数民族散曲家对屈原的接受
曲 钊 志
(包头师范学院 文学院,内蒙古 包头 014030)
屈原,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位浪漫主义诗人,他的刚正不阿、忠君爱国、追求真理一直为古代文人所赞扬,但到了元代,笑屈原的现象在散曲作品中表现十分普遍,作为少数民族统治历史时期,该现象有其存在的原因,元代少数民族作家在对屈原的接受程度上也有所不同。
元曲;屈原;贯云石;阿鲁威
一
屈原,作为一个伟大的历史人物,他的杰出的文学才能和高洁的品格赢得了后人的崇敬和赞美,如西汉刘安在他的《离骚传》中对屈原的为人做出了极高的评价,《离骚传》已经失传,但东汉班固在《离骚序》中引用了部分内容:“昔在孝武,博览古文,淮南王安叙《离骚传》,以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悱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蝉蜕浊秽之中,浮游尘埃之外,爵然泥而不滓;推此志,虽与日月争光可也;”[1](P49)看出刘安对屈原做出了高度的评价,既肯定了《离骚》的文学价值,又赞美了屈原高洁的品格。刘安对屈原全面而又中肯的评价,奠定了后世评价屈原的认识基础,确立了屈原伟大的形象。歌颂屈原成为有关描写屈原作品的主题。但是,历朝历代文学作品中,对屈原持批评态度的也不在少数,尤以元曲最为突出。据我不完全统计,隋树森先生编著的《全元散曲》中与屈原有关的散曲有七十余篇,其中绝大部分对其形象进行戏谑和调侃,成为了一个很有趣的文学现象,值得我们去探讨。
仔细翻看《全元散曲》我们可以发现,在与屈原有关的七十余首散曲中,以批评嘲笑屈原的作品为主。有的作品中对屈原肆意嘲讽,嘲讽他认不清官场的黑暗,如无名氏的《中吕·齐天乐·幽居》:“常笑屈原独醒,理论甚斜和正,混清争,一事无成。汨罗江倾送了残生,无能。”[2](P1712)又如王爱山的《中吕·上小楼·自适》:“思古来,屈正则,直恁得禀性僻。受之父母,身体发肤。跳入江里,舍残生,博得个,名垂百世,没来由管他甚满朝皆醉”[2](P1190)。在王爱山的笔下屈原成了一个性格执拗古怪的人,作者认为他不够明智,在“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儒家传统孝悌观的影响下,作者对屈原投江自尽、自毁生命的做法极不赞同,认为他只是为自己博一个“名垂百世”之“名”,对他“独醒”的态度不以为然。
张养浩《中吕·普天乐》:“楚《离骚》,谁能解?就中之意,日月明白。恨尚在,人何在?空快活了湘江鱼虾蟹,这先生畅好是胡来,怎如向青山影里,狂歌痛饮,其乐无涯”[2](P421)。在这首作品中,作者认为屈原跳江的行为纯属“胡来”,认为他这样的行为没有一点意义,只是满足了湘江鱼虾蟹的口腹之欲,还不如痛痛快快地高歌畅饮享受人生乐趣来得实在。
曾瑞《中吕·快活三过朝天子·警世》:“有见识越大夫,无转理楚三闾。正当权肯觅个脱身术,那的是高才处”[2](P495)。作品将屈原与越国范蠡作比较,认为和范蠡相比,屈原是没有见识的,认为屈原这种舍生取义、以身试法的做法不可取,否定了他跳江的行为,认为像范大夫一样栖身山林,脱身有术才是明智之举。
张可久《正宫·醉太平·无题》:“陶朱公钓船,晋处士田园。潜居水陆脱尘缘,比别人虑远。贤愚参杂随时变,醉醒和哄迷歌宴,清浊混沌待残年,休呆波屈原!”[2](P844)作者还是将屈原与渊明和范蠡作比较,认为渊明和范蠡隐居的行为是深谋远虑之举,对屈原的评价却是“贤愚”,认为他不懂得因时而变的做法,因此发出“休呆波屈原”的感叹。
以上作品都从不同角度嘲笑了屈原,有的认为屈原的做法太过愚钝,不值得效仿,否定了屈原的行为,认为是“无能”的表现;有的更是认为屈原的做法十分可笑,是以投江的做法来获得高名,对屈原的做法嗤之以鼻,对屈原大肆嘲笑。有的作品将屈原和陶潜并举,肯定了五柳先生的做法,却嘲笑了三闾大夫。“尊陶抑屈”这样的主题在散曲作品中屡见不鲜,几成一种文学现象。
元代散曲中的“尊陶抑屈”现象有其存在的原因。具体说来,一是由当时所处的社会环境所决定。元朝是少数民族新兴政权,由于长期战乱动荡不安,统治者采取严酷的民族等级制度,歧视汉人和南人,使得汉族文人的自尊心和心灵受到沉重的打击。“不读书有权,不识字有钱,不晓事倒有人夸荐。老天只恁忒心偏,贤和愚无分辨”(《朝天子·志感》)。“仗权豪施威势,倚强夺弱,乱作胡为。”《普天乐》都是知识分子慨叹命运不公、批判社会的黑暗的感叹。社会发生的种种巨变使文人知识分子的内心受到了巨大的冲击,传统的价值观念受到了颠覆。二是与草原文化和农耕文化的碰撞融合有关。元朝是蒙古贵族为统治民族的政权,以蒙古族为代表的草原文化与汉族为代表的农耕文化在民族习性、历史传统、价值观念等方面存在着明显差异,草原文化尚武豪放,粗犷直率,张扬个性;而农耕文化注重内在修养,讲求温柔敦厚,注重礼让。一方面两种文化发生着碰撞,另一方面两种文化联系又十分紧密。具体说来,元朝统治者一方面坚守本民族文化传统,但是为了治理国家,也不能完全抛弃农耕文化,摒弃汉法,他们不得不接受农耕文化,推行汉化。另一方面,对于汉族而言,异族掌握政权,草原文化成为当时文化的主流基,对于汉人来说,在接受草原文化时带有强迫性,汉人被迫接受,他们不喜欢为异族政权服务,所以他们不想像屈原那样盲目的忠君,从而对隐居的陶渊明情有独钟。三是由于元朝统治者重武轻文,科举考试长期废止,使文人失去了做官的机会。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知识分子失去了传统的“学而优则仕”的传统的人生道路,不得不退而求其次的选择了“独善其身”的隐居生活,选择了回归自然、放身林泉以颐养性情的生活方式,更多地去关注和思考个体自身的命运和生存问题,元代散曲以“幽居”、“隐居”、“闲适”为主题的作品铺天盖地就是最为集中地再现。屈原、陶渊明两位诗人恰恰代表了古代知识分子“仕”和“隐”的两种人生追求,而屈原忠君爱国、为理想执著奉献自己一生的入世进取品格在元代社会就显得突兀、高标,那种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积极追求真理的态度在元代就显得更不合时宜,而陶渊明为自己心灵寻找片刻安静的生活方式得到了元代文人的推崇。
二
我们知道,少数民族散曲家在元代文学史上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在元代尊陶抑屈的文化大背景下,由于身世、经历和价值观的不同,元代少数民族散曲家对屈原都有着不同的解读,他们或是怜惜屈原或是赞赏屈原,观点各不相同,贯云石和阿鲁威就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两位。
贯云石(1286-1324),本名小云石海崖,自号酸斋,又号芦花道人,维吾尔族人。其祖父和父亲都是元朝的重臣,自己也沿袭了父亲的爵位,在朝上担任高官,后隐居于浙江,年三十九而卒。
贯云石精通诗文书画,尤以散曲最为突出。隋树森所编《全元散曲》共收录其散曲87首(其中小令79首,套数8首)。其散曲内容十分丰富,有寄托思乡之情的恋亲之曲,也有描写男女恋情之曲,但表达隐逸情怀占据很大的比重,如《双调·清江引·知足》:“野花满园春昼永,客来相陪奉。草堂书千卷,下琴三弄,子落得这些儿闲受用。”[2](P369)又如《双调·清江引》 “竟功名有如车下坡,惊险谁参破?昨日玉堂臣,今日遭惨祸。争如我避风波走在欢乐窝!”[2](P368)都写出了作者不愿沾染尘世、渴望归隐山林的人生愿望,所以,贯云石特别仰慕陶渊明,其歌颂陶渊明的作品不在少数,如:“畅悠哉,春风无处不楼台。一时怀抱俱无奈,总对天外。就渊明归去来。怕鹤怨山禽怪,问甚功名在!酸斋是我,我是酸斋。”[2](P373)《双调·殿前欢》其一,在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出,贯云石十分推崇陶渊明,他不仅在作品中直接赞扬陶的人品,而且歌颂恬淡的生活,表现了自己对隐逸生活的热爱。这正是云石在官场沉浮中感悟的艺术体现。
贯云石对屈原也有着自己独特的看法,他写到:“楚怀王,忠臣跳入汨罗江!《离骚》读罢空惆怅,日用同光。伤心来笑一场,笑你个三闾强,为甚不身心放!沧浪污你,你污沧浪。”[2](P373)我们可以看到云石对屈原的态度有些微妙复杂,云石敬佩屈原是一个忠君爱国之臣,高度赞扬屈原的行为和品格,认为楚怀王才是使屈原跳江的罪魁祸首,作者责怪楚怀王就是因为他昏庸无能,导致了屈原这样的忠臣“跳入汨罗江”,对楚怀王昏庸的愤恨和对屈原的怜惜之情溢于言表;但是作者又从另一个视角着眼,认为屈原在明知自己的政治理想得不到实现的时候,还要一味的去坚持自己的想法,抱怨屈原不能“身心放”,笑他一味的“愚忠”,深陷险境却浑然不知,非要为他所谓的真理牺牲自己的生命。云石只是希望屈原内心豁达些。从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贯云石所谓“笑”屈原,不是嘲笑屈原的人品,而是对他做事的态度和价值观的追求的不理解,认为屈原欲在复杂的社会环境里保全自己的人格,完全可以选择其它的道路来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贯云石这种哀悼屈原怒其不争的态度和他自身的经历不无关系,前文已经介绍,贯云石的祖父和父亲都是元朝的高官,深得朝廷的重用,云石本人也在年轻时得到了朝廷的重任,委以高官,但是由于当时社会和时局的原因与限制,他在官场上过得并不舒心,据《元史》记载,他的祖父也成为了政治斗争的牺牲品,自尽而死,使他更加清醒地认识到官场的黑暗,他虽然仰慕屈原,但并不想像屈原一样为一个腐朽的政权服务,所以他选择了归隐山林,过起了隐居生活。他隐居去南方“卖药”,正是选择了另外一种生活方式来阐释自己的人生志向。
所以我们说,贯云石之所以“笑屈原”是出于对屈原的可惜与可怜,责怪屈原不够豁达,不能从效忠君王的思想中走出来,最后得到的却是无谓的牺牲;他并不是否定屈原以死明志的精神,而是叹息屈原没有认清“忠君”背后真正的本质,只有在保全自己生命的前提下,才能更好地效忠朝廷,更好地实现政治抱负;而不是屈原这种投江自尽的方式。贯云石在作品中揭示了屈原悲剧的外在原因,作者认为为这样不贤明的君主尽忠不值得,作者把屈原的种种遭遇与历史上无数惨痛的悲剧加以比较和思考,萌生出不能盲目而忠的思想,认为应该选择属于自己的人生道路,这是云石久经官场对人生的感悟,对自己的人生价值有了新的理解。
三
与贯云石相比,元代的另一位少数民族散曲家对屈原又有着不尽相同的一种解读,他所创作的《蟾宫曲》前九首直接模仿屈原《九歌》的形式,既表达了他对屈原的喜爱,也体现了自己的理想志向,他就是蒙古族散曲家阿鲁威。
阿鲁威(1280-1350),字叔重,号东泉,蒙古人。曾任剑南太守,后又任翰林侍讲学士,精通蒙汉两种文字,汉文修养十分深厚,曾参与翻译《世祖圣训》、《资治通鉴》等书。
屈原的《九歌》是春秋时期楚国民间祭神乐歌,诗中通过记载男巫、女巫的祭祀活动来表现作者对上天的敬仰和尊重,作者以虔诚之心歌颂各个神灵,通过对天神的礼赞,表现作者对生活的敬畏和向往。而阿鲁威则在继承中有所发展。研读作品,我们发现,阿鲁威的这些作品都是对屈原《九歌》的继承。从作品的名称和所描写的对象上,都是依照《九歌》原诗,写作者对天神的歌颂和赞扬,但屈原的《九歌》是作者现实的不平之鸣,而阿鲁威做的《九歌》既有现实的感受,而更充溢着自我高洁的志向,寄托了阿鲁威对自己前途的向往。
虽然同是敬仰天神之作,但是在阿鲁威的笔下,各个天神更富有人情味,《湘君》和《湘夫人》中,虽然是写神与神的爱情,但是在描写过程中更具有人间烟火的特点。如《湘君》:“驾飞龙兮兰旌蕙绸。君不行兮河故夷犹。玉佩谁留。步马椒丘。忍别灵修。”[2](P683)作者在这里把两个天神的爱情描绘得十分人性化,让读者感觉就像置身于尘世间的男女的爱情一样,看到的是一对恩爱恋人的不舍分离。
如果与屈原《九歌》艺术化记录楚人祭祀过程相较,阿鲁威的诗作更多体现了诗人主体的影子。“望朝嫩将出东方。便抚马安驱。揽髻高翔。交鼓吹竿。鸣旋组瑟。会舞霓裳。布瑶席兮聊斟桂浆。听锵锵兮丹凤鸣阳。直上空桑。扶矢操弧。仰射天狼。”[2](P684)让我们看到的却是作者高洁志向的体现,作品中具有正义感的太阳神,正是作者理想的化身。阿鲁威虽套用屈原《九歌》的形式,但在本质上却不断宣扬着自己对美好理想的追求。
《蟾宫曲》中更是直接借用屈原的“香草美人”的写法,“香草美人”是屈原创造的一种象征手法,这与楚地文化息息相关。阿鲁威虽为蒙古人,但是他长期在南方游历做官,在阿鲁威的其它作品中,多次涉及与南方、楚地有关的内容,其咏史怀古的散曲多次提到曹操、周瑜、范蠡等历史人物,使其散曲更具有历史文化感,而这些历史人物的活动范围恰恰都在与楚地为中心的长江流域,可见其对楚地文化十分了解,屈原在“楚辞”中借用“香草美人”来比喻美好的事物和人生志向,阿鲁威散曲中也多次借用“杜若”、“秋兰”、“芙蓉”等香草来象征美好的事物,如《湘君》:“问湘君何处翱游,怎弭节江皋,江水东流。薛荔芙蓉,涔阳极浦,杜若芳洲。驾飞龙兮兰旌蕙绸,君不行兮何故夷犹。玉佩谁留。步马椒丘。忍别灵修。”[2](P683)可以说,“香草美人”的楚辞风韵在时隔千年之后的蒙古民族文人笔下依然充满着夺目的光辉,足见阿鲁威对屈原的喜爱。
阿鲁威的《蟾宫曲》虽仿效《九歌》而作,但在继承中有所创新。将“楚辞”的雅致、飘逸与散曲的朴俗、豪放巧妙融合,弱化了《九歌》阴柔之美,有力熔铸了时代特有的刚劲壮伟之曲风,成为散曲创作上的一个奇举。
首先,从两组作品的显著差异来看,《九歌》是屈原根据流传于楚地的神话传说加以艺术加工创作而形成的祭歌,充满着宗教的神秘色彩,其核心是对战国后期楚人祭祀活动的全面艺术记录,突出了楚人祭祀的对象、内容、过程,阅读《九歌》就像置身于楚地祭祀活动一样,展示了楚地祭祀的宏大、热烈、娱乐等特征。而阿鲁威的《蟾宫曲》却重点刻画一个个鲜明的自然神形象,是对楚地神灵的生动描绘,是借神的形象抒写自我人生情怀。同样是写《大司命》,屈原笔下极尽渲染神与人世的距离之远,而阿鲁威更注重神的内在情态,主体情感渗透深刻、鲜明。其次,在作品的形式方面,屈原《九歌》句式皆以一句一兮叹惋、吟唱,分为五言、六言、七言、八言、九言等不同形式,变换不一,形态各异,呈现出一种丰富多彩、错落有致的句式之美,烘托出一种深情摇曳、惆怅百转的迂回折远之态。而阿鲁威改变了《九歌》写作格局,既不是一句一兮,又以极少七言、多作四言为主的句式,营造出一种整饬有力、简劲利落的艺术氛围,体现出一个蒙古民族诗人特有的艺术追求。
人生“不遇”,古为常态。阿鲁威虽为蒙古人,本应平步青云,但他在政治上始终不被重用,内心充满了彷徨、苦闷,于是努力从浩远的汉民族文化、文学世界中寻求可以慰藉自我痛苦、支撑自我追求的文化偶像,而屈原以及《九歌》所蕴含的精神文化使他找到了抒发自我的突破口。他既同情屈原的种种不幸,又赞美他忠君爱国的精神,他的《蟾宫曲》九首,就是以他自己的方式敬仰屈原、抒发自己远大理想的最好例证。
结 语
贯云石、阿鲁威都为少数民族散曲作家,然而,他们对屈原的态度不尽相同,贯云石以由“哀”转“笑”的方式来评判屈原,而阿鲁威则是在作诗和做人上效仿屈原;不管对屈原是“笑”,还是赞扬,都可以看出以屈原为代表的汉民族文化已在少数民族知识分子中深深扎根,影响深远。
[1]洪兴祖.楚辞补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3.
[2]隋树森.全元散曲[M].北京:中华书局,1964.
〔责任编辑 王 宇〕
On the Rise and Fall of Qu Yuan:Acceptance on Qu Yuan by the Ethnic Verse Writers in Yuan Dynasty
QU Zhao-zhi
(Faculty of Arts, Baotou Teachers College; Baotou 014030)
Qu Yuan, the first romantic poet in Chinese history, has always been praised by the ancient literati for his upright and out spoken personality, loyalty and patriotism, the pursuit of truth. However in the Yuan Dynasty, Qu Yuan was often sneered in the verses. In a minority ruling period, this phenomenon has its reason to exist, and the ethnic writers were different in accepting Qu Yuan.
Verse in Yuan Dynasty; Qu yuan; Guan Yunshi; Ar Luwei
2015-05-13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古代北方草原文学美学价值研究”(12XZW016)阶段性研究成果。
曲钊志(1990-),男,内蒙古呼伦贝尔人,包头师范学院文学院硕士生,主要从事宋辽金元文学文化史研究。
I29
A
1004-1869(2015)05-0036-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