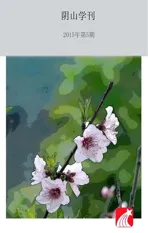辽代饮食结构新探
2015-02-12田晓雷
田 晓 雷
(吉林大学 文学院,吉林 长春 130012)
辽代饮食结构新探
田 晓 雷
(吉林大学 文学院,吉林 长春 130012)
以辽墓壁画做切入点,结合文献资料对辽代饮食进行探讨:西瓜的传入大概在太祖天赞年间,蒸馏酒的制作早在辽代就已经成熟,其食材除了自产外,多通过对外贸易获得。辽代饮食结构的多元化、食材产地的多元化,反映了在辽政权的统治下,各民族之间相互交融,不断彼此融合的历史事实。
辽墓壁画;饮食结构;食品产地;多元化
辽是以契丹人为统治民族建立的王朝,其统治区域包括了适于游牧的草原地带和适于农耕的东北平原、华北平原的大部分地区。在辽的统治下,游牧、渔猎、农耕民族彼此互相交融,形成了多种不同文明的交汇。这一点也充分地反映在辽人的饮食结构之中,随着考古工作的不断深入,一些辽墓壁画的出土,给研究者们提供了一个新的资料来源,从而得以窥探辽人的饮食结构。关于辽人的饮食,岛田正郎、张国庆等前辈学者都已做了不同程度的探讨*参见岛田正郎著,何天明译《大契丹国——辽代社会史研究》,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张国庆《辽代契丹人饮食考述》,《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北京)1990年第1期;张国庆《辽代社会史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其中王大方《从出土壁画看契丹人的蔬菜和水果》[1]、张景明《辽代饮食文化在墓葬壁画中的反映》[2]对辽代饮食从辽墓壁画入手作了开拓性研究。笔者将近年来出土整理的辽墓壁画反映饮食的部分进行整理,以此为基础,并结合文献资料,进行探讨。由于辽朝境内民族结构复杂,出土的墓葬壁画分布不均,本文只是对辽人的饮食结构的基本情况做一笼统的拙论,各民族详细的饮食构成另作他文研究。
笔者将辽人饮食分为主食、副食、饮品三个类别,分别论述如下。
一、主食类
(一)谷物类
通过辽宁朝阳北三家1号墓东耳室《契丹族膳房图》、北京赵德钧墓《卷袖揉面女仆》、解放营子辽墓《契丹人原野宴饮图》、北京赵德钧墓《托盘进食女仆》[3](P30、25、10、25)及辽庆陵陪葬墓耶律弘世墓画《仆佣图》、辽庆陵陪葬墓耶律弘世墓画《敬食图》、赤峰市敖汉旗贝子府镇大哈巴齐拉村喇嘛沟辽墓壁画《备饮图》、通辽市库伦旗奈林稿苏木前勿力布格村辽墓壁画2号壁画《侍仆图》等辽墓壁画[4](P105、120、109、245),可以看出,由谷物类制成的米面是辽代的主要主食。其中辽庆陵陪葬墓耶律弘世墓画《仆佣图》中,仆佣所端盛的食物可以清晰地看出是面条。辽庆陵陪葬墓耶律弘世墓画《敬食图》、四家子镇闫杖子村北羊山辽墓壁画《烹饮宴饮图》、解放营子辽墓《契丹人原野宴饮图》中可以明显地看出包子、馒头、烤饼等食品。通过文献资料和考古壁画可知,辽人的面食烹饪水平已比较成熟,在辽人祝贺宋朝皇帝生日的礼单中就有“麫秔糜梨粆十椀”[5](P226),尤其是北京赵德钧墓《卷袖揉面女仆》、《托盘进食女仆》中清晰地描绘了女仆制作面食的流程方法,其中《卷袖揉面女仆》中女仆揉面的描绘与今天面食做法几无二致。关于烹饪面食的炊具,贝子府镇大哈巴齐拉村喇嘛沟辽墓壁画《备饮图》中清晰描绘有蒸笼一类的烹饪器具。
关于粮食的来源,辽代粮食的主要来源是本国耕种和对宋走私贸易,此外新罗、高丽对辽的朝贡也有一定数量的粮食输入,但并不是主要来源。
由于生活在农牧交界带的两河流域*两河流域:即西拉木伦河,老哈河流域。,契丹民族很早就开始了农业耕作,史载,“初,皇祖匀德实为大迭烈府夷离堇,喜稼穑,善畜牧,相地利以教民耕”[6](P923)。阿保机建国后,将大量汉人迁入契丹内地,设立州县,实行农业开发。辽朝历朝政府都十分重视农业耕种,太祖“平诸弟之乱,弭兵轻赋,专意于农”[6](P923);太宗会同元年(938年)“三剋言农务方兴,请减辎重,促还朝,从之”[6](P43);统和三年(985年),圣宗出外巡视,“见乙室奥隗部下妇人迪辇等,黍过熟未获,遣人助刈”[6](P923)。可知,辽代的农业耕种并不仅限于传统从事农耕作业的汉人、渤海人。在契丹人当中,一些编在部族下的部民也从事农业生产,从上述史实中可见辽朝政府对农业生产的重视。
辽人生产的主要谷类有粟、黍、稻、粱等,小麦也有种植。其中黍、粟、粱、小麦是制作面食的主要原料。辽庆陵陪葬墓耶律弘世墓画《仆佣图》中的面条类食品,联系墓主人皇弟之尊的大贵族身份*耶律弘世系辽道宗耶律洪基之弟,即《辽史·道宗纪》所载秦越国王阿琏。参见《耶律弘世墓志》,转引自向南、张国庆、李宇峰辑注《辽代石刻文续编》,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91页。,笔者推测是为麦面。而且其他壁画中所见面食,或为黍、粱、粟制成的。黍的种植是辽代种植最为普遍的农业作物之一,据竺可祯先生考证,辽代正值北方气候不断转寒的时期[7](P425~498),黍抗寒耐旱,适于在辽朝境内广泛种植。除了一般的州县民户,寺院一般也以其为主要种植作物,寺公大师《醉义歌》中“黍稷馨香棲畎畂”[8](P363)即为一明证。
此外,粟,即小米,也是辽代种植较为普遍的粮食作物之一。辽人粟的产量很高,景宗曾于保宁九年(977年)“诏以粟二十万斛助汉”[6](P99),可见,高产量的粟不仅作为辽人的日常口粮,也用作对外军事援助物资。圣宗时期开始设立的“义仓”,其中的主要储备就是粟,辽朝将其作为备荒的主要粮食,统和十五年(998年),辽朝政府就曾“发义仓粟赈南京诸县民”[6](P149),民间关于粟的交易也很普遍,以咸雍元年(1065年)的春州(今吉林省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西北塔虎城遗址,本辽长春州)[9](P405)为例,当时“春州斗粟六钱”[6](P271),说明粟已经有了明确的市场价格,并得到了官方的认可。
稻也是辽代常种植的粮食作物,种植地主要在辽南京道和西京道,《辽史·地理志》载,“南京析津府。本古冀州之地……其谷黍、稷、稻。”起初,出于对宋战争的需要,辽统治者不允许南京民户种植水稻,景宗“保宁中,(高勋)以南京郊内多隙地,请疏畦种稻,帝欲从之。林牙耶律昆宣言于朝曰,‘高勋此奏,必有异志。果令种稻,引水为畦,设以京叛,官军何自而入?’帝疑之,不纳。”[6](P1317)直到道宗清宁十年(1064年),朝廷还下令“禁南京民决水种粳稻”[6](P263)。但是朝廷的禁令并不能阻碍水稻种植的发展,咸雍四年(1069年),朝廷“诏南京除军行地,余皆得种稻”[6](P267)。对于辽朝政府取消禁令的原因,韩茂莉认为,在认识到水稻的单位产量较高,并可以用来有效缓解辽朝道宗时期粮荒问题的同时,辽宋双方军事对峙的消除,辽朝对宋军事防范的松怠也是辽朝政策发生转变的重要原因[10](P110~111)。
除了辽国本土种植粮食作物以外,宋辽之间的走私贸易也是辽朝获取粮食途径之一,因为宋朝将粮食作为禁品,不能通过宋辽榷场公开贸易[11](P146~156),加之辽本土的粮食产量逐渐不足以满足自身需要——道宗咸雍八年(1072年)就曾发生过“岁饥,免武安州租税,振恩、蔚、顺、惠等州民”,仅《辽史·道宗纪》所载道宗一朝政府赈济百姓的活动就达20余次[6](P251~314)。接连不断的粮食问题,使得辽朝方面持续从宋辽边境走私粮食。其实,早在澶渊之盟前,辽朝方面就已经从宋走私粮食,宋太宗雍熙四年(987年)“五月诏访闻河北河东沿边州军城寨多放斛斗入北界,累降诏旨,断绝其两地供输人户,止许籴上二斗供家食用,今知沿边及两地供输人户托此为名夹带,将过来偷买斛斗将去”[12](P7247)。澶渊之盟签订后,走私贸易依然存在,宋朝方面虽然明令禁止“诏河北州军民有赴北界市粮及不系禁物,为北界所补送者,并决杖一百释之”[13](P2159),但是仍然无法阻止这种走私贸易,仁宗天圣七年(1029年)六月“窃闻今春河北客旅从御河载斛斗往边上州军入中,经由潮河、界河,多将粜与北界人”[12](P5496),可见,粮食的走私活动直到宋仁宗时期仍然在河北一带存在着。
除此而外,各国来使朝贡,粮食也是其中的贡品之一,《契丹国志·横进物件》载,(新罗、高丽)“粳米五百石,糯米五百石”[5](P226),可见,新罗或是后来的高丽都要对辽朝贡一定数量的粮食。这对于辽王朝来说,并不算多,统和二十五年(1007年),“(耶律唐古)移屯镇州,凡十四稔,积粟数十万斛,斗米数钱”[6](P1362),那么平均一年仅镇州(今蒙古国南部布尔根省南都喀鲁河南岸之青陶盖勒古城遗址)[9](P970)一地便可得粟米万斛,斛和石基本相当[14](P238~240),由此可见,总共一千石的进贡粮食,对于一个边城便能年积聚粟米万斛的辽朝,其在整个辽朝粮食总量中的比重是很低的。这部分粮食输入只是朝贡国向受贡国表示顺从的一种表现,其经济意义并不大,也不占辽朝粮食进口的大宗。
应该指出的是,辽王朝的统治者虽然积极鼓励粮食种植,但受环境、生活习惯等限制,其粮食主产区主要集中在汉人聚居区,农耕在传统草原地带并不占主导地位。
(二)肉类
宝山辽墓壁画1号辽墓壁画《犬羊图》,赤峰市巴林左旗前进村辽墓壁画《备宴图》,敖汉旗辽墓壁画南城子城乡兴太村下湾子1号辽墓壁画《备饮图》,四家子镇闫杖子村北羊山辽墓壁画《烹饮宴饮图》、《备饮图》,贝子府镇大哈巴齐拉村喇嘛沟辽墓壁画《烹饪图》,通辽市库伦旗奈林稿苏木前勿力布格村辽墓2号壁画《侍仆图》,7号壁画《野猪图》[4](P40、132、147、162、174、192、249、285),解放营子辽墓《契丹人原野宴饮图》和康营子辽墓《契丹奴仆备食图》[3](P10、23)都描绘了辽人食肉、烹饪肉食的场景,肉类是已知辽墓饮食类壁画中出现频率最高的辽人食品。这些壁画中清晰地描绘出的肉食有:鸭(鹅)、野猪、羊。如宝山辽墓壁画1号壁画《犬羊图》中就描绘有羊,康营子辽墓《契丹奴仆备食图》中则在煮食的三足鼎中有鸭头(鹅头)、羊头的描绘。辽人食用肉类的方法,从壁画中看,主要是用三足鼎加以煮食,康营子辽墓《契丹奴仆备食图》、赤峰市巴林左旗前进村辽墓壁画《备宴图》等壁画中对此多有描绘。此外,也有平底锅等煮食器物。其饮食方式,除了壁画中表现的为煮食外,辽人还会制作肉酱,《契丹国志·岁时杂仪》中载:“出兔肝切生,以鹿舌酱拌食之。”[6](P283)
其中,羊是辽人主要的食用产品。岛田正郎认为,在辽人的畜牧产品中“羊用于食肉”,“牛主要是提供饮乳”,“马在平时可用其乳酿酒”[15](P216)。苏辙《渡桑乾》中云,“羊脩乳粥差便人。”[16](P115)可以和岛田氏的看法互相印证。辽人牧养的牲畜,以马为最多,其次是羊[17]。辽代的养羊之盛,从其与宋的榷场贸易中就可见一斑,当时“河北榷场,博买契丹羊岁数万”[13](P5136),羊是契丹向宋输出的大宗商品之一[11](P146~156),契丹能够向宋输出大量的羊,一方面说明了宋人对辽羊的需求量之大,宋王朝的祭祀用羊几乎都来自与辽之间的榷场贸易;另一方面也反映了辽国国内羊的养殖情况的繁盛。
鸭(鹅)是辽人喜爱的禽类饮食之一,穆宗曾因打猎捕获野鸭“除鹰坊刺面、腰斩之刑”,“庚午获鸭,甲申获鹅,皆饮达旦”[6](P83)。可见辽人对野鸭鹅的喜爱。辽人的鸭、鹅,多为打猎而来,契丹皇帝每年春“捺钵”,三月冰冻解开后,即开始捕捉天鹅、野鸭,并举行“头鹅宴”的活动,《辽史·营卫志》载:“皇帝得头鹅,荐庙,群臣各献酒果,举乐。更相酬酢,致贺语,皆插鹅毛于首以为乐。赐从人酒,遍散其毛。弋猎网钩,春尽乃还。”[6](P347)“头鹅宴”对于当时的辽人来说,是十分隆重欢闹的庆典活动。
(三)乳粥、汤羹
辽庆陵陪葬墓耶律弘世墓画《仆佣图》、《归来图》、《调羹图》,康营子辽墓《契丹奴仆备食图》,北三家1号墓东耳室《契丹族膳房图》[5](P104、112、114)[4](P23、30)均描绘了辽人饮食、制作汤羹的场景。辽庆陵陪葬墓耶律弘世墓画《仆佣图》中仆佣所端盛的即应是一种饮汤羹的器具。《归来图》中,领行人所提携的罐装物器,与同一墓葬中《调羹图》所绘的提梁鼎十分类似,可以视为同类型的盛装汤羹的器物,并可充当炊具。这种类似的物件,在康营子辽墓《契丹奴仆备食图》、北三家1号墓东耳室《契丹族膳房图》中也有出现,可视为辽人炊饮汤羹乳粥的器物之一。
乳制品在辽地饮食中很为普遍,是为辽人日常饮食中必备的食品。辽人“行则乘马,食牛羊之肉酪”[16](P86)。《辽史·食货志》载:“马逐水草,人仰湩酪,挽强射生,以给日用,糗粮刍茭。”[6](P923)可见辽人,尤其是从事非农业生产的契丹和其他游牧民部民,乳制品是其维持生计的主要饮食。[17]此外,《契丹国志·王沂公行程录》中“逐水草射猎。食止麋粥、粆糒”和“烹乳酪之珍馐,造醍醐之上味”[18](P345)等记载中都表明了在辽代,乳制品成为社会各个阶层普遍食品。其中,乳粥(即谷物类与乳类混杂的一种食物)是为上品,史载“先公使辽日,供乳粥一椀甚珍”[19](P138),常作为招待宋使之物。
二、副食类
在赤峰市巴林左旗前进村辽墓壁画《备饮图》、四家子镇闫杖子村北羊山辽墓壁画《敬茶图》、《备饮图》,解放营子辽墓《契丹人原野宴饮图》和北京斋堂辽墓《侍女图》[4](P156、164、167)[3](14、25)几幅辽墓壁画中,可以清晰地看到桃子、石榴、西瓜和类似李子、枣子、樱桃等水果。其中,四家子镇闫杖子村北羊山辽墓壁画《备饮图》仅是从其盛装器物与其他几幅图类似,进而推测所盛之物可能为水果。辽人的饮食中,瓜果是其常见的副食类产品。史载“宁江州去冷山百七十里,地苦寒,多草木,如桃李之类,皆成园。至八月,则倒置地中,封土数尺,覆其枝干,季春出之。厚培其根,否则冻死。”[20](P26)可见,在东京道宁江州(今吉林松原市东三岔河镇东北石头城子)[21](P841),辽朝建有果园。除了辽皇室和贵族普遍种植瓜果外,民间瓜果种植也达到了一定规模,尤其是南京道地区,沈括所记“中京始有果蓏而所植不蕃。契丹之粟,果瓠皆资于燕。”[16](P86)而《祐唐寺创建讲堂碑》又载“井有甘泉,地多腴壤,间栽珍果,棋布蔬畦。”[9](P96)说明一般的寺院中也多有瓜果的种植。除了上述所叙外,胡峤《陷北记》“上京东去四十里,至真珠寨,始食菜。明日东行,地势渐高,西望平地松林,郁然数十里。遂入平川,多草木,始食西瓜。”[5](P266)中有关于上京道种植西瓜的记载,这些都表明了辽代瓜果种植的范围十分宽广。对于民间种植瓜果,辽朝政府是积极鼓励的,兴宗就曾“诏内地州县植果”[6](P245)。其饮食方式,除了壁画中所表现的鲜食外,文献中多记载为制成果脯一类食品。述律太后在太宗灭晋后曾“遣使以其国中酒馔铺国赐帝”[5](P45),在庆贺宋朝皇帝生日的礼单中也有“蜜晒山果十束棂椀”[5](P225)。将果脯作为赠送宋帝的礼物,可知果脯作为辽地的特产,其制作工艺在当时已经比较成熟。
桃李多为地产,前文所引史料已述。
西瓜,根据胡峤《陷北记》的记载,“云契丹破回纥得种,以牛粪覆棚而种,大如中国冬瓜而味甘。”[5](P266)可知,西瓜并不源自契丹本土。其传入时间,据胡峤所记应是契丹大破回鹘以后,由于胡峤是在五代后晋时期亡入辽地,《陷北记》所载又为会同七年(947年)至应历三年(953年)故事,所以西瓜传入契丹应是太祖西征之后。太祖时期曾两次西征,其中天赞三年(924年)的第二次西征,“获甘州回鹘都督毕离遏,因遣使谕其主乌母主可汗”[6](P20),重创了甘州回鹘。在此之前并无文献记载辽朝境内已经存在西瓜的种植,因此,笔者推测,大约是在这一次双方之间的军事冲突中,即天赞三年(924年)或稍后,西瓜的种植技术从回鹘传到了辽地,此后辽人开始大规模种植西瓜,按照胡峤所记,“上京东去四十里,至真珠寨,始食菜。明日东行,地势渐高,西望平地松林,郁然数十里。遂入平川,多草木,始食西瓜。”[5](P266)其种植范围大致在今天的敖汉旗附近,也就是说,在会同年间,上京道的辽朝腹地已经有西瓜种植。
一般认为石榴是在张骞开凿西域之后传入中原的,故称蕃石榴。但直到两晋,石榴仍为珍稀水果,并没有大范围地广泛种植。史载“三桃表樱胡之别,二柰耀丹白之色,石榴蒲桃之珍,磊落蔓延乎其侧。”[22](P1506)唐代石榴的种植有所发展,长安一带已经有所种植,“甘露之变”即发生在宫内的石榴树旁。[23](P562)宋代,石榴的种植已经颇为普遍,“懿易款云‘有妻兄张驾举进士,识湛,懿亦与驾同造湛门,尝以石榴二百枚、木炭百秤馈之’”[24](P13059)。石榴已经成为文人、官僚之间互相馈赠之物。张亮采认为,宋辽之间的榷场贸易中存在果实的交易[11](P146~156),而临近宋辽边境的陕西自从唐朝以来就已经有了石榴的种植,那么石榴通过双方的榷场贸易而输入辽地是很正常的。另据漆侠、乔幼梅《辽夏金经济史》中认为,辽与周边各国都存在商业贸易往来[25](P101~108),长泽和俊也认为辽与西域各国之间的贸易数量很大,只是没有被记载下来[26]。那么原产自西域的石榴通过双方的贸易往来到达辽地就是很正常的了。综上所述,石榴的来源基本来自两处,即通过南方的对宋贸易和西部的与西域各国的贸易,使得石榴输入辽地,但是由于石榴本身的生长条件,辽地并不适宜其种植,故推测辽人可能并没有在辽朝境内种植石榴,至少在目前的辽史文献和碑刻资料中尚无直接发现。
《辽史》中有“晋遣使进樱桃”[6](P49)的记载,可知,后晋是曾经给辽人进献过樱桃的,由此可以得知通过与后晋、后汉及后来的北宋政权的贸易交往,辽人是可以获得樱桃的,辽人饮食中的樱桃大概是主要源于这条途径。此外,据《辽史·兵卫志》中“起汉人乡兵万人,随军专伐园林,填道路。御寨及诸营垒,唯用桑、柘、梨、栗。”[6](P399)和《契丹国志·契丹贺宋朝生日礼物》“面枣、楞梨、堂梨二十箱,面粳麋梨粆十椀”[5](P225)的记载,可知,辽人饮食中还有梨、枣等水果。但相关史料和考古资料并不是很充分,无法进行细致研究。
三、饮品类
(一)酒
辽庆陵陪葬墓耶律弘世墓画《仆佣图》、赤峰市巴林左旗前进村辽墓壁画《备饮图》、贝子府镇大哈巴齐拉村喇嘛沟辽墓壁画《备饮图》、康营子辽墓《契丹奴仆备酒图》、解放营子辽墓《契丹人原野宴饮图》[4](P106、107、156、190)[3](23、10)中均描绘了辽人饮酒的场景和备饮状态。同时,这些壁画中表现了契丹人常常是茶饮兼备的,并且酒果同吃。辽人饮酒的器具张国庆在其《辽代契丹人的饮酒习俗》已经做了详细的分类[27](P6~9),在所见辽墓壁画中常见的有壶、高脚杯、罐等物。杨柏怡在《辽朝酒文化与民族文化交流》中将辽人的酒做一详尽的分类[28],笔者以此为参考,现将其对辽人酒品分类如下:奶子酒、挏马酒、菊花酒、茱萸酒、面曲酒、葡萄酒、法酒、糯米酒,有新罗国贡进的法清酒醋。笔者在其基础上,认为可以就其原料加以分类,分为乳酒、谷酒、果酒和其他,共四类。
其中,乳酒是北方民族世代相传的生活饮品,岛田正郎就认为辽代的马除了战备及运输外,“在平时可用其乳酿酒”[15](P216)。辽代畜牧业兴盛,“天祚初年,马犹有数万群,每群不下千匹”[6](P932)。这给辽人饮用乳酒创造了优越的条件。
果酒,有明确记载的是在穆宗应历二年(952年)“汉遣使进葡萄酒”[6](P70)和景宗保宁九年(977年)“汉遣使进葡萄酒”[6](P100),由此可知,辽在北汉政权交往的过程中,有葡萄酒的输入。葡萄原产自西域,自张骞开凿西域而传入中原,五代辽宋时期,葡萄成为河东一带地区广泛种植的水果之一,“今河东及近京州郡皆有之”,太原一带的葡萄酒制作技术闻名遐迩,“今太原尚作此酒,或寄至都下,犹作葡萄香”[8](P363)。北汉政权将本地的特产贡献辽朝合乎当时不同政权之间相互交往的礼仪。至于辽与宋的交往过程中会不会输入葡萄酒或接受宋的馈赠,史载不详,亦不可知。
谷酒则多以黍、粟为原料,多产自南京道一带,《醉义歌》中“旋舂新黍爨香饭。一樽浊酒呼予频”[8](P363)中的浊酒即为这种谷酒,其中的面曲酒还被列入祝贺宋朝皇帝生日的礼单之中。可见辽人酿酒技术水平已经很高。此外,糯米酒多为宋朝劳谢契丹来使的赐物[5](P227)。
应该特别指出的是,近些年来在吉林省大安市发现的辽代酿酒遗址[30]对于探讨中国白酒(烧酒、蒸馏酒)起源,有着重要的学术意义和现实意义。中国早已应用酒曲及酒药酿酒,但在蒸馏用具呈现以前还只能酿造酒度较低的果酒或黄酒。以谷物为原料,采取蒸馏法可取得酒度高的白酒,出现的要晚于发酵酒。至于白酒什么时候出现的,学术界有不同见解,目前比较流行的看法是“元代起源说”,认可李时珍所著《本草纲目》的说法,“烧酒非古法也,自元时开创,其法用浓酒和糟入甑(指蒸锅),蒸令气上,用器承滴露。”[31](P1567)技术来源倾向于蒙古西征的时候,把西欧的一些白酒的酿造工艺带到中国;此外还有东汉起源说、宋代起源说、唐代起源说等。文献记载最早可托的史料是北宋苏轼著《物类相感志》所记载的“酒中火焰,以青布拂之自灭”[32](P6)。能焚烧的酒度数要高。大安发现的辽金时期酿酒遗存,印证了苏轼的记录。目前,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对大安酒厂出土的两件大铁锅,两件小铁锅,一件铁承接器,一件大瓷瓮,以及约三百件炉灶石块进行研究剖析,认为这些遗物为辽金时期文物。冯恩学认为大安出土的大铁锅口径大,腹浅平,直径147厘米,深度只有17厘米,不合适做饭,是专用于烧酒的底锅。两件大铁锅与两件小铁锅配套,合乎烧酒锅具是天锅与地锅旁边接木甑的组合。大铁锅坐在灶口内,上方露出半个筒腹陶器侧壁有穿孔,是承接天锅冷却酒露水的盘,穿孔接收可以引酒水外流到木甑外。这与明代医学家李时珍所著《本草纲目》中对酿制烧酒工艺的描写一致[30]。
(二)茶
张□□墓的《备茶图》[33](P66)详细描绘了辽人制茶、饮茶的程序。而赤峰市巴林左旗前进村辽墓壁画《煮茶进饮图》、敖汉旗辽墓壁画南城子城乡兴太村下湾子1号壁画《备饮图》、辽庆陵陪葬墓耶律弘世墓画《备饮图》[4](P153、147、118)都有辽人饮茶的描绘。茶是辽人不可或缺的饮品。辽人好吃肉和乳品,需要茶来去解油腻,故又称茶药。辽地的茶主要有饼茶和散茶,饼茶是为上品,《辽史·礼志·曲宴宋使仪》载“殿上行饼茶”[6](P525),可见其作为重要的礼仪用品。张舜民《画墁录》也载“自尔辽人非团茶不贵也,常以二团易蕃罗一匹。”[34](P14)辽人的茶基本都来自于南方政权控制的地区,史载“后唐庄宗同光二年(924年)十一月己丑幽州李存贤奏契丹林牙求茶药。”[35](P11560)可知辽人很早就向南方政权通贸茶叶。张亮采认为,宋辽之间的榷场贸易中,茶叶是双方重要的贸易商品[11](P146~156)。除了正常的榷场贸易,走私贸易也存在着。对于茶叶贸易,日本学者加藤繁认为,早在宋太宗时期,宋朝民间的茶叶贸易就已经延伸到河北一带[36](P575),由于此时双方没有建立严格明确的榷场贸易制度,宋辽边境上双方之间存在着茶叶走私是很正常的。澶渊之盟后,由于双方之间榷场贸易的明确建立,茶叶并不在宋朝输入辽地的禁品之列,“辇香药、犀象及茶与交市”[37](P588)。因而宋辽之间的茶叶贸易主要还是通过榷场来进行,走私所占的比重应很有限,仅是在宋辽双方榷场贸易不能够满足彼此的需要时,榷场贸易的必要补充。[38](P18)
此外,宋朝派往庆贺辽帝的生日礼物中,茶叶也是重要礼品之一,《契丹国志·宋朝贺契丹生辰礼物》中载“的乳茶十斤,岳麓茶五斤。”[5](P226)除了通过与南方政权的交往获取茶叶外,新罗和后来的高丽,也是辽地茶叶的产地。《契丹国志·新罗国贡进物件》中就载“脑元茶十斤。”[5](P228)《高丽史》也载,“金元冲还自契丹。诏曰:省所上表谢恩,今朝贡,并进金吸瓶、银药瓶、幞头、沙纻布、贡平布、脑元茶、大纸、细墨、龙须養席等事,具悉,”[39](P85)但与宋朝相比,朝鲜半岛上输入辽地的茶叶量并不大,且基本都为脑元茶这样的单一品种。
综上所述,从辽墓壁画中可以看出辽人的饮食结构并不单一,来源多样。考察其原料产地可以看出,辽人的饮食中舶来品占了十分重要的位置,这一方面由于辽地自身地理环境和当时的气候条件,使得其自身种植能力有限,种植类的粮食和瓜果蔬菜不得不依赖对外贸易,以获取所需食品;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当时各国各地相互之间交流的发达,辽朝接受着周边各国不同文化的影响。辽人的饮食结构呈现多元化,不仅仅是产地的多元化,伴随着饮食原料的传入,不同的文化也在辽地汇聚到一起,这些不同的饮食文化相互影响,促进了统一多民族王朝的发展。
[1]王大方.从出土壁画看契丹人的蔬菜和水果[N].中国文物报,1999-03-17.
[2]张景明.辽代饮食文化在墓葬壁画中的反映[A].中国古都研究(第十八辑上册)——中国古都学会2001年年会暨赤峰辽王朝故都历史文化研讨会论文集[C].赤峰,2001.
[3]项春松.辽代壁画选[M].上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4.
[4]孙建华.内蒙古辽代壁画[M].呼和浩特:内蒙古自治区考古文物研究所文物出版社,2009.
[5](宋)叶隆礼.契丹国志[M].北京:中华书局,2014.
[6](元)脱脱等.辽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
[7]竺可桢.竺可桢文集[M].上海:科学出版社,1979.
[8]陈述.全辽文[M].北京:中华书局,1982.
[9]邱树森.辽金史辞典[Z].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11.
[10]韩茂莉.辽金农业地理[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
[11]张亮采.宋辽间的榷场贸易[C].东北师范大学科学集刊,1957,(03).
[12](清)徐松.宋会要辑稿[M].北京:中华书局,1957.
[13](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M].北京:中华书局,1995.
[14]吴承洛.中国度量衡史[M].上海:上海书店,1984.
[15](日)岛田正郎.大契丹国——辽代社会史研究[M].何天明译.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4.
[16]赵永春辑校.奉使辽金行程录[M].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5.
[17]张国庆.辽代契丹畜牧业述论[J].中国农史,1993,(3).
[18](辽)李夏等.洪福寺碑[A].辽代石刻文编[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
[19](宋)朱彧.萍州可谈[M].北京:中华书局,2007.
[20](宋)洪皓等撰.松漠纪闻[A].李澍田.长白丛书(初集)[M].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86.
[21]史为乐等.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Z].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
[22](唐)房玄龄等.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23](后晋)刘昫等.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24](元)脱脱等.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7.
[25]漆侠,乔幼梅.辽宋金经济史[M].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1994.
[26](日)长泽和俊.辽对西北路的经营(下)[J].陈俊谋译.民族丛译,1984,(5).
[27]张国庆.辽代契丹人的饮酒习俗[J].黑龙江民族丛刊,1990,(1).
[28]杨柏怡.辽朝酒文化与民族文化交流[D].长春:吉林大学,2007.
[29](宋)唐慎微.重修政和证类本草[M].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13.
[30]宋晖,陈曦.吉林发现最早的白酒酿造作坊遗址[N].中国社会科学报,2012-05-18.
[31](明)李时珍.本草纲目[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81.
[32](宋)苏轼.物类相感志[M].北京:中华书局,1985.
[33]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宣化辽墓壁画[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1.
[34](宋)张舜民.画墁录[M].北京:中华书局,1991.
[35](宋)王钦若等撰.册府元龟[M].南京:凤凰出版社,2006.
[36](日)加藤繁.中国经济史考证[M].吴杰译.北京:中华书局,2012.
[37](宋)马端临.文献通考[M].北京:中华书局,2011.
[38]宋一娈.试论宋辽的茶叶贸易[D].长春:吉林大学,2005.
[39](朝鲜·李朝)郑麟趾等.高丽史[M].(日)市岛谦吉辑.东京:书刊行会,1909.
〔责任编辑 常芳芳〕
A Research into the Diets in Liao Dynasty
TIAN Xiao-lei
(College of Humanities, Jinlin University; Changchun 130012)
Studying the tomb murals in Liao Dynasty and the literature, this paper researches into the diets in Liao Dynasty and has a conclusion that the diversification is the most obvious character of the diets in Liao Dynasty which reflects the integration and communication of all nations in Liao Dynasty.
tomb murals; diets; producing area of food; diversification
2014-09-01
田晓雷(1990-),男,辽宁沈阳人,吉林大学文学院博士生,主要从事辽金制度史、社会史及中国地方史研究。
K207
A
1004-1869(2015)05-0074-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