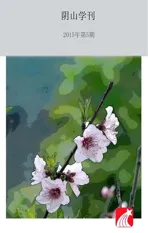借兵平寇的得与失
——简论回纥助唐平定安史叛乱
2015-02-12董文阳
董 文 阳
(安徽大学 历史系,安徽 合肥 230000)
借兵平寇的得与失
——简论回纥助唐平定安史叛乱
董 文 阳
(安徽大学 历史系,安徽 合肥 230000)
唐朝在平定安史之乱的过程中,多次向回纥借兵。前人相关著作多盛赞回纥对于唐朝平叛作用之大,并简单的把唐朝借兵的原因归结于唐回友好关系。以回纥助唐的具体战例为史料,可以看出前人对回纥助战的作用有所夸大,事实上回纥在战争中所起的作用有限。唐朝向回纥借兵,主要是因为唐朝征调少数民族武装的惯例、唐肃宗急于平定叛乱以及消除回纥对唐朝的潜在威胁。这对于我们正确认识平定安史之乱的战争,把握唐朝中后期对回纥关系的本质都有积极意义。
唐朝; 安史之乱;借兵;回纥
唐朝在平定安史之乱过程中,多次借用回纥兵。《旧唐书·回纥传》评论:“代宗诱回纥以平河朔,戡难中兴之功,大即大矣!然生灵之膏血已干,不能供其求取;朝廷之法令并弛,无以抑其凭陵。”明末清初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写道:“借援夷狄,导之以蹂中国,因使乘以窃据,其为失策无疑也。”当今学者则多盛赞回纥助唐之功,诸如刘福全《安史之乱中回纥助唐的根源》认为,“安史之乱中,回鹘汗国倾其全部兵力,助唐平定了叛乱,为大唐立下再造之功”。阿布都外力·克热木《从碑铭文学看唐与回鹘的和谐关系》分析,“回鹘可汗时期的回鹘与唐朝在政治经济和文化诸方面保持了和谐与融洽关系”。李丽杰《回鹘助唐平安史之乱述论》、王有德《论唐与回纥的关系》、徐伯夫《唐朝与回纥汗国的关系》等文均持类似观点。相比而言,陈绍凡《回纥与唐朝关系述论》看待安史之乱时期的唐回关系则更为全面。本文借鉴学术界观点,审视相关文献,试图重新考察安史之乱时期唐回关系。
一、回纥助唐平叛概述
安史之乱爆发后,叛军一路势如破竹,很快控制河北地区。接着洛阳、潼关、长安相继失守,唐玄宗西逃四川,太子李亨(唐肃宗)即位于灵武,依靠朔方军抗击叛军。玄宗曾对太子李亨说:“西戎北狄,吾尝厚之,今国步艰难,必得其用,汝其勉!”[1](P240)当年九月,肃宗即遣敦煌王承寀出使回纥,回纥随后派兵协同唐军平叛。安史之乱期间,回纥共四次出兵助唐,其中三次直接与叛军交战。
(一)助唐击破同罗等部
至德元载(756年)九月,敦煌王承寀出使后,回纥“与朔方节度使郭子仪合讨同罗诸蕃,破之河上”[2](P6115)。此时出兵援唐的回纥可汗,两《唐书》及《资治通鉴》记载不同。《新唐书》记载:“裴罗死,子磨延啜立,号葛勒可汗……肃宗即位,使者来请助讨禄山”[2](P6115),而《旧唐书》、《资治通鉴》皆作怀仁可汗,即磨延啜之父骨力裴罗。据林幹《突厥与回纥史》[3](P379、P403~437)考证,及其所载王静如《突厥文回纥英武威远毗伽可汗碑译释》,毗伽可汗之父为阙毗伽可汗,死于猪年(天宝六载,747年),最初出兵助唐的当是毗伽可汗,也就是后来受唐朝册封的英武威远毗伽可汗(磨延啜)。《旧唐书》、《资治通鉴》有误,当从《新唐书》。
(二)收复两京之战
至德二载九月,广平王李俶(即后来的唐代宗)及郭子仪率诸军伐叛,准备收复两京。“回纥遣其太子叶护领其将帝德等兵马四千余众,助国讨逆”[1](P5198)。唐军开进长安城西之香积寺,迎击驻扎寺北的十万叛军,最初唐军失利,但经大将李嗣业力战,稳住阵脚。朔方左厢兵马使仆固怀恩率回纥兵四千趁机进攻东侧叛军精骑,叛军气势大挫。随后,唐军主力与回纥汇合,歼灭叛军六万多人,大获全胜。叛军趁夜色弃城逃窜,次日唐军收复长安。十月,唐军与回纥军队东进,新店一战,叛军十五万依山而阵,回纥从南山攻击叛军背后,叛军惊溃。唐军占领陕州,安庆绪放弃洛阳。收两京之战胜利结束。此后,肃宗为了厚结回纥,对回纥可汗进行册封,并将幼女宁国公主嫁往回纥和亲。
(三)相州之战
乾元元年至二年(758-759),唐军乘胜追击,力图一举击灭逆首安庆绪。回纥王子骨啜特勒、宰相帝德等率骑三千助讨叛军。乾元元年十月,唐军连战连捷,攻拔卫州,围困安庆绪于相州。史思明降而复叛,率军南下,但怵于官军势大,驻军观望。其时唐军六十余万,分归九大节度使统领,竟不置最高长官总摄军务,仅以宦官鱼朝恩为“观军容使”,致使指挥混乱,加之久困坚城,人困马乏,已成强弩之末。次年三月,蓄势已久的史思明终于出兵,与官军决战。史思明兵少而精,官军轻视敌人,不以为意。两军交锋,势均力敌,胜负难分之际,大风忽起,吹沙拔木,天地昼晦,咫尺不相辨。官军大惊,溃不成军。回纥也败回京师。这一战的失利也使得平叛战争被迫继续下去。
(四)平定安史残部
宝应元年(762年),回纥受史朝义煽诱,率军南下,欲大肆寇略。此时英武可汗已死,其子登里可汗在位。唐朝连派使者进行争取,最终改变了回纥的立场,重新确立了助唐灭史的方针,在就进军路线、雍王会见礼仪等问题反复争论之后,回纥兵终于投入战斗。十月初,两军在横水交战,唐军主力由仆固怀恩率领在西原列阵迎敌,另选精骑与回纥绕至敌后,两面夹击,大破叛军。史朝义倾巢而出,决死一站,官军屡冲敌阵而不能破。关键时刻镇西节度使马璘单骑奋击,杀出缺口,官军趁机而入,叛军大败。唐军追敌于石榴园、老君庙,史朝义仓皇逃遁,官军再克洛阳。仆固怀恩、仆固瑒父子长驱直入,战郑州,拔滑州,败敌于昌乐,大捷于下博,追亡逐北,席卷而进。次年春正月,史朝义自莫州出逃,穷蹙自尽,河北悉平,历时八年的安史之乱最终落下帷幕。
二、回纥在平叛中的作用
唐人认为回纥于国家有救难之勋,屡称“北虏有勋劳于王室”[1](P5211)。回纥军队的强劲战力也被时人所称。叛将阿史那承庆曾说:“唐若独与汉兵来,宜悉众与战,若与回纥俱来,其锋不可当,宜退守河阳以避之”[4](P7134)。杜甫《北征》中称回纥:“所用皆鹰腾,破敌过箭疾”[5](P515)。那么,在平叛中回纥究竟起了到多大作用?是否真的是不可替代的关键角色?现从参战人数、战斗序列、实际战况等方面来分析。
其一,从参战人数来看。据《通鉴》记载,破同罗之战前,回纥可汗“遣其臣葛逻支将兵入援,先以二千骑奄至范阳城下,子奇闻之,遽引兵归”[4](P7006~7007)。收两京之战,“可汗遣其子叶护及将军帝德等将精兵四千馀人来至凤翔……元帅广平王俶将朔方等军及回纥、西域之众十五万,号二十万,发凤翔”[4](P7032~7033)。相州之战,“回纥遣其臣骨啜特勒及帝德将骁骑三千助讨安庆绪,上命朔方左武锋使仆固怀恩领之”[4](P7060),“官军步骑六十万陈于安阳河北”[4](P7069)。平史朝义之战,药子昂迎劳回纥时,“密识其兵裁四千”[2](P6118)。唐军人数,据《通鉴》、新旧《唐书》记载,每次投入兵力总数动辄数万、数十万,回纥历次出兵未曾超过五千人,可见平叛主力无疑是唐军而非回纥。
其二,从战斗序列而言。在唐军战斗序列中,回纥军多隶属于仆固怀恩、仆固瑒父子。收复两京之战,仆固怀恩任“朔方左厢兵马使”[4](P7033);相州之战,为“朔方左武锋使”[4](P7060);平史朝义之战,仆固瑒为“右厢兵马使”[4](P7135),统领回纥兵马作战。而统领全军的至少是节度使一级的武官,往往带有“元帅”的头衔。兵马使、武锋使只是副将。至于唐朝给予回纥的极大礼遇,则事关两国关系和唐朝对外政策,与军事部署无关。从实际战例来看,回纥骑兵骁勇精锐,承担的作战任务往往是“出贼阵后”、“袭其背”[4](P7034、7040),可见回纥善于快速奔袭、突击。唐军便由熟悉回纥情况的仆固父子单独统辖,承担突袭或者侧面进攻,类似突击队的角色,并非主力部队。
其三,从实际效果来看。在破同罗、收两京、平定史朝义残部作战中,回纥都有出色的表现。但不能就此认为回纥是主导战局的决定力量。河曲之战,仆固怀恩大义灭亲,斩杀其次子;香积寺之战,李嗣业挺身而出;昭觉寺之战,马璘单骑奋击,这些都是扭转局势的重大因素。而朔方节度使郭子仪、仆固怀恩等人善于用兵,灵活调度,也使得回纥得以发挥快速突击的长处。况且,相州之战回纥也参与其中,结果依然是以大败告终,回纥骨啜特勒、帝德等十五人也自相州奔回长安。
就以上分析来看,回纥军队有着较强的战斗力,但是并不能决定战争胜负。唐借兵于回纥的原因并不是军力不足,非回纥相助则不能平叛。
三、借兵回纥之原因
安史之乱发生后,吐蕃、回纥甚至西域等地区纷纷遣使请求帮助朝廷讨伐安禄山,但回纥兵入唐参战次数最多,战功最高,影响最大,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第一,唐有征调周边民族军队作战之先例。首先,唐前期国力强盛,为周边民族所拥戴,经常征调周边民族军队。如“永徽二年,贺鲁破北庭,诏将军梁建方、契苾何力领兵二万,取回纥五万骑,大破贺鲁,收复北庭。显庆元年,贺鲁又犯边。诏程知节、苏定方、任雅相、萧嗣业领兵并回纥大破贺鲁于阴山,再破于金牙山,尽收所据之地,西遂至耶罗川……永徽六年,回鹘遣兵随萧嗣业讨高丽。”[1](P5197)“武后时,突厥默啜方强,取铁勒故地,故回纥与契苾、思结、浑三部度碛,徙甘、凉间,然唐常取其壮骑佐赤水军云。”[2](P6114)而在安史之乱中,除了回纥,其他周边部族也被征调参军,“上虽用朔方之众,欲借兵于外夷以张军势,以豳王守礼之子承寀为敦煌王,与仆固怀恩使于回纥以请兵。又发拔汗那兵,且使转谕城郭诸国,许以厚赏,使从安西兵入援”[4](P6998),“广平郡王俶为天下兵马元帅,郭子仪副之,以朔方、安西、回纥、南蛮、大食兵讨安庆绪”[2](P156)。可见唐朝征调回纥,不过是循其常规。再者,安史之乱中,唐军连年激战,军马损失巨大。仅相州一战,“战马万匹,惟存三千,甲仗十万,遗弃殆尽”[4](P7069),而吐蕃尽陷河陇,陇右牧马又沦于敌手,军中骑兵必然不足。回纥自唐初即与唐室关系密切,加之回纥骑兵骁勇善战,自然成为唐朝重点征兵的对象。
第二,唐肃宗急于收复两京,以稳固其统治。肃宗虽为玄宗太子,却是在马嵬坡之变的乱局中上台的。来到灵武之后,先在群臣拥戴下继承皇位,然后才得到玄宗的认可,这并不是常规的合法程序。且当时唐室诸王分节制之命,对肃宗巩固皇位是巨大的障碍。唯有收复两京,立不世之功,才能得天下认可以巩固皇位。王夫之在《读通鉴论》评论,肃宗“急用回纥疾收长安者,以居功固位不能稍待也”,“盖其时上皇在蜀,人心犹戴故君,诸王分节制之命,玄宗且无固志,永王璘已有琅邪东渡之雄心矣。肃宗若无疾复西京之大勋,孤处西隅,与天下县隔,海岱、江淮、荆楚、三巴分峙而起,高材捷足,先收平贼之功,区区适长之名,未足以弹压天下也。故唯恐功不速收,而日暮倒行,屈媚回纥,纵其蹂践,但使奏效祟朝,奚遑他恤哉?決遣燉煌王以为质而受辱于虏帐,其情然也。”[6](P794)可见,肃宗征回纥兵入援,是为了加快平叛战争的进程,立功树威,巩固皇位,甚至不惜损害百姓利益。肃宗为了速得京师,就曾与回纥定约,攻克两京之日,土地、士庶归唐,金帛、子女皆归回纥。回纥兵虽然不是平叛所必须,但毕竟骁勇善战,对快速击败叛军无疑是有利的。
第三,借兵回纥,亦可化解回纥对唐朝的巨大压力。回纥在天宝年间消灭突厥,开拓疆土,东到室韦,西至金山,南控大漠,尽得古匈奴之地。裴罗可汗死后,磨延啜继位,号称葛勒可汗,剽悍善用兵,每年遣使者入朝。唐前期国力强盛,回纥不敢大肆南寇,与唐朝和平交往。安史之乱时期,唐朝抽调军队平叛,造成边防空虚,便于周边民族进攻。战乱之初,回纥对唐朝内情尚不明了,顾未敢轻动。随着几次入唐作战,对唐朝的衰弱了然于胸,终于在史朝义蛊惑下南寇。史载“比使者至,回纥已为朝义所訹,曰:‘唐荐有丧,国无主,且乱,请回纥入收府库,其富不赀。’可汗即引兵南,宝应元年八月也……是时,回纥已逾三城,见州县榛莱,烽障无守,有轻唐色。乃遣使北收单于府兵、仓库,数以语凌靳清潭”[2](P6117~6118)。可以说,在唐朝与叛军鹬蚌相争的情况下,回纥势难雌伏,南下渔利已不可避免。从药子昂与回纥可汗对进军路线的讨论中,所谓“州县虚乏,难为供拟,恐可汗失望”[1](P5203),可以看出,如果不获得可观的经济利益,回纥是不会合作的。
那么,面对回纥的咄咄逼人,唐朝将如何应对呢?此时唐军主力正与安史叛军对峙在陕州、河阳一带,而西北边防精锐早已东归戡乱,障塞空虚,实已无力与回纥争衡。再者,由于唐朝撤西北之军以敌河朔,吐蕃趁虚而入,尽占河西陇右之地,离长安已是咫尺之遥。唐朝陷入了东据叛军,西防吐蕃的不利态势。所幸吐蕃与叛军间隔遥远,无法呼应。但回纥则不同,它同时与唐、吐蕃、叛军三者接壤,其态度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全局。回纥助唐,则叛军不足平,回纥助叛,则战事绵延,难以预料。值此多事之秋,内忧外患,唐朝自然不会自树强敌。最后,回纥为利而来,只要能满足其利益需求,完全可以化敌为友,转害为利。唐朝既能借兵助剿,又能一定程度上控制回纥的行为,用政府的赏赐代替回纥自发的掠夺。虽然回纥的暴行不可能因为唐朝的厚赏而完全终止,但起码在政治上争取了回纥,没有让这样一个强大的游牧国家走向唐朝的对立面。从这个角度来说,两害相权取其轻,唐朝的决策是正确也是无奈的。唐朝后期,延续了安史之乱中内忧外患的局面,故而厚结回纥的政策也被迫保留。只要将唐对回纥的政策放到与吐蕃、国内叛镇博弈的全局中去考量,就不难得出必须联合回纥的结论,这与安史之乱中唐朝被迫借兵实为殊途同归,都是不得已而为之。这就是唐朝被动接受回纥“借兵”的因素。
余 论
唐朝前期开疆拓土,声威远播,周边民族尊唐朝皇帝为“天可汗”,回纥臣服于唐,唐朝占据主动地位。后期,唐朝迫于内外形势,结好回纥,回纥傲慢骄肆,唐朝渐渐处于被动地位。唐朝与回纥关系的全过程,就是一个由主动到被动的变化,而这个大变化,正是通过安史之乱中的小变化来实现的。最初唐肃宗希望借回纥劲旅快速结束战争,从而确立自己合法地位,但回纥也因此了解唐朝虚实,遂想趁唐室之危而南下侵扰,唐朝不得不继续借兵而予以约束。这一转变过程正是唐回关系大变化的枢纽和缩影。如果把唐朝借兵态度的转变,放到唐与回纥整体关系中审视,就可以获得更加清晰深刻的理解。对回纥而言,通过助兵平叛也能够获得经济利益。当然回纥兵不是唐朝平叛的主力,但唐朝借回纥兵来平定叛乱,对于稳定军心,推进平叛进程,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而回纥兵烧杀掳掠也给华北地区百姓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1]刘昫.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2]欧阳修,宋祁.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3]林幹.突厥与回纥史[M].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7.
[4]司马光.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1956.
[5]曹寅.全唐诗(第四函)[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6]王夫之.读通鉴论[M].北京:中华书局,1975.
[7]杜甫.杜工部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8]徐倬.全唐诗录[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9]刘福全. 安史之乱中回纥助唐的根源[J].中国科教创新导刊,2012,(3).
[10]阿布都外力·克热木. 从碑铭文学看唐代与回鹘的和谐关系[J].西北民族研究,2007,(4).
[11]李丽杰. 回鹘助唐平安史之乱述论[J].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6).
[12]王有德. 论唐与回纥的关系[J].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1,(4).
[13]徐伯夫. 唐朝与回纥汗国的关系[J].喀什师范学院学报,1991,(4).
[14]陈绍凡. 回纥与唐朝关系述论[J].新疆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2).
〔责任编辑 韩 芳〕
Discussion about Tang Dynasty Borrowing Army from Uighurrs To Put down An-shi Rebellion
DONG Wen-yang
(History Department, Anhui University; Hefei 230000)
In putting down An-shi Rebellion, the government of Tang borrowed armies from Uighurrs for times. The previous works praise the big effect of Uighurrs, and think the reason of Tang government borrowing the army from Uighurrs is the good relation between Tang Dynasty and Uighurrs. But through the battles of Uighurrs helping Tang Dynasty as the historical materials we analyze the effect of Uighurrs, and point out the fact that Uighurrs’s effect is not very big. Tang government borrowing armies from Uighurrs was a routine of Tang Dynasty; meanwhile it was Suzong’s strategy in eliminating the threats from Uighurrs.
Tang Dynasty; An-shi Rebellion; borrow army; Uighurrs
2015-07-13
董文阳(1990-),男,安徽滁州人,安徽大学历史系硕士生,主要从事唐代史研究。
K242.205
A
1004-1869(2015)05-0067-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