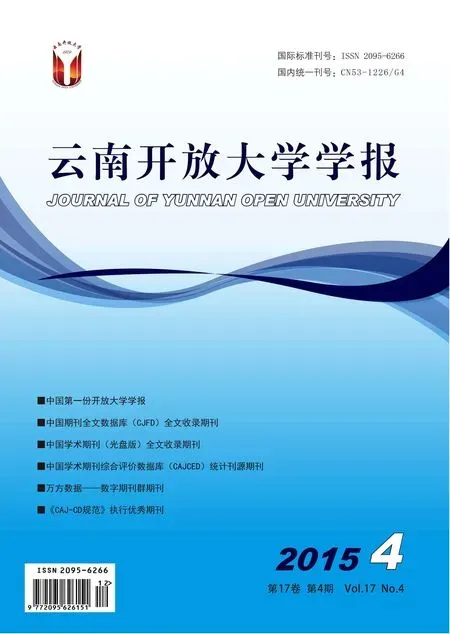中缅边境地区跨境婚姻发生动因追溯
2015-02-09李红军
梅 英,李红军
(滇西科技师范学院 科技处,云南 临沧677000)
中缅边境地区跨境婚姻存在历史悠久,但近年来数量飙升迅速且有向内地蔓延态势。以边境城市德宏、临沧为例,截至2012年6月,德宏州已备案登记入境通婚缅籍边民9412人;同期,临沧市备案登记与缅甸籍人通婚5076人。2014年间,笔者深入临沧市各村寨就此问题作进一步调研后发现,中缅边境地区跨境婚姻之所以呈此态势,其发生动因可以分为外部推力、内部需求及中介联动三个方面。笔者在下文中对该调研结果略作陈述,以供学界参考。
一、外部推力
中缅边境地区跨境婚姻并非近年才出现的新生事物,边境村寨中男女年龄达六七旬的跨境婚姻家庭屡见不鲜。但跨境婚姻数量大增却是近年来才呈现的特征。经笔者深入村寨与当事人访谈得知,中缅边境地区跨境婚姻历史存在与现代递增,与其地域条件、历史文化,以及当前社会发展背景等外部推力相关。
首先,地域条件。中缅两国领土毗邻、边境线长,在缅甸联邦67.6581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中缅边界线长达2185公里。这些边境线除部分设有国家级和省(区)级口岸部分须凭证件出入境外,其余漫长的边境线上还有着上千条日常无人监管的小径,边民来往十分方便。在德宏、临沧、保山等边境城市里,邻国居民看病、贸易、求学的身影随处可见,“出省少,出国多”成了两地边民真实的生活写照。近年来,随着国家“兴边富民”、“沿边开放”等政策实施,边境地区交通往来更加便利,边民交往机会大幅增多。所谓“日久生情”,中缅两国边民在日常事务频繁交往后,跨境婚姻的发生成为了一种必然。在笔者调查的20户跨境婚姻家庭案例中,约有10户家庭是由于男女外出到对方国家打工结识促成的。虽说此种务工流向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特点,在缅甸种植鸦片时期以男方流向缅甸为主,实施替代种植政策后则以流入中国为主,但总体而言跨境婚姻多以女方嫁入中国为主。事实上,历史以来中缅边境地区跨境婚姻一直延续且近年来数量大增,同样也与领土毗邻密切相关。虽然我国相关法律规定对非法入境、非法居留、非法结婚的外籍人员,一经发现必须及时遣送回其本国。但由于边界线长、村与村之间相距较近、民间小道较多,我国执法人员常常出现上午刚将非法入境人员遣送回国,晚上她们又会回到中国家庭中的情形。加之,这些妇女一旦强制遣送回国后,其在中国的子女、丈夫常常会造成更为严重的系列社会问题,边境村寨执法人员对这些人员大多采取睁只眼闭只眼态度。在某种程度上讲,诸多中缅边境村寨里的跨境婚姻发生约束机制极少且效用偏低,在群起效尤的情况下数量得以大幅增长。
其次,历史文化。中缅两国山水相连、两国人民情谊深厚,自古有着“胞波”(缅语“兄弟”之意)之称。众多边境村寨中,居住着很多如傣族、佤族、德昂族、布朗族等历史文化同源的跨境民族。这些民族有着相同的习俗、语言和生活习惯,自古以来交往密切并一直存有相互通婚的传统习俗。他们在长期的生产劳作、生活互动中,形成了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共生共荣关系。这些跨境而居的边民经过为时极长的交往和接触,所持的国家意识和边界意识已经较为淡薄,同族人和亲属感情甚而已超过了其他观念和感情。在边境村寨甚至县城中,大部分家庭都有跨国亲戚,且每逢节日或有重要事情发生之时都会集聚一堂。在亲情联系纽带的维系下,在历史文化的熏陶下,这些边境村寨家庭在有条件之时仍会选择族内婚。对他们而言,这是避免不同民族婚后文化冲突带来不适的最佳选择,这是祖祖辈辈延续的婚姻模式。在此背景下,中缅边境地区的跨境婚姻存续历史悠久且得以延续着。
最后,社会态势。在多种因素共同作用下,我国人口比例构成如今呈现男多女少态势。与此密切相关,男女青年后续的婚姻结合出现了挤压问题。也就是说,在实际婚配过程中,由于女性人口向社会强势群体聚居地发生婚姻迁移,城镇男子以及经济相对发达地区的婚姻挤压问题通过异地婚迁得到了缓解,而最终婚配难的问题挤压在了贫困地区男性婚龄人口身上。中缅边境地区地处我国西南,在地域、历史因素综合作用下,经济发展水平低下,多属重点扶贫地区,从某种程度上讲成了承载压力的最底层,婚姻挤压问题由此极为突出。如中缅边境城市临沧市XX县,2012年间30岁至45岁的未婚大龄单身男青年竟达3662人。这些人大多分布于边境村寨中,大多为家境贫穷者、年龄偏大者、肢体残疾者、丧偶离异者等弱势群体。在正常情况下,这些群体选择婚姻对象或作为被选择婚姻对象时均毫无优势,婚姻困难问题已较为突出;加之近年来外出务工、远嫁他乡女子增多,村寨中青年女子为数极少甚至基本上没有,这些群体在当地甚至邻近村寨解决婚姻问题已没有任何可能性。所谓“穷则思变”,在媒人、邻居、亲戚的介绍引领下,通过各种途径向经济水平更低、女性人口数量较多的缅甸寻求婚姻对象成了自然之举。
综上所述可以发现,中缅边境地区跨境婚姻之所以历史悠久并成功延续,与其拥有地利、人和之背景条件密切相关。在当前社会发展若干政策造成的时势助推下,其存在的必要性进一步得以凸显,数量由此大增。总的来讲,上述三个方面因素的客观存在,为中缅跨境婚姻发生奠定了外部基础和条件。
二、内在需求
中缅跨境婚姻在特定的时间、空间条件下,确实已存有其发生的外部推力;但婚姻作为男女双方自愿结合的行为,在没有主体内在需求推动的情况下一般不可能发生,更不可能呈现数量大幅增长之势。中缅边境地区跨境婚姻发生、延续并大幅蔓延,确实与婚姻主体内在需求的驱动密切相关。具体而言,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低婚姻成本。所谓婚姻成本,简单地说就是婚姻缔结过程完成所需投入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其中以财力为要。调查发现,中缅边境地区跨境婚姻之所以呈现前述态势,与男方的低婚姻成本内在需求驱动相关。换言之,婚姻成本低廉是跨境婚姻发生的一个重要因素。中缅边境地区大多是山区,自然条件恶劣且经济条件较之内地性相差较大。这里的女青年为了改变生存环境,大多要么嫁到外地要么外出打工,外面的女青年更是没有人愿意嫁进来。因此,当地男青年的婚姻成本极高,除订婚彩礼20000-30000元外,还需支付婚礼、订亲、回门以及日常看望对方父母等所支付的费用约10000元。而娶缅甸妇女,除支付约10000-20000元的彩礼钱之外基本不用其余资金。由于跨境婚姻没有进行婚姻登记,婚姻中的缅甸女性大多家庭贫困、大多迫于生活压力选择嫁入中国,因此男女双方大多遵循“一切从简”原则,结婚礼节不依传统而行,举办婚礼也相对低调。婚姻成本由此大大降低,这对于贫困地区的男性无疑是较好的选择。
其次,高物质享受。如前所述,中缅边境地区跨境婚姻以女方迁入为主。由此,中缅跨境婚姻得发生应与女方需求推动相关。若用探讨人口迁移原因的“推—拉理论”对此问题进行分析,发生婚姻迁移的原因不外乎居住地形成推动人口迁移的力量、迁入地形成吸引人口迁移的引力两个方面。这两种力量单方面作用会导致婚姻迁移,形成合力则将加大婚姻流动的力度。事实上,这个理论确实很好地解释了中缅边境地区跨境婚姻中女性迁移现象的原因。调查发现,嫁入中缅边境村寨的缅甸妇女,其家境都较为贫困。她们大多居住在偏僻、交通不便、经济落后地区,这些地方甚至没有通电、通水、通路。由于中国较早进行改革开放,经济发展较快、社会安定、生活条件相对优越,这对缅甸妇女产生了一定吸引力。这在一定程度上将,作为人口流出地的缅甸已经具有了人口迁移的推力因素。而当笔者问及“您为什么要嫁到中国来”问题时,多数妇女都会回答“中国比缅甸好在”、“中国不用交公粮、不用当兵”、“在中国没有在缅甸那么辛苦”、“在中国比较容易赚到钱”。在她们眼里,中国是一个经济发达、生活环境安定、经济水平比缅甸高很多的国家。为了改善生活水平,过上自己心中舒适的好日子,她们大多数人都希望能嫁到中国来。由此看来,其实大部分嫁入中国的缅甸妇女都是在把两国生活条件做了比较后作出的选择,中国作为人口流入地,生活条件好、社会稳定、妇女地位高于她们而言就是拉力因素。为谋求更好的生活条件、满足更多的物质需求,这些缅甸妇女把婚姻当作了改变自身经济状况和社会地位的一条途径,远嫁他乡以求过上富裕的生活。
最后,适龄婚配。满足个体生理、生活需求是人类婚姻个体动机构成之一。具体而言,包括满足性欲的生物性要求和繁衍后代的生活需求两个方面。在现代社会制度规约下,性爱及生育的完成,必须以家庭构建为前提。在性欲满足需求表露被传统文化约束的情况下,此类个体动机通过构建家庭需求得以展示。在中缅边境少数民族地区,“男人无妻则无家”、“女人无夫则无主”的说法甚为流行。当地绝大多数中国男性之所以娶外国老婆,实为在适龄婚配传统文化制约下的一种无奈、被迫行为。当问及“您为什么娶外国妇女当老婆”时,他们大多数的回答基本上是“家里太穷了,在中国娶不到老婆”、“年纪大了没人嫁”、“娶缅甸老婆便宜,中国老婆太贵了”、“自身条件不好,讨不到中国老婆”、“如果有条件,还是希望娶中国姑娘”等等。他们在回答这个问题时,表现出一种无奈的表情、语气以及内心的自卑。由此可见,到了生育年龄,他们有迫切成婚的需求却无人可娶。在焦虑心态的支配下,他们中的部分人将事关后半生的婚姻幸福赌注押在了一个成长环境相异、没有感情基础的陌生女子身上。中缅边境地区跨境婚姻中的男女双方很多没有任何婚前感情基础,某种程度上,传统中国旧式婚姻将生育子女传宗接代作为要务,仅为了传宗接代而不考虑夫妻俩人感情问题的特点极为突出。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若把驱动婚姻主体发生行为的内在动机归结为感情、生理、生活几种类型,中缅边境地区跨境婚姻发生的内在需求推力多以生育、生理需求为主。
三、中介联动
在上述外部推力及内在需求推动下,中缅边境地区跨境婚姻仅具备了发生的可能性。其成为现实并呈现数量递增态势,必定还有其促成因素存在。中缅边境地区跨国婚姻发生确实还与当地“媒介”的中间联动推力密切相关。具体而言,此类“媒介”包括人媒、物媒两种。
其一,人媒。调查发现,中缅边境村寨中经“媒人”介绍形成的跨境婚姻为数不少。这些家庭中,作为婚姻主体中的外国妇女和中国男子事先并不认识,起初也无跨境婚姻的发生需求,但通过“媒人”介绍后他们迈向了婚姻。这些“媒人”一般包括以下几种:一是已嫁入男方所在地的缅甸妇女,二是己娶了缅甸妇女的中国男性,三是本地在缅甸有关系且专门介绍女子的媒婆,四是经常来往于中缅做生意的本地人。其中,多以第一种熟人即以已嫁到中国的外籍妇女居多。这些缅甸妇女多借用回娘家或者与亲属联络的机会,介绍本村未婚妇女嫁入本村寨。一般情况下,嫁入中国的缅甸妇女非常乐意介绍其他妇女嫁到中国来。她们这样做的目的,一方面是为了获取介绍成功后三至四千块的介绍费,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能在本地建立自己的关系网。而对中国一无所知的缅甸女子也由于介绍人为值得信任的熟悉之人,最终来到了中国国并进入了介绍人的关系网中。从目前情况看,中缅边境村寨中的缅甸妇女已成了推动跨境婚姻发生的一个巨大推力。可以肯定的是,此类“媒人”介绍型的婚姻大多家庭和睦,夫妻关系稳定且已生育子女。但值得注意的是,随着介绍次数增多,部分“媒人”已将介绍缅甸女子嫁入中国作为一种获益手段,甚而走向了拐卖人口的非法道路。与此同时,也有部分缅甸妇女迎合中国男子娶妻的迫切需求,与“媒人”配合成为了“职业新娘”。笔者实地调查的村寨中,拐卖诱骗型婚姻目前为数不算多,但其余村寨中此类案例却屡有耳闻。
其二,物媒。中缅边境地区居住着很多历史文化相同的跨境民族,每逢宗教节日或重大事件发生之时,他们便会跨越国界积聚一堂。如,信仰小乘佛教的民众逢重修缅寺做“大供”之时,必定邀请包括缅甸在内相同信仰的村寨前来朝贺;逢泼水节之时,各村寨人必定积聚于历史最悠久的缅寺中,必定“跳摆”庆祝。由此,白塔、缅寺等宗教场所随之成了跨国婚姻发生的“物媒”。在此类特定场合下认识的青年男女由于文化认同而随之进入了后续的“串姑娘”民俗,最终迈入了婚姻的殿堂。中缅边境地区村寨中,由于傣族泼水节、德昂族堆沙节、佤族新米节等民族节日促成的跨国婚姻确实为数不少。这些村寨中至今未婚的男女青年,将寻偶机遇寄托于民俗节日者仍大有人在。由此,笔者以为这些宗教场所实际上已成了促成中缅边境地区跨国婚姻发生的“物媒”。
俗语说,“一方女嫁一方男”。我国中缅边境村寨由于宗教信仰、民族文化等原因,其婚姻流动往往有着比较确定的指向。一定时期内,某乡女子多嫁往某几个乡,某乡男子多娶于某几个乡。即,存有人们所谓“婚姻圈”事实。如今,发生在这些村寨中的跨国婚姻也具备如此特点,迎娶的缅甸女子大多来自相同地域。笔者认为,该情形的出现除与其亲属圈的存在有一定关系外,事实上是与“媒人”托媒议亲择偶方式存有联系的。此外,这些村寨中跨境民族现存的宗教信仰场所至今保留且得到强化,也与此不无相关。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婚姻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它的存在能够保持社会或群体稳定、能够促进种族繁衍、可以增进不同群体之间的联合。于此,社会、个体、群体必将不遗余力促成婚姻以使其发挥上述功能。本文所论述的中缅跨境婚姻发生的三类动因,就其实质而言其实便是社会、个体、群体发力之具体表现。
[1]费孝通.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2]麻国庆.家与中国社会结构之费孝通代序[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9.
[3]张金鹏,保跃平.制度视角下的边民跨境婚姻研究[J].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