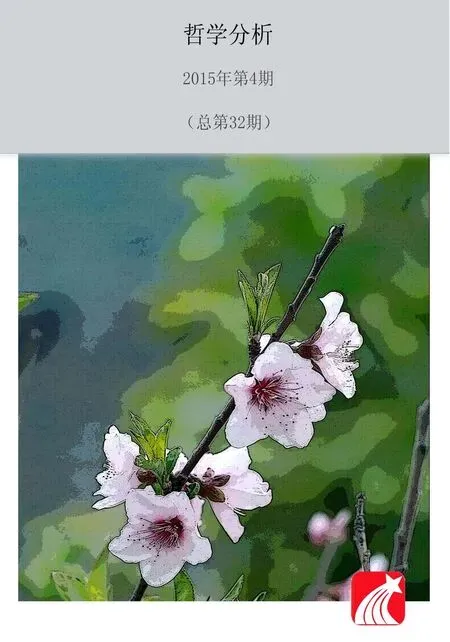从陈康与刘述先的争论看事物的个体性与同一性
2015-02-07黄启祥
黄启祥
从陈康与刘述先的争论看事物的个体性与同一性
黄启祥
陈康与刘述先半个世纪之前关于性质如何结合成个体事物的争论,对于我们今天探讨事物的个体性与同一性仍有启发意义,但是陈康的论述也存在着若干问题。他把“许多性质如何结合成一个个体”的问题等同于“一个个体如何是一个个体”的问题和个体的同一性问题,并把对象的同一性混同于自我的同一性,这使他未能提出解决事物的个体性与同一性的方案。纵观西方哲学史,无论是亚里士多德哲学、英国经验主义,还是康德式的理性主义,都在这个问题上陷入难以摆脱的困境。但是詹姆斯的思想流学说为这个问题的解决提示了一条可能的路径。
性质;个体性;同一性;自我同一性;对象同一性
一、陈康与刘述先的争论
陈康在《性质团结问题与本质概念》①汪子嵩、陈太庆编:《陈康:论希腊哲学》,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504-517页。一文中探讨了性质如何结合成个体事物的问题。他说:“现象方面所给与的只是许多性质,……这些性质如何团结成为一个个体?”②同上书,第505页。在陈康看来,性质结合成个体事物,这是事实,不是问题,问题在于这些性质是如何结合成个体的。比如,一个人赵大,他有许多性质,像面白、无须、身高、体瘦、会说话、能写字等,现象方面所给与我们的只是许多这样的性质,我们却认为他是一个人,这些性质是如何结合成一个人的?
陈康认为西方哲学史上对于这个问题的解决有两种基本方式,即存在论的方式和认识论的方式。亚里士多德用存在论的方式解决这个问题,用物质实体来说明事物的性质结合问题,这样一个实体概念支配了西方哲学思想两千多年,最终受到洛克、贝克莱和休谟等人的批评,并被休谟称为虚构。休谟将虚构的实体概念勾销了,但是性质结合问题非但没有解决,反而更急迫了。康德从认识论方面来解决性质结合问题,认为事物的各种性质统一于理性范畴,但是赋予范畴统一性的自我的统一性却无从解决,因此,“超验哲学所成就的实际上只不过是将我们的问题推远了一步。推向何处去?并不推向它处?乃推到它自己的基本原理身上去了!”①汪子嵩、陈太庆编:《陈康:论希腊哲学》,第506页。
陈康通过对哲学史的考察,断言“性质如何结合成为一个个体”的问题不能从认识论的方向去解决,唯一可行的道路只能在存在论的领域里,因为他认为这是存在论的问题。但是究竟如何在存在论里解决这个问题,他并没有给出答案。
陈康设定了两个前提:一方面,现象给与我们的是许多个别性质;另一方面,这些性质又结合成了个体事物。陈康的学生刘述先也承认这两点,但是他认为无论这些性质还是它们所结合成的个体都是相对的。他说如果我们设想有一个人天生一副显微镜一样的眼睛,我们所说的性质,如面白、无须等性质对他就没有什么意义了,因为他所认识的个体是以细胞为单位的,他只晓得甲细胞、乙细胞和丙细胞等。②刘述先的这个论述源于洛克。当时他正参加陈康开设的“名著选读”课,教材就是洛克的《人类理智论》。洛克说:“我们如果有足够敏锐的感官,足以把物体底渺小分子分辨出来,……则我相信,它们所产生的观念一定同现在完全不一样,……显微镜分明给我们发现出这一点来;因为在感官底敏锐力增加以后,则现在给肉眼所产生的某种颜色会被发现是完全另一种东西;……就如沙或捣碎的玻璃,在肉眼看来,虽是白而不透明的,可是在显微镜下,它就是透明的。”(洛克:《人类理智论》,关文运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272页)但是刘述先的观点与洛克的并不完全相同,洛克通过显微镜的例子来说明第二性质不是事物本身固有的性质,它们依赖于我们肉眼看不到的第一性质。根据洛克,无论我们的感官差别多么大,都只能将第二性质还原为第一性质,而第一性质是不会因感官的变化而消失的。而刘述先认为事物的所有性质都随着感官的变化而变化。既然在不同的动物,甚至在不同的人看来,性质是不同的,刘述先说:“我们所认为当然的面白无须的性质团结,换一个角度看,竟完全没有意义。……如黄色蓝色等颜色之于色盲,是完全没有意义的。”(刘述先:《“性质团结问题与本质概念”的疑团》,载汪子嵩、陈太庆编:《陈康:论希腊哲学》,第519页)
如果在不同动物甚至在不同人看来,一个事物的性质是不同的,那么由这些性质所组成的个体必定也是不同的。天生一副显微镜眼睛的人,很可能根本看不到我们所看到的赵大。即使你告诉他赵大是什么形象,他可能也听不懂。刘述先说,我们都认识赵大,因为我们同是三维空间动物,如果一个二维空间动物遇到赵大,定然极力否定我们所说的赵大存在。因此,赵大只是性质结合的一个模式,但不是唯一的模式。赵大可以同时从不同的视角被视为人、细胞、巨兽等,而不论它被视为人、巨兽还是细胞,它们具有同样的真实性。他进一步认为,如果承认性质结合的模式是相对的,那么实体——支撑个体的托子——必然是想象中的“存在”。由此,我们的实体概念犯了一个绝大的错误。因为我们生活在三维空间,所以我们的个体也是三维空间的托子结合而成。如果二维空间动物也能设想一个性质结合的托子,这托子必然也是二维空间的。“我们与其说‘实体观’,不如说作‘实体感’,只因为我们有一个要求实体的倾向而已!这仍然是由主观的我推衍出的结果。”①刘述先:《“性质团结问题与本质概念”的疑团》,第520页。
简言之,刘述先认为事物的性质是相对的,性质结合成的个体是相对的,结合性质的实体概念也是相对的,它们都是相对于认识者而言的。“所谓存在的组织形态并不如想象中那么客观。我们如果撇开一切主观的角度来谈存在,这存在不过是模糊不清的概念!”②同上。但是他认为独立于观察者的个体事物还是存在的,只是观察者所感觉到的性质是主客两方面的原因造成的:“实在的构造不必变,同一客观世界,有的动物看出十彩,有的动物只看见单纯的灰色。”③同上。既然同一个实在相对于不同的认识者呈现为不同的性质,进而结合成不同的个体,那么,性质如何结合成个体的问题就不是一个纯粹的存在论问题,也是一个认识论问题,至少主客观占有同等重要的地位。这个问题如果无法在认识领域得到解决,它也不可能在存在领域得到解决。“由此问题转入了一个新方向:存在和认识的联袂解决,才能达到这问题的解决。”④同上。因此他提出以下三个问题:
(一)个体是否实在?以何方式存在?
(二)这许多相对模式是否不冲突?为什么?
(三)性质如何结合为个体?
针对刘述先的批评,陈康认为他原来所提出的问题仍然存在,并未改变。刘述先的第三个问题等于承认了这点,只不过在刘述先看来,前两个问题先于第三个问题。陈康认为如果把性质结合问题以一般的形式表示出来,实际上是将刘述先提出的问题包含在内的。这个问题的一般形式乃是:a、b、c等性质如何结合成一个个体X?赵大虽然不再是面白、无须……,但仍有他的性质:甲、乙、丙……,问题仍然是:甲、乙、丙……如何结合成为一个个体——现在不再被称为赵大,让我们称之为Y?或者在另一种可能条件下,子、丑、寅等性质如何结合成为一个个体Z?陈康认为这些皆和原问题是同一问题。
陈康将刘述先的问题“这许多相对模式是否冲突”划分为两种情况,即同一种条件下(都是视觉健全的人)是否冲突和不同种条件下(有的是视觉健全的人,有的是视觉不健全的人)是否冲突。他认为不同种条件下的模式不存在冲突,冲突只有在同一种条件下才有可能。譬如,你我皆是视觉健全之人,如果我们在同样的光照下一人看见赵大面白,一人见其面黄,这样我们所见赵大的面色方才冲突。但是如果视觉健全的人看见赵大面白,而视觉不健全的人看见赵大面黄,那么现象给与的性质是否都是赵大的?这些不同模式所结合成的是否同一个个体?它们之间是什么关系?
陈康意识到了这些问题,但是他认为它们和原问题并非迥然不同,而是问题范围的扩大。原来我们问:a、b、c……如何结合成一个个体X?现在问:a、b、c……一组性质,甲、乙、丙……另一组性质,子、丑、寅……第三组性质,以及第四组、第五组……第n组性质如何结合成为一个个体U?他重新解释了个体的含义,将不同种条件下的性质结合体看成同一个个体的不同方面。由此,“这个个体以何方式存在”的问题就变成了:“U以何方式存在?U乃是各组性质的总团结,因此U亦即存在于X、Y、Z……各方面中,X、Y、Z……乃分别的是a、b、c……,甲、乙、丙……,子、丑、寅……其他等组性质的团结。于是U以何方式存在一问题,乃是各组性质如何团结成为U的这一问题。”①汪子嵩、陈太庆编:《陈康:论希腊哲学》,第523页。也就是说,在陈康看来这个U的存在是不容否认的。这似乎回答了刘述先所提出的第一个问题的第一部分即个体是否实在。个体以何方式存在?以各种不同的性质结合体存在,这回答了刘述先的第一个问题的第二部分。由此也回答了刘述先的第二个问题,即这些不同组性质的结合体并不冲突,因为它们是同一个个体的不同呈现形态。
二、对上述两种观点的分析
陈康最初的问题是许多性质如何结合成一个个体事物?刘述先把问题扩展为不同认识主体所看到的性质和个体是否属于同一个个体,也就是把陈康所问的个别事物的性质如何结合为整体的问题转变为性质和个体事物在不同主体之间的同一性问题。事物的整体性问题可以延伸出事物在不同主体之间的同一性问题,但是,前者并不必然以后者的解决为前提。无论不同认识主体看到的某物的性质多么不同,他们各自都具有该物整体的观念。即使他们分别把该物视为不同的东西,在他们各自那里都有一个性质如何结合成个体的问题。而在任何一个认识主体看来,他所感觉到的性质最初都会被看成实在的,由这些性质所组成的个体事物也会被看成实在的。如果他在不同时间在同一事物上看到了不同性质或个体形象,他可能会认为该对象发生了变化,而不会直接怀疑对象的实在性。所以,刘述先所提的三个问题的顺序应该颠倒过来。首先应该问“性质如何结合为个体?”然后问“这许多相对模式是否冲突?为什么?”最后才是“个体是否实在?以何方式存在?”因为如果没有第二个问题,就不会产生最后一个问题。
陈康实际上把刘述先的第二个问题归结为第三个问题,即把“不同性质如何结合成一个个体”的问题扩大为“不同组性质如何结合成一个个体”的问题,来回应第一个问题。这就难怪让人感到他并没有成功地回答个体是否实在的问题,反而使得这个问题变得更加复杂。他在这里实际上提出了一种新的个体观念,这种新的个体是由各组不同性质分别结合成的个体所构成的总个体。他把这两种个体的结合当成是同样的问题。但是,它们显然是两种不同的个体,属于两种不同的结合。
既然X、Y、Z……分别是不同种类的认识主体在不同种条件下对一个对象认识的结果,它们如何能够结合成一个U?谁来把它们结合成这个U?要么是这些认识主体中的某一个,要么是一个在他们之外的某个认识主体。由于不同种类的认识主体对于这个对象的认识要么是X,要么是Y,要么是Z,……,而绝不可能是U,所以,如果X、Y、Z……能够结合成一个U,结合它们的必定是上述各个认识主体之外的某个认识者。但是这个认识者对这个对象的认识必定是在另一种条件下的认识,因此认识结果必定是一组新的性质的组合,而不可能是上述各组性质的总组合,除非我们假设它具有各种认识主体的认识官能。当然,这种全能的认识者是不存在的,由此,各组性质如何能够结合成U的问题,根本就是一个不可能的问题。
即使我们承认个体U是由X、Y、Z……组成的,也要首先解决X、Y、Z等一个个个体是如何分别由各自的一组性质所结合而成的。而不同认识者关于同一个对象的不同认识使得对象的实在性问题凸显出来。陈康一直主张在本体论的领域解决性质如何结合成个体的问题。根据这一点,他应明确肯定个体是实在的。因为如果个体不实在,就谈不上在本体论领域解决这个问题。如果个体X是实在的,它在什么意义上是实在的?是康德的物自体意义上的个体还是作为诸多性质结合体的个体?如果它是物自体意义上的个体,那么关于物自体本身的具体性质,我们一无所知,这样的个体对于我们来说根本不存在性质结合问题。所以,如果个体X是实在的,它只能是作为诸多性质结合体的个体,这就等于肯定了个体X的性质都是实在的,因为如果这些性质不实在,它们便不可能结合成一个实在的个体。
个体X的性质是否实在或者是否为个体所固有?陈康似乎一直在回避这个问题,至少没有给出明确的表述。但是,他既然认可了刘述先的观点,即个体事物在同一时间对不同认识者呈现为不同性质,他就要解释:这些性质是全都为个体事物所固有,还是像洛克所说的那样只有某些性质为其所固有,还是全都不为其所固有?如果所有性质都不为其所固有,都是观察者的观念,我们就无法用它们结合成一个实在的个体。由此,如何通过它们结合成一个实在个体的问题就是一个假问题。
如果只有某些性质真正属于一个个体事物,就要解释为什么只有这些性质真正属于它?比如,两个人在同一时间看X,一个看他是面白,一个看他是面黄,面白与面黄哪一个是X的真正肤色?如果根据洛克的两种性质学说,颜色属于第二性质,无论黄与白都不是X所固有的,只有广延、形状等第一性质才真正属于X。如果只有第一性质才为物体所固有,第二性质依赖于认识者的感觉,这两种性质怎么可能结合成一个实在的个体?这正是贝克莱对洛克的批评。而且,第一性质自身也有问题:如果巨人与蚂蚁看到的X的第一性质不同,谁看到的是X的真实的第一性质?我们似乎没有确定的标准。
陈康既然认为U是各组性质的结合体,他似乎把U的一切性质都看成了实在的性质。而且这些性质必定是U同时具有的,因为如果U不同时具有这些性质,怎么可能用这些结合成一个实在的U?这里的问题是,U能够同时既黑又白,既大又小,既是平面又是立体吗?如果答案是否定的,它对不同认识主体所呈现的性质就肯定不是独立于他们的认识而实在地存在的,必定依赖于认识者的感觉。换言之,如果承认X、Y、Z是不同的个体,它们由不同组性质结合而成,同时这些性质又都是同一个U给与的,那么,为什么同一个U给与不同认识者的现象性质如此不同?这显然不能仅仅从外在的个体事物本身来加以解释。这就涉及问题的关键,即现象性质的给与是离不开感觉者的,现象性质并不表示外在对象自身固有的性质,而是感觉者参与的结果。如果不同观察者所得到的现象性质不是外部对象所固有的,由各组性质a、b、c……,甲、乙、丙……,子、丑、寅……分别结合成的X、Y、Z就肯定不是独立于认识者的实在个体。
就是说,如果现象性质是相对于观察者而言的,我们就永远不可能用这些性质结合成一个独立的实在个体,许多性质如何结合成一个个体的问题就不可能在存在论里得到解决。这似乎等于承认了刘述先的观点:性质是相对于认识者而存在的,性质结合的模式是多样的和相对的,个体的单位观念也是相对的,所以性质如何结合成个体的问题不是一个纯粹的存在论问题,同时也是一个认识论问题。
尽管刘述先所说的性质和个体事物与陈康所说的不同,他否认存在着独立于认识者的性质和个体,但是他仍然认为,现象给与我们的是彼此分离的个别性质,个体是由彼此分离的性质结合成的,只不过他认为“性质如何结合为个体”的问题不是哲学所能回答的,而应属于生理学和心理学的范围,即从主客双方的构造上去解释。但是,这个说法也有问题。因为刘述先说:“我们如果撇开一切主观的角度来谈存在,这存在不过是个模糊不清的概念!”而且它是我们想象的结果。既然如此,我们如何能够知道这客观对象本身的结构呢?进一步,我们如何能够从主客双方的构造上去解释性质如何结合成个体呢?
所以,无论陈康的存在论解决方案还是刘述先的存在论与认识论联袂解决的方案似乎都行不通。
三、性质如何结合成个体与个体之为个体
陈康和刘述先尽管观点不同,但他们都认为个体事物是由现象性质结合成的。陈康把“许多性质如何结合成一个个体”的问题等同于“一个个体如何是一个个体”的问题。初看之下,它们似乎是同一个问题,但事实上并非完全等同。确切地说,“许多性质如何结合成一个个体”的问题包含在“一个个体如何是一个个体”的问题之中。
作为整体的个体事物和它的性质是怎么被给与我们的?它们是同时被给与我们还是一个在先一个在后?如果首先被给与我们的只是许多性质,然后它们结合为一个整体,“一个个体如何是一个个体”的问题才变成“许多性质如何结合成一个个体”的问题。陈康认为现象方面所给与我们的只是许多性质,就是说现象方面没有给与我们作为整体的个体事物。在这种情况下,只有两种可能,其一,这些性质自身把它们结合起来,其二,这些性质之外的东西把它们结合起来。根据陈康的观点,结合这些性质的东西必定在它们之外。这又可以分为两种情况:一是我们的心灵,二是心外的某个东西。贝克莱认为是前者,而亚里士多德和洛克认为是后者。可是,如果知识最终来自经验,如果现象所给与我们的只是许多性质,而没有性质结合者,那就意味着我们不可能得到外在的性质结合者,从这一点来看,陈康所说的本体论的解决方案也行不通。可是,如果首先被给与我们的是对象整体而不是许多分散的性质,“一个个体如何是一个个体”就不再是一个问题。所以,“许多性质如何结合成一个个体”的问题不能解决并不意味着“一个个体如何是一个个体”的问题无法解决。
“许多性质如何结合成一个个体”的问题之所以难以得到解决,是因为人们一开始就假定现象给与我们的只是个别的彼此分离的性质,另一方面又把事物的整体性看成一个既成事实,从这两个设定出发,我们如果不假设一个将它们结合起来的第三者(物质实体、精神实体、自我等),我们必定无法解释这些性质如何结合成一个完整的个体。但是,如果我们假设现象给与我们的首先是作为整体的个体,性质只是后来对这个个体进行分析的结果,性质如何结合成整体的问题就不存在了,至少在认识论的范围内就不成其为问题了。但是陈康说:“即使现象方面所给与的,真是……整个的,仍然产生这一问题:它如何是整个的?整个的乃是由部分组成;部分即是分析所得的性质,于是问题仍是:这些部分——这些性质——如何团结成为一个个体?”①汪子嵩、陈太庆编:《陈康:论希腊哲学》,第505页。
这里,陈康把两个问题混淆在了一起。第一个问题是,作为整体的个体观念,我们是如何获得的?第二个则是,我们将整体的个体加以分析之后,得出许多性质,如何再将它们结合成一个完整的个体?不能回答第二个问题并不意味着不能解答第一个问题。例如,一个小孩把一个玩具汽车拆成一个个零件,不能再将它组装成原来的样子,这不表明他原来没有一个完整的玩具汽车。这个简单的机械的例子或许不能真正表达我要说的意思,因为如果这个孩子手里掌握了所有的零件,并且有适当的能力,他是可以重新组装成一个完整玩具的。如果我们把所有的个体都看成简单的机械,性质结合的问题或许能够比较容易得到解决。但是古往今来的哲学家难以解释性质如何结合成个体的问题,这说明个体观念不止是机械式的结合。
或许一个生物方面的例子更能说明我们为什么不能用分析后的性质结合成一个完整的个体。例如,一头生猪在肉联厂里被屠宰成数个部分,即便是不太多的几个部分,我们也无法用它们再还原出一头生猪。性质如何结合成个体的问题与此类似。这正是亚里士多德、洛克、贝克莱、休谟和康德等西方哲学家所犯的错误。他们把从经验整体分析出的性质观念作为最原本的东西,然后问它们如何能结合成一个个体?这就像把猪头、猪腿、猪蹄等部分看成最先的最原初的东西,然后问它们是如何结合成一头活生生的猪的。试想一下,既然从古至今没有一个人能够用分散的性质完整地结合成活生生的个体,而人人又都承认这样的个体存在,那么很清楚,这些个体根本就不是由后来的性质结合成的。
另一方面,如果像康德所说的那样,性质是人与物自体相互作用的结果,我们可以从一个事物那里得到多少性质?类似地,如果性质是人对个体事物进行分析的结果,我们从一个事物那里可以得到多少性质?是有限多个还是无限多个?如果是有限多个,它究竟是多少?如果是无限多个,我们对它的分析如何能进行得完?如果进行不完,我们如何能通过分析出的有限性质结合成完整的具有无限性质的个体事物。如果随着我们的分析,事物的性质不断增加,而且不同认识主体对于同一个对象的分析所得出的性质是不同的,那么通过性质结合来组成一个完整的个体U也就是根本不可能的。
再者,如果物自体本身并没有任何清楚的性质,我们对个体性质的分析,就不是从事物抽出这些性质,而是使它增加了这些性质,就是说,个体的性质是不断增长的,这样一个个体是永远无法通过性质结合而还原为原来的个体的。这正如出生后不断长大的婴儿一样,他是无法再还原为胎儿的。
当然,即使我们设定现象首先给与我们的是作为整体的个体,人们仍然可以问这一设定的根据是什么?这就涉及认识论的一个基础性的转变。在这方面,威廉·詹姆斯的学说值得我们重视。根据詹姆斯,从洛克到休谟的原子主义经验论都认为现象最初给与我们的只是相互分离的简单性质,这是不符合事实的;而康德的先验自我是一个弥补原子主义经验论缺陷的理智的虚构,同样是不真实的。詹姆斯通过心理学的观察和实验发现,现象最初给与我们的不是简单性质而是事物整体,“从一开始,经验就是一个综合的而非简单的事实”①William James,The Principlesof Psychology,Beijing:China Social Sciences Publishing House,1999,Vol.1,p.610.。从一开始经验呈现给我们的就是浑然一体的、与世界的其他部分隐约相连的对象。经验在任何时候呈现给我们的真实单位都是总体性的诸多对象的场。这个场没有一个明确的硬性的边界,只有柔性的模糊边缘。②William James,The Varieties of Religious Experience,New York:Penguin Books USA Inc.,1985,pp.231-232.这些对象包含在这个世界的时空中,潜在地可分为内部的元素和成分。简言之,经验一开始给与我们的就是作为整体的事物,性质如何结合成个体的问题是一个次生的问题。
但是,即使我们承认现象首先给与我们的是作为整体的个体,然后我们才从它那里经验到各种性质,这里仍然有一个问题,即人们为何会认为这些不断变化的性质属于同一个个体?
四、个体的同一性之根据
陈康讨论的“许多性质如何结合成一个个体”的问题是西方哲学史上的一个重要问题。他虽然没有为这个问题提出确定的答案,但是他看到西方哲学史上对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案都行不通。首先,在陈康看来,赵大的许多性质像面白、无须、身高、体瘦、会说话等性质所以结合成一个人不是因为“赵大”这个名字,因为如果他不叫“赵大”而叫“赵二”,我们仍然会认为这一组性质是一个人。其次,赵大的统一性也不是由于固定的完整的身体,因为人的身体并不固定,每时都在进行新陈代谢,而且,如果赵大因交通事故不幸失去一条腿,我们仍会认为他是赵大。第三,赵大之所以是一个人也不是因为他有一个心灵,因为心灵比身体的变化还要快?第四,赵大的同一性也不是因为有连续的记忆,因为即使赵大失去记忆,我们仍然会认为他是赵大而不是别人。第五,这些性质的结合也不能说是由于生命,因为所谓生命就是一切生活机能,这样,问题仍然是这一切如何团结成为一个个体,即通常被命名为生命的东西?①汪子嵩、陈太庆编:《陈康:论希腊哲学》,第506页。
根据陈康的说法,赵大的身心处在不断变化之中,赵大所以是一个人不是因为其固定不变的身心。陈康没有意识到,如果赵大的身体是不断发生变化的,他的性质像面白、无须、身高、体瘦、会说话等必定也是在不断改变的,这些不断变化的性质如何能结合成赵大呢?即使能够结合,在不同时刻由不同性质所结合成的个体是否同一个人?陈康认为他们是同一个人,因为他说即使赵大的体貌发生了变化,比如肤色变黑,甚至失去了一条腿,我们仍然认为赵大是同一个人。既然是这样,赵大之为赵大就不只是由不变的现象性质结合的结果,而必定是由于变化的现象性质之间所存在的同一性。
我们看到陈康将共时性的性质结合问题与历时性的个体连续性问题纠缠在一起。“性质如何结合成赵大”与“身心不断变化的赵大如何是同一个赵大”是两个不同的问题,前者要解决的是事物的整体性问题,而后者要解决的是个体的同一性问题。个体的同一性来自何处?陈康在酝酿他的这篇文章时正在讲授洛克的《人类理解论》。洛克认为自我或同一的人格是由意识造成的,由意识的同一性所决定的,“只有凭借意识,人人才对自己是他所谓自我”②洛克:《人类理解论》,关文运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310页。。根据洛克,人格的同一性只存在于意识中,不能超出意识所及的范围。这个意识扩展到什么地方,这个自我就扩展到什么地方。
如果像陈康所说的,心灵的变化比身体还要快,意识如何能具有同一性呢?如果意识没有同一性,怎么会有自我或同一的人格呢?洛克认为同一的人格并不意味着意识的不变,而是指我通过记忆把过去的某个东西同我现在的自我意识联系起来。“这个意识在回忆过去的行动或思想时,它追忆到多远程度,人格同一性亦就达到多远程度。现在的自我就是以前的自我。”③同上。
陈康不同意洛克的这个观点,他说一个人的同一性并不是因为有连续的记忆,因为即使赵大失去记忆,我们仍然会认为他是赵大,而不是别人。我们还可以为陈康再增加两个反驳洛克的例子。如果赵大少年时与一个朋友分别,数十年后在他乡偶然相遇,赵大仍然知道自己是赵大,但他的朋友未必认得容颜衰老的他,他们很可能相见不相识。这就是说,即使赵大的记忆能形成自己的自我统一意识,别人也不一定认为他是赵大。再者,一个身体相貌都与赵大酷似的人,例如他的孪生弟弟赵二,赵大不会认为赵二是赵大,但是别人却可能将赵二认成赵大。这似乎也说明赵大的个体同一性与自我意识的连续性没有多少关系。
进一步审视,我们发现洛克所说的个体同一性与陈康所说的个体同一性并不是同一种同一性。洛克借助自我意识所阐述的是自我或人格的同一性,即一个人对自己的自我认同。而陈康方才所说的则是对象的同一性。关于一个人的同一性问题关涉到两个方面,即作为自我的同一性和作为对象的同一性。一个人失去了记忆,记不得昨天发生的事情,他就不能把昨天的自己与今天的自己看成一个人,从而丧失了自我或人格的同一性。但是,别人根据他的体貌、言语、活动等特征仍然把他视为同一个人。这就是说,自我的同一性是通过意识和记忆形成的,而作为对象的同一性有赖于身体、言语、活动等特征。洛克通过区分人格和人这两个概念来阐明这两种同一性。他说只有意识能使人成为自我或具有人格同一性,但是人的同一性是由同一的连续的身体与同一的非物质的精神共同合成的,而且人们对一个人的同一性的判断主要取决于他的体貌特征。
洛克好像比较合理地解决了个体的同一性问题。可是,他的学说包含着更深层的困难。在对象的同一性问题上,他没有进一步说清楚我们如何对一个对象具有同一感。另一方面,洛克认为我们之所以能够具有人格同一性是因为我们具有一个永远保持同一的能思维的自我意识,它永远伴随着当下的感觉和知觉,并且能够回忆过去的行为和思想。但是,正是这个精神实体受到了休谟的激烈批评。休谟说:“如果没有某个或更多的知觉,我绝不能知觉到这个自我;而且除了这些知觉,我也绝不能知觉到任何东西。”①David Hume,A Treatise of Human Nature,London:Penguin Books Ltd,1969,p.676.休谟认为这些知觉以飞快的速度相互接续、永远处于流动和迁徙之中,没有哪个属于灵魂的不变能力。“我们所归于人类心灵的那种同一性只是一种假想的同一性”②Ibid.,p.306.,它“不能把若干不同的知觉结合成一体”③Ibid.,p.307.。
针对休谟的这种学说,我们看到两种捍卫自我同一性的反应。一种是以康德为代表的理性主义。他认为个人同一感来自先验自我或者一切思想都不可或缺的纯粹综合形式。但是,正如陈康所指出的,这个先验自我的存在却是一个问题。另一种是詹姆斯的彻底经验主义。詹姆斯认为我们的意识实际上是一个不断变化而又连续的思想流,其中并没有一个保持不变的自我或先验统觉。他认为自我的同一性是“一种被思想知觉到的同一感,是对所思考的事物的判断。这些事物是现在的和昨天的自我,思想不仅思想到二者,而且认为它们是同一的”①William James,The Principles of Psychology,Vol.I,p.332.。而它们之所以被看作是同一的,是因为它们之间有一种温暖和亲切感:我们在思想时对思想本身所具有的某种感觉或对身体当下实际存在的某种感觉,或者二者兼有。我们在意识到现在自我的同时,不可能意识不到这二者之一。任何使二者呈现给意识的其他事物都会像附于当下自我之上的那些事物一样被温暖地、亲切地思想到。②Ibid.,p.333.任何满足这种条件的遥远自我都会被温暖地、亲切地思想到,即新的思想到来,它们回顾老的经验,觉得它们“温暖”,欢迎它们并把它们据为己有,使之成为“我的”。③William James,Essays in Radical Empiricism,edited by R.B.Perry,New York:Longmans,Green And Co.,1922, p.129.温暖、亲切感就像一条线贯穿着一串珠子一样贯穿着它们,使它们成为一个整体。詹姆斯将对象的同一性问题与自我的同一性问题统一起来,认为“我们的个人同一感与我们对现象中的其他任何同一性的感觉是完全相像的。这一结论的根据是:被比较的现象在根本方面是相似的,或者在思想面前是连续的”④William James,The Principles of Psychology,Vol.I,p.334.。由此,詹姆斯既解释了自我的同一性,又解释了对象的同一性。
综上所述,“许多性质如何结合成一个个体”的问题不等于“一个个体如何是一个个体”的问题,也不等于个体的同一性问题。而在个体的同一性问题上,对象的同一性也不同于自我的同一性。无论传统的经验主义还是康德式的理性主义对事物的个体性与同一性的解释都难以令人满意。詹姆斯能够比较有说服力地解释自我与对象的同一性,但是他似乎没有解释事物在不同种类的认识主体之间的同一性问题。至于一个事物以何方式存在,我们只能说有多少种认识方式,它就有多少种存在方式。要问它本身以什么方式存在?我们恐怕是不知道的。
(责任编辑:张琳)
B94
A
2095-0047(2015)04-0053-12
黄启祥,山东大学犹太教与跨宗教研究中心暨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副教授。
本文是山东大学自主创新基金青年团队项目“经典诠释与哲学创新”(项目编号:IFYT1213)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