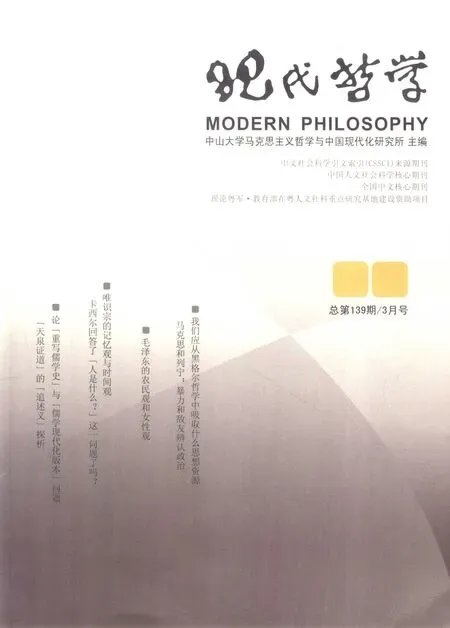数学哲学中的基础主义与心理主义之争
——从《算术基础》到《真之追求》
2015-02-07刘钰森
刘钰森
数学哲学中的基础主义与心理主义之争
——从《算术基础》到《真之追求》
刘钰森*
在《算术基础》中,弗雷格追溯了数学表达式之不变的逻辑基础的同时,清理了带有主观性和相对性的心理主义。但心理主义并没有因此销声匿迹,反而在蒯因那里得到复兴,而且蒯因还基于自然主义的心理主义,否定了弗雷格对数学基础的探寻。本文试图借由解读弗雷格和蒯因的文本,展示数学哲学中的基础主义与心理主义之争,并借由弗雷格的文本对蒯因的心理主义做出回应。
基础主义;心理主义;分析性;整体论
蒯因(W·V·Quine)在《从刺激到科学》开头“追忆往昔”一章中提到弗雷格(Gottlob Frege)时,将弗雷格的理想概括为探寻数学知识的本质以及数学真理的基础。他认为弗雷格和罗素、怀特海在这一方面是同路人,他们的结论是认为数学可翻译为纯逻辑,由此可以进一步推导出数学真理是逻辑真理,并且它的全部都能还原为自明的逻辑真理。蒯因认为弗雷格等人的这种观点是错误的,而且哥德尔1931年的论文以及罗素1902年的发现使得弗雷格等人的理想烟消云散①本文主要讨论弗雷格基础主义与蒯因复兴的心理主义之争以及弗雷格可能的回应,至于哥德尔的不完全性定理并不适用于弗雷格,因为正如达米特所指出的,在弗雷格那里并没有完全性概念(Cf.Dummett,Frege:PhilosophyofMathematics,Duckworth,1991,p.30)。至于罗素悖论对于弗雷格的挑战,一方面,罗素本人有类型论解决自己提出的悖论;另一方面,新弗雷格主义的研究表明,直接面对罗素悖论,将矛盾局部化并排除,也许可以恢复弗雷格的基础主义(参见邢涛涛:《从弗雷格到新弗雷格》,《科学文化评论》2008第6期,第62—73页)。。
弗雷格当年在《算术基础》等著作中所提出的如蒯因以上所说的基础主义②对于弗雷格的观点,有人称为理性主义,有人称为柏拉图主义,有人称为欧几里得主义,本文主要从其对于“外在”基础的探寻称之为“基础主义”,主要是与“内在”探究的心理主义相对。理想,否定了密尔等人关于数学的心理主义所带有的主观性和相对性。然而,蒯因否定弗雷格等人对数学基础的探寻的背后,恰好是他在《真之追求》等著作中所概括的自然主义的心理主义立场。本文试图通过从《算术基础》到《真之追求》的解读,展示数学哲学中基础主义与心理主义之争的某种面貌,也试图基于弗雷格的文本,回应蒯因新兴的心理主义。
一、弗雷格的“基础主义”
“如果在万物长河中,没有任何东西是不变的,永恒的,那么世界就不再是可认识的,一切就会陷于混乱。”③[德]弗雷格:《算术基础》,王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第6页。弗雷格要探求的就是这种永恒不变的东西。作为一名数学家,他的这种探索是从数字入手的。比如数字1,惯常的说法是它指示一个事物;将1这个数说成属于事物,却没有说明事物是哪个;这将使得每个人都可以任意理解这个名称,关于1的同一个句子对于不同的人意味着不同的东西。心理主义会导致的这种相对主义是弗雷格所反对的。
弗雷格认为,思维本质上在哪里都是一样的:绝不能根据对象而考虑不同种类的思维规律。不同于心理主义从具有相对性的心理表象来解释意义,弗雷格要找的是一个客观的外在基础:“人们从本书将能看出,甚至像从n到n+1这样一条表面上专属于数学的推理,也基于普遍的逻辑规律,而且不需要特殊的聚合思维的规律。”①同上,第3页。弗雷格要的是在语言、数字后面的那个永恒不变的东西,他要的是一种在哪里都是一样的“思维”、一种普遍的逻辑规律。
弗雷格力图说明,感觉与内在图像具备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而数学概念和对象则具备确定性和明确性;因此算术与感觉根本没有关系,内在图像对于数学是无关紧要和偶然的。如果从心灵本质对概念进行心理学解释,并以为由此可以得到概念的本质,那么这只会使一切成为主观,走到底甚至会取消真。要认识到概念的纯粹性质,需要大量的理性工作以追溯定义普遍的逻辑基础:
如果定义仅仅在后来由于没有遇到矛盾而被证明是有理由的,那么进行证明的严格性依然是一种假象,尽管推理串可能没有缺陷。归根到底,人们以这种方式总是只得到一种经验的可靠性,实际上人们必须准备最终还是会遇到矛盾,而这个矛盾将使整个大厦倒塌。为此,我认为必须追溯到普遍的逻辑基础……②同上,第8页。
普遍的逻辑基础的追溯需要坚持三条基本原则:“要把心理学的东西和逻辑的东西,主观的东西和客观的东西明确区别开来;必须在句子联系中研究语词的意谓,而不是个别地研究语词的意谓;要时刻看到概念和对象的区别。”③同上,第8—9页。换言之,坚持客观性原则,要求只在心理学意义上使用“表象”,把表象与概念和对象区别开来,前者代表心理的和主观的,后者代表客观的和逻辑的;坚持语境原则,要求避免将个别的心灵的内在图像或活动当作语词的意谓;函项原则要求的是,未充实的概念不可成为不变的客观对象。
客观性原则预示着弗雷格所追溯的基础将是与具有相对性的心理表象无关的客观逻辑基础,它是普遍性的;而函项原则与语境原则将在获得作为算术基础的数定义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提出这三个原则之后,弗雷格指出他那个时代的数学回到一种甚至要努力超越欧几里得的严格性,那就是人们对各种概念进行严格的证明;而且他相信沿着严格证明之路,必然能获得构成整个算术基础的数概念以及适合于正整数的最简单的句子。
于是在弗雷格眼中,数学本质上只要能用证明就不用归纳来获得确证。证明的目的在于使句子的真摆脱各种怀疑,并且提供关于句子的真之间的相互依赖性的认识。句子间的真的依赖性在哲学上需要对先验和后验、分析和综合做出区分。在弗雷格看来,与此区分有关的是判断的根据(justification),而非其内容。因此,通过证明达到的根据如果是普遍的逻辑真理和一些定义,获得的是分析的真;而根据非普遍逻辑性质的特殊知识领域的真得到证明的句子,则是综合的。类似地,是否完全从本身不能够也不需要证明的普遍定律得到证明,则是区分一个句子的真是否先验的标准。
从根据而不是从内容区分真的先验和后验、分析和综合,这也是弗雷格追溯基础理想的一种体现,更直接的是,它与追溯算术基础时所必需的严格证明之路密切相关:在数学领域,要尽可能严格地证明算术定理,避免推理串中的每个缺陷,找到证明所依据的原初真命题。比如:
2加2等于4,这不是直接的真;假定4表示3加1。人们可以如下证明这一点:
定义:1)、2是1加1;2)、3是2加1;3)、4是3加1
公理:如果代入相等的数,等式依然保持不变。
证明:2+2=2+1+1=3+1=4(定义1,定义2,定义3)
所以;根据公理:2+2=4
弗雷格认为莱布尼茨的上述证明有缺陷,应该更精确地书写为:
2+2=2+(1+1)
(2+1)+1=3+1=4①同上,第16—17页。
莱布尼茨的证明缺少2+(1+1)=(2+1)+1,它是a+(b+c)=(a+b)+c的一种特殊情况;以这条定理为前提,其它公式都能以这种方式被证明,并且每个数就能够由前面的数定义。“我们甚至没有关于这个数的表象,可确实就这样把它据为己有。通过这样的定义,数的无穷集合化归为一和加一,并且无穷多数公式均能够由几个普遍的句子证明。”②同上,第17—18页。基于这种证明方式,弗雷格试图从a+(b+c)=(a+b)+c的形式来说明,借助几条普遍规律,仅从个别数的定义可以得出数公式,但这些定义既不断定观察到的事实,也不假设其合法性(不需要justification)。他在批评前面提到的密尔等人的聚合性思维的同时,认为数的规律不可能是归纳的真命题:归纳如果是习惯的话,“习惯(作为一种主观状态)完全没有保真的能力”,“归纳必须依据概率学说,因为它至多可以使一个句子成为概率的。但是如何能够在不假设算术规律的前提下发展概率学说,却是无法预料的”。③同上,第25页。
弗雷格认同莱布尼茨的观点,数学中发现的必然真的命题必须有一些原则,其证明不依赖于例子及感觉证据。他认为几何学定理之间可以互相独立,它们不依赖逻辑的初始规律,因而是综合的;但经验综合的性质并非算术规律的性质。就数而言,每个数都有自己的独特性,它要求关于数的科学原理是分析的,数相互之间是紧密相连的。关于数的普遍句子不必只适用于眼前存在的事实,数学的真命题“会有一系列未来使用的推理串,其用途将在于:人们不必再进行个别的推理,而是能够立即说出这整个系列的结果。”④同上,第32页。
如果真的可以达到上面提到的作为根据的普遍句子,以便由之推导出数公式,那么这样的句子应该是从更基本的数定义得出的。因此,接下来需要进一步考虑数的定义。
以往由于定义尝试的失败,数总被认为是不可定义的。把数看作事物性质,数是主观的东西,把数解释为集合、多或众多,通过对不同的实物集合加以不同的命名来解释数,这些说法都被弗雷格一一驳斥了。而对欧几里德的“数是一种单位集合”的解释,在指出后人的很多说法中的问题及困难之后,弗雷格提出解决困难的方法是:把一和单位做出区别。具有客观性的“一”作为数学研究的一个对象的专名,不能是复数;相应地,单位应该是一个概念。概念不同于专名,只有当概念带上定冠词或指示代词时才能被看做一事物的专名,但因此它就不是概念了。因此,“数是单位”的解释把概念词混淆为专名了。
弗雷格认为,“数的给出包含着对一个概念的表达”,“数的给出表达了一种独立于我们理解的真实的东西”。⑤同上,第65—66页。上述观点提醒我们:每一个个别的数词是专名,它不等同于概念词,当一个概念词被它“充实”而饱和了之后,我们就得到了专名。在贯彻语境原则的前提下,弗雷格认为,为了获得数这个概念作为对象的数,必须确定数相等的意义。他借助的是莱布尼茨“用一个事物替代另一个事物而不改变真,这样的事物就是相同的”⑥同上,第82页。的解释,把数相等界定为外延相等(数值的相等)。这与他在《含义与指称》中提到的等值置换原则相一致:在逻辑中,真值相同的词项和命题可以互相置换。我们可以由两个等数的概念得到其下的数相等,加上“n在自然数序列中紧跟m”这个表达式,就能定义0和1,并且进一步确定数序列是无穷的。
基于客观性原则,弗雷格反对心理主义的相对主义和主观主义,他把算术奠基于一种不变的逻辑基础之上。遵循语境原则和函项原则,他在《算术基础》中主要展示了一种追溯算术基础的方法。根据这种严格证明的方法,弗雷格认为从一些自明的公理(即他所谓的普遍的逻辑基础、普遍句子)出发,加上数的定义,可以演绎出所有关于数的真命题。虽然这有循环论证嫌疑,但是弗雷格明确地认为按照他的严格证明的方法,可以追溯作为算术基础的数的定义以及自明的公理。他在《算术基础》中谈及其基础主义的哲学动机,在于澄清算术真是属于先验还是后验、是属于分析还是综合。如前所述,从判断的根据而非内容解释真,由算术真所根据的是不可证明的普遍句子来看,算术真(truth)当然是先验分析的。换言之,从算术真的基础可以得出算术真是先验分析的。这种哲学动机促使弗雷格进行基础的追溯,而分析性也因此成了算术命题的特性,并且将其与综合性的心理命题区分开来。
二、蒯因的《真之追求》及弗雷格应对的可能性
弗雷格以澄清算术真的分析性为其哲学动机,蒯因则由对分析性概念的批判而提出一种整体论的彻底经验主义,他的经验主义就是所谓的自然主义的心理主义。基于对分析命题的态度,这种经验主义并不承认数学中存在如弗雷格所追求的那种分析性的基础。
蒯因在他著名的《经验论的两个教条》中所批判的第一个非经验论教条,就是分析与综合之分:奠基于非事实的意义的真(truth)是分析的,而奠基于事实的真是综合的。而且,对分析与综合之分根源同一的还原论的清理之后,他的结论是:由真一般地依赖于语言和语言之外的事实得出,每个陈述的真可分解为语言部分和事实部分,这是很多胡说的源头。根据这种划分,如果某陈述的真只与语言部分有关,那么该陈述就是分析的。这种分析和综合之分,在蒯因看来是顽固地抗拒任何明确的划分。科学看起来总体上依赖于语言与事实,但逐个地审视科学陈述,却能发现并非如此。①Cf.W.V,Quine,TwoDogmasofEmpiricism,ThePhilosophicalReview,Vol.60.No.1.,1951,p.20、38.没有教条的经验论应该主张:“我们所谓的知识或者信念的总体,从最具因果性的地理和历史的事实到相当复杂的原子物理或者甚至纯数学和逻辑,是一个人造的构架,其仅仅是沿着边缘侵入经验。”②Ibid.,p.39.
把架构在经验基础之上的人类知识体系比喻成一个倒扣的碗的话,纯数学和逻辑即便处于碗顶,也最终要与经验相关。这种思想在蒯因后期的《真之追求》得到了进一步的阐述,与弗雷格固守理性、固守不变的基础不同的是,蒯因固守的是他心中的经验论规范:“nihilinmenterquod nonpriusinsensus(心灵中没有任何东西是以前感觉中没有的)”。③Quine,W.V.,PursuitofTruth,HarvardUniversityPress. 1992,p.19.他的出发点是:感觉的刺激-感受才是我们关于外在世界的知识客观性的保证:
有关我们外在世界的知识的客观性保持在我们与外在世界的接触中、从而在我们的神经摄取和与之相应的观察句中得以确立。我们从整个句子而非从词项出发。代理函项的一个教益是,我们的本体论,像语法一样,是我们自己对关于世界的理论做出的概念的贡献的一部分。人类提出建议,世界付诸实施,但这仅仅是经由对具体表达人的预见的观察句做出整句的“是”或“否”的判断来达到的。④Ibid.,p.36.
在蒯因看来,我们经由感官刺激(stimulation),在历代累积的创造性之下构造关于外部世界的系统理论。在刺激和感受的关系或者刺激和我们的外在世界的科学理论的关系的分析中,神经科学、心理学、心理语言学、遗传学或者历史学都可以提供资源,而其中有一个部分可以仅借助逻辑分析来加以考察,那就是理论被预言检验的部分,或者属于证据支持关系的部分。这就进入到了“求真”的领域,并且看来他也将采取逻辑分析和语言分析的方式,从目标和方法上看似乎与弗雷格对算术基础的追求是一致的。
但事实并非如此,究其一生,蒯因直到最后的著作《从刺激到科学》都立足于前面提到的那个经验论规范。虽然蒯因有时候认为有些数学命题是没有经验内容的,但是不同于弗雷格所认为的对每个对象都必然有意义的命题都是重认命题(recognition-judgment),比如数学中的等式,他认为有意义的命题恰好是有经验内容的命题,也就是能被检验、值得检验的命题。
蒯因更直接要解决的是所谓“科学游戏的目的”的问题。他认为,科学游戏的压倒性目的是技术和理解。从技术和理解的角度来看,“所指和本体论如此后退到单纯的辅助者的地位。真句子,观察的和理论的,是科学事业的始终。它们由结构联系起来,而对象扮演了结构的纯节点的角色”。①Ibid.,p.31.这种结构就是逻辑的联系,在代理函项的理论下,px原来意味x是p的地方,可以重新诠释为x是p的f;即在重新解释后的句子逐词保持不变的情况下,观察句依然和以前一样与相同的感觉刺激结合在一起,而且逻辑联系完好无损,理论的对象却被随意大幅度地移换了。
这说明对象“对于观察句的真是无关紧要的,对于观察句对理论句提供的支持是无关紧要的,对于这个理论预言中的成功也是无关紧要的”。②Ibid.,p.31.只要能保证与感觉刺激结合,那么作为“人造架构”的观察句、理论句的对象就可以随意移换。语词、句子不过是人类使用的符号,人类可以“任意”地解释,当然,前提是与感觉刺激结合:“人类提出建议,世界付诸实施。”对象在蒯因这里并不重要,对真句子来说更重要的是与感觉刺激相合。但这种相合并非是孤立的,而是整体的。在他看来,直接面临经验检验的是所谓的观察范畴,而蕴含观察范畴的是一个理论的整体,其中,算术和其他数学的分支是理论背景的一部分。在《真之追求》第6节中,蒯因试图通过在整体论所要求的最低限度肢解整体的准则之下,保护任何纯数学的真,但这种保护不是因为数学的基础性,而是因为数学渗透到人类关于世界的知识系统的各个分支,对数学的破坏将令人无法容忍。蒯因认为,这可以解释数学必然性,并且基于一个所谓的未阐明的原理:人类在自由地拒斥其它信念的同时却要捍卫数学。由于整体论,加上数学对我们关于世界的知识系统的渗透,在数学得到应用之处,经验内容也被数学所分享。
蒯因的老师卡尔纳普在他的数学哲学中,使用分析性来解释缺乏经验内容的数学如何有意义以及为何数学是必然真。之所以使用分析性,在蒯因看来,是因为类似于形而上学的必然性反映出事物的本质,分析性反映了语词的意义。不过,如前所述,蒯因认为通过整体论就可以解决卡尔纳普通过分析性所解决的那两个问题。蒯因对于数学必然性的说明,并不是给出像弗雷格那样的基础主义证明,而更主要是从数学应用的效果来说明;与其说他想说明数学的基础性的必然性,倒不如说他想通过整体论来说明数学如何跟经验关联。
在《真之追求》第40节,蒯因专门讨论“数学中的真”。在他看来,数学有一部分因为不应用于自然科学而不享有经验意义,集合论的高级部分也是这样,而它们的意义在于它们是与应用数学一样用相同的语法和词汇来进行表述的。或许因为这种数学的高级部分的非应用性,蒯因认为要是将之排除在二值逻辑之外,就需要不自然地划分语法。因而,由于简单、经济和自然的考虑,这些高级部分或者是不必要的想象,或者可以在谓词逻辑和集合论这类基础上给出来;并且这样处理缺乏经验内容的纯数学,跟自然科学内部进步的简化和经济达到一致,“它是关乎使我们关于世界的整体系统紧凑(tightening)和简化(streamlining)的问题”。③Ibid.,p.95.
从以上对蒯因在《真之追求》中的观点的述评可见,蒯因自然主义的心理主义把人看作自然的一部分,而人们使用的数学(包括逻辑、集合论作为其组成部分)只是人们的工具。蒯因不像弗雷格那样试图分析出一种外在的数学的基础,他只是从数学的应用来说明数学的必然性;这种必然性最终与经验相关的应用关联起来:数学作为理论背景的一部分,蕴含观察范畴,并且当观察范畴遇到反例时,唯有数学不能被破坏。在《从刺激到科学》中蒯因用一章的篇幅专门讨论了逻辑和数学,其中的观点与《真之追求》是一脉相承的,并且可以增进对他关于逻辑和数学的心理主义观点的理解。
作为自然一部分的人对于逻辑的习得有一种“进化”的过程:人类从孩提时代习得“并非”、“并且”、“或者”这些逻辑联结词以及“有的”、“每个”这些量词的时候,就逐步把蒯因界定的狭义的逻辑的基本律内化了;而当人类数学理论成熟时,就能够在一种形式化中把这种逻辑压缩为:证明一个给定的前提集对预期结论的蕴含,就是证明该前提集与结论的否定的不一致。这种观点把数学当成比逻辑更加高级的知识体系,蒯因接下来的一句话可以更清楚地看出这一点:“我乐意于如此狭义地限制词项‘逻辑’,而把集合论处理为数学另一更高级的分支。”①Quine,W.V.,FromStimulustoScience,HarvardUniversityPress,1995,p.52.他在后面甚至把集合论当成数学的代名词,即逻辑是数学的分支、集合论则是更高级的分支。并且,这种“狭义”的逻辑和集合论及数学的其它分支,有着三个重要的区别:一、逻辑没有能称为属于它自己的对象,其变量允许所有离散的值;二、除去同一性,逻辑没有自己的谓语;三、逻辑允许有完全的证明程序,而数学其它分支则由于哥德尔不完全性定理而不允许有完全的证明程序。②Ibid.,p.52.
从以上对比可见,就没有对象与谓语而言,逻辑如前面所引述的《真之追求》的观点所表明的那样,更主要的是具有一种联系的功能;就证明的完全性来说,逻辑看来比之数学的其它分支更有优势。如前所述,在蕴含观察范畴方面,蒯因把数学律与自然律的作用等同起来,因为集合论和数学其余部分的规律排列在进行蕴含的前提之中,等同于自然科学的规律和假说。不过,这并不与公认的数学缺乏经验内容的看法相冲突,蒯因认为数学的这种参与并不赋予经验内容,因为经验内容是属于进行蕴含的集合并且不被其成员所分享的。
在《真之追求》里能够享有经验内容的是应用中的数学,而这里作为进行蕴含的集合一部分的数学,是所谓的非诠释数学(uninterpreted mathematics),它们不仅缺乏经验内容,且缺乏真假。蒯因在比拟这一类数学真理为经验真理时,主要出于其对观察范畴的蕴含有帮助的考量,而将其对经验的背离忽略不计。蒯因认为许多这样的语句可以用应用数学中所坚持的规律来处理,另外一些解证地独立于先前理论的情形则还是用经济原则来处理。加上哥德尔的不完全性定理,令蒯因为难的还有:有许多属于数学的闭合句在一致的证明程序中,不可证明也不可证伪。最后,蒯因只能与这种超出他认为的值得并且能够检验的才是真陈述的要求的句子做出妥协。但是,他还是强调,即使这涉及到康德的物自体问题,关键却还在于人类的用法,而并非宇宙之秘。
与密尔等心理主义的前辈相比,蒯因并不否认数学尤其是纯数学对于经验的背离;而对于逻辑,他则更主要从一种工具的角度来对待。在写作《经验论的两个教条》时,蒯因认为人类的知识最终都与经验相关;而到了《从刺激到科学》,他却承认非诠释的数学对于经验的背离。即使借用应用数学的规律处理部分这样的数学陈述的真假问题,同时用奥康的剃刀处理另外一些数学命题,还是存在着真假不定的数学命题,蒯因提到非诠释数学即抽象代数时说它们没有经验内容、也没有真假。而这与前面提到的他所贯彻的经验论的规范是冲突的。
蒯因的这种困境在弗雷格看来或许并不成为困境。弗雷格其实并不否认经验的作用,他承认感觉印象是认知数和其他一些东西的条件,但他强调在数学基础方面中经验是无关的。在《概念文字》的序言中,他把科学真理分成两类:一类是其证明纯粹由逻辑完成,另一类是必须被经验支撑的。不过,即使是第一类,也是与这样的事实相一致的:“没有任何感觉活动的话它是绝不会在人心中称为意识”①Frege,Gottlob,Begriffsschrift,I.Angelelli(ed.),Hildesheim,1879;GeorgOlms,1964,p.5.;只是它并非源起于心理学,而是基于分类之上的最好的证明方法。感觉活动是意识形成的必要条件,包括其证明纯粹由逻辑完成的科学真理也是如此,不过感觉活动却并非基础。泰勒·伯奇(TylerBurge)考究了奠基(grounding)一词的德语,认为基础和奠基是与理性相关的。②Cf.TylerBurge,FregeonKnowningTheFoundation,Mind,Vol.107.426,1998,p.307.哲学家所谈论的理性,一般意指源自亚里士多德的范畴理性,即弗雷格在《算术基础》第31节提到的,使我们与动物区别开来的更高精神力量。作为算术基础的命题恰好是不需要检验的、自明的,其作为真命题的意义因此不在于蒯因所要求的值得检验和能被检验,而在于它们所含有的内容是理性所必须确认的。
与《算术基础》开篇建立的那三个原则相适应,弗雷格把科学真理分成两类,其中,客观性的算术真理纯粹由逻辑得到证明。算术领域的真在弗雷格那里如同赤道与北海的存在一样,具有超乎经验的客观性。算术真理在弗雷格那里具备的独立于经验的地位,恰好就标出了蒯因极不情愿地作出妥协后逐步接近的那种立场。另一方面,即使蒯因的经验论看起来似乎更符合人类的实际(人们通过微弱的纽带与包括数学对象这一类抽象对象的外在世界相连,更多的时候,人们谈论知识就是在谈论人们经验中的知识,在此意义上,人类提出建议,世界付诸实践),但是他却无法将经验主义的规范贯彻到非诠释数学的领域。
最后回到本文开头转述的蒯因对于弗雷格理想的否定。自明的逻辑真理作为算术基础的探寻在蒯因看来之所以是失败的,与蒯因对分析性概念的态度密切相关。如前所述,弗雷格基础主义探究的哲学动机是进一步澄清分析与综合之分,把通过证明由非事实的普遍逻辑真理或定义得到辩护的数学真视为分析性的,并且在《算术基础》结尾部分还认为他在这一点上推进了康德的研究。③[德]弗雷格:《算术基础》,王路译,第122页。蒯因在《经验论的两个教条》中虽然直接针对的是卡尔纳普的分析与综合之分,但就以奠基于非事实与事实来区分分析与综合而言,他的这种批判也可以针对弗雷格的分析与综合之分。蒯因否定奠基于非事实的分析的真的存在,最终目的是得出他的整体论的经验主义。克里斯托弗·皮卡克(ChristopherPeacocke)指出,蒯因拒斥分析性与他的整体论、可错论相关联,而他的整体论是刺激意义(stimuli-meaning)的整体论。如前所引的《真之追求》中的观点所显示的,在蒯因那里,可以说感官刺激才是所有知识的基础。皮卡克指出,刺激意义并不必然具有一般的意义同一性。比如,对一个严重散光的人来说,“那条线是直的”的刺激意义将与他视力更好的朋友不同,但是这个句子在两种情况下都有同样的意义。④Cf.ChristopherPeacocke,Holism,inACompaniontoPhilosophyofLanguage,BobHaleetal(ed.),BlackwellPublishers,1998,p.231.
如此一来,固守经验论规范的蒯因与以往的心理主义一样,将摆脱不了经验所带来的“相对化”。这种相对化把判断后退到心理活动之上,同时也带来了以往心理主义所带有的主观性。如果不像弗雷格那样设定一种永恒不变的基础的话,这种后退将有无穷后退的危险。总而言之,蒯因主要是从人类理解的局限来说明弗雷格这种基础的探寻的无效;而弗雷格面对这种挑战,他大可固守自己的立场,强调一种超乎经验的能力使得人类能够获得算术的基础这一类基础性的知识,即使人类的与动物区分开来的能力不能胜任这项寻求基础的工作,那也不能由此断定此类知识的不存在。如弗雷格所言,没有基础的知识将是无源之水;而心理主义的主观性和相对性,尤其对于数学知识来说是危险的,其无限后退的可能性将会使得一切陷入混乱。这也正是前面提到的蒯因所陷入的困境的原因所在。
(责任编辑 任 之)
B089
A
1000-7660(2015)03-0063-07
刘钰森,广东潮州人,哲学博士,(广州510006)华南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哲学研究所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