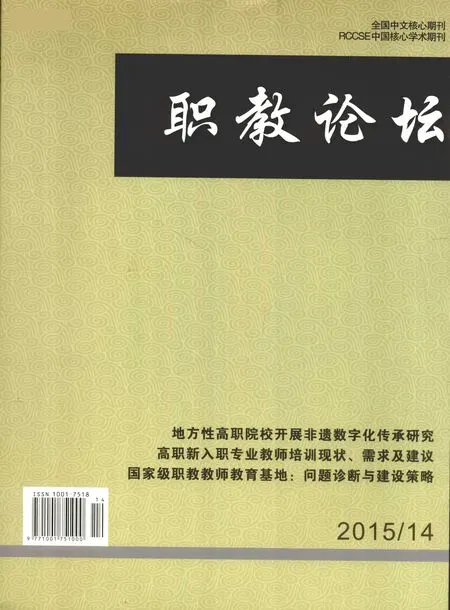法律职业教育的社会化和专业性
——以西方现代家事调解实践为视角
2015-01-31来文彬陈小燕
□来文彬 陈小燕
法律职业教育的社会化和专业性
——以西方现代家事调解实践为视角
□来文彬 陈小燕
当前法律职业教育在方法或者内容上较多关注于法学本身专业技能培养,而较少关注综合性、跨学科专业技能的培养。针对性地适用现实生活需要,借鉴各学科知识技能,走综合性法律职业教育发展之路,或许是法律职业教育值得探讨的路径或方式之一。西方现代家事调解的职业化、专业性和综合性不仅值得调解实务借鉴,也对我国法律职业教育社会化、专业性发展有所启示与思考。
法律职业教育;综合性;专业化;家事调解
当前关于法律职业教育该如何进行,理论与实务界看法不一。实践中,无论是专科还是硕士等法律类职业教育,其在方法或者内容上总体趋势是更多关注于法学本身专业技能的培养,如课堂讨论、案例分析、模拟法庭、法律诊所、法律援助等,甚至是应用型的司法考试,而较少关注综合性、跨学科专业技能的培训教育。其伴随的一个社会现象是法科学生“难就业”或者只完成基础性学历的法律人才“就业难”。简单分析而言,千军万马挤独木桥,法科人才就业紧盯着“公、检、法、司”等专业对口部门,忽视法律在现实社会生活中的综合应用或者说法律职业教育过多倾向于法律专业本身知识与技能的学习与培养而非综合性应用,可能是上述问题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事实是,法律人才特别是应用性法律人才的需求是非常大的,就业或者说发展方向的前景是可观的。在法律职业教育的内容上,如针对性地适用现实生活需要,借鉴各学科知识技能,走综合性、社会化法律职业教育发展之路,或许是法律职业教育一个值得探讨的路径或方式。以西方现代家事调解模式为例,其不仅在专业技能或者说知识上跨学科应用(综合社会学、法学、心理学、谈判与沟通技巧、甚至是叙事学等),有效应对家事纠纷解决的现实需要,实现了诉讼或者其他纠纷解决机制不能达到的实效(如友好、合作、根源性解决纠纷存在的障碍,实现结果的双赢);而且设立了专门的家事调解员职业,并在实务中为法律职业者或者再教育学习者提供家事调解人员就业培训等,践行调解职业化、社会化发展之路。
因此,本文以家事调解实践模式为分析视角,对其主体的职业化和社会化、内容的综合性和专业性予以探讨,以期对我国法律职业教育相关理论与实务有所裨益[1]。
一、职业化的法律社会服务
(一)根据社会需求,针对性提供法律职业服务
为应对和妥善处理现实生活中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的婚姻家庭纠纷,维护纠纷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以及子女的身心健康,西方国家(以美国和欧洲主要国家为主力军,其他地区或国家均不同程度发展)法律实务中发展出了各种卓有成效的家事调解社会服务。
总结域外发达国家家事调解实践可知,其突出特点是家事调解服务的社会化,即是一个面向社会的职业性家事纠纷解决机制,不仅调解人员社会化、调解机制社会化,职业教育的内容也是社会化的。例如,其调解基本上由专门的社会组织负责;调解的性质是社会组织等第三方进行的替代纠纷解决机制;调解人员均是取得官方资质认可的社会工作人员,如律师、心理咨询专家、社工等专业性社会工作者;调解职业培训的内容也是跨学科的综合性专业知识与技能,可以说是整体理念和具体制度构造均鲜明表现其社会化的家事纠纷解决服务的性质和特征。
(二)确立法律地位,制度保障社会化法律服务
因为现实需要且关系重要,家事调解服务不仅社会化,而且获得强有力的制度保障。例如,域外这些国家或地区定位家事调解人员为社会工作者,相关立法和司法实务均官方承认并确立其社会工作者资格。例如,法国早在2003年就专门颁布其第284号法令《家事调解国家文凭法令》,明确规定家事调解员为社会工作者,并将其纳入国家专门职业资格文凭体系,面向社会公众招考。有的国家则是通过在法院附设调解、转介调解时提供社会化专门调解机构和调解人员清单等方式来制度性保障从业者的法律地位。
(三)建立执业资格要求,严格职业资格考试、培训和服务
如前所述,其调解人员法律地位为社会化的专业法律服务人员,可能是律师、心理咨询专家或社工,但想要从事家事调解服务,必须具备相应的资质要求、通过培训和考试,取得专门的执业资格证书方可上岗。培训内容大多既有法律知识、调解技巧等法律方面的知识与技能,也有家事冲突理论、心理咨询与治疗等专业性纠纷解决辅助知识,以及家事调解员职业准则等职业伦理内容,甚至是实务锻炼的安排,如督导实习或实务从业等[2]。
家事调解员的资质认证过程包括提出申请、技巧评核以及理论考试等环节。通过所有环节考核后才可获得从业认可,取得家事调解执业资质,获得家事调解从业证书。如果是法院附设的调解,法院还会通过法院自身制定的实务规则等对哪些机构和人员可以获得委任负责附设调解事宜予以进一步具体规范和要求。
二、专业化的发展道路
(一)专门的委员会
在西方家事调解工作中,调解人员职业化、专业化的特点非常突出。各国关于调解员的任职通常都制定了严格的法律或职业规范,要求调解从业人员不仅要具备相应专业背景知识,还得接受专业理论与技能培训,通过考试或考核并取得相应的职业证书方可上岗执业。例如,法国将家事调解员明确纳入社会工作职业之中,经过培训考核获得专业资质的人员可独立提供社会性家事调解服务并收取相应的费用。
而且,各国也大多成立专门的调解委员会负责家事调解员之业务培训与资质认可以及家事调解培训事务之管理和发展。例如,英国的“家事调解协会”(FMA)、“全国家事调解协会”(NFM)以及“家事调解员协会”(SFMA)、美国的“家事调解员协会(后改名称为“冲突解决协会”,ACR)、加拿大的“家事调解中心 “(FMC)、法国的 “家事调解促进协会”(APMF)和“全国家事调解联盟”(FENAMEF)、德国的联邦家事调解协会(BAFM)和 BM等等[3]。甚至连欧盟都成立专门的工作组,指导、协调欧洲家事调解发展事宜。如早在1998年,欧洲委员会就出台了专门的家事调解建议,其司法效率委员会还专门为此设置了工作组,2007年制定了指导家事调解实施之基本原则;2009年,家事法会议专门以欧洲家事调解为主题,深入探讨如何指导各成员国家事调解之发展,协调和统一家事调解之立法、调解职业规则与培训等具体事宜。
(二)专业的从业规则
实务中,这些专业的调解委员会通常还会制定各种家事调解专业规程来指导规范家事调解之实务操作,明确规定家事调解员从业标准、行为规则和职业道德准则等,以更好的管理和规范家事调解服务健康发展,并建立相应的监督、考核以及奖惩机制。例如,美国家事和解法院协会与家事调解员协会共同制定的行业示范准则《家事与离婚调解实务标准》、律师协会家事法委员会制定的《律师调解员从事家事法纠纷实务标准》;欧洲委员会司法效率委员会制定之《关于更好实施现行家事调解以及民事案件调解建议之指导方针》等等。
(三)多种职业教育形式
社会化的家事调解服务需要职业化的培训和发展,因此,西方家事调解实务十分重视家事调解员职业化教育的发展。例如,早在20世纪80年代,美国著名的家庭法律事务代理人和家庭心理咨询师、后来被誉为“现代家事调解之父”的奥库勒(O.J. Coogler),即借鉴、运用“结构型冲突解决理论”创立了结构性家事调解来为离婚等家事纠纷当事人提供家事调解法律服务,还率先成立了美国第一家社会性的专业家事调解组织——家事调解协会,负责指导和培训律师和心理健康专家等实务人员如何更好从事专门的家事调解服务工作[4]。其他国家和地区也有诸多类似的职业教育培训服务。例如,我国香港地区不仅有社会性的、政府推动性的家事调解服务,国际仲裁中心有专门的调解委员会、家事法庭大楼里还有专门的家事调解统筹主任办事处,负责指导、协调法院附设家事调解的“诉、调对接”事宜。
有些机构和专家甚至走出国门,向世界传播其先进成熟的家事调解理论与经验,指导和辅助其他国家或地区开展家事调解之发展,如指导培训家事调解员、参与制定家事调解发展计划等,并取得较好的实效和影响。例如,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的岳云(Howard H.Irving)教授曾在香港指导社会性家事调解服务发展,并提供专门的家事调解员培训项目[5];而美国加尼弗尼亚州大学的约翰·温斯雷德(John Winslade)教授则在新西兰开展家事调解员辅导培训工作,他们的这些努力和帮助均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该地区家事调解理论与实务之发展。
三、综合性的教育内容
(一)调解模式的综合性
西方现代家事调解服务及其培训在调解理念与内容上均具有综合性,是一个跨学科知识综合应用的模式。具体而言:
1.调解理念的综合性。西方现代家事调解实务中,家事调解有不同的模式。每一种模式都有自身独特的调解理念,建立在不同的专业理论基础上,采取了不同的调解方法、调解技术和干预方式,并在理念基础、框架体系、调解目标、培训内容以及调解人员的专业性等方面各有侧重。
例如,结构型家事调解认为阻碍当事人有效调解的关键因素在于对抗性家事诉讼模式以及律师全面代理等诉讼规则的不合理。因而,调解重心在于构建合理的纠纷解决规则,意图通过此举保障当事人能够自主、理性决策并减少对抗,增强合作;而劳务管理型家事调解则认为谈判双方实力失衡、地位不平等是阻碍调解顺利进行的主要因素,因而保障当事人在平等基础上自利性协商是其中心任务,设想通过调解员的积极斡旋、协议公正性评价等方式来促进纠纷双方当事人的合作、妥协;治疗型家事调解却认为,纠纷当事人之间的误解与不信任、敌对与攻击冲动等隐藏在纠纷背后的心理因素才是最大的障碍,如何协助其克服情绪与心理障碍才是问题的关键,因此特别注重心理咨询与治疗方面的技巧与经验进行调控,以期能够跨越心理障碍,促使当事人理性合作,妥善处理纠纷。交流与信息型家事调解则将问题归结于纠纷双方信息之不对称或者说缺乏沟通,因而针对性为其提供相关法律信息、心理辅导以及沟通技巧,以便当事人能在信息对称、及时沟通的基础上理性决策、积极合作。
调解模式千千万万,且各有千秋。但总体而言,均遵循了一个共同的理念,即旨在严格遵循 “家事纠纷尽量由当事人自主决策,鼓励和解”的基本理念下,更多采取一些专业性的辅助手段帮助当事人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友好、合作、实效性的解决纠纷,以达到双赢的最终理想。
2.调解内容的综合性。从内容或者方法上看,无论是哪一种调解模式,均是根据需要针对性地充分借鉴其他专业学科的知识与技能来辅助调解的进行,并保障实现其实效与高效。例如,在调解实务与劳务管理理论结合而形成的劳务管理型家事调解模式中,调解员被要求同时具有心理治疗、谈判以及法学知识背景。因而,不仅可协助纠纷解决,在当事人情绪阻塞阻碍调解进程时,还可提供常规性治疗,以克服谈判双方实力失衡、地位不平等这一阻碍双方达成调解协议的关键因素或者说主要障碍,保障当事人理性协商、积极合作并最终达成双方均可接受的公平协议;调解实务与心理学结合形成的治疗型家事调解,则是将家庭治疗的背景及训练、临床与治疗理论与技巧应用于家事调解服务的一种家事调解模式。在家庭治疗理念、制度的基础上融合问题解决型家事调解方法而成,因而,通常是由心理健康专家和咨询服务机构提供服务。而调解实务与谈判理论结合形成之交流与信息型调解,则主要是由律师和心理治疗师组成的调解团队中立性地为当事人双方提供法律、协商谈判以及心理咨询等方面的必要信息,以辅助谈判当事人理性抉择,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妥善解决纠纷。
(二)专业内容的综合性
针对不同的家事调解模式,家事调解服务和职业教育的内容也不同,总体上呈现跨学科交叉、综合化发展的趋势,例如,在加拿大,家事调解员被分为家事人身关系调解员、家事财产关系调解员以及全面型的家事调解员三个类型,调解员的资质要求因此而差异。其中,家事人身关系调解员的执业培训包括:冲突解决与调解的基本理论学习与实务技巧培训、分居与离婚家庭动力方面的培训、家庭与子女法律知识学习、权力失衡以及家庭暴力影响方面的培训、与分居、离婚有关的财产事务培训、调解道德规范等等。而全面型家事调解则是人身关系与财产关系的综合,其有更高之要求。即使经过专门培训、通过专业考核,还得完成一定时间段的督导实习后方可上岗执业[6]。
四、结论与启示
综上可见,西方现代家事调解是一个跨学科专业知识技能的应用,其运作、配套的规程、人员的培训均是跨学科综合的典范。其家事调解服务和家事调解职业教育的社会化、家事调解教育培训内容的专业性和综合性均值得我们一定程度地借鉴和参考。例如,家事调解员不仅需要进行资质认证,经过专业培训,而且就知识背景而言,通常需要跨学科、多领域的知识与技巧,例如家事法律知识、调解与谈判等冲突理论与技巧、心理咨询与治疗技能以及家庭、成年人与儿童发展方面的知识等等。因此,相比于我们国家乡土气息浓郁的“经验式调解”,其在人员、机构、规程、内容上似是更专业、综合一些。
事实上,调解在我国不仅历史悠久,如曾被誉为“东方经验”,而且,实务发达,例如我们不仅有官方司法性质的法院调解、行政管理(行业)性质的人民调解、社会团体以及社会公益人士也积极热心参与各种民间调解。但总体来看,其存在诸多值得商榷甚至是改进之处。例如,从调解主体来看,虽然多元化,但专业性不足,可以利用现代理念、跨学科知识专业处理家事调解的鲜有;从调解性质来看,不管是司法性质、行业性质还是民间性质都与调解作为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第三方中立解决纠纷的基本属性不太相符;从调解的进行来看,其大多都是经验式的,较少有专业理论的指导与支撑,或者仅仅是从法律专业本身来就事论事;从调解人员的培训来看,少有专门的培训机构和专业的培训项目;从调解的效果来看,虽然成绩斐然,但从问题根本解决这一最终效果来看,尚有不足,很多案件并不能真正做到“案结事了”。对此,理论与实务中不断在改进和加强,如开始注重对调解员的专业培训、借鉴心理咨询等专业知识与技能辅助调解业务等。但我们不能仅仅认为只要加强家事调解人员的职业技能,适当借鉴心理咨询等其他学科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就能克服问题或改进不足。事实上,我们不仅迫切需要开展社会化、专业性的家事调解员队伍建设,还需要建立健全“以问题解决为中心”的调解理念,充分借鉴综合性专业理论和技能来滋养和充实家事调解服务与家事调解职业教育之实践发展。
正如有学者所言,“中国具有发展职业调解的文化土壤;社会对职业调解的需求越来越强烈;社会管理体制改革为职业调解提供了发展机遇;强大的人民调解员队伍和发达的调解事业为职业调解发展提供了人才储备。如果抓住当前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的大好时机,抓住职业调解发展的关键问题,中国的职业调解就大有可为。”[7]套言之,发展有中国特色的家事纠纷解决制度,不仅有效解决纠纷,并为法律职业教育的社会化、专业性发展提供有利的契机和广阔的前景;增强综合性与专业化,法律职业教育的社会化发展更应是大有可为!
[1]来文彬.家事调解制度研究[M].北京:群众出版社,2014:83.
[2]See CEPEJ,Guidelines for a Better Implementation of the Existing Recommendation Concerning Family Mediation and Mediation in Civil Matters,CEPJ(2007)14,p.4.
[3]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委员会立法秘书处.选定海外司法管辖区家事调解员的认可制度[EB/OL]. http://www.doj.gov.hk/chi/public/pdf/2010/med2010 0208c.pdf.
[4]See Coogler O.J.Structured Mediation in Divorce Settlement:A Handbook for Marital Mediators. Lexington,Mass.:D.C.Heath.1978.
[5]岳云(Howard H.Irving).家事调解:适用于华人家庭的理论与实践[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1-2.
[6]Lawyers and Divorce Mediation in Florida,at:http://www.fmc.ca/index.php?page=12/2009-09-09.
[7]龙飞.职业调解大有可为[N].人民法院报,2013-04-03(02).
责任编辑 秦红梅
来文彬(1978-),男,湖北麻域人,南昌大学法学院讲师,法学博士,研究方向为民商法学;陈小燕(1981-),女,湖北黄梅人,江西科技师范大学讲师,研究方向为岩土工程、家事法。
2012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纠纷解决与家庭和谐:家事调解制度研究”(编号:12YJC820046),主持人:来文彬。
G717
A
1001-7518(2015)141-0093-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