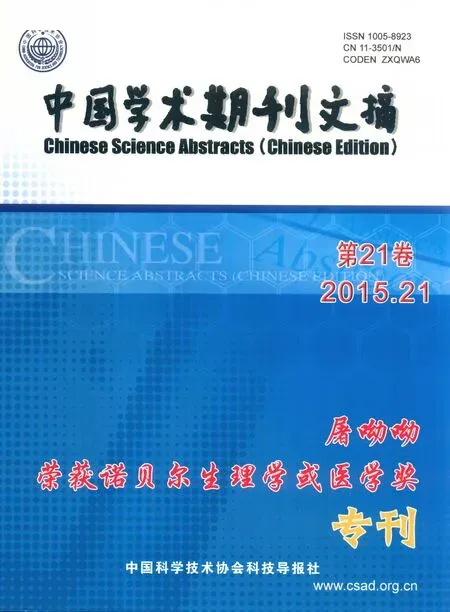恶性疟原虫对青蒿素类药物产生耐药性的全球现状和基础研究
2015-01-30赵绍敏王满元
赵绍敏,王满元
(首都医科大学中医药学院,北京100069)
恶性疟原虫对青蒿素类药物产生耐药性的全球现状和基础研究
赵绍敏,王满元
(首都医科大学中医药学院,北京100069)
根据WHO《2013年世界疟疾报告》,2012年全球约有2.07亿疟疾病例,死亡62.7万人,其中77%为5岁以下儿童[1]。在中国,疟疾主要流行于云南省境内。2009年李奔福等[2]报道云南省疟疾3163例,恶性疟占19.82%;2012年云南共报告疟疾853例,其中恶性疟9例[3]。广西、安徽、江苏和四川等省(区)也有疟疾分布。广西疟疾发病病例数仅次于云南省,2012年疟疾病例数220人,占全国发病人数的7.1%[3,4]。近年来,我国的疟疾总病例数呈下降趋势,2009—2012年,总病例数由14491大幅降至2718[3-5]。
青蒿素(artemisinin)是我国科学家从青蒿(黄花蒿,Artemisia annua)中发现的新型抗疟药物。据WHO统计,由于青蒿素类药物的使用,自2000至2012年,疟疾死亡率下降了45%,对于5岁以下儿童,疟疾死亡率下降了51%[1]。青蒿素类药物的耐药性问题早在2000年就引起了关注,虽然当时没有确切证据显示在临床出现了耐药性。但由于青蒿素及其衍生物在临床上的大量、广泛和反复应用,分别在泰国(1998)、印度(2000)和塞拉利昂(2001)出现临床疑似青蒿素抗性病例的报道[6-8]。2005年WHO在相关报告中指出要严肃面对抗疟药敏感性降低的情况,并警告很可能会出现青蒿素耐药性[9]。2006年1月19日,WHO正式发出通告,要求停止生产、销售单一青蒿素制剂或使用青蒿素单一疗法治疗疟疾,并呼吁临床医生使用复方青蒿素制剂,也就是以青蒿素类药物为基础的联合用药(artemisinin-based combinationtherapies,ACTs)。但由于疟疾多流行于经济欠发达地区,医疗水平相对落后,当地民众对耐药性的认识不全面,很多地区仍然存在大量使用青蒿素单方制剂的现象。同时,很多患者服药后,未彻底根治就停止用药等不规范治疗,又进一步加速了青蒿素类药物耐药性的产生。同年,WHO宣布在东南亚大湄公河流域的柬埔寨与泰国边境地带对青蒿琥酯的恶性疟原虫耐药性已经产生[10]。
《中国消除疟疾行动计划(2010—2020年)》的目标是“到2015年,全国除云南部分边境地区外,其他地区均无本地感染疟疾病例;到2020年,全国消除疟疾”。因此,关注该类药物耐药性的发生和发展,对制定相应的策略非常重要。
1 青蒿素类药物的应用现状
临床使用的青蒿素类药物主要包括:青蒿素、双氢青蒿素、蒿甲醚和青蒿琥酯等。为提高该类药物的疗效,降低复燃率,延缓耐药性的产生[11],WHO自2001年开始推荐使用ACTs。目前主流ACTs疗法大多都是青蒿素类药物与已经产生抗药性的氨基喹啉类药物联合应用。WHO于2010年发布的疟疾治疗新指南[12]中推荐了5种ACTs,分别为蒿甲醚+苯芴醇、青蒿琥酯+阿莫地喹、青蒿琥酯+甲氟喹、青蒿琥酯+磺胺多辛(周效磺胺)/乙胺嘧啶以及双氢青蒿素+哌喹。联合用药的实质是为了避免产生耐药性,将半衰期较短的青蒿素类药物与半衰期较长的药物联合用药。一般联用药物的抗疟机制与青蒿素类药物不同,即利用不同作用靶点的抗疟药使疟原虫的不同代谢环节受到药物的干扰,避免低血药浓度的出现,延缓抗药性产生[13,14]。
2 疟原虫对青蒿素类耐药性的全球现状
病原体从体内清除的时间是WHO衡量疟原虫对青蒿素类药物产生耐药性的基础指标[15]。若患者在服药3 d后体内疟原虫检测仍呈阳性则判定为产生疑似耐药性;若在7 d后疟原虫仍呈阳性则判定为已产生耐药性[16]。全球热带和亚热带地区90多个国家存有恶性疟流行[10],主要集中在东南亚、非洲和南美洲。其中非洲和南美洲尚未出现对青蒿素类药物产生耐药性的病例。2006—2013年,柬埔寨、缅甸、泰国、越南和老挝等地相继证实出现青蒿素类耐药疟原虫株[17]。在我国,虽然尚未报道发现对ACTs产生耐药性的疟原虫株,但在21世纪初,云南和海南曾相继报道抗蒿甲醚的恶性疟病例[18,19]。杨恒林等[20,21]分别在1989和1997年应用Rieckmann体外微量法测定云南恶性疟原虫对青蒿琥酯的敏感性,结果显示,1997年云南省恶性疟原虫对青蒿琥酯的敏感性与1989年的相比已经降低。
2.1 大湄公河流域
大湄公河流经中国云南省、老挝、缅甸、泰国、柬埔寨和越南,从越南胡志明市流入南海,最先开始确定恶性疟原虫产生耐药性的地区在泰柬边境一带,并从此处扩散至大湄公河区域。柬埔寨自2006年确诊青蒿琥酯-甲氟喹抗性病例后,2008年采用双氢青蒿素-哌喹进行替代[17]。在柬埔寨拜林市,2008—2010年,使用双氢青蒿素-哌喹治疗疟疾,3 d后体内仍存在疟原虫的患者比例从26%上升至45%[22]。自2009年以来,缅甸东南部5个省分别出现对青蒿琥酯-甲氟喹、双氢青蒿素-哌喹和蒿甲醚-苯芴醇3种ACTs组方的耐药性。2008年,泰国确认对青蒿琥酯-甲氟喹产生耐药性后,采取措施将之前的2日剂量改为3日,但在北碧府等4个地区,治疗失败率仍超过10%。2001—2010年,在泰国西北边境地区,疟原虫对药物的敏感性明显降低;经ACTs治疗后,体内疟原虫清除速度较慢的患者比例从0.6%上升至20%[23]。2013年的数据显示,22.2%的疟疾患者使用蒿甲醚-苯芴醇治疗3 d后体内仍存在疟原虫[17]。自2010年起,在使用不同组成的ACTs联合用药治疗3 d后寄生虫检测呈阳性的病例地区蔓延至缅甸的西南部、越南南部和泰国缅甸边境等处[24-26]。
泰柬边境地区也是疟原虫对氯喹和乙胺嘧啶等抗疟药产生抗性的起始地,从此处扩散至东非再至整个非洲大陆[27]。在这一地区,产生耐药性的恶性疟原虫株之所以能产生并迅速扩散,除疟原虫基因变异等内在因素外,最主要还是大湄公河流域国家医疗条件以及国情等一系列原因造成的。首先,疟疾流行地带多在丛林中或近丛林区域,受感染的也大多是一些移民和流动人口,这类人群自身对疟原虫感染的免疫力低下,且感染后不规范治疗,这在很大程度上加速了疟原虫耐药株的产生[28,29]。其次,大湄公河流域也是最早使用乙胺嘧啶和磺胺多辛等药物作为一线抗疟药的地区[30]。另外,1960—1962年,泰柬边境地区推广含有乙胺嘧啶的食盐用于烹饪,恶性疟原虫对乙胺嘧啶的耐药性随之产生[31]。最后,由于疟疾流行的区域多在各国边境地带,耐药性控制措施难以实施,致使青蒿素类药物耐药性的状况更加复杂化[26]。
2.2 非洲
截至目前,虽然在非洲境内尚未发现对青蒿素类药物联合用药产生耐药性的病例,但由于撒哈拉以南地区属于严重的疟疾流行区,产生耐药性的可能性极大,且一旦产生将很难控制,所以非洲地区的耐药性情况一直被人们密切关注。在WHO提出的全球抗击青蒿素类药物耐药性计划中,最有效控制耐药性的方法是建立全面且持续的用药监控网络。20世纪90年代,非洲出现了对单方青蒿素类药物的耐药性,非洲国家的耐药性监控网络也自那时起建立。但由于该地区政治局势复杂,医疗条件差,在2001年WHO建议使用ACTs治疗无并发症疟疾时,仍有很多国家沿用单方青蒿素类药物进行治疗,直到2004年以后,各种类型的组织机构强烈呼吁使用ACTs取代单方用药,非洲各国才逐渐采纳这一建议,并且开始重点关注疟疾的治疗,改变了治疗策略,提高一线医疗工作者的素质,并获取充足的资金用以购买药品,以确保疟疾患者能得到充分治疗。但与此同时,却忽视了对于抗疟药耐药性的系统监控。近年来,随着东南亚地区对ACTs耐药性的出现,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在非洲进行有导向、重点和全面的系统监控刻不容缓。在2004年之前,东非地区的用药监控网络得以有效实施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其迅速将研究成果应用于相关政策的制定。很多研究者认为,目前成功建立用药监控网络的关键是非洲各国的监控机构能与学术团体进行有效交流与合作[32]。
3 恶性疟原虫对青蒿素类药物耐药性的基础研究
由于ACTs的组成为青蒿素或青蒿素衍生物与哌喹、甲氟喹等氨基喹啉类抗疟药联用,因此研究耐药性机制时需要区分是对青蒿素类药物还是对联用药物产生耐药性。而实际上,大量研究表明,联用药物耐药性的产生被认为是青蒿素类药物产生耐药性的前提条件。这主要是因为青蒿素类药物与其联用药物的作用并非同时进行,青蒿素类药物吸收迅速,先于氨基喹啉类药物达到最高血药浓度,更早发挥药效。青蒿素类药物的迅速作用和较短的半衰期一直以来被认为是疟原虫难以对其产生耐药性的原因[33],也就是说,如果疟原虫对联用药物未产生耐药性,将很难对青蒿素类药物产生耐药性。
恶性疟原虫对氨基喹啉类抗疟药物的耐药性产生机制已基本确定,在大湄公河流域,多数国家使用的联用药物主要是甲氟喹、本芴醇和哌喹等。疟原虫基因片段pfcrt和pfmdr1上的基因变异会影响对甲氟喹和本芴醇的耐药性。虽然哌喹的耐药性机制尚未明确,但由于其结构与氯喹相似,所以推测基因片段pfcrt和pfmdr1上的基因变异也会导致对哌喹耐药性的产生[34]。2010年,Folarin等[35]开展的研究表明,pfcrt和pfmdr1基因的多态性与阿莫地喹的耐药性有关。
恶性疟原虫对青蒿素类药物的耐药性产生机制一直是各国研究者关注的热点,但由于青蒿素类药物的作用机制尚不明确,所以耐药性产生的机制就显得更加复杂。随着研究的广泛开展和深入探究,几种与耐药性产生相关的原因也逐渐被发现。疟原虫导致传统抗疟药产生耐药性的基因片段pfcrt和pfmdr1上的基因变异也会影响对青蒿素类药物的敏感性。1999年,Price等[36]在对泰国西部边境地带的恶性疟原虫开展的研究中发现,导致恶性疟原虫对甲氟喹敏感性降低的pfmdr1基因片段变异也会影响其对青蒿素类药物的敏感性。Fidock等[37]的研究结果显示,引起对氯喹敏感性降低的pfcrt基因上的突变会提高对青蒿素的敏感性。但2006年Afonso等[38]报道,经筛选得到的具有稳定遗传性的青蒿素、青蒿琥酯抗药株与敏感株进行比较发现,pfmdr1、tctp、cg10和atp6等基因既无遗传突变,也无基因拷贝数目的增加。随后,研究者启用分子标记的方法监控青蒿素耐药性的传播。2014年的一份研究报告表明,变异的K13-螺旋体基因片段对青蒿素类药物的耐药性产生起决定性作用[39]。此项研究成果不仅可以对大湄公河流域耐药性情况的大规模监控提供帮助,同时,对今后研究其他与青蒿素类药物耐药性相关的基因也有深远意义。除基因突变的原因外,由于青蒿素类药物产生耐药性的判断标准是疟原虫体内清除率,而体内疟原虫密度越高,其清除时间就越长,所以体内疟原虫的高密度也是导致其耐药性产生的原因[40]。
4 结语
控制与避免青蒿素类药物耐药性的蔓延迫在眉睫。诊断的及时性,治疗的有效性,传染媒介的控制和疟原虫配子体的消除等因素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耐药性的产生。其中,控制传播媒介属于较为直接有效的措施之一,且成本较低,便于开展实施[41]。具体的防控用具包括蚊帐、灭蚊喷雾以及杀虫器具。通过这些用具的发放,在越南中部,柬埔寨等地区有效的控制了传播媒介[42]。
WHO建议的措施主要为常规耐药性监控。在WHO最新发布的“针对大湄公河流域青蒿素类药物耐药性的紧急应对”[43]一文中,明确提出了针对包括柬埔寨、越南、缅甸和泰国在内的4个耐药性高发国家的具体控制措施。这些控制措施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1)为移民人口提供及时的就医途径,具体措施包括训练具有诊断治疗疟疾能力的志愿者,以及提供免费的治疗等;2)通过控制按蚊繁殖、提高个人防护从而控制耐药性疟原虫株的传播;3)快速检测已有症状的疟疾病例,从而确保治疗和清除疟原虫配子体的有效性;4)通过筛查等手段检测无症状感染者。
青蒿素类药物耐药性的现状不容乐观,疟疾流行国的国情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各项措施的开展。想要有效遏制恶性疟原虫耐药性的蔓延,仅靠基础研究是不够的。因此,科学、政治和经济领域的系统合作就显得十分必要。在科研方面,研究方向主要应集中于:1)开展疟原虫体内清除率的研究,2)开发体内外疟原虫检测的新方法,3)探索新的抗性蛋白标记物,4)研究新的有效杀灭疟原虫并阻断其在按蚊体内发育的治疗方法[24]。在政治方面,各流行国政府的公共卫生部门应在WHO的正确引导下,通过有效的政策支持开展抗疟工作,同时应加强耐药性的实时监控。在经济方面,医药产业也应同样纳入到遏制耐药性产生或蔓延的行动中。除此之外,来自全世界的人道主义组织、慈善机构的经济援助也必不可少。
伴随着全球气候变暖的趋势,热带病开始向温带蔓延,疟疾的发病率呈现出抬头趋势。全球气候变暖所带来的气候变化对蚊虫北移带来可能性,致使疟疾流行区扩大。同时,气候变暖可使原疟疾流行区传播季节延长,使疟疾流行程度增高。加强合作是不断被各界学者提及的一个词汇,它除了代表世界发展的总体趋势外,在抗击耐药性的工作中也有现实的意义。标准化收集、分析、共享数据样本,能够使纷繁复杂的关于青蒿素类药物耐药性的研究更加系统化;同时,合作还可以提高研究方法的质量控制和质量保证,从而避免对于耐药性产生的误报。正如WHO报告中阐述的一样:“强有力的政治支持,跨学科跨领域的合作,不断完善的医疗体系,疟疾流行国的经济发展以及持久的经济援助,青蒿素类药物耐药性的蔓延终将得到有效控制”。
摘编自《中国寄生虫学与寄生虫病杂志》2014年32卷5期:380~384页,图、表、参考文献已省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