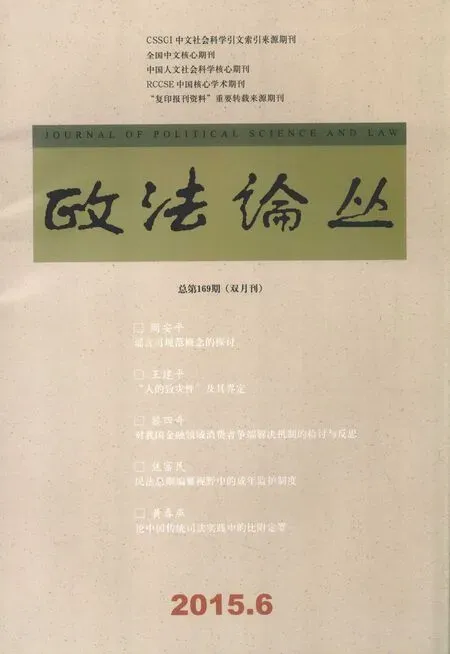从立法权更迭看埃及的政治危机*
2015-01-30贺鉴
贺鉴
(西南政法大学行政法学院,重庆 401120)
从立法权更迭看埃及的政治危机*
贺鉴
(西南政法大学行政法学院,重庆 401120)
穆巴拉克执政末期,埃及出现严重的政治危机,有关修宪权与修宪程序的争议引发广泛关注。2011年“颜色革命”后,埃及立法机关屡次更迭,由原世俗的人民议会转移至权威的军方政权,后又落入宗教团体控制的舒拉议会手中。可见,埃及政局的动荡伴往往随着立法权的流转和立法机关的变更。从立法权更迭的现象,能够发掘埃及政治变革中的基本矛盾,亦能探析影响未来政局走势的关键因素。
立法机关 人民议会 舒拉议会 埃及变局
穆巴拉克执政末期,埃及出现严重的政治危机,有关修宪权与修宪程序的争议引发广泛关注。2011年“颜色革命”后,埃及立法机关屡次更迭,由原世俗的人民议会转移至权威的军方政权,后又落入宗教团体控制的舒拉议会手中。由此可见,立法权和立法机关的更迭,是埃及变局中最为重要的一环,它成为了埃及局势变革的风向标,也最能够体现埃及动荡的阶段特征,应当引起相关学界的关注。
立法权通常有广义和狭义两层含义。广义的立法权包括制定和修改宪法的权力、制定和修改普通法律的权力、授权行政机关制定法规的权力等。而狭义的立法权则专指宪法确认的,制定部门法律和普通法规的权力。本文采用广义的立法权。无论是制宪权还是修宪权,它们的享有者都应当是人民。可是,在政治危机或社会革命等特殊时期,制宪权通常由军人政权、政变领袖或强势政党来行使。他们成立政治会议等特别机构,以全体国民的名义,依据法理和革命形势,或委托专人、或委托专门机构,修改与制定新宪法,后交由全民公投、正式生效以重新确认国家结构与公民权利,再次分配各阶层和各政党的政治利益。在持续三年多的埃及政治危机中,围绕宪法的废止、修改和制定等问题,反反复复困扰并影响着埃及政局的稳定与走势。各时期执政者对宪法与法律的关切与垄断成为了埃及政治危机中的关键要因。
(一)埃及“永久宪法”对立法权的规定
在穆巴拉克执政的30年中,以“永久宪法”为核心,埃及确立了一套完备的总统制政体。按照宪法规定,埃及的议会下院,即人民议会,拥有类似于西方总统制国家议会的绝大部分权力,主要职责是主持制定和修改宪法,决定国家总政策,批准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及国家预算、决算,并对政府工作进行监督。议会向国家元首负责,议会与国家元首、政府、最高司法机关、宪法监督等机构之间保持良好的沟通和互动关系。埃及人民议会下设18个机构,第一个就是“宪法与立法事务委员会”。这些规定表明,作为最高立法机关,埃及的人民议会能够制定、修改、通过或废止法律。同时,它也是唯一的立法机关,与之相对应的议会上院,即舒拉议会(协商议会)仅仅是为尊重伊斯兰教的国教地位,依据伊斯兰宪政的原则而设立的国家重大事务或立法建议的讨论、协商机构,其本身不具备立法权。虽然,在2007年3月26日穆巴拉克的修宪中,增加了协商会议的立法职能,使得埃及议会制真正从“一院制”改为“两院制”。[1]P10但是,它仍不能独立的行使立法权,其立法协商的建议必须得到人民议会同意,才获效力。
然而,埃及的宪政制度不简单等同于美国三权分立制衡的总统制,在穆巴拉克强大的威权统治下,埃及总统权力过大,并且总统选举与议会选举相互分开进行,这就造成了政府的更迭时常由总统定夺,与议会大选中政党席位分配和变更毫无关联。在埃及,经公民投票产生的国家总统,虽在法律上向全体公民负责,却不向议会负责,埃及总统甚至可在无须经议会同意的情况下,随意任免高级官员。在必要时,也可以经人民公决,获绝对多数的赞同票后,解散议会。因此,在立法权上,埃及总统享有非常大的自主权,“在议会休会或被解散期间,如需必要,总统有权作出具有法律效力的决定;必要时,在特殊情况下,总统受三分之二以上议员之托,能颁布具有法律效力的政令。”[2]P427事实上,穆巴拉克执政末期,通过多次修宪将总统权力无限扩充,导致了议会权力在理论和实践上都相对不足,且时常受到总统的干预和指示,使得“立法权实际上仍被总统所控制”,出现了“总统独大、议会弱小”的局面,总统享有紧急立法权;总统享有一般立法权;总统通过影响人民议会议员的构成,间接执掌立法权。例如,穆巴拉克最后一次修宪连任时,“民族民主党赢得了议会90%的席位,然而,反对派和无党派候选人的份额,由2005至2010年时的24%缩减为当前不到10%。”[3]这表明,穆巴拉克及其民族民主党实现了对议会的高度垄断,将立法权牢牢控制在手中。
(二)穆巴拉克通过议会掌控立法权
基于上述分析,埃及的最高立法机关人民议会长期被执政党和总统所控制,导致了立法不公和修宪扩权的现象时有发生。因为,“执政党完全垄断立法程序将意味着议会中的少数派在未来的五年中极易失去立法的监管作用……这不可避免地导致了一个问题,即,议会能否真实地代表选民的实际偏好和政治选择。它将会缺失对合法性的普遍认可,而这种认可来自于公平和透明的选举。”[3]例如,在2005年,穆巴拉克为了缓解诟病多年的“一人参选”现象,于2月26日发动修宪,组织对现行宪法进行修正,提出“为各政党提供参加总统选举的机会,确保总统候选人不止一人,允许多名候选人参与总统选举。”但其结果,仍然是穆巴拉克本人从10名总统候选人中脱颖而出,第四度高票连任埃及总统,其余候选人则因为政党在议会的席位不足而沦为“多党制选举”的陪衬。又,在2007年,为缓解因“连选连任”而带来的执政危机,并压制崛起势头良好的穆兄会,穆巴拉克第二次提请修改宪法,“加强对公民权中平等、自由的强调,禁止以宗教信仰的不同而加以区别对待;维护多党制,禁止在宗教基础上成立政党;加强议会对政府的监督作用;增加协商会议的立法职能;立法保护公共自由,打击恐怖主义。”[4]P10最终,自“永久宪法”颁布以来,修改幅度最大的一次宪法修正案,在穆巴拉克及其政党对议会的强大控制之下,以75.9%的得票率获全民公投通过。
因此,在穆巴拉克时期,依据宪法和法律,埃及的立法机关名义上为人民议会(议会下院),但由于总统享有紧急立法权和民族民主党对人民议会的垄断,埃及的立法权实则掌握在穆巴拉克及其领导民族民主党手中。穆巴拉克总统对立法权的垄断,对行政权的集中,导致了埃及出现“长老统治”、司法腐败屡见不鲜,穆巴拉克家族的执政激起民怨。最终,“颜色革命”浪潮席卷中东,穆巴拉克被迫在2011年初“1 ·25政变”后辞职,随后身陷囹圄。
二、变局后军方对立法权的攫取与穆尔西时期立法机关的新特征
(一)军方暂时中止“永久宪法”控制局势
2011年初,穆巴拉克在示威和抗议中宣布辞职,军方开始全面接管埃及国家事务,直至新的民选总统产生。为了肃清穆巴拉克及其政党对宪法、特别是立法权的影响,缓和民众对政府的矛盾。国防部长坦塔维领导的武装部队最高委员会宣布暂停适用“永久宪法”,解散由大量民族民主党成员所组成的立法机关人民议会,并任命8人宪法修改委员会,提出修宪草案,着手对穆巴拉克时期“总统过于集权”的宪法进行修正。此时,埃及的立法权和立法机关发生了变化,军方作为特殊局势下的接管者,暂时获得了修宪立法的代理权。2011年2月26日军方颁布了由11项议题组成的宪法修改草案:修改了“永久宪法”第75、76、77、88、93、139、148、189条,共8条;废止“永久宪法”第179条有关反恐主义的条款;制定新条款第189条和新结语,共2条。该修宪声明旨在放宽总统参选资格,限制总统任期为4年且不得连任两次,防范总统滥用权力,加强选举监督和司法裁判权,规范制宪和修宪的法定程序等等。最终,变局后的首部修宪草案到了埃及民众的认可,在1800万人参与的公投中,有近1400万人赞成军方公布的宪法修改草案,投票率达到41.19%,成为变局后三次宪法公投中,获投票率最高一次。可见,军方借助埃及的混乱局势,重回政治舞台,通过解散人民议会、中止适用“永久宪法”、提出修宪声明,争夺立法的主导权,从而控制宪法的修改朝着有利于军方的方向发展。
然而,局势在2012年6月发生了转变。随着自由与正义党和萨拉菲派光明党为主的伊斯兰政党赢得人民议会超过70%的席位,穆兄会下属的自由与正义党成为人民议会的第一大党,该党主席穆尔西在总统选举中获得51.7%的选票,以微弱优势击败前总理沙菲克,成为埃及历史上首位“民选总统”。因此,按照军方的修宪草案,负责政权过渡的武装部队最高委员会,应当依规定把立法权交还给议会,并在2012年6月30日前向当选总统穆尔西全面交权。但是,民选总统穆尔西及其伊斯兰派别的政治盟友,借助当选的势头,牢牢控制着上下议会的多数重要席位,并就立法权的争夺与军方展开拉锯战,企图利用日渐扩大的总统权力,联合伊斯兰政治团体,排挤并削弱准备将立法权交还给议会的埃及军方。此时,面对立法权流转的危机形势,一贯自认为是民族优秀势力代表的军方,在6月18日突然发布宪法补充声明,要求解散刚刚完成选举的议会,并将立法权暂时收回武装部队最高委员会手中。
(二)军方颁布补充宪法声明攫取立法权
此次军方颁布的63条补充宪法声明针对性极强:一方面,为了解决制宪委员会的争议,树立军方特权,规定:“如果现有的制宪委员会因某种原因不能完成任务,军方将在一周内组建新的宪法起草小组,3个月内完成宪法起草,然后15天内付诸公投。”另一方面,为了解决埃及议会及其立法权(制宪权)的争议,避免当选总统穆尔西及伊斯兰党派对人民议会立法的操控,武装部队最高委员会主席坦塔维向议会下发决定,告知其最高宪法法院认定议会选举无效的判决,要求解散议会,通过补充宪法声明规定:“新宪法通过后的一个月内,举行新的人民议会选举。在新人民议会(议会下院)选举产生之前,埃及武装部队最高委员会将行使立法权。”可见,军方寄希望于颁布补充宪法声明强行霸占立法权(制宪权),最大限度地维护军方利益,保障军方在埃及宪政革命中的核心地位。显然军方的补充宪法声明,是出于时局所迫,埃及武装部队最高委员会不希望让出因局势动荡而从人民议会攫取到的立法权,更不希望丧失对国家最高权力的垄断地位。因此,颁布补充声明、强占立法权、解散议会的做法,遭到了穆兄会领导下的自由与正义党以及部分宗教派别的反对,他们利用穆尔西的政治权力和宗教背景,大肆鼓吹用全民公投来决定议会的解散与宪法的修改。在变局过去的一年之中,军方先后颁布修宪草案和补充声明,并针对立法权的归属问题展开反复争夺,这既凸显出军方在埃及宪政革命中的权威地位,又表明立法权的争夺才是埃及变局中各派别追逐的核心利益。然而,通过全民公投而走向政治前台的伊斯兰政党和穆兄会势力,在穆尔西当选之后显露出其本性,他们利用埃及总统的巨大权力,开始推动埃及宪政改革走向宗教化的道路,并企图排除一切世俗和军方势力的干扰。就在军方补充声明颁布后的一个星期,6月25日民选总统穆尔西宣誓就职。随后,在8月12日宣布废止军方补充宪法声明,取消军方特权,重夺议会的立法权,并下令国防部长、武装部队总参谋长及其他几位上将退休,通过人事的变动和任免,实现军方领导“大换血”,以控制军界。至此,穆尔西及其宗教势力与军方领导下的世俗势力之间,就埃及立法权的争夺进入白热化,这次总统对军方的“清洗行动”,虽然能使其独揽行政与立法大权,但对日后的立宪活动造成了消极的影响,也埋下了未来埃及政局动荡的隐患,酿成了2013年夏军方与穆兄会冲突的恶果。
(三)穆尔西赢得选举控制行政权与立法权
如前所述,在新的议会选举中,以穆兄会为根基的自由与正义党在人民议会(议会下院)和协商议会(议会上院,又称“舒拉议会”)分阶段选举中,分别赢得了47%和59%的席位,自由与正义党成为埃及议会中居于压倒地位的第一大党,人民议会议长、协商会议主席以及议会中的重要委员会主席职位均由该党议员担任。可见,秉承伊斯兰主义的宗教派别已经在新一届的埃及议会上下两院中占据了2/3以上的绝对优势。这使得穆尔西时期的立法权和立法机关出现了新特征——“舒拉议会”(协商议会)由原来宗教性质的参政协商机构变成了具有立法职能的权力机关。穆兄会及伊斯兰党派可以通过把持舒拉议会和制宪委员会,从而控制着新宪法能够朝着伊斯兰化的目标起草。
穆尔西当选以来,先后调整军界、政界和司法界的主要负责人,获取了强大的行政权力,同时颁布宪法声明,企图利用宪法性文件的权威重掌埃及的立法权。2012年11月22日,穆尔西第一次颁布宪法声明:首先,极力扩充总统权力。规定“所有总统令、宪法声明、法令及决定在新宪法颁布和新议会选出前都是最终决定,任何方面无权更改。”藉此,穆尔西解除并任命了新的总检察长,获得了部分司法和立法权;其次,保障舒拉议会的特权。宣布“将制宪委员会工作期限延长至2013年2月12日,并称任何司法部门无权解散协商会议(舒拉议会)和制宪委员会。”[5]P10表明,穆尔西明确保障负责草拟新宪法的制宪会议和舒拉议会免遭解散,牢牢控制立法权,从而间接影响司法权。但是,总统能否利用宪法声明对自身授权,干预立法权和司法权,这本身也存在着合法性与合宪性的争议。最后,在伊斯兰化的宪政改革下,穆尔西时期的立法机关发生了改变,由大量穆斯林成员所组成的“舒拉议会”被赋予了立法权。“舒拉议会(议会上院)在2012年穆尔西宪法中,显然被指定具有立法权。或者,至少其成员明显认为他们已具备了立法权。”[6]然而,在埃及的宪政体制中,议会由上下两院组成:人民议会为议会下院,是埃及传统意义上的立法机关,享有最高立法权;协商议会(也称“舒拉议会”)为议会上院,它是1980年修宪中设立的机关,当时规定在人民议会之外,增设“协商会议(舒拉议会)”,改议会的“一院制”改为“两院制”,但协商会议的性质只是政治和立法咨询机构,不具有立法权和监督权,它可对重大问题提出意见和建议,后交由人民议会定夺。在2011年“1·25政变”以后,埃及协商议会共有270个席位,其中180席通过选举产生,剩余90席由国家元首任命,其成员包括各阶层、各机构和各派别的代表,每届任期6年,3年改选一半委员,可连选连任,也可再次任命。
(四)新宪法规定舒拉议会为立法机关
在2012年穆尔西宪法的起草过程中,舒拉议会成立了专门审议立法草案的11人委员会,而且众党派纷纷向舒拉议会提交各自的立法建议以供讨论。最终,当地时间2012年12月26日,新宪法在埃及舒拉议会(议会上院)中获得审议通过。据新宪法的相关规定,由伊斯兰团体主导的舒拉议会32年来将第一次执掌立法权。随着穆尔西新宪法以63.8%的得票率获公投通过,新宪法浓厚的伊斯兰色彩开始显现,这使得原本作为宗教协商机关的舒拉议会被赋予了新的职权。它能够单独行使“通常由议会上下两院联合行使”的立法权。一方面,确定舒拉议会具有立法权。新宪法第131条规定:“在众议院(议会下院)解散的情况下,舒拉议会(议会上院)可以执行其联合立法的职责。在众议院(人民议会)解散时期,任何由舒拉议会通过的法案应当在新的众议院(人民议会)召集之前尽快提交考察。”另一方面,确定特殊时期下,舒拉议会具有完全地立法权。新宪法第230条规定:“在新的众议院(议会下院)完成选举之前,现有舒拉议会应当承担‘完全的立法权’。在新的舒拉议会选举后,完整的立法权应当在众议院会议开始后6个月内被转移至众议院。”
至此,在穆尔西新宪法的框架下,埃及的立法机关发生了改变,原立法机关人民议会(议会上院)在争议中反复开闭,而舒拉议会(议会上院)则首次独立的享有立法权。但此举遭致了埃及众世俗派和反对党的强烈抵制,以全国拯救阵线等为代表,他们将继续反对舒拉议会行使立法权,反对新宪法的合法效力,反对埃及走向伊斯兰化的改革路径。所以,即使舒拉议会(议会上院)能够避开那些有关司法权与立法权的争议,但是其制定的法律还必须通过世俗政治的阻碍。因为,所有的法律必须提交至即将完成选举的议会下院(人民议会)。内阁议员(议会下院)的不作为,事实上会默许并导致在舒拉议会(议会上院)上通过的法律将持续有效。然而,倘若议会下院(人民议会)拒绝承认舒拉议会上通过的法律,那么这个决定将具有溯及既往的效力,导致更多的法律无法确定。[6]由此可见,穆尔西宪法赋予舒拉议会以独立的立法权,引发了埃及局势的不安。在2013年7月军方的“政变”中,穆尔西的总统职务被废除,新宪法亦连同废止,而埃及临时总统曼苏尔更是在5日宣布,解散由穆兄会主导的舒拉议会(议会上院),埃及再次陷入对立法权的争夺之中。
三、临时政府对立法程序的新规定及其对埃及未来政局的影响
(一)曼苏尔新宪法对立法权的新规定
面对立法权的争议和穆尔西政府伊斯兰色彩浓厚的宪法,在世俗派别和示威民众的抗议声中,军方于2013年7月4日再度干政。国防部长塞西将军突然宣布,解除穆尔西的总统职位,公布埃及政治发展的线路图,暂停使用穆尔西宪法,提前举行总统选举,最高宪法法院院长曼苏尔暂行临时总统职权,成立联合政府和专门委员会商讨修改宪法等。随后,在7月8日与20日,军方和临时总统曼苏尔先后颁布过渡时期宪法声明与共和国令,组建专门负责修改2012年穆尔西宪法的修宪委员会,12月1日“50人宪法复议委员会”完成了新宪法草案的修订。不久,新宪法草案在2014年初以98.1%的支持率获得通过。
临时政府新宪法共247条,大约五分之一的内容为新增内容,它的通过使埃及的立法活动告别了宗教色彩,再次回归世俗化进程。其中,对于立法权的归属与行使问题,新宪法作出了新的规定,尤其对于穆尔西宪法中伊斯兰舒拉议会行使完全的立法权和由此带来的教俗冲突,新宪法对此作出了重大修改:其一,“禁止以宗教为基础成立政党;改‘两院制’为‘一院制’,取消协商会议(议会上院),仅保留人民议会,并改称‘议会’”。[7]P1该规定显然是对伊斯兰势力通过垄断舒拉议会进而干涉立法的行为作出明令禁止,同时,撤销舒拉议会也意味着埃及的最高立法机关再次发生了变化,协商议会的立法权被新宪法所禁止。其二,新宪法草案第122条对法案的提出程序进行了详细规定:“共和国的总统、内阁和每一位众议院议员均有权提出法律。每一个由政府或十分之一议员提出的法案,应当由议会专门委员会提交相关的报告至议会。对于该立法问题,委员会可寻求专家意见。没有被议员提出的法案能够在被建议委员会批准许之前,提交至专门委员会。如果建议委员会拒绝该项法案,它必须给出拒绝的理由。任何被众议院拒绝的议案或法案,不得再次提出同样的立法请求。”该条款阻止了穆尔西企图利用人民议会(议会下院)的关闭,而将立法权赋予舒拉议会(议会上院)的做法,消除了埃及立法伊斯兰化的倾向。其三,确定最高宪法法院是立法的监督机关,使之成为“被授权对法律是否符合宪法而实行司法监督的机构。”最高宪法法院是在总统的批准下,由上诉法院的高级法官和著名学者组成。他们对审查法律是否符合宪法具有专有管辖权,并且审理新通过的法律条文是否与宪法相抵触,普通法院和行政法院、议会会员如果认为有关法律条文不合宪法,也可以向最高宪法法院提起诉讼。最高宪法法院审理后,认为法律条文确实违反宪法,可以判决撤销,普通法院、行政法院都应当执行。此外,还允许最高宪法法院对破坏人权、宗教信仰、性别歧视的行为进行监督。所以,“最高宪法法院被放在了一个强有力的位置,即,监管者、仲裁者以及对新宪法模糊原则的有效定义者。”[8]综上,曼苏尔新宪法中的相关规定,弥补了穆尔西时期立法权和立法程序混乱的缺陷,还为法律的制定明确了监督机关,保障了宪法的权威,因此,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
(二)立法程序新规定引发的争议
新宪法对立法权和立法机关的规定,体现出了世俗势力在此次修宪中的主导地位。一方面,取缔由宗教人士控制的埃及议会上院(舒拉议会),剥夺穆尔西时期通过宪法而赋予舒拉议会的独立的立法权,消除立法的伊斯兰化倾向;另一方面,改“两院制”为“一院制”,保留人民议会,并改称“议会”,重新确定议会才为唯一的立法机关,维护埃及宪政改革走向世俗化的道路;此外,还规定了严格的立法和修宪程序,并再次赋予最高宪法法院以立法监督权和违宪审查权,以此保障立法的公正、公平与公开。然而,由于大量条款的世俗性和立法权力机关的变更,导致临时政府新宪法在全民公投前后,招致了包括穆兄会在内的十余个伊斯兰党派的强烈反对,作为回应,临时政府总理贝卜拉维则宣布穆兄会为恐怖组织。可见,宗教派别对宪法的抵制,还是带来了一些消极影响,从新宪法仅38.6%的投票率可以折射出埃及的教俗分歧依旧存在,有关立法权的争夺还在继续,政治危机的隐患仍未消除。随着新宪法公投的通过,埃及也许能够在军方的武力威慑和世俗势力的协商合作下,暂时实现短期的和平与稳定。但是,这种安定仍不会长久,因为总统大选先于议会选举,这使得新宪法规定的“议会有权罢免总统,而总统却无权解散议会”成为了泡影。国防部长塞西在军方的授意下,辞去军职并当选为埃及新总统。那么,他是否会重现穆巴拉克时期总统通过干预议会从而影响立法权的现象,这种猜想不无可能。
(三)未来局势预测——“长老统治”与“民主选举”的博弈
自2014年7月3日塞西当选总统以来,埃及局势趋于稳定,在军方强大实力的笼罩下,塞西不仅获得了较高的支持率,其执政基础也日益牢固。然而,被罢免入狱并经历多次法庭审理后的首位民选总统穆尔西却在2015年5月16日被埃及开罗刑事法院以“越狱罪”判处死刑。穆尔西连同多名穆兄会高官等106名被告被判死刑,引发了轩然大波。对新总统塞西而言,他接手了一个经过三年社会革命、早已千疮百孔的埃及。军方、世俗派别和穆兄会对立法权的争夺拉锯战让宪法的权威大为削弱,多次选举和公投及其带来的混乱让公民的政治参与度大大下降,丧失政治热情的青年群体很难成为国家恢复安定发展的主力军,宪政变革与民主建设更是在大步倒退。面对这样一个“烂摊子”,公众的社会心理早已厌乱,也许他们不会有太久的耐心来协助塞西将国家带回上行的轨道。此时此刻,摆在塞西面前的是一个经济萧条、社会混乱、民生凋敝、教俗分歧、民主缺失的埃及。塞西是否有足够的政治智慧解决上述问题并缓和立法权争议下的阶级矛盾,我们拭目以待。短短四年的任期,倘若能够尽快恢复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国民生活的稳定,塞西将会成为埃及乃至整个阿拉伯世界的铁腕总统。另一方面,三年的政权轮回告诉我们,埃及民众再次选择了强人统治下的国家稳定,而塞西究竟会成为长老统治的继任者,还是埃及民主选举的开创者,答案将在八年后揭晓。遥望2022年,现年60岁的塞西将会面临艰难的选择,是像穆巴拉克那样牢牢控制立法权,操控立法机关以修改宪法谋求连选连任,沦为埃及的“新法老”,以“长老统治”的方式在民众的积怨中老去,还是像美国“国父”华盛顿那般尊重宪法与宪政,接受两届任期的限制,在民主选举的光环下全身而退,成为埃及的“民主之父”?不论上述哪一种结局,我们所期待的,是埃及民众能够从革命的轮回中走出来,让立法权真正地交由人民及其代议机关行使,逐渐恢复经济、稳定社会、改善民生,重拾地区性大国的信心。毕竟,安定的社会秩序、团结的国家氛围、充分的民主自由才是埃及宪政变革的最终目标。[9]
四、由穆尔西的死刑判决引发的几点思考
(一)穆尔西的死刑判决体现了世俗派执政者对宗教派别的打压和限制
对穆尔西的死刑判决与近年来针对宗教团体的大面积死刑判决一样,其本质仍然是执政者对立法权与司法权的高度垄断和控制。一方面,开罗刑事法院认为“1·25革命”中穆尔西与多名穆兄会领导人、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及黎巴嫩真主党成员策划并实施了瓦迪·奈特伦监狱等三座监狱的越狱事件,导致50多名警察和囚犯死亡、超过2万名囚犯逃走,并造成大量财产损失。此外,还有一百余参与实施越狱行动的穆兄会领导人也一同被判处死刑。[10]另一方面,自塞西执政起,针对宗教人士和穆兄会成员的死刑判决就不绝于耳。期间,埃及地区法院曾分别判处529名前总统穆尔西的支持者死刑、683名穆兄会支持者死刑。在这场针对穆兄会的司法报复行动中,埃及当局已经拘留了超过1.6万名穆兄会的支持者。可见,近期对穆尔西的死刑判决与去年大面积针对穆兄会的死刑判决如出一辙,实乃以塞西为首的世俗派执政者对宗教派别的打压和限制,其本质就是通过垄断埃及立法权,用修宪立宪和颁布社会秩序特别法的方式提升军方及世俗政权的统治地位。同时,以控制国家司法权的手段干预和指导司法审判实践,从而达到排挤和威慑宗教政党与反对派的最终目的。
(二)穆尔西死刑案的相关程序充分体现了教俗分歧与冲突
从穆尔西死刑判决的二审程序、上诉程序和刑罚执行等来预测,埃及的司法制度将依旧体现出强烈的教俗分歧与冲突。首先,开罗刑事法院对穆尔西的死刑判决是一审宣判的结论,其判决书将提交至埃及宗教领袖穆夫提以征询其意见,而穆夫提则可依据沙里阿(伊斯兰教法)的原则和内容对穆尔西的死刑判决提出二审的改判意见(就像去年那些大面积针对穆兄会的死刑判决得到穆夫提改判一样)。这将会是塞西世俗政权与伊斯兰宗教势力在司法活动中的第一次正面交锋。其次,经过征询宗教领袖穆夫提的审理建议后,开罗刑事法院将于6月2日再次开庭宣判,这将再次引发法庭外教俗阶层的第二轮社会冲突。再次,即使二审维持了穆尔西的死刑判决,那么根据法律,穆尔西仍有提出上诉的权利,经过上诉法院的重审,埃及最高法院方能做出最终的裁定,这会是执政者与宗教反对派的第三次司法交锋。当然,由穆尔西的司法审判而引发的三轮教俗冲突也可能进一步扩大化,从而足以警醒总统塞西,使其产生赦免穆尔西退而求稳定的想法。可见,穆尔西司法审判和死刑判决的未来走势将会是新一轮教俗分歧与冲突的导火索,也是世俗执政党与宗教在野派别关于立法权与司法权争夺的延续。
(三)穆尔西的死刑判决有可能使埃及社会矛盾和教俗矛盾进一步激化
因穆尔西的死刑判决引发针对法官的暴力袭击事件表明,新一轮的小幅政局波动在所难免,但本质上仍不会改变塞西已牢牢控制的立法权和日趋稳固的执政根基。这场针对穆尔西及穆兄会的司法裁决极有可能破坏当前稍显稳定的埃及局势。于是,在宣判穆尔西死刑后仅两个小时,埃及北西奈省首府阿里什市即发生法官遇袭事件。这便是死刑判决所导致的第一波暴力反抗塞西政权的事件,它有可能成为埃及社会矛盾和教俗矛盾激化的新开始。相比以往宗教极端组织的暴力报复行动,他们大多将安全部门和执法警察作为恐怖袭击的对象,很少对司法人员和法律工作者进行武装袭击。可见,对穆尔西的死刑判决很可能是造成这一局势新波动的主要原因。当然,被认定为“恐怖组织”的穆兄会及其领导下的“支持合法性全国联盟”将继续从事声援穆尔西和宗教团体的游行示威活动。但是,在强大的军方威慑力和牢固掌控的立法权下,穆兄会已在今后一段时期内失去发起大规模游行和破坏活动的能力。这些小规模抗议将不会对塞西政权产生太大的冲击。加之,曼苏尔过渡政府曾颁布的《抗议法》,让内政部门有权拒绝公民在公共场所的集会、游行及和平示威等行为。这一切将使埃及局势在新一轮的小幅波动下,继续朝有利于塞西和世俗派的发展道路前进。
(四)穆尔西的死刑判决表明埃及政局缺乏政治妥协和民主协商精神
对比穆尔西与穆巴拉克的司法审判与结局可以发现,埃及统治者依旧保留着浓厚的教俗派别对抗观念,缺乏一种政治妥协的艺术和民主协商的意识。作为第五任也是埃及首位民选总统,穆尔西在2013年7月3日被解除职务并受到多项罪名指控而遭持续拘押。2014年1月穆尔西接受审讯被控逃狱、藐视司法制度、煽动示威和损害国家利益这四项罪名。2015年4月21日,埃及法院以对杀害抗议者负有责任为由,判处穆尔西20年监禁。2015年5月16日,埃及刑事法院则以越狱罪等罪名判处其死刑。然而,对比穆巴拉克的审判,却呈现出另外一番景象。穆巴拉克自2012年6月被判处终身监禁,其后经历重审却不断拖延。虽然审判工作在2013年6月军方通过政变重掌政权后再次步入正轨,但2014年11月29日,开罗刑事法院判决穆巴拉克涉嫌蓄意谋杀抗议者的罪名不成立,穆巴拉克被当庭释放。他的家族腐败案也以超过十年追诉期为由不再追究其法律责任。可见,两位前总统的司法裁决形成了鲜明对比。这不禁让人反思,难道民主合法的权力运作和政治模式在埃及无法生存?事实上,这些问题不仅体现出埃及执政者对立法权的激烈争夺,更表明统治者依旧保留着浓厚的教俗派别对抗观念。不论是具有穆兄会背景的民选总统穆尔西,还是与穆巴拉克军方背景一脉相承的现任总统塞西,他们均缺乏一种政治妥协的艺术和民主协商的意识。这些缺陷将会是制约未来埃及局势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关键因素,应当被学界所关注。
综述,作为最高国家权力,立法权来源于人民的联合意志,一切人民权利的产生都是立法权的衍生。诚如孟德斯鸠的著名论断:“在一个自由的国家里,每个人都被认为具有自由的精神,都应该自己统治自己,所以立法权应该由人民集体享有。”[11]P158在当今世界各民主国家里,立法权通常交由代议机关行使,不论是西方的议会,还是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其运行模式都是让人民选出的代表来讨论和拟定法律,然后提交代议机关审议批准。倘若立法权为其它机构或个人行使,则无法体现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势必导致法律的不公平,长此以往,任何个人、团体或机构以一己私利寻求立法,这样的法律必将与人民的整体意志相违背。那么,损害人民利益的情况随时可能出现。但基于“自己不会伤害自己”的原则,立法权只有交由人民,在他们的联合意志下颁布自己的法律,这样才能够最大限度地保障法律的公正、维护公民的权益和社会的安定。故,立法权是国家最高的权利,且必须交由人民来行使。综合考察现代埃及立法权的变革历程,从穆巴拉克通过扩充总统权力进而操控立法权,到军方利用其权威反复攫取立法权,再到穆尔西通过立宪赋予伊斯兰舒拉议会独享立法权,最后到曼苏尔临时政府修宪使议会(一院制)重获立法权,其实质,乃是不同势力希望通过垄断立法权,进而编纂或修改适用于本集团利益的法律,最终奠定本集团统治的法律根基,为一些政策的制定披上合法的外衣。如前所述,立法权与国家制度密不可分,“立法权本身是国家制度的一部分,国家制度是立法权的前提。”[12]P315随着政权的更迭,为了稳固新执政、树立国家的权威,统治者往往将目光聚集与立法权的争夺上,通过立宪或修宪的方式更改最高法律中有关立法权和立法机关的规定,并将自己的政治势力安插于新的立法机关之中。比如穆巴拉克时期的人民议会,在其政党占绝对多数的情况下,行使有利于穆巴拉克的立法权;又如穆尔西时期的舒拉议会,基于穆尔西特殊的穆兄会背景,完全由伊斯兰政治团体组成的舒拉议会(议会上院),由原来的政治协商机构上升为享有完全立法权的机关,显然这种变化对穆尔西的执政十分有利,确保了其新宪法得以在伊斯兰主义的指导下完成起草。因此,对于立法权的争夺才是埃及变局中的核心问题,它成为了政治势力垄断国家政权的主要途径。当前,虽然军方已经在临时政府宪法的框架下争取了暂时的和平与稳定,但是随着军方代表塞西成功当选总统,就立法权的归属将再起争议,若该权力争议未能妥善处理,那么未来埃及的局势势必反复,甚至会走向“内战”。
[1]练育强.埃及权力移交的宪政进行曲[N].法制日报,2011-02-22(10).
[2]王彤.当代中东政治制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
[3]Amr Hamzawy.Egypt’s Legitimacy Crisis in the Aftermath of Flawed Elections[EB/OL].http://egyptelections.carnegieendowment.org/ 2010/12/02/egypt’s-legitimacy-crisis-in-the-aftermath-of-flawed-elections.(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4]洪永红,洪流.从埃及宪法考量穆巴拉克下台[N].法制日报,2011-02-15(10).
[5]练育强.总统声明再次引发埃及“宪政危机”[N].法制日报,2012-12-4(10).
[6]Nathan J.Brown and Mokhtar Awad.Egypt’s Judiciary Between a Tea Ceremony and theWWE[EB/OL].http://egyptelections.carnegieendowment.org/2013/05/16/egypt’s-judiciary-between-a-tea-ceremony-and-the-wwe.(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7]于毅,于杰飞.埃及修宪实现过渡“路线图”[N].光明日报,2013-12-4(01).
[8]Nathan J.Brown.The Egyptian Political System in Disarray[EB/OL].http://egyptelections.carnegieendowment.org/2012/06/19/theegyptian-political-system-in-disarray.(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9]张小虎.埃及政局陷入轮回塞西执政阻力重重[N].法制日报,2014-07-15(10).
[10]王云松,王会聪.美国表示“严重关切”埃及声称“司法独立”穆尔西获死刑引发埃及西方争吵[N].环球时报,2015-05-18(02).
[11][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册)[M].张雁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
[12][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M].范杨,张企泰,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
On Egypt's Constitutional Crisis from the Alternate Perspective of Legislative Power
He Jian
(Administrative Law School of Southwest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Law,Chongqing 401120)
At the end of Mubarak Period,constitutional crisis occurred in Egypt,the dispute of legislative power and procedure caused widespread concern.After the Color Revolution of 2011,Egypt’s Legislative Body alternated frequently which from People’s Assembly to Supreme Council of the Armed Forces(SCAF),then to the Shura Council controlled by religious group.Therefore,the political unrest of Egyptwas accompanied by legislative power and organization changing.In consequence,we could the basic contradiction of Egypt’s Transition from the phenomenon of legislative power change.And we could also explore and analyze the key factor of Egypt’s Situation in the future.
legislative authority;Egyptian People's Assembly;Shura Council;Egypt’s transition
DF02
A
1002—6274(2015)06—094—08
(责任编辑:唐艳秋)
一、立法权与穆巴拉克时期埃及立法权争议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北非阿拉伯国家政治发展研究”(12BGJ027)、湖南省教育厅青年项目“北非阿拉伯国家宪法变迁与政治发展研究”(12B121)、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项目与重庆市博士后特别资助项目“非洲社会主义宪法变迁及其对中国的启示”(2013M542253)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贺鉴(1975-),男,湖南绥宁人,法学博士,西南政法大学法学博士后,中国海洋大学法政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比较法与比较政治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