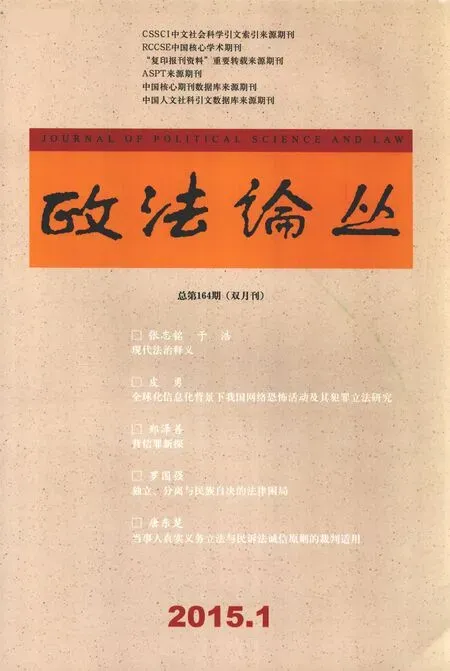适当生活水准权:当代人的基本权利*
2015-01-30李超群
李超群
(西南政法大学行政法学院,重庆 401120)
适当生活水准权:当代人的基本权利*
李超群
(西南政法大学行政法学院,重庆 401120)
《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已将适当生活水准权认定为一项基本经济权利。西方旧有的人权理论往往忽视了经济权利,而片面强调政治权利。但是,人权的本质与人的本性决定了经济权利是一项最基本的人权,适当生活水准权更是最核心的经济权利。适当生活水准权具有丰富的具体内容,也为当代人权保障事业提出了新的要求。
适当生活水准权 经济权利 《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
一、问题的提出:关于《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的争论
经过漫长而曲折的过程,《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以下简称《公约》)终于在1966年12月16日联合国大会第2200A(XXI)号决议以105票通过。该《公约》第11条将适当生活水准权认定为一项基本人权:“本公约缔约各国承认人人有权为他自己和家庭获得相当的生活水准,包括足够的食物、衣着和住房 ,并能不断改进生活条件。各缔约国将采取适当的步骤保证实现这一权利,并承认为此而实行基于自愿同意的国际合作的重要性。”然而,围绕着该《公约》与上述条款,却一直存在争论。
目前有140多个国家批准加入了该《公约》,但也有60多个国家只是签署而并未批准加入该《公约》。这本身就说明,关于经济权利是否为一项人权,国际社会还存在着广泛的争论。否认经济权利为一项基本人权,主要有如下原因:
首先,从人权发展的历史来看,人权首先是针对专制国家的。当时人们面对的首先是政治专制和政治压迫,如人身束缚、身份等级、滥用特权、奴役压迫、缺乏安全、权无保障等。在这种情况下,人们首先寻求的就是获得政治解放,享有政治权利,其根本途径就是向专制国家争取人权,用人权对抗政权,政治解放成了人权的首要使命。这直接决定了第一代人权文件的基本面貌和主要性质,即人权首先是政治权利。
其次,人权的产生和发展深受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影响。自己为自己谋利、自己对自己负责是个人主义的基本信条。意思自治、自我选择,并自觉地承担自治和选择的结果,是自由主义的基本要求。而经济权利是每个人自己的私事,应由每个人自行解决。因此,只要国家给我政治权利,如让我享有平等的机会,给我充分的自由,允许我公平地参与市场竞争,我自会获得相应的经济权利,照顾好自己和家人的生活,无需别人包括国家为我操心。如果国家给予了我政治权利,我依然不能获得相应的经济权利,那只能怪我自己无能或不幸,与他人和国家无关,我根本无权要求别人和国家对我的经济权利负责,更不能上纲上线通过诉诸人权去诉求经济权利。由于别人一般不愿意为其他人的经济权利负责,为了强迫别人这样做只能通过国家干预。而国家干预将导致国家权力的扩大和滥用,这在自由主义者看来,必然会侵犯人权,是最不能容忍的。
再次,经济权利缺乏可诉性。权利的关键在于救济,没有救济的权利是空头支票。即使确认经济权利是一项人权,也难以度量、不可操作,如人们享有什么范围或程度的经济权利才算保障了人权,实施起来就十分困难。由于《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的条款措辞模糊,国际监督机制薄弱,公约的义务主要是针对国家的,具有政治性,缺乏法律约束力,无法强制国家去履行相应的义务。这些因素导致经济权利缺乏可诉性,法院不能援引这些权利,法官也不能适用它们,因而不是真正的权利,更不能称为人权。
作为经济权利的一部分,适当生活水准权是否是一项基本人权,也存在争议。除上述否认经济权利的一般理由外,否认适当生活水准权的观点还在于:
首先,适当生活水准权是一种积极权利。根据权利的实现方式、特别是权利实现与政府义务的关系可以把权利区分为消极权利与积极权利。这两类不同的权利对应着不同的政府义务:前者禁止政府,并把它拒之门外;而后者需要并盛情邀请政府;前者需要公职人员蹒跚而行,而后者需要公职人员雷厉风行;前者的特点是保护自由,而后者的特点是促进平等;前者辟出了一个私人领域,而后者要再分配税款;前者是剥夺阻碍,而后者是慈善与奉献。[1]P23显然,适当生活水准权是一种积极权利,要求政府积极作为,如要求政府采取措施、积极干预、分配税款、举办慈善等。这与自然权利概念和自由主义是对立的,因为后者强调的是个人与政府之间的对立,认为政府权力是侵犯个人权利和自由的最大危险,要保障个人权利和自由就必须限制政府权力、排斥政府干预。
其次,不具有司法可裁决性。适当生活水准权因其“适当”标准过于抽象、模糊、任意和复杂而不具有司法可裁决性,在现实中司法机关也非常慎于受理和裁决该类案件。所以,即使在比较重视保护适当生活水准权的南非,虽然出现了一些案例,但真正具有人权意义的案例并不是很多。[2]P269如果司法机关对此类案件强行司法裁决并要求政府采取积极措施予以救济的话,就会影响到部门分权、民主机制等原则性问题,并会与政府部门发生直接冲突,从而具有反民主的倾向。[2]270
再次,保障适当生活水准权受到客观因素的制约。一般说来,只有实现了工业化、现代化和民主化的国家才能真正做到保障适当生活水准权。因此,这不是想不想保障适当生活水准权的问题,而是能否保障它的问题,是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是否达到了保障它的能力和水平的问题。与其奢谈适当生活水准权,不如切实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在Grootboom一案中,南非政府就认为,之所以不能为原告提供相应的住房,是因为为每一个申请人提供住房,必然会增加政府的财政负担,这是政府财力所不及的。[2]271
第四,福利国家政策将造成不利后果。目前许多国家没有能力实行福利国家政策,这种高福利待遇超出了许多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一些实行福利国家政策的国家已先后陷入严重的财政困难或债务危机,已不堪重负,亦将难以为继。同时,福利国家政策滋生了不劳而获、“搭便车”、好吃懒做等恶习,扭曲了社会分配公平原则,损害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等美德,打击了人们努力向上、勤劳致富的积极性。这也会违背人权的宗旨,因为人权保障的根本宗旨是使人成之为人,成为一个独立自主、自强不息、自力更生的人,而不是适得其反。
第五,适当生活水准权是西方特别是发达国家的人权概念,也是它们干涉别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和欠发达国家内政的借口或工具。它们把适当生活水准权作为一种“普遍接受的基本权利”,旨在使西方价值观念在全球得到渗透、推演和扩张。1998年,美国总统克林顿访问南非时,南非总统曼德拉曾公开批评美国等西方国家借人权问题干涉非洲国家内政并减少对非洲国家的援助。[3]P23这也可能是南非虽早在1994年就签署了《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但至今没有批准该公约的一个重要原因。
二、经济权利作为人权的理由
作为适当生活水准权的上位概念,经济权利是且应该是当代人权体系中的最基本的一项权利。
人权的本质与人的本性决定了人权具有内在的经济内容。人权是人成之为人必不可少的权利,其根本宗旨在于保障人有人格尊严、有权利自由地生存和发展。然而,人怎样才能成之为人呢?在构建西方经典人权理论时,以霍布斯为代表的启蒙思想家将自然状态设定为人的原初状态,在此状态下,各种激情与欲望构成了人的本性,而最大的激情便是自我保存。[4]P93也如马克思所指,“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而且是“有生命的自然存在物”。[5]P209因此,只有首先解决人的经济问题才能谈得上其他的一切,人享有一定的经济权利以后才能解决其衣食住行等基本问题,人才能有人格尊严地生存和发展,人才能成其为人。这亦意味着,经济权利也根源于人本身固有的人格尊严,正如《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所确认的,“这些权利是源于人身的固有尊严”。人格尊严、权利自由无不建立在一定的经济权利的基础之上,并往往以经济权利为目的。没有经济权利作基础、为目的,人格尊严、权利自由、政治权利就徒有其名。这正如美国总统罗斯福在1944年时所指出的:“我们清楚地认识到以下事实,没有经济安全和独立,真正的个人自由即不会存在。‘贫困者不是自由人’。饥饿和失业的人是被专政的要素。”[6]P124可见,对于人权保障来说,经济权利最为直接、更根本,人们不享有经济权利,就不可能真正享有人权、真正保障其人权。尽管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在出现的时间上可能先于经济权利,但在性质和地位上决不可能高于经济权利,它们应该是同等的、不可分割的。1950年12月4日,联合国大会第421E(v)号决议指出:“享有公民、政治权利与享有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两者相互联系,不容偏废”,“人如果遇到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被剥夺时,就不能体现《世界人权宣言》所确认的自由人的理想”。实际上,正由于经济权利直接关乎人的生存,并且是人权其它各项内容的基础,因此,政治权利与经济权利相比,是手段与目的、出发点与落脚点的关系。经济权利本身就是政治权利的具体内容,平等、自由等政治权利都要落实到经济权利方面,如经济平等、经济自由等。如果政治权利不能服务于经济权利,或者政治权利不能实现为经济权利,那么这种政治权利就没有落到实处。如果仅仅在政治权利的角度抽象地谈论形式上的平等和自由,并不能真正地实现人权。由于人与人之间固有的千差万别,使得人们的平等能力和自由程度有所不同,而经济上的贫富悬殊、阶层分化,正是其集中表现,久而久之,必然造成平等和自由的异化。
个人主义与自由主义不足以解释人权。虽然人权首先是个人的人权,包括集体人权最终也要分解、落实为个人人权,但这并不意味个人主义是人权的唯一根据。实质上,单个的个人无所谓人权,人权存在于人类中,存在于社会关系中。虽然人权应为人人所享有,但真正存在人权问题的是社会弱势群体,他们仅凭自己的能力和努力不能保障自己有人格尊严地生存和发展,为了使自己有人格尊严地生存和发展,他们只能诉诸其他社会成员。他们之所以有权利向其他社会成员要求人权,其他社会成员之所以有义务保障他们的人权,归根结底是因为他们和其他社会成员同属一类,都是人类的一员,他们之间有着共同的“类本质”、固有的“类意识”、不可分割的“类联系”、类似的“类生活”。人既然是同类,就应享有类似的人权,这是人权最常识而又最有力的根据。人权的根据就在于“人类”本身,“人类”超越了个人主义。从人权的保障来看,人权保障实质上是通过社会其他成员对那些凭自己的能力和努力不能有人格尊严地生存和发展的人提供援助而实现的,人权保障是通过群体的力量来实现的,如果人们各顾自己,不救济他人,就不能保障人权。所以,人权有着牢固的群体维度和内在的人类情怀。自由主义与第一代人权产生于同专制国家的斗争中,在当时,国家权力是侵犯人权的主要危险,因而只有削弱、限制国家权力才能保障人权。但是,人权与国家并不是天敌,特别是现代民主、法治国家,它们还是保障人权的重要力量。所谓的保障人权,实质上是要求社会上的一部分人去无偿地援助另一部分人,以保障他们也能有人格尊严地生存和发展。保障人权如果没有国家权力的介入和运用是实现不了的,如财政税费、转移支付、公共支出、社会保障等等是人权保障的重要举措,但它们都离不开国家的组织和国家的干预。在民主、法治的国家,受到有效制约和依法规范的国家权力不但不会侵犯人们的自由和人权,而且是实现人权保障的重要力量。
在国际人权法的实践中,经济权利已日益具备“可诉性”。如1990年通过的《保护所有迁徙工人及其家庭成员国际公约》所使用的周密明确的用语已证明,有可能以满足“可诉性”的所有要求的方式来制定有关经济和社会权利的公约条款。[7]P33此外,国际劳工组织设立了详细标准和大量解释的领域,也部分地使《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的条款更为明确。由于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与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的相互依存和密不可分,如婚姻家庭的权利、就业的权利,《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都有规定,它们具有两重性,既是公民权利、政治权利,也是经济权利、社会权利,1989年通过的《儿童权利公约》也是两组权利相互结合的例子。即使是平等权这种一直被认为是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的权利,也涉及到经济权利和社会权利,因为仅有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的平等是远远不够的,没有经济平等、存在就业歧视、不能享有平等的社会保障,就没有真正的平等权可言。这就使得可以把设在《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下的申诉机制援用到经济权利、社会权利上来。联合国人权事务委员会于1987年4月9日通过了荷兰三桩有关社会保险案件的最终意见,确立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26条所规定的“不歧视条款”也适用于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的情况。[7]P43经济权利的可诉性取决于国内立法,即国内立法是否赋予权利人以主张权利的资格,如欧洲社会权利委员会通过审查政府报告和对报告提出评论,已为《欧洲社会宪章》第13条第1款发展出了“判例法”,它强调缔约国须保证事关医疗和社会帮助的行政决定时,当事人可诉诸法院或其他独立机构。[7]P43就国际监督机构来说,有经济和社会理事会,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委员会,它们不断地发布一般性评论并处理对该公约诸条款的解释,有助于加强《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诸条款的适用性。[7]P45
三、承认适当生活水准权的理由
适当生活水准权已被《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明确地规定为一项经济权利,因此,其在逻辑上必然属于人权的范畴。正如前文所述,经济权利之所以是一项核心人权,其根本在于,经济权利是直接针对人的基本生存之保障所提出的。而适当生活水准权,其实质是人们维持其有人格尊严地生存和发展所应当享有的生活水准的权利。可见,适当生活水准权是最为贴近经济权利本质的一项权利,理应成为经济权利的核心内容。
当然,如前文所述,也存在否认适当生活水准权的观点,否定的理由是:适当生活水准权是一种积极权利、不具有司法可裁决性、受制于客观因素等等,这些理由均不能成立,原因如下:
人权是针对政府而提出的,是人们向政府所主张的权利,政府对于保障人权负有神圣而不可推卸的责任。这种责任不仅体现为政府不妨碍、不干预等消极方面,也表现在政府作为、促进等积极方面。而且,不同的人权对政府的要求不甚相同,对于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的保障而言,它们也许更多地要求政府消极地不作为,但对于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的保障而言,它们更多地要求政府积极地作为。适当生活水准权就是如此,它要求政府积极作为以保障人们的适当生活水准。其实,决定某项权利是否为人权,根本因素不在于政府作为或不作为,而在于某项权利是否影响到人之成为人。如果某项权利影响到人之成为人,而且某项权利的保障又离不开政府的积极作为,那么政府就应积极作为以保障某项权利,某项权利就应该确立为人权。
将“无救济则无权利”的标准适用于人权,实际上颠倒了人权保障的基本逻辑。人权是一种关系到人之成为人的一种不可剥夺的权利。因此,人权必须救济,问题的关键不是有无救济、能否救济,而是应该如何救济。人权的确立不能仅仅局限于目前,更应着眼于未来,应具有一种与时俱进和不断提高的导向。即使政府现在救济不了或救济不够,并不能否定某项权利为人权,反而是要进一步完善制度,以期使该项人权得到有效救济。南非在保障适当生活水准权方面,就规定了国家具有一种逐步实现的义务,这种义务不是即时性义务,而是体现为一种“不倒退原则”,即“政府不得采取导致获取食物状况恶化的倒退政策”。[2]P270人权不仅仅是现实的写照,也是未来的期望和努力的目标。
确实,适当生活水准权的保障并不仅是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客观问题,更是社会分配体制的制度问题。阿马蒂亚·森等人的考察和研究表明,贫困不单纯是一种供给不足,而更多的是一种权利分配不均,即对人们权利的剥夺。虽然饥荒与自然灾害密切相关,但客观因素往往只起引发或加剧作用,而权利的不平等、信息的不透明、缺乏言论自由、政治体制的不民主,才是加剧贫困和饥荒、导致大规模死人的主要原因。在一个自由和民主的社会中,是不大可能发生饥荒的,因为公共意见能够确保政府采取应对危机的措施。实践也证明,“现代世界的所有饥荒的确可通过人的行为来加以预防,许多国家——甚至一些非常贫穷的国家——都坚持不懈地努力预防它们;当人们大量死于饥饿时,几乎毫无例外地都存在着某种重大的社会失败。”[8]P49-50这里就指出了权利保障对于反饥饿的极端重要性。如果把适当生活水准权确立为人权,那就更能强化社会舆论和公开社会信息,更能有效地促进社会的民主化进程、更能有力地督促政府采取防范饥饿的措施,因而实为反对贫困、防范饥荒的治本之策。
毋庸讳言,适当生活水准权是源自西方发达国家的人权概念,因为它们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较高,人们对生活水准的要求亦水涨船高,它们也更有能力保障适当生活水准权。但不能因此就拒绝适当生活水准权。人权具有普遍性,一切合理的东西都应大胆拿来为己所用,这正是国际人权公约得以存在和发挥作用的根本原因。当然,保障适当生活水准权从根本上是出于国内的迫切需要,是一个人民或民主的国家负有保障人们适当生活水准权的神圣职责。如果不能保障适当生活水准权,即使不被外国“和平演变”所颠覆,也会为内乱或内战所推翻。保障适当生活水准权,主要不取决于国外势力,而主要取决于国内努力。国家应把保障适当生活水准权看作是自己内部的事情,自觉而努力地做好,并有信心、有能力、有责任把它做好。
不可否认,适当生活水准权与福利国家政策密切相关,因为适当生活水准权是福利国家政策的基本内容,福利国家政策是保障适当生活水准权的政策措施。但两者没有必然联系,不是说只有实行福利国家政策的国家才保障人们的适当生活水准权,不实行福利国家政策的国家就不保障人们的适当生活水准权。严格说来,现代一切国家,不管是否实行福利国家政策,都应具有或多或少福利国家的性质,都应实行一定的福利国家政策以保障人们的适当生活水准权,因为各国都有义务根据自己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不断地提供和提高国民福利,为人民谋福祉是一切民主国家的共同宣言,或如我们经常所说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目的是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的需要”。尽管一些国家因实行福利国家政策而出现了财政困难和债务危机,这只能说福利国家政策还存在问题,比如福利待遇过高等,还需要改进,但这不能成为否定适当生活水准权的充分理由。在现当民主和法治社会,福利国家是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向和奋斗目标之一,福利国家政策是国家必然采取的基本政策之一。
适当生活水准权与鼓励滋生懒惰没有必然的联系,关键是要确定其“适当”的标准。该标准当然与各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密切相关,各国关于“适当”的标准也不会是一致的。但无论如何,所谓“适当”肯定不能过高,过高就不是适当,就会鼓励和滋生懒惰,一些福利国家之所以陷入财政困难或债务危机,正是因为它们所提供的保障不是“适当”而是过高,以至于覆盖了“从摇篮到坟墓”的全过程。“适当”的标准只应保持在足以维持人们有人格尊严地生存和发展的水准即可,这样就可以使寄生者与自力更生者、受救济者与施救者明显地区别开来,他们是不可能平起平坐的。只要贯彻这一原则,就不可能鼓励和滋生懒惰等不良社会恶习。
因此,否认适当生活水准权的几点理由都不过是“多余的担心”。事实上,人的生活必然需要适当的生活条件,如衣食住行,这些生活条件切实关系到人能否成之为人,因而成为人权关注和保障的核心内容之一。人应该享有适当生活水准权,适当生活水准权是最低限度的人权,也是最低限度的经济权利。要保障人权、保障经济权利,首先就要保障人的适当生活水准权。各项经济权利乃至各项人权,最终都要归结为或落实到适当生活水准权,这对于那些社会弱势群体来说尤其如此。
四、适当生活水准权的具体内容
《世界人权宣言》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人人有权享受维持他本人和家属的健康和福利所需的生活水准。”《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十一条规定:“本公约缔约各国承认人人有权为自己和家庭获得相当的生活水准,包括足够的食物、衣着和住房,并能不断改进生活条件。”《儿童权利公约》第27条规定:“缔约各国承认每个儿童均有权享有足以促进其生理、心理、精神、道德和社会发展的生活水准。”根据上述三个公约的条文,适当生活水准权具体包括免于饥饿权、食品安全权、衣着权和居住权。
免于饥饿权,是指人们有权获得足够的食物,能够满足人的生理需要和身心健康。1974年世界粮食会议宣布:“无论男女老少,人人皆有免于饥饿与营养不足的权利,以发挥个人身体与心智的能力。此等权利不可任意剥夺。”饥饿者无人格尊严。如果一个人连温饱问题都解决不了,整日饥肠辘辘,还何谈其它权利,更没有什么人格尊严可言的。
食品安全权。人们不但有权吃得饱,而且有权吃得安全。食品不得含有有毒和有害物质,不能损害人的身心健康;此外,食品还要符合人们的饮食习惯、文化传统,不违背人们的宗教禁忌。不安全的食品,如含有三聚氰胺的牛奶、含有苏丹红的食品等,它们不但导致病从口入,而且直接危及人的生命健康。为此,国家要加强食品安全、卫生环境的监管。在巴西,食品问题已经上升为宪法上的问题,确保日常食品的供应并保证数量特别是质量是一项重大责任,国家需要采取坚决的行动来解决赤贫问题,保证人们的食品权利。[9]
衣着权,简单地说,就是人穿着衣服的权利。衣服是人的必需品,衣着权是最低限度的人权。御寒保暖是衣服的基本功能,因而衣着权首先与人的基本生存相关。同时,衣着权更与人的尊严相关。在历史上,衣服的出现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为它表明人有羞耻感。一个有羞耻感的人,会将心比心,知道自己有耻,也知道别人有耻,不让自己蒙羞,也不会让别人蒙羞,这样,人们之间就会注重礼节,文明相待,相互尊重,进而才有人权,人权存在于有羞耻感的人们之间。衣服是一条重要的分界线,它使人与人分隔开来。自此,人有了独立人格、个人观念和私人权利,进而有了人际分界,群己权限。衣服也是一条神圣不可侵犯的边界,它保护个人不受其他个人特别是国家的侵犯。在衣服之下,个人拥有完全属于自己的领域,任何人哪怕是拥有公权力的国家都不能进入的神圣领域。衣服也许是世界上最脆弱但又最坚固的权利保护屏障,它赋予人以完整的身体、坚强的人格和神圣的尊严。上述这些因素培育出人权的基础,可见,衣服是权利之幕,在其之下笼罩着一系列与人密切相关的权利,而如何对待衣服怎样保障衣着权是评判人权的底线,也是检验人权的试金石。
居住权,指的是人们居住房屋的权利。人总是生活在一定的空间里,要有立足之地和栖身之所;人要安身立命,安居才能乐业;人有隐私,需要有所遮蔽;人有亲情,要有家可归;等等,这些都决定了住房是人的基本需要,人应享有居住权。居住权包括安全居住权。这里的安全,既包括住房在物质上的建筑质量安全,如结构坚固、防风抗震、材料无害、设备齐全、环境安全,等等,也包括住房在法律上的安全,如人们不管是在自己所有的住房里,还是在租用的住房里以及在其他一切形式的住房里,都受到法律的保护,住宅神圣不可侵犯,任何人不得非法侵入、查封拆迁住房,不得非法威胁、骚扰和驱逐住户等。居住权,应具有享有它的可行性,即住房应具有可获得性。这包括,人们有权公平地获得自己的住房(如自建住房、集体建房、自买住房、统一分房、公平租房等),住房应基本具有宜居性和其他配套设施,住房的位置应便于人们的生产生活,居住环境应符合人们的文化传统和宗教信仰,住房的费用不得超出人们的购买能力,政府应采取各种有效措施(如抵押贷款、住房补贴、房租管理等)帮助人们获得住房;等等。住房已经成为了民生之首,民众关心的焦点,必须保障人们的居住权。
需要指出的是,这里所说的生活权是“适当水准”的生活权。至于何谓“适当的”,国际上并没有统一的标准。1990年,联合国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委员会在《第3号一般性意见》中要求“每个缔约国都有责任承担最低限度的核心义务,以确保每项权利的实现均达到一个最基本的水准”。1999年,联合国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委员会又在《第12号一般性意见》中对获得适当食物的权利作了解释:“当每个男子、妇女和儿童单独或与他人一起,在物质和经济上随时能够得到适当的食物或获得适当食物的方法时,就实现了获得适当食物的权利。”其中,“‘适当’一词的精确含义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普遍的社会、经济、文化、气候、生态和其他条件。”尽管这种解释依然很抽象,但可以肯定的是,“适当”标准的具体操作应包括:其一,要综合各国的自然资源情况、经济发展能力和社会生活水平来考量,不能盲目攀比;其二,人们获得适当生活水准权的方式不会损害其人格尊严,如乞讨、苦役和卖淫等不能成为获得适当生活水准权的方式。其三,人们获得适当生活水准权的方法比较便捷,不存在如下不合理的障碍:如成本过高、品种有限、供应不及时,等等;其四,可以参考各国或各地的最低工资标准,以及联合国划定的贫困线标准等来确立,以是否高于它们来考量是否保障了适当生活水准权;其五,它只能是最低标准的生活权,或者略高于它,以足够保障人们有人格尊严地生存和发展为限,否则就会培养懒人,增加社会和国家的负担,妨碍或者侵犯其他人的合法权利。
五、基于适当生活水准权的经济权利保障
人权必须得到保障,但人权根据其不同的内容便有不同的保障方式。
在第一代人权中,仅有一项经济权利得到承认,即财产权,这是经济自主权或个人的经济自由。在此意义上,经济权利的保障措施或本质要求主要在于经济自由和市场经济两个方面。
经济自由是经济发展的基本动力,只有如此,才能激发和调动人们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才会有经济繁荣,才能使经济权利保障获得物质基础。经济自由在根本上赋予人以自由人格,自由最现实而直接的表现便是,一个人能够自由地运用自身所有的各种能力和资源创造物质财富。正如洛克认为,处于自然法范围内的人,“按照他们认为合适的办法,决定他们的行动和处理他们的财产和人身,而无须得到任何人的许可或听命与任何人的意志。”[10]P3这正是经典人权理论对自由的基本界定。一个自由的人也是一个对自己负责的人,他能够通过自身所创造的财富而满足自己的生活所需,这便大大降低其对他人和国家的依附性。只有当人人享有经济自由,人人可以创造物质财富,人人能够自己负责的情况下,才能真正实现经济权利。
市场经济是实现经济自由的最佳经济形式。市场经济让人们自由自治,人们能够根据自己的境况和所掌握的信息灵活应对变化多端的经济形势,进行正确的经济决策;市场经济实行分散决策,人们能够有效地利用分散在社会上的各种信息和知识以发展经济;市场经济允许人们自我谋利,人们有最大的动力去追求自己极大化的利益;市场经济遵循自由竞争、优胜劣汰的市场规律,能够大大提高经济效率。环视全球,经济发达的国家都是市场经济国家,经济落后的国家都是非市场经济国家。这就为实现经济权利指明了道路,即要实现经济权利,必须发展市场经济。
值得注意的是,经济自主权实际上是面向强者的经济权利,无论经济自由还是市场经济,优胜劣汰皆是其题中固有之义。显然,若片面地保障经济自主权,弱者的经济权利不仅得不到实现,反而会成为强者实现经济权利的牺牲品。因此,经济权利的保障必须是“两条腿走路”:一是那些强者通过市场谋利实现自己的经济权利;一是那些弱者通过社会保障实现自己的经济权利。适当生活保障权正是面向弱者的权利,它对保障经济权利提出了新的且更具本质意义的要求。
首先,必须承认国家干预。经济自由不是绝对的,市场经济也不是纯粹的,所有这些都要求国家依法对经济自由、市场经济进行必要的监管。由于人与人之间存在着固有的差别,这些差别足以导致人们之间的经济自由会发生异化,会蜕变为经济强者支配经济弱者的恣意,结果只有经济强者的自由,而没有经济弱者的自由。这就需要国家依法进行干预,抑制经济强者,扶持经济弱者,平衡他们之间的经济地位和经济力量,保障他们享有同等的经济自由。由于市场经济具有自身无法克服的盲目性和无序性,任其发展会导致经济波动乃至经济危机。为此就需要国家依法对市场经济加强宏观调控和具体规制,维持市场经济沿着有序、均衡、健康、既定的轨道发展。市场竞争是有限度的,它的范围仅限于可市场交易的那些权利,但人格尊严不受市场竞争的支配;市场竞争经过优胜劣汰、生产集中、会形成垄断,国家要依法加以反对,重新恢复市场竞争。国家要维持公平正当的市场竞争秩序,不能使其沦为弱肉强食。从历史上看,放任自流的经济导致经济危机,出现大规模的失业和普遍的贫困饥荒,直接导致了专制独裁政权和两次世界大战。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时任美国总统罗斯福提出了著名的“四大自由”,它们成为了许多经济社会权利的基础,由于他的巨大影响和组织推动,这些经济社会权利直接载入了《世界人权宣言》。可见,从诞生之日开始,经济权利就与国家干预密切相关,尽管后来发生了许多变化,但至今无人能够否认,国家干预对于经济权利实现的重要意义。经济社会权利的实现不但不能排斥国家干预,而且必须依赖国家干预的积极作为,这恰恰是经济权利、社会权利与公民权利政治权利的一大区别。这正如有人所指出的:“这些权利不是保护个人以对抗政府或其他当权者的,而是提请公共权力机构注意要让诸如个人自己拥有的那种自由权通过另一些自由而得以实现。”[11]P94-95
其次,国家干预必须在一定的限度内进行。国家干预必须有明确的指导思想和根本宗旨,即以人为本,大力改善民生,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的需要。国家干预应该以保障弱者的基本经济权利为价值导向,社会保障应当作为国家干预的突出目标,并成为一项国家义务。经济权利的实现离不开经济繁荣,因此,国家干预必须遵循经济规律,依然要采取市场经济体制,承认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地位,尊重市场交易的结果,保护一切合法的财产权。
再次,必须加强法治建设。只有建立起法治政府,才能在根本上确保国家干预实现其目的,而不至于异化为侵犯经济权利的工具。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委员会承认,“在许多情况下,立法是非常适宜的,而在某些情况下,立法是责无旁贷的。”[7]P80如为了保障人们的居住权,我国有关立法机关制定了许多法律政策。对于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的实现,国家承担着主要的义务,政府只有动用全社会的经济资源才有可能实现它们,这就必须加强政府执法。如为了实现就业权,政府要扩大就业机会、消除就业障碍和就业歧视、保障择业自由;要加强职业培训、技术指导等就业服务,要提供劳动保护和失业保障,等等。要加强司法,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委员会认为,在许多情况下,《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2条第1款所规定的为实现这些权利所采取的其他“方法”,“如果得不到司法救济的强化和补充,就会成为无效之谈”。[7]P63-64法院有权对有关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的立法和执法进行审查,作出评论和指示;在有关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的诉讼中,有权要求当事人负举证责任;有权对有关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的案件作出判决并予以执行,等等。
结语
时至今日,“人权的时代”已毋庸置疑地到来,保障人权已成为世界上绝大部分国家的正当性基础,尊重和保障人权已被庄严地载入我国宪法,在中国共产党十八届四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更是明确将“增强全社会尊重和保障人权意识”作为建设法治中国的一项重要部署。因此,我们应当更加认真地对待人权。然而,若拘泥于西方旧有的、基于自由主义与个人主义的人权理论,并片面地强调政治权利,并不足以解释人权,亦无法把握人权的实质与全貌。从人权的本质与根本价值出发,理应承认,经济权利尤其是适当生活水准权是最基本且最核心一项人权。作为当代人的基本权利,适当生活水准权具有丰富的具体内容,且密切关涉当代人的基本生活,更为当代人权保障事业提出了新的要求。
[1] [美]史蒂芬·霍尔姆斯,凯斯·桑斯坦.权利的成本——为什么自由依赖于税[M].毕竞悦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2] 姚建宗等.新兴权利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3] 曾强.新南非外交工作的成就[J].国际资料信息,1997,3.
[4] [英]霍布斯.利维坦[M].黎思复,黎廷弼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
[5]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
[6] [美]罗斯福.罗斯福选集[M].关在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7] [挪]艾德等.经济、社会和文化的权利[M].黄列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8] [印度]让·德雷兹,阿马蒂亚·森.饥饿与公共行为[M].苏雷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9] [巴西]曼努埃拉·达维拉.人权:需要巩固的现实[N].光明日报,2011-9-23(16).
[10] [英]洛克.政府论(下篇)[M].叶启芳,瞿菊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
[11] [美]卡尔·弗里德里希.超验正义——宪政的宗教之维[M].周勇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
(责任编辑:黄春燕)
Proper Living Level Right:the Fundamental Right of Contemporary People
LiChao-qun
(Administrative Law School of Southwest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Chongqing 401120)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Right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has taken proper living level right as a basic economic right. The western old human rights theories often ignored the economic rights,and one-sided emphasis on political rights. However, on the nature of human rights and human nature, economic rights are basic human rights, and proper living level right is the core of the economic rights. Proper living level right is consisted of many specific content, and puts forward new requirements for the contemporary human rights protection.
proper living level right; economic right;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Right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1002—6274(2015)01—052—08
李超群(1987-),男,重庆人,西南政法大学人权教育与研究中心副研究员、法理学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西方人权理论。
DF2 < class="emphasis_bold">【文献标识码】A
A
*写作此文过程中,辽宁大学法学院江游教授给予非常多的建议与指导,作者表示由衷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