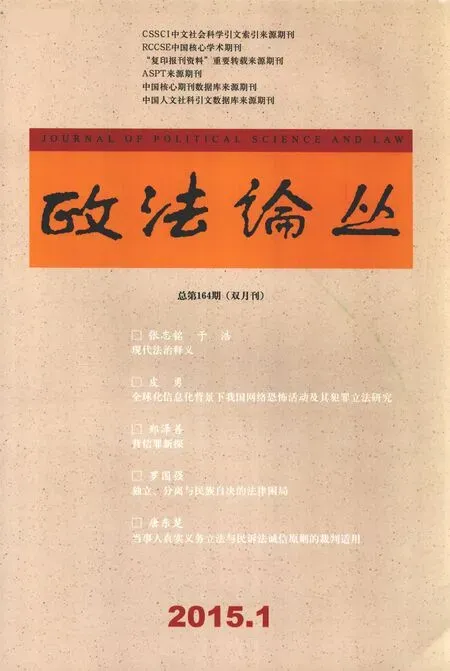司法原情:传统及当代价值*
2015-01-30王国龙
王国龙
(西北政法大学刑事法学院,陕西 西安 710063)
司法原情:传统及当代价值*
王国龙
(西北政法大学刑事法学院,陕西 西安 710063)
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是司法公信力的建构基础,而形式法治主义理念往往强调“法律效果至上”而忽视了其社会效果。作为传统中国重要司法裁判方法的“司法原情”,其对依法裁判当中“情理”因素和法律因素的综合考量,至今仍然具有重要的司法实践价值,以积极回应社会对实质法治主义的相关诉求,建构司法的权威性和公信力。
司法原情 依法裁判 司法公信力
德国学者拉德布鲁赫在谈到“仁慈与法”的问题时指出,“正义与仁慈——这是法律职业的根本问题……与根据平均计算的法律不同,个案的正义之具有效力,是由仁慈所决定的……在仁慈那里,面对法的全面的理性化要求,和亲可爱的偶然性必定提出自己的要求。”[1]P33-34毫无疑问,司法要实现正义,既要依据法律严格依法裁判,以实现一般法律层面的法律正义;又要依据社会所客观存在着的“仁慈之心”,以实现个案情理层面的仁慈正义。我国古代自汉朝所确立的“引经决狱”以来,“天理、国法、人情”三位一体的司法理念无疑构成了中国司法传统中最重要的司法理念之一,所谓“志善而违于法者免,志恶而合于法者诛”(《盐铁论·刑德》),就是这种司法理念的核心法哲学依据;而在司法裁判方式上,“法不外乎人情”抑或“司法原情”无疑就是其集中的体现。
近代以来,伴随着市民社会对法与道德相对分离性的不断强调,与所有发展中国家的法律变革一样,以形式法治主义为理念的中国司法改革逻辑,开始发挥着某种程度的主导性作用。至今乃至未来,法治已经成为中国新时代背景下对国家和社会实现转型治理的必然发展趋势,“法治的兴起与从自然国家到开放准入秩序的转型重合。”[2]P42需要指出的是,尽管形式主义法治理念对于推进未来中国社会治理方式的整体性转型而言,具有支配性的意义,但对于公正司法而言,形式法治主义的司法裁判方法自身所具有的诸多弊端,难以保障相关实质主义法治价值的实现,以致于实质主义的法治诉求已经成为了当下中国社会需要认真对待的一个“时代主题”了。与形式法治主义所倡导的严格依法裁判相区别,实质法治主义更强调个案当中实质正义的实现,强调法官在严格依法裁判的基础之上,需要充分地考虑个案事实的特殊性,尤其需要充分考量个案当中纠纷背后的“情”与“理”的因素,以实现个案裁判的实质正义。本文立足于充分承认形式法治主义理念的司法改革逻辑基础,主张法官在坚持严格依法裁判的同时,也要尝试采取“司法原情”的相关传统司法裁判方法,有针对性地加强司法判决在情理论证层面的说理能力和在个案实质正义层面的充分考量,积极回应社会对实质主义法治的相关社会诉求。
一、作为传统的司法原情
法律和司法都是社会的产物,并以特定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为最终依托。甚至可以说,社会性构成了司法的本质属性,合情合理并合法地实现“案结事了”,构成了任何社会中司法权运行的终局性理想目标,“司法权的本质部分……就是执行分配正义……时至现代,市民性司法权的此等职责功能依然继存,并未因历史的变迁而消失”[3]。具体就中国传统社会中司法与情理之间的关系而言,“差序格局”的相对稳定社会结构,构成了中国特有的儒家化法文化传统,这种法文化传统往往将法视作为“法上之法”(即天理)、“法中之法”(即国法)以及“法外之法”(即人情),而将司法裁判的过程视作为一个将“天理”和“人情”凌驾于“法理”之上的综合性考量过程。对于前者,费孝通指出,“一个差序格局的社会,是由无数私人关系搭成的网络。这网络的每一个节都浮着一种道德要素,因之,传统的道德里不另找出一个笼统性的道德观念来,所有的价值标准也不能超脱于差序的人伦而存在了。中国的道德和法律,都因之得看所施的对象和‘自己’的关系而加以程度上的伸缩。”[4]P36而对于后者,瞿同祖指出,“除了法典内容已为礼所掺入,已为儒家的伦理思想所支配外,审判决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也是可注意的事实,儒家为官既有司法的责任,或参加讨论司法的机会,于是常于法律条文之外,更取决于儒家的伦理学说。我国古代法律原无律无正文不为罪的规定,可以比附,伸缩性极大。这样,儒家思想在法律上一跃而为最高原则,与法理无异。”[5]P361
与传统法制不同,以实现“规则治理”为目标的现代法治,往往强调法律与道德的相对分离性,法律体系的自主权威性,以及法律适用当中的明确性、一致性、普遍适用性等,主张法官“依法裁判”而反对司法自由裁量权超越法律边界的行使,以实现对权利的平等保护。其中,法律内容的不断被理性化构成了现代法治建构的内在动力,而法律适用过程的不断被技术化甚至是高度形式化,则构成了现代法治建构的社会知识基础,“这种法律分析话语与19世纪理性主义和较为松散也更加依据具体语境的类比推理相去甚远,它正逐渐在美国以及其他地方取得支配地位,律师与法官的实践推理大多数采取这种方式。”[6]P55现代法治对法律确定性的追求是建立在法律的技术性知识基础之上的,而对法律的实践性知识则往往关注不足。由此,法律的理性化分析则集中体现为对法律的技术化分析和建构,甚至凸显为一种“法律技术的霸权”,“技术知识似乎是唯一满足理性主义者选择的确定性标准的知识”[7]P12。
需要指出的是,在人类追求法律确定性的过程中,除了法律的技术性知识之外还包括广泛的法律实践性知识。尤其是在司法裁判过程中,法官不应该满足于通过某种传统的法律理性化分析来获得结论,而需要掂量各种可能冲突的相关因素,包括诸如逻辑的、历史的、习惯的、道德的、法律的形式和实质等,“历史或者习惯、社会效用或某些逼人的正义情感,有时甚或是对渗透在我们法律中的精神的半直觉性领悟,必定要来援救焦虑不安的法官,并告诉他向何方前进。”[8]P24-25不仅如此,法律知识和公正司法的裁判方法最终必定归结于法律的历史实践和社会的现实治理境况,传统的“司法原情”裁判方法,正是传统中国法律实践和社会治理境况的产物。具体而言,作为传统的“司法原情”裁判方法,其具体内容集中体现在以下三个基本方面:
第一,以“情理”来协调“天理、国法、人情”三者之间的可能冲突,建构司法裁判内在统一性的社会基础。传统中国既是一个高度集权又是一个地方高度分散治理的社会形态,在行政兼司法的社会治理模式当中,通过对相关职权的某些重叠设置或者留有空隙,以达到实现对中央和地方各级官员权力相互牵制的平衡状态。由此,某种“集权的简约治理”就构成了传统中国社会治理的突出特征,而“儒法合一的治理”则构成了传统中国社会治理的法律实践模式之一,“之所以是中央‘集权’,是因为帝国以皇帝个人名义声称拥有绝对(世袭)的权力,行政权威并没分割于相对独立的政府各部门,也没有为政府和市民社会所共享,而是聚集在中央……儒法合一,或者说是‘儒化的法家’治理,能够涵盖集权的简约治理实践的一部分”[9]P70-71。
在社会治理的依据层面,国法即“王法”,是实实在在可以看见并直接感受到的实在法,而“天理”和“人情”则既无确定的内容,又无确定的表现形式,但却在现实当中客观存在道德规范。尤为重要的是,“天理”乃是一种至高无上的的行为准则,往往表现为客观真理、必然规律或者人际关系准则,具有鲜明的自然法属性,但是其具体内容最终往往要体现在“人情”的内涵当中,“法不外乎人情”就是指法律体现了人情、符合人情或者法律是人情的具体表现形式。当三者之间发生可能冲突的时候,“情、理、法”三者要相互兼顾,通盘考量,努力消除三者之间的冲突并达到高度融合的状态,这才是理想状态下的法律,也是人们判断是非善恶的最根本依据。不仅如此,“情、理、法三概念的前后顺序排序也断非偶然,而是反映着人们对其轻重关系的一定认识。即是说,在中国人看来,‘合情’是最重要的,‘合理’次之,‘合法’更次。此即所谓‘人情大于王法’。”[10]P24
当然,“人情”不能够体现为“私情”,司法原情如果“原”的是私情,就必然会出现徇私枉法和漠视法律权威的现象。相反,“人情”乃是一种符合“天理”的公共性道德准则,具有“礼”和“义”的本质内涵。“情”与“理”之间的辩证统一,构成了中国式的理性和良心,是中国古代社会中道德伦理和常识的集中体现,“情理判断的中心部分是任何人都不会想到提出异议的普遍而不言而喻之理,其边缘部分则依具体情况可以呈现出千变万化的灵活性。不过,这种灵活性并非完全无原则,其程度和范围是熟悉这个环境的人们大体上能够把握的东西。”[11]P80因此,在一个“集权的简约治理”的中国传统社会中,以“情理”来协调“天理、国法、人情”三者之间的可能冲突,构成了“司法原情”裁判方式具体展开的实践性要求,从而建构司法裁判内在统一性的社会基础,“凡此,都是谈论人情之‘情’,而非专指案件之‘情’;以及,如何在礼义上治理‘情’,而非在断狱上重视‘情’。另外,就‘情’与‘义’的关系而言,我们看到了它们之间的互动和张力。一则必须顺从人情、正视人情,二则却又必须规训人情、节制人情,这是问题的关键所在;人情与礼义之间的平衡,乃是良好社会秩序的基础。”[12]P43
第二,以“情理”来平衡法律实践和道德实践中的相关现实利益冲突,建构司法裁判在实质正义层面的公正性,凸显司法实践的现实人文关怀。法律与道德都是两种最基本的社会规范,各自都发挥着重要的社会控制功能。其中,前者侧重于对行为及其后果的惩罚性调整,而后者则侧重于对个人良心及其社会核心价值观形塑的引导性调整。在传统中国社会中,当法律调整与道德调整发生冲突的时候,司法到底是“宁屈法律以全道德”还是“宁屈道德而不枉法律”,则一直是一个存在着激烈争论的问题。对于前者,有学者指出,由于“情理场”是中国古代司法中无处不在的由情理精神所构成的法律文化特质,司法过程只有按情理才能被广泛认可。由此,在情理场中,道德教化式的语言,不顾当事人权利和利益的做法,都成为可能,而且能被各方接受和认可。地方官在司法中的任务,不是维护当事人的权益,而是恢复社会平衡,尽量息讼,息事宁人。[13]而对于后者,有学者指出,就明清时期的司法实践而言,既非简单的“法律裁决”,又非纯粹的“情理裁决”,而是由诸多原因导致了二者之间的紧张和融合,最终以“情法两尽”为目标和理想。通过辨析法律表达和解读司法案件我们可以发现,从类型角度来看,明清时期的司法属于“情法两尽”的裁决模式;而就局部而言,司法官员在审理某些案件时,确实存在严格“依法裁决”的现象。据此,我们并不能将明清中国的“依法裁决”视作为一个“伪问题”。[14]
对于上述两种看似难以调和的基本立场,实际上都是建立在法律实践与道德实践相对分离的现代司法知识类型基础上而展开争论的,即把法律实践简约为一种“依据法律”的司法技术性知识逻辑推论过程,而把道德实践简约为一种“依据情理”的司法实践性知识判断过程。然而,传统中国“差序格局”的社会整体结构和“儒法合一”的社会治理模式,在某种程度却决定了传统中国司法实践的道德性智慧判断趋向和对个案实质正义的集中关注,而司法的技术性知识往往穿插于相关的论证当中。尽管情理和法律都是司法裁判必须予以参酌的依据,只是在具体个案当中存在着相对的差异性,但是“准情酌理”却是个案裁判实质正义架构的最终理想状态。“无论是‘情’,还是‘理’,都不是一种个体性因素,而是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合理性。只不过,这种普遍意义的合理性因素,在具体的案件中,相对于一般规则而言,它通常是一种需要予以特殊考量的情形。因此,对于因利益纷争而引起的诉讼而言,无论‘情’或是‘理’,都蕴含着一种利益主张的合理性条件。”[15]
不仅如此,对于民众在日常法律实践和道德实践中相关现实利益冲突及各自的合理性,“‘合乎情理’与否”都是最直接和最普适性的判断依据和平衡标准,以突显司法实践的现实人文关怀,“传统中国法的道德原理对于人与法和社会的意义最后都集中到了道德上,表现为基于道德所拥有的共通原理和内在价值……传统中国法的人文观实质是一种道德人文观”[16]P99。如果我们仅仅依据法律实践与道德实践相对分离的现代司法知识类型,来透视传统中国司法原情的裁判方法,就可能陷入到法律实践和道德实践截然对立的二元困境当中。相反,传统中国“差序格局”的社会整体结构和“儒法合一”的社会治理模式,最终决定了传统中国司法原情所采取的乃是“情法两尽”的利益平衡裁判艺术,以防止“宁屈法律以全道德”或“宁屈道德而不枉法律”二元困境的出现,“所有各种知识,尤其是关于同一些对象的一般性知识,都以某种方式决定着社会——就其可能具有的所有方面而言——的本性。最后,反过来说,所有知识也是由这个社会及其特有的结构共同决定的。”[17]P65
最后,以“情理”来论证司法判决的正当性,并不断强化法官公正裁判的社会责任感,以达到“教谕的调停”和“息讼”的社会效果。传统中国社会是一个“家—国同构”的二元结构社会,在法律渊源上集中体现为“家法—国法的二元法律结构”,而在司法裁判的依据上则呈现出“法律多元,伦常一贯”的一元决讼标准,即强调以“情理”来论证和统合司法判决的正当性,“为使法律有效,涉及法律的所有事务必须具有自动性……通过这样的方式,统治者以恰如其分的方式让人们感受到,他的正当性完全基于法律规则实施过程的自动性,因为臣民们看到赏与罚的分配并不是统治者的行动,而是由臣民们自己的举止所引起的结果。”[18]P142-143同时,在国家相对有效地垄断和控制暴力使用的基础上,传统中国的政治治理方式是努力实现“化家为国”,将政治治理的基础构筑在人性和情感之上,以实现民众在情感上对于皇权的普遍性认同。由此,某种“诉诸于情感”的断狱策略和纠纷化解方法则成为必然要求,“在‘情感本体’的传统中国社会里,连接和维系人们之间相互关系或社会秩序的基本准则,乃是情感;而情感的生物根基,则是人性;道德、道理和礼法的基础,也不外乎是人性和情感;而情感的发轫、养成、表达和功能,则与社会文化和具体事态有关。”[12]P5当然,“诉诸于情感”的断狱策略和纠纷化解方法,也并不排除采取以解决实际问题为目标的某种实用主义司法裁判立场,但是断狱的主要指导思想是儒家的“仁”和各种道德原则。正是这种“情感本位”的文化结构,催生出民众“申诉冤情”的诉讼心态和官员“哀矜折狱”的裁判心态,并发挥着统合国法依据的司法论证功能。司法审判最理想的状态乃是“当事人必须作出‘甘结’(即表示自愿服从裁决、结束诉讼)”,以实现“教谕的调停”和“息讼”,而非单一的“依法裁判”。因此,“在古代中国人看来, 司法审判并不都是为了判断是非、求得公正、伸张权利,有时不过是为了化冤解仇,求得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安宁而已。在这中间,与其说国法重要,倒不如说伦常、人情更重要。”[19]P94-95
当然,司法原情在强调以“情理”来论证司法判决正当性的同时,也必须不断强化法官公正裁判的专业素养和社会责任感,即好法官(能主持正义的“官员”) 不仅需要具备过人的才华,更要具备良好的品德,甚至法官良好的品德在公正裁判当中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例如,两宋之交时期的地方司法官郑克认为,一个好的法官既要有仁恕矜谨、勇于为义、尽心不苟的品德,又要具备明辨深察、博闻广见、妥善处事的才能,做一个“不苟”的君子。[20]需要指出的是,在一个以“文官主治”的传统中国社会,儒家的传统教义深深地形塑着官员对公正司法的社会责任感,尽管官员在审判当中主要关注的是对现有社会秩序的维护,审判本身只是社会治理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是司法伦理的形成主要源自于官员个人对传统儒家教义的内心信仰。在一个以儒家教义为传统的中国道德社会,这种内心信仰的魅力无疑是巨大的,司法的“无讼”终极价值目标无疑就是要建立一个“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的安定、平静和有序的社会,并具备深厚的社会基础。日本学者滋贺秀三在评价传统中国的司法伦理和“无讼”的司法价值时指出,“如果同欧洲诉讼这种内在的性质相对照而探索中国诉讼的原型,也许可以从父母申斥子女的不良行为,调停兄弟姐妹间的争持这种家庭的作为中来寻找。为政者如父母,人民是赤子,这样的譬喻从古以来就存在于中国的传统中。事实上,知州、知县就被呼为‘父母官’、‘亲民官’,意味着他是照顾一个地方秩序和福利的‘家主人’。知州、知县担负的司法业务就是作为这种照顾的一个部分的一个方面而对人民施与的,想给个名称的话可称之为‘父母官诉讼’。”[21]
在近代以来法制现代化改革逻辑占支配性地位的历史变迁当中,这种传统的“司法原情”裁判方式,由于集中体现了传统中国人治主义伦理社会的治理本质,以及司法自由裁量权行使的鲜明“泛道德主义”特征等,难以承担起建构现代法治国家的历史使命,从而不断地成为了法制改革尤其是司法改革的对象,“应该看到,传统法制的泛道德主义必然导致对法律的不信任,进而动摇法律在治理国家中的重要地位……法制领域的泛道德主义,势必影响法律权威和机制的建构,从而不可避免地为人治主义奠定了基础。”[22]P191-192
二、司法原情的当代价值
作为一个法治建设的发展中国家,长期以来,中国法治进程的推进从来就是在中国传统法制实践的历史逻辑和西方发达国家法治实践的应然逻辑之间的不断调试当中而展开的。在“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为指导思想的中国法治实践现实逻辑展开进程当中,伴随着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为基本依托的现代社会治理方式,正处在不断的自我探索中。与之相适应的是,围绕着贯彻和落实法治理念的相关司法制度改革,也已经成为了推进中国法治进程的关键环节之一,实现“公正、高效、廉洁、为民”的人民司法,则构成了中国司法改革所追求的核心目标,“司法部门有责任向公民、经济机构和国家提供公平、快捷和透明的法律服务……司法改革是新发展模式的基本组成部分,是善治的基础……从本质来看,对司法进行管理是国家向社会提供的一种服务,旨在通过争端来保证社会和平和促进经济发展。”[23]P390不过,与所有发展中国家的法治建设实践一样,中国的司法改革在推进中国社会法治进程的同时,其自身所暴露出来的相关问题,却同样构成了司法改革甚至是中国法治社会建设的问题之所在。在当前追求法治社会治理的时代背景下,人们对司法改革关注的焦点往往集中在对个案实质正义的关注,期待司法能积极回应社会对基本的善治、平等和权利有效保护等相关诉求。尤其是在诸多涉及社会公共价值和道德性较强的影响性诉讼个案当中,人们迫切地期待法院能通过个案司法发挥其形塑公共道德和社会核心价值观的积极作用。
具体而言,中国司法实践陷入到以下的相关现实困境当中:其一,以法律规则体系为导向的司法救济,难以清晰化法律调整与非法律调整之间的可能界限,法律调整的有限性缺陷在不断凸显。尤其是在公共道德和社会习惯的常规性调整出现式微的状态下,人们对公正和高效的司法救济往往予以了更高的社会期待,但由于司法发挥对权利救济的能力和程度均有不足,相关社会纠纷的解决及其后果,反而形成了某种“示范性的放大效应”,从而不断地在冲击着公正司法的公信力。例如,近些年来所发生的大规模非正常上访,“信‘访’不信‘法’”的现象,某种程度上似乎正在不断地压缩着“司法调整的空间”和“法治的领地”。其二,以法律规则适用和程序法为导向的司法权运作体系,难以有效应对深层结构性和具有历史继承性的社会纠纷,司法的正当性不断地在遭遇着社会相关的质疑。例如,司法在审理相关涉及社会基本的善治和平等这样的社会纠纷当中,难以发挥其对权利的有效救济和对义务的有效落实之社会效果,个案实质公正的问题在不断地凸显,并在不断地侵蚀着司法的权威性。最后,以追求法律效果和判决合法性为导向的司法裁判实践,职业化的法官往往会选择司法成本相对较低和社会风险相对较小的实用主义司法裁决方案,在诸多影响性诉讼的个案当中难以发挥其应有的公共价值导向作用和社会核心价值观形塑功能。由此,司法判决的公共性和司法职业的伦理性都难以得到充分的彰显,司法的社会效果和正当性也难以得到切实地体现和保障。
对于司法当中法律与情理之间的相互关系,需要指出的是,由于任何社会中的法律在内容上始终和情理保持着千丝万缕的关联,司法如果出现“以法律效果超越社会效果”,法律的情理性维度就会不断地丧失,最终必然会危及司法自身的正当性和权威性,“理性地处理情感,在此也就存在着审判的手段的合理性。因此这本来并不意味着审判规范无视或轻视人的伦理情感”[24]P32-33。对于克服当前中国司法实践所陷入的上述相关现实困境,从司法裁判方法的层面而言,传统的“司法原情”则具有当代的实践价值,集中体现在以下三个基本方面:
第一,以情理丰富法律论证的内在结构,增强法官公正司法的社会责任感和职业良心。“依法裁判”是法官公正司法的基本职责,但是公正司法不仅要求法官严格依法裁判,而且要求法官不带有任何私心和偏见地履行司法职责,公正必须是客观的、平等和以“看得见的方式”充分展开,尤其是当法官个人的判断与他人的观点发生可能冲突的时候,法官则需要通过寻找社会所公认的情理因素来丰富法律理性论证的内在结构,这构成了公正裁判的关键环节之一。就法律的具体内容而言,任何时代的法律都是特定社会背景的产物,社会背景不仅仅体现为具体的政治运作、经济格局和社会语境,还体现为固有的司法历史传统和法律自我传承的内在精神。就具体个案当中的法律论证而言,法律的内部论证只是实在法体系层面的合法性论证,而法律的外部论证则扩及到对实在法体系层面之外的合理性论证,既包括经验论证,也包括法律解释规则的论证等。在当前社会权利意识不断崛起的社会背景下,如何正确地处理个人权利和群体利益之间的可能界限,如何正确地形塑公共道德和社会核心价值观的内容,则成为法官公正司法所必须承担的社会责任。法律论证是司法裁判结论的应然性论证,这种应然性论证要转化为具有最终法律效力的法律论证,法官必须要具备健全的心智和职业良心,反对各种形式的“虚假论证”和“带有偏向性的论证”,“法律者,尤其是法官,虽然从制定法那里证立他的具体的应然决定,并因此显得满足了执法的合制定法性原则,但是,经常发现,实际上是在大多数情况下,他的决定所依据的完全是另一种方式,即直觉地、本能地求助于是非感,实践理性,健全的人类理智。”[25]P51
传统的“司法原情”裁判方法,对于丰富法律论证的内在结构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可以极大程度地防止单纯机械司法的法律教条主义。例如,主张性善论的孟子曾言:“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孟子·公孙丑上》)。可见,法官如果具备恻隐之心,就能施以必要的仁慈;如果具备羞恶之心,就能具备一身正气;如果具备辞让之心,就能平等地对待当事人;如果具备是非之心,就能将“善”端导入司法裁判的每一个环节,最终就能具备公正司法的健全人类理智。传统的“司法原情”裁判方法,往往强调“情法两尽”或“情法兼施”,这明显是主张将“情理”高度地融入到依法裁判的思维当中,实现“天理、国法和人情”的高度统一。法律论证不是将法条通过逻辑简单地涵射到具体的案件事实当中,而是一个具有高度实践理性的思维过程,“苏格拉底说:‘法官应具备四种素质:认真地听、聪明地答、仔细地想和公正地判’。从广义上讲,法官的思维成果不过是其作为人的各项素质的综合反映。这种素质是通过教育来培养的,经验是在学习和总结的基础上建立的。它们反映出一长串法官渴望具有但却很难达到的人的素质:如耐心、勇气、才智、仁慈、决断、理智和常识。也许这一词可以概括它们的全部含义。”[26]P291有学者指出,在“依法判决”的情况下,虽然“情理”可能缺席,但是并非无关紧要的,法律也可能隐身其中,然而,同样不是可有可无的东西,它依然是司法官员必须予以关注的参照基准,斟酌“情理”与法律也就成为司法裁判不可忽视的前提。[27]P339
同时,以情理来丰富法律论证的内在结构,还是法官公正司法的良心要求和良心所在。法律论证不仅是司法裁判的技术性要求,也是一种极具艺术性的实践理性判断过程,目的性往往对法律论证发挥着某种指引性的判断功能。法官在综合平衡“情理”因素与法律因素的论证当中,其自由裁量权的范围和空间总是很大的,不可能从根本上加以消除,否则就是法律教条主义的机械性司法了。而法官对自由裁量权的正确性行使,归根结底却取决于法官的司法伦理和个人良心。卡多佐指出:在所有的法律发现和法律解释当中,从长远来看,除了法官的人格之外,没有任何其他东西可以保证实现司法正义了。[8]P6因此,法官的职业良心乃是公正司法必须具备的主体性要素,也是社会实现善治的最终依托。
第二,以情理平衡现实社会中的利益冲突和价值冲突,凸显司法个案的实质公正和人文关怀。在当前转型社会时期,社会纠纷和矛盾往往具有结构性和历史继承性的基本特点,人们对权利的追求和捍卫,在客观上存在着将应然性的相对权利,视作某种实然性绝对权利转变的倾向,这一倾向加深了人们对权力行使的警惕甚至是某种仇视。在双方的博弈当中,社会对权力合法性和正当性行使的不断追问,往往导致其不断地陷入到相对妥协的现实困境当中。同样,在司法裁判领域当中,权利意识的崛起和法律意识的普遍增强,人们对司法权行使的合法性和正当性也在不断的质疑当中。诸多的难办案件说明,建立在法律规则性权威和司法程序自治性权威基础之上的现代技术性司法权威,难以保障司法对现实社会中利益冲突和价值冲突的有效调整,甚至会出现法官固守实在法层面的司法不作为困境,“由于逻辑法条主义致力于实现讲求原则的逻辑自洽性,经不住严格分析批判的既有程序安排不会被赋予神圣性,而且很难存续下去,全面检查整个系统的压力持续存在。”[28]P84-85需要指出的是,难办案件当中技术性司法权威困境出现的根本原因在于,现代技术性司法权的运行理念,存在着简单地将“合法性”界定在符合实在法的层面,并人为将法律从社会现实尤其是从社会基本的道德观念当中剥离出来,其结果必然危及到个案实质正义实现的可能性。同时,司法职业化背景下的法官也多少呈现出某种冰冷甚至是不尽情理的现实困境,司法情理性说理能力的不足甚至是缺失构成了司法实践的普遍性状况。
与现代技术性司法权运行的实践不同,传统的“司法原情”裁判方法,则能够克服上述的相关困境,尤其是通过情理来实现对社会中各种利益冲突和价值冲突的平衡作用,从而能够有效地发挥息诉和纠纷化解的社会效果。例如,曾经担任过凤翔府判事官的苏东坡曾言:“凡事之可以赏、可以不赏者,赏之;可以罚、可以无罚者,不罚;此忠厚也。凡事之可以赏、可以不赏者,不赏;可以罚、可以无罚者,罚之;此刻薄也。刻薄成家,理无久享”(苏轼:《刑赏忠厚之至论》)。可见,如果法官在司法裁判当中通过情理性的说理来平衡双方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冲突和价值冲突,给出一个“符合情理”的裁判方案,当赏则赏,当罚责罚,才能有效地建构司法判决正当性的社会基础。美国学者梅丽在研究法庭话语的类型时指出,在法庭上,法律、道德和治疗性三种话语在对特定问题的讨论当中往往时而浮现,时而隐匿,并针对不同的当事人尝试性地评估其相应的社会效果,甚至是在调解和开庭审理阶段,涉及道德义务性的日常道德话语甚至构成了庭审程序当中的最常用话语,而法律话语则较少使用。当然,当某种话语的效果不佳时,法官也常常会转向另一种话语以看其效果如何。[29]P153不仅如此,法官对情理性话语的适当使用,还是彰显其对个案“特殊性”关注的集中体现,从而拉近与当事人之间的可能距离,消除当事人甚至是社会对公正司法权威性的怀疑和对立情绪,从而最大程度地提升司法裁判的可接受性和社会公信力。当然,法官通过情理来实现对社会中各种利益冲突和价值冲突的平衡,并不能陷入到简单的“和稀泥”司法实践妥协困境当中。利益平衡或者价值平衡需要建立在相应的法律规范基础之上,脱离开法律规范基础的情理论证势必会导致“盲目飞行”的困境,从而直接损害到法律的应有权威性,而相关的法律义务和道德义务自然也就难以得到最终的有效落实。
另外,通过情理来平衡现实社会中的利益冲突和价值冲突,还是充分彰显法官裁判人文素养和人文关怀的实践需要,以突显法律的仁慈之心。法律权威的树立最终依赖于良好法律文化的形成,法律文化是人们关于法律与法律过程的一般性体念、态度和期待,并最终形塑着法律制度及其自身的良好运行。“司法原情”传统集中凸显了法官自身的人文素养和对社会的人文关怀,这一传统在当前中国司法不断职业化的时代背景下具有极其重要的实践价值,传统社会的人情、习惯、风俗、传统和关于“善恶”的基本共识等,是建构司法正当性权威的社会基础。
最后,以情理来融合司法的法律效果,凸显司法对公共道德与社会核心价值观的导引和形塑功能。在近些年以来的中国司法职业化历史进程当中,一方面,伴随着司法裁判对法律权威性和司法技术性的不断强化,往往要求法官要努力超脱对社会道德的考量,以充分追求司法的法律效果,这往往导致司法官僚化现象的凸显;另一方面,伴随着司法过程的不断流程化和科层化,法官虽然加强了自身在适用法律和论证判决上的能力,但同时法官却缺乏足够的对个案事实的洞察能力和对社会现实复杂结构的判断能力,司法无法发挥其对公共道德与社会核心价值的必要导引和形塑功能。有学者指出,现代职业化的司法往往过分强化法官要超脱人情世故,只追求法律效果而忽视了社会效果,从而导致法官的仁慈之心在司法的现代性与传统性、普适性与本土性上脱离,“司法不仅是威严的,也是温情的。司法的温情有赖法官的真诚恻怛、哀矜裁判之心。真诚恻怛是法官的真诚心、恻隐心,哀矜裁判是法官的同情心、怜悯心。”[30]尤其是在某些涉及公共道德和婚姻家庭的纠纷当中,单纯依据法律所作出的相关裁决,往往引发出社会的广泛质疑,甚至是出现难以预料的“轰动性”社会反响。例如,南京彭宇案的社会“示范性”效应仍然在持续引发相关的连锁反应,而最近几年有关老年人的精神赡养问题也在学术界引发出了普遍性的争论。
我们需要承认的是,在一个道德多元和转型社会时期,司法对涉及公共道德和社会核心价值观的个案审判,其引发出社会的可能反响和争论,总是在所难免的。但是,无论是古今中外的影响性诉讼个案,其发挥对公共道德和社会核心价值观的必要引导和形塑功能,无疑是司法和法官所应当承担的神圣社会责任。无论是在法律发现还是在法律解释当中,可能发生相互冲突的不同裁判方案,最终判断的可能抉择,总是取决于公共道德和社会核心价值观所体现出来的“公共利益”,其构成了法官个案判决所必须参考的权威性依据之一,“‘公共利益’的标准事实上要求法官在作出决定时考虑那些诸如公众看法和有效分配诉讼资源的非司法性因素。”[31]P128在传统的中国礼法社会中,“司法原情”裁判方法通过对“情理”因素的充分考量来融合司法的法律效果,往往发挥着重要的维护社会良好道德秩序的实践价值。例如,海瑞在总结财产纠纷的审判经验时指出:“窃谓凡讼之可疑者,与其屈兄,宁屈其弟;与其屈叔伯,宁屈其侄;与其屈贫民,宁屈富民;与其屈愚直,宁屈刁顽。事在争产业,与其屈小民,宁屈乡宦,以救弊也。事在争言貌,与其屈乡宦,宁屈小民,以存体也。”[32]P117海瑞对财产纠纷的上述审判经验至今无疑仍然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这对于通过司法裁判来建构稳定和谐的家庭秩序和公平合理的社会秩序而言,无疑是极其重要的。法律与道德虽然具有一定程度上的可分离性,但在深层次上无疑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没有良好道德秩序所支持的法治社会,归根结底将会失去其赖以存在的社会基础;而司法如果不积极回应社会的公共道德和核心社会价值观,其结果只会导致法律与道德的对立甚至是冲突,最终必将丧失其自我的正当性。
不仅如此,当下处于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人们对法律权利的强烈维护意识往往在弱化着对法律义务、婚姻家庭义务和社会义务的自觉履行,只顾个人权利的极端观念严重地削弱了社会有机团结的合作意识。近些年来所发生的诸多典型个案说明,以法律来建构社会秩序的实践在诸多方面是急需我们加以深刻反思的,没有良好的道德秩序和诚信体系作支撑,没有良好的司法职业伦理作依托,司法的社会性维度和社会效果最终必然会大受影响。正如美国学者亚伯拉罕所言,法律,无论是从其程序方面还是实体方面,它在本质上都是由那些其观念和解释受到随时间变迁而改变的流行风尚影响的人创立和执行的,因此,“正义的品质更多地依赖于那些执行法律的人的品质,而不是这些人贯彻执行的内容。”[33]P1
三、结语
就社会治理方式而言,现代社会中的权利冲突和多元道德观念冲突无疑需要以具有稳定性和可预测性的普适性法律规则来加以调整,法治必然成为现代社会治理的基本方式,“法治的兴衰与国家的发展息息相关”[34]。然而,人类的法律史和道德实践史总是相互交错和相互促进的。具体到我国的法律实践当中,长期以来在“法律是社会最低限度道德”的观念影响下,法律与道德之间发生了绝然的社会分离;而在司法裁判领域当中,法官只对法律“忠诚”而不得考虑个案“情理”因素的司法裁判观念,无疑在加剧着道德从社会生活当中的隐退。上述现象,说明了人们只关注自己的权利而严重忽视了自己义务履行的社会生活现实,道德尤其是公共道德和社会核心价值观似乎在日益显得不重要了。但是,人类法律实践史告诉我们,法律与道德作为两种最重要的社会规范总是相辅相成,人们对法律的信仰总是以良好的社会道德秩序为基础的,现代国家不仅是法治建设的承担者,也是道德建设的承担者,并保障法律实践与道德实践之间的高度有机统一。
司法原情作为传统中国的司法裁判方法,其服务于人治主义的伦理社会,必然会陷入到某种“泛道德主义”的司法实践困境当中,但是对于当前处于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而言,司法原情却具有重要的社会实践价值,是增强司法的社会性维度和追求司法社会效果的重要方法论资源。在司法裁量当中,法官总是面临对法律、政策、社会情理、个人权利和公共需求等之间关系的微妙权衡,这种权衡应该建立在努力保障法制统一性和实现个案实质正义的基础之上。[35]尤为重要的是,司法原情所强调的对法律因素和“情理”因素的综合考量,保障司法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之间的有机统一,这对于树立司法的权威性和公信力而言,无疑发挥着不可取代的司法实践价值,能够积极回应社会对实质法治主义的相关诉求,“司法的目的应视为赋予我们的公共价值以意义,判决应当被视为对这种意义的检验和精确化。”[31]P16
[1] [德]古斯塔夫·拉德布鲁赫.法律智慧警句集[M].舒国滢译.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
[2] [美]詹姆斯·J﹒赫克曼.全球视野下的法治[C].高鸿钧,等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4.
[3] 林来梵,刘练军.论宪政政制中的司法权[J].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2.
[4] 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5] 瞿同祖.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M].北京:中华书局,2003.
[6] [美]罗伯托·曼戈贝拉·昂格尔.法律分析应当为何?[M].李诚予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7.
[7] [英]迈克尔·欧克肖特.政治中的理性主义[M].张汝伦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
[8] [美]本杰明·卡多佐.司法过程的性质[M].苏力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9] [美]黄宗智.清代以来民事法律的表达与实践(卷三)[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4.
[10] 范忠信、郑定、詹学农.情理法与中国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11] [日]滋贺秀三等.明清时期的民事审判与民间契约[C].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
[12] 徐忠明.《情感、循吏与明清时期司法实践》[M].上海:三联书店,2009.
[13] 邓勇.论中国古代法律生活中的“情理场”[J].法制与社会发展,2004,5.
[14] 徐忠明.明清时期的“依法裁判”:一个伪问题?[J].法律科学,2010, 1.
[15] 汪雄涛.明清诉讼中的情理调处与利益平衡[J].政法论坛,2010,3.
[16] 张中秋.原理及其意义[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0.
[17] [德]马克斯·舍勒.知识社会学问题[M].艾彦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2.
[18] [法]罗伯特·雅各布.上天·审判[M].李滨译.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3.
[19] 高浣月.清代刑名幕友研究[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
[20] 张全民.郑克法律思想初探[J].法制与社会发展,2004,6.
[21] [日]滋贺秀三.中国法文化的考察[J].比较法研究,1988,3.
[22] 公丕祥.法制现代化的理论逻辑[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
[23] [英]博温托·迪·苏萨·桑托斯.迈向新法律常识[M].刘坤轮,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24] [日]川岛武宜.现代化与法[M].申政武,等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
[25] [德]卡尔·恩吉施.法律思维导论[M].郑永流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
[26] 加拿大司法委员会.加拿大法官行为评论[A].怀效锋.法官行为与职业伦理[C].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
[27] 徐忠明.众声喧哗:明清法律文化的复调叙事[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
[28] [美]米尔伊安·R·达玛什卡.司法和国家权力的多种面孔[M].郑戈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
[29] [美]萨利·安格尔·梅丽.诉讼的话语[M].郭星华,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30] 江必新.法官良知的价值、内涵及其养成[J].法学研究.2012,6.
[31] [美]欧文·费斯.如法所能[M].师帅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8.
[32] 陈义钟.海瑞集(上册)[M].北京:中华书局,1962.
[33] [美]亨利·J﹒亚伯拉罕.司法的过程[M].泮伟江,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34] 蒋晓伟.论我国的法律文化[J].政法论丛,2012,5.
[35] 王国龙.裁判理性与司法权威[J].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3,4.
(责任编辑:黄春燕)
Judicial Emotion: the Tradition and Its Contemporary Value
WangGuo-long
(the Northwest University of Politics and Law, Xi’an Shanxi 710063)
Both legal effects and social effects are the foundation of judicial credibility, but the formlism of the rule of law often stresses the supremacy to legal effects and ignores its social effects. As an important judicial method in the tracditional China, the judicial emotion gives a comprehensive considerations between the law and the emotions, which is still very important to the construction of judicial authority and judicial credibility now. The judice can positively response to the relevant appeals in society by judicial emotion.
judicial emotion; judgement of law; judicial credibility
1002—6274(2015)01—027—09
本文为2014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法律统一适用与自由裁量的规范问题研究”(项目编号:14XFX003)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王国龙(1976-),男,江西吉安人,法学博士,西北政法大学刑事法学院教授,陕西师范大学哲学博士后流动站研究人员,西北政法大学“法律方法与法律思维研究所”副所长,研究方向为法律方法论。
DF0-051 < class="emphasis_bold">【文献标识码】A
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