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恶魔抽中的少年
2015-01-2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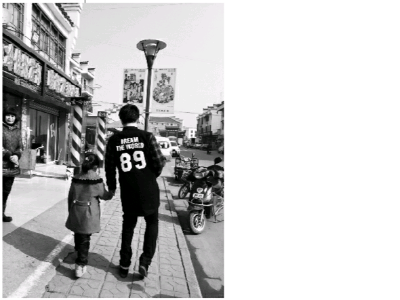


南方周末记者 郭丝露 发自安徽马鞍山 江苏镇江
随着国产脊灰灭活疫苗上市,因疫苗不良反应致残的苦难将彻底终结。然后,那段历史遗留下来的上百个家庭仍在为获得应有的赔偿和尊重而奔走。
“国家发明灭活疫苗了。”当章科推门进屋时,他的姐姐章燕小声对他说。
“别说了!你能不能让我安静一会!”章科吼道,他攥紧拳头,转身冲出家门。
“疫苗、糖丸、瘫痪……11年过去了,这些词在他面前还是不能提。”章燕说。章科是小儿麻痹症患者雅昕的父亲。
2015年1月14日,在一个名为“无辜的孩子”的QQ群里转发着一条新闻:中国自主研发的Sabin毒株灭活脊髓灰质炎疫苗(以下简称灭活疫苗)已正式获批,2015年5月将投产上市。
群里两百多个家长意识到,他们或许将是中国最后的脊灰(脊髓灰质炎的简称,俗称小儿麻痹症)家庭。
他们的孩子疑似因为接种脊灰减活疫苗(俗称糖丸)而引发疫苗相关病例(以下称VAPP),用灭活疫苗替代减活疫苗被认为是根除这一问题的有效手段。
家住河北燕郊的章燕看到新闻时,她的侄女雅昕正趴在身边。11岁的雅昕脊椎向左弯成S形,挤压左侧内脏。她至今无法站立行走,向右趴着是最舒服的姿势。
直到2014年7月,雅昕才被户口所在地廊坊市医学会鉴定为VAPP患儿。
据世卫组织估计,因接种首支脊灰减活疫苗染上脊髓灰质炎的概率是两百五十万分之一。按这个概率以及中国2000年至2014年首次接种约2亿支糖丸估算,仅最近15年间,中国VAPP患儿的总数在百人左右。
在日本,这种合格疫苗引发的严重不良反应伤害事件被形象地称为“恶魔抽签”。
“不知情”的家长“不能说”的医生
当天晚上,章燕将国产灭活疫苗即将上市的消息贴到了群里,应者寥寥。
在群里能引起热烈讨论的,多是治疗小儿麻痹症的偏方。
家长们的偏方千奇百怪:新鲜的蝙蝠煮水喝;摘一百支莲蓬,每支取一颗莲子吃……几乎每个家长,都曾涌进电视广告里的私人诊所,也曾到乡下求助过“神婆”。
“新家长一入群,就着急问哪个医院治病比较好。老家长只能告诉他,哪家都一样,小儿麻痹症治不好。”44岁的群主周寒冰说。
她自称“苗一代”——1995年起,中国宣布本土已无脊髓灰质炎野病毒,她的儿子松涛1995年1月出生,是获得国家鉴定最早发病的VAPP患儿之一。
吃下糖丸,实际上等于吃下一颗毒性已被削弱可控的脊髓灰质炎病毒。北京大学医学部免疫学系副主任王月丹解释,对绝大多数孩子来说,病毒很容易就能在消化道中被免疫系统“打败”,一般不会出现任何症状。
有时,病毒经由消化道侵入血液,孩子就会发热、嗜睡,这种普通不良反应症状和普通感冒相似。在非常罕见的情况下,病毒随着血液流向全身,如果侵犯神经中枢细胞后,孩子则会浑身瘫软无力。
在多数家长看来,嗜睡是感冒快好的征兆。周寒冰的母亲倪延风记得,高烧过后,松涛整整睡了一天。
倪延风是安徽马鞍山医院妇产科门诊的护士长,但她并不知道,脊灰病毒正在外孙神经系统肆虐。在自己工作的医院,她亲手为外孙肌肉注射了抗生素。
大连的小艾就是因为显得“很没精神”,才被妈妈抱到广场透气。大人们变着法逗小艾开心,她咯咯笑着,忽然浑身抽搐,脸色青紫,翻起了白眼,被送到医院后下肢已经不能动弹。
家长通常很少意识到,这会是使用疫苗后的严重不良反应。
“一般发烧感冒,都会到村卫生所和县医院看,不可能找到我们这里。”陈义亮是镇江市三五九医院医生,这里曾经是全国小儿麻痹症后遗症矫治中心,行医二十多年来,他从未接诊过一个发病中的小儿麻痹症患者。
即便是及时找到了专业医生,也很难轻易被诊断为小儿麻痹症。
根据原卫生部发布的《预防接种异常反应鉴定方法》,接种后的异常反应,应该由各地疾控中心组织专家调查诊断。2010年,卫生部再次强调:任何医疗机构和个人,不能对预防接种异常反应做出调查诊断结论。
专业医生,大多已失去了脊灰诊断权。
在北京儿童医院神经科检查后,章燕一再追问雅昕病情,医生攥紧了拳头说:“我不能说。”
因为自责,倪延风辞去了主任护士的职务,多年来她一直百思不得其解:“我打了那么多年针,怎么一下子把自己外孙打瘫了呢?”
“打针伤到神经和儿麻后遗症的症状是完全不同的。”陈义亮说。2000年,倪延风带松涛来到镇江,当时5岁的松涛成为陈义亮接诊的第一个VAPP患儿。“我刚说完,松涛姥姥就立刻哭了出来。”
但在鉴定结果出来前,陈义亮只能在松涛病例“诊断”一栏中,写下“迟缓性麻痹”。“我可以治疗,但不能说是不是脊灰,更不能说是不是糖丸引起的。”
多闹多赔、不闹不赔?
随着越来越多的病例涌现,2008年以后,VAPP鉴定比过去顺畅些,但国际通行的疫苗不良反应赔偿却迟迟不能到位。
安安出生在医学世家,2013年4月接种糖丸时,她的妈妈金娟英问遍周围医生亲戚,回答都是:吃吧,没问题。
灭活疫苗获批的那天,心神不宁的安安父亲把自己的出租车开入了河沟,只能在零下4度的深夜,穿着裤衩把车拖上岸。那天,他刚拿到安安“脊灰减活疫苗预防接种异常反应”的鉴定书,但与当地政府讨论赔偿金额,却并不理想。
2008年,卫生部联合七部委下发《关于做好脊髓灰质炎疫苗相关病例鉴定及善后处理工作的指导意见》,明确规定对于VAPP患儿,应当给予一次性补偿。
但文件也规定,补偿费用由各省级政府财政部门在预防接种工作经费中安排,具体补偿方法,由各省决定。
QQ群里的家长大多来自城市,对这些文件如数家珍。
群里年龄最大的家长吴霖,已经帮几十个家长成功获得鉴定;周寒冰为松涛准备的材料,厚度超过一厘米,一些医学资料甚至是用英文写成。群里分享的大多是各省的具体规定、国际通行的做法。
在美国,减活疫苗异常反应的补偿经费,是从疫苗厂家缴纳的税收中支取;法国在国家预算中设立了专项基金,台湾地区则规定,政府采购的中标疫苗企业必须为此捐款,金额为每支疫苗10元新台币。
而在中国大陆,主要还是地方政府埋单。
尽管2014年卫计委再次发文,要求“进一步做好预防接种异常反应处置工作”,但这份文件的名称,仍是“指导意见”,各级政府该怎么做,仍无具体标准。
9岁的俊晖是在河北吃下的糖丸,但因为户籍所在地是安徽,两边的疾控部门,就曾打起拉锯战。
松涛最后拿到来自安徽省政府52万元人民币的一次性赔偿。周寒冰说,这只占松涛20年来医药费的三分之一。
缺乏完整且持续的救济制度,想要赔偿只能靠“个人能力”了。
2013年,松涛入大学前,当地政府给予2000元补贴。周寒冰问:“明年呢?”得到的回答是:“明年看政策吧,有就有,没有就没有。”
2008年之前出生的VAPP患儿的家长,自称“苗一代”。此后的则被算作“苗二代”。与“一代”的冷静相比,“二代”维权更积极。
吴霖是QQ群里最年长的“苗一代”。年关将至,他在群里贴了“2014年总结”。在倡导了一番理性维权之后,吴霖在最后写道:“遗憾的是,‘多闹多赔、少闹少赔、不闹不赔仍是众所周知的硬道理。”
失去的尊严
面对南方周末记者,章燕拿出了雅昕在各地上访的照片。
上访的家长队伍后,通常是孩子们组成的队伍。雅昕站不起来,只能趴在地上,她将树叶摆成一排,抓来蚂蚁放在树叶上爬。因为长时间呆在地上,无论在哪儿,蚂蚁都是她最好的玩伴。
松涛和小凯都在1995年出生,松涛瘫痪的那一天,小凯也吞了糖丸。松涛只记得,他和小凯曾在原卫生部门口“撒了一泡尿”。
两岁的安安,还不能清晰发出“爸爸、妈妈”,但医生问安安你哪里不好时,她却已学会清晰的童音回答:右脚。“右脚”是安安两年多以来听到最多的词。
“孩子没有错,不应该承担这些。”父亲丁力尽量避免和俊晖谈到上访、索赔的字眼。爸爸在做什么,他不全懂。坐在爸爸旁,俊晖翻看健康课本上“计划免疫”一章,对计划免疫,他的理解是“打针”。
因为不能出门,许多VAPP患儿的房中都摆满了绿色植物。俊晖的窗前,是北京朝阳区最繁华的街道之一。
周寒冰心里清楚,国产Sabin株灭活疫苗上市后,松涛他们或许将是最后一批VAPP患儿了。和卫生部门打交道20年,她觉得这是“卫生部做得最好的一件事”。
知道VAPP患儿故事的人,都会发出一声叹息:太可怜了。不知道的,会啐一口,叫一声“瘸子”或“怪物”。
周寒冰为自己的孩子抱不平:“他们是为计划免疫做出牺牲的孩子,但没有人同情他们,也没有人给他们应有的尊严。”
现在,“无辜的孩子”QQ群中,家长们的共同目标是追求长期、持续的赔偿,为的是维护孩子的尊严。
“这样,孩子或许会觉得自己不是累赘:家人虽然要照顾我,但也会因为我给家人补贴,就像是给家人发工资一样。”周寒冰说。
松涛最经常穿的两件外套,一件写着“Sick and Tired”(生病且累),一件写着“Dream the world”(远大理想)。
身心俱疲,让更多家长早已坚持不住。小凯的母亲蔡善香带领全家,已经搬离安徽,在苏州定居。群里的人来了又走,有些得到一次性补偿的人,QQ头像更是再也没有亮起。
“这本来就不是一件好事,他们想好好生活,忘记这段苦难。”周寒冰说。
雅昕写了一封信,仔细地封好,要交给在她一岁时就离家的妈妈。“我觉得孩子的妈妈要么已经疯了,要么早就不在人世了。”姑姑章燕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此时,雅昕就静静趴在一旁,瞪大眼睛听。
(文中未成年人均为化名,所拍摄图片已获监护人书面授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