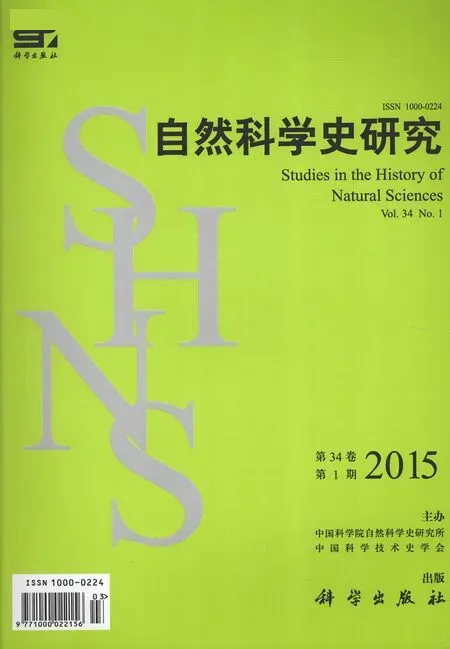宋代士人对农学知识的获取和传播——以苏轼为中心
2015-01-29曾雄生
曾雄生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北京 100190)
中国的读书人,自孔夫子以后就一直认为农学是一个不太体面的行当。学稼、学圃被视为“小人之事”。流风所至,不仅学农之人鲜少,偶尔一、二杰出之士也自觉难登大雅之堂。[1]如北魏贾思勰在著《齐民要术》时,就交待“鄙意晓示家童,未敢闻之有识”,担心“览者无或嗤焉”。([2],5页)唐末韩鄂著《四时纂要》也“希好事英贤,庶几不罪于此”[3]。然而,宋代以后,出于生计之虑,职责所需,以及学术追求,士人对农学的态度始有所改变。这种改变带动了农学知识的增长。仅从农学知识的载体农书来看,宋代的农书数量空前增加。①据《汉书·艺文志》所载,汉代及汉代以前,共有农书9种;又据《隋书·经籍志》所载,隋代及隋代以前,共有农书5种19卷,而据《宋史·艺文志》的记载农书107部,423卷篇。这还不包括散见于“五行志”、“医家类”及“杂艺术类”中,诸如《辨养马论》、《相马经》、《马经》、《相马病经》、《疗驼经》、《明堂灸马经》等畜牧、兽医著录。印刷术的发明及使用自然是农书得以流传的一个重要条件,但农学知识的增长才是农书得以出现的根本原因。
农书中的农学知识是由知识的生产者农民,经过农书的作者士人的提炼加工形成文字,并得以在读书人中传承。农书出现的背后,是一支数量相应的作者队伍,他们是士人的代表。但他们在人数上只占到士人的极少部分。农书作者之外,广大的士人对于农业知识也多少有所接触和了解,一些人甚至也有自己的心得,并形成文字,部分辗转于农书之中。考察士人对农学知识的获取,可以帮助我们更加深入地农学知识增长的机制,以及农学在中国传统学术中的状态。
本文以苏轼为主要线索,试图在农书作者之外,探寻士人对于农学知识的获取与传播。士为古代四民之一,指读书人,也泛指知识阶层。士与四民中的农、工、商相比,有其显著特点,这就是读书。读书使其“通古今,辩然不”(《白虎通·爵》),具备这一条件便可出仕做官,参与管理社会,所以古人又说,“学以居位曰士”(《汉书·食货志》);“以才智用者谓之士。”(《后汉书·仲长统传》)苏轼是宋代士人的典型代表和全部人生的缩影。他自幼读书,在文学艺术方面有极高的造诣,是唐宋古文八大家之一,在诗、词、赋、散文、书法、绘画等众多领域都有杰出的贡献。他也在中央机构和地方衙门担任过行政职务。同时他自小接触过农业,并亲身从事过农业生产,热心推广过他所发现的农具,对同侪的农学著作予以高度的肯定,也偶发一些关于农业的议论。他虽然没有系统的农学著作问世,也没有人将其视为农家者流,但这并不能掩盖苏轼在农学上的贡献。元代王祯《农书》提到或引用苏轼的文字就有不下10处之多。理解苏轼与农学的关系,解剖苏轼对于农学知识的获取和传播,就可以了解农学在宋代乃至传统中国知识与社会之一斑。
1 出身
苏轼的故乡眉州眉山位于成都平原西南部,岷江中游和青衣江下游的扇形地带。是农业最发达的地区之一,以水稻为主产,蔬菜和林木种植也较为发达。这在苏轼的笔下都有所反映。苏轼在23岁之前,一直生活在老家眉山。从小的耳濡目染,使他对当地的农业十分熟稔。故乡的生活给苏轼打下深刻的烙印,构成了他认识世界的基础。在离开家乡的日子里,他总是记起蜀人或蜀事,以及年少的过往。宋仁宗嘉祐四年(1059),24岁的苏轼侍奉父亲老泉南行,第一次离开家乡,想念起家乡的蔬菜,作《春菜》一诗,细数蜀地丰富多彩的蔬菜品种及其生产和食用方法,包括蔓菁、韭、荠、青蒿、茵陈、甘菊、坡棱(菠菜)、菘、葛、笋等多种([4],第9248页)。嘉祐六年(1061),在凤翔任判官时,看到当地有大片的稻田,留下了“平湖种稻如西蜀”([4],9125页)的诗句。元丰元年(1078)七月十五日,时年43岁在徐州任职的苏轼在为家乡远景楼所作题记中记载了当地水稻生产的全过程,其中尤以水田除草为详。其曰:
……岁二月,农事始作。四月初吉,谷稚而草壮,耘者毕出。数十百人为曹,立表下漏,鸣鼓以致众。择其徒为众所畏信者二人,一人掌鼓,一人掌漏,进退作止,惟二人之听。鼓之而不至,至而不力,皆有罚。量田计功,终事而会之,田多而丁少,则出钱以偿众。七月既望,谷艾而草衰,则仆鼓决漏,取罚金与偿众之钱买羊豕酒醴,以祀田祖。……([5],前集,390页)
这应是早年生活留给他的印记。川西和整个东亚地区一样高温高湿,十分有利于杂草繁殖,如果不进行积极的除草,就很难有收获,于是中耕除草成为东亚农业的特点。东亚的农业技术也最早围绕着除草展开。精细的稻作技术也最先体现在除草上面。所以苏轼在无意中接触到东亚农业的本质。
因为从小在稻乡长大,对种稻比较熟悉,所以他在黄州东坡躬耕时能够驾轻就熟。他在《东坡八首》诗之三中一再提到蜀人的种稻经验:
种稻清明前,乐事我能数。毛空暗春泽,针水闻好语。(蜀人以细雨为雨毛,稻初生时,农夫相语稻针水矣。)分秧及初夏,渐喜风叶举。月明看露上,一一珠垂缕。秋来露穗重,颠倒相撑拄。但闻畦垄间,蚱蜢如风雨。(蜀中稻熟时,蚱蜢群飞田间如小蝗状,而不害稻。)新春便入甑,玉粒照筐筥。我久食官仓,红腐等泥土。行当知此味,口腹吾已许。([5],前集,175 页)苏轼及其弟苏辙(子由)在家乡时还学会了果树嫁接技术,他说:
蜀中人接花果,皆用芋胶合其罅。予少时颇能之。尝与子由戏用若(当作苦)楝木接李,既实,不可向口,无复李味。《传》云:‘一熏一莸,十年尚犹有臭。’非虚语也。芋自是一种,不甚堪食,名接果。[6]
相比之下,苏轼对于种麦的了解较少,所以后来他在东坡种麦时要向当地老农请教。这也可能是他的家乡蜀中种麦不多的缘故。
传统中国是个农业社会,即便是出身书香门第的苏轼,也不可避免地要接触到农业实际,而对于农家子弟来说,其接触农业的机会更多。这些农家子弟较之官宦世家对农业有更多的体会。比如,黄震说:“太守是浙间贫士人,生长田里,亲曾种田,备知艰苦”([7],2222页);高斯得自言“太守蜀人也,起田中,知农事为详”([8],99页),故《宋史》本传中说他是“稼之子也”;陈造说:“权守,淮人也,亦以农起家”[9];真德秀诗:“使君元起自锄犁,田野辛勤事总知”([10],卷1,60页)。这些地方官员强调自己的出身,意在拉近与农民的感情。虽然农家子弟做官并不一定要为农业服务,但身处农家环境还是会受到农业潜移默化的影响。陆九渊就记载了他家利用长大镢头进行深耕,通过提高粒数提高水稻产量的经验。[11]显见一个人的出身背景对于其农学知识获取的影响。放大历史来看,中国历史上但凡在农学上有所贡献之人,多少都是从小就接触过农业,并对农业产生兴趣。传说中农业的始祖之一,周人的祖先后稷如此①《史记·周本纪》:“弃为儿时,屹如巨人之志。其游戏,好种树麻、菽,麻、菽美。及为成人,遂好耕农,相地之宜,宜谷者稼穑焉,民皆法则之。帝尧闻之,举弃为农师,天下得其利,有功。”,发现早熟御稻米的清康熙大帝也如此②康熙《庭训格言》:“朕自幼喜观稼穑,所得各方五谷、菜蔬之种,必种之,以观其收获”。。
家庭是农业社会的基本单位,在知识的创造和传承方面起到重要的作用。生于斯,长于斯。自幼的耳濡目染,使家中的每个成员对于生产和生产相关的知识都有相当的了解。苏轼十岁那年,“父洵游学四方,母程氏亲授以书”,苏轼从母亲的行为中直观地感受到了人与环境,特别是人与生物之间的关系。苏轼记得“少时所居书堂前,有竹柏杂花丛生满庭,众鸟巢其上。”这都是他的母亲“武阳君恶杀生,儿童婢仆,皆不得捕取鸟雀”的结果。于是“数年间,(鸟雀)皆巢于低枝,其鷇可俯而窥。……闾里间见之,以为异事”。进而悟得人与动物的和谐相处之道,认为人想要免除“蛇鼠狐狸鸱鸢之忧”,则不能离鸟雀巢太远,人既不杀鸟雀,则鸟雀自然就会接近人,人也就此可以免除蛇鼠狐狸鸱鸢之患。([6],2374页)设使苏轼长于畎亩,他对于农业的认知必将更进一步。
孔子有言,“吾不如老农”、“吾不如老圃”,客观地点出了士人知识的局限性。历史上很多士人由于人生的某种境遇,而被迫躬耕之时,往往发现自己从事农耕的体力和智力是不够的。体力不支,所以他们需要“佣人代作”。知识不足,所以他们需要接受农民的指导。晋代陶渊明辞官归田时,因缺乏基本的农事常识,不清楚何时整地,何时播种,需要农民来告诉他,“农人告余以春及,将有事于西畴”。由于缺乏经验,尽管他“晨兴理荒秽,戴月荷锄归”,早出晚归,仍然不得其法,结果是“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苏轼在他的生涯中也遇到过陶渊明一样的困惑。这也是他后来需要努力学习的地方。
2 读书
老农的知识有用,但也有限。他们的知识和经验仅适合于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上,且大多也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读书是士人本色。借助于读书,士人能够突破农民的局限,接触到更为久远和宽广的知识,且这些知识为一般老农所不具备。今本《齐民要术·杂说》言:
夫治生之道,不仕则农;若昧于田畴,则多匮乏。只如稼穑之力,虽未逮于老农,规划之间,窃自同于后稷。([2],15页)
士人从事农业,体力上虽然比不上老农,但有智力上的优势。士之为士,在于他们能够读书识字写文章,可以运筹帷幄。也就是说,就农学知识而言,士人在一些方面不及农民,但在另一些方面则胜于农民。
苏轼出身于书香之家,“生十年,父洵游学四方,母程氏亲授以书,闻古今成败,辄能语其要。……比冠,博通经史,属文日数千言,好贾谊、陆贽书。”(《宋史·苏东坡传》)他年轻时即“发愤识遍天下字,立志读尽人间书”,非常认同好友黄庭坚的说法,“士大夫三日不读书,则义理不交于胸中,对镜觉面目可憎,向人亦语言无味。”([6],2542页)他认为读书不应有任何功利色彩,“治生不求富,读书不求官。”([5],前集,241页)即便是在艰难的环境里仍然没有放弃读书,谪居黄州期间,读书成为他唯一的乐趣,“自到此,惟以书史为乐,比从仕废学,少免荒唐也。”([6],1520页)同时他有自己的读书方法,认为“旧书不厌百回读,熟读深思子自知……我昔家居断还往,著书不复窥园葵。”([5],前集,54页)“退笔如山未足珍,读书万卷始通神。”([5],前集,94页)读书使苏轼具有广博的知识,他在认识事物的时候,除了可以很自然地联系起自己的经验以外,相关的历史掌故也可以随手掂来。
博览是宋代许多士人的共同特点。与苏轼有过交集,写作水稻品种专志《禾谱》一书的曾安止曾经跟大学博士程祁谈到“黄帝问师旷之说”,诸如“杏多实不虫者,来岁秋必善。五木为五谷之先,故欲知五谷,但观五木,择其木之盛者,来年必益种之”。这些内容来自《师旷占》一书,该书是古代的一本占候书,北魏贾思勰的《齐民要术》中便有引用。可见曾安止应该是读过这类的书籍。曾安止还撰写过《车说》一篇,据程祁所说,该书“兼收博引,凡所以为车者,洪纤小大,无不具有。”[12]《禾谱》也是如此,就其现存文字来看,其内容除了引经据典之外,书中所记水稻品种近自龙泉(江西遂川),远至太平(安徽当涂),而以西昌(今江西泰和)为主,一共有50余种之多。是中国农学史上最早的一部水稻品种专志。显然像这样的一些知识,是一般农人和手工业者所不具备的。绍圣元年(1094),当苏轼被贬惠州,南行经庐陵西昌(今江西吉安泰和县),获赠曾安止所著《禾谱》。苏轼读后的评价是“文既温雅,事亦详实”。
读书是使一个士人在农学上做出贡献的前提。南宋洪兴祖对《陈旉农书》的作者陈旉做过这样的介绍:
西山陈居士,于六经诸子百家之书,释老氏黄帝神农氏之学,贯穿出入,往往成诵,如见其人,如指诸掌。下至术数小道,亦精其能,其尤精者,《易》也。[13]所谓“小道”,即包括农学在内的诸多学问。
农书是士人获取农学知识最快捷的途径,尽管当时能够读到的农书还不多,主要有汉代的《氾胜之书》、北魏贾思勰的《齐民要术》及唐末五代韩鄂的《四时纂要》等。但自唐德宗贞元五年(789)以后,已形成了一种阅读农书的机制。每年的二月初一中和节,官员都要向朝廷进献农书,朝廷经过审订之后,再向地方推广。宋真宗天禧四年(1020)下诏刻唐韩鄂《四时纂要》及《齐民要术》二书,“以赐劝农使者”。宋真宗还曾下令朝臣编纂了一部十二卷的《授时要录》。类似的官修农书还有《大农孝经》、《本书》等。在献与赐的往复之间,阅读农书成为一些官员的必修课。田锡在《谢赐历日》中提到“读氾氏之农书,合周公之时训”[14],也就是说官员试图将历日和农书的内容统一起来,以便因时行事。司马光在一首诗中也提到“喜观氾氏述”([4],第9册,第6021页)。南宋初年葛祐之在为《齐民要术》所作后序中提到:
《齐民要术》旧多行于东州。仆在两学时,东州士夫有以《要术》中种植、畜养之法为一时美谈。[15]
除了《氾胜之书》、《齐民要术》等外,宋代士人感兴趣的农书中还有一本是由唐道士王旻所著的《山居要术》。祖无择曾向余靖借阅该书,二人曾题诗唱和。祖无择诗云:
张衡已作归田赋,氾胜仍修种树书。愿借山居精要术,欲将嵩洛葺吾庐。([4],4432页)
余靖诗云:
第3步:对Opt_rules中的每条规则(xi)B→Dk,如果存在(xj)B→Opt_rules{(xi)B→Dk}满足(xi)B⊆(xj)B和conf((xj)B→Dk)=conf((xi)B→Dk),更新Opt_rules为Opt_rules{(xi)B→Dk};
经济谅周当世务,收藏敢秘老农书。相逢莫羡山居好,归去蓬山有直庐。([4],2674页)
显见该书在宋代士人之间较为流行。
士人读农书目的在于学以致用。宋代官员衔劝农之命,一些地方官员根据自己的理解,把占候作为劝农的举措之一,在诸如丙午、正旦、月朔、甲子、先分后社以及有闰之岁等一些重要的日子里都要进行占候活动,以便使其治理下的农民对于未来一段时间的农事安排早做准备。占候的依据之一便是来自类似《田家五行》一类的农书。真德秀说:“农书之占,厥有常验。此某之所以奔告于神,而不敢后也。”([10]卷四十九,12页)
农书对于在位的官员如此,对于不在其位,或者是那些厌恶官场,有归田之心的士人来说,更是不可或缺。尤其是当生计发生变故的时候,农书更成为重要的参考依据。南宋官员陈造,“遭宋不竞,事多龃龉,自以为无补于世,置之江湖乃宜,遂号江湖长翁”,他曾赋诗明志,表露对隐居生活的憧憬,“夹沟欲插柳千株,绕舍先营五亩蔬。供爨御冬须次第,西归新得务农书。”([4],第45册,第28248页)失禄之人希望农书能够为自食其力的生活提供指导,以便如陆游所言“闻鸡而起,则和宁戚之牛歌;戴星而耕,则稽氾胜之农书”[16]。陆游认为,“谋生在衣食,不仕当作农。识字读农书,岂不贤雕虫。”([16],924页)陆游的诗中多次提到读农书的情形,如,“农书手自钞”([16],363页),“旧学樊迟稼,新通氾胜书”([16],437页),“农书甚欲从师授”([16],962页),“诵咏农书儆惰偷”([16],1000页),等。也因为陆游喜读农书,又善诗,所以当曾之谨在完成《农器谱》一书后,连同他祖父曾安止的农书《禾谱》一起赠送给了他,并向他求诗([16],3771页)。
读书是区别士人和农民的地方,也是士人的农学知识得以增长的途径。无论出于何种动机,读书,特别是读农书对于士人农学知识的增长都是大有裨益的。苏轼在武昌发现秧马之后,便能很快想到他曾读过《史记》的相关记载。
《史记》:禹乘四载,泥行乘橇。解者曰:橇形如箕,擿行泥上。岂秧马之类乎?([5],上册,499 页)
后来他又将秧马与他所读过的《唐书》联系起来。他说:
吾尝在湖北,见农夫用秧马行泥中,极便。顷来江西,作《秧马歌》,以教人,罕有从者。近读《唐书·回鹘部族黠戛斯传》:“其人以木马行水上,以板荐之,以曲木支腋下,一蹴辄百余步”,意殆与秧马类欤?聊复记之。异日详问其状,以告江南人也。([6],2153 页)
王莽末,天下旱蝗,黄金一斤,易粟一斛。至建武二年,野谷旅生,麻、菽尤盛,野蚕成茧,被于山泽,人收其利,岁以为常。至五年,野谷渐少,而农事益修。盖久不生谷,地气无所耗,蕴蓄自发,而为野蚕、旅谷,其理明甚。庚辰岁正月六日,读《世祖本纪》,书其事,以为卫生之方。([6],2366 页)
苏轼的老师欧阳修也有这样的认识,“久废之地,其利数倍于营田”[17]。也是基于对历史的认识,苏轼反对开汴水支流八丈沟以种植水稻,他说:“汴水独流,自生民以来不以种稻。秦人之歌曰:‘泾水一石,其泥数斗,且溉且粪,长我禾黍。’何尝言‘长我粳稻’耶?”([5],奏议集,404页)于此可见,读书读史对苏轼农学知识的增长的作用。
3 宦游
士人的农学知识还有一点为普通农民所不及的地方,这就是他们的见识比较广泛。农业生产必须经历春耕夏长秋收冬藏的过程,要求人们过着相对定居的生活,受到农业文化的影响,中国传统的农民养成了安土重迁的生活习惯。一般人的生活范围也就在方圆10里左右。只有“读万卷书”的士人和极少数的商人才可能“行万里路”。这其中有自觉,有无奈,更有制度的安排。
苏轼除在京任职史馆及中书舍人外,曾经担任过凤翔府判官(1061)、杭州通判(1071)、密州太守(1074)、徐州太守(1076)、湖州太守(1079)、黄州团练副使(1080)、登州太守(1085)、杭州太守兼浙西军区司令(1089)、颍州太守(1091)、扬州太守(1092)、定州太守、河北军区司令(1093),还曾谪居惠州(1094)、儋州(1097),往来于常州(1084、1101)等地。每到一地,他都要“入境问俗”,与农民进行交流,了解风土人情。元祐七年,苏轼在自颍州移扬州赴任的路上,舟过濠、寿、楚、泗等州,所至之处,见“麻麦如云”。他经常“屏去吏卒,亲入村落,访问父老。”([5]奏议集,538页)而地方父老也会“戴白扶杖,争来马前。”([5]前集,322页)这种交流使他对各地的农业和农民有较多的接触和了解。
在杭州和湖州等地任职期间,苏轼发现浙西地区的农业以水稻种稻为主,“种麦绝少”,但水稻种植又一直受到雨水的侵袭,尤其是在种、收两个环节,收成没有保障,生理为艰:
耕于三吴,有田一廛。禾已实而生耳,稻方秀而泥蟠。沟塍交通,墙壁颓穿。面垢落塈之涂,目泫湿薪之烟。釜甑其空,四邻悄然。鹳鹤鸣于户庭,妇宵兴而永叹。计无有食其几何,矧有无衣于穷年。([5],后集,543页)
熙宁五年(1072),他在《吴中田妇叹》一诗描述了雨水对成熟期晚稻的危害:
今年粳稻熟苦迟,庶见霜风来几时,霜风来时雨如泻,杷头出菌鎌生衣,眼枯泪尽雨不尽,忍见黄穗卧青泥,茆苫一月垄上宿,天晴获稻随车归。([5],前集,76页)元祐四年(1089)十一月初四日苏轼奏称:“勘会浙西七州军,冬春积水,不种早稻,及五六月水退,方插晚秧”([5]奏议集,470页)。元祐六年(1091)三月二十三日奏称:
窃以浙西二年水灾,苏湖为甚。……自下塘路由湖入苏,目睹积水未退,下田固已没于深水,今岁必恐无望,而中上田亦自渺漫,妇女老弱,日夜车畎,而淫雨不止,退寸进尺。见今春晚,并未下种。自今(即三月二十三日)已往,若得淫雨稍止,即农民须趁初夏秧种。([5],奏议集,507页)
也就是说,苏、湖等地的水稻播种期须推迟到四月以后,加上不少于一个月的秧龄,水稻移栽的时间最早也得在五月初以后。这和苏轼老家四川的情形大段不同。苏轼发现苏、湖、常等地的百姓采用“就高田秧稻”的办法,等到五、六月水退之后,再行移栽。([5]续集,354页)高田育秧可以避免水灾,同时也解决了水退之后,有效生产时间不足的问题。这也是后来江南地区应对季节性水灾所采取的主要办法。①明·宋应星:《天工开物·乃粒》:“湖滨之田,待夏潦已过,六月方栽者,其秧立夏播种,撒藏高亩之上,以待时也。”(广陵书社,2005,第2 页)。苏轼应是这一方法的最早记载者。
苏轼也注意到浙西水灾的另一面,即旱灾和蝗灾。苏轼在阳羡(江苏宜兴)躬耕时就曾遭遇过严重的旱灾。([6],1487页)他在《无锡道中赋水车》一诗提到龙骨水车在水稻抗旱中的作用。
翻翻联联衔尾鸦,荦荦确确蜕骨蛇。分畦翠浪走云阵,刺水绿针抽稻牙。洞庭五月欲飞沙,鼍鸣窟中如打衙。天公不见老翁泣,唤取阿香推雷车。([5],前集,100页)
苏轼在浙西期间还遭遇了严重的蝗灾,并从老农那里了解到蝗虫的发生规律,“从来蝗旱必相资”,认为蝗旱之灾具有并发性,同时也了解到“蚕一眠,则蝗不复生矣”([5],前集,109页)的自然现象。随后苏轼在出任密州太守期间又遭遇了更为严重的旱蝗之害,并引发社会动荡。由于亲眼亲历过江南的蝗灾,且一路由南向北赴任过程的感受,苏轼断定淮浙一带的蝗灾为京东“波及”所致,京东是重灾区的结论。苏轼在请求上级政府给予一定的农业税减免的同时,也希望农民在次年春雨调匀的情况下“可以广种秋稼”,以从根本上维护社会稳定([5],奏议集,412页)。这一判断和当地官吏的判断相比简直有天壤之别,当时地方官吏“皆言蝗不为灾,甚者或言为民除草。”([5],前集,359页)宦游带来的知识,于此可见一斑。
苏轼也会将宦游中所获得的知识用诸实践。浙西水乡除种植水稻之外,河湖之中还生长着丰富的水生动、植物资源,如葑、菱、莲等。宋朝时,这里的农民曾利用茭葑自然浮泛,开发人造架田。①《陈旉农书》卷上《地势之宜篇第二》:“若深水薮泽,则有葑田,以木缚为田坵,浮系水面,以葑泥附木架上而种艺之。其木架田坵,随水高下浮泛,自不渰溺。”但葑田的恶性发展也会淤塞河道,影响正常的生产和生活。苏轼在担任杭州知州时,主张开挖葑田,疏浚西湖。他从农民那里得到知识,“八月断葑根,则死不复生”,希望当时主政的皇太后能早日批准工程上马。([5],奏议集,479页)至于在开湖过程中出现的反复,苏轼发现“吴人种菱,每岁之春,芟除涝漉,寸草不遗,然后下种。”进而主张“将葑田变为菱荡,永无茭草堙塞之患。”([5],奏议集,481页)虽然菱角的种植在《齐民要术》中就有记载,但技术非常简略,无非“秋上子黑熟时,收取,散着池中,自生矣。”([2],344页)相比之下,苏轼的观察比农书的记载详细,并且将其运用于环境的整治。这也是前人所没有的知识。
苏轼每到一地都会对当地的农艺物产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在首都开封,苏轼发现“近时都下菊品至多,皆智者以他草接成,不复与时节相应。始八月,尽十月,菊不绝于市,亦可怪也。”([6],2363页)原来古人通行物候历,以物为节,不失毫厘。宋代都市及城近郊区花卉业发展迅速,嫁接技术得到广泛采用,培育出大量花卉品种。这些新品种在人工的干预之下对于自然条件并不敏感。在黄州,他首次见到了传闻已久的一种味道鲜美的蔬菜蒌蒿。“久闻蒌蒿美,初见新芽赤。”([5],前集,195页)在武昌(今湖北鄂州市),“见农夫皆骑秧马,以榆枣为腹,欲其滑;以楸桐为背,欲其轻。腹如小舟,昂其首尾,背如覆瓦,以便两髀。雀跃于泥中,系束稿其首,以缚秧。日行千畦,较之伛偻而作者,劳佚相绝矣。”([5],499页)在以后的日子里,他对此种农具进行推广。在凤翔时,他曾“时绕麦田求野荠,强为僧舍煮山羮”([4],9126页);在密州期间,他品尝到“黄耆煮粥”([4],9221页)。流放岭南期间,他发现“海南多荒田,俗以贸香为业,所产秔稌,不足于食,乃以藷芋杂米作粥糜,以取饱。”([5],续集,71页)苏轼和他的儿子还在烹调上做文章,作玉糁羹,以改进山芋的食用质量。([4],9557页)苏轼对成熟期的稻麦等作物进行过比较观察,发现“黍、稻之出穗也必直而仰,其熟也必曲而俯,麦则反是。”([6],2368页)苏轼还发现海南秫稻品种变异很快,并较早发现铁脚糯及马眼糯这两个在南方稻作区种植较为普遍的糯稻品种。②苏轼《杂记·马眼糯说》:“黎子云言:海南秫稻,率三五岁一变,顷岁儋人,最重铁脚糯,今岁乃变为马眼糯。草木性理,有不可知者。如欧阳公言,洛中牡丹时出新枝者,韩缜〈花谱〉乃有百余品,若随人意所欲为者,可奇也夫。”(《苏轼文集》卷73,第2369页)在岭南期间,最令他感兴趣的还是各种热带水果,有卢橘、杨梅、荔枝、龙眼。他最喜欢的是荔枝,认为荔枝“厚味、高格两绝,果中无比。”([5],后集,510页)他希望“日啖荔支三百颗,不妨长作岭南人”([5],后集,516页)他也喜欢龙眼,认为“廉州龙眼质味殊绝,可敌茘支。”([5],后集,530页)他也吃过槟榔,感叹“奈何农经中?收此困羇旅”([5],续集,5页)。苏轼和许多栽培植物都有过亲密接触,除了稻、麦、桑、麻、蔬菜、果树等常见农作物之外,见于诗文中的还有牡丹、芍药、菱、芡、桃、李、杏、梨、枣、樱桃、石榴、柑、橘、柚、荔枝、杨梅、枇杷、橄榄、海棠、樗、槐、松、桧、柳、杉、竹、柏、桧柏、含笑、栀子、菖蒲、桄榔、菊、土芋、等。可以说,苏轼接触和记载的农作物远在一般农书之上。
宦游增长了见闻。宋人已注意到农田中虫吃虫的现象,“甲辰兖州言,蚄虫生,有虫青色,随啮之,化为水。时谓‘旁不肯虫’”([18],第6册,卷76,1731页)。沈括在《梦溪笔谈》中也提到过这样的一个例子:
元丰中,庆州界生子方虫,方为秋田之害。忽有一虫生如土中狗蝎,其喙有钳,千万蔽地,遇子方虫,则以钳搏之,悉为两段,旬日子方皆尽。岁以大穰。其虫旧曾有之,土人谓之“傍不肯”。([19],21页)
苏轼虽然没有亲见过,但他在宦游中却听到了这样的故事:
元祐八年五月十日,雍丘令米芾有书,言县有虫食麦叶而不食实。适会金部郎中张元方见过,云:“麦、豆未尝有虫,有虫盖异事也,既食其叶,则实自病,安有不为害之理?”元方因言:“方虫为害,有小甲虫,见,辄断其腰而去,俗谓之旁不肯。”前此吾未尝闻也,故录之。([6],2364页)
这是关于麦田害虫生物防治的一项记载。苏轼曾见丞相王安石喜欢放生,自己也有放生鲫鱼的经历。因而发现有的鱼能在流水中存活,有的鱼,如䲡,入江水中辄死,鲫鱼生流水中,则背鳞白,生止水中,则背鳞黑而味恶。([6],2373页)苏轼曾读过苏子美《六和寺》诗,诗中有“松桥待金鱼,竟日独迟留。”最初并不明白这句诗的意思。到杭州做官后,“乃知寺后池中有此鱼,如金色也。并且在“复游池上,投饼饵,久之,乃略出,不食,复入,不可复见”之后,才最终明白“迟留”之语。这也是最早关于金鱼及其习性的记载之一([6],2145 页)。
基于对于农业和农民的理解,苏轼对一些流行的农业文化提出了批评。当时洛阳和扬州等地都盛行举办“万花会”,洛阳以牡丹为主题,扬州则以芍药为主题,从各大花园中征集名品花卉集中展示,结果使各花园遭到破坏,在此过程中,又有官吏因缘为奸,侵害百姓。苏轼在扬州任职期间首先停办了这种劳民伤财的“万花会”,并认为首创万花会的洛阳有朝一日也会停办。([6],2293~2294页)
不是所有的士人都有苏轼一样的对于农业物产的兴趣。有些士人就认为,很多农作物及品种“往往其名鄙俚,不足载”([20],4858页)。但作为传统社会中流动最为频繁的群体之一①宋代的地方官多为临时性差遣,秩满三年,离开任地,另行任用,即所谓“三年一易”。同时又因地域回避制度,本地人不得在籍为官。迁任流放之外,官员们还因公事私宜往来于各地。可以说官员是流动较为频繁的群体之一。其流动的频繁和距离远非一般农民所能比。,士人见多识广,其中也包括对于各地农业的接触和体认。丰富的阅历使士人对于自己的农学知识非常自信。朱熹就说:“当职久处田间,习知穑事”([21],卷99,1767页);吴泳自称“识字一耕夫”([22],654页)。这在地方官员在任时的《劝农文》、任满后的工作汇报(札子),以及游记、书信等文献中多有所反映。
4 躬耕
《论语·微子》载丈人言:“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孰为夫子”。后世多以之形容脱离生产劳动,缺乏农业知识。也有一解认为此只是丈人对自己的一种判断,认为自己四肢也勤劳,五谷也分得清楚,只是不知道谁是孔夫子。无论如何,古今人都认为实践出真知,躬耕是农学知识增长的主要途径。陆游有言,“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士人的农学知识在阅读和游历中增长,同时他们更将来源不同的知识“验之行事”,通过实践来扩大农学知识的来源和理解,从而增长出更多的知识。
苏轼所到之处,但凡居住过一段时间,都想在当地“买田筑室”([6],1531页),这个过程中他总是亲力亲为,前往“相田”([6],2164页),这也成为他躬耕的一部分。苏轼一家在阳羡、蕲水等地有自己的田产。但宦游的过程中更多的时候需要借田地耕种。苏轼较为集中的农耕生活是在黄州。苏轼《东坡八首,并序》中写道:
余至黄州二年,日以困匮,故人马正卿哀余乏食,为于郡中请故营地数十亩,使得躬耕其中。地既久荒,为茨棘瓦砾之场,而岁又大旱,垦辟之劳,筋力殆尽,释耒而叹,乃作是诗,自愍其懃,庶几来岁之入,以忘其劳焉。([5],前集,175页)
在黄州期间,除了种稻、种麦,还种桑、养蚕、种枣、种松、种菜、种柑等①苏轼:《与李公择十七首之九》:“某见在东坡,作陂种稻,劳苦之,亦自有乐事。有屋五间,果菜十数畦,桑百余本,身耕妻蚕,聊以卒岁也。”(《苏轼文集》卷51,第1499页)。。在与他的朋友王定国的诗中,也提到东坡种麦的情况:
近于侧左得荒地数十亩,买牛一具,躬耕其中。今岁旱,米贵甚。近日方得雨,日夜垦辟,欲种麦,虽劳苦却亦有味。([6],1520~1521页)另一首诗也提到了他在东坡的躬耕生活:
去年东坡拾瓦砾,自种黄桑三百尺,今年刈草盖雪堂,日炙风吹面如墨,平生懒惰今始悔,老大勤农天所直。([5],前集,187页)
苏轼在东坡所种植的蔬菜中,有一种是通过好友元修从四川老家引种过来的巢菜,这是他在家乡时爱吃蔬菜之一②苏轼:《元修菜并叙》:“菜之美者。有吾乡之巢。故人巢元修嗜之。余亦嗜之。元修云。使北海见。当复云吾家菜邪。因谓之元修菜。余去乡十有五年。思而不可得。元修适自蜀来。见余于黄。乃作是诗。使归致其子。而种之东坡之下云。”(《苏东坡全集》前集卷13〈诗八十一首〉,第185页。)。苏轼还曾问大冶长老乞桃花茶栽东坡,以使有限的耕地得到充分的利用([5],前集,183页)。
苏轼对自己所种植的这些作物大多比较熟悉,但对种麦则是个外行。原本他没有种麦的打算,只是桑柘刚刚种下,尚未成林,在桑柘的空隙之间种麦,可以充分用地,给收成带来新希望。他把东坡种麦称为“奇事”([5],181页)。因为他没有种麦的经验,而且也没有人想到他会种麦。苏轼就是在躬耕的过程中,从农民那里学到了麦作丰产的关键技术。原来秋天播种的冬麦,如果冬前旺长,赶上寒冬雨雪冰冻,容易遭受冻害,影响麦的收成。他从农民那里了解到要抑制麦苗前期的过快生长,最好的办法就是放纵牛羊践踏觅食。这既可以控制麦苗的过快生长,同时还可以给牛羊提供难得的越冬青饲料。苏轼在《东坡八首》之四中记载了自己新学到的这一知识:
农夫告我言,勿使苗叶昌。君欲富饼饵,要须纵牛羊。
其实利用牛羊践踏抑制麦苗冬前旺长是北方冬麦区农民的常识,但对于南方稻作区长大的人来说,则会觉得非常难以理解。南宋人周紫芝就有这样的记载:
东坡诗云:‘君欲富饼饵,会须纵牛羊’,殊不可晓。河朔土人言:河朔地广,麦苖弥望。方其盛时,须使人纵牧其间,践蹂令稍疏,则其收倍多。是纵牛羊,所以富饼饵也。([23],2 页)
果不其然,苏轼利用所学知识,取得了种麦的成功,渡过了青黄不接的难关。“今年东坡收大麦二十余石,卖之价甚贱,而粳米适尽,乃课奴婢舂以为饭,嚼之啧啧有声。”([6],2380页)
躬耕的经历不仅使他学习到了种麦等新知识,而且使他认识到土地休闲的重要作用。苏轼说:
吾昔求田蕲水。田在山谷间者,投种一斗,得稻十斛。问其故。云:‘连山皆野草散木,不生五谷,地气不耗,故发如此。’吾是以知五谷耗地气为最甚也。([6],2366页)
基于对于地力的认识,苏轼主张休闲地力,他说:
曷尝观于富人之稼乎?其田美而多,其食足而有余。其田美而多,则可以更休,而地力得完。其食足而有余,则种之常不后时,而敛之常及其熟。故富人之稼常美,少秕而多实,久藏而不腐。今吾十口之家,而共百亩之田,寸寸而取之,日夜以望之,锄耨铚艾相寻于其上者如鱼鳞,而地力竭矣。种之常不及时,而敛之常不待其熟。此岂能复有美稼哉?([6],339~340页)
这是他年少时对农业观察所得到的知识([6],1563页)。苏轼对于农业的这种认识和后来农学家陈旉的思想是一致的①《陈旉农书》卷上〈财力之宜篇第一〉提出,从事农业生产必须“先度其财足以赡,力足以给,优游不迫,可以取必效,然后为之。倘或财不赡,力不给,而贪多务得,未免苟简灭裂之患,十不得一二,幸其成功,已不可必矣。虽多其田亩,是多其患害,未见其利益也。”。苏轼也把从农业中悟出的道理用之于读书和学习,主张“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他在勉励年轻的朋友张嘉父,“君年少气盛,但愿积学,不忧无人知。譬如农夫,是穮是蓘,虽有饥馑,必有丰年。”([6],1563页)
苏轼在东坡所种的植物中还有松,故《东坡八首》之六中有“种枣期可剥,种松期可斫”的诗句。此前十多年,苏轼就有过种松的经历,他在“戏作种松”一诗中写道:
我昔少年日,种松满东冈。初移一寸根,琐细如插秧,二年黄茅下,一一攅麦芒,三年出蓬艾,满山散牛羊,不见十余年,想作龙蛇长。([5],前集,167页)
他似乎对种松情有独钟,“人皆种榆柳,坐待十亩阴;我独种松柏,守此一寸心。”([5],前集,149页)以后还曾有过多次种松的经历。在“台头寺送宋希元”诗中提到“是日与宋君同栽松寺中”([5],前集,153页)。苏轼发现栽种松树的成活率很低,他在“种松得来字”一诗中提到“青松种不生,百株望一枚”([5],前集,153页)。这也可能是他钻研种松技术的最初动机。事实证明苏轼对种松颇有心得,他在一篇杂记中详细地介绍了松树山地直播技术。从十月后松子的收取,到入春后的播种,出苗后的养护,到五年、七年后的洗枝、间采,头头是道,入情入理,极富可操作性①苏轼〈种松法〉:“十月以后,冬至以前,松实结熟而未落,折取,并蕚收之竹器中,悬之风道。未熟则不生,过熟则随风飞去。至春初,敲取其实,以大铁锤入荒茅地中数寸,置数粒其中,得春雨自生。自采实至种,皆以不犯手气为佳。松性至坚悍,然始生至脆弱,多畏日与牛羊,故须荒茅地,以茅阴障日。若白地,当杂大麦数十粒种之,赖麦阴乃活。须护以棘,日使人行视,三五年乃成。五年之后,乃可洗其下枝使高,七年之后,乃可去其细密者使大。大略如此。”(《苏轼文集》卷73,第2361)。。古书中言及种松之法,无出其上。苏轼的种松经验及成就引起了时人的注意。元祐初年,东坡过都梁(在江苏盱眙),秀才杜舆请求向他学习种松。苏轼也有诗记其事,“予少年颇知种松,手植数万株,皆中梁柱矣。都梁山中,见杜舆秀才求学其法。”([5],后集,481页)
苏轼的躬耕生活多以园圃为主,尤其是到了晚年。大概是园艺作物对体力的要求相对较低,而对技术要求更高,因此历史上许多士人躬耕时多选择灌园治圃。熙宁十年(1077),苏轼权知徐州军州事,借王参军地种菜,不及半亩。种植芦菔和芥菜,他和他的儿子得以“终年饱菜”,即便是“夜半饮醉,无以解酒,辄撷菜煮之”。他亲自种植的蔬菜“味含土膏,气饱风露,虽梁肉不能及也”([5],续集,60页)。他很享受“煮蔓菁、芦菔、苦荠而食之”([5],续集,93页)的滋味,甚至认为“芥蓝如菌蕈”,“白菘类羔豚”。他很高兴地看到雨水滋润他的菜园。午夜梦回,当听到雨声时,仍然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要亲自到菜园中去察看蔬菜的生长([5],后集,514~515页)。在岭南期间,苏轼仍然不忘“灌园以餬口”([5],续集,5页)。园圃中,除芥蓝、白菘、蔓菁、芦菔等常见蔬菜外,还有一些药用作物,如人参、地黄、枸杞、甘菊、薏苡等([5],后集,519页)。他还在自家的院墙四周种岭南特有的作物红薯与紫芋([5],续集,72页)。②薯芋是唐代首次见诸农书,如《山居要术》、《四时纂要》等,记载的粮食作物。这些农书在宋代士人之间较为流行。苏轼种红薯和紫芋也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这种流行的程度。只是“红薯”一词常与明代以后从美洲传来的番薯(又名红薯或甘薯)混淆。详见游修龄、李根蟠、曾雄生,《苏诗“红薯”名物考辨》,《古今农业》2010年第3期67~80页。还曾将“松间旅生茶”,“移栽白鹤岭”,希望“有味出吾圃”([5],后集,514~515页)。苏轼“在南海,艺菊九畹”,发现南北方菊花的花期大不相同,“北方随秋之早晚,大略至菊有黄花乃开,独岭南不然,至冬乃盛发。”([6],2366页)
苏轼的农学知识在不断的学习和实践中得到丰富。这也可从与他朝夕相处的他的老伴身上得到反映。从事过农耕的人都知道牛是农民的宝贝,“农民丧牛甚于丧子”([5],前集,360页),因而苏家也非常注重牛病的防治。苏轼在给友人的一封信中提到:
仆居东坡,作陂种稻,有田五十亩,身耕妻蚕,聊以卒岁。昨日一牛病几死,牛医不识其状,而老妻识之,曰:此牛发豆斑疮也,法当以青蒿粥啖之。用其言而效。勿谓仆谪居之后,一向便作村舍翁。老妻犹解接黑牡丹也。([6],1639页)
苏轼的言下之意是说,老妻对牛病的诊疗技术甚至高出牛医,老夫当更为了得。他并没有因为个人遭遇,就放弃学习,而是在不断的实践中增长知识。黄州期间,苏轼对水稻生长进行过细致的观察。他在与弟苏辙的和诗中有“露珠夜上秋禾根”一句,这是他经过亲自观察所得出的结论。他在自注中说:
或为予言草木之长,常在昧明间。蚤作而伺之,乃见其枝起数寸,竹笋尤甚。又夏秋之交,稻方含秀,黄昏月出,露珠起于其根,累累然忽自腾上,若有推之者。或入于茎心,或垂于叶端。稻乃秀实。验之信然。([5],后集,513页)
实践出真知也是许多士人所走过的心路历程。陆游在读书和治圃的过程中,增长了对蔬菜等作物栽培的认识。他在一首诗中写道,“小圃漫经营,栽培抵力畊,土松宜雨点,根稚怯鉏声。”([16],782页)应该是他经营小圃的心得体会。陆游在一首诗中提到,“曩得治中俸,湖山偶卜居,身尝著禾谱,儿解读农书。”([16],947页)说明他已由农书的读者变为农书的作者,并且在他的影响之下,他的儿子能够解读农书。农学家陈旉也是在读书和实践中成长起来的。一方面,他“于六经诸子百家之书,释老氏黄帝神农氏之学,贯穿出入,往往成诵,如见其人,如指诸掌。下至术数小道,亦精其能,其尤精者,《易》也”;另一方面,他“不求仕进,所至卽种药治圃以自给”。二者的结合成就了《农书》。陈旉在《农书》“自序”中写道:“旉躬耕西山,心知其故,撰为《农书》三卷,区分篇目,条陈件别而论次之。是书也,非苟知之,盖尝允蹈之,确乎能其事,乃敢著其说以示人。孔子曰,盖有不知而作者,我无是也。”([13],22 页)
5 传播
苏轼在获取农学知识的同时,也在对农学知识进行传播。这其中有客观上的因素,也有主观上的努力。传统社会中,相对于安土重迁的农民而言,由士人是流动最为频繁的群体。士人的知识随着迁徙而增长,也随着迁徙而扩散。元丰二年(1079),苏轼因乌台诗案被贬至黄州。他躬耕东坡,很自然地就把蜀人的种稻经验在这里做了一次“嫁接”。从他所作诗“东坡八首”及自注中就可以了解到相关的内容。苏轼不仅将家乡的种稻知识带到了黄州,而且还在频繁的流动中不断地扩大他对于种稻的知识,并加以传播。
秧马发现之后,苏轼致力于秧马的推广。绍圣元年(1094),他被贬岭南。在到达岭南之前,苏轼行经江西庐陵(今江西吉安),在庐陵属下的西昌(今江西泰和),宣德致仕郎曾安止将自己写作的《禾谱》给东坡雅正,东坡看过之后,觉得该书“文既温雅,事亦详实,惜其有所缺,不谱农器也。”([5],499页)于是向曾安止介绍了秧马发现的经过及其形制,并作《秧马歌》,用以推广秧马。抵岭南惠州后,又继续致力于秧马的推广工作。苏轼《题秧马歌后》四首详细地记录了秧马的推广经过,是为农具推广史上重要的史料,兹录如下:
惠州博罗县令林君抃,勤民恤农,仆出此“歌”以示之,林君喜甚,躬率田者制作阅试,以谓背虽当如覆瓦,然须起首尾如马鞍状,使前却有力。今惠州民皆已施用,甚便之。念浙中稻米几半天下,独未知为此,而仆又有薄田在阳羡,意欲以教之。适会衢州进士梁君琯过我而西,乃得指示,口授其详,归见张秉道,可备言范式尺寸及乘驭之状,仍制一枚,传之吴人,因以教羡阳儿子,尤幸也。本欲作秉道书,又懒,此间诸事,可问梁君具详也。试更以示西湖智果妙总禅师参寥子,以发万里一笑,尤佳也。绍圣二年四月二十二日,轼书。
又
林博罗又云:“以榆枣为腹患其重,当以栀木,则滑而轻矣。”又云:“俯伛秧田,非独腰脊之苦,而农夫例于胫上打洗秧根,积久皆至疮烂。今得秧马,则又于两小颊子上打洗,又完其胫矣。
又
翟东玉将令龙川,从予求秧马式而去。此老农之事,何足云者,然已知其志之在民也。愿君以古人为师,使民不畏吏,则东作西成,不劝而自力,是家赐之牛,而人予之种,岂特一秧马之比哉!
又
吾在湖北,见农夫用秧马行泥中,极便。倾来江西,作《秧马歌》教人,罕有从者。近读《唐书·回鹘部族黠戛斯传》,其人以木马行水上,以板荐之,以曲木支腋下,一蹴百余步,意殆与秧马类欤?聊复记之,异日详问其状,以告江南人也。([6],2152~2153页)
从上述材料中可以看出,苏轼为了推广秧马,尽可能地动用各种社会关系,既有官员(如林抃、翟东玉),也有农民(田者),还有知识分子(进士梁琯),而他自己更是口传身授,详解秧马的范式、尺寸及乘驭之状(即使用方法),还亲自参与样式(秧马式)和样品的制作。在这个过程中,苏轼等人也结合实际对秧马进行了一些改进,包括形制和材质等。经过前后十余年的努力,秧马的足迹遍布湖北、江西、广东、浙江、江苏等地。从实际效果来看,岭南惠州一带的推广较为成功,“今惠州民皆已施用,甚便之”。江西等地则不尽如人意,“罕有从者”。但苏轼并没有放弃推广的努力。南宋时,秧马已广为人知。许多诗人的诗作中都提到秧马①如楼璹、王之道、曹勋、陈棣、陆游、张孝祥、赵蕃、韩淲、释居简、洪咨夔、郑清之、黎廷瑞、林希逸、刘克庄等。。其中南宋於潜县令楼璹更在《耕织图·插秧》一诗中明确表示:“我将教秧马,代劳民莫忘”([24],2页),发出了官方推广秧马的信号。更为重要的是在苏轼《秧马歌》的启发之下,《禾谱》作者曾安止的侄孙南宋耒阳县令曾之谨完成了《农器谱》的写作。当曾之谨为此向陆游求诗时,陆游很自然地想到了苏轼的《秧马歌》,于是便有了这样的诗句:“一篇秧马传海内,农器名数方萌芽。”([16],3771页)经过苏轼和后来者的宣传,秧马和《秧马歌》也顺理成章地进入了王祯《农书》,成为农书中的内容之一。苏轼对秧马的传播成为农业史上农业技术传播的一个经典案例。
这个案例值得关注还在于它能够为传播过程中知识的变异提供更深一层的解读。古语曰:“事传三人,辄失其真。”由于苏轼主要是借助文学描写的方式来传播秧马,且从他发现秧马,到最后形成文字,中间已有十余年,记忆可能会发生差错。文学性的描述,在没有农事经验,或者是没有见过秧马实物的士人看来,对于秧马的功用也容易产生歧见。很多人只是借助于文字知道有秧马一物,但对于秧马的功用却缺乏真实的了解。是拔秧?插秧?还是运秧?很多人其实并没有一个真实的概念。元王祯《农书》中出现的秧马图像,系根据苏轼文字描写来绘制,也很容易使人产生误解。现在越来越多的学者倾向于认为秧马是一种拔秧的辅助器具,但还有不少人认为秧马系作插秧之用。围绕着秧马的争论至今还在持续,传播的失真应负有主要责任。
文本是士人传播知识的主要方式。苏轼主要是通过他的笔,把他从各种途径所获得的知识及价值观与他的读者分享。在岭南时,苏轼发现岭南旧俗皆好杀牛,便抄写柳宗元的《牛赋》,宣讲牛对于农业生产的重要性,以谕其知者。([24],607页)又发现“海南多荒田,……所产粳稌不足于食,……乃和渊明《劝农》诗,以告其有知者。”([4],第14册,第9544页)借助文字的力量,苏轼在包括农学在内的许多领域里都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如苏轼关于种树的见解就就一再被人引用①宋人陈师道在《后山谈丛》一书卷四中就收录了“东坡居士种松法”。明人陈继儒《岩栖幽事》仍然认为“种树之法,莫妙于东坡”。。
传播的过程,其实就是一个从无到有,从未知到有知,从落后到先进的过程。士人对农学知识的传播往往是在比较了各地农事的差异基础上进行的,而迁徙流动成为农学知识传播的主要途径。24岁那年,苏轼与弟陪父亲经嘉陵到荆州,落后的楚地农业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楚地阔无边,苍茫万顷连,耕牛未尝汗,投种去如捐,农事谁当劝?民愚亦可怜。平生事游惰,那得怨凶年。([5],续集卷2,33页)
约20年后,当他有机会再次来到楚地黄州时,他便试着将家乡蜀地的农业技术,甚至于蔬菜品种引进到楚地。
苏轼一生到过很多地方,晚年他在一首《自题金山画像》的诗中,对自己的一生做过这样的总结:
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4],14册,第9624页)
流动性使士人其在农学知识的传播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像苏轼一样,四川人高斯得在浙江和安徽等地做官时,发现三地的稻作技术水准宁国比不上蜀中,蜀中又比不上浙江,并首次将浙江等地行用的“靠田”、“还水”等稻作技术推向宁国([8],99页)。四川人吴泳在浙江、江西等处做官时,发现两地的耕作制度、水稻品种等有很大的差异([25],654页),劝导江西隆兴府(今南昌市)的农民向浙江农民学习。浙江人黄震在江西抚州任职时,发现江西和浙江两地在土地利用、水利、耘田管理及施肥和秋后整地等众多方面有较大的差距,因而向抚州人灌输浙江的经验。([7],2222~2223页)江西人陆九渊任荆门知军时,发现“江东、西田土,较之此间相去甚远”([11],205页),试图把江东、西在土地利用和水稻种植等方面的经验向荆门推广。婺源(今属江西)人王炎在担任崇阳(今属湖北)主簿时发现,湖北路和江浙闽中的农业产业结构,农业技术水准及生产率方面存在较大的差距。因而主张湖北向闽浙学习。([26],150页)浙江永嘉人周去非则发现桂(广西)人的养牛技术无法与浙人相比。([27],42页)在夸耀家乡的同时,也把家乡的经验介绍到了岭外。士人的流动性极大地扩大了士人的视野。而士人对各地农事所作对比宣传的过程,其实也是农学知识的传播过程。
宋代有大量南方士人通过科举考试等途径流入北方,南北方农业的巨大反差,使得这些南方士子产生了向北方传播南方先进农业技术的想法和行动。宋初,四川阆中人陈尧叟认为,水田有“兼倍”之利,建议在陈、许、邓、颕、蔡、宿、亳、寿春等地,大开屯田,以通水利,发展农业生产,以省江淮漕运。(《宋史·食货志·屯田》)这一思想对后世许多政治家、思想家和农学家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宋仁宗时,光化军阴城(今湖北老河口市)人张士逊治理许州,从家乡襄、汉等地召募农民,前来种稻,使原不善种稻的许州出现了“压塍霜稻报丰年,镰响枷鸣野日天”的景象。([28],287页)宋神宗时,由江西抚州人王安石主导的改变中,农田水利是重要内容之一,而大兴水利的目的之一就是为了发展水稻种植。“欲化西北之麦陇,皆为东南之稻田。”([4],第17册,11610页)王安石本人就建议利用流经京师的蔡河水源“相旱地为塘,多引沟洫作水田”,以解决陈、颍数州及京师的粮食供应。([19],第18册,卷247,6017页)王安石主政期间,许多南方的农民被有组织地移民到北方种稻。积极执行王安石改革路线的官员也多是南方籍士人。如,在汴水一带引淤种稻的侯叔献是王安石的同乡。主张在甘肃洮河一带种稻,请求朝廷调发一批稻农前来此地从事此项生产的王韶,是江西德安人。奉使镇定(今河北正定),与当地统帅薛师政议论将海子开垦为稻田的沈括则是钱塘(今浙江杭州)人。沈括的兄长沈披在同一时期任河北安抚副使,曾请治保州东南沿边陆地为水田,得到采纳。建议在陈留县旧汴河下口的新旧二堤之间修筑水塘,以满足开封、陈留、咸平(今河南通许)三县种稻的需要并得到采纳的杨琰也是杭州人。(《宋史·河渠五·河北诸水》)
宋代福建士人在稻作推广方面的作为尤为引人注目。福建人以善于种稻著称。在土狭人稠、山多田少的条件下,福建人成功开发了梯田,并在稻作方面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经验。这些经验通过福建出生的官员的努力传到了闽省之外。其中比较著名的人物有泉州人黄懋、建安人江翱、闽县人沈厚载、福唐(福清)人陈襄等。黄懋首倡并积极配合何承矩在河北宋辽边界利用淀泊种稻,同时在技术方面扮演关键角色。江翱曾从老家建安取耐旱稻种,至汝州(今河南汝州市)鲁山种植,大获成功,使百姓的口粮得以保障。([29],283页)沈厚载到怀、卫、磁、相、邢、洺、镇、赵等州,教民种水田。(《宋史·食货志·农田》)陈襄知河阳县(今河南孟州市)时,教民种稻。(《宋史·陈襄传》)
苏轼虽然反对在北方强行推广水稻种植,但有迹象表明,他曾经在他任职的河北定州推广水稻种植。元祐八年(1093)苏轼转任定州太守。定州北部总是遭受洪涝灾害,因此并不合适耕种。苏轼建议种稻,并提供秧苗,还从南方请来农民教授稻田耕种方法。[30]为了减轻水田劳作的辛苦,苏轼还编了歌曲,教他们在插秧的时候唱,使他们忘了疲倦,这就是秧歌名称的起源。不久就传遍了定县,男女老幼都会唱了。农民多半不识字,就一代一代的口传下来。[31]
有宋一代自最高统治者到普通农民都在一定程度上参与了农业知识传播的进程。如,宋真宗大中祥符四年,遣使就福建取占城稻三万斛,分给江、淮、两浙三路为种,并内出种法,命转运使揭榜示民(《宋史·食货志》)。北宋元祐六年(1091)十一月苏轼上奏中所提到的汝阴县百姓朱宪往淮南籴得晩稻稻种一事([6],945页),实际上也扮演着农事知识传播的角色。介于朝廷和百姓之间的士人成为知识上下流动的管道。一方面士人将农民的知识进行提炼,形成文字,写成农书,进献朝廷。楼璹的《耕织图》就是通过这种途径引起朝廷重视的。另一方面又将朝廷所总结的农业技术在更大的范围内做进一步的推广。占城稻就是通过这种方式来传播的。士人在知识传播中的作用虽不及朝廷诏令具有广泛的覆盖能力,但比一般农民的活动范围大得多。和农民的言传身教的知识传播方式不同,士人更多的是借助于文字的力量。也正是有士人队伍的努力传统的农学知识才得以实现跨越时空的存在。
6 结语
北魏贾思勰《齐民要术序》中提到该书中农学知识的来源,即“采捃经传,爰及歌谣,询之老成,验之行事”。苏轼及宋代士人对于农学知识的获取也不出此四端。除此之外,本文将出身加入考察,认为早年的经历,约当人生的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的时间,也是农学知识获取的重要时段。宋人与前人的不同之处在于其一定程度地突破了自孔子以来在农与学之间所设置的樊篱,更为自觉地投身于农学知识的获取和传播之中,这也就是宋代农学知识快速增长的内在原因。士人的流动性,特别是南方士人向北方的流域,又大大促进了农学知识的传播。
1 曾雄生.儒学与中国传统农学[J].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5(6):55~62.
2 缪启愉.齐民要术校释[M].北京:农业出版社.1982.5.
3 缪启愉.四时纂要校释[M].北京:农业出版社.1981.1.
4 傅璇琮,等.全宋诗[Z].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
5 苏轼.苏东坡全集[C].北京:中国书店.1996.
6 苏轼.苏轼文集[C].孔凡礼,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6.
7 张伟,何忠礼.黄震全集[C].第7册.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3.
8 高斯得.耻堂存稿[C]//丛书集成初编.2041册.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
9 陈造.江湖长翁集[C]//宋集珍本丛刊.第60册.北京:线装书局,2004.669.
10 真德秀.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C]//四部丛刊初编.上海:商务印书馆,1912.
11 陆九渊.陆九渊集[C].北京:中华书局.1980.424.
12 曹树基.《禾谱》校释[J].中国农史,1985(3):75.
13 洪兴祖.农书后序[M]//万国鼎.陈旉农书校注.北京:农业出版社,1965.63.
14 田锡.咸平集[C].罗国威,校点.成都:巴蜀书社,2008.282.
15 江葛祐.齐民要术序[C]//中国科学技术典籍通汇·农学卷·齐民要术.郑州:河南教育出版社,1994.1~167.
16 陆游.陆放翁全集[C].北京:中国书店,1986.132.
17 欧阳修.欧阳修全集[C].北京:中华书局,2001.641.
18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M].北京:中华书局,2004.
19 沈括.元刊梦溪笔谈[M].北京:文物出版社,1975.
20 谈钥.嘉泰吴兴志[Z]//宋元方志丛刊.北京:中华书局,1990.
21 朱熹.朱文公文集[C].四部丛刊初编.上海:商务印书馆,1912.
22 吴泳.鹤林集[C]//宋集珍本丛刊.74册.北京:线装书局,2004.
23 周紫芝.竹坡诗话[M].北京:中华书局,1985.
24 楼璹.耕织图诗[M].北京:中华书局,1985.
25 缪启愉.东鲁王氏农书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
26 王炎.双溪类稿[M]//宋集珍本丛刊.63册.北京:线装书局,2004.
27 周去非.岭外代答[M].卷4.踏犁//丛书集成初编.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
28 宋祁.景文集[C].第4册.卷23//丛书集成初编.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
29 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30 耿保仓,等.定县大秧歌探源[C]//保定地区庙会文化与民俗辑录.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7.538.
31 李景汉.定县社会概况调查[M].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3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