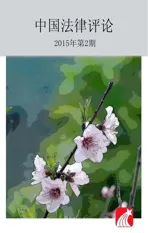法律背后的沉默之音
——弗里德曼大众法律文化思想解析*
2015-01-29赵彩凤
赵彩凤
清华大学法学院2013级博士研究生,广西桂林电子科技大学讲师
法律背后的沉默之音
——弗里德曼大众法律文化思想解析*
赵彩凤
清华大学法学院2013级博士研究生,广西桂林电子科技大学讲师
引言:当中国富豪遭遇纽约乞丐
2014年6月,有一则网上新闻曾轰动一时。中国富豪陈光标在美国纽约街头向流浪者高调施善,遭到一流浪汉的冷眼拒斥。1相关报道参见http://news.xinhuanet.com/local/2014-06/26/c_126673040.htm;http://business.sohu.com/20140625/ n401378766.shtml;http://news.mydrivers.com/1/309/309806.htm等,2015年3月21日访问。这则看似与法律文化无甚关联的“旧闻”之所以值得一提,是因为它同美国当代法律文化研究大师劳伦斯·M.弗里德曼(Lawrence Meir. Friedman)近三十年前所捕捉的镜头,形成了跨越时空的拼贴效应。1989年腊月,纽约街头正在上演类似情景剧:纽约市政府基于社会福利保障的权责,实施了一项政令,建造屋宇千间以安置街头无家可归的人们越冬,却遇到了被救助者的抵制。2[美]弗里德曼:《选择的共和国》,高鸿钧等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2页。虽世易时移,剧情有所差异,但两者所传递出的文化信息,却何其相似乃尔。三十年前的那一幕,弗里德曼敏感捕获了其间的文化符号讯息:那些无家可归者对着记者的镜头高谈阔论“自由”,宣称选择浪迹街头生活是他们的“权利”——弗里德曼认为,作为大众边缘群体的流浪者发出如此“奇异”之声,在某种方式上深刻地反映出了美国现代法律文化的核心特征,即大众的选择共和国及其深层人格文化类型:表现型个人主义(expressive individualism)3参见前引2弗里德曼书,第2、50页。。而当今中国富豪与纽约乞丐的趣闻虽无涉法言法行,却于一定程度上印证了弗里德曼当时的预言:自由选择、表现型个人主义的现代法律文化终将趋向全球化。
弗里德曼是当代研究法律文化理论的领军人物。早在20世纪60年代,他最先提出了“法律文化”(legal culture)的概念;继而以法律社会学范式,从法律的外部视域对美国法律文化尤其是大众法律文化进行了长达半个世纪的持续思考,由此创建了一套较为完整的法律文化理论体系。他的法律文化概念、法律社会学研究范式在国际上引起很大反响,对中国学者亦影响深远。他对现代法律文化及其发展趋势的探索,对于我们深刻理解当代社会文化及法律文化的诸种现象,建构现代法律文化与法律制度,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故本文从大众法律文化入手,对弗里德曼的法律文化、现代法律文化以及法律文化全球化思想进行解析,冀此愚者之虑或能撩开一叶斑斓,以便于方家观察法律文化的清晰面目。
一、大众法律文化语义:在法律文化与大众文化之间
在弗里德曼看来,法律并非一堆抽象的纸面规则,而是一套由结构、实体和文化组成,并由文化要素主导的动态法律制度。因此只有研究法律中的文化元素即法律文化,才能认识法律的真实面目,发现文本背后真正起作用的沉默力量。而法律文化的考察并无定量参照指数,必须通过其外部测量指标——大众文化来观知,具体言之,主要是观察两者的交集区域即大众法律文化。故理解法律文化、大众文化、大众法律文化的语义及其关联,是研究弗里德曼大众法律文化思想的逻辑起点。
(一)法律文化
弗里德曼的法律文化概念及理论,是其在参与美国“法律与发展运动”研究的过程中逐步建立的。在1969年《法律文化与社会发展》一文中,他首次提出并界定了“法律文化”(legal culture)4See Lawrence M.Friedman,“Legal Culture and Social Development”,Law and Society Review,4/1,1969, p.34.弗里德曼的“法律文化”用语显然受到了阿尔蒙德、维尔巴“政治文化”概念的启发。弗里德曼曾解释过,法律文化这个词大致描述了关于法律的态度,和政治文化多少有些相似,阿尔蒙德和维尔巴将政治文化界定为“表现在人们认识、感情和评价中的政治制度”。参见[美]劳伦斯·M.弗里德曼:《法律制度》(修订版),李琼英、林欣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7—18页;Gabriel A.Almond & Sidney Verba,The Civic Culture,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63,p.12。的概念,此后又屡次对法律文化的含义予以重申和拓展。综合其各时期表述,弗氏法律文化可理解为:法律制度中的文化要素和观念之维,意指特定社会中的人们对法律所持有的看法、期待、信念、意见及意向等。它是“价值和态度的网络”,决定着法律人的法律作为方式,即如何制定、执行或适用法律,也决定着普通人的法律行为模式,即“何时、为何及在何种情况下求助于或回避法律”;5弗里德曼用两个词区分法律人的专业活动及相对人的反应行为,前者用“legal act”表述,指任何掌权者在法律制度范围内采取的任何有关作为;后者使用“legal behavior”,指人们对前述掌权者法律作为所作出的直接反应。对此二者目前中译文不尽一致。根据学界用语习惯,笔者在此将legal act译为“法律作为”,legal behavior译为“法律行为”,两者统称时则用“举动”。参见前引5劳伦斯·M.弗里德曼书,第4—5、29页;[美]傅利曼:《法律与社会》,吴锡堂、杨满郁译,巨流图书公司1991年版,第163—164、168—169页;Lawrence M.Friedman,The Legal System:A Social Science Perspective,New York:Russell Sage Foundation,1975,pp.4-5,25;Lawrence M.Friedman,Law and Society:An Introduction,Eaglewood Cliffs:Prentice-Hall,Inc.,1977,pp.111-112,115。它是推动法律变化的直接源泉,是连接法律与社会的桥梁。6关于法律文化的定义,综合参见Lawrence M.Friedman,“Legal Culture and Social Development”,p.34;前引4劳伦斯·M.弗里德曼书,第17—18、226—227页;前引2弗里德曼书,第251—252页;前引5傅利曼书,第114—115页;Lawrence M.Friedman,Total Justice,New York:Russell Sage Foundation,1994, pp.31-32;高鸿钧:《法律文化的语义、语境及其中国问题》,载《中国法学》2007年第4期,第23页。
弗里德曼的这一概念,其他学者也有类似表述。比较有影响力的有:第一,法律传统(legal tradition)。这由美国法学者梅里曼提出,用以指称一套关乎法律的“植根深远、并为历史条件所制约的观念”;它将法律制度与它置身其中的文化联系起来,从而“将法律制度置于文化视域之下”。7J.H.Merryman et al.,The Civil Law Tradition,Charlottesville:The MichieCo.,1994,pp.3-4.法律传统和法律文化概念相似性在于,两者均指称关于法律的观念因素,均关照历史维度。它们的不同之处主要有两点:一是两者与文化和法律制度的关系不同,法律传统是文化的一部分,却不属于法律制度;法律文化既属于文化的组成,也是法律制度的要素。二是两者对历史因素的注重程度不同,法律传统单一强调历史向度,法律文化则给予历史和现实同等关注。梅里曼对法律传统概念的理解有过窄之嫌,一般意义上的法律传统除了法律观念之外实际上还应包括法律制度,而且还可以指称跨越国别和民族界限的有共同特征的法律制度。8参见前引6高鸿钧文,第24—26页。另外加拿大比较法学者H.帕特里克·格伦也论及法律传统,也意指法律的观念维度,视其为一种“高度自觉”的“长久的规范性信息体”,很难将其物化为某些“外在于我们”的事物。参见[加]H.帕特里克·格伦:《比—较》,鲁楠译,载[英]埃辛·奥赫绪、[意]戴维·奈尔肯编:《比较法新论》,马剑银等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15页;[意]戴维·奈尔肯:《法律文化概念的界定与使用》,鲁楠译,载前引8埃辛·奥赫绪、戴维·奈尔肯书,第129页。
第二,法律意识形态(legal ideology)。英国法学者科特雷尔提出此概念,试图以此取代他认为过于模糊的“法律文化”,意指“对实践所包含、表达以及塑造的流行的观念、信仰价值和态度的一种概括”。9参见[英]罗杰·科特雷尔:“法律文化的概念”,沈明译,载[意]D.奈尔肯编:《比较法律文化论》,高鸿钧等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7—50页;前引6高鸿钧文,第28页。较之法律文化,法律意识形态更强调法律的专业智识和制度之维,更关注法律原则与系统化的法律学理。对此,弗里德曼回应科特雷尔,认为两个概念只是侧重点不同:法律文化侧重于非正式的法律观念、期待和态度对于制度性机制的影响,而法律意识形态概念则看重职业化的机制对于大众法律观念的影响。10参见劳伦斯·M.弗里德曼:《法律文化的概念:一个答复》,沈明译,载前引9D.奈尔肯书,第51—61页。
第三,法律“心智”(mentalité)。法国皮埃尔·罗格朗等学者用此指涉一种“集合性的思想程序”,一套描述形塑行动方式的信念及阐释性观念,它提供着法律推理的深层结构,成为隔离普通法法系和民法法系法律人的思维屏障。11参见[英]约翰·贝尔:《法国法律文化》,康家昕等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5—28页;P.Legrand,“European Legal Systems are not Converging”,45International and Comparative Law Quarterly,1996,pp.60-61。较之法律文化,此概念亦偏重法律职业者观念。与其他类似概念相比,弗里德曼的“法律文化”因其具有跨越时空的解释力,目前仍是该领域研究认同度最高的范畴。
弗里德曼所研究的法律文化,其主体涵摄了法律职业者与普通大众,据此他将法律文化分为两种基本类型:内行法律文化与外行法律文化。前者是法律职业者的法律思维、观念与态度,后者是法律人之外的普通大众或外行关于法律与法律制定过程的想法、态度以及期待12前引2弗里德曼书,第5页。。这两者既有区别,又相互关联。他指出内行与外行法律文化的分殊主要是针对存在法律专家的现代社会,并不适于解释传统社会。在两者之间,弗里德曼更留意外行法律文化,关注考察普通大众对于法律的看法、态度与价值观念,认为这些才是在制度背后默默推动法律运行的原动力,是大众文化的产物与内容。这使弗氏法律文化与大众文化的概念密切关联起来。
(二)大众文化
法律文化的运作是以大众文化作为场域和环境进行的。弗里德曼认为,在现代工业社会中,尽管人人强调个性,但社会整体却是一幅由千差万别的人混同一体而组成的“盲脸”大众群图。但他所说的“大众”并非包括所有人,而是主要指“中产阶级及其之上阶层的那部分人”,13前引2弗里德曼书,第10页。这部分人的态度、价值观念之聚合力量,便代表大众文化,会形成塑造法律的强势社会力量。弗里德曼指出“大众文化”14现代英语用以指称“大众文化”的主要有两个词组:“mass culture”、“popular culture”,两者产生时间及初始含义有所差别,但现代学者包括弗里德曼在内,一般使用时不作区分,笔者在此亦将二者作同义解。有两层含义,首先,较一般意义上说,是普通人,或者至少是非知识分子所持有的标准与价值观,与知识分子的高级文化或“权贵文化”相对。其次,更狭义地说,是书籍、歌曲、电影、戏剧、电视节目及诸如此类意义上的文化产品;尤其指那些以一般公众而不是知识分子为其目标受众的作品,“是猫王而不是玛丽莲·霍恩的作品”。15参见Lawrence M.Friedman“,Law,Lawyers,and Popular Culture”,Yale Law Journal,Vol.89,1989,p.1579。猫王即维斯·普雷斯利 (Elvis Aron Presley,1935-1977) ,美国20世纪流行乐坛的重要明星,被誉为摇滚乐之王。玛丽莲·霍恩(Marilyn Horne(1934- ),美国当代女中音歌唱家,在歌剧界很有影响力。
从定义看,一方面,弗里德曼广义的大众文化用语,坚持了文化学术界对这一概念的一般界定16关于文化学术界对大众文化的定义,可参见[英]约翰·斯道雷:《文化理论与大众文化导论》,常江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6—18页。,使用的是“剩余”、“他者”的范畴,即与精英文化相对的“其他人”的文化;不过他显然并不认同大众与精英之间的低俗与高雅之价值判断,故将精英置换成“知识分子”,凸显了专业知识的地位,同时淡化了时间维度。另一方面,弗里德曼对于大众文化的狭义概念,则突出了时间因素——现代工业社会,彰显了“流行”和“大众传媒”两个关键词,并将作为文化载体的大众传媒视作文化本身;但他又使用“知识分子”对受众进行排除,虽意在强调其非专业性之征,但在大众教育普及化的现代社会,知识分子与大众的文化消费界限愈益模糊,故而这种排除使该定义显得似是而非。弗里德曼的大众文化概念主要是在研究现代法律文化时使用,从其相关论述中我们可以发觉大众文化更清晰的轮廓,两层含义均坚持了一个核心理念,即力图滤除意识形态的偏好,将主要意涵限定在专业与非专业亦即内行与外行的区别之内。这与他的外行与内行法律文化理论形成了勾连。据此,我们不妨这样理解弗里德曼的大众文化概念:大众文化是现代工业革命以后兴起,以畅销书籍、广播、影视、网络等大众传媒为生存空间和传播渠道、以不预设其专业知识背景的一般大众为消费受众的通俗、流行文化。
(三)大众法律文化
当大众文化与法律文化衔接,便形成了大众法律文化。弗里德曼认为,作为法律文化与大众文化竞合地带的大众法律文化,是在背后形塑法律的沉默力量,是法律制度中居于核心地位的能动要素,是在社会生活中实际运行的“活法”。与前述大众文化的两种含义相对应,弗里德曼认为大众法律文化亦具有两种意义和使用语境:一种为广义用法,与外行法律文化为同义语;但更多语境是指另一种狭义界定,特指与现代大众传媒相绑定,以一般公众为目标受众,包括在大众媒体、艺术和文字、娱乐中的法律表达,外在呈现为关于法律及法律人的书籍、歌曲、电影、戏剧及电视节目等作品。此种大众法律文化是狭义的大众文化的子系统,具有大众文化的一切特点,像大众文化一样,是去官方的、非精英的,通过大众传媒广泛流行、共享,是一座蕴藏着普通人对法律、法律家和法律机制看法、态度、价值观的潜在信息收藏库。17Lawrence M.Friedman,“Law,Lawyers, and Popular Culture”,pp.1588-1589.
事实上,弗里德曼对于大众法律文化的广义及狭义界定,核心含义并无实质性区别,均是指现代社会大众文化场域下,法律职业者以外的外行即普通大众对法律及法律职业者的看法、态度、价值、期待等观念意识。但两者的具体外延有所不同:首先,从担纲主体而言,广义概念(相当于外行法律文化)的主体指非法律专业人士之外的所有外行,而狭义概念的主体仅指作为社会主流的中产阶级大众;其次,从载体而言,广义大众法律文化并不注重外显载体的必要性,它可以只经由外行们的言语、行动体现,甚或只存留于其内心,而狭义大众法律文化,外在的表达载体是基本构成要素;最后,从流播程度而言,广义的大众法律文化可以是分散的、个别少数的观念,而狭义的大众法律文化则以流行度、聚合性为判断要件,看重其因流行与聚合而产生的影响社会制度的力量。
二、大众法律文化的现代意象:“选择共和国”
弗里德曼关于现代法律文化的描述,是在托克维尔的“民情”18参见[法]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上卷),董果良译,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4、320、332、354—359页;[法]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下卷),董果良译,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625—627页。、罗伯特·贝拉等的“心灵习性”19[美]罗伯特·N.贝拉等:《心灵的习性——美国人生活中的个人主义和公共责任》,周穗明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基础上,为美国文化撰写的“续集”。在他看来,自步入现代工业革命尤其是20世纪以降,美国现代法律文化总体而言,展现为一个“选择的共和国”20前引2弗里德曼书,第109页。,这种新型法律文化以大众传媒为传播介质、以大众文化为展示场域,其个人主义、权利、自由等价值理念都发生了巨大变迁,并以大众法律文化的面目得以全面呈现。弗里德曼用超市购物隐喻这种意象:人们就如同置身巨大的商场,推着巨大的购物车,在琳琅满目的货架上随心所欲选取商品,像选购不同品牌的汤料和肥皂一样。这种“超市”不仅可以陈列于传统政治、经济的领地,还可展示于个人事务领域,表现为一种性别“商店”,一个宗教“购物中心”,甚至还会体现为一种人民法院;21前引2弗里德曼书,第228—229页。可选择的“商品”范围极其广泛,除了诸如种族、性别等天生不可改变的事实之外,人们对个人生活中的所有事务均可进行个人化的自由取舍。正是大众社会诸领域所呈现的这番图景,让弗里德曼捕获了现代法律文化的“元代码”:选择。
(一)私人事务的选择:自由权利与生活方式
弗里德曼认为,大众文化的一个预设前提是,绝大多数人排斥一个被预先规划、天生身份固定又不能更改的自我,22前引2弗里德曼书,第56页。因此自由选择成为现代大众确信的基本理念。大众法律文化在各方面展示了自由选择的想象与可能。
第一,从选择领域看,大众法律文化日益展现着物质及精神生活方式的多元选择景观。领取养老金的老年人可以继续工作、恋爱或探险,不只有躺在摇椅上一种选择;婚姻早已不再是固定身份和永久结合,毋宁是一种搭伙、持续的契约,如不能从中实现自我,双方均可自由选择解除婚约;生育也成为个人的选择,就像决定选购一台冰箱或一次旅行那样。精神生活层面,伦理道德和公共舆论对个人的束缚日益松弛,甚至宗教信仰也有了自由选择的可能,成为“私人精神消费”的对象。当然,弗里德曼注意到,选择存在一定的虚假性,选择的范围看似琳琅满目,但选择限度实际上受到社会现实及大众传媒的无形操控。23前引2弗里德曼书,第154、237页。对此他认为,选择自由更多是观念上的存在,并不依赖于是否能够真正兑现选择,人们“相信自己是自由的”就足够了。24前引2弗里德曼书,第70页。随着电影、电视、互联网等大众传媒的广泛普及,大量可供拣选的商品、信息、生活样式以及观念被推送到大众面前,可供选择的范围在不断扩展和推陈出新,人们从冗余的信息消费中产生多元选择的想象、信念和生活态度,是现代大众法律文化的必然。
第二,从选择内容看,大众法律文化呈现出普遍的权利与人权需求。选择的自由在法律语境中,是以“权利”的面目体现的。多元的自由选择观念促使大众提出更多的权利要求,于是如弗里德曼所说,当代社会呈现“权利爆炸”的局面,尤其是出现了一些新型权利、特殊权利,如流浪汉主张露宿街头的权利,性少数派要求公开生活不受歧视的权利等。同时,位居各类权利之首的人权,成为大众法律文化中持续升温的主题。弗里德曼认为,最近几十年,随着资本主义发展、现代化及社会结构的变迁,人权意识及运动蓬勃兴起,人们逐渐普遍意识到存在神圣不可侵犯、永不灭失、人人平等的人权25Lawrence M.Friedman,The Human Rights Culture:a Study in History and Context,New Orleans:Quid Pro Books, 2011.。这种人权意识经由种族、性别、性取向平等题材的大众影视及畅销小说的宣扬得到了强化。
第三,大众法律文化重释着隐私的理念与表现方式。由于现代传媒高科技的迅猛发展,官方“老大哥”的耳目与民间大众传媒无所不在的可能监控,26前引2弗里德曼书,第213—214页。个人很难完全保持生活私密,于是现代隐私的含义发生了转变,不再强调私密性,而是注重个人性和不受干涉的意蕴,隐私的经典表述从“不关你的事,你不可以知道”变为“你可以知道,但不可以干涉我”。27前引2弗里德曼书,第213—215页。针对官方,现代隐私表现为一种对抗公权力的“忘却权”28前引2弗里德曼书,第215页。,据此参加示威游行者有权要求不被政府正式记录在案,以便自己明天的生活不会因昨日之为而丧失自由选择权。29前引2弗里德曼书,第155—222页;Lawrence M.Friedman,Private Lives:Families,Individuals,and the Law, Cambridge,London: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4,pp.1-16,44-189;Lawrence M.Friedman,Guarding Life's Dark Secrets-Legal and Social Controls over Reputation,Propriety,and Privacy,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7,pp.1-21, 75-272。针对大众传媒,隐私则意味着保护个人生活方式的选择权,使之不会因所选而受公共控制和社会羞辱。甚至当今还出现了一种隐私公开炫耀化的新动向,大众将公开分享隐私、寻求认同视为新的正义需求与期待。
(二)公共事务的选择:法律与权威
如弗里德曼所言,大众传媒创造出了一个“孤独的、隐居式大众”的世界。30前引2弗里德曼书,第149页。置身于陌生人社会的人们为了使选择真实而有保障,便对法律提出了大量要求。于是现代法律的领地急剧扩展,法律数量迅速膨胀,与之伴生的是“诉讼爆炸”、律师人数剧增、法院不堪重负以及司法权迅速扩张等副产品。31参见[美]劳伦斯·傅利曼:《美国法导论》,杨佳陵译,商周出版社2004年版,第384—391页;前引2弗里德曼书,译者导言,第10—11、19页;Lawrence M.Friedman,Total Justice,New York:Russell Sage Foundation,1985, pp.6-23,76。这在影视、畅销小说等大众法律文化中有明显体现。
随着法律与诉讼的激增,现代国家也被要求承担更多的法律义务和责任。人们不再对守夜人式的小政府抱持艰深信念,而是期待政府越来越多地有所作为。以往人们对瘟疫、地震、洪水,或其他“天灾”的唯一共同反应,是斋戒、祈祷和认命。今日的国家却有责任为其国民提供各种灾难救济和社会福利。在此情境下,大众法律文化成为福利国家及其政府判断自身权威的指示计。
大众法律文化对权威类型的改变在于,其凭借大众传媒瓦解了依靠隔离公众、制造神秘气氛维持的传统权威32前引2弗里德曼书,第242—243页。,促使平行、开放的现代理性—法律型权威的盛行。这种权威有两个特点:一是采用科层制和程序技术进行国家管理和社会治理;二是权威首领的人选和产生都与个人选择相关,是基于同侪群体选举产生的“牧羊人”——名人。名人虽然是由于幸运或遭际而成名,但在空间和情感上仍非常接近大众,是“与我们相似的人”。大众对名人的效仿,是名人权威得以建立的方式。名人作为新型权威,体现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各领域。弗里德曼尤其强调,现代国家政治领袖的权威与领导力,不同于马克斯·韦伯所谓的克里斯玛型人物,大部分来源于其“名人效应”,须通过大众传媒显示其平易近人的形象。
随着名人文化、平行权威的伸展,大众法律文化也日益显示出社会扁平化的倾向。因为名人文化的效仿意味着社会界限的模糊或消解,社会不同等级之间具有流动性。根据个人选择、自愿组成的群体有了更多的存在空间,人们倾向于借助大众电子传媒,进行非面对面交流,其成员方以类聚,以某种身份认同自由组合和重构扁平团体,以此方式展示其存在,并援其友声表达对正义的一般期待和需求。33Lawrence M.Friedman,The Horizontal Society,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99;前引2弗里德曼书,第130—154页。
(三)选择的正义期待:完全正义
法律作为公平与善良的艺术,在理论上最终以实现正义为依归。“选择的共和国”更多强调法律对于社会正义的捍卫作用,由于大众传媒的普遍采用,司法过程高度公开,对法律运行的权力利维坦之监督似乎越发真实,催生了大众法律文化中更多的正义想象和期待。弗里德曼指出,现代大众对正义的需求与期待,体现为“完全正义”(total justice)。完全正义包括两类正义期待和两条正义理念,并与宽容原则密不可分。
首先,存在两类正义期待:(1)对正义的一般期待,即公民在任何情境下都应受公正对待的预期。此处的公正不仅限于法庭程序,也适用各种公共及私人场合,既包含实体也关涉程序。由这种一般期待,衍生出对平等权利和非歧视的期待及要求。(2)对救济的一般期待,即人们可以预期,假如受到不公正的对待或伤害,如果不是(至少不全是)由于受害人自己的过错,则均应当获得救济、赔偿或补偿,而不再是自认霉运。
其次,由完全正义观衍生出两条正义理念,即“第二次机会”34前引2弗里德曼书,第116页。和“失败者的正义”35前引2弗里德曼书,第121页。。“第二次机会”主要表现在两方面:其一,现代法律文化反对不可改变的选择和安排,比如禁止出卖自己的身体或生命,因为这剥夺了未来进行再次选择的机会;其二,人们即使选择错误,也应有第二次机会重新选择和再次尝试,像破产法、婚姻法、青少年犯罪不入档案的刑事法等,均包含了这样的正义理念。“失败者的正义”主要体现在,人们即使竞争或挑战失败,也不应当因此承担后续更多不利后果和风险。
最后,与完全正义紧密相联的宽容原则。正义的期待和衍生理念表明,现代法律文化倾向于对人的过错和失利予以宽宥,给予人们充分的自由选择机会。这是法律文化走向宽容的体现。个人生活方式的多元选择本身,以及有关种族、性少数派、“越轨”行为等在大众法律文化中频频出镜的现象,也均体现了现代法律文化的宽容精神。可以说,宽容为怀是“选择的共和国”之基石,是选择权利和完全正义得以实现的观念基础,是表现型个人主义在大众法律文化舞台得演主角的“后台”。36前引2弗里德曼书,译者导言,第20—22、116—129、155—189页;Lawrence M.Friedman,Total Justice,New York:Russell Sage Foundation,1985.
(四)选择背后的文化人格:表现型个人主义弗里德曼指出,大众的“选择共和国”背后,实质上隐含着一种新型的人格文化类型:表现型个人主义(expressive individualism)37前引2弗里德曼书,第50页。表现型个人主义之“表现”,并非通常语境下略带贬义的对自我长处的故意炫耀,而是用身体、行为、语言等做出的对内心想法的外在表达或展现。。这种个人主义不同于托克维尔所描述的那种“只顾自己又心安理得的情感”——追求个人政治、经济领域的成功,私人生活严格自律的功利型个人主义,而是一种“以多彩的生活风格和方式来彰显自我”的激进的个人主义;在20世纪取代功利型个人主义,成为美国大众心灵习性的“第一语言”38参见前引19罗伯特·N.贝拉等书,前言第59页,第24、190页。。
表现型个人主义的基本含义强调,每个人发展他/她自己作为个人的权利,尽可能自由选择一种合适和满意的生活方式。在外观上,表现型个人主义便呈现为选择的广泛性及生活方式的丰富多样性。大众文化为表现型个人主义提供了舞台,因为大众文化本身潜含着一项基本社会理念:每个人都是独特的,都应然是自由的,都应有权利选择、创造或形塑属于自己的生活。由此,大众法律文化容许人们推崇自我表现,在合法范围内随心所欲地选择自己的生活形式(forms)、模式(models)和方式(ways),淋漓尽致地体验独特的生活,发挥自我的个性、享受此在的生命。
当然,表现型个人主义本身也呈现多样性。就其终极意义和最高级形式而言,表现型个人主义隐含的是一种表现本真和实现自我的价值理念,据此生命的意义在于“自己成为自己”、“自己创造自己”。39前引2弗里德曼书,译者导言,第13、8—10、42—56、70—74页;Lawrence M.Friedman,The Human Rights Culture, pp.157-159.但这只是理想模型,现实中的个人形象很少完全符合这种假设。在“选择的共和国”中还含纳着一种最低级形态的表现型个人主义,其个人选择“可以降至只是细琐的、自我陶醉式的日常生活的决定,所涉及的不过是衣服、假期和唱片专辑等之类的东西”,甚至仅仅喜欢“在小饰物的丝带之间自由选择”。40前引2弗里德曼书,第151、53页。而在两端之间的表现型个人主义,主要展示为各种率性任情的个人行为模式,以及自由选择的生活方式。要言之,即“我的生活我做主”。这种表现型个人主义在当代经由大众传媒的广播,正在成为全球性的法律文化趋势。
三、大众法律文化的趋势:全球化及其成因
弗里德曼对现代法律文化的描述,是以美国为范本的;但他认为这种大众法律文化主导的现代法律文化,并非美国独有的特产,它在现代化的推动下,借由法律移植和大众文化的推力,终将蔓延及整个地球村。
(一)趋势:同质化与异质化
弗里德曼认为,现代大众法律文化趋势表现出同质化与异质化的双重动向,但总体方向是趋于全球化。
一方面,现代法律文化同质化趋向主要表现:其一,承载现代法律文化内容的好莱坞大众法律影视、通俗小说等跨越国界,在全球流播与消费;其二,法律及诉讼爆炸的势头,权利及人权的主张,自由及多元选择的理念,已开始成为全球性现象或话语,塑造着世界不同国家和地区大众的法律观与生活观;其三,现代大众传媒的普及,为越来越多的表现型个人提供了展示自我、寻求认同的契机。总之,现代大众法律文化随着大众文化四处游走,已成为“麦当劳化”的全球精神快餐41Lawrence M.Friedman,The Horizontal Society,preface,p.viii.,并呈现出对各“部落文化”进行剿杀的同化态势。42前引2弗里德曼书,第241—243页。
另一方面,现代大众法律文化异质化动向主要体现在,发展呈现不平衡和多元样态。第一,即便在美国,这种法律文化也只是大众法律文化体现出的主流趋势,并非普遍存在和全民认同;迄今仍有人宁愿固守传统生活,支持规训与家长式权威,或者在同一个人身上存在既喜欢自由又想被领导的矛盾状态43前引2弗里德曼书,第55、218页。。第二,这种法律文化内部存在分歧,对于选择、自由、权利等价值,人们理解和需求不一,如有人认为选择在街头流浪是个人的自由,而有人认为接受国家福利保障或社会救助才是个人应有的权利;选择、表现型个人主义不仅有高下层次之分,且其本身并非普适真理,在现代世界里将自由选择看作超越所有问题的至善或绝对美德,恰恰是违背“选择共和国”精神的。44前引2弗里德曼书,第53、55—56页。第三,这种法律文化趋势并非线性发展、一成不变,而是充满曲折,甚至存在相反的趋向;虽潜含了诸多正面的解放征象,也强化了负面的规制隐忧,如在滋育平等身份认同的同时,也助长了极端的排异势头;而且在互联网时代甚至出现了群体极化的反智45参见鲁楠:《互联网反智吗?》,载http://www.vkadoo.cn/E14B213E8ED7AFE09F5FAE748B220072.wxhtml,2015年3月23日访问。现象。46Lawrence M.Friedman,The Horizontal Society,pp.120-126.
需要指出的是,虽然现实情境中现代美国法律文化趋势代表了西方法律文化的发展潮流,而当代西方法律文化主导着世界法律现代化的总体方向,但弗里德曼特意声明,他所宣称的法律文化全球化并非法律文化“美国化”。这种大众法律文化全球化的成因,非美国推行霸权所致,而是受到了其他一些全球性的力量推动。47前引2弗里德曼书,译者导言,第23、60—69、83—89、236—245页;前引4劳伦斯·M.弗里德曼书,第227—233、255—260页;[美]劳伦斯·M.弗里德曼:《美国法律史》,苏彦新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731—742页;Lawrence M.Friedman,The Horizontal Society,pp.131-134,214-216,242;Lawrence M.Friedman,The Human Rights Culture,pp.126-132;Lawrence M.Friedman,Total Justice,pp.153-156。
(二)成因:现代化、法律移植与大众文化
在弗里德曼看来,现代大众法律文化全球化是社会现代化及其所导致的社会变迁、法律移植/借用以及大众传媒文化共同作用的产物。
首先,现代化是法律文化全球化的根本动因。大众法律文化是工业革命以来“现代化”的产物。现代化只是率先侵入并征服了美国,继而是其他西方国家,随后向全球挺进。现代化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一是科技创新。作为驾驭物质世界、促进社会变革的关键力量,新的科学技术改变了人们的交流、交通、生活方式,进而塑造了人们新的生活及价值观念。二是急剧的社会变革以及高度的社会流动与陌生化。交通和通讯技术的变革,促成了社会物质、制度和观念诸层面个人化的快速流动,这种高度流动性导致了全球性的陌生人社会和风险社会,从而催生了人们借由法律应对陌生与风险的全面需求。48前引2弗里德曼书,第21—31、60—69、70—83页。三是现代化导致社会诸方面的变迁,经济、一般社会结构和一般文化等发生了深层次的变革,尤其是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经济日趋加速前进,带来了物质的富庶和时间的闲暇,以及通过各种消费满足自我欲求的生活观念。这使普通人得以追求个人需求和梦想,选择并创造个人化的生活方式与风格。49Lawrence M.Friedman,The Human Rights Culture,pp.15,46-54;Lawrence M.Friedman,Total Justice,pp.30-34,38-43.
其次,与社会现代化几乎同步兴起了一种世界性的法律现代化运动——法律移植,或用弗里德曼的词语“法律借用”(borrowing)50前引4劳伦斯·M.弗里德曼书,第228页。,成为法律文化全球化的制度基础。根据弗里德曼的阐释,一般而言,法律会随着社会现代化自然演进到现代法律及其法律文化状态;但在某些社会情境下,某些国家和地区出于被迫或便利的考虑,会借用别国法律。在现代社会,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社会环境、条件和文化日渐趋同,这有助于法律的移植。不仅如此,现代法律文化本身在一定程度上亦可移植,当今世界不同地区的法律文化出现了汇合或融合,他认为这当中有些借用的原因。51前引4劳伦斯·M.弗里德曼书,第228—229、258—260页;Lawrence M.Friedman,The Horizontal Society,pp.62-63;前引5傅利曼书,第70—72页;高鸿钧:《文化与法律移植:理论之争与范式重构》,载《环球法律评论》2008年第5期,第8页。21世纪以来,全球法律移植的新气象印证了弗里德曼所言,当“经济的需要、政治的决断和人类的共同价值”52参见前引51高鸿钧文,第12—13页。日渐成为决定法律移植的共同因素时,民族地域性的法律文化也愈益获得了直接沟通和融合的可能。
最后,大众传媒的世界性弥散对法律文化全球化直接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弗里德曼看来,表现型个人主义和自由选择的概念并不是魔术般地进入人们头脑的。电影、电视等大众传媒塑造了人们的生活环境,进而塑造了他们看待世界的方式。电视向大众展示“从火奴鲁鲁到莫斯科再到新加坡”的同样体验53弗里德曼借用了乌尔里希·贝克的观点,前引2弗里德曼书,第149页。,为大众呈现出世界各地域文化、生活模式和典范的丰富多样性;加之传媒广告业的不懈鼓吹,选择的观念与真实性渐被植入人们意识当中,成为一种遍在信念,从而聚合成了大众法律文化。54前引2弗里德曼书,第70页。
四、评说:影响及评价
毋庸讳言,弗里德曼在法律文化、大众法律文化研究领域,做出了重要贡献,产生了广泛影响。
第一,弗里德曼最先提出了法律文化的概念,并系统阐释了法律文化的含义及其与法律制度的关系。他的研究为后来的法律文化研究奠定了重要基础,引领了世界范围关于法律文化的讨论,甚至引发了关于弗里德曼法律文化研究的专门国际学术会议。55如2005年10月,美国斯坦福大学专门举行了一场关于弗里德曼思想研究的学术会议;同年11月,一群来自不同国家的学者,在美国俄亥俄州辛辛那提市荟萃一堂召开法律史年会,设专场对“弗里德曼作品在美国社会”议题进行了集中研讨。这两场会议的成果及其后一些评述弗里德曼法律文化思想的论文,被辑录成书,正式出版。参见Robert W.Gordon,Morton J.Horwitz,Law,Society and History:Themes in the Legal Sociology and Legal History of Lawrence M.Friedman,pp.1-2。近几十年来,在美国及国际上历届比较法和法律社会学会议中,关于法律文化的议题越来越多。弗里德曼的著作成为当代引用率最高的文献之一,他的许多著作被译成了各种语言。中国最近三十年也开始了法律文化的各种讨论,并举行许多专题性全国学术研讨会。弗里德曼的很多著述被译成中文。凡此种种,都表明了弗里德曼法律文化思想影响之广。
第二,弗里德曼的法律社会学范式及其大众法律文化思想,从法律与文化作为社会要素的内部一致性出发,揭示了法律文化、大众法律文化与法律制度的关系,法律与社会的关系,以及大众文化与法律、法律文化的关系。这一研究对于我们超越书本之法,探索作为“活法”的大众法律文化;超越法律现象,探索影响法律的各种社会因素;超越法律文化,关注法律文化与一般文化的互动关系,具有重要的启示。
第三,弗里德曼关于现代法律文化、法律文化全球化的研究,主要揭示了现代大众法律文化的总体特征和一般趋势。他的理论对于协调外行法律文化与内行法律文化的冲突,协调传统法律文化与现代法律文化的冲突,协调现代法律制度与现代法律文化的冲突,协调本土法律文化与外来法律制度和法律文化之间的冲突,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第四,弗里德曼从文化之维研究法律,将大众法律文化作为研究重心,有助于人们避免把法律等同于统治者的意志、阶级压迫的工具以及政治意识形态。法律文化尤其是大众法律文化的概念,提示我们关注社会、历史传统和文化内涵,重视法律演进的一般规律和独特的语境,从而构建既具有本土特征又具有普世精神的现代法治。
当然,与其他理论一样,弗里德曼的法律文化理论也存在某些不足。首先,其作为分析工具的法律文化、大众法律文化、大众文化等概念,均存在模糊性,不易把握。他的研究主要得自对法律文化现象的一般观察,缺乏实证性调查,因而一些结论感性色彩明显,欠缺严谨。其次,弗里德曼关于大众法律文化的论述,主要基于美国法律文化。诚然,美国文化曾被视为大众文化的代名词56参见前引16约翰·斯道雷书,第34—36页。;但美国法律文化无论如何具有典型性,也不能反映世界现代法律文化的整体形象和多样形态。最后,他在大众法律文化作为活法的能动性以及法律变革、法律移植、法律文化全球化趋势方面,持论过于乐观,对于其中的复杂性和曲折性估计不足。
弗里德曼的法律文化理论尽管存在上述不足,但对于他的法律文化体系和关于大众法律文化的许多洞见,这些不足并无大碍。他的法律文化理论是西方乃至世界法律思想中一份珍贵的财富。另值得一提的是,弗里德曼近些年连续发表了多部法律类悬疑小说57参见弗里德曼“弗兰克·枚律师纪事”系列小说(The Frank May Chronicles),如Who Killed Maggie Swift? (2014),Death of a One-Sided Man(2013),An Unnatural Death(2012),The Book Club Murder(2012),Death of a Wannabe(2011),The Corpse in the Road(2008)等。参见https://www.law.stanford.edu/profile/lawrence-m-friedman/publications,2014年8月27日访问。,跻身大众法律文化的创造者之林,从而现身说法地为“选择共和国”、表现型个人主义的现代大众法律文化做出了进一步诠释与论证。
五、余音:他山之鉴与中国法治文化建设
在理析了弗里德曼大众法律文化的基本理论之后,让我们再回到开篇纽约街头施舍与拒受的一幕。单就法律文化视角而言,中国富豪赴美施善的行为,不管其动机是标榜高尚、追求个人名望,还是致力于“兼济天下”的理想实践,都是乘借大众传媒文化的全球化效应,践行了一番表现型个人主义的权利;而乞丐的拒施行为,无论是出于对自我尊严的维护,抑或“我流浪我乐意”心态下对个人生活样态的自洽,均在以沉默之音诠释着“选择共和国”之“国民”的自由。由是同一时境下不同意识的社会行动者,在不经意间一同彰显了弗里德曼所研究的法律文化主题:大众法律文化,现代法律文化,法律文化全球化。其实这出跨国“雷剧”只是信手拈来的网络“旧闻”之一,更多与之相仿、昙花一现的“雷人雷事”均可用弗里德曼大众法律文化的范式予以阐释。这些朝生暮死的信息在今天之所以得闻天下,最主要是由于大众新传媒——互联网的全球漫卷。
(一)当互联网成为“精神象征物”:中国的“选择共和国”征象
“正如牛顿时代和霍布斯时代以机器为时代象征物”,互联网已成为当代社会的“精神象征物”。58参见余盛峰:《互联网是当代社会的精神象征物》,载http://huyong.blog.sohu.com/301622573.html,2015年3月29日访问。互联网时代地球上各个隅落的人和事,似乎均可同步直播全世界;即使离群索居于最偏僻的地角,也能足不出户神游太虚;并且这种网络信息盛宴并非某种限供的特权,而是普通大众共享的资源。互联网的便利与大数据的信息冗余,使得弗里德曼二十多年前的这一预言开始变为现实:“选择的共和国”终会将它的“疆域”扩展到人类居住的整个世界;中国也必然走上表现型个人主义的现代法律文化之路。
21世纪的中国不仅通过法律移植实现了社会制度上的现代化变革,而且日趋融入了全球化的法律文化潮流,在私人生活领域及公共事务场域,均呈现出“选择的共和国”征象:其一,人们拥有了极为丰赡的商品消费、生活方式体验及价值观的选择,自由、平等、权利成为普遍性的大众语言;其二,各层次的表现型个人借助互联网空间,以各自方式表达及创造着自我,彰显着多元的个性差异与审美满足;其三,互联网使沉默的大多数真正有机会发出声音,寻求广泛的关注与认同,呼吁完全正义的期待及实现;其四,中国社会日益扁平化,同侪群体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政治权威亦趋平行化、名人化,法律地位上升,政治领导人一改深居红墙之内的传统,频频在大众传媒中亮相,甚至秀早餐、生活照、家人及个人爱好等生活细节,运用大众名人文化展示平易近人的形象。从法律文化的边缘到中心,一个“我的生活我做主”的大众“选择共和国”正在落地生根。
(二)“全球信息化秩序”59余盛峰博士认为,20世纪80年代以降,民族国家制造业社会向全球信息化秩序转型;法律全球化与信息全球化相互推进,对全球法律产生了革命性影响。关于全球信息化秩序与法律的详解,参见余盛峰:《全球信息化秩序下的法律革命》,载《环球法律评论》2013年第5期,第106—118页。下的选择:走出洞穴构建法治文化
深入理解当代法律文化转型中的大众“选择共和国“意象,对我们全球化时代的法治文化建设具有导航意义。但我们目前对这一转型及意义显然认识不足。这体现在法律实践和法学研究两方面的某些滞后性。法律实践方面,法治建设整体思路仍待继续更新,目前仍在遵行后发国家通过制度扭转生活的单一模式;法治建设主体仍以内行法律人独自担纲,未真正认识到现代大众的强大力量和应有的主体地位,只将其当作被普法、被启蒙的对象;对于现代社会复杂系统分化运作的认知缺位,仍动辄以政治权力代俎法律系统的运转,尽管越来越重视在法律的框架内行使权力。法学研究方面,近三十年在弗里德曼法律文化思想影响下,我国学者对法律文化概念、类型等基本理论的研究已较为深入、精微;但对弗里德曼现代大众法律文化思想关注者不多,有关中国现代法律文化的观察及研究仍相对薄弱;主流法学研究范式仍固守近代西方主流实证分析法学的内在视角,并力图以此形塑实践,推动形式理性法的建构;法律文化研究重心仍未完全摆脱古与今、中与西论战的泥淖。60自近代以来,围绕中国法律及其文化的本土派与西化派一直在中与西、古与今之间争鸣不休。高鸿钧教授和鲁楠博士后对历来各执一端的争论做了系统梳理,并分别从理论与方法范式视角提出古今中西合奏观,成为学界颇具影响力的观点。参见高鸿钧:《法律文化与法律移植:古今中西之争》,载《比较法研究》2008年第5期,第12—24页;鲁楠:《全球化时代比较法的优势与缺陷》,载《中国法学》2014年第1期,第102—124页。但随着法律文化全球化及中国文化自信力的增强,法学界和实务界的执端战火有余烬重燃之势。笔者认为当下再启此类论战已不合时宜,古今中西文化交响曲是全球化时代中国必然的主旋律。
西方现代社会自然转型之时,法学者深居目的理性的洞穴描画出现代法律的影子,并照此铸造了规训的铁笼;而今他们已走出洞穴,力图从现实生活演绎和诠释法律的故事。如果先前我们一直在亦步亦趋地追随其影,那么现在是甩开影子,一同感受洞穴外真实世界的时候了。不同时空的法律文化凭借互联网的瞬时集结一应俱呈,对此我们应当敏锐把握机遇,做出合理化选择。要放下过时的做法、想法——制度牵引生活的模式可以休矣!政治对法律系统的越俎代庖可以休矣!古今中西之争可以休矣!要正视现代大众法律文化全球化的事实,重估大众作为“选择共和国”担纲者的主体性,发掘“雷人雷事”潜藏的表现型个人主义力量,从当代中国、当代西方、当代世界中发掘滋育当代法治建设的正能资源。惟其如此,中国才能在全球信息化秩序下的法治文化道路上,阔步前进。
* 本文节选自高鸿钧、赵晓力主编:《新编西方法律思想史》,将由清华大学出版社2015年7月出版,略有改动。本文写作得到业师高鸿钧教授的悉心指导与鼓励,《中国法律评论》董飞编辑也给予了精心的指教与帮助。在此深表谢忱!与鲁楠、余盛峰、姜昊晨、赵聚各位仁兄及同道读书会诸友的交流也让我受益匪浅,特此一并致谢!当然文责自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