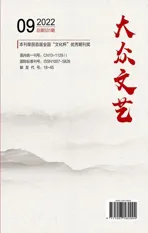浅谈“圈舞”舞蹈文化遗存的萌芽与发展
2015-01-28海维清四川大学610207
海维清 (四川大学 610207)
浅谈“圈舞”舞蹈文化遗存的萌芽与发展
海维清 (四川大学 610207)
“圈舞”是人类最初创造的舞蹈艺术形式之一,中华大地上的“圈舞”舞蹈文化遗存历史悠久,形式丰富,传播地域广泛,堪称活着的舞蹈“化石”,它也是民族文化的一种重要信息载体,昭示着人类童年特殊的社会生活内容和人类心理、情感“进化”的复杂记忆。舞蹈作为“非物质”属性传承的艺术门类,使我们试图研究“圈舞”历史萌芽与发展脉络的进程显得异常艰难,而研究“圈舞”文化的产生、传播与发展进而考察“圈舞”功能、形式和审美的历史嬗变也因此显得尤为重要,因为这将为我们在当下时代认识并继承好"圈舞"这笔宝贵的舞蹈文化财富提供更为科学合理的方法。而当我们正确地认识这些“圈舞”舞蹈现象之所以萌芽、产生、发展、传承的因素时,我们就能为这些即将消失的历史久远的舞蹈形式,重新找回属于它们自己的灵魂。
圈舞;舞蹈;文化;萌芽;发展
一、“圈舞”舞蹈文化遗存及其萌芽
中华“圈舞”舞蹈文化源远流长:其有据可考的历史至少可从青海大通上孙家寨出土的新石器时代“舞蹈纹”彩陶盆算起,到当下仍在藏区广为流传的各类“锅庄”,四川羌族的“萨朗”,摩梭人的“甲蹉舞”,云南纳西族的“热美蹉”“维蒙达”“东巴舞”,佤族的“木鼓舞”,独龙族剽牛祭天牵手围圆的“剽牛舞”,新疆维吾尔族苏菲派宗教性“萨玛”圈舞,东北鄂伦春族“篝火舞”……传承至今约五、六千年。
由此可见,中华大地上的“圈舞”舞蹈文化历史悠久,“圈舞”遗存形式丰富,“圈舞”舞蹈文化传播地域广泛。
而“圈舞”舞蹈文化之所以能在这些不同的民族中普遍萌芽、发生并传承、发展,体现出如此宽广的文化跨度及“适应性”,仅依赖舞蹈文化自身的传播能力是无法达到的。究竟是什么样的条件,才如土壤和甘露般,促成“圈舞”舞蹈文化在这些民族文化生活中萌发与生长?
通过对拥有“圈舞”舞蹈文化遗存现象的多个民族比对与分析,我们可以肯定,在这些瑰丽的“圈舞”舞蹈文化遗存现象背后,积淀着中华民族深厚的人文内涵。而初民原始、朴素、平等的特殊社会结构和“崇拜意识”下“万物有灵”观念的产生,则是“圈舞”萌发的重要诱因。
统观具有“圈舞”文化遗存现象的这些民族,他们都具有或曾经具有“万物有灵”观念下的“多神崇拜”信仰传统,如以“锅庄”著称的藏族,古代曾普遍信仰具有原始崇拜特征的巫教——“苯教”,直至公元7世纪后才逐步改信佛教;西北蒙古族、维吾尔族、土族以及东北鄂伦春、鄂温克等民族,历史上曾长期信仰萨满教;而西南地区的羌族、彝族、纳西族、苗族、侗族、普米族、瑶族、基诺族、独龙族、佤族等少数民族,其信仰种类繁多,如羌族“释比”,彝族“毕摩”、“苏尼”,纳西“东巴”,摩梭“达巴”……但这些信仰大都具有“多神崇拜”的某些基本特征,且其社会成员多具有较为朴素、平等的社会关系。
在这种“崇拜意识”支配下“重巫尚神”的信仰中,崇拜仪式与祭祀活动较为频繁,而由崇拜、敬畏心理引发初民情感、意识的集体性投射与集中,聚焦至核心崇拜对象上,便交集出一个客观存在的“圆心”,从而促使人们围绕这个“圆心”相互聚拢,在向神灵诉说族群共同的愿望、感激、哀伤与敬畏时,情不自禁的联袂集中,呼号顿踏,最终踏歌而舞,从而促使“圈舞”舞蹈形式的萌芽与产生。
二、“圈舞”舞蹈文化传播及其形式、功能流变
需要指出的是,“圈舞”文化的发生和传播是多因素的,例如由民族战争、迁徙造成民族之间文化(包括舞蹈文化)的传播与融合,也是促成“圈舞”舞蹈文化现象在少数民族舞蹈文化中普遍传承的另一个重要因素,而这个因素在西南地区少数民族的“圈舞”文化传播历史中更为突出。
笔者较为认同贾安林老师的观点——羌系民族是“圈舞”在西南地区的重要传播者。
羌族历史渊源悠久,殷甲骨卜辞中有役使“羌”或“多羌”以及以大量“羌”作“人殉”的记载,而关于羌族的历史渊源及秦汉时期向西南地区迁徙的历史,在马长寿先生遗著《氐与羌》和任乃强先生著《羌族源流探索》以及其他大量关于羌族历史、文化研究的著作、论文中,都作过非常系统的研究和阐述。
秦汉之际,古羌族先民通过费孝通先生所提出的“藏彝走廊”大量向南迁徙,与西南本地土著民族逐渐融合,产生了彝族、纳西族、白族、哈尼族、僳僳族、普米族、景颇族、拉祜族、基诺族等众多兄弟民族。
此外,藏族与羌族在族源上也有密切的联系:7世纪松赞干布时期,吐蕃从山南迁都逻些(拉萨),随后兼并了北方的苏毗、象雄等西羌部,又破党项、白兰羌部,击败西迁甘、青的辽东鲜卑“吐谷浑”政权。随着战争兼并,西北羌族大范围融入吐蕃并被不断同化。综上所述,汉藏语系藏缅语族的多数民族族源上与羌族之关系密切,这一点也为众多学者所认同。
通过对马家窑“舞蹈纹盆”的研究,专家们普遍认为这就是西北地区古羌先民乐舞活动的真实摹写。其舞蹈文化特征与今天聚居茂县一带的羌族民间“莎朗”非常类似,它也与今天甘肃南部舟曲县(与古羌故地之一的“宕昌”相望)藏族“罗罗舞”舞蹈形态酷似。
我们可以设想,由于古羌先民长期大量南迁,加之古代民族间战争、兼并造成的民族文化融合,促使“圈舞”舞蹈文化也随之向更遥远的西南地区传播。古羌民族“圈舞”文化基因伴随南迁的脚步,与途中“土著”民族的舞蹈文化相互消解并相互融合,因而使西南众多藏缅语族形成了较为普遍的“圈舞”舞蹈文化现象,因此也促使西南地区各民族中的“圈舞”舞蹈文化分布更趋集中。不过,上述现象仅能解释“羌系”民族或“藏缅语族”圈舞文化传播、传承的主要因素,而东北和新疆地区“圈舞”文化的传承因素还需另做它论。
正如社会生物学家爱德华·奥斯本·威尔逊的观点:“在进化的意义上讲,文化的大部分内容都是适应性的。”在广义社会“文化”发生变化的同时,其影响也同样直接或间接体现在作为“意识形态”的舞蹈文化之中,“圈舞”舞蹈文化在不同的社会历史阶段,其功能、形态、审美均呈现出不同的特征。
虽然艺术起源有着非常复杂的机理,但在这里,“群体意识”的确是早期“圈舞”形式发生的重要诱因。初民在狩猎、采集归来后,围于篝火边炙烤的食物周围,共享食物,分享猎获成功的兴奋。饱食庆祝之余,呼号振臂,顿踏击节,逐渐形成“圈舞”雏形,其舞蹈以强化群体认同与沟通,维系初民朴素平等的社会关系为主要功能。
而随着“神灵意识”的产生,“圈舞”则逐步以“娱神”或“巫术”为主要目的进行,并促使人们联结成各种形式独特的圆圈,例如佤族“猎头祭谷”的“木鼓舞”,独龙族“剽牛祭天”的“剽牛舞”等,往往借助这样的“圈舞”活动,以达到初民操纵自然的企图,可见这时的“圈舞”功能已逐步发生变化。
伴随着历史社会的不断发展,“世俗化”的社会文化逐步形成,昔日敬献神灵的舞蹈,却成为了人们自娱、社交的媒介,舞蹈恢复了它本来的形态,其功能从“娱神”走向“娱人”。这样的转变在今天还在发生,那许多祭祀鬼神的舞蹈,如佤族“猎头祭谷”的“木鼓舞”,今天再敲响起舞的时候,根本不需要“人头落地”来作为祭品,或许它正在某个旅游景点的舞台上,成为供人欣赏的艺术;羌族的“莎朗”有“忧事”、“喜事”之分,土家族摆手舞分的“大摆手”“小摆手”,嘉绒藏族锅庄舞分“大锅庄”和“小锅桩”,凡此种种,大抵也是这个道理,只是在很早时候,这类“圈舞”已衍生出两种甚至多种不同的功能与形态。
从形态来看,西部民族“圈舞”舞蹈形式的发展,应该符合艺术形式发展的一般规律,即从“朴素、稚拙”走向“繁复、华美”再到“抽象、简约”的阶段,呈“螺旋式”发展。
因为“童年期”人类的构形能力并不发达,最初的“圈舞”大多结构松散,形式朴野——它们往往步伐简单,动作即兴,多呼号顿踏,重复循环,若以今人视之,或无几分美感。
而宗教观念产生之后,人们才怀着敬畏、崇拜的心理,结手成环,歌舞祈愿,以祀鬼神。这种联臂舞蹈,结构较缜密,恰如一系列马家窑“舞蹈纹盆”所描绘的那种“圈舞”舞蹈形式。
此后,“圈舞”的形式,向着更为繁复的方向发展,出现许多“圈舞”形式的变形和变体,例如侗族“多耶”舞变单圈为多圈相套;苗族“芦笙舞”和云南彝族“左脚舞”开始内外圈互相穿插;景颇族“目脑纵歌”则是在圈舞队形上变出更为复杂的纹路调度;羌族“莎朗”变幻出热烈欢快的复杂舞步;摩梭人的“甲蹉”在圆圈中绕出“U”形和“S”的调度,嘉绒藏族的“锅庄”更是出现了在舞蹈中将“圆弧”切成男女各异的两个半圆,为面对面的直排舞蹈埋下伏笔。
在自娱的功能下,人们以更为繁复的联结方式将手臂“编织”在一起,或者干脆松开“链”接的双手,在圆圈中更洒脱、自由的手舞足蹈,创造出新的“圈舞”形式美感。
三、当下时代“圈舞”舞蹈文化遗存的继承与发展
正如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说过,“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现代人演绎的古人“圈舞”,即使动作完全相同,但它也已经不是古人所跳的那个“圈舞”了。
随着整个世界的现代化,曾经积淀在中华民族“圈舞”身后那些古老厚重的历史和文化正在被现代文明慢慢消解。当下“旅游文化”的兴起,以往“圈舞”中的“庄严神秘”的美,早已被“欢快、热烈”的喧嚣所代替,以“创收”为目的“圈舞”,其舞蹈“功能”也早已嬗变,它们多沦为满足游客猎奇心理,体验参与“互动”的某个环节,“圈舞们”踏出越来越快却愈发苍白无力的舞步。
面对这样的现状,作为艺术工作者,我们无法因当下“圈舞”繁华的表象而沾沾自喜。如何合理对待这种古老舞蹈文化的传承和发展,绝不是金钱和“一哄而上”的热情所能替代的。它还需要科学、合理的引导,方能真正达到保护和传承良好心愿。因为不恰当的方法致使意图与结果南辕北辙的例子在舞蹈文化的传承和保护工作中并不鲜见。
在当年“锅庄舞”的普及与推广中,在达到普及目的的同时,也曾一度使部分藏区的“锅庄舞”呈现出“单极化”的局面,因为在普及的过程中,那些本身极具本土特色的地方锅庄被极度“边缘化”甚至失传,令人非常惋惜。因此,如何更科学合理地继承并发展“圈舞”,不是一个简单的议题,笔者曾和他人做过一些讨论,对此有一些不尽成熟的观点,以下抛砖引玉,以供探讨。
对待“圈舞”文化的传承问题,应该实行“双向并列”的战略性方针路线。所谓“双向并列”,简言之,就是“民间草根”和“舞台高端”采取截然不同但却并行不悖的两条路线:
1.在圈舞“民间传承”中借鉴并采取类似韩国传统文化保护的一些方法,恰如现在国家出台的一系列“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措施一样,将那些本土“圈舞”文化的重要继承人以“传承人”的方式进行重点保护,同时指定一定的本土“继承人”,通过“言传身教、口传心授”的方式进行传承。其传承方式尽可能以“原封不动”的模式进行,以最大限度地保持这种传承的“纯正性”,禁止“继承人”的随意的改动或编撰。同时做好相关影音、文字记录和整理工作,做到即使意外失传也可以“有据可考”,甚至可以逆向恢复。
2.在“圈舞”的“舞台发展”和弘扬上,则可不必拘泥于那种过于保守的发展方式,在不破坏所发展“圈舞”的文化根基上,利用相关舞台艺术手段,进行合理的发展和创新。但务必切记的是,这种创新不能为了让“圈舞”适应舞台表演而彻底破坏它作为“圈舞”的基本形式和基本语汇,应该在创新中有一定比例的“原型”出现。此外,更应注意“圈舞”外在形态和内在审美相对统一的问题,不应扭曲“圈舞”固有的人文内涵和舞蹈语汇,这些也是所有传统舞蹈创新发展中必须重视的要素之一。
而在这两者之间,还应注意“双边路线”的“并行”,以及各自路线实行“领地”的界限。所谓“并行”,是指这两种方针必须同步,否则就会重蹈覆辙,不能很好的兼顾“继承”和“发展”这两方面内容;所谓“领地”,就是各自方针所实行的范畴和区域,粗略看我们就可以以“民间业余”或“专业舞团”的角度划分其领地。
此外,在“民间草根”和“舞台高端”这二者之间,还有一个“灰色”的地带,是最不容易实行引导的部分——“旅游文化”演出。
在这一范畴内,“圈舞”的发展现状往往随本地旅游业的发展情况各自为政,良莠不齐。但“旅游演出”的受众最广,影响深远,同时“伪民俗”和“外来文化”对这部分的冲击更为直接,究其原因,往往是由“文化自信”不足甚至“文化自卑”的心理造成。
对这一部分而言,笔者认为,即使“土”,即使有些“单调”,但游客千里迢迢慕名而来,希望看到的其实应该是极具民族文化特色,原汁原味的本土“圈舞”艺术瑰宝,而不是迎合商业需要,看似华丽实则廉价的“赝品”和“山寨”。
因此,对待这一区域内的传统“圈舞”,应该充分利用旅游业的资金优势,吸引当地更多人加入到“继承人”的行列。而在旅游文化范围内,应该采取较为保守的艺术态度进行引导,不盲目地强调创新,不人为扭曲“圈舞”舞蹈语汇和形式以迎合观众,才能最大限度保持进入这一区域的“圈舞”以“原生”形态进行有效继承与传播。
研究中我们还发现,“圈舞”活动往往随着相关民俗或宗教节日而存在,因此可以利用本土的这些民俗节日,以一定的物质奖励,鼓励引导乡镇群众“圈舞”汇演或“圈舞”联谊活动,促使“圈舞”艺术能够在民间仍然保持深厚的群众基础,将有利于“圈舞”文化的良性的发展。
不可否认,“圈舞”是最有生命力的传统舞蹈艺术形式之一,从有据可考的“圈舞”艺术萌芽、诞生至今约6000多年,仍然莘莘不息。而在现代文明高度发展的今天,来自天南海北的陌生游客依然能够很轻松地加入到旅游景点“圈舞”的舞蹈队列之中,不仅透露出今天人们返璞归真的一种内心需要,而且还昭示着“圈舞”这种古老舞蹈文化遗存所蕴含的巨大魅力和潜力···
透过那轮转不息的一个个舞圈,我们依稀还会发现,这个人类童年诞生的“精灵”,依旧如此天真烂漫,毫无拘束地站在我们对面,用真挚的手,邀请我们加入到他那稚拙、唯美的圆圈,而当你、我的手触及他指尖的那刻,你我还应该意识到——研究、继承承并发扬好“圈舞”舞蹈文化遗存,是为孩提时代的中华先民,重新找回那颗被人们遗落在荒原,埋没于尘埃之下的星辰。
[1]贾安林.《“篝火之舞与联袂踏歌”—藏缅语族圈舞文化特征和功能》《北京舞蹈学院学报》,2005(2).
[2]芈一之.《从精美舞蹈盆说到民族发祥地》《青海民族研究》,1998(1).
海维清,男,满族,四川省舞蹈家协会会员,艺术学硕士,四川大学艺术学院舞蹈系教师,研究方向:民间舞蹈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