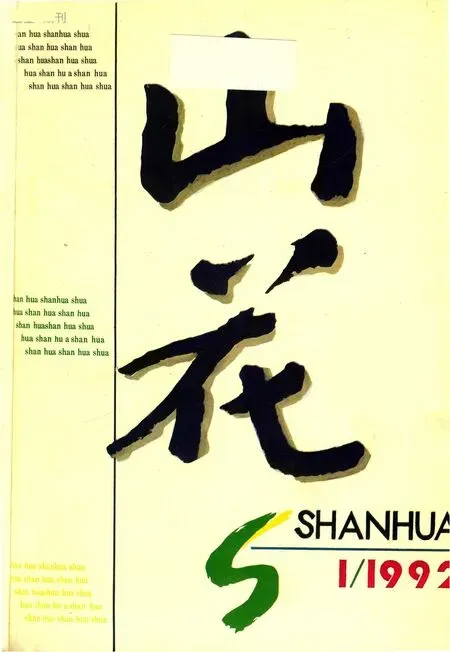“可靠”的不可靠叙述——论《黑猫》中的叙述话语的选择
2015-01-26刘碧珍
刘碧珍
聪明的作者擅长讲故事,会把各种叙事策略运用得天衣无缝,恰到好处。有些看似平常的布局却是作者的匠心独运,看似表里不一、自相矛盾的叙述可能是作者刻意而为之,故意引起细心读者的发现,从而使作者与读者能在叙述话语层外进行深入的交流,而不为表面现象所迷惑。
韦恩·布斯在《小说修辞学》曾提出距离控制的概念,并指出作者、叙述者、其他人物、读者之间在价值、道德、情感、理智、时间、空间等各方面存在的距离,可以由作者选择的叙述技巧控制变化,并产生不同的阅读效果。[1]同时他还首创了“不可靠叙述”的概念,此时他认为不可靠叙述也是由于叙述者与其他主体之间的距离造成的,而对不可靠叙述并未作细致的划分。直到后来经典叙事学学家詹姆斯·费伦不仅以叙述者和隐含作者之间的叙述距离为基准来考量不可靠叙述,而且还将叙述者与作者的读者之间的叙述距离纳入研究视阈,得出六种不可靠性类型:误报、误读、误评、不充分报道、不充分读解、不充分评价”[2],同时他提出不可靠叙述的伦理取位,指出“伦理取位既指叙事技巧和叙事结构决定读者对于叙事位置的方式,也指个体读者不可避免地从特定位置进行阅读的方式”。[3]
鉴于以上理论,我们解读爱伦·坡的小说《黑猫》,会得到与众不同的阅读效果。
爱伦·坡的小说《黑猫》以死囚的身份回忆并讲述“我”养黑猫、虐猫、杀猫、再养猫,最终杀妻的经历。通过表层的故事情节分析,读者很容易受第一人称叙述者的表述影响,认为“我”从一个善良的人演变为冷酷的杀人犯完全是由于黑猫在作祟,因为黑猫在中世纪西方文化中就是不祥的象征,而且小说中叙述者也多次提醒读者注意这一文化元素。但如果对叙述话语进行细致分析,我们会发现随着情节的发展,叙述者内在的情感不自觉地流露出来,叙述话语随之变换,从开篇忏悔的叙述话语变成矛盾的叙述话语,最终暴露其最本真的话语——冷酷无情的叙述话语,从而在叙述的结尾,读者明白之前的叙述都是伪善的、虚假的和不可靠的,会觉得毛骨悚然、不寒而栗。从而,叙述者与读者之间的距离也会随之改变,作者真实的创作意图和情感价值态度也就显露无疑了。
善良、忏悔的叙述话语
小说开篇,作为死囚的“我”告诉读者自己明天就要死了,必须在临死前“把一系列家常琐事清楚简洁,不加评语地公诸于世”,并表明“唯有趁今天说出一切,我才能让灵魂安生”。“人之将死,其言也善。”这样的话语显得真诚、可靠。读者自然与叙述者拉近距离,读者很容易对叙述者报以同情,而且完全相信他临死前即将讲述的故事。
接着叙述者告诉我们:“从小我就表现出善良温驯的性格。因为心肠软得出奇,我甚至曾经是班上朋友们的笑柄。”“我特别喜欢动物。”“我与它们寸步不离,童年中最大的快乐就是能这样喂养抚爱我的宠物们。这爱好随着时间步步加深,到我成人之后,都依然是我获得喜悦满足的源泉。”从这些讲述中,读者看到一个善良、有爱心的叙述者,甚至会跟随叙述者为他的罪行寻找非主观原因。“我”坦诚地告诉读者,我的脾气发生变化是因为酗酒造成的,性情改变的“我”不再喜欢动物,包括那只曾经一度挚爱的名叫“普路托”的黑猫,尽管妻子迷信地认为黑猫都由巫婆变化而来,但“我”和猫的交情友好地维持了好几年。然而,酒却让“我”丧失了本性,“我”越发喜怒无常,甚至由辱骂演变成对妻子拳打脚踢。对于可怜的宠物们,关爱转为了虐待。最终连普路托也难逃挖眼的厄运。对于这些罪行,叙述者供认不讳,甚至发出“天啊,此刻我面红耳赤,写出这幕该死的暴行,我自己都不寒而栗”的感叹。可见,此时的叙述者还是敢作敢当,有忏悔意识的,他并没有泯灭基本的人性。他的所作所为只是在喝醉酒意识不清醒的状况下发生的。此时的叙述者让人感觉是正直、善良的,是读者所能接受的,因而,他此时的话语是能被读者相信并给予一定同情的。
矛盾的叙述话语
随着故事的逐渐展开,读者发现叙述者的忏悔话语在不知不觉中发生了变化,叙述者对待家人和宠物犯下的过错已经不仅仅是辱骂和虐待这么简单。他在残忍地挖去黑猫的一只眼睛后,发觉一种带有恐怖的悔意涌上心头。但这至多不过是一种淡薄模糊的感觉而已。他依然狂饮无度,没有忏悔的行动,对它更加不满,终于在一天早晨,他心硬如石,拿绳索套紧猫的脖子,把它吊在树枝上。但同时叙述者又说“我吊死了它,正因为深知它曾深爱我,正因为它不曾丝毫冒犯我。我吊死了它,正因为知晓这份罪恶——致命的罪恶,罪大之极,足以让我的的灵魂永不得超生,哪怕是严厉公正宽恕一切的天主,也绝不宽恕这罪恶”。并在家中失火之后,有好几个月摆脱不了那猫的幻象纠缠,心里又滋生一股说是悔恨又不是悔恨的模糊情绪,非常后悔害死了那只猫,甚至开始到处物色外貌多少相似的黑猫做填补。终于找到一只酷似普路托的黑猫,“我”把它带回家,抚爱有加。这时,读者会感觉叙述者良心并未完全泯灭,他在杀猫之后还有些顾忌,还有悔恨,哪怕是一种模糊的感觉。我们会猜想他一定会好好对待后来带回的那只黑猫,以弥补曾经对普路托的伤害。但很快,从叙述者讲述的故事中我们发现事实与叙述者先前的描述以及给读者留下的心理预期有出入,甚至颠覆了叙述者最初给读者留下的善良印象。此时读者与叙述者之间的距离无形中拉开了,读者对叙述者由同情转为怀疑。
冷酷无情的叙述话语
捡来的黑猫对叙述者亲近,可是“我”心里却日渐生出一种对它的厌恶。厌恶之情与日俱增,终于变成莫名的仇视了。尤其发现黑猫的眼睛也被挖去和脖子上有刑台的痕迹后,叙述者发出这样的惊呼:“一只没有理性的畜生竟对我,按上帝形象创造出来的人,带来如此不堪忍受的折磨!”“我身受这般痛苦煎熬,心里仅剩的一点善性也殆尽。唯有恶念于我显得亲密——转来转去都是极为卑鄙龌龊的邪恶念头。我脾气长久已经喜怒无常,如今发展到痛恨一切事,痛恨一切人了。我可怜的逆来顺受的妻子,她成了我所有自我放任的频繁而狂暴的怒火的牺牲品。”[4]在叙述者的观念中,我是人,是高贵的,猫是动物,是低级的,我不能受动物的摆布和折磨,而且我也是凌驾于其他人之上,所以我会为我的罪行开脱,会把自己的不幸都归结于他人。黑猫跟我下地窖,在楼梯上差点把我绊得摔断脖子,我气得发疯,抡起斧头,盛怒之下忘了自己对猫那份幼稚的恐惧,对准猫一斧砍下,带着彻底要一击毙命的杀意。但由于妻子阻挡,我竟然残忍地将妻子杀害。并且更令我们咋舌的是“谋杀已然犯下,我索性细细盘算要怎样藏匿尸首。无论白天还是黑夜,要把尸首搬出去,难免要给左邻右舍撞见。我心里掠过无数计划。起先我想把尸首剁成小块烧掉,来个毁尸灭迹。又或者扔到院子中的井里去。再不然就把尸首当作货物装箱,按照常规,雇个脚夫把它搬出去。最终,我忽然想出一条自忖万全的良策:把尸首砌进地窖的墙里——就像有传说,中世纪的僧侣把殉道者砌进墙里”。[5]并且更不可思议的是,“我”竟然在杀妻碎尸藏匿之后,酣然入梦。这是一个怎样无情的丈夫和冷血的人啊!最后,真相大白,“我”仍然抱怨黑猫是诱使我理智丧尽亲手杀妻的邪恶的畜生,如今用尖叫送“我”到刽子手的手中。
讲述藏尸时,叙述者极尽语言之能是。“我用了一根铁撬轻松地撬开墙砖,再仔仔细细把尸首贴着里边的夹墙放好,让它撑住不掉下来,然后不多费神就把墙照原样砌上。我弄来了石灰、黄沙和一切必要材料,配调了一种跟旧灰泥分别不出的新灰泥,小心翼翼地把新砌的砖墙抹平抹匀。完工后,我心满意足地审视着成果。看不出任何动土的痕迹,地上落下的垃圾也细细拾干净。我洋洋得意,暗念说,到底没有白忙。”[6]一个凶残无人性的凶手形象跃然纸上。在警察来时,“我”居然没有悔意,认为自己高兴得已经忘乎所以,随心所欲说起胡话,并且不希望自己的罪行东窗事发,在暗地祈祷:“主啊!愿主保佑,至少拯救我于罪恶和魔鬼的恶爪吧!”听到猫在墙里发出声音,居然这样表述“——敲墙的回响余音未寂,就听得墓塚里发出一声回应!——一种呻吟,先是瓮声瓮气,断断续续像个孩童抽泣,随即一下子变成连续不断的高声长啸,声音凄厉,惨绝人寰——那是一阵,半似恐怖,半似得意的号叫——仿佛自地狱的业火——永世轮回受刑者的悲鸣,和着施酷刑的地狱魔鬼的欢呼才能混合出这样的声音!”[7]这明显是把自己的罪行都描述为黑猫这一不祥物带来的。
读到这时,读者不禁恍然大悟,与叙述者的距离越来越远,明白叙述者一直在欺骗我们,他先前表达出的忏悔性的话语都是不可靠的,其实,他临近死亡对自己所犯下的罪恶虽供认不讳,但并无悔意。而且,细心的读者如果稍加留意或者再对故事进行重读,就一定不会被叙述者的伪装所迷惑。因为在他刚刚讲述故事不久,叙述话语就显示出了不可靠表述。此时善良与正直的读者必然对叙述者的所作所为产生厌恶和不解,从而重新审视叙述者与他的不可靠叙述。
不可靠叙述
小说开篇叙述者故弄玄虚,想告诉大家他要讲一个荒唐而又平凡的故事,而且不祈求受众相信,因为他自己也不相信,但又告诉我们他的亲身经历,明天即将赴死,今天必须讲出。这样的开场营造了一个恐怖、不寻常的氛围。叙述者表明这些事对他来说是彻彻底底的恐怖,他认为一般人对其故事会做因果关系的推断,所以不想详细解释,似乎恐怖不是他制造出来的。但其实,他一直是事无巨细、喋喋不休地讲述或描绘他性情的改变,他自身命运的变化,并力图在讲述中表明他是无辜受害者,黑猫才是罪魁祸首,或者酒精是造成悲剧的始作俑者。尽管语言表述与实际行为构成矛盾,但目的只有一个,即误导读者,相信他是真实善良的。当然,误导只是暂时的,开篇伪装得越善良,越能与结尾的凶神恶煞、冷酷无情形成鲜明对比,彰显不可靠叙述的艺术魅力。
在第三段,“我必无须费力解释个中无穷的乐趣。正是人与人之间习以为常的薄情作反衬,这份对宠物真挚之爱,这种无私之情,才更显温存暖心。”叙述者交代“我”爱动物是与人之间的薄情形成对比,同时又说“我”曾因为心肠软被伙伴们笑话。长大后的“我”依旧记得和在意儿时朋友的笑话及和人相处时所遇到的不快与伤害。这样的叙述内容无形中告诉读者:“我”不是一个豁达之人,严格来说,也不是一个真正善良温顺之人。只要有机会,“我”会报复,“我”会证明“我”的心肠并不是软得出奇。叙述者现在的境遇也就证明了这一点。而且,叙述者对如何虐猫、杀猫以及杀妻并且碎尸进行了详细的描述,没有任何的不舍与害怕的说明,就让“我善良”的谎话不攻自破。所以,冷酷、可怕、有一定心理疾病的叙述者形象在其自我描绘和叙述的过程中自然生成。爱伦·坡作为优秀小说家的功力也就可见一斑了。
总之,读者只有细读文本,对作品的叙事结构和遣词造句进行全面仔细的考察,认真分析叙事策略,才能不被话语或故事的表象所迷惑,与作者之间能进行坦诚的对话与交流,明白与理解作者的创作意图,并获得奇妙的阅读效果。
[1]韦恩·布斯.小说修辞学(中译本)[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175.
[2]安斯加·F.纽宁.重构不可靠叙述概念:认知方法与修辞方法的综合[A].詹姆斯·费伦等主编.当代叙事理论指南(中译本)[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81.
[3]尚必武.叙述谎言的修辞旨归:詹姆斯·费伦的“不可靠叙述”观论略[J].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08,(9).
[4][5][6][7](美)爱伦·坡.爱伦·坡短篇小说集[M].陈良廷等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239-2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