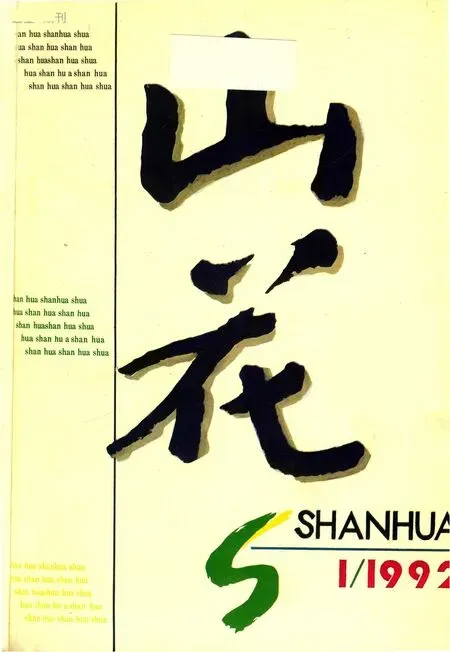神秘还是混沌——《印度之行》的后殖民解读
2015-01-26谭万敏
谭万敏 熊 华
《印度之行》作为福斯特最杰出的作品,自出版以来一直备受关注。自20世纪70年代撒义德的《东方学》(1978)问世以来,学者们纷纷从他者、种族主义、文化身份、东方主义等后殖民视角来解读这部著作,可谓蔚为大观。然而鲜有学者注意到福斯特对东方文化“神秘性”的描写其实等同于混沌。本文拟从“神秘”一词入手来追寻《印度之行》中神秘东方的真实面目,以此揭示出福斯特对东方文化的“神秘”书写其实折射出了他潜意识中的西方中心论思想。
“mystery”一词源自古希腊,在古希腊语中,mystery指的是某些不为人知的宗教仪式,这些宗教仪式只能被神职人员观看且必须发誓绝不泄露其本质。随着社会的发展,该词的意义发生了变化,渐渐演变成某种不为人知的、无法解释的事情。在后来的基督教中,“mystery”一词等同于圣事、圣餐等宗教仪式。究其词源,mystery和宗教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然而,“mystery”一词发展到今天,作为宗教事务的特殊能指早已有多个所指。许多神话评论家如Robert Graves、Francis Fergusson、Richard Chase以及最有影响力的Northrop Fry 都把许多文学作品流派、情节结构及表面上看起来很复杂的现实主义作品看作是神秘规则的再现。然而,西方在用“mystery”一词表述东方时却另有所指,神秘即是异己,是为理性所不能解释的习俗或现象。《印度之行》中对伊斯兰教和印度教神秘性的叙述正好体现了这种西方意识形态,也即伊斯兰教和印度教是非理性的、异己的宗教。
自然环境的神秘性
1.昌德拉普尔城的神秘
当穆尔夫人和阿黛拉小姐初来印度时,她们对小城神秘性的向往在文本中被多次提及,阿黛拉小姐多次宣称自己想看看真正的印度。也就是说,她想看看印度神秘之所在。然而,小说一开篇我们就目睹了一幅了无生气、肮脏、混乱的昌德拉普尔小城的鸟瞰图。“河岸和小城随便堆置的垃圾简直无法区分”,[1]“这儿的街道鄙陋,寺庙冷清”[1],“巷子里污物成堆,除了应邀而来的客人外,无人不望而却步”,[1]“在这儿所看到的一切都是那么的卑微而败落,那么单调而无生气”,[1]“在印度人居住区,看不到任何绘画艺术,也没有什么雕刻作品,树木都像是用泥做成的”,[1]“恒河发了大水,都希望把赘疣冲进土里,可大水一来,房子倒塌,人被淹死,尸体腐烂,无人料理……活像一种低等而又无法毁灭的生物体”。[1]俱乐部上空有秃鹰盘旋,昌德拉普尔常有豹子和蛇,阿齐兹家到处是苍蝇,至此,作者眼中的印度图景是无法为西方人所理解和接受的混乱。而当视角转向城内时,却完全是另一幅画面,“简直就是一座花园之城”,[1]一切都井然有序,“这地方与城区除了共有头顶上那个圆拱形的天空之外,再也没有什么共同之处”。[1]除了居住环境的显著差别之外,居住区的海拔高度也存在很大差异,印度人居住在恒河边低矮的洼地,“大水一来,房子倒塌”。[1]而欧亚混血人的住宅却位于火车站附近的高地上,就连那个“小小的英国行政官署便建筑在这第二个高地上”。[1]这样的地理位置显示了欧洲人和印度人之间看与被看的关系,也即俯视与仰视的不平等关系。撒义德在其《东方学》中指出,“东方就像在课堂上、法庭里、监狱中和带插图的教科书中那样被观看。”[2]“东方被观看,因为其几乎是冒犯性的行为的怪异性具有取之不尽的来源;而欧洲人则是看客,用其感受力居高临下地巡视着东方,东方成了怪异性活生生的戏剧舞台。”[2]福斯特在小说中对英国人和印度人居住区地理位置作这样的布局无论出于何种用意,无疑都体现了作者潜意识中的优越感和凝视者的身份特征。由此可见,神秘的自然环境实际却是一片混沌。
2.恒河的神秘
恒河是印度人心中最神圣的河流, 是印度人民的精神依托,同时也是印度文化的表征。[3]作为印度神话的发源地,众多的神话故事和传说构成了它独有的神圣内涵。从远处眺望的话,“月亮在恒河长长的河道上映了出来……河水把月亮的倒影放大,所以水中的月亮看上去比天上的月亮又大又亮,这美妙的景色使她俩心旷神怡。”[1]此处的月色增添了恒河的视觉美感和神秘色彩,孤寂、朦胧、变幻莫测。“这河多么可怕啊!但又何等的奇妙!”[1]穆尔夫人说。然而近距离观看的话,河岸和小城随便堆置的垃圾简直无法区分。“恒河发了大水,都希望把赘疣冲进泥土里,可大水一来,房子倒塌,人被淹死,尸体腐烂, 无人料理。”[1]福斯特展现的这幅图景立刻让读者联想到一条臭气熏天、肮脏的河流。这一叙述实际是对恒河进行去圣化处理,神秘的恒河在福斯特眼中不过是一条污浊混沌的普通河流而已,无法与神圣相联系。
月亮也增添了恒河的神秘色彩。文本对恒河美景的描述始终是以月光为背景的,而日光下的恒河却浑浊脏乱。和太阳相比, “月亮往往代表着负面的力量,也代表着无法预知的茫然和隐藏的危险。”[4]同时,月亮这一意象在西方是阴柔的、女性的象征。在希腊神话中,月亮之神是位美丽的女性,至此,神秘的恒河同样只可远观。
3.马拉巴山的神秘色彩
马拉巴山是福斯特浓墨重彩之笔。“从市政官署所在的高地来看马拉巴山,已经令人感到惊讶,眼下从火车上看到的马拉巴山简直是天上的神仙,”[1]阿德拉称赞道,“那山是多么奇妙啊!”“山上岩石的外层有一种奇怪的现象,用语言简直难以描述。”“说这岩石‘神秘’暗指鬼神,而一切鬼神都没这岩石古老。”[1]
当靠近马拉巴山时却是另一番景象,山洞的“样式单调,缺乏变化,里面没有石雕,甚至连蜜蜂的巢穴或是一只蝙蝠也没有”,[1]在这些空无一物的山洞里,最引人注意的就是回声:“回声又生回声,就像一条大蛇占据了这个山洞,这大蛇由许多小蛇组成,小蛇都在任意地翻滚。”[1]然而,“那回声以一种难以描述的方式在破坏她控制生活的能力”。[1]无论是穆尔夫人还是涉世未深的阿黛拉小姐, 回声都在很大程度上对她们产生了影响,进而导致了穆尔夫人的信仰危机及阿黛拉的幻觉。然而这神秘的、引起冲突的回声究竟是什么却无法被言说。“火车一离开马拉巴山,那令人烦恼的小世界就消失了,马拉巴山又恢复到从远处看到的那个样子, 还颇有些浪漫色彩。”[1]马拉巴山及其山洞的这些特征表明了印度的神秘只可远观,近看就只是一片空无与混乱。
人物性格的神秘性
在描写普通印度人时,作者使用了一些贬义的词语,而如阿齐兹、戈德贝尔、哈米杜拉等在菲尔丁眼中能与之平起平坐的印度中产阶级人士也被描述成了懒惰、不诚实、怀疑、奴颜婢膝以及不负责任的东方人。例如阿齐兹,受过教育、相貌英俊而且还是一名医生,然而他总在说着这样或那样的谎话。戈德贝尔无论是在菲尔丁的茶会上还是在阿齐兹被捕之后,对眼前所发生的一切总是视而不见, 要么拼命地吃,要么闪烁其词,缺乏西方人所具有的正直品格。吉勃指出:“东方哲学从来未曾欣赏过正义这一希腊哲学的基本观念。”[2]与他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阿黛拉小姐在意识到自己错了之后却能勇敢地站出来澄清事实,即使最后导致她众叛亲离、成为孤家寡人也在所不惜。菲尔丁也因维护正义而被赶出了俱乐部。
东方人易于怀疑的性格特征也为西方人所无法理解。怀疑的火焰轻易地就在阿齐兹和他的朋友之间产生,也正是由于阿齐兹怀疑的性格特征才导致了他与菲尔丁友谊的破灭。阿齐兹在他的印度朋友离开之后警告菲尔丁要小心印度人:“菲尔丁先生,你不得不处处小心,在这个该死的国家无论你说或做什么,总有一些嫉妒的家伙在盯着你。”[1]小说中福斯特借叙述者之口评论道:“东方人的怀疑是一种恶性肿瘤,是一种心理的疾病。”[1]他们以一种西方人所不能理解的方式既信任又不信任。文本中对东方人怀疑的性格特征叙述正好体现了作者的欧洲中心论思想,也即东方人是非理性的、野蛮的、不诚实的。Evelyn Baring 认为,“东方人或阿拉比人缺乏热情和动力, 大都沦为阿谀奉承、阴谋和狡诈的奴隶。且东方人对谎言有顽固的癖好,他们‘浑浑噩噩,满腹狐疑’,在任何方面都与盎格鲁·撒克逊民族的清晰、率直和高贵形成鲜明对比。”[2]福斯特在《印度之行》中塑造的这群鲜活的人物正好符合这些东方主义特征。
东方宗教的神秘性
卡尔·贝克认为,“尽管‘伊斯兰’继承了希腊的传统,它却既不能抓住也不能运用希腊的人文主义传统;而且,为了理解伊斯兰,人们首先需要,不是将其视为一种‘原创性’的宗教,而是将其视为东方人试图运用希腊哲学但缺乏我们在文艺复兴的欧洲所发现的那种动力的一种失败的尝试。”[2]伊斯兰教在文本中被描述成了一种排外的、善于嫉妒的狭隘宗教,坚信安拉之外无他神。阿齐兹对印度教的仪式感到厌恶而认为伊斯兰教是世上最完美的宗教;他认为印度教的鼓声节奏不合他的情趣,其他宗教的教堂或庙宇都无法唤起他的美感意识。马西农认为,“伊斯兰是源于以实玛利的宗教,从上帝许给以撒的希望之乡中被驱逐出去的那一民族的一神论信仰。”[2]而所谓神秘的印度教实际上却是难以理解和漠不关心、排外的宗教。印度教祭司戈德贝尔是个孤独、无依靠、无朋友、 对人们的疾苦几乎麻木不仁的人,只有一点抽象的泛爱精神。戈德贝尔在茶会上唱的那首宗教歌曲显得毫无意义。 而在戈德贝尔重复唱的那段对牧牛神的祈求中,教授断然拒绝了让牧牛神来到挤牛奶的少女身边,表现了其宗教淡漠、冷酷的一面。印度有82%的居民信奉印度教,就印度教而言,“它比伊斯兰教和基督教都更能理解和代表生活的严重混乱。”[5]茂城寺庙举行的为庆祝爱神黑天诞生的盛大庆典上,充满了音乐、吵闹、狂欢和神秘膜拜的声音,以及无法用言语所能描绘的混乱场景。而在庆典结束时,“那歌声延续的时间比较长久……宗教濒于失常……不能最令人满意的,平淡无奇的混乱。”由此可见,作为东方宗教代表的印度教庆典的神秘性实质上是一片混沌。
结 语
总之,在《印度之行》中,福斯特对伊斯兰教和印度教的叙述夹杂着许多神秘色彩,而这些神秘叙述却又总是体现着狭隘、混沌、非理性等特征。神秘的东方宗教在福斯特看来,其实就是肤浅和混乱的代名词。无论是故作清高的伊斯兰,还是晦涩难懂的婆罗门,都不过是缺乏美感和秩序感的异己宗教。这就暗含了作者对东方宗教的西方中心立场。一言以蔽之,神秘的东方宗教在福斯特的眼中实际等同于混乱。“神秘只是脏乱的一种动听的说法,不管是神秘还是脏乱,两种说法分不出优劣。”[1]
[1]E.M.福斯特.印度之行[M].杨自俭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3:1.
[2]撒义德,爱德华·W.东方学[M].王宇根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1.
[3]毛世昌.恒河——象征印度文化的圣河[J].科学·经济·社会,2010(4).
[4]满智慧.浅析中西方文学中月亮的意象[J].芒种,2012(9):30.
[5]刘彦欣.论《印度之行》中的三大宗教[J].飞天,2009(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