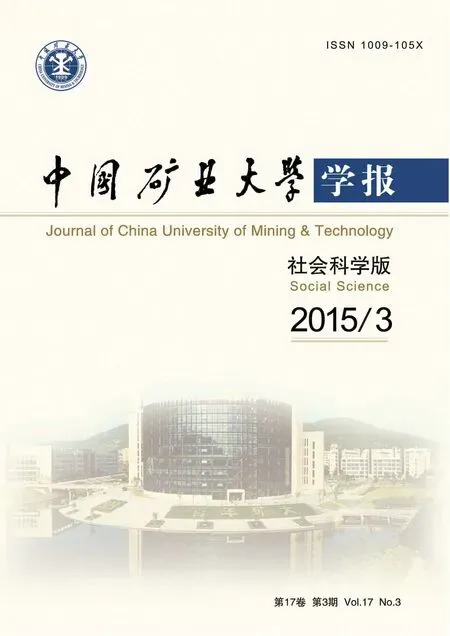南斯拉夫“实践派”的实践概念与批判的历史唯物主义观
2015-01-22许恒兵
许恒兵
(南京政治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 南京 210003)
南斯拉夫“实践派”的实践概念与批判的历史唯物主义观
许恒兵
(南京政治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 南京210003)
摘要:以极力彰显“实践”范畴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为前提,南斯拉夫“实践派”有力地批判了苏联历史唯物主义的实证主义、教条主义的错误倾向,并在重释历史唯物主义的过程中展现了其本应具有的批判性维度。但是,由于南斯拉夫“实践派”对实践概念的单向度理解,即仅仅强调实践范畴的“规范性”内涵,忽视实践概念的“物质性”内涵,以致在历史唯物主义重释上出现了重大的偏颇,即将历史唯物主义的“内在批判性”导向了一种为马克思所批判过的“外在批判性”。作为历史唯物主义出发点的实践范畴乃是“物质性”与“规范性”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只有准确把握实践范畴的双重内涵,才能真正彰显历史唯物主义科学批判性的意蕴。
关键词:南斯拉夫“实践派”;实践概念;批判的历史唯物主义观
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明确指出:“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做感性的人的活动,当做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1]499在这段标识“新唯物主义”与一切旧唯物主义之根本区别的经典论述中,马克思明确指出要从“实践”出发去阐释周围世界及其历史展开。既然如此,要完整准确地把握历史唯物主义的独特本质,就必须完整准确地理解实践的内涵。从这一视角出发可以发现,南斯拉夫“实践派”虽然在重新奠基实践——相对于苏联历史唯物主义——在理解历史唯物主义中的基础性地位上做出了重要贡献,但由于其对马克思实践概念的“单向度”理解,即仅仅强调实践范畴的“规范性”内涵,而忽视了实践范畴的“物质性”内涵,以致在历史唯物主义重释上出现了重大的偏颇。
一、 南斯拉夫“实践派”的实践观
与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其他学派和哲学家一致,南斯拉夫“实践派”是在反思和批判斯大林主义的过程中兴起的。南斯拉夫“实践派”的代表普遍认为,斯大林主义从根本上背离了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而这种背离的核心就在于其在根本上忽略了人及其实践本质在理论建构中的中心地位和作用,并由此导致将马克思主义塑造成为仅仅只是论证现实发展过程之客观规律性的纯粹科学,而全然不顾马克思主义中的人道主义关怀维度,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基于人道主义的诉求对现实的激进批判维度。对此,马尔科维奇指出:“除了一些关于人的伟大性、异化(仅指资本主义中存在的)、自由作为对必然性的认识,实践作为真理的检验标准等极其一般的辞句外,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家(即以斯大林为典型代表的苏联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引者注)并没有发展任何关于人性、实践、人的真正需求和基本能力、积极的自由异化和人类解放的概念——所有这些出自马克思的哲学著作的重要主题。”[2]257正是基于斯大林主义的根本缺陷,南斯拉夫“实践派”的代表普遍要求重新确立人在马克思主义中的核心地位。正如彼德洛维奇所说:“我国战后哲学发展的基本成就之一,就是发现了人,这个人,是被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斯大林主义版本中作为抽象物除掉了的,而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中,人却居于中心位置。”[2]242而由于人的本质就是实践,即“与以前的一切哲学截然不同,马克思认为人与动物的区别不仅在于一个特定的特性,而是在于他的整个的性质与结构。人既不是一个‘理性动物’,也不是‘制造工具的动物’,人是实践”[2]242-243,因而以人为中心,实质上也就是以实践为中心。也就是说,南斯拉夫“实践派”普遍确立了实践在重新理解历史唯物主义中的核心地位和作用。
对此,马尔科维奇在说明1961年人道主义与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在布莱德展开的一场决定性争论的结果时也明确指出:“主张马克思哲学的核心范畴是自由的人的创造性活动——实践——的观点占了优势。物质和精神、客体和主体的二元论被这些范畴是如何可能从实践概念中推演出来的观点取代了。”[3]10在他看来,“历史实践的范畴是马克思对人和历史的哲学解释的根本范畴”[3]219。与此同时,作为南斯拉夫“实践派”公开表露心声的杂志直接以《实践》为名则更为直接地说明了他们在重新理解历史唯物主义的过程中对“实践”的倚重。那么,南斯拉夫“实践派”到底如何理解实践呢?如果说实践在马克思实现历史观的革命性变革中起着关键作用,那么这个问题的先行解决对于理解南斯拉夫“实践派”的历史唯物主义观无疑具有前提性的作用。对于这个问题,马尔科维奇作了明确解答。他指出:“必须把实践(Praxis)同关于实践(Practice)的纯认识论范畴区分开来。实践(Practice)仅指主体变革客体的任何活动,这种活动是可以被异化的。而实践(Praxis)则是一个规范概念,它指的是一种人类特有的理想活动,这种活动就是目的本身并有其基本的价值过程,同时又是其他一切活动形式的批判标准。”[3]导论19
从上述这段话出发,并同时结合南斯拉夫“实践派”关于实践概念的其他论述,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概括其实践观的基本内涵。首先,实践是一种理想性、价值性活动,彰显的是人摆脱了一切限制之后的本真性存在,这种存在同时也是人的未来的可能性存在。对此,马尔科维奇强调指出:“实践是人的一种理想活动,是人实现其生命的最理想的潜在可能性的一种活动”[2]266,这种活动体现了人的根本性特质,“人在本质上是一种实践的存在,即一种能从事自由的创造活动并通过这种活动改造世界、实现其特殊的潜能、满足其他人的需要的存在。对人来说,实践是一种根本的可能性”[3]18。其次,与上述内涵密切相关,即实践作为一种“理想极限”,是思想设定的结果,并由此在性质上表现出“先验性”的特征。正如马尔科维奇所说:“人作为实践的存在这个概念,显然是一个设想性概念。一旦产生巨大社会差别的所有这些社会结构被移开,人便将日益强烈地以一个自由的、理性的、社会的、创造性的、普遍的存在的姿态而活动。”[2]270最后,从功能上来说,实践构成了任何一种现实批判的根本性规范或标准,即“这种人的规范概念是指人的最理想的历史可能性,它已成为所有社会批判的基本标准”[2]270。
而从理论渊源来看,南斯拉夫“实践派”对实践的理解无疑导源于青年马克思的实践观。此种内在关联首要地体现在南斯拉夫“实践派”普遍强调青年马克思的思想在马克思思想演进过程中的主导性地位和作用。对此,弗兰尼茨基将历史唯物主义的成熟时期定位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无疑对此种取向作了典型说明。在他看来,“这部手稿(指《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说明了马克思思想的全部丰富深刻的内容,以及后来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最终精辟地表述出来的那些理论前提。这同时也使我们在后面没用必要特别阐释《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而只是把它作为马克思基本哲学思想的重要文件和完整表述而加以引用。”[4]100而从实践的具体内涵以及由此形成的内在关联来看,南斯拉夫“实践派”的实践观无疑汲取了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基于人的本真性存在对实践的界定,即“一个种的整体特性、种的类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而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恰恰就是人的类特性”[5]57。而当马尔科维奇认为实践“有明确的审美性质,它是除其他法则外还‘服从美的法则’的一种活动”[2]269时,无疑源自于马克思关于“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5]58的论述。
二、 南斯拉夫“实践派”批判的历史唯物主义观
如何开端,便如何保持。南斯拉夫“实践派”对实践的基本理解决定了其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阐释方向,即其根本旨向在极力凸显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性维度。从理论所指来看,这种凸显无疑是为了批判斯大林主义将历史唯物主义视为对人类历史最一般规律的把握,并在此前提下将新的历史事实视为对前者的例证的理论取向。历史唯物主义由此蜕变为教条主义化的绝对真理体系,并由此丧失了其内在具有的批判性特质。正如彼德洛维奇所说:按照斯大林主义的教义,“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能够和必须发展的,但其发展不能、也不必引向对于马克思主义任何一个基本命题的否定,而只能证实、诠释和‘加深’这些命题”[2]230。这种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僵化理解从根本上支撑着斯大林认为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是一般的社会主义模式的实践信念。而从基本的理论诉求来看,南斯拉夫“实践派”则力求通过彰显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性维度来为本国的自治的社会主义道路提供坚实的理论支撑。
在具体阐述南斯拉夫“实践派”的实践观与其批判的历史唯物主义观之间的内在关联之前,我们有必要简单概述一下南斯拉夫“实践派”对历史唯物主义批判性的强调。需要指出的是,虽然南斯拉夫“实践派”在具体的理论阐述中并不总是采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名称,而是在很多时候运用了“马克思的理论”、“社会批判理论”、“实践哲学”等名称,但究其在总体上将理论视角主要指向对历史及其未来走向的考察上而言,它们在实质上所指的无疑就是“历史唯物主义”。而对于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性品质,南斯拉夫“实践派”的核心刊物《实践》杂志的发刊词明确指出:“我们这个杂志上的哲学,应该是革命的思想,应该是对现存一切的好不容情的批判,应该是对真正的人的世界的人道主义展望,应该是鼓舞革命行动的力量。”[2]327同样,马尔科维奇以“社会批判理论”概括南斯拉夫“实践派”的总体性理论取向,同样充分地说明了这个问题。他指出:“一旦人们清楚地认识到,革命哲学的作用不在于对现存的现实(无论是社会主义的,还是资本主义的)作理性的解释,哲学的根本任务在于发现现实世界的根本局限并进一步发现克服这些局限的历史可能性,那么,用具体的、在实践上具有一定倾向的社会批判超越原有的、抽象的批判理论也就成为必要的了。”[3]导论11
那么,南斯拉夫“实践派”是如何从其规范性的实践观中引发出批判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的呢?大致而言,此种内在关联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实践是历史唯物主义批判性特质生成的根本前提。从一般意义上来看,一种理论能够生发出批判性特质必须具备两个前提:一是发现所批判的对象的局限性;二是提供超越对象的根本路径。而南斯拉夫“实践派”将实践视为这两个条件形成的关键所在。就前者而言,南斯拉夫“实践派”认为,正是由于确立了“规范性”实践的一般性基础,历史唯物主义才能以此出发洞察到现实的根本局限性,具体来说就是人遭受异化的生存状况的残酷现实。也就是说,异化的发现是基于消除了异化状态后的实践的前提才有可能。对此,坎格尔加明确指出:“只有在有了废除异化的要求时,异化才表现出来”[3]54,而如果说“废除异化”体现的是未来的实践要求,那么“马克思思想之最本质、最深刻的意义”在于,“未来是历史过程和历史运动的出发点和根本点”,“历史是通过现在从未来向过去运动的,反之不然”[3]55。就后者而言,实践同时提供了消除异化的根本路径,作为一种人的未来的理想性存在方式,它同时内含着超越和变革现实的要求。这一点充分地表现在“实践派”极力凸显实践的“革命”形式的意义和作用上。而彼德洛维奇则直接将“革命”本体论化,视为历史走向自我超越的内在根基。正如他所说:“革命是创造性最发达的形式,是自由最真实的形式,是一个开辟了多种可能性的领域,是一个全新的王国。它是存在的真正‘本质’,是其本质的存在。”[3]143
其次,实践的“极限”理想性决定了历史唯物主义批判性的彻底性。所谓极限理想性,就是实践作为人的本真性存在,其最终实现要以消除人所受的一切限制为前提。对此,彼德洛维奇指出:“只要人的历史(至少在最根本意义上)还由它的某一领域决定,那么我们就还始终处于史前史阶段,处在作为人的自由的和创造性的活动的真正人类历史的门口。在马克思看来,人作为人是自由的创造性的实践存在物,而真正的人的历史只有在人开始自由地创造与实现自身与自己的属人世界时才能开始。”[6]280正是这种至高至善的要求以及由此所激发出来的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精神信念,使得南斯拉夫“实践派”极力强调历史唯物主义批判性的彻底性。既然任何外在的限制妨碍了人的本真性存在的实现,那么,历史唯物主义批判的利箭就必定要射向社会的每一个领域,正是在此前提下,南斯拉夫“实践派”批判性地考察了经济、政治、理论、技术、职业、语言乃至心理等方面对人的生存所造成的危害或限制。同时,既然人的实践本质的实现在于消除一切外在限制,从而实践的历史本身就是批判的历史,所以从实践的视野去衡量和审视人类历史发展的一切阶段时,其批判的触角必定是广泛的,即涉及到一切社会,其中包括社会主义社会。对此,弗兰尼茨基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性不仅表现在对资产阶级社会的态度上,而且也表现在对待一切社会,包括对待社会主义社会的态度上。”[6]375
上述两个方面充分说明了南斯拉夫“实践派”基于对实践范畴的独特理解彰显历史唯物主义批判性的根本理论旨向。但是,如果说马克思由于对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深入而从《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开始开启了一个全新的实践视域,即提出了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主导性实践观有着本质不同的新的实践观,并由此实现了历史观的革命性变革,那么,南斯拉夫“实践派”通过彰显《手稿》中的实践概念来重新阐释历史唯物主义,势必会出现重大的理论偏颇。这种偏颇尤其体现在南斯拉夫“实践派”所凸显的历史唯物主义批判性在总体上体现为一种漂浮于现实历史发展过程之上的“外在批判性”,以致激进的批判话语隐藏着深层次的无批判的实证主义倾向。
三、 “外在批判性”的历史唯物主义观
正如上文所述,南斯拉夫“实践派”的实践概念主要汲取了马克思在《手稿》中所阐述的实践概念的理论营养,因此,为了有效说明其在基于实践范畴重塑历史唯物主义批判性的过程中所造成的严重理论偏颇,我们有必要简单审视一下马克思《手稿》中所阐明的主导性实践范畴的基本内涵,并进一步审视马克思在《提纲》和《形态》中对实践概念的重塑,并基于新的实践概念实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大理论变革。毫无疑问,此种厘清对于充分说明南斯拉夫“实践派”的批判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的根本缺陷具有前提性意义。
无疑,马克思在《手稿》中所阐述的实践范畴具有丰富的内涵,但从主导性的内涵来看,它作为人的“类本质”无疑是马克思基于人的本真性存在方式——相对于资产阶级社会人的普遍异化的生存状态——所预想的理想性概念。实践概念的理想性特征尤其体现在马克思对共产主义社会作为人的实践本质的真正占有的激进化的描述上,即“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5]81。实践本质的实现因为消除了一切矛盾和冲突,并且因为在迄今为止的历史过程中从未出现过,所以便具有了乌托邦式的理想性色彩。为了更加具体地说明这一点,我们还可以采用马克思本人所强调的从后思索的方法。马克思在《形态》中指出:“生命的生产,无论是通过劳动而生产自己的生命,还是通过生育而生产他人的生命,就立即表现为双重关系:一方面是自然关系,另一方面是社会关系。”[1]532这段话所概括的说明“实践”范畴的双重关系无疑也体现在上述马克思关于未来的激进描述之中。但是,实践所内涵的“双重关系”却在两个地方表现出了本质性的差异。对于后者,我们将在后文中论述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性特质时具体说明。但是,对于前者,实践所内涵的双重关系即“人与自然”以及“人与人”的关系以及两者之间的相互关系无疑体现为一种“超历史”的特质,并且这种特质首要的决定于马克思对一种“本真性社会”或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设定。对此,马克思指出:“社会性质是整个运动的普遍性质;正像社会本身生产作为人的人一样,社会也是由人生产的。……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对人来说才是人与人联系的纽带,才是他为别人的存在和别人为他的存在,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才是人自己的人的存在的基础,才是人的现实生活的要素。只有在社会中,人的自然的存在对他来说才是自己的人的存在,并且自然界对他来说才成为人。”[5]82-83与以后的观点相比,这段话至少包含着两个原则性的理论缺陷:第一,人与自然的关系的具体的历史的内涵及其对人与人的关系的历史性制约作用没有被凸显出来;第二,因为这个现实前提的缺失,马克思对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理解实际上是一种“超历史”的理解,并成为马克思阐释实践的根本前提。而如果说人与人的关系构成了实践概念的“规范性”内涵,其功能侧重于调整人与人之间的社会性关系,即在其作用之下,“各种使用价值以及相应的技能和需求依据这种机制在社会中被分配给不同的由个人组成的群体,赋予这些个人不同的社会属性,把他们转变为特定历史类型的‘社会角色’,相互之间维系确定的社会关系”[7]77-78,那么,马克思实际上在《手稿》中着重强调的就是实践的“规范性”内涵,并因为其对人与自然之具体的历史的关系的脱离,这种“规范性”便必然性地表现出乌托邦式的理想色彩。这样我们就不难理解,致力于从青年马克思思想中寻找理论支撑的南斯拉夫“实践派”为何将实践视为一种“规范性”实践了。
但是,随着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深入,马克思最终在《提纲》和《形态》中实现了对实践概念的重塑,这种重塑集中体现在马克思从抽象的实践概念走向了具体的历史的实践概念。诚如施密特所言:“不是所谓物质这抽象体,而是社会实践的具体性才是唯物主义理论的真正对象和出发点。”[8]31而对于具体的社会性实践活动的出发点,马克思明确指出:“以一定的方式进行生产活动的一定的个人,发生一定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经验的观察在任何情况下都应当根据经验来揭示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同生产的联系,而不应当带有任何神秘和思辨的色彩。”[1]523-524其中的两个“一定的”无疑表明了实践的历史性、具体性内涵。进一步来看,这种具体性内涵又体现在实践内涵的双重关系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上。对此,马克思在指出实践在一般意义上包含着双重关系后紧接着指出:“一定的生产方式或一定的工业阶段(亦即人与自然关系的历史性发展水平——引者注)始终是与一定的共同活动方式或一定的社会阶段(亦即人与人的关系历史性特质——引者注)联系着的。”[1]532
这种实践概念的重塑使得马克思实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变革,即核心无疑在于马克思将《手稿》中的基于理想性的实践活动对资本主义社会现实所展开的一种外在式批判,转向了基于对社会现实进行内在分析和把握基础上的内在式批判。具体来说,首先,马克思在《手稿》中基于理想性实践的前提,无法深入到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内部就工人何以陷入异化的生存状态做出科学的说明,相反,马克思在《形态》以及以后的《资本论》及其手稿中,基于对资本主义社会雇佣劳动(实践的一种历史性的形式)的分析,找到了工人陷入异化的现实根源;其次,马克思在《手稿》中基于理想性实践对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激进批判,隐含着否认资本主义阶段的出现本身对人的解放的重大意义,从而不能将未来社会的解放扎实地奠定在对资本主义社会提供的历史性条件分析的基础上,而是借助于一种黑格尔式的纯粹逻辑上的“复归”来述说人的解放。而前者恰恰构成了马克思此后展开资本批判和探寻人的解放路径的现实出发点;最后,与上述两点相关,马克思基于实践概念的重塑,从一种游离于历史之外的纯粹价值性批判转向了深入历史发展过程内部的科学分析,并将价值批判有力地建基于科学批判的基础之上。
基于上述梳理,并由此反观南斯拉夫“实践派”的批判的历史唯物主义观可以发现,由于执着于青年马克思的“规范性”实践概念,南斯拉夫“实践派”基于对苏联马克思主义的反叛而重新确立的批判的历史唯物主义观必定具有青年马克思激进批判理论的根本缺陷,并由此从整体上背离了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观所开启的全新理论视域。首先,也是必然性的,南斯拉夫“实践派”的批判的历史唯物主义没有致力于对人的异化的生存现实的根源做出科学阐发,即没有说明人如何基于特定的实践活动方式而走向了人与人之间的分裂和异化。他们虽然也在不断地揭露异化对人的戕害,但归根结底是比照于人的本真性的实践存在来进行述说的。例如,坎格尔加将合理性的实践存在视为历史发展进程中的本体论基础,即“历史的领域,真正的新生事物和社会主义的任务在于,哲学作为真正的人类世界之可能的合理性(人性)实现——这种合理性是未来在现在就起作用的世界的合理性,是一种通过历史的发展将自身显现为积极的、有意义的、被证明了的世界和历史的起源与基础的合理性,即这种先于所予和直接真实的必然性的可能性、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仍然是真实的”[3]50,其所提供的无疑是一种判定人的异化生存的理想性标准,即凡是与这种实践合理性相悖的存在都归结为异化的存在,正如他所说,“如果历史变化的这种本质的、唯一人道的可能性发生在人自我异化的前提下,以一种‘人与人分离’(马克思语)的形式,作为一种异己的、外在的、超验的和敌对的力量进入历史,那它就不是人自身的历史”[3]51-52。而当马尔科维奇指出,“没有一种一般的哲学眼光(亦即理想性的实践视角——引者注),人就肯定看不到整个‘史前史’的矛盾和限制,就看不到摆脱整个异化劳动时代的途径”[2]260,则无疑直截了当地将“实践”视为洞悉人的异化生存的根本前提,在他看来,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和《资本论》中对资本主义社会所作的科学剖析,是建立在其人本主义哲学观基础之上的,即在它们之中,马克思“用具体的经验知识补充哲学,把先验的人本学观点融合到一种具体的、切合实际的理论中去”[2]260。在此种理解下,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中具有原则性意义的科学维度便被整体性地替换为纯粹的价值批判维度,并由此成为游离于现实历史过程之外的纯粹理论。对此,马尔科维奇直言不讳地指出:“马克思的理论是对历史的可能性所作的批判研究的结果。它是一种模型,是一种理想化的结构的符号表现——而不是一种经验的描述。”[2]273
其次,南斯拉夫“实践派”无法提供实现人的解放的有效路径。由于撇开了历史唯物主义内涵对历史现实进行科学分析的维度,即如马克思所说的,“在思辨终止的地方,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实证科学开始的地方”[1]526,南斯拉夫“实践派”最终只能提供一种旨在实现人的解放的抽象的人道主义理论。当坎格尔加将人的实践本质的“复归”视为人的解放的最终实现,即认为“人铲除异化的过程,即人向其自身、向作为自由与可能的存在恢复的过程”时,无疑借用了青年马克思的逻辑复归的思想,但是,诚如日本新马克思主义者广松涉所言:也许“变化”本身可以套用“异化和复归的图式”,但“不论是称之为异化、复归也好,还是称之为正、反、合也好,如果仅仅只是这样的话,(a)→(b)→(c)①其中,从(a)到(b)的变化实指从“非异化状态”到“异化状态”的变化。的变化,为什么,又是怎样地在事实上是必然的,以及在当为上是必然的,实际上没有得到说明”[9]55。既然如此,它就只能是一种抽象的解放理论。同样,当马尔科维奇以“彻底的人道化”来述说人的解放时,同样带有抽象性的根本缺陷,虽然马尔科维奇认为为了实现彻底的人道化,必须直击造成人的异化的根源,但由于他没有对人的异化发生的根源作出科学说明,所以他将异化的消除最终归结为一种先验的可能性,或一种“愿望的可能性”。南斯拉夫“实践派”的抽象的解放理论还集中体现在其所倡导的自治社会主义道路本身带有浓烈的理想主义色彩。而自治的核心就是充分民主的实现,正如弗兰尼茨基所言:“具有充分的民主传统和发达的工人阶级的发达国家面临着一项紧迫的任务,那就是要考虑实现这样一种社会主义,这种社会主义将使民主自由(以及政治自由)得到进一步的发展,新的社会主义自治结构得以建立。”[6]374固然,马克思也将社会自治视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状态的实现,但是,这种状态的实现最终要建立在物质生产充分发展的基础之上,正如马克思所言:“这需要有一定的社会物质基础或一系列物质生存条件,而这些条件本身又是长期的、痛苦的发展史的自然产物。”[10]但是,南斯拉夫“实践派”将自治的现实前提悄悄隐去,而在一个物质生产较为落后的地区倡导自治社会主义的发展路径,从而陷入了自治“早产论”的谬误当中。
总之,南斯拉夫“实践派”诉诸于理想性的实践活动来重释历史唯物主义,以致造成了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改写”。在改写的过程中,虽然其代表者彰显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性维度,但在其貌似强大的理性批判精神背后,恰恰深层次地隐藏着无批判的实证主义倾向。实际上,这种借助于抽象的实践概念对现实展开批判的做法,早已被马克思批判过。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在批判赫斯时就曾指出:他以为,“只要把费尔巴哈和实践联系起来,把他的学说运用到社会生活中去,就可以对现存社会进行全面的批判了”[11]。既然如此,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在总体上“决不是今日之东欧从中编造出来的那种积极的‘世界观’”[8]32。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2]《哲学译丛》编辑部编译.南斯拉夫哲学论文集[M].北京:三联书店,1979.
[3]马尔科维奇等.实践[M].哈尔滨: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0.
[4]弗兰尼茨基.马克思主义史: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5]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年.
[6]衣俊卿等主编.当代学者视野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东欧和苏联学者卷:下卷[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7]马尔库什.语言与生产——范式批判[M].哈尔滨: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1.
[8]施密特.马克思的自然概念[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
[9]广松涉.物象化论的构图[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
[1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97.
[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580.
湖北省教育科学“十一五”规划课题(项目编号:2010B381)
Practice Concept of Yugoslavia's "Practice School"
and Its Critical View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XU Heng-bing
(Institute of Marxism, PLA Nanjing Institute of Politics, Nanjing 210003, China)
Abstract:Preconditioned by highlighting the important position and role of "practice" category, Yugoslavia's "Practice School" criticized the tendency of positivism and dogmatism typical of the historical materialism in Soviet Union, and showed its critical dimensions in its reinterpreting historical materialism. However, because of their one-dimensional understanding of the concept of practice and their emphasizing the "normative" contents of the practice category, Yugoslavia's "Practice School" ignored the "materiality" contents of the concept of practice, thus causing great bias in interpreting historical materialism. This made the "internal criticalness"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change into "external criticalness" which was criticized by Marx. The practice category as the starting point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is the unity of "materiality" and "normalization" on a concrete and historical basis. Only by accurately grasping the double connotations of the category of practice can we really highlight the scientific and critical implications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Key Words:Yugoslavia's "Practice School"; concept of practice; critical view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社会生态研究”(项目编号:10YJA710040);
收稿日期:2015 - 01 - 15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105X(2015)03-0014-06
作者简介:许恒兵(1979-),哲学博士,南京政治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