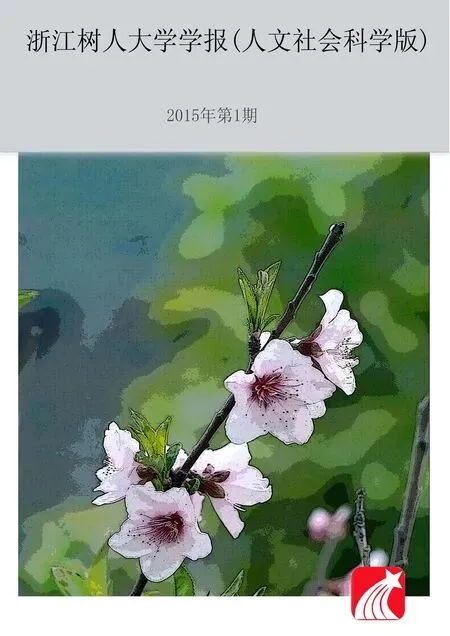政治、时代与观念:“十七年”童话的文本规训与主题模式
2015-01-21罗文军
何 霞 罗文军
(西华师范大学,四川 南充 637000)
政治、时代与观念:“十七年”童话的文本规训与主题模式
何 霞 罗文军
(西华师范大学,四川 南充 637000)
“十七年”时期童话的任务是对年轻一代进行共产主义教育,由此形成教育本位的童话观。文章梳理了这一时期的儿童文艺政策,概括了童话理论,归纳了童话的主题模式,发现存在“政治-童话理论-童话创作”这一封闭式结构,导致了这一时期的童话主题存在模式化的现象。1950年代的童话寓教于乐,将教育性和趣味性结合得很好,而1960年代的童话流于说教,政治意味浓烈。通过探讨主题与政治话语的关系,希望能对“十七年”童话进行一次深入性、整体性的研究,展现这一时期童话的独特风貌,挖掘“十七年”时期文学书写的内在复杂性。
“十七年”童话;政治话语;儿童观;模式化
近年来,“十七年”文学成为热门,尤其是由海外学者实践,逐渐在现当代文学研究引起广泛注意的“再解读”,把“十七年”成人文学研究推向更具体深入的层面。但是相对成人文学研究的日臻成熟,“十七年”儿童文学的考察梳理则明显不够,尤其是童话。既往的童话研究显得过于粗犷,或是只看到童话的主题模式化这样一个文学事实,而忽略其背后深层次的原因,或是重视空间意义上的主题探索而轻视时间跨度上的研究,没有从史的角度全面考察。还有一批童话创作研究,着重探讨其艺术手法,归纳艺术价值,但是他们选取的大多是1980年第二次全国少年儿童文艺创作评奖评出的17篇优秀童话。1980年代虽还多少保留着“十七年”时期的审美取向,但毕竟时过境迁,其在多大程度上反映“十七年”童话的风貌,这是值得深入研究的。研究者急于发现“十七年”童话的闪光点以及对当下童话的创作意义而自动忽略了许多带着强烈“十七年”印记的童话,这样无形中提高了“十七年”童话的艺术高度,为研究者得出结论提供了方便,然而这样的研究毕竟没有回到当时当地,过于简化了历史,在一定程度上还带有作者的主观臆测。
这一时期的儿童小说、散文、儿童剧、诗歌大多充斥着“左”的思想,成人文学的痕迹在很大程度上被体现于儿童文学中。需要说明的是,散文、儿童剧、诗歌创作量少,成就不高,这里不予讨论。笔者以1999年出版的《紫薇童子——人民文学五十年精品文丛·儿童文学卷[上][下]》①刘白羽、程树榛:《紫薇童子——人民文学五十年精品文丛·儿童文学卷[上][下]》,新世纪出版社1999年版。收录的7篇“十七年”时期的儿童小说为例:《海滨的孩子》(1954)、《小豆儿》(1955)、《妈妈的故事》(1955)、《活命草》(1956)、《过年》(1961)、《阿舒》(1961)、《红芽儿》(1965),除了最开始的《海滨的孩子》,描绘了渔家孩子的勇敢精神,可以说几乎看不见时代的印记,与后来的儿童小说和时代感鲜明的成人小说相比已经没有多大区别。《小豆儿》表彰了小豆儿在肃反斗争中大义灭亲,检举犯有反革命罪行的叔叔和父亲;《妈妈的故事》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残酷杀害母亲及三个孩子的罪行;《活命草》揭露美国侵略者发动的侵朝战争,破坏家园,使孩子流离失所;《过年》控诉了资本家残酷剥削和压迫童工致死的恶行;《阿舒》描绘了一个“不懂人事不知愁”的女青年渐渐意识到参加生产的重要性,转变成一个劳动好手;《红芽儿》表扬了儿童团为生产队争做好事。这些儿童小说的主人公虽然是孩子,但他们的政治觉悟之高,丝毫不逊于成人。但是,在这部集子里收录的6篇童话:《一只想飞的猫》(1955)、《野葡萄》(1956)、《亲爱的妈妈》(1957)、《宝葫芦的秘密》(1957)、《“小黑点儿”的故事》(1962)、《小铁脑壳遇险记》(1962),或讴歌了伟大的母爱,或赞扬了奋发向上的时代精神,或褒奖了无私奉献的高贵品质,或委婉批评了自大、懒惰、骄傲等不良行为,从中我们看不到太多意识形态的痕迹,而是塑造儿童美好心灵的永恒主题。
这些例子不免有池鱼之感,反之却不无窥豹之用。在这样一部1999年由官方编辑出版的优秀儿童文学选中,把小说和童话两相对比,可以看出童话因为是写给低幼儿童看的,其在主题“深度”上有限制,所以时代印记较弱,从而体现了童话这种文体的顽强与“幸存”的一面,其在寻求自身合法性的同时,自动地排斥了政治意识形态对它的规训,虽然这种排斥是有限的。因此,研究“十七年”童话更能认识政治规训与文化观念之间的纠葛,探讨特殊时期童话创作的复杂性和关联性问题。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完成培养革命接班人的任务,为了“与资产阶级争夺下一代的斗争”,党会如何继续组织领导儿童文学的发展,会如何规训儿童文学作家?而作家们又会如何迎合党的规训,形成新的童话观,在这一过程中又会和主流话语有怎样的龃龉,会在文本中体现怎样别有意味的审美性?本文立足“十七年”童话,从儿童观角度出发,爬梳史料,还原历史,探讨这一时期的童话主题与政治话语的关系。希望经由这一视角,对“十七年”童话进行一次深入性、整体性的研究,展现这一时期童话的独特风貌,挖掘“十七年”时期文学书写的内在复杂性。
一、“文代会”“评奖”以及《大量创作、出版、发行少年儿童读物》
1949年7月召开的第一次文代会,有专业的儿童文学作家出席。会后,中国作家协会及各地分会纷纷成立“儿童文学组”。1949年10月13日,党中央委托“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建立“中国少年儿童队”(即后来的“中国少年先锋队”),团章明确指出,“儿童文学”是党用以“培养教育少年一代的有力工具”。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第一次对儿童文学的明确定义,其着重强调了儿童文学的教育性和工具性。团中央积极响应文代会精神,迅速创办了三个直属单位,即“两社一报”(1952年在上海成立的少年儿童出版社、1953年在北京成立的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1951年在北京创办的《中国少年报》)。共青团以此为依托和基地,实施了一系列直接影响1950年代儿童文学建设的举措。
1953年第二次文代会召开,会上提出要努力学习苏联文学艺术事业的先进经验。会后出版了一大批介绍苏联儿童文学的译著,包括《苏联儿童的历史文学读物》(1953)、《论儿童读物中的俄罗斯民间童话》(1953)、《儿童文学、儿童影片、儿童音乐(苏联大百科全书选译)》(1954)、《论苏联儿童文学的教育意义》(1954)等。可以说,在理论体系还没有完全建构起来、儿童文学创作还没有积累到足以出版选集的1950年代初,翻译苏联的儿童文学理论和作品,填补了我国儿童文学出版行业的空白。作家们主动地向苏联学习,一方面是响应文代会的号召,另一方面,是1950年代初党进行了反对黄色书刊、肃清反动资产阶级儿童读物的斗争。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成长起来的儿童文学作家们所崇尚的“儿童本位论”(周作人提出)在新诞生的社会主义国家显得不合时宜,作家们对新生的政权充满信心,想要在“我们这个伟大的时代”(金近语)有所作为,因此都以一种虚心的态度真心实意地向苏联这个有着丰富经验的社会主义国家学习。
严文井就曾经在1953年反省自己二三十年代写作童话的经历,他认为当时自己没有考虑读者对象和效果的问题,童话里弥漫着个人的某些感伤情绪。建国后他虽然对此作了修改,可终究还是不满意。他如是说:
延安文艺座谈会开过后,给我启开了一扇大门:原来世界上有很多比一个人的悲痛或欢乐更值得注意的事情。我对自己有了批判,对自己的写作发生了怀疑。一大堆问题摆在面前。文艺工作是多么严肃的一件工作啊!该怎么干呢?我必须重新迈步,首先我必须真正成为工人阶级当中的一员。这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时间过得很快。十五年来,我学着做了好几样工作,断断续续也写了一点童话,其中也有作新尝试的企图,但是我总感觉距离自己预定的目标还差得远。我多么想抛掉那个过去而专门来写现在和未来啊!我只盼望多得到一些写作时间。亲爱的读者们,如果今后我能不断为你们写作,一直写,一直写下去,这本身就是一件最愉快的事情。我想这一次不会只是一个幻想了。*严文井:《严文井文集 第3卷 童话寓言卷》,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2000年版,第337页。
从严文井的深情剖白中,可以看出作家们此时的主要矛盾是与自己内心残存观念斗争,努力改造自己,生怕自己被时代抛弃。虽然表面上他们对自己充满了自信,但从字里行间,还是可以读到一丝焦虑、困惑和担心。延安文艺座谈会为作家们指明了一条道路,提供了一个范本,但是艺术创作有太多的不可知因素,愈是明确的条条框框愈是让人生畏,害怕无法达到预设的标准。
1954年6月举行“1949——1954全国儿童文学艺术创作的评奖”,在评奖公告里发起人中国人民保卫儿童全国委员会充分肯定了儿童文艺的发展:“全国已有十一种儿童报刊,三个专为儿童演出的剧团”、“新的儿童文艺创作受到了广大儿童的欢迎,对培养儿童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护公共财物的品质,培养儿童勇敢坚强不怕困难的进取心和守纪律、讲礼貌、团结互助的精神,都起了不少作用”,但也明确指出“目前儿童文艺的创作还不够旺盛,与全国儿童的日益增长的实际需要相差还很远;另外也有一些作品在不同程度上存在着公式化和概念化的倾向,甚至也有个别作品包含不正确、不健康的思想内容,对儿童起了不良的影响。”
这次评奖表彰了22篇儿童文学作品,包括3篇童话:秦兆阳的《小燕子万里飞行记》、严文井的《蚯蚓和蜜蜂的故事》和金近的《小鸭子学游水》,并分别获得一二三等奖。童话作为“儿童文学标志性体裁”,*王瑞祥:《儿童文学创作论》,浙江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51页。“3篇”不管从数量上还是从比例上都显得过少。但纵观这3篇童话,无一例外都是对孩子们进行思想品德教育,分别用燕子飞往南方过冬、蜜蜂采蜜、小鸭子学游水象征勤学苦练、谦虚勤劳、勤能补拙,可以说都表现了一个“勤”的主题。建国初期的童话虽然数量不多,但情节优美,语言生动,充满了感情,表现了一种风和日丽的和平景象和作家们宽松愉悦的心境。这些童话至今仍为人们所称道,成为新时期出版童话集的必选篇目。*例如,金近、葛翠琳:《1949—1979童话寓言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中国优秀童话选(1922—1979)》,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1983年版。
对于这次建国后儿童文学的全面阅兵,作家们一直津津乐道。冰心在为《1956年儿童文学选》作序的时候这样评价道:“少年儿童文学作品全国评奖大会为新中国儿童文学的创作开辟了一大片的土地……举目四望,我们看见了到处油然的新绿!”*冰心:《儿童文学选1956·序言》,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7页。贺宜也在1959年回忆道:“1953年12月举办了少年儿童文学作品的全国评奖,对于鼓励创作起了良好的作用。”*贺宜:《散论儿童文学》,百花文艺出版社1960年版,第96页。注:1953年12月指评奖开始时间,而非颁奖时间。足见其反响之大,影响之广。如果说建国初,尚且以召开文代会、评选优秀作品等举措鼓励儿童文学乃至童话的发展,儿童文学开始呈现出蒸蒸日上的景象。那么随着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全面展开,相关部门则开始采用行政命令促进儿童文学的产量了。1955年《中国少年报》(团直属)以团中央的名义向党中央写了一个《关于儿童读物奇缺的报告》,经毛泽东亲自批准,责成国务院贯彻执行。同年9月《人民日报》发表社评《大量创作、出版、发行少年儿童读物》。*“人民日报”社论:《大量创作、出版、发行少年儿童读物》,《人民日报》1955年9月16日。当天,郭沫若、宋庆龄等也纷纷在《人民日报》《中国少年报》上撰文,请求作家们“为少年儿童写作”*郭沫若:《请为少年儿童写作》,《人民日报》1955年9月16日。、“源源不断地供给孩子们精神食粮”*宋庆龄:《源源不断地供给孩子们精神食粮》,《中国青年报》1955年9月16日。。次日,国务院第二办公室在毛泽东的指示下召集文化部、作协、教育部、团中央等单位举行会议,汇报了关于改进少年儿童读物工作的进展情况,并要求各部门尽快做好这一项工作。两个月后,中国作家协会下发了《关于发展少年儿童文学的指示》,其中指明要求近200位作家在一年内写出一些儿童文学作品或者评论。从上到下一时形成党、组织、儿童拼命向作家索要作品的紧急状况,作家们只好纷纷撰文“领旨”。叶圣陶发表《响应号召》,冰心发表《一人一篇》。同年这些党报社论、作协指示、作家文章又都收入进《大量创作、出版、发行少年儿童读物》*中国青年出版社编辑:《大量创作、出版、发行少年儿童读物》,中国青年出版社1955年版。这本书里,更大范围、更强力度地起到宣传鼓动作用。除了儿童文学作家,许多著名成人作家如郭沫若、魏金枝、靳以、周而复、周波、马烽、康濯、臧克家、田间、李季、阮竞章、袁水拍、贺敬之、袁静、刘知侠等*贺宜:《散论儿童文学》,百花文艺出版社1960年版,第116页。也都制定规划为少年儿童创作,许多新生力量涌进了创作队伍。
可以说,经过“文代会”、“评奖”以及《大量创作、出版、发行少年儿童读物》,童话乃至儿童文学至少已经从数量上开始摆脱建国初期的贫乏状态,儿童文学正式进入它的“黄金时代”*蒋风:《中国当代儿童文学史》,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1991年版,第11页。。
二、“黄金时代”
1950年代儿童文学的繁荣是在1954年全国第一次儿童文艺评奖后才真正出现的,在此之前,新中国儿童文学为了实现自身的飞跃经过几年时间的准备和酝酿。从1956年“中国少年报”和“少年文艺”联合征文的四万个应征者的人数看来,*冰心:《儿童文学选1956·序言》,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7页。在儿童文学创作上努力尝试的人真是不少。
这一时期翻译家们以更大的热情继续翻译苏联儿童文学作品和文艺理论,出版了《苏联国内战争时期的儿童文学》(1955)、《苏联童话的讨论》(1956)、《高尔基论儿童文学》(1956)、《苏联儿童文学》(1956)、《苏联儿童文学教程》(1957)、《盖达尔的生平和创作》(1958)等。而作家们也积极介绍苏联儿童文学情况和自己学习的经验。以陈伯吹为典型,他曾经发表《苏联儿童文学中的党性和人民性》*陈伯吹:《苏联儿童文学中的党性和人民性》,《人民日报》1957年11月18日。(1957)、《苏联儿童文学作品中的阶级教育》*陈伯吹:《苏联儿童文学作品中的阶级教育》,《北京文艺》,1957年11月号。(1957)、《苏联儿童文学作品中的国际主义教育》*陈伯吹:《苏联儿童文学作品中的国际主义教育》,《儿童文学研究》(内部发行)1958年第4期。(1958)、《谈苏联儿童文学作品的思想性和艺术性》*陈伯吹:《谈苏联儿童文学作品的思想性和艺术性》,《红岩》,1958年6月号。(1958)等,甚至还出了一本专著《在学习苏联儿童文学的道路上》*陈伯吹:《在学习苏联儿童文学的道路上》,少年儿童出版社1958年版。(1958)。从这些文章和专著里,可以看出作家们除了学习苏联儿童作家的创作经验,更是学习他们忠诚地为培养与教育幼年儿童而不倦工作的精神、他们对孩子们高度负责的崇高感情,最重要的是学习他们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来武装自己的头脑,对社会主义祖国的无限忠诚和对革命事业的坚定信心,在儿童文学创作实践中坚持正确的观点立场和社会主义斗争——重要的政治任务和中心运动联系一起,提高作品的战斗性和思想性”。*贺宜:《向杰出的少年儿童文学作家盖达尔学习》,《人民日报》1955年10月4日。
以贺宜、金近、陈伯吹、蒋风等为代表的一批儿童理论家在苏联儿童文学理论的基础上成长起来,他们分别在1950年代后期出版了《散论儿童文学》(1960)、《童话创作及其他》(1957)、《儿童文学简论》(1957)、《中国儿童文学讲话》(1959),为新中国儿童文学理论的建设奠定了基础。
贺宜曾在1952年严厉批判过“鸟言兽语”等脱离现实、脱离政治的童话,他说:“我们有些儿童读物的作者,把活生生的人,活生生的事丢在一边,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却整天坐在书房里望着天花板挖空心思地想出一套牵强附会的‘鸟言兽语’,自以为这样又简单又生动,结果却是使作品显得格外空洞玄虚,甚至弄得不伦不类,叫小读者猜了半天,还不懂作者到底在告诉他什么。”*贺宜:《给新中国的儿童更多更好的读物》,《人民日报》1952年6月2日。从表象上看,贺宜似在批判童话作品多以动物口吻书写,即所谓的“鸟言兽语”,但通观全文,其实他主要批判的是童话的主题,即忽视了身边火热的社会主义建设中“活生生的人,活生生的事”,或者作者在表现这些时过于隐喻,以至于小读者猜了半天,还不懂作者到底在告诉他什么。所以后来人们把这种现象概括成“古人动物满天飞,可怜寂寞工农兵”,是更加生动形象且一针见血的。第一次全国儿童文学艺术创作评奖中获奖的三篇童话,就是贺宜批判的典型,即使用“鸟言兽语”,主题没有反映社会主义建设。
第二次文代会和第一次评奖后,也就是从1954年起,每年从短篇作品中编选一部内容丰富的《儿童文学选》,第一年由中国作家协会编选,人民出版社出版。这项工作几乎贯穿整个1950年代,所选的童话代表着一年来的收获,反映了当时童话的实际水平。作家们受到贺宜等人的批评后开始把现实和政治引入童话中。但是在《儿童文学选1954.1—1955.12》的序言里严文井谈及童话:“今天童话创作的情况确实不能令人满意。关于童话的问题有很多,首先是新的童话产量少;而在那很少的童话里我们又看到了那么多的狼,总是同样代表着帝国主义,那么多的小白兔和小白鸽,总是同样代表着和平人民,几乎看不见什么个性。”*严文井:《儿童文学选(1954—1955)·序言》,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版,第11页。作为一个擅长童话的专业儿童文学作家,严文井认为把现实和政治引入童话固然是正确的,但是当今的童话模式化太严重,甚而至于已经形成了“狼”和“小白兔”这样的固定刻板形象,没有个性。对于贺宜等批评的“鸟言兽语”,严文井回应道:“我们仍然也要‘小狗小猫说话’的故事。少年儿童喜欢动物和植物,他们除了想了解关于动物和植物的科学知识外,还希望从动物和植物的生活里找到诗;既是关于动物和植物的诗,同时也是,而且主要的是关于人的诗。”*严文井:《儿童文学选(1954—1955)·序言》,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版,第11页。他还给童话指明即几条努力的道路,即科学幻想童话、寓言、民间传说和神话。
一年后,《儿童文学选1956》由冰心作序:“童话的题材,比去年宽阔了些。我们相信跟着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工作队伍而深入到祖国各个角落的作者们,一定还会发掘出许多关于我国各族人民生活斗争的童话材料,来丰富这个领域的内容。”*冰心:《儿童文学选1956·序言》,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4页。两年后选编和出版《儿童文学选》的工作移交至作家出版社继续进行。在《儿童文学选1957》的序言里作家出版社编辑部总结当年的儿童文学作品时说:“1957年比一九五六年有了更大的收获,具体表现在下列几个方面:首先是儿童文学创作反映现实斗争的题材多起来了。童话特别发达……”序言作者用了一个“特别”也就是说童话相对其他文体进步最快,这里的“进步”主要是“反映现实斗争的题材”方面。童话因为历来被认为无法直接描写社会生活,此次尝试自然受到文学批评家的热情赞赏。尔后,更是用诗一般的语言再次提及童话创作的丰收:“值得特别一提的是童话创作的异常活跃。从春天到冬天,都不断有新的童话涌现出来。”*作家出版社编辑部:《儿童文学选1957》,作家出版社1958年版,第3页。但是这种“异常活跃”并没有持续多久。
1958年是社会主义建设全面发展的一年,文学创作也得到了空前的丰收。按照1955年以来的规例,儿童文学作品选集的编选和出版工作由作家出版社承担。但是1958年为了体现文学的大跃进,除了以往的“儿童文学选”,另外还编选出版了“短篇小说选”、“诗选”、“散文特写选”、“曲艺选”,参加编选的文艺机关团体也增加了“诗刊”编辑部、“新观察”编辑部、“曲艺”月刊编辑部,以上均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儿童文学选”由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编选并出版。短短4年时间,“儿童文学选”的编选出版工作由中国作家协会、人民出版社(1955,1956)转交作家出版社(1957)后又转至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其中的人世浮沉是值得深思的。1958年的“儿童文学选”序言由贺宜书写。作为一个一直以来关注童话创作的儿童文学理论家,贺宜肯定了童话开始选用某些现实生活与斗争的题材:“反映现实斗争的创作比过去多了,甚至在历来被认为无法直接描写社会生活的童话中,也开始有人尝试选用某些现实生活与斗争的题材”,但是他进一步指出:“1958年的儿童文学创作还有一个特殊现象,那就是最显著地具有儿童文学特征的童话创作有一蹶不振的模样。”*贺宜:《1958年儿童文学选·序言》,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1958年版,第12页。接着贺宜分析了童话一蹶不振的可能原因:“大家知道,前些时候在少年儿童读物出版工作中曾批判了脱离政治,脱离儿童,厚古薄今,厚动物薄人的倾向……但是由于某些编辑工作者和作者思想方法上的片面性,把批判‘古人动物满天飞’,理解为对一切‘古人、动物’的否定,因而在编辑思想和创作思想上产生了只要现代题材而摒弃古代题材,欢迎人物故事而厌恶童话的倾向,这就形成了1958年以迄目前童话歉收的状态。”显然,贺宜认为童话歉收的原因是某些编辑工作者和作者把“鸟言兽语”的批评矫枉过正了。此后,反映童话创作兴衰的一年一度的《儿童文学选》编选工作停止了三年,童话创作真的是“一蹶不振”了。
儿童文学理论家根据政治的风向标提出相应的文学理论,这些理论指导了儿童文学创作,表面上这三者配合得天衣无缝,但实际情况是,根据政治风向标提出文学理论,无非是“政治第一性、艺术第二性”、“儿童文学要反映现实、反映政治斗争”,于是根据文学理论要求创作出既有政治教育性又符合艺术审美性的童话就显得捉襟见肘了。“由于文学创作行为是一种单纯而自由的行为,因而对社会提出的要求应当有所超脱。换言之,如果说既作为人,又作为艺术家的脑海里呈现出自己的读者,并与他们同呼吸共命运的话,那他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创作方向受这些读者摆布就是危险的。”*[法]罗贝尔·埃斯皮卡:《文学社会学》,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2页。在文学理论家批评“鸟言兽语”的大环境中,作家们彻底地抛弃了“鸟言兽语”,作家的脑海里时时刻刻呈现出文学理论家,到最后竟出现“过犹不及”的现象——童话“一蹶不振”了。由此可以看出,1950年代的童话创作实际上形成了一个封闭式结构:政治主导文学理论,文学理论影响童话创作。文学理论作为中介,起到了关联政治和童话的作用。而这一封闭式结构随着政治斗争的愈演愈烈,必然会导致童话创作的异化,这种异化主要通过主题的模式化乃至1960年代的僵化表现出来。
由中国作家协会发出的《关于发展少年儿童文学的指示》提出,儿童文学的任务是“对年轻一代进行共产主义教育”*中国作家协会:《中国作家协会关于发展少年儿童文学的指示》,《文艺报》,1955年第22号,第27页。。共产主义教育涵义广泛,包括革命传统教育、阶级斗争教育、集体主义教育、爱国主义教育、思想品德教育、忆苦思甜教育、认真学习科学文化知识……但由于儿童文学接受主体的独特性,共产主义教育进入儿童文学,必然有限,它要回避一些,也有些是无法回避的,而这些无法回避的,它又通过转化和变异,最终在童话主题上形成固定的套路,使得整个童话创作呈现模式化的趋势。
一批带着“左倾”色彩的童话是“十七年”(当然也包括文革时期)区别于当今童话的最鲜明的特色。这些作品往往用狐狸、老鼠、蛇、“媒鱼”等代表坏人、敌人,而小猫、鲤鱼、喜鹊等善良的小动物能及时识别他们的诡计,与之进行英勇的斗争,最后取得胜利。这些作品反映不同时期的政治斗争,旨在引导儿童去认识复杂的社会。但是这类主题的童话很容易陷入严文井批评的“那么多的狼,总是同样代表着帝国主义,那末多的小白兔和小白鸽,总是同样代表着和平人民,几乎看不见什么个性”*严文井:《儿童文学选(1954—1955)·序言》,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版,第11页。之弊端。
上述童话流传下来的并不多,很多都已经湮没在历史的长河中。今人看到的“十七年”时期的“优秀童话”大多数属于“思想品德教育”主题,这类童话长期为人们所称道。《小猫钓鱼》(1950)、《小马过河》(1955)、《小蝌蚪找妈妈》(1960)等童话在当今小学课本上,依然很受孩子们的欢迎。这类童话善用对比,从题目一看便知:《蚯蚓和蜜蜂的故事》(1954)、《小红花和松树》(1956)、《月季花和雪人》(1957)、《野鸭子和家鸭子》(1957)、《两只小泥蜂》(1957)等,“蜜蜂”“松树”“月季”“野鸭子”“小泥蜂”昂扬的精神风貌大多是克服困难、勤学苦练、谦虚善良、朴素低调、勇往直前、永不休息……而“蚯蚓”“小红花”“雪人”“家鸭子”则是反面典型,他们好吃懒做、挑肥拣瘦、不思进取、骄傲自大,童话通过前者的成功和后者的失败来揭示主题,完成对孩子们的思想品德教育。
也有一部分以“坏孩子”为主角的童话,当然“坏孩子”并非十恶不赦的阶级敌人,只是有一些缺点而已。这类童话针对少年儿童中普遍存在的问题,例如“不劳而获”“不动脑筋”“贪玩”“没有集体意识”“骄傲”“懒惰”“依赖性强”等等,对孩子们进行讽喻和指导。如:《小雁归队》(1956)、《小铁脑壳遇险记》(1962),分别讲了骄傲的小雁和蚂蚁,自认为能力过人,脱离群体单独行动,结果小雁迷路差点冻死、小蚂蚁遇到红蚁的围攻落入险境。童话故事最后安排小雁和小蚂蚁回到温暖的集体怀抱,并且深深地意识到自己的莽撞无知,改正了错误。这类童话是“十七年”童话的精品,其中严文井的《“下次开船”港》(1957)和张天翼的《宝葫芦的秘密》(1957)当时并称为童话园地中两朵奇葩,作品发表后曾被译成英、俄、捷、日、朝等多种文字,受欢迎程度可见一斑。
“十七年”童话里有一类特立独行的童话作品,他们改编自民间传说。如《野葡萄》(1956)、《神笔马良》(1956)、《龙王公主》(1957)、《渔童》(1958)、《九色鹿》(1961)、《猪八戒学本领》(1962)、《金花路》(1963)等。民间文学曾是培育儿童文学的主要土壤,从儿童文学分离出来以后,它仍是孕育儿童文学的重要来源。“十七年”时期,儿童文学家、民间文学工作者从解放了的人民大众的角度来看待历史,他们把“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一思想作为选择、改编过去时代民间文学的主要依据和尺度。因此,那些侮辱劳动人民的故事、笑话被摒弃;许多有损劳动人民形象的情节被重新修正,大量出版的是反映劳动人民优秀品质的作品,格调上也消除了这些作品在其产生年代不可避免的某些沉重和忧郁,显得清新、明朗。
“从某种意义上说,一部儿童文学发展史,就是成年人儿童观的演变史。有什么样的儿童观就有什么样的儿童命运、地位、权利、也就有什么样的儿童文学艺术精神与美学品格”。*王泉根:《现代中国儿童文学主潮》,重庆出版社2004年版,第3页。“十七年”儿童文学,突出体现了社会主义中国不同于以往时代的“儿童观”和“儿童文学观”——“教育本位”儿童观,这种儿童观强调儿童文学对儿童的教育作用,儿童作为接受群体在阅读过程中被设定为谦恭受教的接受者,成人隐藏在文本背后扮演着“精神导师”的角色,引导儿童尽快告别童真年代,快快长大,担当起新中国赋予的未来重任。
三、在曲折中前进
从1949年至1959年,经过十年的蓬勃发展,儿童文学有了一批优秀的原创作品,并且在建国前的基础上完善了自己的文学理论。“儿童文学已经有了一支不算太小的队伍,在各地作协分会有四五十个从事儿童文学创作的会员”,*贺宜:《散论儿童文学》,百花文艺出版社1960年版,第116页。除了专业的作家之外,各地还纷纷成立儿童文学业余创作小组。以1962年6月下旬在上海成立的“儿童文学业务创作小组”为例,“参加小组的近六十位组员,多数是中、小学校教师,也有来自各条战线的儿童文学爱好者。”*儿童文学研究编辑室:《儿童文学研究丛刊》,少年儿童出版社1962年版,第51页。十年间我国儿童文学的蓬勃发展,从每本作品的印刷数量上也可以看出。“在解放前,一般儿童文学作品能够印行一、两千册就不错了,至于发行到上万册的那将被认为奇迹。然而现在我们的书平均可印行四、五万册,至于印数达数十万至数百万册的也不是少见的。”*贺宜:《散论儿童文学》,百花文艺出版社1960年版,第116页。
由于社会政治生活的变化,1950年代与1960年代之交成为童话创作的转折点。反右运动后,1959年《儿童文学研究》应时创刊,作家和批评家们在上面发表理论文章,在第二辑里蒋风、里方和贺宜突然发表文章,批判陈伯吹的“童心论”、“儿童本位论”。这场批判来势汹汹,像一场腥风血雨腰斩了刚刚出现的“黄金时代”。
1961年,《上海文学》第8期发表《六〇年少年儿童文学漫谈》,作者是时任中国作协主席和国家文化部长的茅盾,他对全国29种杂志和两种儿童期刊上的几百篇作品尤其是童话进行分析,得出的结论是大体相似。他说:“……绝大部分可以用下列的五句话来概括:政治挂了帅,艺术脱了班;故事公式化,人物概念化,文字干巴巴。”总之,“童话有点抬不起头来了”。他还在文章中对刚刚批判过的“童心论”和“儿童本位论”作了巧妙的辩解。他其实是以一人之力,为这些被批判的理论“平反”。
陈伯吹“欣喜”地说:“果然,事情已经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童话曾经在暂时的被‘廉价的’评论者们的任意贬价下,又一次从‘山穷水尽疑无路’的境地欣逢‘柳暗花明又一村’了,此去康庄大道,前程无量。”*儿童文学研究编辑室:《儿童文学研究丛刊》,少年儿童出版社1962年版,第2页。他提到:“在第三次全国文代会(1960年)以后,由于党的文艺方针的贯彻,有关领导方面的重视和大会繁荣创作的精神所鼓舞,作为文学体裁样式之一的童话,也‘闻鸡起舞’了。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出现了为数不算太少的童话作品,这当然是可喜的收获,尽管还不是一次丰收,离特大丰收还远着哩,但是‘月晕而风,础润而雨’,好的预兆来了!”
确实,少年儿童文学理论斗争最热烈的1960年过后,儿童文学包括童话确实出现了一个小井喷。一年一度的《儿童文学选》,其编选出版工作被停了三年,1963年7月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编选了1958到1961年期间的作品,由冰心作序,并且计划每三年编选一次。这个计划因为1963年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主编的《儿童文学》杂志创刊而没有继续执行下去。然而,这之后并没有出现陈伯吹预言的“大丰收”。
这里不得不提到1960年代提倡的“新童话”,有学者认为“新童话”“对中国童话发展而言意义重大。它不仅是对新时代童话走向的一次梳理和思考,其中触及到了现代童话创作的一些重要命题,而且通过童话作家的成功实践,基本完成了中国童话创作的现代转型。”*钱淑英:《“十七年”童话:在政治与传统之间的艺术新变》,《文艺争鸣》2013年第11期,第42-47页。“新童话”是1960年那次“少年儿童文学理论斗争最热烈的一年”*茅盾:《六〇年少年儿童文学漫谈》,《上海文学》1961年第8期,第4-15页。的附属品,是参与论争的作家们(无论是批判者还是被批判者)找不到出路而寄希望于未来的一种权宜之计。陈伯吹曾热烈参与“新童话”的讨论,然而在1962年,他对此进行了反省:“在这一年多来的创作童话中,似乎运用‘拟人’手法写的作品不多。事实的确也是如此。是不是作家还怀有‘古人动物满天飞……’的顾虑呢,还是受了所谓创作‘新童话’的影响?还是这二者兼而有之?其实,用‘拟人法’写童话,一样可以写出好作品来,《金色的蜜蜂》是个例子,问题是不是在于作者的思想、生活和技巧上,可以研究。”*儿童文学研究编辑室:《儿童文学研究丛刊》,少年儿童出版社1962年版,第15页。
“作者的思想、生活和技巧”的改革正是“新童话”所提倡的,然而作家用了一个“可以研究”,这只是委婉的说法,即“不正确”,至少是“不全面”的。在经过那次疾风骤雨般的批判,陈伯吹作为一名党外人士说话越发小心翼翼,再也不会像之前那样高谈阔论,总是一副权威的、不可商议的语气了,1950年代热情洋溢主动学习苏联儿童文学的陈伯吹变得被动了。
政策上的鼓励确实能激发童话的产量,但是过多的童话理论只会是加在童话创作上的紧箍咒,束缚童话的自由发展。“政治—童话理论—童话创作”这一封闭模式由于政治愈演愈烈而慢慢走向失调乃至瓦解。如果说1950年代围绕童话《慧眼》的争论,还是从纯文学的角度出发,那么1960年代初针对陈伯吹的“童心论”的批判则带有某种政治目的的团体打击报复了。此后,作家们发声变得小心翼翼了。
包蕾在1962年出版的《儿童文学研究丛刊》上谈到其代表作猪八戒系列童话:“交代一下写作经过,原无不可”,“但主要倒是想把写作中接触到的一些问题,提出来向大家请教!”就利用民间传说改编童话要多吸收一些中国传统的东西,他为自己澄清:“当然,我不是说,要向传统的东西中学点玩意,只能去仿古作文,为现成的人物作新编(要是真能这样,岂不笑话);也不是说,可以不向外国儿童文学作品中吸收养料。我是说,在我,当时是想再多写几篇这一类的故事,在写作中间,尝试去学点传统的东西罢了。另外,我也并不是说可以‘无批判’的学习,这些都是误会不得的。”*儿童文学研究编辑室:《儿童文学研究丛刊》,少年儿童出版社1962年版,第79页。作家一开始就强调了种种“误会不得”,在获得某种政治稳妥后才敢放心地阐述。包蕾说,《猪八戒回家》在《少年文艺》上发表后引起朋友们的一番议论,原因是这中间有些和《西游记》里的设想很有出入(如天堂之类)。这样是否允许,各有不同的意见。然而“我对这些问题,也不敢贸然肯定,而同志们能关心这篇小东西,却使我很感兴奋。”其实童话创作原本就是作家自己的艺术想象,即使是改编自《西游记》,和原著有些出入也是正常的,但是文艺问题由于涉及政策、规定、斗争、立场而变得异常敏感,作家们只能保持“述而不作”的态度,即表现出对于“多写文艺批评”号召的“原无不可”的配合,实际上对于很多问题只是点到为止,“也不敢贸然肯定”。
当然作家们一旦掌握了话语权,站在正确的立场上,态度则变得强硬得多。例如,贺宜批判肖平(亦作萧平):“那么肖平同志所作的结论是完全错误的”,“其真正的目的,只是要以‘艺术第一’来代替‘政治第一’,实质上就是要取消社会主义的童话而代以资产阶级的童话”*贺宜:《散论儿童文学》,百花文艺出版社1960年版,第170页。。文艺争鸣贵在切磋,各人有各人的看法,没有标准答案,而贺宜一口咬定肖平的结论“完全错误”,并且由此认为肖平是要把童话拉出社会主义儿童文学的轨道。用一种非此即彼的大是大非的态度来进行童话批评和童话理论建设,套用贺宜自己的一句话,早晚“意味着童话的衰老和走向死亡!”
至此,成人文学理论开始渗透到儿童文学理论中,高沙在《给儿童丰富多彩的精神食粮》里写到“主题明朗首先要求人物形象鲜明,是好是坏,属善属恶……作品中的英雄人物应该是完整无缺的人物,英雄身上的任何缺点,都是孩子们难以理解的。”*儿童文学研究编辑室:《儿童文学研究丛刊》,少年儿童出版社1962年版,第118页。这些言论不禁令人想起“十七年”时期小说创作中“三突出”原则。连一向重视“童心”的冰心也在1963出版的《儿童文学选》序言里如是说:
我们首先要帮助他们懂得什么是阶级,什么是剥削,谁是朋友,谁是敌人,新旧社会的区别在哪里,作为新中国的儿童应当有什么样的雄心大志等等,我们要教育他们学习无产阶级的优秀品质:团结友爱,勇敢诚实,关心集体,热爱劳动,爱护公物,遵守纪律,艰苦朴素等等。我们也要引导儿童关心国际大事和资本主义国家的儿童生活,用当前的国际阶级斗争事实,来激发他们的爱国主义、国际主义精神和热爱阶级朋友、反对我们的共同敌人——帝国主义者的决心。*冰心:《儿童文学选1959—1961·序言》,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第3页。
如果说“教育他们学习无产阶级的优秀品质”是1950年代童话的应有之义,那么“引导儿童关心国际大事和资本主义国家的儿童生活,用当前的国际阶级斗争事实”则是1960年代童话在上一时期主题模式的进一步僵化。
贺宜曾经“反对那种观点,以为把事情直截了当地告诉孩子是孩子们所不能接受的,因而一切必须用象征影射、明譬暗喻的方式。因为这是低估了我们现代儿童的理解能力和觉悟水平。”*贺宜:《散论儿童文学》,百花文艺出版社1960年版,第2页。于是到了1960年代,1950年代童话里常出现的“坏人”“敌人”开始明确化,变成过去的皇帝、军阀、洋鬼子、财主、资本家。《雪夜奇遇》(1963)讲了发生在“一个财主们当家做主的国家里”,善良的雪娃娃按照老爷爷的意愿给穷人们下了一场棉花和白面的大雪,雪娃娃满以为这样就能解决穷人们的饥饿寒冷问题。没想到财主们和议会勾结,规定所有的棉花和面粉归国家和大资本家所有,个人取用必须缴纳昂贵的赋税。警察们以此为据对穷人们进行搜查,把穷人们本来可怜的一点白面和棉花也拿走了。雪娃娃好心办坏事。最后,穷人们忍无可忍终于起来爆发起义,“一颗大红星,在队伍的前面闪耀着”。童话的主题是由雪娃娃领悟:“你们也决不能指望我的帮助解除你们的不幸。你们只有一条路,像我在那闪耀着红星的国家看到的那样,把欺压你们的财主们都打倒,做你们国家的主人,你们才能够得到真正的幸福!”*贺宜:《太阳鸟和秃鹰》,四川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97页。
童话中经常出现“红星”,红星象征着党、社会主义、红军、解放军……在孩子们心中“红星”是个既明确又模糊的概念,是一个值得崇拜的东西。1960年代的童话中还经常出现“财主”“军火大王、面粉大王、棉花大王”“资本家、阔太太、娇小姐、洋人”,这类反面形象,他们无恶不作、压榨穷人、贪得无厌。童话主题自然是“红星”战胜这类反面形象,穷人们过上幸福的生活。通过这类革命传统教育,阶级斗争教育,培养儿童对穷人的怜悯同情,对资本家大财主的痛恨之情,和对“红星”的敬仰依赖之情。“主题明确”是当时一些文章褒扬某些儿童文学时常用的一句话。所谓“明确”,就是要求所有的作品都围绕着阶级斗争、反修防修这一主题而展开,甚至童话也不例外。
1960年代童话中不再出现有缺点的儿童形象,取而代之的是对儿童优秀品质的无限讴歌,《小鲤鱼跳龙门》(1960)、《“小黑点儿”的故事》(1962)、《一群小金鱼儿》(1963)分别是用蜜蜂采蜜、溪流入海、鲤鱼跳龙门、金鱼长大等来象征着少先队员长大后要为人民服务,从小就要好好学习,练好本领。童话中还经常直接出现少先队员或小社员的形象,他们做好事、参加集体劳动,这类童话接近儿童小说,逐渐失去想象力,失去童话的本质,即幻想性。《山顶上的萝卜》(1959)讲小龙和小虎种出一个大萝卜,后来他们把萝卜送到生产队,生产队又把萝卜送到北京,送给毛主席,从中可以看到大跃进的浮夸风。也许人们可以把这种夸张理解成幻想,但是过多地树立高大的劳动模范形象,一味地给孩子灌输英雄意识,而不是像1950年代童话那样正反对比,让小读者从主人公身上看到自身的不足。童话中成长的过程被忽略,成长的阵痛被高大的典型遮盖住了,这显然不利于孩子的成长。过于把修水坝、种萝卜、为集体做贡献等高强度劳动强加给孩子,也不符合孩子的天性,更何况童话是针对低幼儿童,即学龄前儿童的。这种童话作品,使主题意向过于浅层化,缺少意蕴和内涵。
“政治,完全压倒了文学……历史真会开玩笑,当政治式写作以为自己走上金光大道时,实际上,恰恰走上自己终结的末路。”*唐小兵:《再解读:大众文艺与意识形态(增订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47页。这段文字虽然指的是成人文学,童话相对成人文学而言有其特殊性,但说到底童话还是文学,过多的包袱压在作家的头上最终也只能导致作家顾此失彼,艺术性下降乃至停产。1950年代在一系列政策的鼓励下,“政治—童话理论—童话创作”这一封闭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对童话创作起到积极的影响,出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黄金时代”;但1960年代文化大革命的影响,政治愈演愈烈,过多不属于儿童的东西渗入童话,使趣味性流失,而教育意味又显得过于浓烈,最终导致童话创作陷入困境。
(责任编辑 孟莉英)
Politics, Times and Ideas: The Text Discipline and SubjectPattern of Fairytales in “Seventeen Years”
HE Xia & LUO Wenjun
(ChinaWestNormalUniversity,Nanchong,Sichuan, 637000,China)
The mission of fairytales in “seventeen years” is to educate the young about communism, and then form the education-based view on children. This paper sets out policies of literature and art in “seventeen years”, summarizes fairy tale theory and conclude subject pattern of fairytales. Finding that there is an enclosed structure called “politics-theory-creation” which resulting in phenomenon of subject pattern.
Fairytales in “seventeen years”; Politics; View on children; Subject pattern
2014-08-03
何霞,女,江苏常州人,文学硕士,在读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10.3969/j.issn.1671-2714.2015.01.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