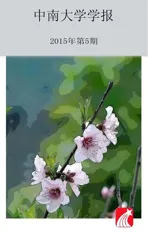汤用彤佛学研究的文化特质
2015-01-21胡永辉
胡永辉
(南京大学哲学系宗教学系,江苏南京,210093)
汤用彤佛学研究的文化特质
胡永辉
(南京大学哲学系宗教学系,江苏南京,210093)
汤用彤将“汉以后中国佛学的发展”看作不同文化冲突融合的已有案例来研究,因此,他的文化主张与其佛学研究有着内在精神上的暗合。汤用彤通过自己广搜精求的佛学研究,表达了对当时文化研究失于浅隘的不满。他在研究中,一方面表现出对佛教史上转折性人物、佛教发展的地域性差异、佛学研究方法论等方面的关注;另一方面也对佛学与中国本土固有思想文化互动问题给予较多讨论,同时也注重在动态的三教冲突与融合中考察中国佛教的发展轨迹,这些都体现出汤先生的佛学研究具有浓郁的文化特质。这一特质根源于他追问“中国文化向何处走”的问题意识。
汤用彤;佛教史;佛学研究;文化特质;问题意识
随着西学东渐影响的逐步深化,晚清以来的中国思想界对“中国文化走向”问题日益关注。具体表现在对“中国文化向何处走?”“外来文化如何融入本土文化?”等问题的追问。这些问题的实质是“中、西”之间、“传统、现代”之间的二元论争。[1]面对当时思想界的纷争局面,作为20世纪最有成就的佛学研究者之一,汤用彤对上述问题有着怎样的回应?
汤先生曾指出:“‘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现在虽不能预测将来,但是过去我们中国也和外来文化思想接触过,其结果是怎么样呢?这也可以供我们参考。”[2](278)可见汤先生是把佛教当作外来文化融入本土文化的已有案例来加以研究,他对文化问题的关注与其佛学研究的关系密切。因此,本文以汤用彤的佛学研究成果为主要研究对象,透过他的文化主张,考察其佛学研究的文化特质。
一、反对文化研究的浅与隘:佛学研究的精与广
汤用彤对于当时的文化研究表达了强烈的不满,指出文化研究流于“浅、隘”,并用自己的佛学研究回应了文化研究应该持有何种态度的问题。
(一) 反对文化研究流于“浅、隘”
汤先生曾直言不讳地批评当时流行的文化主张说:
维新者以西人为祖师,守旧者藉外族为护符,不知文化之研究乃真理之讨论,殽新旧然,意气相逼,对于欧美则同作木偶之崇拜,视政客之媚外恐有过之无不及也。时学之弊,曰浅,曰隘。浅隘则是非颠倒,真理埋没;浅则论不探源;隘则敷陈多误。[2](275)
汤用彤认为当时新旧文化主张者,都有失于“浅”和“隘”。他指出对文化问题的讨论不应脱离“探求真理”的本质。如果“意气相逼”则必使“是非颠倒,真理埋没”。他认为,失于“浅”的文化研究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失于“隘”的文化研究目光陈旧多有错误。
他之所以批评当时文化研究“浅”与“隘”,是对研究者未能“精考事实,平情立言”[2](276);对中外文化之材料“未广搜精求”[2](276)的不满。对此,他曾评论说:
时学浅隘,故求同则牵强附会之事多;明异则入主出奴之风盛。世界宗教哲学各有真理,各有特质,不能强为撮合。……夫取中外学说互为比附, 原为世界学者之通病。然学说各有特点,注意多异,每有同一学理,因立说轻重主旨不侔,而其意义即迥殊,不可强同之也。……至若评论文化之优劣,新学家以国学事事可攻,须扫除一切,抹杀一切;旧学家则以为欧美文运将终,科学破产,实为“可怜”。 皆本诸成见,非能精考事实,平情立言也。[2](275−276)
除了指责当时文化研究多有牵强附会之事,非能精考事实,平情立言之外,汤先生还指出:
时学浅隘,其故在对于学问犹未深造,即中外文化之材料实未广搜精求。旧学毁弃,固无论矣。即现在时髦之西方文化,均仅取一偏,失其大体。……夫文化为全种全国人民精神上之所结合,研究者应统计全局,不宜偏置。在言者固以一己主张而有去取,在听者依一面之辞而不免盲从,此所以今日之受学者多流于固陋也。[2](277)
汤先生认为当时文化研究未能对材料广搜精求,观点也易于以偏概全。他对这种现象甚为不满。他认为文化是全国人民精神之结合,研究者应统计全局,不宜有所偏置,以一己之主张而有所取舍必会误导众人,使受学者流于偏执狭隘。
总的来看,汤先生对当时的文化研究评价是“浅、隘”,原因是研究者不仅不能精考事实,平情立言;而且对材料未广搜精求,观点往往以偏概全。
(二) 佛学研究的“精”与“广”
基于上述对当时文化研究“浅”与“隘”流弊的批评,汤用彤主张:“凡治史者,就事推证,应有分际,不可作一往论断,以快心目。”[3](19)这在他具体的佛学研究过程中体现的尤为明显。
汤用彤佛学研究的精深,素为学界所推崇。他研究某一问题时,必会尽力穷尽所有相关资料文献,研究过程又会客观严谨地看待资料,结论往往是建立在大量文献的具体辨析之上。比如他对《四十二章经》的研究,他所提出的《四十二章经》汉晋间有两译、非汉人伪作,是现有资料基础上最广为接受的观点。
《四十二章经》因梁《高僧传》、隋《开皇三宝记》、梁《祐录》等文献中记载不一致,表明梁代时对于该经译者、译出地已经有争议。汤先生基于现有文献的详细梳理,至少使用了文献74种,对该经存在争议的地方给予了厘清。具体来看他的研究过程。
第一,据巴利佛经中不乏类似《孝经》的文体,反驳了梁启超据《四十二章经》文体类似《孝经》,认为该经为中国撰本的观点,维护了隋费长房所言该经系“外国经抄”的观点。其间,列举《法句经》《道行品》作为旁证。
第二,据东晋郗超《奉法要》、三国《法句经序》已引用《四十二章经》,汉末牟子《理惑论》似曾引用该经,判断在汉晋间固有该经。
第三,据《后汉书》中襄楷上书汉桓帝中“不三宿桑下”“革囊盛血”等句,与经中表述类似,判定后汉时,该经已经存在。
第四,僧祐《出三藏记集》为最早着录《四十二章经》的目录,祐录称“旧录云,《孝明皇帝四十二章》,安法师所撰录阙此经。”汤用彤通过对比指出《祐录》中所指“旧录”为晋成帝时支愍度所作,且旧录在“安录”之前。因此,道安时,《四十二章经》已经存在。对于“安录”阙此经的原因,汤先生据“值残出残,遇全出全”等句,推知安公治学严谨,非亲眼所见不着录。
综合以上意见,汤先生最终的结论是“东汉时,本经之已出世,盖无可疑”[3](24)。对于梁启超判《四十二章经》为伪书,汤先生也给予反驳。梁先生的理由主要有两点:其一,该经的名称译名多为新译,不像汉代译佛为“浮屠”,译沙门为“桑门”。其二,该经文辞优美不像汉代作品。汤先生据《祐录》称天竺字为“胡文”,元明刻经改为“梵文”,汉译佛经已用“佛”与“沙门”两个译名,认为佛经旧时都是抄传,名称的翻译的新旧译变化并不能作为判定该书为伪书的证据。对于该经文辞优美,不像汉代作品的疑问,汤先生通过对比《大周经录》《长房录》,推断刘宋时《四十二章经》犹存两个译本。之后,汤先生将汉晋所引用的《四十二章经》经文进行了对比,证实了汉晋间《四十二章经》确有两个译本。
通过考察汤先生对《四十二章经》问题的研究,可以从中看出他每涉一事必将相关史料网罗穷尽,研究目光十分广阔,分析过程严谨客观,每一个结论都立足于缜密的推理过程和有力的文献基础之上,全无他所批评的“浅隘”之风。也正因为如此,他的研究成果历久弥坚,为学界所公认。他用自己佛学研究的“精”与“广”回应了文化研究应该持何种态度的问题。
二、文化研究不应脱离本土语境:立体式的佛学研究
外来文化如何与本土文化相融合?汤用彤认为外来文化必须适应本土文化才能生存下来,才有融合的可能,文化研究不应脱离本土文化的语境。佛教作为外来文化融入本土文化的已有实例,成为汤先生的主要研究对象,他通过自己富有特色的立体式佛学研究来回应对文化融合问题的看法。
(一) 外来文化必须适应本土文化:注重佛教与儒道的互动
对于外来文化如何与本土文化融合,汤先生给予较多的关注。当时西方科学主义泛滥,汤先生对此有着清醒的认识:
希腊哲学发达而科学亦兴,我国几无哲学(指知识论、本质论言。人生哲学本诸实用兴趣,故中国有之),故亦无科学。因果昭然,无俟多说。处中国而倡实验以求精神及高尚理想之发展,所谓以血洗血,其污益甚。[2](275)
他反对过分夸大实验科学主义在文化领域的作用。他认为,如果以西方的哲学概念来衡量中国文化,可以称之为无哲学。但是,不应忽视以希腊哲学为源头的西方科学精神,与以人生哲学为特点的中国文化有着本质的不同。如果在中国“倡实验以求精神及高尚理想之发展”,实际上脱离了中国的文化语境,是“以血洗血”,反而会适得其反。对于中国文化之精神,汤先生认为:
言事之实而不究事之学。重人事而不考物律。注意道德心性之学,而轻置自然界之真质。此亦与科学精神相反。中国是矣。[2](276)
在这里,汤先生具体指出了中国文化的三个特质是:言事实不究事之学;重人事而不考物律;重道德心性之学,而轻自然界之真质。同时,他认为这三者与科学精神相反,所以说在中国以西方之科学精神求精神之发展,实际上脱离了中国文化的实际情况,忽视了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根源上的特质不同。
基于这种判断,汤用彤提出自己对于不同文化间融合的看法。大体来说,汤用彤对于文化融合的看法受到西方文化人类学的影响①。他主张外来文化必须作出改变才能对本土文化发生作用,而本土文化不会改变自己的特质。汤先生认为:
现在科学中的文化人类学,也对于文化移植问题积极地研究,他们所研究的多偏于器物和制度,但是思想上的问题,恐怕也可以用他们的学说。[2](278)
源于西方的文化人类学对文化移植问题大致有三种主张:较早的演化说;后来较为流行的播化说;反对播化说的批评派和功能派。如果将这三种学说分别应用到思想领域,汤先生认为“演化说”实际上意味着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毫无关系;“播化说”意味着本土文化的来源是外来的,外来文化总可以改变本土文化。他认为,外来文化对本土文化有影响本来是无问题的,但是如果推得太大太深,就会出现疑问,所以才有第三派“批评派的人或者功能派”的主张出现。对于第三派的看法,汤先生认为:
批评派的人或者功能派的人以为外来文化与本地文化接触,其结果是双方的,而决不是片面的。……第一,外来文化可以对于本地文化发生影响,但必须适应本地的文化环境。第二因外来文化也要适应本地的文化,所以也须适者生存。[2](280)
事实上,汤先生是同意第三种主张。他认为一个地方的文化思想往往有一种保守或顽固性质,虽受外力压迫而不退让,所以文化移植的时候不免发生冲突。又因为外来文化必须适应新的环境,所以一方面本地文化思想受外来影响而发生变化;另一方面因外来文化思想须适应本地的环境,所以本地文化虽然发生变化,还不至于全部放弃其固有特性,完全消灭本来的精神。
基于对文化人类学的吸收借鉴和对中国文化特质的观察,汤先生认为外来文化要想融入本土文化必须经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因为看见表面的相同而调和;第二个阶段,因为看见不同而冲突;第三个阶段,因再发见真实的相合而调和。[2](282)他指出:
一个国家民族的文化思想实在有他的特性,外来文化思想必须有所改变,合乎另一文化性质,乃能发生作用。[2](282)
通过以上的阐述可以看出,汤用彤对于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的融合之道给出的解答是:文化的融合是双向的,一国的文化思想固然受外来影响而发生变化,但是外来文化思想的本身也经过改变,乃能发生作用。所以本地文化思想虽然改变,但也不致于完全根本改变。
汤用彤对文化融合之道的看法虽然受到西学的影响,但他通过对佛教的研究印证了自己看法的合理性、客观性,认为“过去我们中国也和外来文化思想(佛教)接触过,其结果是怎么样呢?这也可以供我们参考”[2](278)。
汤先生以佛教的中国化来说明外来思想的本土化问题,他举例说:
比方佛教已经失却本来面目,而成功为中国佛教了。在这个过程中与中国相同相合的能继续发展,而和中国不合不同的则往往昙花一现,不能长久。[2](282)
由此可以看出,文化问题是汤先生佛学研究总的出发点,也可以说古今、中外的二元论争问题是汤先生佛学研究的根本问题意识。佛教自传入中土后,与中国本土文化的互动,一直伴随着其发展历程。前面提到,汤先生不止一次地强调佛教传入中国是在历史上已有的外来文化融入中国文化的典范。那么,以此为研究角度,探索文化互动的规律,就成了汤先生佛学研究首先关注的问题。
大体上,汤用彤认为隋唐以前的佛教在发展过程中,在与本土文化互动方面经历了两个比较重要的阶段。其一为佛道时期;其二为玄佛时期。
汉代佛教依附道术而生存,魏晋佛学于义理上与玄学沟通,使佛学思想逐渐为中土所接受,而后宗派佛教兴起,佛教于隋唐遂自主发展,但仍注重与儒道之融合。佛教与儒道之互动,“构成了汉代以后中国思想学术和文化发展的重要内容”[4](1)。汤用彤通过佛教与儒道之互动,实际上描绘出佛教传入中土后,从依附到会通,再到开宗立派的变化轨迹。不仅如此,汤用彤还继续追问这种变化的内在动因。他指出:
研究时代学术之不同,虽当注意其变迁之迹,而尤应识其所以变迁之理由。理由又可分为二:一则受之于时风。二则谓其治学之眼光之方法。[5](25)
在汤用彤看来,新学术之兴起,虽发端于时风环境变迁,但如果没有新眼光、新方法,也只是支离片段的言论,而不能完成学术之转变。
汉末直到刘宋初年,中国佛典最流行者为《般若经》,而这一时期又是学术上大变动时期。汉代经学向魏晋玄学的转变是这一时期学术上的转变。般若方便义、法华权教说与玄学“得意忘言”之义有着旨趣上的暗合,般若学与玄学尚“虚无”之谈也存在理论上沟通的可能性。按照汤用彤的看法,开启这一时期学术新时代的新方法就是“得意忘言”。他认为,王弼依此方法,将汉易象数之学一举而廓清之,奠定了汉代经学转为魏晋玄学的基础。
在这里,汤用彤实际上指出了佛教摆脱神仙道术进入玄佛合流阶段后,玄佛沟通的根本契合点也在于“得意忘言”。佛学不仅是玄学发展的助因,同时也在依附玄学发展的同时扩张自己的势力,这一阶段佛学与中国本土思想的互动是佛学发展史上最早的一次深入沟通。自安世高小乘毗昙之后,大乘义学开始盛行。由此,自东晋佛学大盛,抛弃格义方法,提倡法华诸经之会通,佛学学风为之一变②。自此,晋代思想家变佛经之繁重,为玄学之会通,领会大意成为当时的学术风气。[5](45)也正因为如此,晋代佛教撰述不以事数为主旨,与隋唐的佛教注疏特点迥异。
(二) 文化发展的阶段性与转折性:注重佛学发展转折性人物的研究
汤用彤曾不无忧虑地说:
中国现处精神物质过渡时代,外洋科学之法则,机械之势力均渐输入。吾人或将为此新潮之重要人物,自不可不明其利害。[2](57)
汤先生认为当时的中国处于“精神时代”向“物质时代”过渡的阶段,其表现为西方科学法则与西方科技逐渐输入中国。因此,他尤其对文化发展的过渡转折时期尤为关注。这在他的佛学研究上,主要表现在他既注重佛教发展的历史分期问题,又注重突出重点人物的历史地位。如在南北朝佛教分流以前,他特别注意对个别代表性人物的考察。具体来看,汤用彤所重点考察人物包括:释道安、鸠摩罗什及其门下、释慧远、竺道生。
道安是汉以后禅法、般若两系的集大成者。之后,正始玄风兴起,《般若》《方等》因颇契合而流行;佛教经典的翻译也渐具三藏,至鸠摩罗什来华佛经翻译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以上魏晋玄学之三大变化,皆与道安有密切联系。道安“兼擅内外,研讲穷年,于法性之宗之光大,至有助力”[3](173)。罗什的《三论》能为时人很快接受,与之前道安对《般若》的研讲密不可分。道安晚年译经,已具三藏,多为罽宾一切有部之学。在关中讲学译经,道安拢聚了大量英才,为罗什开辟经典翻译新时代作了人才上的预备。
鸠摩罗什在佛经翻译方面,功绩显著。③古代中国译经,必须先为佛学大师,才可为译经大师。只有深通其义,才能进行传译。罗什对《般若》《三论》的理解相当精深。他的译经为佛学经典的整体传入中土贡献卓越。在罗什门下,汤用彤尤为推崇僧肇,认为“僧肇为中华玄宗大师”[3](249)。僧肇融合《般若经》《维摩诘经》《中论》《百论》诸经论,兼采《庄子》齐是非,一动静等命题,而用中国论学文体扼要写出《肇论》,在印度学说中国化方面有绝大建树。僧肇批判性总结当时般若学的研究成果,在他之后,佛教义学南渡,涅槃学实际上“自真空入于妙有”[2](251)。
慧远弘传“提婆之毗昙,觉贤之禅法,罗什之三论”[3](255)东晋佛学三大业于南方。在学问上“兼综玄释,并擅儒学”[3](270)。慧远后来莅止庐山,北方佛法因此而流布江左。
竺道生之学问集鸠摩罗什《般若》、僧伽提婆《毗昙》、昙无谶《涅槃》等晋宋佛学之大成。在佛经翻译上方面,直承道安之一切有部、罗什之《般若》三论、昙无谶之《涅槃》三大源头,吸收众流,又加以慧解,“是中华佛学史上有数之人才”[3](456)。在佛学史上,竺道生扫除旧学“深会于般若之实相义,而彻悟言外。于是乃不恤守文之非难,扫除情见之封执”[3](470)。他开造了此后数百年之学风,是唐以后大行于世的“顿悟见性”之说的源头。
因为以上几位人物实际构成了汉以后佛学发展的主要线索,所以汤用彤对以上几位人物作出了重点讨论。道安集汉以后佛教禅法、般若两大系之所成,下启玄学与般若学合流之势。至鸠摩罗什三论之学广为接受。僧肇融会老庄与佛学,以中观之“有无双遣”集般若学六家七宗之大成,使学术界对于“空”的理解进入一个新时代。慧远弘传毗昙、禅法、三论使北方佛法流布江左。到竺道生集晋宋佛学之大成,扫除旧学,开顿悟见性之源头。汤用彤对以上人物的选取,是以点带面描绘出魏晋佛学的整体演变轨迹。
这些人物无疑就是汤用彤在书中所推崇的“高僧”。汤用彤认为,名僧“和同风气,依傍时代以步趋,往往只使佛法灿烂于当时”[3](141)。高僧则“特立独行,释迦精神之所寄,每每能使教泽继被于来世”[3](141)。两者最大区别在于,高僧能“为释教开辟一新世纪”,且“佛教全史上不数见也”。[3](141)
由此可以看出,汤用彤选取代表性人物的内在标准是“使释迦精神继被于来世”和“开辟释教新世纪”,也就是说这些“高僧”皆为佛学史上集大成之转折性人物,对中国文化的发展与接续都有着卓越的贡献。
三、文化研究的复杂性:关注中国佛学的区域性差异和研究方法
汤先生认为文化研究“应统计全局,不宜偏置”[2](277)。同时,也要注意不同文化的方法选择,不能以偏概全,指出:“世界宗教哲学各有真理,各有特质,不能强为撮合。”[2](277)因此,他对中国佛学的研究注重佛教发展的地域性差异。在研究方法上,他基于“平情立言”的研究态度,提出了“佛法亦宗教亦哲学”,既要有陈迹之搜讨,也要有无同情之默应。
(一) 关注文化发展的地域性:对中国佛学南北差异的研究
汤用彤非常关注佛学发展的地域性差异。这尤其体现在他对南北朝佛教在南北不同发展轨迹的研究。
大致来看,汤用彤对南北朝佛教的总体观察是:罗什慧远以后南北佛学逐渐分途。南方自永嘉南渡,继承三国以来之学风,偏尚义理,玄佛合流,不脱三玄之轨范。北方佛教重在宗教行为,下接隋唐以后之宗派,且与经学俱起俱盛。罗什以后,北方玄谈转而消沉。
汤用彤对于南北佛学发展的研究思路是不尽相同的,本文认为这是因为他以佛学发展自身实际情况为出发点,按照不同地域的不同特点展开研究思路。南方佛学虽历经政权更迭,但学风偏重义学。在刘宋与南齐,《涅槃》《成实》在南方相继流行,其学风颇异于东晋之特重虚无。梁代《成实》极盛,但已颇有人非议。梁陈二代,玄谈又盛,三论得到复兴。所以在研究思路上,汤用彤大致以时间为线索,详述南朝佛学前后之不同。对北朝佛教的考察,汤用彤采取不同的研究思路,并非以时间为纵向结构,北方佛教重在宗教行为,所以汤用彤大致从法难、造像立寺、佛法与经学等方面述佛教之北统。义学上北方偏于有学,其于大乘,则研《涅槃》④《华严》《地论》,于小乘则行《毗昙》《成实》[3](618)。所以,汤用彤从彭城佛学、北方四宗、毗昙学、成实师、地论师相宗南北派等方面详述北朝佛学之发展轨迹,并附之以《摄论》之北传。
北朝佛学的发展与南北学术交通有着密切的联系,如昙迁出游金陵,获《摄大乘论》,而后去彭城弘扬《摄论》,开创了北土《摄论》兴盛局面。又如魏宣武帝,北方佛法盛行者为《地论》《毗昙》、以及禅法净土等。《成实》之学,并不兴盛。后来,南北学术上交通益盛。陈隋之际,僧人多有南方学《成实》,而后至北方弘传。《成实》之学,又由江左流入北土,成为当时之流行学说。有鉴于此,汤用彤对南北佛学不同历史轨迹的考察过程中,同时注重南北学术交通对佛学发展的影响。
(二) 文化研究方法的复杂性:强调佛学研究方法的特殊性
汤用彤曾在《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跋》中提出了他对佛学研究的方法论理念:
佛法亦宗教亦哲学。宗教情绪,深存人心,往往以莫须有之史实为象征,发挥神妙之作用。故如仅凭陈迹之搜讨,而无同情之默应,必不能得其真;哲学精微,悟入实相。古哲慧发天真,慎思明辨,往往言约旨远,取譬虽近而见道深弘。故如徒于文字考证上寻求,而乏心性之体会,则所获者其糟粕而已。[3](655)
佛教作为研究对象,历来都存在信仰与理性的张力问题。研究者基于不同的立场往往会采用不同的研究方法,结果往往导致研究结论的莫衷一是。对于这一问题,当时的学界已有所争论。比如同样是研究藏传佛教史,吕澂、法尊得出的结论往往不同,这实际上与两者的研究立场有很大关系。[6]由此也可以看出,方法论的抉择往往反映出研究者对研究对象所持的立场。汤先生注意到文化研究的复杂性,指出文化研究应“平情立言”,研究佛教不仅要注重历史文献的搜集与考证,同时也要注重佛教作为宗教的特殊性,应持有“同情之默应”的态度,兼顾到心性体会的一面。
四、结论
综合来看,汤用彤佛学研究的文化特质,与他追问“中国文化向何处走”的问题意识有着密切关系。汤用彤基于对当时文化状况的不满,提出文化研究应避免浅隘。他主张文化融合是双向的,外来文化应主动适应本土文化,文化研究过程中要认识到文化研究的差异性、复杂性。他将“汉以后中国佛学的发展”看作不同文化冲突融合的历史借鉴,因此,他的文化主张与其佛学研究有着内在精神上的暗合,他的佛学研究体现出浓郁的文化特质。这一特质主要体现在他的佛学研究中,包括“突出转折性人物”“重视思想演进的地域性差异”“注重方法论抉择以及在研究中关注佛学与中国固有本土思想文化的互动,在动态的三教冲突与融合中考察中国佛教的发展轨迹”。值得一提的是,汤先生的佛学研究所折射出的这一文化特质,是当时许多学术研究共同的特征之一,由此也可以看出,时代共同的“问题意识”对学者学术研究的影响。从某种意义上说,任何学术研究都处于一定的或隐或现之时代背景中,也必然会留有时代的烙印,只不过这一烙印同样或隐或现。
注释:
① 文化人类学(Cultural anthropology)是人类学(对于人类的全貌视野研究)的其中四或五个分支之一。这个学科分支将文化视为有意义的科学概念。文化人类学家探讨人类的文化变异性,搜集观察结果,这往往透过名为田野调查工作的参与观察,并检视全球的经济与政治过程对地方文化的影响。
② 汤用彤认为,此变有三:一则弃汉代之风,依魏晋之学; 二则推翻有部,专弘般若;三则同归殊途,会合三教。
③ 《高僧传》载,罗什在长安译经三百余卷,《祐录》卷二着录三十五部,二百九十四卷。(《名僧传抄》作三十八部,二百九十四卷。《祐录》十四,则作三百余卷。)
④ 《涅槃》是空宗经典,汤用彤认为北方讲说者则常堕于有。
[1] 胡永辉. 胡适禅学研究的文化向度[J]. 北京社会科学,2014(6): 67−72.
[2] 汤用彤. 汤用彤全集·第5卷[M]. 石家庄: 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
[3] 汤用彤. 汤用彤全集·第1卷[M]. 石家庄: 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
[4] 洪修平. 中国儒佛道三教关系研究[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
[5] 汤用彤. 魏晋玄学论稿[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
[6] 胡永辉. 民国时期西藏佛教通史研究的路径抉择[J]. 西藏研究,2013(6): 1−6.
The cultural traits of Tang Yongtong’s study of Buddhism
HU Yonghui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Nanjing University,Nanjing 210093,China)
Tang Yongtong considered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Buddhism after the Han Dynasty as merging of different cultural conflicts. And his cultural advocation coincidentally agreed with his Buddhist studies in inner spirit. Based on his own extensive and intensive study of Buddhism,he expressed his discontent with the cultural studies at that time. On the one hand,he focused on some transitional figures in the history of Buddhism,the regional differenc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Buddhism and the methodology of Buddhist research. On the other hand,Tang paid attention to interac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Buddhism and indigenous thought of China,and observed the development track of Chinese Buddhism in the dynamic collision and integration of Confucianism,Taoism and Buddhism. All these demonstrated a strong cultural trait in Tang Yongtong’s study of Buddhism,which was deeply rooted in his questioning consciousness and his exploration into which direction Chinese culture chooses.
Tang Yongtong; history of Chinese Buddhism; the study of Buddhism; cultural trait; questioning consciousness
B26
A
1672-3104(2015)05−0032−06
[编辑: 颜关明]
2014−12−03;
2015−09−11
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百年佛学研究精华集成”(10JZD0004);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研究成果“民国时期汉传如来藏学研究”(14MLC004); 南京大学文科青年创新团队培育项目“二十世纪佛学学术成果的整理与研究”(20620130695)
胡永辉(1982−),男,河南周口人,哲学博士,南京大学哲学系宗教学系助理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近现代佛学,中国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