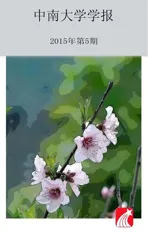《三子会宗论》中的遗民思想论析
2015-01-21宋健
宋健
(汕头大学文学院,广东汕头,515063)
《三子会宗论》中的遗民思想论析
宋健
(汕头大学文学院,广东汕头,515063)
觉浪道盛在《三子会宗论》中,视孟子、庄子和屈原同为儒家孤脉的传承者。他设立“怨与怒”“天与人”和“生与死”三个命题,以孟子为标准,弥合庄子和屈原之间的差异,最终将三子会宗为一。道盛所论并非着眼于纯粹的学术研究,而是在特殊时代背景下明遗民情志的表达。他通过三个命题层层寄托其光复之心与守节之志,这在遗民中得到了深刻的认同和广泛的响应,因而具有极为浓厚的时代色彩。然而,《三子会宗论》作为一种“六经注我”的阐释方法,也不可避免地在对原著的解读过程中,带有过度阐释的偏颇。
《三子会宗论》;觉浪道盛;遗民;孟子;庄子;屈原
觉浪道盛是曹洞宗第二十八世法嗣①,他虽出自佛门,却对儒学颇为尊崇,这与他修行所在的青原山有着一定的关系。青原山本为禅宗胜地,后又是阳明书院所在,该地浓厚的儒、释文化背景,使得道盛这位释家子弟却有着深厚的儒者情怀,这在《三子会宗论》中也有所体现。②所谓“三子”,即孟子、庄子和屈原。道盛主张当以孟子为标准,消弭庄、屈之间的差异与隔阂,并最终实现三子的会宗为一。其实,道盛作此文章并非着眼于单纯的学术研究。道盛在文中设立三个命题,既出于会宗三子的理论需要,更是借此寓托其内心深处的遗民情志。
一、《三子会宗论》中的三个命题
《三子会宗论》开篇即点明孟子的儒家正统地位,“其所著述亦皆直揭圣学王道之微,以光大五经之统也。”[1](571)道盛又指出庄子和屈原亦为儒宗别传,“此外有庄子之《南华》,屈子之《离骚》,其貌虽异,究其所得,皆能不失死生之正,以自尊其性命之常,曾无二致。岂不足与五经四子,互相发明其天人之归趣,可为儒宗别传之密旨哉!”[1](571)众所周知,庄子本出自道家,屈原也非纯粹的儒生,道盛将此二人纳入儒家,实令人匪夷所思。对此,道盛引出第一个命题,以自圆其说。
(一) 怨与怒
《三子会宗论》指出屈原虽有所“怨”,但并非怨责君王,而是“自求其不得君父之故”[1](571),以求感悟怀、襄二王。屈原的良苦用心甚至可与虞舜、文王比肩:
孰以屈子之怨忧,未能格君之心,遂谓不逮于大舜、文王哉?舜幸瞽瞍自能底豫,以获玄德升闻,而卒协帝,使天下万世之为父子者定。文幸暴纣尚有良心,赐西伯以专征,而服事殷,使天下万世之为君臣者定。[1](571)
文末又言,“(三子)夫固各自潜行以泯其亢变,各以怨、怒、戒惧而致中和,其相忘于无言也。”[1](574−575)文中的“戒惧”,当出自《孟子·滕文公下》:“吾为此惧,闲先圣之道,距杨墨、放淫辞,邪说者不得作。”[2](3714−3715)那么“怒”指庄子,亦无疑问。因为《逍遥游》中怒而南飞的大鹏,早已成为《庄子》中的经典形象之一。按照道盛的说法,屈原怀怨、庄子生怒、孟子有戒惧,三子又能因之达致于中和、相忘于无言。然而,《三子会宗论》只点出其然,而未明言其所以然。
其实,道盛在多篇文章中论及怨和怒的概念,且常以上述三子为例证。如《论怨》:
予以庄生善怒字,屈原善怨字,孟子尤善怨怒二字,盖未有怨而不怒、怒而不怨也。庄子以怒而飞,怒者其谁?草木怒生,达其怒心。即达其怒心,尤妙尽怒者其谁也?屈子怨而不怒③,则怨即怒也,不见《离骚》皆不平之怨耶。孟子云“一怒而安天下”,又以舜如怨如慕,以自求其不得于父母之故;太甲自怨自艾,终得阿衡之意。凡皆以怨怒成此浩然之气。[3](788)
文中正式提出“庄生善怒,屈原善怨,孟子尤善怨怒”的观点,并强调“未有怨而不怒、怒而不怨”,即怨怒实为相通的关系。在道盛看来,怨怒蕴含着巨大功效,“此怨乃能以天地人物不平之气,保合天人性情之太和”[3](788)。为此,他又列举了古代圣贤因怨怒而成功的例子:
即尧不得其子而举于舜,非怨怒而何能如此神远哉?舜以怨而得底豫,禹以父鲧殛死而治平水土,何怨如之?即汤武以臣伐君,不避惭德,何等怨怒耶!文王拘于羑里,口无怨言而此中之怨艾,至以一怒安天下何如?若周公以大义灭亲,流言居东,怨可知也。《春秋》,怨史也;孔子惧,作《春秋》,擅天王之进退褒贬。孟子距杨墨,只此一惧,乃不肯避万世乱贼之讳忌,此又何等怨怒哉
庄子之“怒”与屈原之“怨”,也具有“安天下”的功效。道盛《一字法门》曰:
庄生怒而飞‘怒’字,与孟子、文王一怒安天下‘怒’字,皆是自心中创出造化来,变易天地人物,即此一字。[4]
关于屈子之怨忧,《三子会宗论》有如下描述,虽不能即身使怀、襄感悟,然其忠贞贯于天地,文与日月争光,又何尝不使天下万世之为君臣者,不敢乱贼其心,以自陷其名义于生死,而定天命之有归哉
这同样体现出“怨”的功用。那么,庄子之“怒”与屈原之“怨”就互为融通。至于孟子,他曾言“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2](2675),又说过舜有怨慕之心、太甲自怨自艾[2](2673,2378),自然也就被视作兼善怨怒。
道盛对怨怒的推崇,是有思想渊源的。日本荒木见悟在《觉浪道盛初探》一文中指出,道盛有所谓“怨”的禅法,并对“怨”与“恨”加以区分:
道盛所谓的“怨”,与受害者对加害者所抱持的憎恶感完全是两回事。觉浪道盛所谓的“怨”,系指痛惜加害者之所以成为加害者。更仔细地说:并不是指咒骂加害者之所以变成加害者一事,而生怨怒加害者丧失了自己的本分,使自己的人格低落,遂变成了加害者。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怨”和“恨”的区分便十分明白。“怨”不是恶质的烦恼,而是参禅学道者应该深自警惕的法则。[5]
荒木视道盛的“怨”为禅法,诚为确论。④但其本质是自我反省,而非荒木所谓“痛惜加害者之所以成为加害者”。道盛特别看重由怨怒引发的自省,他说:
吾尝与儒者云,夫子称诗可以兴观群怨,此怨之一字,即吾禅门疑情也。所谓臣不得君,子不得父,乃至不得于朋友百姓,皆此自怨之疑情。孟子善于形容大舜,谓如怨如慕如泣如诉,此正是自怨自艾、自起疑情。曰我何以不得于父母兄弟哉?非有怨恨于顽父嚣母与傲弟也,才有怨及父母兄弟,则此自怨自艾之心,终无以自悟,亦终不能感格其父母使底豫也。[6]
文中言及“自怨自艾、自起疑情”,其本质即“返求诸己”。《孟子•离娄上》云:“爱人不亲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礼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已,其身正而天下归之。”[2](2718)朱熹对“反求诸已”的解释是,“谓反其仁、反其智、反其敬也。如此,则其自治益详,而身无不正矣。”[7](278)舜之怨就在于“自怨自艾”,反诸己而追问其仁、智、敬为何不得于父母兄弟,而非“怨恨于顽父嚣母与傲弟”。
(二) 天与人
《三子会宗论》开篇已言孟子继承了五经所开创的天人一贯的宗旨,庄子和屈原亦可“互相发明其天人之归趣”[1](571)。具体而言
庄子者,道心惟微之孽子也,天之徒也,先天而天不违其人也;屈子者,人心惟危之孤臣也,人之徒也,先人而能奉其天也。此二子者,岂不交相参合天人于微危之独乎
文中的“人心惟危”与“道心惟微”,皆出自《尚书•大禹谟》。对此,道盛认为,“危者,即显见昭著之人心,为已发已形之幾也”[1](574);“微者,即于穆不已之天命,为不睹不闻之独也”[1](574)。而他在《大心精心》中的解释更为精炼:“戒慎恐惧,惟危也;不睹不闻,惟微也。”[8]在道盛看来,屈原洁身自好之行与恐皇舆败绩之心,正是“戒慎恐惧”的集中体现,所以屈子“不忍偷生而甘死于义命”[1](571),又“能尽臣子之心,以极人伦之变,而不失其性命之常”[1](574),此即所谓“人心惟危之孤臣”[1](572);庄子虽独与天地精神往来,但绝非“独贵于脱出尘坌之外,不肯敝敝以世为事”[1](572),实不过“推尊老聃无为自然之旨,以寓于经世”[1](573)罢了,仍不失重振儒家孤脉之心,故为“道心惟微之孽子”[1](572)。由此可知,庄子的“道心”与屈原的“人心”,看似有天人之别,实则存在相通之处,二子均可以先天不违人、先人能奉天,皆入于天人一贯之道。这恰恰与道盛在《〈学〉〈庸〉宗旨》中的论断遥相呼应:
天即是性,性即是诚,诚即是独。慎独者,人尽而天不能外,故自天而之人;诚之者,则自人而之天。[9]
“独”犹如不睹不闻之道心,是“自天而之人”的;“诚”犹如戒慎恐惧之人心,是“自人而之天”的。既然,“天”“性”“诚”“独”彼此间通彻无碍,那么道心与人心也就相互融合,庄子、屈原的天人旨趣也便贯通为一。进而,道盛加以总结:
惟尽乎人者,乃能尽乎天;惟尽乎天者,乃能尽乎人;惟洁净精微者,乃能天人不二。后世之人,孰能有能精道心之微如庄子者乎?孰有能一人心之危如屈子者乎?又孰有能存天人几希如孟子者乎?[1](574)
至于孟子如何兼具天人一贯之道,道盛以庄子为“道心惟微之孽子”,以屈原为“人心惟危之孤臣”。其中“孽子”“孤臣”之词当引自《孟子·尽心上》:“人之有德慧术知者,恒存乎疢疾。独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虑患也深,故达。”[2](2765)孙奭《孟子疏》曰:“此孟子所以执此喻以自解也,言孤臣不得于其君者也,孽子不得于其亲者也。不得于其君与不得于其亲者,故能秉心常危、虑患常深,以勉力于为道德,故能显达也。”[2](2766)由于“孤臣孽子”乃是不得于君亲的远臣庶子,其处境正与《三子会宗论》对庄、屈的定位相符合,即皆为儒宗别传。同时,孤臣孽子“秉心常危、虑患常深”近似于屈原的“戒慎恐惧”,“勉力于为道德”又近似于庄子的“不睹不闻之独”。这样,在道盛看来,孟子执以自喻的孤臣孽子就涵盖了庄、屈各自的秉性,亦即所谓的兼具天人一贯之道。即所谓:
惟尽乎人者,乃能尽乎天;惟尽乎天者,乃能尽乎人;惟洁净精微者,乃能天人不二。后世之人,孰能有能精道心之微如庄子者乎?孰有能一人心之危如屈子者乎?又孰有能存天人几希如孟子者乎?[1](574)
通过比较可以发现,孟、庄、屈三子的天人之旨,实乃以孤臣孽子的形式延续儒家孤脉,这与此前“怨与怒”的命题在思路上是一脉相传的。但有所不同的是,在此节的命题中,道盛开始有意识地弥合庄子与屈原之间的差异。如果说怨与怒尚在感情上存在相通之处的话,那么天与人之间的差距还是相当悬殊的,毕竟庄子以“不睹不闻之道心”善其终身,屈原则以“戒慎恐惧之人心”杀身成仁,二子最终的归宿悬隔天壤。因此,这也就需要进一步在理论上拉近庄、屈之间的差距。或许道盛在完成“天与人”的论述后,仍觉得意犹未尽,便深入到下一个命题中。
(三) 生与死
《三子会宗论》指出,天道与人伦之间的关系,对于生死的意义有着深刻影响:
盖人伦而不知天命,则终惑于形器争夺,而不能死生以此身所出之天,为归根复命之极;天道而不知人伦,则终惑于虚无断灭,而不能死生以此身所在之伦,为全体成人之地矣。[1](573)
天道与人伦必须并行,若偏废一方,要么“惑于形器争夺”,要么“惑于虚无断灭”,生死亦难得其正。面对天命,人们只有尽心知性以知天,存心养性以事天,修身俟之而已。至于生死,莫非命也,只有尽其道而死,才是顺受其正。此正所谓上顺天道,下修人伦,得乎正命也。⑤而每个人尽死生之道亦有所不同:
夫子之生身于亲也,则当竭此身力以报其所生,竭力不以孝,则何以安此身于上下之生死哉!臣子之受命于君也,则当致此身行以报其所受,致行而不以忠,则何以当此身于荣辱之生死哉!妇之配命于夫也,则当终此节义以报其所配,终节而不以贞,则何以洁此身于离合之生死哉!统此身世之因于性命也,则当使此身世以尊其性命,尊其性命而不能以中正,则何以超此身命于迷悟之生死哉
生死之义,于子、于臣、于妇各有所宜,子死孝、臣死忠、妇死贞,如此方能以身世以尊性命,而得其中正,并超乎生死之迷悟。
道盛在《癸甲全提》中,亦有类似的观点,他说“能于生死蜕然者,儒门大略亦有三种”,具体而言:
上焉者如朝闻道可以夕死,彼能原始反终,知生死之故,通乎昼夜之道,循环无端,生本无生可生,死本无死可死,故幻身之生死,不足以惊骇其无生死之心。中焉者如忠臣孝子、义夫节妇,知义理名分,臣必死忠,子必死孝,夫必死义,妇必死节。知此忠孝节义四字,亦自能死与日月争光,不必尽见道也。下焉者如愚痴无知百姓,偶然犯法,囚狱禁锢,求死不得。或情真罪当,甘死如归;或逼迫之极,投水自缢。又如刺客报仇,荆轲、聂政之辈,或死于知己,或死于侠气,或死于愤恨,或死于恩爱,此皆死于妄想颠倒,未得死所,尤不足以语见道也。[10]
上者乃是尽道而死,也是道盛所推重的;中者虽然未必见道,然亦知忠孝节义,可谓死得其所;道盛对下者最不以为然,因为其死既不见道,亦不得其所。
那么,孟子、庄子皆寿终正寝,屈原则投水自尽,对此截然不同的生死抉择,道盛是如何看待的呢?《三子会宗论》认为:
以故庄子之与孟子,皆能自全而不陷于死,此善于居亢而能无悔,所谓知进退存亡而不失其正之圣人也。屈子与伯夷,皆能自尽而不陷于生,尤善于居亢而能无所撼,所谓知进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丧之圣人也。[1](574)
从文中可以得知,孟子、庄子与屈原、伯夷皆被道盛视为圣人,但有所不同的是孟庄能够“知进退存亡而不失其正”,屈原、伯夷则“知进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丧”,此间还是存在些许差别的。若一定要对上述四位圣人中划分等级的话,那么孟、庄属于《癸甲全提》中得道的上者,屈原、伯夷则近乎于中者,当然屈、伯亦为见道者。但是,如果屈原、伯夷选择求生,则是背道失身,“天下之人,皆藉此以偷生自全为名节,而万世之下,又孰能高其汨罗、首阳之忠烈哉!处亢之中,有当慷慨捐生,不捐则失道;有当从容就义,不就则失身。”[1](574)所以,“如比干之死、微子之去、箕子之狂、与伯屈之死、庄孟之生,是皆重道尊身,乃大圣大贤以大仁大义,善于处亢,无悔无憾,其于易地则皆得而不失其正者也。”[1](574)这样,道盛巧妙地运用孟子的“正命”说,不但弥合了庄、屈之间的生死界限,并使三子同处于生死不二的境地。
二、遗民情志的独特表达
在《三子会宗论》的最后,道盛附有一段自评:
世不绝贤庸,讵知此后无有若而人,读吾此论,不大为赏鉴倡同心者,建一祠庙,貌三子之像,以孟居中,而左右庄屈同堂共席,相视莫逆,以配享千古。使景仰此天人不二之宗,岂不为甚盛事哉
虽然,孟子、庄子与屈原生活时代相近却又未曾谋面,出身、经历与归宿都相差悬殊,但经过道盛的融通与诠释,三子得以共处一宇、同享千古。然而,如果三子有灵,他们同堂共席的时候,恐怕不会如道盛所说的“相视莫逆”吧。孟子绝对不能容忍庄子诋非圣人的“邪说”,也肯定不满屈原忿怼君王,必视二子为异端而力辟之。庄子必然不会将孟子的辩驳和屈子的狷介放在眼里,如此汲汲然,其为名乎,其为宾乎?屈原又怎能甘心像庄子那样聊逍遥于无为,更不会忍心离开楚地,如孟子一般周游列国。所以,从学理上讲,孟、庄、屈三子同堂恐怕是行不通的。
据研究者考证,《三子会宗论》大致成文于清顺治十年之后。也就是说,道盛在明亡之后,以遗民的身份写下了《三子会宗论》。⑥道盛虽身为禅师,却是一位以忠孝闻名天下的遗民。顺治五年,他因在《原道七论》中出现“明太祖”字样而下狱。由于该著成于明亡之前,不久道盛即被豁免。然而,满清的政治高压与思想禁锢迫使明遗民的表达方式不得不转向隐晦。作于顺治十年稍后的《三子会宗论》,正是道盛遗民心志在此种文化背景下的特殊表达,也因此在明遗民群体中引发了广泛的认同和共鸣。《三子会宗论》开篇即点明孟子是儒家正宗、庄屈为儒家别传,三子共同肩负着儒学复兴的重任。众所周知,孟子在宋代以后才被尊为儒家“亚圣”,即使如此在明初也一度被逐出孔庙;庄子本是道家代表,屈原杂取儒、法、道等诸家思想,也并非醇儒。所以,孟、庄、屈三子实难会通为一。然而,道盛不但为三子涂抹上浓厚的儒家正统色彩,还以孟子为标准来会通庄、屈,并努力弥合二人之间的思想差异。道盛如此苦心孤诣,乃暗含着对时局的隐忧,已超越了一般的学术意义。儒学发展至晚明渐趋衰落,后来曾一度出现复兴的迹象。但随即而来的异族统治,加剧了士人对包括儒学在内的华夏文明未来的命运的忧惧。《三子会宗论》正是这种忧惧的体现,寄寓着明遗民在异族统治下保全传统文化孤脉的心迹。
进而论之,道盛在《三子会宗论》中所设立的三个命题,从不同层面寓托着遗民的心迹。首先是“怨与怒”,该命题当源自《诗大序》“乱世之音怨以怒”。道盛所处的时代,正是千古一遇的乱世。在明亡之前,外有清兵,内有流寇,又天灾连年。在崇祯帝殉国之后,盘踞南京的弘光小朝廷并没有给民众带来希望,更无力挽救岌岌可危的国运。南明缺少王导这样的中流砥柱,却不乏内讧乱局之臣。先是左良玉以“清君侧”为由,与马士英、阮大铖兵戎相见,被满洲人乘隙渔利。后隆武朝始有中兴迹象,又突遭郑芝龙挟天子降清的变故。可见,内耗一直伴随南明王朝的始终。身遭如此乱世,岂能无怨无怒?道盛于此时大力提倡怨怒之旨,正是有感而发。他希望世人能够如虞舜一般自怨自艾、自我反省,毕竟明末士风日下是不争的事实。阉党猖獗之际,众多士人争相阿谀献媚。一时间,黄钟毁弃,瓦釜雷鸣。然而,在宦官失势、东林党复起之后,倾轧之风甚至盛于往昔。至于明朝天子之昏聩荒淫,更不必细言。《三子会宗论》中一再强调屈原之“怨”堪比虞舜、文王,原因在于他们皆“使天下万世之为君臣者定”[1](571)。道盛特别重视“怨”的精神,恐怕正是借此晓喻遗民,当自怨自艾、自省自励,严守节操、牢记志向。道盛又提出庄子之“怒”,意在鼓舞遗民当有大鹏怒而飞、胸怀天下的气势,效法文王一怒而安天下的精神,承担起复明的重任。虽然,庄、屈不免各有偏至,但借孟子加以会通,最终使得“怨”与“怒”合而为一,共同成为明遗民的精神支柱。道盛据此激励遗民,应如孟、庄、屈三子复振儒宗一样,大兴怨怒之功以复兴明室。恰如研究者所论:“道盛与方以智以‘怨’论诗,以‘怨’论生命的原动力,其最为深沉的蕴意实即收束于此复明理想的实践中。”[11]
紧接着,道盛又引出“天与人”的命题,其中借用“孤臣”“孽子”的概念来突显三子儒学传承者的身份。对于《孟子》中涉及“孤臣”“孽子”的那段话,朱熹的理解是,“(孤臣孽子)皆不得于君亲而常有疢疾(灾患)者也”,“人必有疢疾,则能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也”。[7](354)这或许来自《孟子·告子下》中的名言:“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人恒过,然后能改;困于心,衡于虑,而后作;征于色,发于声,而后喻。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2](2762)孤臣孽子固然不得于君亲,但在经历了种种磨难和考验之后,最终能够有所成就。在道盛看来,孟、庄、屈三子正是孤臣孽子的典型代表。在“天道人伦几乎灭绝”的战国时代,孟子之道不行于世,“乃退而著书,使后世知有孔子之集大成者,全赖于是”[1](571);庄子“生平自能高尚其志,奋其身如鲲鹏之化,洁其神如藐姑之游,故所著作,独揭向上一路”[1](572);屈原自怨自艾“只以自求其不得君父之故……使天下万世之为君臣者,不敢乱贼其心”[1](571)。反观道盛,虽身为方外之人,却也如孤臣孽子一般,以匡扶明室为己任。在明王朝内忧外患之际,他不避艰险多次于南京、麻城等地登坛说法,鼓舞士气民心以对抗天灾人祸。道盛还提出多项济民守战的策略,受到世人称赞。明亡后,他入主金陵天界寺,大批遗民纷纷皈依门下,以逃避剃发易服的屈辱。一时间,天界寺成为遗民汇聚的中心,也是明室孤臣孽子在暗中筹划复国的联络地。道盛提出“天与人”的命题,与传统思想中的天人合一并无太多关联,反倒是巧妙的利用了命题中“孤臣”“孽子”的概念,来强化明遗民的身份认同。并借助庄子“不睹不闻之道心”,来告诫遗民应独善其身,严守“孤臣”的节操;又标举屈原“戒慎恐惧之人心”,来警醒遗民当时刻兢兢业业,不忘复明之志。
尽管,前两个命题已完全将道盛的遗民心志蕴含于其中,但仍有一个重大问题亟待解决,那就是生死的抉择。固然,出身佛门的道盛已超然于生死之外,但既然以遗民自居,就意味着放弃死节。这就要求道盛不仅为自己,也要为整个遗民群体的存在寻求合理性。明代士人颇有死节的风尚,故王夫之以“戾气”评之。易代之际,明遗民的生死观渐趋通明。如顾炎武云:“天下之事,有杀身以成仁者;有可以死,可以无死,而死之不足以成我仁者。”[12]孙奇逢曰:“窃意古来纯忠大义不一途,应死而死,则死有攸当;应遁而遁,则遁有攸当——此微、箕、比干所以同归于仁也。”[13]道盛所设立的“生与死”的命题,也是当时遗民生死观的反映。如前所论,道盛对生死价值的判断在于是否“得道”。在《会宗三子论》中,道盛称赞屈原是“自尽而不陷于生”的圣人,屈原的殉节是以身殉道、舍生取义的体现。由此联想到明朝末年,抗清殉国的臣民比比皆是,最著名的如陈子龙、夏完淳等。道盛高标屈原的死节,正是对明末死节之士的肯定与称赞。这也是遗民告祭英烈时,在心灵世界的自我救赎之道。道盛选择做遗民,并未因为贪生怕死。据《住寿昌观涛奇禅师塔铭》记载,道盛在下狱期间面对生死全无或喜或悲之情,钱澄之赞之曰:“不怕死,固杖人家法也。”[14]道盛选做遗民的心路,或可在其《正庄为尧孔真孤》中得以窥见。文曰:
夫立孤之人,视殉节为尤难,隐身易状,转徙于莽渺,以存其真。又谨护其所证,非直寄之以避一时之危而已,固将图复昌大其后也。[15]
道盛认为庄子乃是儒家真孤,其托身于道家是为了在后世伺机光大儒宗。所以,庄子身为立孤之人是不敢轻易死节的,因为其担负着护佑所托之孤而图昌大其后的重任。其实,道盛自己也承认《正庄为尧孔真孤》并非阐述《庄子》本义:“即有谓予借《庄子》自为托孤,与自为正孤,谓非《庄子》之本旨,予又何辞。”与其说庄子自托于儒家,不如说道盛借庄子以托其复兴故国之志,而他的托孤说也在遗民中得到广泛的认同。所以,肩负托孤重任的遗民,怎能随意捐生殉节?恰如他在《谭东里居士痛饮读离骚图》中说:“所以读之愈不容己兮,抑自招其魂且不敢死只。”[16]由此反观《会宗三子论》中称许孟子、庄子“自全而不陷于死”,实即道盛为遗民选择生存而非死节确立理论依据。而在“生与死”的命题中,将孟、庄、屈三子会宗为一的意义,恐怕就在于:“明遗民们一方面表达了对于死节之士的推崇和赞扬,另一方面也巧妙的为自己的生存价值提出了合乎义理的论证。”[17]
三、余论
由于觉浪道盛在思想上的不拘一格,因而在佛教史上并未受到太多关注。但是,他胸怀儒者般的济世之心,却使之在明遗民中享有盛誉。他作《会宗三子论》旨在借题发挥,以暗喻其遗民情志,更是深得信徒们的响应。嫡传弟子方以智在道盛圆寂后,依师命在江西青原山修建了三一堂,“药地老人居归云阁时,因与诸子举杖人孟、庄、屈《三子会宗论》,欲以一堂享之。因建三一堂,起四望楼。”[18]并作《鼎新闲语》追述先师遗愿:“杖人尝欲建鼎新堂祀孟庄屈,以三子同时不相识,特置一堂,作《会宗论》,谓屈以怨致中和,惟危尽人者也;庄以怒致中和,惟微得天者也;孟以惧致中和,合天人者也。”[19]道盛对“怨怒致中和”的诠释,在于以兼善怨怒的孟子,会宗各善怒怨的庄子和屈原,并强调由怨及怒、一怒安天下的自我激励的心理过程。对此,方以智也是非常认同的,并运用家传易学中的“公因反因”说,对“怨怒致中和”做出了自己的阐释。对道盛执弟子礼的钱澄之作《庄屈合诂》,重在会宗庄屈二子。他借助家传易学和诗学,通过“以《庄》继《易》,以《屈》继《诗》”的方式,阐发庄屈本无二致的道理。曾短暂师从道盛的屈大均作《读庄子》一文,认为庄子有天放的特征、屈原有人放的气质,但二者之间又并非悬隔天壤,实则“天与人为一,生与死而不二”。由上可知,道盛的三位弟子对其《三子会宗论》各有传承。方以智对“怨与怒”的命题做了深入阐发,钱澄之侧重会宗庄屈二子,屈大均则兼论“天与人”和“生与死”两个命题。⑦同时,这三位弟子还行动上继承道盛的遗民气节。方以智在落发为僧期间仍四处联络抗清势力,后因受粤案牵连被捕,乘隙投水全节而终。钱澄之、屈大均都曾参与复明起义,并以遗民身份终老。
然而,遗民终究属于时代的产物,具有历史局限性。遗民们为自身存在寻求合理性而作的著述,也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失去后人的认同。四库馆臣对钱澄之《庄屈合诂》有如是评价:“盖澄之丁明末造,发愤著书,以《离骚》寓其幽忧,而以《庄子》寓其解脱,不欲明言,托于翼经焉耳。”[20](1139)方以智的《药地炮庄》同样寄托着遗民意识,也得到了相似的评论:“借洸洋恣肆之谈以自摅其意,盖有所托而言,非《庄子》当如是解,亦非以智所见真谓《庄子》当如是解也。”[20](1256)以道盛为首的明遗民,运用儒学对孟、庄、屈三子做出全新的阐释,得出了与众不同的结论。但他们的终极目的并不在纯粹的学术研究,而是借此寓托遗民情志。当道盛将庄、屈纳入儒宗别传时,无疑取消了二子独特的魅力与价值。然而,这种六经注我的阐释方法在学术史上并不罕见。时至晚清,康有为等奉孔子为改制先祖,借此宣传变法,这在方法论上与三百年前道盛的《会宗三子论》如出一辙。遗民的身份固然不能世系,但古代知识分子对国家前途、民族命运的关怀与忧惧,永远不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磨灭。
注释:
① 道盛,号觉浪,俗姓张,福建柘浦人,明末高僧兼遗民领袖。生于明万历二十年(1592),卒于清顺治十六年(1659)。主要著述有《天界觉浪盛禅师语录》《天界觉浪盛禅师全录》《天界觉浪盛禅师嘉禾语录》。
② 关于道盛的思想特点,参阅宋健:《道盛“三教并弘”思想述论》,载《吉林师范大学学报》,2013(4)。
③ 原文作“屈子怨而不怨”,后“怨”字当为“怒”之形误,因改之。
④ 《青山小述》载:“儒门有一‘怨’字,如大舜如怨如慕,太甲之自怨自艾,与《诗》之可以怨等,乃禅家所谓‘疑情’,必欲求其故而不得也。”道盛视儒门之“怨”等同于禅家之“疑情”,亦可辅证荒木之论。
⑤ 道盛此观点当受孟子“尽心知性”与“正命”说的启发。《孟子•尽心上》:“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殀寿不贰,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莫非命也,顺受其正。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岩墙之下。尽其道而死者,正命也。桎梏死者,非正命也。”
⑥ 有关《三子会宗论》的成书时间,参阅谢明阳:《明遗民的庄子定位论题》,第46~48、159页,台北,台湾大学出版委员会,2001。
⑦ 关于方、钱、屈三人的观点,参阅宋健:《论道盛弟子对〈三子会宗论〉的再阐释——以方以智、钱澄之、屈大均为中心》,载《南京师范大学学报》,2010(1)。其他门人对《会宗三子论》的回应和赞许以眉批的形式保存下来,这里不再赘引。
[1] 觉浪道盛. 三子会宗论[C]// 天界觉浪盛禅师全录. 北京: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
[2] 赵岐,孙奭. 孟子注疏[C]// 阮元. 十三经注疏. 北京:中华书局,1980.
[3] 觉浪道盛. 论怨[C]// 杖门随集. 北京: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
[4] 觉浪道盛. 一字法门[C]// 杖门随集. 北京: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 781.
[5] 荒木见悟. 觉浪道盛初探[C]// 明末清初的思想与佛教.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168.
[6] 觉浪道盛. 胡洪胤盛高姚诸士云莲净修禅侣请茶话[C]// 天界觉浪盛禅师全录. 北京: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 460.
[7] 朱熹. 孟子章句集注[C]// 四书章句集注. 北京: 中华书局,1983.
[8] 觉浪道盛. 大心精心[C]// 杖门随集. 北京: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 804.
[9] 觉浪道盛. 《学》《庸》宗旨[C]// 天界觉浪盛禅师语录. 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 767.
[10] 觉浪道盛. 癸甲全提[C]// 天界觉浪盛禅师全录. 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 747.
[11] 谢明阳. 明遗民的“怨”“群”诗学精神[M]. 台北: 大安出版社,2004: 111.
[12] 顾炎武. 与李中孚书[C]// 顾亭林诗文集. 北京: 中华书局,1983: 82.
[13] 孙奇逢. 寄王生洲[C]// 夏峰先生集. 北京: 中华书局,2004:43.
[14] 钱澄之. 住寿昌观涛奇禅师塔铭[C]// 田间文集. 合肥: 黄山书社,1998: 456−457.
[15] 觉浪道盛. 正庄为尧孔真孤[C]// 天界觉浪盛禅师全录. 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 729.
[16] 觉浪道盛. 谭东里居士痛饮读离骚图[C]// 天界觉浪盛禅师全录. 北京: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 562.
[17] 谢明阳. 明遗民的庄子定位论题[M]. 台北: 台湾大学出版委员会,2001: 199.
[18] 欧阳霖滕. 谷口别峰[C]// 方以智. 青原志略. 清康熙八年刻本.
[19] 方以智. 鼎新闲语[C]// 方以智. 青原志略. 清康熙八年刻本.
[20] 永瑢. 四库全书总目[M]. 北京: 中华书局,1965.
On Ming descendants’ sentiments in Viewpoint of Relation of Mengzi,Zhuangzi and Quyuan
SONG Jian
(College of Literature,Shantou University,Shantou 515063,China)
In the Viewpoint of Relation of Mengzi,Zhuangzi and Quyuan,Juelang Daosheng viewed Mengzi,Zhuangzi and Quyuan as successors of Confucianism,raising three propositions of Resentment and Anger,Heaven and Humans,Life and Death,taking Mengzi as the criteria,making up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Zhuangzi and Quyuan and finally merging the three into one. In fact,what Daosheng stated was not simply academic research,but implication of Ming descendants’ sentiments. Daosheng,through the three propositions,expressed his ideals of revival and loyalty,which received profound recognition and response,hence hosting strong significance of the time. However,the Viewpoint of Relation of Mengzi,Zhuangzi and Quyuan,as a way of interpreting such classics as Mengzi,Zhuangzi and Chuci,inevitably carries partial misinterpretation in the process of decoding the originals.
Viewpoint of Relation of Mengzi,Zhuangzi and Quyuan; Juelang Daosheng; descendants; Mengzi; Zhuangzi; Quyuan
B22
A
1672-3104(2015)05−0038−07
[编辑: 颜关明]
2015−03−11;
2015−06−13
2010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项目“战国时期的社会转型与诗歌创作演变研究”(10YJC751069);汕头大学科研启动经费项目“庄屈并称现象研究”(STF12014)
宋健(1978−),男,河北邯郸人,文学博士,汕头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学术思想史,先秦诸子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