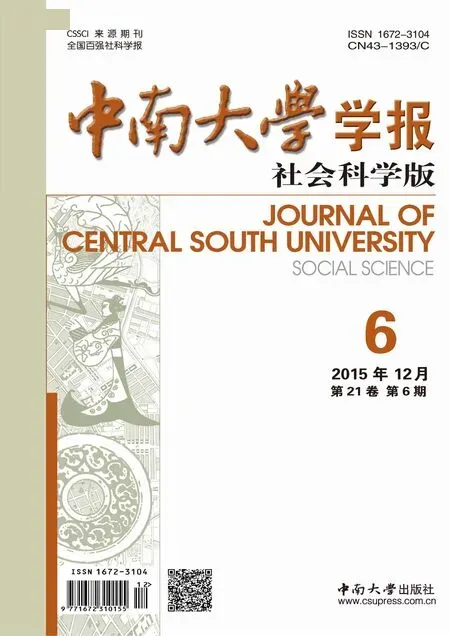流散视角下的历史再现
——《上海孤儿》对英、日帝国主义侵华行径的双重批判
2015-01-21邓颖玲王飞
邓颖玲,王飞
(湖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湖南长沙,410081)
流散视角下的历史再现
——《上海孤儿》对英、日帝国主义侵华行径的双重批判
邓颖玲,王飞
(湖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湖南长沙,410081)
当代日裔英籍作家石黑一雄的代表作《上海孤儿》选取英、日帝国主义相遇的上海租界作为历史背景,透过流散视角再现了20世纪30年代遭受英国鸦片贸易、日本侵华战争双重侵略的中国历史。小说中的人物既是为历史洪流所夹裹的个体,同时也具有历史象征意义。在细读小说历史语境的基础上,通过分析小说主人公班克斯、戴安娜及山下哲的个人遭遇,认为小说从人物既是中心又是边缘的相对位置出发,审视了那段被西方学者压抑的中国殖民历史,批判了英、日帝国主义罪恶的侵华行径。
石黑一雄;《上海孤儿》;流散视角;鸦片贸易;侵华战争;历史再现
石黑一雄(Kazuo Ishiguro,1954−)自20世纪80年代起在英国文坛走红,并成为当代最重要的作家之一。生于日本、长在英国的他与拉什迪、奈保尔并称为当代英国文坛“移民三雄”。石黑一雄擅长从流散视角出发,以优雅细腻的语言叙述回忆历史、个人与社会的交互关系,被誉为“寻觅旧事”的圣手。[1](34)他的小说以反思英、日历史为主题,继承了英语文学的隐忍节制和日本文化的“物哀”“幽玄”[2](92),充满了对历史问题的深切思考。石黑一雄的大部分小说都是关于日本或英国历史的,尤其是两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历史。《浮世画家》反思了二战时期日本所犯的罪行及战后日本普通民众经历的伤痛;荣获布克奖的《长日留痕》批判了二战前英国针对德国法西斯主义的绥靖政策;而《上海孤儿》则综合发展了前两部小说的主题,把故事背景设定在上海租界这样一个英、日帝国主义侵华历史的时空交点,从流散的视角对英、日帝国主义侵华行径做了双重批判。
在这个“英国文学国际化”的时代[3](1),石黑一雄的日裔英籍双重身份尤为引人注目。石黑一雄于1954年生于日本长崎,5岁时随父母迁居英国,在家接受日本文化的熏陶,在学校受着纯正的、典型的英式教育。东西方双重教育背景使得他对两种文化既有部分认同,又有一定程度的疏离。正如石黑一雄本人所说:“我认为我是一个无根的作家。我既不是真正的英国人,也不是真正的日本人。在我身上没有明显的文化身份。”这也是他坚称自己是“国际主义作家”的原因。[4](58)正是这种既认同又疏离、既居于其内又处于外部的流散身份使他“拥有不同的思维方式,以及看待事物稍显不同的视角”[5](35)。独特的双重身份让他看待历史、反思过去更加全面、客观、公正,因为他“没有要为之代言、抑或作为写作对象的社会或国家”[4](58)。
流散,英文diaspora,源自希腊语,意指植物通过花粉的传播而繁衍生长。《圣经》中用来指上帝有意将犹太民族散布于世界各地的状态。20世纪80年代之后,经过文学文化研究派的语义重构,流散一词的内涵从流离失所的凄苦扩展至跨越文化的喜悦,其外延也随之从散居的犹太民族推至任何离开故土的民族和个人。童明教授据此认为,“任何跨民族的”“跨界的、旅行的”“翻译的、混合的形式”都具有“飞散性”。①[6](89−91)《上海孤儿》从多方面体现了石黑一雄看待事物的流散视角,反映了他流散的历史观。小说的背景上海租界,是多文化杂存、英日势力冲突的典型流散空间。小说人物班克斯、戴安娜以及山下哲都是旅居国外的流散人物。特别是通过生于上海租界、长于英国的主人公班克斯追寻民族“原罪”、解构“母亲”形象以及亲历日本侵华战争,石黑一雄表明了自己流散的历史观。流散的历史观,不以单一民族的意志来篡改、美化历史,而是透过人道主义精神,通过客观的叙述,为被压迫、被侵略民族的历史提供复现的途径。在《上海孤儿》中,作者表现了罕见的正视历史的勇气,不仅向人们揭示了英国向中国运送鸦片牟取暴利的历史, 而且对日本的武力侵华行径进行了无情批判。
一、班克斯的“原罪”:英国对华鸦片贸易
在西方及日本学者普遍遗忘甚至歪曲历史的背景下,石黑一雄的《上海孤儿》对英、日帝国主义侵略历史的反思和批判显得弥足珍贵。《上海孤儿》讲述了侦探克里斯托夫·班克斯在“有可能吞噬整个文明世界的大漩涡中心”,试图解开历史迷案的离奇经历。[7](147)男主人公班克斯的父亲是英国一家鸦片贸易公司的职员。9岁那年,他的父亲从家中消失。后来,他母亲也失踪。他被送回英国抚养,最终成了著名的大侦探。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为了揭开父母失踪之谜,班克斯回到了正遭受日本侵略的上海租界。上海这一流散空间重叠了他的记忆与现实,也成为他醒悟自己民族“原罪”的起点。
动身去上海之前的班克斯对鸦片贸易不明就里,他一直认为父母是反对英国在华鸦片贸易的斗士,所以一直以父母为“榜样”,“与罪恶作斗争”。下面是班克斯记忆中母亲因鸦片贸易而责骂公司卫生检查官的描述:
接下去母亲便开始滔滔不绝、语气激烈但又不失克制地指责起来。[……]正是因为整个英国[……]向中国大量进口印度鸦片,才给整个中华民族带来了极度痛苦和堕落。[……]
“先生,你难道不觉得羞耻吗?身为一名基督教徒,身为一名大英帝国的臣民,一个做错事还能感到良心不安的人,为这样一个公司服务你不觉得羞愧吗?告诉我,靠这种充满罪恶的财富生存,你不觉得良心不安吗?”[7](56−57)
在接下来的回忆中,班克斯却“不再有十分把握她是不是真的一字不差地对检察官说了那些话”[7](63)。他认为可能自己“把她说那些话的时间、地点、人物整个记错了。换句话说,那些言辞针对的根本不是卫生检查官,而是父亲,并且是在另外一个早上”[7](64)。显然,班克斯母亲激烈言辞所针对的对象不同,意义就会截然不同:若是针对卫生检查官,那么她则是在公开场合批判鸦片贸易;若是针对父亲,那么不过只是私下的反对罢了。根据班克斯的叙述,针对卫生检查官的可能性可以排除,因为“在我看来,就算她情绪再激动,也该能想到这些话多么不合时宜,多么容易招来耻笑。我不相信妈妈会糊涂到这种地步”[7](64)。我们甚至可以认为,班克斯的模糊叙述正说明他批判鸦片贸易的观点不过是内心想法的投射,因为他们家“‘赖以生存’的公司竟专门经营十恶不赦的行当”,对他的心灵“是个十足的折磨”[7](64)。
事实上,直到小说结尾处了解到事实真相之前,班克斯一直都是个主观性极强的人。从儿时开始便坚信父母是反对鸦片贸易的英雄,长大后重返战火频仍的上海依旧“刻舟求剑”般地坚信父母多年来一直被关押在以前的一所房子里,甚至将自己视为能够解决眼前这场世界大战危机的不二人选。透过自己模糊的主观叙述,班克斯将服役于英国对华鸦片贸易公司服役的父母摆在正义的一边。这样模棱两可、甚至时而颠倒是非的叙述,一方面为班克斯对故事(或者说历史)的主观性论断找到了开脱的理由,另一方面,这种似是而非的模糊叙述使文本产生了强烈的反讽意蕴,向读者表明了对鸦片贸易的尖锐批判。
小说中班克斯母亲对检查官或父亲的质问,“身为一名大英帝国的臣民,一个做错事还能感到良心不安的人,为这样一个公司服务你不觉得羞愧吗”[7](57),不禁让人联想起班克斯在战场上对那位日本上校的质问。在小说结尾处,我们同班克斯一起从菲利普叔叔那里得知,班克斯在伦敦的地位和优裕生活源于鸦片贸易所得的“肮脏财富”[7](321)。因此,班克斯母亲的质问“告诉我,靠这种充满罪恶的财富生存,你不觉得良心不安吗”[7](57)同样也适用于班克斯自身,同样是对班克斯自己的辛辣反讽。班克斯在对往事模糊回忆的过程中,一直站在母亲一边。所以,正如上文论及的,母亲的话其实是班克斯自己的心声。在小说结尾处得知自己的“原罪”时,他批判的矛头最终指向了自己。其实,从隐喻意义上来讲,班克斯象征了整个大英帝国。正如班克斯受益于英国在华鸦片贸易,英国经济的飞速发展靠的也是对中国等众多国家的殖民、侵略以及鸦片贸易。透过班克斯探寻自己“原罪”的心路历程,读者领会了隐含作者的反讽用意,跟随作者一起重访了那段帝国主义罪恶的侵略历史。
但西方人却往往没有班克斯(或石黑一雄)的这种“原罪”意识,他们通常刻意遗忘甚至美化自己的侵略历史,正如小说中的大多数西方人一样。罗兰∙巴尔特就曾指出,西方人习惯将中国人与吸食鸦片相联系[8](84),将中国人视作“东亚病夫”。但他们却从不曾扪心自问,不曾追责自己。千万中国人成为“病夫”的根源不正是英国在华的鸦片贸易吗?历史表明,中国也正是由于深受鸦片的毒害,才让野心勃勃的日本侵略军有了可乘之机。正是英国在华的鸦片贸易及其对日本侵华所实施的绥靖政策,将整个中华民族置于日军的铁蹄之下。小说中班克斯对自己罪恶的反省,实际上是对整个英国民族的批判。在上海租界这一流散空间内,结合日本侵华战争的亲身经历,班克斯追问了自己(象征意义上则是自己的民族)的历史“原罪”。从小说开始时表现出的主观模糊、不可靠的狭隘民族主义视角,到结尾处渐变为流散的国际主义视角,班克斯最终醒悟到了自己民族的“原罪”,从而实现了精神上的成长。
二、戴安娜的遭遇:上海外国租界的兴衰
从叙事空间来讲,《上海孤儿》故事发生的背景是在英国的伦敦和日本侵华战争期间的上海,但小说主要的故事空间却是上海。这里的“上海”主要有两层涵义:一是班克斯通过回忆描述的儿时生活的“国中之国”上海租界,二是班克斯成年后为了寻母而重返的“孤岛”上海②[9](27)。从某种程度上讲,我们可以将《上海孤儿》看作是一部上海租界的兴衰史。同时,班克斯对上海租界的回忆与对母亲的回忆相互交织。上海是他的出生地、“母”国,母亲失踪后班克斯便不得不被迫离开上海,多年后为了寻找母亲他又只身重返上海。可以说,对母亲的回忆就是对上海的回忆。母亲的人生际遇随着上海外国租界的兴衰或沉或浮,或风光无限或流离失所。鉴于此,母亲戴安娜的遭遇与上海外国租界的兴衰之间存在着不可分割的关联,因此也带有了象征色彩。
正如班克斯象征着英国对帝国主义“原罪”的主观歪曲和美化,我们也可以说,戴安娜的遭遇影射了英租界及英国势力由盛而衰的过程。最初,戴安娜随同丈夫来到上海租界,代表英国在华经营鸦片,英国在华势力盛极一时;之后她因丈夫失踪而被迫做了中国军阀的姨太太,此时英国只能借助军阀之手进行鸦片贸易;而日本侵华战争爆发后,她又跟随国民党流落重庆、转而被遣送香港,最终导致精神崩溃,此时英国势力完全退出中国。
从戴安娜的生命历程与地理位置的转变,可以反观上海租界英国势力的衰落与日本势力的兴盛。纵观她的生命历程:从贩卖鸦片到反对鸦片,再到重新做了贩卖鸦片的同谋(军阀的姨太太);纵观她的地理位移轨迹:从上海租界到战时陪都,最终回归到英国殖民地香港。戴安娜轮回的命运暗示,个人与社会、个人与历史密不可分。作为英国在华鸦片贸易公司的一员,她始终逃脱不了自己的英国身份与罪恶历史。同时,她的颠沛流离和精神失常也象征了英国在华势力的彻底衰落,其中最直接的历史原因便是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
从小说叙述层面上来讲,戴安娜从未成为一个独立的角色。她一直存在于主人公班克斯的回忆里。小说对她的描述都是透过班克斯的主观叙述完成的。她的形象由班克斯回忆里的“维多利亚时代”的美最终转变为扭曲而痴呆的丑。这种美—丑的根本性转变所具有的象征意义,我们可以从小说首尾两处班克斯对她的描写中窥见一斑:
在我整个成长过程中,我一直以一种客观冷静的态度认为妈妈很“美”。人们总是这么说她,而在我看来,“美丽”不过是张贴在妈妈身上的标签[……]。如今每当我凝望她的相片[……] 我总会被她那种传统的、属于维多利亚时代的美所震撼。[7](53)
她比我料想中瘦小得多,两边肩膀弓得厉害。[……]她的脸皱纹虽不是很多,但眼睛下面却又深深的两道眼袋,仿佛刀刻一般。可能因为某种伤病,她的脖子已经深陷入体内[……]。[7](277)
说母亲有着“传统的、属于维多利亚时代的”美,表明母亲是英国的象征,她的美正是班克斯对英国文化的期许。而小说结尾处“她比我料想中瘦小得多”则暗示着她并非班克斯回忆或者想象中那么伟大。班克斯对“母亲”形象的解构,也即对英国文化的质疑。他从回忆返回现实,寻到母亲的同时也发现了自己“原罪”的真相。母亲的“美”原来只是自己的一厢情愿。而自己能够独自解决大战危机的幻想,也成了对自身的辛辣反讽。连自己的母亲都难以保护,何谈拯救整个世界?
《上海孤儿》横跨的时段(除了1958年班克斯在香港与母亲最终见面之外)是20世纪初至1937年日本侵华战争爆发。这个时段正上演着日本与英美激烈较量的历史。上海租界的兴起源自于英国为首的欧洲帝国主义的贸易侵略,而它衰落于1937年日本的武力侵略。日本侵华战争使得上海租界成为一座“孤岛”。因此,可以说,日本的侵华战争直接改变了上海租界的命运,也改变了戴安娜的命运,导致二者的衰落。戴安娜后来之所以几易其主,颠沛流离,是因为作为个人,她势必与英国的在华势力、与历史的洪流一起沉浮。她流离失所的直接原因正是日本对华侵略,而她的大本营——英国在华鸦片贸易公司,以及由英帝国始作俑的上海租界,正是由日本侵华战争画上了一个句号。因此,上海租界成了英、日帝国主义罪恶行径的交点,也成了批判两国帝国主义侵略历史的流散空间。
三、山下哲的忏悔:英国人眼中的日本侵华战争
《上海孤儿》有两大场景,前半部是静谧安逸的伦敦,后半部是战火频仍的上海。西方评论家们大都把前半部视作现实主义,而把后半部看成与《无可慰藉》相似的超现实主义。笔者认为,小说后半部即使是班克斯的心理超现实主义想象,也是基于小说对日本侵华战争(更确切地说是淞沪战役)的现实主义描写。不管战场上的日本士兵是否是班克斯的儿时伙伴山下哲,小说对于他和班克斯一起经历的战争以及他对战争的忏悔都让读者身临其境并胆战心惊。
对于中日淞沪战役的惨状,小说通过英国人班克斯中立的流散视角这样描写到:
事实上,我常常感觉自己并非走在贫民区里,而是走在某个有无数房间的大厦废墟里。尽管如此,我还是会时时想到,脚下的碎片中不知埋藏了多少传家之宝,孩子的玩具,以及虽然简陋却备受家人珍爱的生活用品。每当这时, 我内心便会顿然愤慨万端,越发气愤那些给无辜民众带来如此厄运的罪魁祸首。[7](220)
这一段描述了正遭受战争摧残的上海,读起来令人震撼, 激起读者对侵略者罪行的愤慨。被战火“夷为平地”的贫民窟其实点明了英、日帝国主义的双重罪恶:先是英国的贸易侵略造就了这些贫民窟;继而日本的武力侵略毁灭了这些贫民窟以及里面的无数生命。班克斯在这里还只看到了被毁的房屋,接下来的经历却让他更加深刻地认识到战争带给生命的残酷。在寻找他自认为关押父母的房子的路上,班克斯亲历了中、日两个士兵的死亡过程:
一阵沉默之后,一个奇怪的声音穿过重重围墙传到我们耳边。它先是悠长、无力,像荒野中野兽的嘶鸣,最终变成放声大哭。随即又转为尖叫抽泣。接着那位伤者开始喊叫什么,听起来和起先那位濒死的日军士兵一模一样。由于处在极度疲倦的状态中,我恍惚觉得肯定是同一个人。正想开口对哲说这个人真是倒霉透顶,却突然意识到那人说的是中文,而不是日语。 想到这是两个不同的人令我不寒而栗。[7](235)
“没有国别民族的差异”的“死前号啕”体现了班克斯(和石黑一雄)的人道主义精神,同时也反映了他居于两个民族之间流散的双重视角。在他看来,侵华战争给中国和日本带来了同样的伤痛。不同的是,中国人民是受害者,而日本士兵却是咎由自取的侵略者。
亲历了残酷战争并身负重伤的山下哲在战役间隙和班克斯聊起了“恋旧”的话题。当听到班克斯说“人千万不可过于恋旧,老是怀念童年时光”的时候,山下哲反驳道:“能恋旧真好。它对我们非常重要。”“怀旧,意味着回忆过去。那个世界比我们长大面对的世界美好得多。回忆会促使我们向往美好世界重回身边。”[7](240)他还请班克斯帮忙转告他远在日本的儿子:“告诉他,我为国身亡。告诉他,好好对待妈妈。捍卫,创造一个美好的人间。”[7](239)在这里,山下哲在这里所说的恋旧其实不仅仅是回忆童年,而是要回忆“过去”。从个人角度来讲,过去是记忆,而从社会层面来讲,过去是历史,历史就是通过每个人的记忆得以保存的。让儿子记住父亲是“为国身亡”,或许不是将自己视为民族英雄,而是要儿子记住,侵华战争是整个日本民族对中国犯下的罪行。记住惨痛的历史,目的在于憧憬美好的未来,而这也正是山下哲对儿子“捍卫,创造一个美好人间”的殷切期望。通过同样是流散人物的山下哲的反思,小说不仅从历史角度描述了当时的日本侵华战争,而且还从现实角度警醒人们不要遗忘已成过去的历史,只有记住历史才有美好的未来。正如日本东亚历史文化学会会长纐缬厚所言,“妨碍[中日]两国人民自由沟通的最大问题还是历史问题。”[10](35)而作为“步入了现代国家的日本,应该对这场战争不断地进行检讨和反思”[10](10−11)。其实,对于帝国主义侵略历史,我们需要的不仅是作为侵略和被侵略双方的日本和中国的民族主义反思,更需要《上海孤儿》这样流散、客观的人道主义反思。
四、结语
《上海孤儿》带我们重访了1937年正遭受英国鸦片贸易和日本侵华战争双重侵略的中国。作为日裔英籍作家,石黑一雄透过自己独特的流散视角,选择从既是中心又是边缘的相对位置上对帝国历史进行审视和批判,揭露了英、日帝国主义相似的侵华罪行。历史表明,英、日对中国不同方式的侵略,不仅相互抗衡,而且相互纠缠、并形成因果联系:由英国牵头霸占的上海外国租界与英国在华的鸦片贸易紧密相关,而上海租界的兴衰则体现了英、日帝国主义在华势力的强弱对比。小说中的人物(班克斯、戴安娜以及山下哲)一方面是历史潮流中的个体,透过个人视角回溯社会历史,但另一方面却都带有象征色彩:通过渐渐接近鸦片贸易真相,流散人物班克斯揭开了一直被英国学者掩藏的英国对华鸦片贸易的“原罪”;戴安娜的命运则与上海租界这一流散空间密切相关,她的遭遇反映了英、日帝国主义在华势力的较量以及英国势力的衰落过程;山下哲对于历史重要性的强调,从反省日本侵华罪行上升到了流散的人道主义高度。另外,同石黑一雄一样,班克斯和山下哲都有生在上海、长在各自国度的流散经历,他们对两种文化既熟悉又疏离,正是这一有利视角让他们能够更加公允客观地再现、反思被遗忘和歪曲的历史。
历史是一面镜子,它映射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曾经有过的辉煌与苦难、荣耀与耻辱、成功与失败。反思和批判历史的目的在于教人以史为鉴。正如西班牙小说家乔治·桑塔亚纳所言,忘记过去就注定会重蹈覆辙[11](21);不尊重历史或歪曲历史,必将遭到历史审判和淘汰。
注释:
① Diaspora一词有流散、离散、散居等多种译法。童明教授新译“飞散”,因为他认为其他译法只传达了该词社会学、人类学范畴中的涵义,而飞散却能兼顾diaspora一词社会学派与文学文化学派的双重涵义,“唤醒词源的寓意,符合重构的新意,又可借比喻和犹太历史经验保持关联”(2007:91)。本文选择了“流散”这一更为学界熟知的译法。
② 陶菊隐认为“孤岛”这个名称很不恰当,因为租界的行政管理权握在包括日本帝国主义在内的列强手中,这个嵌在中国领土上的“国中之国”,在中日战争时期成了一个“中立国”,但并不是中国人的“孤岛”(2005:27)。
[1] 钟志清.寻觅旧事的石黑一雄[J].外国文学动态, 1994(3): 34−35.
[2] 邱华栋.石黑一雄: 寻觅旧事的圣手[J].文学月刊, 2009(9): 92−97.
[3] King, Bruce.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english literature [M].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07.
[4] Oe, Kenzaburo, Kazuo Ishiguro.The Novelist in Today’s World: A Conversation [C]// Brian W.Shaffer and Cynthia F.Wong (eds).Conversations with Kazuo Ishiguro.Jackson: University Press of Mississippi, 2008: 52−65.
[5] Swift, Graham, Kazuo Ishiguro.Shorts: Kazuo Ishiguro [C]// Brian W.Shaffer and Cynthia F.Wong (eds).Conversations with Kazuo Ishiguro.Jackson: University Press of Mississippi, 2008: 35−41.
[6] 童明.飞散的文化和文学[J].外国文学, 2007(1): 89−99.
[7] 石黑一雄.上海孤儿[M].陈小慰译.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1.
[8] Sim, Wai-chew.Globalization and dislocation in the novels of kazuo ishiguro.university of warwick [D].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2002.
[9] Barthes, Roland.Mythologies [M].Trans.by Annette Lavers St Albans: Paladin, 1973.
[10] 陶菊隐.大上海的孤岛岁月[M].北京: 中华书局, 2005.
[11] 纐缬厚.何谓中日战争[M].申荷丽译.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2.
Historical representation through a diasporic perspective: Double exposure of British and Japanese imperialist invasion into China in When We Were Orphans
DENG Yingling, WANG Fei
(Foreign Studies College,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1)
When We Were Orphans, the representative novel of the contemporary Japanese-born British writer Kazuo Ishiguro, is set in the Shanghai foreign settlements where the imperialist Britain and Japan met.Through a diasporic perspective, the novel reconstructs the 1930s China under the double invasion of British opium trade and Japanese military aggression.Characters in the novel are individuals involved in the historical events with historical significance.Based on a close-reading of the historical context of the novel, this essay analyzes the personal stories of Banks, Diana and Akira with the conclusion that, from the characters’ relative positions of being the center as well as the marginal, the novel reproduces the colonization history of China repressed by western scholars and criticizes the UK and Japan’s evil invasion of China.
Kazuo Ishiguro; When We Were Orphans; diasporic perspective; opium trade; invasion of China; historical representation
I106.4
A
1672-3104(2015)06−0141−05
[编辑: 胡兴华]
2015−09−10;
2015−10−28
湖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重点项目“石黑一雄小说的记忆叙事研究”(14A104);湖南省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个人记忆与社会历史——石黑一雄小说的历史叙事研究”(CX2014B182)
邓颖玲(1965−),女,湖南醴陵人,文学博士,湖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英美文学和叙事学;王飞(1983−),男,河北张北人,湖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英美文学和叙事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