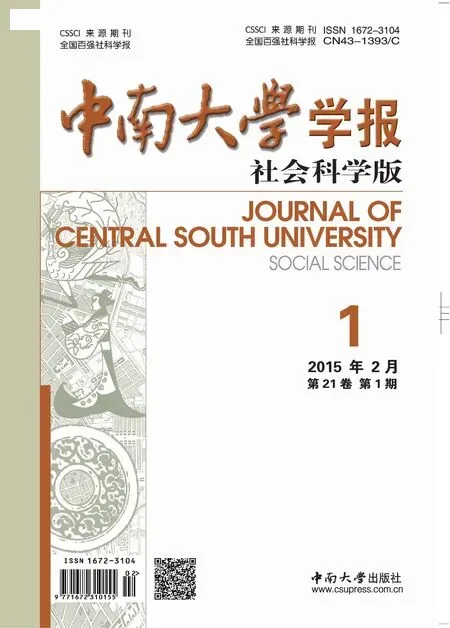梁武舍道事佛与唐代三教论衡
2015-01-21刘林魁
刘林魁
(宝鸡文理学院关陇宗教文化研究所,陕西宝鸡,721013)
梁武舍道事佛与唐代三教论衡
刘林魁
(宝鸡文理学院关陇宗教文化研究所,陕西宝鸡,721013)
梁武帝舍道事佛是中古思想文化史上的一大疑案,但此一说法真正被关注是在唐代。与其斤斤计较此说的真伪,不如从唐代宗教文化环境中考察其发生与功能。从现存文献来看,唐代帝王史臣在反思南北朝政教关系的潮流中,将梁武帝崇奉佛教与萧梁亡国联系起来,道教徒也乘势将此提升为佛教亡国论,但梁武帝舍道事佛并未被儒、道二教关注。唐初佛徒对儒家、道教的批判采取了不同的回应方式,梁武帝舍道事佛主要承担起了抨击道教的使命,但受儒、道联合批评佛教惯例的影响,此事同时具有了扬佛、抑儒、贬道的宗教功能。唐代佛徒对梁武帝舍道事佛的叙事突出了宗教对抗关系,这是对傅奕等道教信徒攻击佛教的响应。
唐初三教关系;梁武帝舍道事佛;弘法
天监三年(公元504年)四月八日梁武帝下诏舍道事佛,此为中古思想文化研究中的重要事件之一。然而,自20世纪以来,学术界对此事的真伪聚讼纷纭。或认为佛教徒为自张其教而伪造①,或认为基本可信②,或认为真假参半③。但不管持何种观点,有一种实情是学界有目共睹的。即,此一事件最早出现在唐初佛道辩论文献中。从发生学和传播学的角度来看,研究梁武帝舍道事佛与唐初三教关系的关联性,比单纯考证此事的真伪更为可行,结论也将更为客观。基于此一设想,本文从唐初宗教生态出发,尝试考察梁武帝舍道事佛一事最初传播的一些情况。
一、唐初儒道二教批判佛教思潮中梁武舍道事佛的缺席
梁武帝舍道事佛一事,在唐初高祖、太宗、高宗三朝的三教论衡中频繁出现。佛教徒征引此事,意在为佛教争胜。依照常理,儒、道两家理应有所回应。然而,仔细搜检此一时期的文献,频繁征引者仅集中在佛教一方,正史、文集、小说以及道教文献中,似乎都没有提及此事。这是一个奇特的现象。
舍道事佛是梁武帝众多崇佛举措之一。对梁武帝舍道事佛的评述,既关联道教与佛教的优劣高低,又牵涉梁代乃至整个南北朝政教关系、宗教政策的得失利弊。恰恰就在唐初,随着政权的建立与稳定,唐王朝掀起了一股反思南北朝政权兴亡根由的潮流。这股反思潮流波及政教关系,梁武帝崇奉佛教就成了批判的焦点。
武德四年(公元621年),高祖李渊质问法琳等僧人,说“弃父母之须发,去君臣之章服,利在何门之中,益在何情之外”[1](283上)。此一质疑透露出唐王朝对佛教与世俗政权关系的反思。至贞观二年(公元628年),太宗言:
梁武帝父子志尚浮华,惟好释氏、老氏之教……未尝以军国典章为意。及侯景率兵向阙,尚书郎已下,多不解乘马,狼狈步走,死者相继于道路。武帝及简文卒被侯景幽逼而死……此事亦足为鉴戒。朕今所好者,惟在尧舜之道、周孔之教……[2]
太宗联系梁武帝父子“志尚浮华,惟好释氏、老氏之教”的思想取向与“被侯景幽逼而死”的政治结局,从而认识到玄佛之学不能作为治国思想。于是,他以史为鉴,选择儒家作为治国之道。
至贞观二十年(公元646年),太子少保萧瑀请求出家为僧,太宗又一次谈及梁武帝崇佛的历史教训:
至于佛教,非意所遵,虽有国之常经,固弊俗之虚术。何则?求其道者,未验福于将来;修其教者,翻受辜于既往。至若梁武穷心于释氏,简文锐意于法门,倾帑藏以给僧祇,殚人力以供塔庙。及乎三淮沸浪……子孙覆亡而不暇,社稷俄顷而为墟,报施之征,何其缪也
太宗虽然认可佛教作为“有国之常经”的现实存在,却又清醒地意识到佛教“弊俗”之本质。对佛教理论虚妄的评判,是基于梁武父子崇奉佛教却丧身亡国的历史教训。在太宗看来“穷心释氏”的梁武父子不能得善果善报,连江山都丢失了,佛教因果报应之说也就根本不可信了。
太宗虽然已经将梁武父子崇佛与梁朝覆亡联系起来,但尚未明确得出崇佛必然亡国的论断。唐初的崇佛亡国论,是在史臣笔下形成的。魏征《隋书》云:
普通二年(公元524年)五月,琬琰殿火,延烧后
宫三千余间……是时帝崇尚佛道,宗庙牲牷,皆以面代之。又委万乘之重,数诣同泰寺,舍身为奴,令王公已下赎之……天诫若曰,梁武为国主,不遵先王之法,而淫于佛道,横多糜费,将使其社稷不得血食也。天数见变,而帝不悟,后竟以亡。及江陵之败,阖城为贱隶焉,即舍身为奴之应也。[4](620)
梁武暮年,不以政事为意,君臣唯讲佛经、谈玄而已……其后果致侯景之乱。[4](623)
此外,李延寿对武帝的评价,与《隋书》如出一辙。其《南史》也说,武帝“留心俎豆,忘情干戚,溺于释教,弛于刑典”,最终导致“悖逆萌生,反噬弯弧”,并“卒至乱亡”。[5]
与太宗相比,唐初史臣不但将梁武父子与佛教的关系提升为具有普遍警醒意义的崇佛亡国论,而且更关注梁武帝崇佛的具体行为。这些行为主要有:宗庙牲牷以面代替、舍身同泰寺为奴、溺于释教不以政事为意。
唐初上层社会的这种历史批判,明显立足于儒家政教观。这种观点唐前就已存在。梁武帝朝的荀济,撰写《论佛教表》批评武帝崇佛,他说:
岁时禘祫,未尝亲享。竹脯面牲,陵诬宗庙。违黄屋之尊,就苍头之役。朝夕敬妖怪之胡鬼,曲躬供贪淫之贼秃。耽信邪胡,谄祭淫祀。[1](129上)
这里就以面食祭祀宗庙、舍身佛寺为奴两件事情为武帝崇佛之代表。北齐魏收《魏书》批评萧衍崇信佛教,也叙述了四件事情:兴建佛寺、以身施同泰寺为奴、令王侯子弟受佛诫、祭祀祖祢不设牢牲[6]。荀济之上疏,言辞激烈,用意甚殷,然有悖于梁朝上流社会之崇佛热情,最终引火烧身,“梁武将诛之,遂奔魏”[7]。魏收之批评,一如其“岛夷萧衍”之称,带有南北对立政权之间相互攻击的意图。虽然荀济、魏收等人从政权利弊角度对萧衍崇佛进行了批判,但都没有将这种危害明确上升到亡国的高度,也未在当时的思想界产生大的影响。相比较而言,这种梁武帝崇佛亡国论,是唐初上层社会反思南北朝政教关系的成果。
唐初形成的梁武帝崇佛亡国论,促使政权在宗教政策上对佛教采取限制、防范措施,如高祖武德九年(公元626年)下诏,令“京城留寺三所,观二所。其余天下诸州,各留一所。余悉罢之”[3](17)。不过,崇佛亡国论影响所及,不限于宗教政策。道教徒也趁着上层社会的这股反思潮流,掀起了排佛高潮。武德七年(公元624年),傅奕上疏十一条请除去释教:“请胡佛邪教,退还天竺。凡是沙门,放归桑梓。”[8]理由则是“降自牺、农,至于汉、魏,皆无佛法,君明臣忠,祚长年久。汉明帝假托梦想,始立胡神……洎于苻、石,羌胡乱华,主庸臣佞,政虐祚短,皆由佛教致灾也。梁武、齐襄,足为明镜”[3](2715−2716)。这种无佛则“祚长年久”、有佛则“政虐祚短”的说法,将崇佛亡国之说提升为佛教亡国论。证明这种观点的证据之一,就是唐初帝王史臣热衷探讨的梁武帝崇佛亡国一事。傅奕之排佛观点并没有落实为惨烈的灭佛运动,但附和傅奕者不在一二。
由帝王史臣掀起的反思前代政教关系的潮流,形成比较清晰的崇佛亡国论。这一观点经过道教徒的推波助澜,发展成了信奉佛教则“政虐祚短”的排佛言论。舍道事佛在梁武帝诸多崇佛举措中并不具有典型性,因而也就不会出现在帝王史臣以及道教徒的批判视野中。
二、佛教护法热潮中梁武舍道事佛叙事的功能
梁武帝对于佛教发展推波助澜之功,唐初佛徒心知肚明。抹杀梁武帝的奉佛之功,将使南朝佛教大大失色。但唐初佛徒要记载、传诵梁武帝的奉佛之举,势必先要与当时盛行的诸种崇佛亡国论乃至佛教亡国论辩驳。因此,梁武帝舍道事佛一事被唤起记忆,进入三教论衡话题,将与佛教界弘法护教的整体活动密切相关。
针对以梁武帝为标本得出的崇佛亡国论、佛教亡国论,佛教界采取四种路线进行了反击。其一,正面宣扬历代王公大臣之奉佛举措。释法琳在《辩正论》中专列“十代奉佛篇”,“略陈十代君王、三公宰辅、通儒博识敬信佛教者”[9](502下)。这种反击,绕过了傅奕有佛则政虐祚短的观点,延续了唐太宗佛教为“有国之常经”的说法,宣扬上层社会信仰佛教的传统,从而达到反驳傅奕“胡佛邪教退还天竺,凡是沙门放归桑梓”的目的。其二,以史为证,说明佛教入华前后中土政权都有“虐政”和治世。释明概《决对傅奕废佛法僧事》、李师政《内德论》既是如此。此种方法,常常以事实证据反驳佛教亡国论使用的不完全归纳法,由此而达到对佛教亡国论的否定。其三,辨别佛教与政权的不同功用。如李师政云:“盛衰由布政,治乱在庶官。归咎佛僧,实非通论。且佛唯弘善,不长恶于臣民。戒本防非,何损治于家国。若人人守善,家家奉戒,则刑罚何得而施,祸乱无由而作。”[1](187下)其四,以佛教报应说解释政权更替。如道宣说:
夫运业废兴,天之常数。禅让放诛,有国变通……齐、宋诸帝所以重佛敬僧者,知帝位之有由,故衔恩而酬厚德也。又知帝位之无保,故行因而仰长果也。昔因既短,不可延以万年,故有梁之受禅也。今因未就,不可即因而成果,故受报于未来也。[1](131中)
道宣在中土固有的命数说中融入佛教因果报应之说。他说,帝王崇信佛教,实为感恩报德,是对昔日行善造就今日登上帝位的前因的回报。前因不可永存,今果也不会永久,所以王位“不可延以万年”;今日“重佛敬僧”之因尚未“即因而成果”,只能将来受报,因而会出现“禅让放诛”。按照此种说法,大凡位及九五之尊者,必得奉佛。一则因获得帝位而需以之衔恩酬德,二则为了来世有更大的福报。因此,亡国非帝王崇佛所致,崇佛是获得善报的长远准备。
不过,佛教频繁征引的梁武帝舍道事佛一事,并不在以上四种反击路径之内。这四种反击,要拆散帝王史臣在佛教与政权盛衰之间建立的关联性,并没有涉及佛教与道教的关系问题。自魏晋以来的三教论衡,道教常常借助儒家理论来攻击佛教。佛教在对付儒道联盟时,对儒家常常耐心而谨慎地劝导,对道教则以直接而尖刻的攻击。梁武帝舍道事佛一事,似乎是佛教徒用来攻击道教的一个历史证据。
梁武帝《敕舍道事佛》中有:“老子、周公、孔子等……为化既邪,止是世间之善,不能隔凡成圣。其公卿百官,侯王宗室,宜反伪就真,舍邪入正。”[1](112上)此数句为梁武帝舍道事佛诸文之核心思想。舍道事佛若按照这层意思,应该完整表述为“舍儒、道事佛”。那么,在唐初佛教徒的表述中,梁武帝是舍道事佛,还是舍儒、道事佛?或者说,《敕舍道事佛》是回应儒家?还是回应道教?抑或二者兼而有之?
唐初佛教撰述中收录萧衍舍道事佛一事者,主要有法琳《辩正论》,道宣《集古今佛道论衡》、《广弘明集》,道世《法苑珠林》等著作中。此数部佛教著作,常常将诸多文献汇总起来表述一定的宗教态度。从这些文献的整体倾向上,可以看到唐初佛徒对梁武帝舍道事佛一事弘法功能的定位。
《辩正论》共8卷12篇。这12篇文章[9](490中),按照内容可以分为3类。第一,叙佛教为“有国之常经”。“十代奉佛篇”,列举两晋至唐之帝王、三公、宰辅、通儒等敬奉佛法的故实。第二,抨击道教。“气为道本篇”,辩明道教的一般信仰。“出道伪谬篇”,论道经、道法虚妄荒谬。“历世相承篇”,抨击道教经典。第三,宣扬佛法精妙深远,优于道教。“三教治道篇”论儒、释、道与治国的关系,扬佛教于道教之上。“佛道先后篇”论佛教产生于道教之前。“释李师资篇”论佛为老子之师。“十喻篇”辩释迦与老子的高卑优劣。“九箴篇”力辩奉佛非是迷惑。“信毁交报篇”记信佛与毁佛的报应故实。“品藻众书篇”,论佛教典籍、教义优于中土。“归心有地篇”说明放弃道教信仰、归心佛教为必然选择。
《辩正论》是武德九年(公元526年)针对清虚观道士李仲卿《十异九迷论》和刘进喜《显正论》而撰写。李、刘之文,曾对佛教进行全面抨击,并上达高祖。因此,《辩正论》“对儒家礼仪政纲贬损不多”,集中在“三教治道篇”和“品藻众书篇”中。对道教则“大加鞭挞,列数种种事例,指责道教剽窃佛教”[10]。梁武帝舍道事佛的文献,收在《辩正论》“归心有地篇”。从《辩证论》的总体倾向来看,法琳以梁武舍道事佛抨击道教意图甚为明了。
《集古今佛道论衡》与《广弘明集》都是道宣汇编的佛教弘法文献集。前者成书稍早于后者,两部著作的弘法思想又有明确的一致性,因而参照《集古今佛道论衡》的选文录事,即可知晓梁武帝舍道事佛的宗教功能:
《集古今佛道论衡》卷1:后汉明帝感梦金人腾兰入雒道士等请求角试事一,前魏时吴主崇重释门为佛立塔寺因问三教优劣事二,魏陈思王曹植辩道论附,晋孙盛老聃非大贤论附,晋孙盛老子疑问反讯附,元魏君临释李双信致有兴废故述其由事三,宋太宗文皇帝朝会群臣论佛理治致太平事四,魏明帝登极召沙门道士对论叙佛道先后事五,梁高祖先事黄老后归信佛下敕舍奉老子事六,北齐高祖文宣皇帝下敕废道教事七。[11]
此为《集古今佛道论衡》卷1辑录的文献。其内容大致分为两类:破斥道教,张扬佛教于儒、道之上。扬佛于儒、道之上者,有吴主孙权事、宋文帝刘义隆事,仅占整卷内容的20%,其余80%为破斥道教者。从这一比例来看,梁武舍道事佛以攻击道教为主。
释道世编纂《法苑珠林》共100篇。梁武舍道事佛出现在第62篇“破邪篇”。此篇又分3部分:述意部、引证部和感应缘。述意部总述一部大意,引证部广引佛典为证,感应缘广引事实为证。武帝舍道事佛出现在“感应缘”中。“感应缘”略引六验:
辩圣真伪一,邪正相翻二,妄传邪教三,妖惑乱众四,道教敬佛五,舍邪归正六。[12]
“辩圣真伪”中收录:《列子》中太宰嚭问孔子圣人、《吴主孙权论佛化三宗》《宋文帝集朝宰叙佛教》等事件。这些事件证明佛陀为大圣,佛教优于儒、道二教。“邪正相翻”至“道教敬佛”四类都是针对道教的应验记。“舍邪归正”则包括:梁代萧衍和萧纶舍道归佛、北齐高洋禁绝道法、唐初禁绝道经《三皇经》、晋释道融辩胜师子国婆罗门、北魏昙谟最辩胜道士姜斌、晋道教徒陈道慧游地狱、唐释昙琼劝化李氏宗族舍道归佛。是则,从“舍邪归正”感应类文献看,释道世以梁武帝舍道事佛斥责道教是不容置疑的。
由以上分析可见,在应对唐初帝王、史臣、道教徒的抨击中,佛教界掀起的弘法热潮并没有完全失去理智。佛徒们依然继承前代弘法的经验,将道教与儒家区别对待,有分别、有针对地加以回应。针对儒家的回应,集中在切断佛教与亡国之间的关联性。针对道教,则是无情痛击,并在打击道教中抬高佛教。佛教徒于弘法热潮中叙述的梁武帝舍道事佛一事,包含了佛优道劣的价值评判和弘扬佛法、禁绝道教的宗教意图。此一叙述不管其本源是否真实,总能增强佛徒的宗教信心和自豪感,满足他们的宗教期盼和弘法意愿。不过,对于佛教徒的这一回应、挑战,道教一方的失声不语倒是令人困惑!
三、三教论衡对舍道事佛叙事的影响
唐初释法琳《辩正论》卷8“归心有地篇”最早完整收录梁武帝《舍道事佛疏》《敕舍道事佛》和邵陵王萧纶《遵勅舍老子受菩萨戒启》、萧衍《敕答邵陵王》等文献。这四篇文章的最大特点,就是大量使用佛教有关宗教关系的词语“邪”“正”“外”等。
佛教典籍中,“邪”指邪曲,“正”指中正。一切法随顺自性清净者,为“内”、为“正”;若诸法违逆此理,则为“外”、为“邪”。这四篇文章中,共计使用“邪”字9个、“正”字7个、“外”字5个。其中,“正”的涵义毫无疑问是指代佛教的。“邪”的用法较为复杂,有时“邪”指代道教,有时兼指儒、道二教,如萧衍《舍道事佛疏》:“弟子经迟迷荒,耽事老子,历叶相承,染此邪法……老子、周公、孔子等,虽是如来弟子,而为化既邪……”[9](549中−下)
在中土语境中,“邪正”指邪恶和正直。其参照物是社会伦理规范和政治秩序,如孔子评价《诗经》则云“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邪”字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极其严厉的批判色彩。葛兆光说:
在古代中国,“妖”常常与“邪”、“淫”、“乱”这样的一些词语互通,也常常与以下这几种行为相连,如反叛朝廷犯上作乱、自行祭祀妄立神鬼、违背伦常男女淫乱,这些行为的直接社会后果就是导致秩序之“乱”。“淫”为“邪”、“邪”为“妖”,而“妖”则为“乱”,“乱”之一字,从广义上说,就是在伦理规范和社会构建被破坏时,家、共同体、帝国中产生的无秩序。[13]
佛教“邪”“正”之分,在于宗教标准,“邪”即可以称呼与佛教对立的九十六种外道,也可以称呼佛教内部的不同派别,它具有相对性。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邪”“正”,却是以现有的占统治地位的国家政权以及为维护此一政权的伦理道德为标准。它具有一定的绝对性和延续性,凡危害政权稳定的派别和思想意识都可以称为“邪”。梁武帝舍道事佛时,称儒教、道教为“邪”,是否为当时的中国社会普遍接受呢?
唐前三教论衡文献中,“邪”“正”的用法大致有两种情况。第一种,“邪”指代一切与佛教不同的观念、做法。这一种用法非常普遍,如:
佛地所知者,得善之正路;凡夫所知者,失善之邪路。凡夫得正路之知,与佛之知不异也。(沈约《佛知不异众生》)[1](252下)
此外道之邪见,岂可御瞿昙之正法。(张缅《答释法云书难范缜神灭论》)[14](67中)
沈约说凡夫之“邪路”是与佛教之“正路”相对而言。张缅说范缜《神灭论》为“外道之邪见”,无法抵御佛教“正法”之反驳。此二人正、邪之分辨,与佛教一般理念无差别。
第二种是佛、道二教互指对方为“邪”。《高僧传·帛远传》说道士王浮与沙门帛法祖互争佛、道之“邪正”,这是“邪”“正”专指佛、道二教的最早的文献。此后多有此类用法。如道教著作《三破论》云:“盖闻三皇、五帝、三王之徒,何以学道并感应,而未闻佛教,为是九皇忽之?为是佛教未出?若是佛教未出,则为邪伪,不复云云。”[14](51上)佛徒释玄光《辩惑论》云:“闻道诸经,制杂凡意,教迹邪险。”[14](48上)
虽然称道教为“邪”者南朝大有人在,然而现存梁武帝著作中的“邪”字多与佛教之“正”相对而言。至少就目前所见文献而言,除了舍道事佛诸文献外,梁武帝没有用“邪”来指代道教。故而,大致可以做这样的推测:从南朝宗教文化背景来看,梁武帝在舍道事佛诸文献中称道教为“邪”的可能性或许有,但就现存梁武帝本人的文献而言,称道教为“邪”者从未出现。至于称“周公、孔子”为“邪”者,不管是梁武帝个人文献还是南朝三教论衡文献,都没有丝毫证据证明其有可能。
梁武帝舍道事佛诸文献之“邪”“正”宗教关系论的强化,与唐初三教论衡息息相关。唐初攻击佛教亡国的道教徒傅奕,频频使用“妖”“邪”来斥责佛教:
这项活动终于把我和我太太带到了你们这片伟大非凡的国土上,我从心底里感谢你们。今天我们尚处在数字革命的初级阶段。也许历史刚刚完成了第一章,接下来的章节,会更加深刻地影响我们如何理解自身的人性,进而影响我们的文学和我们所有的艺术形式。此时此刻,这些新章节正在书写之中。小说还会继续存活下去,小说家会在这种巨大的信息风暴当中找到一个静止的中心,严肃小说家将在这个中心,继续探究人性,继续研究所有的这些真相以及谎言。
(周武帝)既除妖邪之教,惟务强兵。[1](125下)
(佛图澄)翻三玄妙旨,文饰邪教。[1](126中)
请胡佛邪教,退还天竺。[1](160下)
搢绅门里,翻受秃丁邪戒。。[1](160中)
佛生西方……盖妖魅之邪气。[1](163中)
佛是妖魅之气,寺为淫邪之祀。[1](189中)
傅奕对佛教的攻击中充满了“妖”“邪”等字眼。如前所论,“妖”“邪”“淫”“乱”立足于伦理规范和社会构建时,是对破坏“家、共同体、帝国”的异端宗教、文化、势力的称谓。虽然傅奕的这些言词,等同于辱骂、诬蔑,毫无学术理性可言,但却对佛教极具有杀伤力。佛教徒对傅奕的这些攻击极为反感,也积极响应维护佛教。以“邪”攻击道教、以“正”自称,在唐初佛教徒的许多文献命名上就突出表现出来。如:释法琳为回应道士傅奕《减省寺塔废僧尼事十有一条》而作《破邪论》,为回应道士李仲卿《十异九迷论》、刘进喜《显正论》而作《辩正论》;道宣《广弘明集》分10篇辑录佛教文献,第一篇即“归正篇”。
由此言之,梁武帝舍道事佛诸文献中“邪”“正”的大量使用,应该有唐初三教论衡中佛教徒增益、强化的可能。这一点,在法琳之后道宣《集古今佛道论衡》《广弘明集》等节录梁武舍道事佛诸文献中,可以得到印证。法琳《辩正论》中“道有九十六种,唯佛一道是于正道。其余九十五种,皆是外道。朕舍外道,以事如来”一句中,“皆是外道”《广弘明集》作“皆是邪道”;“朕舍外道,以事如来”,《集古今佛道论衡》作“朕舍邪外,以事正内,诸佛如来”,《广弘明集》作“朕舍邪道,以事如来”。道宣可以改“外”为“邪”,道宣之前的佛教护法斗士沙门法琳也可能有同样的举措。此外,从行文逻辑来看,“老子、周公、孔子等,虽是如来弟子,而为化既邪,止是世间之善,不能隔凡成圣”的第一要义是三教同源且佛优于儒、道,“为化既邪”四字令此句语义不畅。如果“如来弟子”“老子、周公、孔子”等“为化既邪”,那么,如来“为化”何以能正?如果删掉“为化既邪”四字,似乎句意全通。虽然不能确定舍道事佛诸文原作是否全部用“外”指代道教,但法琳、道宣等佛教徒的节录,改造原文、突出道教为“邪”,应该可以肯定。
而舍道事佛诸文中称“周公、孔子”“为化既邪”,也与唐初佛教徒的宗教关系论存在某种联系。道宣《广弘明集》汇集了有关唐初三教论衡的诸多文献。其《归正篇》“明佛为大圣,凡俗攸归,二仪三五,不足师敬”[1](97中)。“二仪”,指天地;“三五”,即三皇五帝。“二仪三五,不足师敬”者,即儒家道教不值得敬奉。《归正篇序》中,道宣认为,邪正之分,在印度为佛教与九十六种外道之分,在中土则为佛教与儒、道之分。至于“鲁邦孔氏”、“楚国李公”“匪称教主,皆述作于先王;赞时体国,各臣吏于机务”[1](97下−98上)。道宣的宗教关系论,虽然没有直接称“孔、老”之教为“邪”,但其逻辑来分析,要强调佛教之“正”,势必会肯定儒、道之非“正”。而且,道宣之“彼孔、老者,名位同俗,不异常人,祖述先王,自无教训”,与梁武帝之“老子、周公、孔子等……止是世间之善,不能隔凡成圣”,用意大致接近。虽然三教论衡逼迫佛教徒对儒、佛之关系表态、定位,但在中国这片文化土壤上,佛教徒绝对不可能公开指责儒家为邪教。佛教徒的这种局促、困惑在道宣《归正篇序》中留下些许痕迹。而现存梁武帝舍道事佛诸文献,很可能就是佛教徒这种潜在的宗教关系论的外化。
梁武帝舍道事佛原文面貌如何,已不得而知。但在弘法护教热情中,为了完成打击道教、抑制儒家的意图,佛教徒对此一事件的叙述做了有利于自身的修饰和调整。其一,增益“邪”“正”“外”等词突出道教之邪妄、佛教之真正,以表明佛道正邪、优劣之争早在南朝就已有定论。其二,增益了“周公、孔子”“为化既邪”等意思,以便在打击道教的同时抑制儒家。这两种调整,前者比重大于后者,态度明确于后者。这种对于儒家抑制的隐约曲折,表现在对此一事件的称谓上,从来没有敢于表达“舍儒、道事佛”的意思。正是因此这种欲言又罢、躲躲闪闪的做法,令后代学者对其称周、孔为邪之说产生了种种质疑。
四、结语
综前所论,梁武帝舍道事佛一事与唐代三教论衡密切相关。他为佛教徒期望的帝王弘护佛教和排斥道教提供了最为直接的证据。从现存记述梁武帝舍道事佛的文献来看,不但无法证明梁武帝舍道事佛的历史真实性,而且还可以毫不意外地发现其与唐初佛徒的宗教关系思想非常接近。唐代皇室尊老子为始祖和崇奉儒家的国策,致使佛教徒在三教论衡中对儒释道宗教关系的陈述有所避忌。同样,梁武帝舍道事佛的记述中既有“老子、周公、孔子等”“为化既邪”,又有“止是世间之善”,因而,梁武帝舍道事佛一事对南朝宗教关系史的研究价值有限。其更大的学术价值,应该是在唐代三教论衡或者三教关系史上。
注释:
① 详见:内藤龙雄《梁武帝舍道非史实性》《印度学佛教学研究》第五卷第二号,第490-491页,东京:日本印度学佛教学会,1957年。太田悌藏,《梁武帝舍道奉佛疑》,第417-431页;《结城令闻教授颂寿纪念论文集》,东京:大藏出版社,1964年。鎌田茂雄著、关世谦译《中国佛教通史》卷三第三章《南朝的佛教(二)梁·舍道归佛文的问题点》,高雄:佛光出版社,1986年,第202-204页。
② 任继愈等《中国佛教史》(第3卷)认为“从有关史书的记载来分析,个资料还是可信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第16页)。谭洁《梁武帝天监三年发菩提心“舍道”真伪辨》(《世界宗教研究》,2010年第3期)认为,梁武帝舍道事佛是佛道二教斗争的结果,之所以出现时间、人物上的衔接问题,是因为收录此文的《辩正论》屡遭禁毁,造成了文献上的相互抵牾。
③ 刘林魁《梁武帝舍道事佛考辨》(《学术探索》,2007年第5期)认为此事不伪,应发生在大同后期。赵以武《关于梁武帝“舍道”与“事佛”》(《嘉应大学学报》,2000年第1期)认为天监十六年舍道,天监十八年事佛。丁红旗《梁武帝天监三年“舍道事佛”辨》(《宗教学研究》,2009年第1期)认为梁武帝天监三年不可能舍道事佛,若舍道事佛也在大通元年以后。
[1] 道宣. 广弘明集[C]// 大正藏·第52册. 台北: 新文丰出版公司, 1985.
[2] 吴兢. 贞观政要[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8: 195.
[3] 刘昫. 旧唐书[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5.
[4] 魏征. 隋书[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3.
[5] 李延寿. 南史[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5: 226.
[6] 魏收. 魏书[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4: 2187−2188.
[7] 李延寿. 北史[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4: 2786.
[8] 释彦悰. 唐护法沙门法琳别传[C]// 大正藏·第50册. 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 1985: 198下.
[9] 沙门法琳. 辩正论[C]// 大正藏·第52册. 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 1985.
[10] 陈士强. 大藏经总目提要·文史藏二[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8: 363.
[11] 道宣. 集古今佛道论衡[C]// 大正藏·第52册. 台北: 新文丰出版公司, 1985: 363中−下.
[12] 释道世. 法苑珠林校注[M]. 周叔迦, 苏晋仁校注. 北京: 中华书局, 2003: 1647.
[13] 葛兆光. 屈服史及其它: 六朝隋唐道教的思想史研究[M]. 北京: 三联书店, 2001: 120.
[14] 僧佑. 弘明集[C]// 大正藏·第52册. 台北: 新文丰出版公司, 1985.
On Emperor Liang Wu abandoning Taoism to Buddhism Three-religions Debate in the Tang Dynasty
LIU Linkui
(Institute of Guanlong Religious Culture, Baoji University of Arts and Science, Baoji 721013, China)
It is a great mystery in the history of medieval culture that Emperor Liang Wu adandoned Taoism, which, however, became a special concern in early Tang Dynasty. The article proposes that, rather than commenting on whether the event was true or false, a better way of working out the mystery is to investigate its happenings and functions in the religious and cultural context of Tang Dynasty. Judging from the existing literature, emperors and ministers connected Liang Wu’s Buddhism worship with the national subjugation, which was taken advantage by Taoists who propagated that Buddhism resulted in the subjugation. However, the event itself of Liang Wu’s abandoning Taoism to Buddhism has not been paid any attention to by either Confucianists or Taoists. In early Tang Dynasty, Buddhists responded in a different way to both Confucianist and Taoist criticisms, believing that the event itself was undertaking the mission of attacking Taoism. But influenced by the practice that Confucianism and Taoism collaborated in criticizing Buddhism, the event also functioned in glorifying Buddhism, suppressing Confucianism and diminishing Taoism. The Buddhists’ narration of the event in Tang Dynasty highlighted the adversial relations among the three religions at the time, and the event was a response from Taoists like Fuyi.
B92
A
1672-3104(2015)01−0234−06
[编辑: 颜关明]
2014−03−12;
2014−12−16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唐代三教论衡及其文学影响研究”(12XZW003);宝鸡文理学院科研项目“西魏北周三教论衡与隋唐宗教文化研究”(2K14016)
刘林魁(1972−),男,陕西宝鸡人,文学博士,宝鸡文理学院关陇宗教文化研究所研究员,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佛教与中国文化
Key: three-religion relationships in the early Tang Dynasty; Emperor Liang Wu abandoning Taoism to Buddhism; promote Buddhis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