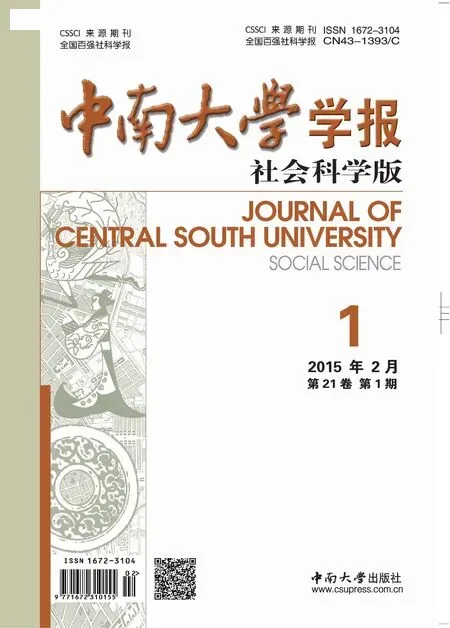论张爱玲的女性意识与价值体验
2015-01-21王攸欣
王攸欣
(中南大学文学院,湖南长沙,410083)
论张爱玲的女性意识与价值体验
王攸欣
(中南大学文学院,湖南长沙,410083)
张爱玲具有突出的女性意识,在西风东渐的中国文化现代性进程中,她因其个人的特殊经历和作为女性的生存体验,再加上在英式教育背景中培养起来的具有突出的个人主体意识的理性反思,寻找不到人生的价值根基,强烈体验女性乃至人的价值虚无感。所以她的女性书写弥漫着阴郁、逼仄、无望的苍凉氛围。张爱玲缺失审美超越性追求与自由体验,这是理解张爱玲创作整体审美风格的关键。
张爱玲;女性意识;价值体验;虚无
一、引言
张爱玲是现代中国文学史上女性意识甚为突出的作家,其女性价值体验和生存展示极具特点:一方面似乎相当精微、颇为逼真地显示了现代处境中中国女性的真实生存状态,并着意表达了其独特的性别体验和独立的价值立场,也有着某种程度的深刻反思;另一方面又相当程度地扭曲了女性的生存价值取向和体验,甚至颠覆了女性生存的价值基础,带给读者一种荒凉的价值虚无感。同时,她希望在这种虚无感上创构出自己的价值体验世界,虽不乏敏感、细腻、自尊的特点,却终究是一种较为阴郁、逼仄、无根的世界。这是她作为一个女性作家的风格和成就所在,也可以说是她自身生存之拘囿。当然,她自己也在反思着这种拘囿,在某些文本中表现出突破传统女性生存样式的努力,其理性化的倾向相当突出,尽管这种努力既有成功,也有失误。正是在这种努力中展示她特殊的文学生存。以往研究者对其女性意识有所分析,也有文本解读甚为出色者,如林幸谦的两部著作《荒野中的女体》《女性主体的祭奠》,都对张爱玲女性主体意识及其价值体验、女性书写有相当深入的探讨。①这些研究往往运用女性主义的理论,揭示了某些女性书写的特征,但又有着对深层人性特征的遮蔽,对张爱玲特定的价值取向的形成逻辑和生存体验探析得还不够细致深入,所以在这方面尚有足够开拓的空间。本文在笔者《路翎张爱玲小说审美内蕴比较论》对张爱玲小说之女性书写及价值特征有所阐述的基础上,力求进一步探讨其价值体验、自觉的反思以及女性书写中显示出的不同生存探索方向。[1]
二、张爱玲价值取向的文本投射
《小团圆》(1975)是张爱玲晚年作品,也是一部极为少见的真诚的自传体小说——小说一词恐容易引人向虚构性方面过分联想,所以毋宁说是自传性文本,其真实性甚至可能超过一些所谓的回忆录或自传。固然,就人类大脑的神经生物学功能而言,任何回忆本身必定带有想象虚构的成分,也和个体的价值取向有关——最为充分地展现了张爱玲自己作为女性的生存、价值体验,作为独特个体的人生经历和性情得失,没有青年时期乃至整个现实生活中张爱玲的那种矜持、造作乃至表演倾向。当然,这也只是她自身的生存真实,不意味着她的叙述完全契合她叙述对象的生存真实,事实上,她对周围人的叙述,都带有某种根于其自身个性的扭曲,包括她母亲。②其自我意识与性别意识之突出,在中国这样一种女性性别意识受到严重压抑的宗法文化背景中尤为难得。作者对于自身生存状态与价值意识的逼真性叙述是相当出色的,如第五章曾写到主人公盛九莉——实即张爱玲本人——30多岁时在美国堕胎的经历:
夜间她在浴室灯下看见抽水马桶里的男胎,在她惊恐的眼睛里足有十吋长,毕[引者按:应为笔]直的欹立在白瓷壁上与水中,肌肉上抹上一层淡淡的血水,成为新刨的木头的淡橙色。凹处凝聚的鲜血勾划出它的轮廓来,线条分明,一双环眼大得不合比例,双睛突出,抿着翅膀,是从前站在门头上的木雕的鸟。恐怖到极点的一刹那间,她扳动机钮。以为冲不下去,竟在波涛汹涌中消失了。[2][157]
这一段是文本所着力叙述的她人生历程的最后一个关节点,也可以说是她一生性情、经历导致的重要人生决断,理应引发读者对张爱玲的女性意识及价值观的深思。为什么九莉在怀孕四个月后还要打胎?她为何要在丈夫汝狄说“生个小盛也好”的情况下回答:“我不要。在最好的情形下也不想要——又有钱,又有可靠的人带。”[2](155)③其根源和具体价值观念究竟如何?这种价值观念关涉到张爱玲创作的整体价值取向和题材选取,也影响到她的审美风格和人物造型,因此是真正深入理解把握张爱玲创作的关键。可惜以往的研究都没有关注到这一点,这就使对张爱玲的理解没有深入到其生存之根,不仅限制了对于张爱玲小说的理解,也影响了对于其审美风格与创作成就的适当评价。
纵观张爱玲一生及其诸多小说与散文,可以发现她以其天赋的敏感忧郁性情,成长于充满利益纠葛、个性冲突的阴郁家庭和现代性处境中,又受到了高度理性化的现代教育,对人生充满悲观,形成一种强烈的对于中国传统女性价值规范的反叛。④家人之间的关系在她成年以后看来,更多的是一种利益关系,如在与胡兰成结婚前,她提到要还母亲抚养她的钱,不久胡兰成送了一手提箱钱给她后,终于赢得她的认可。她此后又担心胡兰成误以为她以这种方式索要财产,自己不便也不愿分辩疏解。[2](161)⑤后来抗战胜利,胡兰成逃亡,不愿意割断和另一位年轻护士情人的关系,并在张爱玲面前无所顾忌地炫耀与其他情人的爱意,张爱玲终于在难以言喻的嫉妒和痛苦中,感觉自己“从此萎谢了”,下定决心断绝这种不正常的婚姻关系。同时也因胡兰成是被通缉的逃犯,她从某种意义上,又有些大难解脱而能免除良心不安地奉还了这笔钱,算是作了一个彻底的了断。用别人的钱,在张爱玲看来,意味着某种独立性和人格尊严的失去。她甚至还在十来岁被父亲继母暴打禁闭,逃离父亲家到离婚的母亲那里,打碎了一只茶壶,即马上花高价配了一只,“她从家里垫在鞋底带出来的一张五元钞票,洗碗打碎了一只茶壶,幸而是纯白的,自己去配一只,英国货,花了三块钱。蕊秋没说什么”。[2](116)⑥这也表现了她强烈的自尊心以及与母亲的感情隔膜。正是这样一种亲人间疏离、隔膜的情感体验,使得张爱玲小说表现出的女性生存处境的整体氛围是压抑、悲凉的,她的女性意识和价值取向尽管是高度理性化的、自觉的,却是不太正常的。因此,她笔下的女性形象在性格上也极少康健积极的,倒是变态者居多,如《心经》中恋父入迷的许小寒、《金锁记》中变态杀亲的曹七巧、《红玫瑰与白玫瑰》中麻木自卑的孟烟鹂、《沉香屑·第一炉香》中奢华淫靡的梁太太、《沉香屑·第二炉香》中临性恐惧的愫细姐妹,诸如此类,甚多,这还不算《沉香屑·第一炉香》中的葛薇龙、《连环套》中的霓喜、《红玫瑰与白玫瑰》中的王娇蕊、《封锁》中的吴翠远、《留情》中的淳于敦凤等,因为她们的选择似乎悖于情理,却也还可算得是常情,不失为一种对于无奈处境合乎理智的自觉应对,至于写作是否成功是另一个问题。⑦相对阳光的女性形象如言丹朱等又较空洞。正因为在张爱玲冷静锐利的眼光中,女性与男性的关系大多是一种利益的关系,“以美好的身体取悦于人,是世界上古老的职业,也是极普遍的妇女职业,为了谋生而结婚的女人全可以归在这一项下”,即使她也说“可爱的女人实在是真可爱”[3](72),但她笔下的女人实在很少真正可爱的,大多在利益的漩涡中,少数在情欲的煎熬中,表演人性的丑陋和偏执、残酷与悲哀。张爱玲也写情爱,但很少健康的情爱,大都是被扭曲的,甚至极端变态的情爱。她似乎认为女人们都把情爱的根基建立在物质利益的基础上,她所看到的现代性处境中的人际利益关系,其实也是较为狭隘的,每每只是一种浮面的物质利益而已,并非真正深层次的生存利益。白流苏算计范柳原只是想获得一个稳定的饭碗,淳于敦凤嫁给米晶尧甚至没有什么情欲的需求,吴翠远只是摆脱无聊而被冷落的处境而堕入荒唐的白日梦。⑧倒是张爱玲自己命名为《金锁记》的女主角曹七巧,主要并非被金钱枷锁,恰恰是被宗法伦理和遗产继承制度所禁锢,正如笔者在他文所述,在对姜季泽为谋财产的虚情假意作出选择时:
曹七巧所面临的选择其实并不是金钱欲和情欲的选择,而是金钱欲和靠不住的虚假情爱之间的选择。这是多数研究者没有注意到的,甚至张爱玲本人取名《金锁记》也偏离了她实际表现的故事内涵。如果有真正的爱和性,黄金并不一定构成曹七巧的枷锁。曹七巧选择金钱是合乎情理的,这次选择对她来说几乎是无可选择。[3]
这也正说明,张爱玲关注的主要是金钱、财产。但即使曹七巧这样的情况在张爱玲的小说中也并不算多见,即如《连环套》中的霓喜,似乎只在乎身份的稳固和情欲的满足,而不在乎儿女们的抚养存活。
三、张爱玲价值取向辨析
达尔文进化论揭示了自然选择的秘密,是人类文化史上最具有价值的发现之一。自然选择通过对于生物基因变异的选择性留存,使物种出现进化,即适者生存。[4]达尔文似乎把物种作为了主体。而现代生物基因研究,在接受达尔文进化论基本框架的基础上,已经认识到进化的主体是基因,任何生命个体包括人类个体都是基因延续、扩展的载体,对于基因而言,都只具有工具的意义。⑨人类为了实现这种工具的功能,发展出了适应于各种不同层级、不同范围的主体所需要的文化,包括各种复杂的伦理行为规则和价值观,这样造成文化的多层次和复杂性。但这些都是以适应于增大各个层级主体的基因延续机会而发展起来的。任何人类个体的价值,从根本上说,建立在基因延续因而导致基因以及物种的进化、长存上,文化所发展起来的一切伦理规范和价值取向也都根源于此。⑩女性的价值根基在于以其特殊的性别本能和理智,寻找到最佳的基因交换对象而使自身的基因获得更好的遗传机会,从而也使族群基因获得更好的延续机会。宗法文化发展出来的爱情及贞节观念,也是有利于女性与男性建立稳定的基因交换关系而获得繁育后代的更好的资源、处境优势。在漫长的自然进化和文化发展历程中,男性与女性分化出性别的差异与分工,男性更倾向于向外去获得生存资源,扩展人类从自然中获得资源的能力,调整群体的资源分配方式,为缓解资源竞争发展出超越性的价值理想和人生境界;而女子更倾注精力于抚育后代,以感情维系基因延续的家庭单位的稳固,更关注于由情感的细腻性和调节能力实现自身的功能。张爱玲对此似乎是有所认识的,尽管她可能还没有充分理解人类个体作为基因承载者的功能价值,她在《谈女人》(1944)中就说:
在任何文化阶段中,女人还是女人。男子偏于某一方面的发展,而女人是普遍的,基本的,代表四季循环,土地,生老病死,饮食繁殖。女人把人类飞越太空的灵智拴在踏实的根桩上。[3](70)
她没能理解男子的发展,也根源于最根本的基因延续机会,张爱玲清楚地意识到的只是男女间物质层面而非基因层面的利益关系,却因而更多地表现爱情的匮乏而不是爱情对于男女关系的滋润,更不是爱情对于实现女性价值的意义。这使她冷酷地掀去了其他多数女性作家赋予爱情的温情面纱,显示出她所看到的现实男女关系的残酷。她很少看到,她的小说也很少表现爱情的健康状态和正面意义。这与她的生存体验密切相关,她父母失败的婚姻以及各自的情感经历给予她的挫折感,她的亲戚如三姑张茂渊的人生选择对她的影响等等,再加上她的看似理性冷静深刻,实则不无偏颇狭隘自私的对于生命之意义的反思,使她得出的一些价值判断往往似是而非,违背人性之根本。如她认为母爱是人类同于兽类祖先的特征,本能的仁爱只是兽性的善,而不是人性的善,这就把人的自然属性与人性割裂开来了,如《造人》所说:
自我牺牲的母爱是美德,可是这种美德是我们的兽祖先遗传下来的,我们的家畜也同样具有的——我们似乎不能引以为傲。本能的仁爱只是兽性的善。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并不在此。人之所以为人,全在乎高一等的知觉,高一等的理解力。此种论调或者会被认为过于理智化,过于冷淡,总之,缺乏“人性”——其实倒是比较人性的,因为是对于兽性的善的标准表示不满。[3](95)
“人之所以为人”,绝不是只在“高一等的知觉,高一等的理解力”,而是在于以“高一等的知觉,高一等的理解力”为适应生存环境,实现基因的持存与进化服务,善这样的伦理观念的产生,也是为这一根本需求服务的。张爱玲试图去掉人类的本能基础而仅仅把超出于兽性的部分作为人的定义,实质上是不符合人类在亿万年进化中建构起来的生物机能和认知逻辑的。但她进一步的思考,也显示出她的价值虚无取向的理性思维逻辑基础,那就是人类思维不能“止于自然”,而应该眼光长远地看到,在生存竞争的长途中,一切个体迟早会被淘汰:
兽类有天生的慈爱,也有天生的残酷,于是在血肉淋漓的生存竞争中一代一代活了下来。“自然”这东西是神秘伟大不可思议的,但是我们不能“止于自然”。自然的作风是惊人的浪费——一条鱼产下几百万鱼子,被其他的水族吞噬之下,单剩下不多的几个侥幸孵成小鱼。为什么我们也要这样地浪费我们的骨血呢?文明人是相当值钱的动物,喂养,教养,处处需要巨大的耗费。我们的精力有限,在世的时间也有限,可做,该做的事又有那么多——凭什么我们要大量制造一批迟早要被淘汰的废物?[3](95)
她也注意到人类的本能,自然会繁殖后代,但在她看来,即使是留下了遍布大地的种子,也都是因为天性的自私而相互仇恨的种子,没有什么价值:
我们的天性是要人种繁殖,多多的生,生了又生。我们自己是要死的,可是我们的种子遍布于大地。然而,是什么样的不幸的种子,仇恨的种子
这就是上文所引《小团圆》表现九莉堕胎一节文字的思想根源和价值基础,也充分明确地显示了张爱玲的价值取向多么违背人类的本性以及传统宗法文化所建立起来的伦理规范和价值准则。
然而,我们不必急着彻底否定张爱玲似乎极端的断言,因为她的这种思考和价值体验又有其深刻性和超越感,体现了人类文化现代性的普遍趋向。甚至可以说,这是现代文明发展出强烈的个体自由意志和独立意识的必然产物。人类以基因延续为基础的伦理观,是在个体自我意识并没有充分自觉的情势下建立起来的,以往人们的伦理价值观,一直被认为是以人的族群、种群或个体为主体的,实际上却是以基因为最为真实的主体。文化发展到现代,由于人类理性的高度发达,个人主体意识越来越强烈,似乎凸显了个体生存的尊严和价值。但是诡异而具有某种辩证意味的是,强烈的个人意识并不能为自身寻找到坚实的价值根基,而追求价值根基的需求也更强烈,却越来越难以找到也许永远也无法找到这样一种价值根基,人们只能在价值虚无体验中感受人生之无根与无望——具有独立意识的古代哲人们也有着自己的价值迷茫和悲剧性体验——现代理性似乎只能让人在个人生存体验的层面上理解人的价值。张爱玲是现代中国女作家中最能表现出这种人类的现代性倾向的。正是因为对于人类价值根基的迷茫,所以张爱玲仅仅在个体意识或直接生存体验的层面上,挥霍着她的才华,她笔下的女性大都是在价值虚无体验中感受人生的苍凉,找不到自己的人生坐标和伦理位置,并且为这种状态付出痛苦、孤独、无聊、无奈、无告的代价。从张爱玲笔致的细腻、尖新、微妙来说,她是成功的,不仅这些人物的生存状态和价值体验都有她自己的真实生活体验为范本,在文字的运用上她也能使之逼真地呈现于读者面前。从她被现代中国人所广泛接受欣赏,被当代中国的现代文学史书写高度评价这一点来说,她也是成功的。确实可以说,此前无人像她那样细致入微地表现现代中国女性在性、情、爱、嫉妒尤其是性、情、爱匮乏方面的微妙感受,凸显出中国女性在极为特殊的文化处境中的性别体验。曹七巧、姜长安(《金锁记》)、白流苏(《倾城之恋》)、葛薇龙(《沉香屑·第一炉香》)、吴翠远(《封锁》)、王佳芝(《色·戒》)、盛九莉等都是写得相当充分、极为逼真的人物,《小团圆》尽管作为小说来说不能算非常成功,但盛九莉完全就是张爱玲本人的真实写照,在写其情爱体验、性体验、嫉妒体验、憎恨体验、冷漠疏离感、自我执著而又冷静克制的性格方面是很出色的——这些都是在她的实际人生经历中一遍一遍地回味,不断重新激活,因而刻骨入髓的——而且具有无可比拟的真实性,可以说远超过她笔下所有的其他人物。盛九莉像她笔下的多数人物一样,找不到生存的价值之根,所以非常沉溺于一生所经历的生活细节。张爱玲自己写小说,对此有甚为自觉的思考,她认为,正是因为生活没有意义,人生充满悲哀,所以小说家只能在细节的叙述上得到欢悦,中国古代最成功的作品《金瓶梅》《红楼梦》都是如此。
就因为对一切都怀疑,中国文学里弥漫着大的悲哀。只有在物质的细节上,它得到欢悦——因此《金瓶梅》《红楼梦》仔仔细细开出整桌的菜单,毫无倦意,不为什么,就因为喜欢——细节往往是和美畅快,引人入胜的,而主题永远悲观。一切对于人生的笼统观察都指向虚无。[4]
不过《红楼梦》的作者和张爱玲毕竟是不同的。《红楼梦》是作者带着悲悯情怀的书写,而且能发现生命的美妙与欢愉,以及这种美妙欢愉消逝的悲哀。尽管作者仍然留恋着逝去的繁华,但有明显的超越性追求,这种追求使其叙述的世界具有一种超越自然主义的意味。而张爱玲,更多写生命的丑陋和怨愤,尤其是她的同样具有自传性的《小团圆》,更多地是带着个人的自怜、自恋,对世界的疏离感而写的。然而,张爱玲为人所称道的作品似乎恰恰都带有较强的故事性,不少还有都市传奇的意味,这又是为何?那是因为她希望获得读者的喜欢,尤其是期待她最熟悉的上海市民读者的认可。她在1950年代初给朋友邝文美信中说:“除了少数作品,我自己觉得非写不可(如旅行时写的《异乡记》),其余都是没法才写的。而我真正要写的,总是大多数人不要看的。”[5−6]她自己真正要写的《异乡记》(1946,当时未刊),则是对于她旅行途中所见到所感受的各种互不关联的细节的不择意义的叙述,这是一个缺乏价值感的世界。不过,即使在一个张爱玲觉得价值虚无的世界里,她也在努力探索叙述着各种女性的生存方式与各自的悲欢,也能引起读者对人性、人生的悲哀和反思。《金锁记》《倾城之恋》《封锁》《十八春》《色·戒》《小团圆》中的主人公不用说,都具有某种代表性的意义。不过,张爱玲像中国现代大多数作家一样,在审美与价值的超越性上无所用力,而且她比多数新文学作家更为冷静地执著于阴暗的现实,在她自己看来,当然是把握住了现实的残酷真相,显示了人性的深刻性与无可逃避的悲剧性,她小说中的人物,往往是前景黯淡的,正如《金锁记》写长安“一级一级,走进没有光的所在”。这既是张爱玲创作的长处,也可以说是她的拘囿,正是如此,在读者阅读她的小说时,因为她那种阴冷氛围和人生体验,不容易产生一种审美的超越感,更难以产生一种人生价值的提升,达到一种看透人性真实以后的人生境界的自由。
注释:
① 林幸谦《荒野中的女体》《女性主体的祭奠》,均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出版,个别文本解读有过度阐释之嫌。
② 《小团圆》可以看作较为严格意义上的张爱玲自传,所有人物都可以找到张爱玲生活中的实际对应者,本文不作详细论证。比较张爱玲《小团圆》与《对照记》(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7年版),可见在一些生活细节上,《小团圆》都保留了她所记忆的真实,只是在人名上作了虚构。也可参见邓昭祺《张爱玲自传小说〈小团圆〉索引》,《北京化工大学学报》,2009年第3期。
③ 汝狄即张爱玲第二任丈夫费迪南德·赖雅Fedinand Reyher的代称。
④ 张爱玲因家境关系,对中国传统文化有所了解,但从小进入教会学校读书,后入香港大学,受英国式教育,高度理性化的思维得益于这种求学经历。英国文学的主题和风格,对她也有相当大的影响。可参看陈娟博士论文《张爱玲与英国文学》。
⑤ 邵之雍是胡兰成代称。
⑥ 卞蕊秋即张爱玲母亲黄逸梵代称。
⑦ 张爱玲在《〈张看〉自序》(1976)中就说:《连环套》“三十年不见,尽管自以为坏,也没想到这样恶劣,通篇胡扯,不禁骇笑”。《张爱玲文集》,第4卷第337页。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下引《张爱玲文集》,均据此版。
⑧ 张爱玲自己的实际认识或不致这样偏颇,但小说中表现的女性形象大多如此,《小团圆》中的九莉对生存利益的理解就不一样了,尽管也每着意于物质利益。
⑨ 请参看英国学者理查德·道金斯的《自私的基因》,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当然,在人类认识的意义上说,除基因主体以外,生命个体包括人类个体,生物群体,物种,人类群体包括家庭、家族、民族、国家、种族、人类本身都可以作为主体来看,但其意义远不如基因作为主体那么根本。
⑩ 请参看王攸欣《论王国维〈红楼梦评论〉与〈红楼梦〉根要——为纪念〈红楼梦评论〉发表110周年作》,该文对基因延续机会与文化的关系,作了概要阐述,提出一种新的文化观。刊于《曹雪芹研究》,2014年第4期。
[1] 王攸欣. 路翎张爱玲小说审美内蕴比较论[J]. 浙江学刊, 2013(4): 76−86.
[2] 张爱玲. 小团圆[M]. 北京: 十月文艺出版社, 2009.
[3] 达尔文. 物种起源[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63: 96−153.
[4] 张爱玲. 谈女人[C]// 张爱玲文集合肥: 安徽教育出版社, 1992.
[5] 张爱玲. 中国人的宗教[J]. 天地, 1944(11): 13−15.
[6] 张爱玲. 异乡记[M]. 北京: 十月文艺出版社, 2010.
Eileen Chang’s female consciousness and value experience
WANG Youxin
(School of Literature,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3, China)
Eileen Chang is endowed with an extraordinary female consciousness. In the process of the eastward spread of western culture, Eileen Chang loses the root of life value and renders life a nihilistic existence, which can be attributed to her own special growth experience, the female survival experience and her outstanding self-consciousness of rational reflection cultured in the English educational background. As a result, her female writing presents a desolate atmosphere which is gloomy, cramped and hopeless. Eileen Chang fails to pursue the aesthetic transcendence and free experience, which is the key to understanding the overall aesthetic style of Eileen Chang’s creation.
Eileen Chang; female consciousness; value experience; nihility
I209
A
1672-3104(2015)01−0223−05
[编辑: 胡兴华]
2014−08−18;
2014−10−28
王攸欣(1966−),男,湖南湘乡人,文学博士,中南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国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