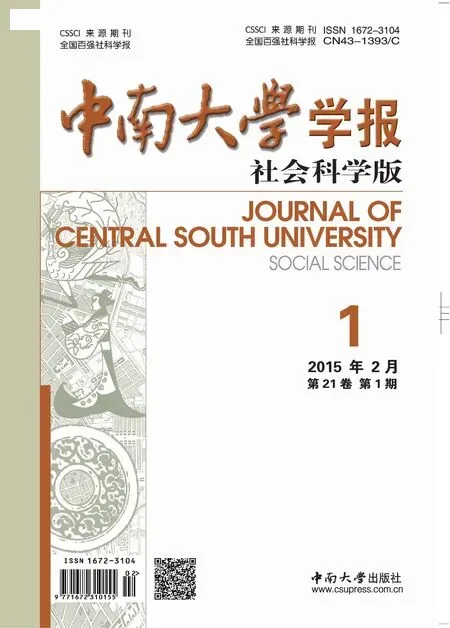积极守法:一个被忽视的法治维度
2015-01-21胡国梁
胡国梁
(中南大学法学院,湖南长沙,410083)
积极守法:一个被忽视的法治维度
胡国梁
(中南大学法学院,湖南长沙,410083)
从法治实践来看,我们的守法观经历了从以服从为中心的消极守法观到以维权为中心的有限积极守法观的变迁,并已经有了朝以护法为中心的全新积极守法观进化的趋势。从法律规范性角度分析,积极守法可以分为法定的积极守法与法律未予以禁止的积极守法;从行为表现角度分析,积极守法可以分为制止与劝阻两类行为。从公共领域的视角来看,积极守法观其实是一种个体公民意识的表达,并能够在此基础上生成社会整体公民意识与公共理性。积极守法所蕴含的公民意识及公民参与的要求对破除臣民意识、建设法治社会与实现善治具有重要意义,是法治建设的一个重要维度。
积极守法;公共领域;公民意识;法治社会
守法并不是一个新鲜的议题,但正因如此,其中往往沉积着让人不假思索就主动接受的潜在偏见。一旦论及守法,首先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必定是公民对法律的服从,这种解读也进一步构成了我们对法治内涵的理解,即“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看,那些不经充分讨论就被普遍接受的观点往往最值得怀疑,从“地心说”到“日心说”的艰难转变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明。
一、从消极守法到积极守法:守法观之变迁
就守法的内涵而言,显然并不只局限于公民对法律的消极服从,即便在某一个历史阶段,守法所指向的主要是服从法律,在现今法治中国建设背景下,仍然有对其进行拓展的必要。无论从公共讨论还是从政策规范来看,人们对守法所持的态度基本上是基于服从的消极守法观,间或有立足于维权的有限的积极守法观,但鲜有论及致力于护法的扩大的积极守法观。
(一) 传统的消极守法观:服从
在讨论法治问题时,人们总会不约而同地想起亚里士多德在两千多年前关于法治的经典总结:“法治应当包含两重含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定得良好的法律。”[1]我国古代思想家也有类似的精辟论述,《管子·任法》有云:“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此谓为大治。”在传统观点看来,作为公民,其在法治国家中的角色定位就是服从法律的忠实守法者。这种以服从为中心的守法观可称为消极守法观,其基本特质是以义务为导向,强调令行禁止。不难看出,消极守法观的义务导向是将法律作为一种命令来理解,即奥斯丁所主张的法律命令说。奥斯丁认为:“每一条法律或规则(就能恰当地给予这一术语最为广泛的含义而言),是一个命令,或者,恰当指称的法律或规则,是一种命令。”[2]将法律理解为一种命令,也就隐含着立法者和守法者之间的区分,是立法者对守法者的一种命令。法律命令说虽然从某个层面阐释了法律所具有的强制性,但却饱受争议。莫里森就曾指出:“奥斯丁的法理学代表了他所处的那个时代的一种明显的政治趋势,就是人治。”[3]这种批评是成立的,正是因为法律命令说中所蕴含的人治色彩,才让立法者与守法者之间形成鲜明对立,并最终型构了以服从为中心的消极守法观。
对奥斯丁更广为人知的批判来自哈特,“对于法律的命令理论,哈特第一个不满意的是,法律命令理论忽视了法律的多样性。”[4]从法律规范的类型来看,虽然强制性规定占重要地位,但任意性规定、提倡性规定乃至奖励性规定也逐渐丰富起来,并日益成为法律规范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不论是法律命令说,还是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消极守法观,都只能适用于强制性规定。诚然,法治的建立和维护离不开公民对法律的服从,但如果仅仅停留于此,并不能彰显公民在现代法治中的主人翁地位,也不利于塑造现代公民意识,进而影响法治的真正确立和长远发展。
(二) 有限的积极守法观:维权
已有不少学者提出了积极守法的论题,比如冯粤就认为“维护法律、积极行使法定权利,信仰和尊重法律,即积极守法”[5]。但现有论述的分析视角主要集中于公民积极行使和维护合法权利,因而是一种有限的积极守法观。这种积极守法的表现形式往往局限于通过诉讼或仲裁等争端解决方式来实现其权利主张,当然也包括自助行为和部分正当防卫行为等所谓的私力救济形式。如果说传统的消极守法观是以义务导向为基本特质,那这种有限的积极守法观则是以权利导向为其本特质。之所以判定权利导向能够作为这种积极守法观的基本特质,在于不论是维权行动还是维权诉求,都说明公民正以一种积极主动的姿态来实现法律赋予的权利,而非“把自己置身于法律的对立面”[6],被动接受和履行法律义务。相较于仅仅强调服从法律的消极守法观,这种积极守法观更注重公民的主体地位,关注其自身权利的实现,而不是单纯地为彰显法律的权威而存在,体现了“为权利而斗争”的进步意义。
曾经引起社会极大争论的“王海现象”生动地诠释了这种以维权为中心的积极守法观的正面意义。虽然“王海”能否认定为消费者在理论和司法实践中都存在不少分歧,但必须承认,“曾几何时,王海所到之处,奸商们闻风丧胆,那真是让消费者舒心的日子”[7]。积极守法观下的某些行为方式已经具有了正外部性,守法者在维护自身权利的同时也维护了公共利益,其他公民也能从中受益,这是消极守法观所不能比拟的。虽然也有学者将这种行为定位为民间执法,但从该行为的内容和形式来看,冠以积极守法之名可能更恰如其分。这种行为的本质是对私人权利的行使,其权利的基础只能在私法中去寻找,包括民法通则、合同法、侵权责任法等。虽然这种积极守法观跳脱了义务论窠臼,但仍然只能局限于私法领地,因而也是有限的。
(三) 扩大的积极守法观:护法
1. 以护法为中心的积极守法观
2009年7月12日《兰州晨报》报道:“7月9日晚,兰州一老人手拿砖块站在斑马线上,只要有车辆闯红灯经过,便用砖块砸向违章车辆。直到目前,警方尚未追究老人责任,车主们也没有找老人赔偿。”[8]消息一出,引发热议,各大网站对此进行的调查结果显示:33万人中有26万人支持老人砸车行为——闯红灯的司机拿他人性命当儿戏,应该受到教训,砸得好砸得解气;仅有6万多人认为老人行为过激——砸车违法,不应提倡。从法律视角进行分析,老人的行为虽然得到了绝大多数网民的支持,但显然是违法的。警方之所以没有追究老人的责任是因为这纯属民事侵权,公安机关无权介入;车主们没有找老人赔偿显然也是一种道义上的选择。但如果仅仅对该事件作如上法律分析无疑遗漏了太多可以挖掘的东西。首先,老人为什么要砸违章车辆?一个显而易见的理由是车辆闯红灯违章,而这背后则隐含着另外两个重要的原因:一是交警部门执法不严,乃至执法缺位,使得这种违章行为无所顾忌;二是车主规则意识不强。这两点都指向了我国法治建设的软肋。其次,老人砸违章车辆的行为是否还有其他含义?该老人在斑马线上砸闯红灯的违章车辆显然和一般的破坏车辆的行为不同,而且这种区别可能是本质性的,其影响着车主是否决定索要赔偿。老人砸违章车辆的行为显然不能仅仅用侵权来解释,尽管其毫无疑问构成侵权。事实上,如果剔除其违法性,这种行为可称为积极守法。
这种积极守法表现为守法者以自身为主体来矫正违法行为。相比于上一种积极守法形态,这种类型的积极守法在范围上得到了扩大,因此称为扩大的积极守法。虽然也有论者将之名为私人执法,但其主要是在私力救济的语境中进行讨论,所列举的商场搜身、私人罚款等具体手段也仅限于对私益的维护,并往往伴随着一定的非法性,这也就决定了其存在空间比较小。而且在现代社会,执法权应当由国家垄断,如果认为私人也具有执法权,无疑破坏了这一重要的文明规则。以积极守法代替私人执法,对守法的外延进行扩张并同时予以必要的规范,既能够避免执法权泛化并被滥用的危险,又可以有效回应上述这种必要的行为方式。
2. 积极守法类型的初步分析
积极行使权利与抑制不法行为皆可以说是积极守法的重要内容,但本文所着重讨论的还是后者,因为这里强调的积极守法主要目的在于维护法律,而积极行使权利并不意味着必然存在违法行为。对积极守法的深刻认识离不开对其进行类型分析,从不同的角度可以对同一概念进行不同的类型分析。为了提升对积极守法类型分析的价值与意义,我们可以参考徐昕教授对私力救济的分析路径。他在《论私力救济》一书中从实体法视角与纠纷解决视角两个方面对私力救济的类型进行了展开。从实体法角度来看,私力救济可以分为法定的私力救济与法外的私力救济,其中法外的私力救济包括法无明文规定的私力救济与法律禁止的私力救济;从纠纷解决角度来看,私力救济可分为强制与交涉。循此思路,我们亦可从法律规范性视角和表现形式视角对积极守法进行类型化。
从法律规范性视角来看,积极守法可以分为法定的积极守法与法律未予以禁止的积极守法。法定的积极守法,是指能够从现行法律当中寻找到明确法律依据的积极守法。比如我国《刑法》第20条对正当防卫的规定:“为了使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权利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而采取的制止不法侵害的行为,对不法侵害人造成损害的,属于正当防卫,不负刑事责任。”该规定通过反面否定刑事责任的形式肯定了“采取的制止不法侵害的行为”的合法性。另有《刑事诉讼法》第82条规定:“对于有下列情形的人,任何公民都可以立即扭送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处理:(一) 正在实行犯罪或者在犯罪后即时被发觉的;(二) 通缉在案的;(三)越狱逃跑的;(四) 正在被追捕的。”该规定则是从正面赋予公民“扭送”的权利,而“扭送”的背后其实也隐含着制止不法行为或防止不法行为发生等积极守法行为。还有一些表现为积极守法的行为是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但也未予以禁止的,比如劝阻车主闯红灯、不按规定停车等。将积极守法进行法定与法未禁止的二元划分,一是出于“法不禁止即自由”的考虑,需要承认公民在法律规定授权之外还享有一定权利,二是要谨防这种权利过分放大并演变成私刑。
从积极守法的行为表现来看,我们可以将其分为制止与劝阻。制止展现出的是双方对抗较为激烈的场景,并往往伴随着一定的强力。制止的实现并不要求对方予以配合,积极守法者单方行为即可达成。劝阻则大不相同,往往展现的是双方处于相对温和的场景,其实现也以对方的合作为前提。劝阻一词在我国现行法律中其实也有规定,我国《婚姻法》第43条规定:“对正在实施的家庭暴力,受害人有权提出请求,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应当予以劝阻。”只是这里的劝阻以受害人提出请求为前提,并且主体是居委会或村委会,不是公民个人,难以将其解释为积极守法。无独有偶,法国也曾一度出现过关于劝阻的讨论,主要针对的是交通事故中饮酒致害民事责任中共同饮酒者的驾车劝阻责任。“事实表明,仅仅讨论一下这个问题,就引起了降低车祸的社会效果。报纸和电视开始讨论这个问题的头两个月,与前一年同期相比,交通事故就有明显的下降迹象。”[9]但从我国法治建设的实际来看,将劝阻定位为义务还不适当,将其定位为积极守法的表现形式可能更有利于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二、公共领域与公民意识的拓展:积极守法的存在基础
(一) 公共领域内涵总结及其拓展
虽然关于公共领域的研究由来已久,但却并未形成一个被普遍接受的定义。从当前的研究成果来看,对公共领域的理解可以总结为以下几点。第一,公共领域是表达和形成公共意见或舆论的载体。公共意见是公民基于某种立场对公共事务所表达的看法或建议之集合。哈贝马斯认为:“公共领域最好被描述为一个关于内容、观点也就是意见的交往网络;在那里,交往之流被以一种特定方式加以过滤和综合,从而成为根据特定议题集束而成的公共意见或舆论。”[10]在现代社会,任何人都有就公共事务进行讨论并发表意见的权利。并且随着网络技术的突飞猛进,公共表达将以更加迅速便捷的方式呈现出来,承载公共意见的公共领域也将被进一步拓宽。第二,公共领域是制约国家权力的重要渠道。国家权力应当是为社会公共利益服务的,但随着国家与社会的分离,国家权力并不总是以社会公共利益为依归。这是哈贝马斯提出的公共领域存在的前提之一。由此,公共领域是矫正乃至制约国家权力的重要通道。公共领域以对公共权力的实践的批评为主旨,使公众能够对国家活动实施民主控制。[11]就此而言,公共领域及其所承载的公共意见往往表现出很浓厚的政治色彩。第三,公共领域是现代社会国家权力和国家制度的法统基础。人类历史就是从野蛮不断走向文明的过程,在政治领域主要表现为从君权神授向君权民授的转变,从君主独裁向人民主权进化,君权民授或人民主权实现的基础乃在于公共领域的发展与成熟,否此,公共讨论无法进行,社会契约也就不可能达成。
对公共领域的现有研究已经提炼出了公共领域至关重要的内涵及功能,但随着社会本身的发展以及新情况的出现,公共领域的内涵也有了进一步反思和拓展的空间。首先,公共领域是否仅局限于对言论的承载?公民对于某一涉及公共领域的事件是否只有发表言论的权利?显然,公民所享有的集会、游行、示威等基本政治权利已经对此进行了制度性突破,公民当然能够以行动的方式存在于公共领域之中。2012年10月宁波市镇海区群众为阻止PX项目而进行游行示威活动,虽然其中也裹挟着一定的不法行为,但最终迫使政府承诺不再建设PX项目。可见,在公共领域中,公民的行动在功能、意义上并不逊色于言论。其次,在公共领域是否只能形成对国家权力的制约?制约国家权力,防止国家权力对公民权利的侵蚀固然是公共领域存在的重要理由,但显然也有必要将视野进一步拓宽。正当防卫等私力救济形式所对抗的就未必是国家权力,而主要是其他公民或组织的不法行为。在公共领域对其他非国家权力主体采取某些适当的行动(如正当防卫)不仅不是对国家权力的制约,反而构成对国家权力在维护公共利益方面的重要补充。最后,公共领域当然是现代社会中国家存续的法统基础,然其也同时构成个体呈现为公民并以公民身份参与国家治理的重要基础。如果个体只是在私人领域进行私人活动或参与私人交往,其所呈现出来的身份无非是消费者、经营者、监护人、继承人、所有权人等等,不涉及公民身份,亦不涉及公共领域范畴。但若其意欲以公民身份表达公共意见或参与国家治理,则必须越出私人领域,进入公共领域。换句话说,如果这个社会的公共领域没有向普通个体开放,则其就无法借由公民身份参与公共事务的讨论和治理。
(二) 从公共领域的拓展到公民意识的深化
公共领域“培养了民主政治所必需的参与意识、权利意识、责任意识、义务意识和公共精神等公民意识”[12],因而,公共领域的拓展必然带来公民意识的深化,即便我们对这种深化并未获得充分的理解。对于公民意识具体内涵的理解虽然各有千秋,但多数意见倾向于从公民与国家、公民与社会这样一个宏大的视角来探讨公民意识的积极作用。例如,魏健馨认为,公民意识的存在“展示了社会权利制约从社会中产生并凌驾于其上的国家权力的一种努力”[13]。张金岭亦主张,公民意识的增强对其社会领域内诸多“合法性”的建构起到重要的影响作用,为其提供思想基础与民主实践的动力。[14]在我们法治国家和法治社会建设过程中,当然必须强调公民意识在国家权力的制约与社会合法性建构当中的重要功能,这是长期以来法治建设的重要短板,但这并未充分发掘出公民意识的深刻内涵以及由此衍生出来的其他潜在功能。
既然公共领域能够在言论之外承载一定的私人行动,也并不局限于对国家权力的制约和监督,亦能为公民参与国家治理提供更广泛的空间,那我们也有必要在此基础上重新认识公民意识及其重要功能。朱学勤在《书斋里的革命》一书中提到:“公民意识是近代宪政的产物,它有两层含义,当民众直接面对政府权力运作时,它是民众对于这一权力公共性质的认可及监督;当民众侧身面对公共领域时,它是对公共利益的自身维护和积极参与。”[15]对公民意识的这种解读触及了其另外一层面相。当公民面对的是国家或政府的时候,公民意识将与公权力及其行使主体发生勾连;当公民面对的是公共领域的时候,公民意识将与公共利益及其他公民、组织发生勾连。这种勾连可以表现为认可、监督,也可以表现为行动,比如面对不法行为时采取的正当防卫,如果将其进一步拓宽的话,就是本文所说的积极守法。易言之,积极守法是公民处于公共领域之中时,基于强烈的公民意识而与其他公民或组织发生的表现为行动的一种勾连。
三、积极守法对公民意识的呈现与促成
从已被拓宽的公共领域视角分析,积极守法乃公民意识之呈现,并且,在此过程中,其也将进一步促成公民意识的成熟,因而也同时成为公民意识生成的重要路径。
(一) 作为公民意识呈现方式的积极守法
由于公民是个人进入国家政治生活状态下的一种身份,围绕着公民意识的核心内涵,公民意识的具体内涵就相应地体现为公民作为政治权利义务的主体而应具有的意识。[16]因此,在以往的认知结构中,我们判定某一个国家或社会的成员具有或不具有公民意识,以及公民意识的成熟与否,主要是通过该国家或社会的成员发表言论、主张权利、履行义务等情况来观察。倘若其公民中的大多数能够针对公共事务发表言论,包括对国家或政府的行为进行批评、建议等,能够积极行使自己的权利与履行自己的义务,就可以被认为具有比较强的公民意识。反过来说,公民意识以往主要是经由发表言论、主张权利、履行义务等方式而呈现出来的。然而,这并没有完整概括公民意识的呈现方式,积极守法同样可以发挥这一作用。
首先,积极守法者乃以公民身份置身于公共领域之中。这里的公共领域不仅表现为理念上的公共领域,还表现为物理空间上的公共领域。在文章开头列举的案例中,老人站在斑马线上对不遵守交通规则的车主施加一定的“惩罚”。尽管这种行为是一种侵权行为,但如果暂时将其实行行为予以搁置并回溯到其行为动机则可以发现,他并不是由于其本身某种具体权益受到侵犯而采取“私力救济”的行动。换句话说,他不是以受害者身份出现在车主面前的。他所持的立场是基于对公共利益的维护,因而,他此刻所呈现出来的是一种公民意识,所展示的是公民身份。正是这种身份上的特殊性,使积极守法区别于行政执法。行政执法者代表的是国家,与违法者处于不对等的地位,并以国家暴力机关为后盾。积极守法者与违法者之间在法律上是平等的,所采取的措施主要限于劝导、教育以及法律所允许的某些特殊措施,比如正当防卫。
其次,积极守法者面对的是损害公共利益的违法行为。积极守法者所面对的首先是损害公共利益的行为,如果损害的仅仅是私人利益,由受害人在私法框架下通过调解、仲裁与诉讼等方式即可解决。当下中国,损害公共利益的行为十分普遍,可并不见多少人站出来予以维护,“但这绝不是因为中国人的国民性如何糟糕,也不是因为民众缺乏权利意识”[17],而是“搭便车难题”与“集体行动的困境”所塑造的“理性经济人”自然选择的结果。于是,有学者认为,公共利益获得有效维护之关键, 就在于国人之君子意识的觉醒。[17]其所谓“君子”即积极公民,也即本文所论之积极守法者。因此,积极守法对公共利益的维护是极为重要的,也是极为可贵的。另外,积极守法者面对的是违法行为,而不是悖德行为,尽管二者在很多情形下会交织在一起。虽然有些违背道德的行为,同时也违反了法律,但还是要牢记“在我们没有决定要放弃法律权威的概念之前,我们不应取消法律与道德之间的区别”[18]。如此,方能将积极守法从一般的道德说教中区分出来,并体现出一种更为纯粹的公民意识。
最后,积极守法者采取的行动是维护公共利益的适法行为。公民意识当然应当在现有体制框架中以合法的方式呈现出来,积极守法者也必须以适法行为来维护公共利益。适法行为之外衣为积极守法的存续和展开提供了正当性基础。这里的适法行为并不必然要求具有法律上的依据,只要法律不予禁止,就可以判断为是适法的。因此,站在斑马线砸违反交通规则的车辆并不能解释为积极守法,而是一种违法行为。将积极守法限定在适法行为之内,既构成积极守法展开的前提,也能够消解对积极守法的某些质疑,为其作为公民意识之呈现方式提供重要支撑。
(二) 作为公民意识生成路径的积极守法
美国智库兰德公司在2010年发表了一个关于中国的报告,预测中国2020年后将成为世界上最穷的国家,原因之一即是中国人不了解他们作为个体对国家和社会应承担的责任和义务。[19]不得不承认,个体社会责任的缺失折射的是这个国家公民意识的薄弱,由此,公民意识的生成或建构成为中国走向现代化的重要任务。一般认为,中国与西方在公民意识发展路径上存在重大分野,一为国家建构,一为自发生成。有论者据此进一步认为,“在中国当前正处在价值共识探索阶段的情况下,如果单单凭借公民个人的自觉很多时候就不仅不能形成共识,反而会导致价值交锋过于激烈而抵消共识达成的可能性,或者是个人沦为犬儒主义的状态”[20],因此,应当主要强调自上而下政府主导的方式在公民意识建构中的作用。但布赖恩•特纳的提醒同样值得关注:“如果公民身份发展于一个为权利而进行革命斗争的背景下(如法国和美国),那么,就将形成一种积极且激进的公民身份参与传统,相反,如果公民身份仅仅是自上而下被给予的,那么,公民身份就可能发展成为一种被动而相当消极的形式。”[21]这些论述虽立场不一,但都潜藏着同一个共识,即公民意识的发展不能仅仅依赖于单一的力量,而必须走多元化的路径。这一基本认识对于转型时期的中国而言意义更加重大。如何尽可能地探索出多元的方式来发展公民意识也是法治中国和国家治理现代化中的重要命题。积极守法既是单一公民意识的表现,又能同时在公民意识的整体生成中发挥重要作用。
首先,积极守法的理念在于鼓励公共参与。“参与是公民身份的学校”[22],公共参与对塑造公民身份与公民意识至关重要。积极守法观的核心理念就是积极参与,并且这种参与同我们以往宣扬的公共参与还不太一样。我们以往对参与的理解虽然也具有多样性,但仍然主要集中于权利与权力之间的博弈或合作的语境下,强调对权力的制约或修正。比如有学者从行政决策的角度来探讨公共参与的意义与方式[23],也有学者在社会问责的视野中观察公共参与的重要性[24],还有学者从共同治理的角度探讨公共参与的正面价值[25],等等。积极守法所倡导的公共参与相比过往的阐述更能体现公民的主人翁地位,这种主人翁地位是通过具体的行动表现出来的。
其次,积极守法的实现有利于唤醒公共责任意识。公共责任是社会主体间共享共生的基础条件[26],公共责任意识也因而构成公民意识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中国出现的各种社会问题,无论是毒奶粉事件、皮革胶囊事件还是每天都在上演的地沟油事件等等,其背后都是公共责任意识的缺失,兰德公司发布的预测报告其实极为深刻。积极守法对唤醒公民公共责任意识的意义可以从两方面进行解读:其一,积极守法主要作用于公共领域,积极守法者面对的是损害公共利益、缺失公共责任意识的行为,通过采取一定的措施纠正对方的行为,可以增强对方的公共责任意识;其二,积极守法的具体实现能够产生示范和带动效应,这种基于具体行动的示范和带动效应远远强于意识层面的教育,能够在唤醒公共责任意识方面发挥更好的作用。
四、积极守法之于法治建设
从公民积极守法的角度来看,弘扬法治精神,实现全民守法,要求公民以积极作为的国家主人翁态度,做到“信任立法、配合执法、倚赖司法、努力护法”[27]。积极守法对推动法治中国的建设具有重要意义,但却并未引起我们的足够重视。
(一) 推动臣民意识向公民意识的转变
“臣,牵也。事君也。象屈服之形。凡臣之属皆从臣。”[28]因而,臣民从来都是以屈从者的面貌出现的,臣民意识也是一种没有自我主体的意识。臣民意识不仅与中国历史上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一脉相承,而且已经深深地嵌入了中国传统的儒家伦理之中,这就是为什么“传统儒家伦理培育出来的是对专制权力盲目崇拜与服从的臣民意识,而非现代民主法治国家必具的公民意识”[29]。因此,在儒家伦理依旧深刻影响着人们言行举止的今天,即便君主专制制度已经一去不复返,我们仍然面临推动臣民意识向公民意识转变的艰巨任务。而且,这也是法治中国建设最复杂的工程。对于这一重要而艰难的转变,有学者提醒道:“形成普遍的公民意识必须以每个人的具体实践为必要环节。”[30]在此语境下,我们就能够看到并理解积极守法的价值所在。前文已经论及积极守法在发展公民意识中的巨大意义,如果将视角进一步延伸至法治中国的建设,那积极守法无疑可借由公民意识的培育,在破除臣民意识的同时,助力法治中国加快推进。
(二) 为法治社会建设夯基固本
习近平总书记在新一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四次集体学习时指出,要“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法治国家、法治政府与法治社会三者虽指向不一,但却紧密相连。其中,“建设法治社会是建设法治国家的条件……建设法治社会是建设法治政府的目标”[31]。法治社会是在规则治理基础上的社会自我之治。[32]社会自我之治的实现有赖于社会共同体的形成,而社会共同体形成的关键又在于每一个公民主体意识和法治意识的提升。积极守法观之实践在推动公民意识形成,确证公民身份的同时,亦使得公民的主体意识与法治意识逐步养成,并最终成为法治社会中“法律上的人”。不仅如此,积极守法作为基于法律规范上的公民间的互动,其良性发展还有助于形成对于法律规范与法律精神的认同,并在此基础上逐渐生成法治社会所必需的公共理性。因此,我们在讨论法治社会的建设之时,不仅要关注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强弱关系、法治社会建设的战略定位等宏大命题,亦不能忽视能够切实推动法治社会向前迈进的具体措施。积极守法作为法治社会夯基固本的有效方法应当得到我们应有的重视。
(三) 推动善治的同步实现
如果将法治置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语境中进行讨论的话,就必然涉及善治的问题。对于法治与善治的关系,有学者评论道,“一般意义上的法治应当是良法与善治的有机结合”[33],还有观点主张,“法治是一种自治性的善治,它需要公民参与治理过程”[34]。因此,善治作为一种国家治理理论,也同时构成法治建设的重要内容,善治实现的过程也是法治化的过程。善治的核心思想是使国家的权力向公民社会回归[35],多元参与和合作治理是其区别于以往国家治理方式的鲜明标志。公民参与的实现当然能够在现有体制中得到一定程度的实现,但如前所述,积极守法也是公民参与的重要实现机制。如果我们可以建构一个系统对积极守法这一形式予以支持的话,在丰富公民参与渠道的同时,还能弥补公权力的短板,让公民社会与民主政府相得益彰,进而推动善治与法治的实现。
[1] 亚里士多德. 政治学[M]. 吴寿彭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65: 199.
[2] John Austin. The Province of Jurisprudence Determined [M].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21.
[3] 韦恩·莫里森. 法理学: 从古希腊到后现代[M]. 李桂林, 等译.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3: 353.
[4] 甘德怀. 从命令到规则: 哈特对奥斯丁的批判[J]. 法制与社会发展, 2007(5): 34.
[5] 冯粤. 论积极守法[J]. 伦理学研究, 2008(3): 11.
[6] 倪正茂. 法律的主体与法律的主人[J]. 人文杂志, 2002(2): 46.
[7] 陈云良. 打假要靠谁——对梁彗星先生的诘词[J]. 书屋, 2003(2): 68.
[8] 李晓亮. 老汉砸车发泄“斑马线之怒”[EB/OL].http://opinion. voc.com.cn/article/200907/200907160933367950.html.2009-07-16.
[9] 高永周, 杨遂全. 共饮人的酒后驾车劝阻责任[J]. 贵州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9(3): 129.
[10] 哈贝马斯. 在事实与规范之间——关于法律和民主法治国的商谈理论[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3: 446.
[11] 詹世友. 公共领域·公共利益·公共性[J]. 社会科学,2005(7): 67.
[12] 杨仁忠. 论公共领域对培养当代中国公民意识的独特作用[J].理论探讨, 2013(1): 74.
[13] 魏健馨. 论公民、公民意识与法治国家[J]. 政治与法律, 2004(1): 36.
[14] 张金岭. 公民意识与社会领域内“合法性”的建构[J]. 浙江社会科学, 2011(5): 49.
[15] 唐君毅. 人文精神之重建(一)[M]. 广西: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 61.
[16] 胡弘弘. 论公民意识的内涵[J]. 江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 2005(1): 71.
[17] 秋风. 公共利益呼唤积极公民[J]. 中国新闻周刊, 2013(6): 59.
[18] Hart, H L A. Positivism and the separation of law and morals [J]. Harvard Law Review, 1958(71): 615.
[19] 美国智库兰德公司: 2020年, 中国将成为世界上最穷的国家[EB/OL]. http://ido.3mt.com.cn/Article/201009/show2003114 c31p1.html. 2010-09.
[20] 朱彩霞. 中西方公民意识发展路径及特点的比较分析[J]. 东岳论丛, 2013(4): 41.
[21] 布赖恩·特纳. 公民身份与社会理论[M]. 郭忠华, 蒋红军译.吉林: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公司, 2007: 10−11.
[22] Norman Fainstein, Susan S. Faristein. Participation and in New York and London: Community and Market under Capitalism [C]// Robert Fisher, Joseph Kling. Mobilizing the Community: Local Politics in the Era of the Global City. California: Sage Publications, 1993: 55.
[23] 徐文新. 专家、利益集团与公共参与[J]. 法律科学, 2012(3): 47.
[24] 黄冬娅. 以公共参与推动社会问责: 发展中国家的实践经验[J]. 政治学研究, 2012(6): 99.
[25] 尹文嘉, 唐兴霖. 迈向共同治理: 社会建构下的公共参与及模式转换[J].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 2014(3): 152.
[26] 程关松. 社会管理创新领域的公共责任及其法治化[J]. 江西社会科学, 2012(5): 148.
[27] 李林. 全民守法是法治建设的基础工程[N]. 人民日报, 2013-11-07(07).
[28] 汤可敬. 说文解字今释(上册)[M]. 长沙: 岳麓书社, 1997: 424.
[29] 陈云良. 加快建设法治中国可走的四条捷径[J]. 法制与社会发展, 2013(5): 22.
[30] 刘泽华. 从臣民意识到公民意识的转变[J]. 炎黄春秋, 2009(4): 81.
[31] 姜明安. 论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建设的相互关系[J].法学杂志, 2013(6): 1.
[32] 江必新, 王红霞. 法治社会建设论纲[J]. 中国社会科学, 2014(1): 144.
[33] 何志鹏. “良法”与“善治”何以同样重要[J].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4(3): 138.
[34] 肖北庚. 法治社会: 法治演进的逻辑必然[J]. 法制与社会发展, 2013(5): 40.
[35] 陈秀娟. 公民教育·公民社会培育·善治的当代诉求[J]. 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9(4): 120.
Observing the law positively: a neglected dimension of rule by law
HU Guoliang
(School of Law,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3, Chin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aw practice, our view of abiding by the law has experienced from the negative view of obey the law to the limited positive concept of observing the law, from obedience-centric to human rights-centric. And it has built up a brand new positive law-observing concept, centered on the protection of legal interests. In the view of the normalization of law, observing the law positively can be divided into the legal part and the part on which the law does not impose banning. From the analysis of behavior, observing the law positively can be divided into two types of behavior: inhibition and dissuas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public domain, observing the law positively is actually an expression of the consciousness of individual citizens. On this basis, the whole society can generate a citizen consciousness and public rationality. The citizen consciousness and the requirements of citizen participation implied in observing the law positively exert great impact on breaking the subject consciousness, constructing the society ruled by law, and realizing the good governance. Hence, observing constitutes the law positively an important dimension of the legal construction.
observing the law positively; public domain; citizen consciousness; a society under the rule of law
DF052
A
1672-3104(2015)01−0066−07
[编辑: 苏慧]
2014−09−03;
2014−09−30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加快建设法治中国研究”(13&ZD032)
胡国梁(1989−),男,江西泰和人,中南大学法学院2013级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经济法学,法治基础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