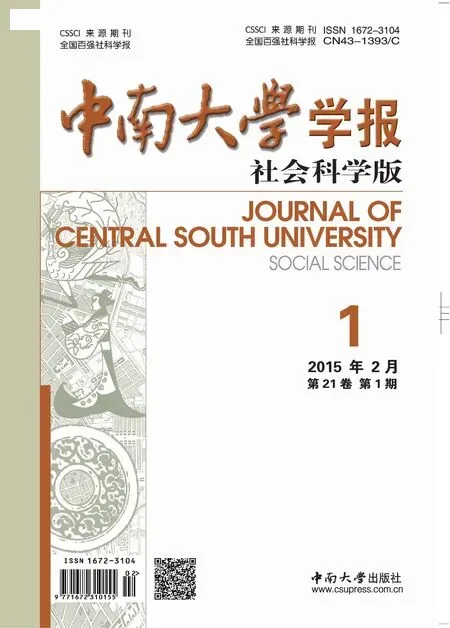对积极的一般预防论中量刑基准的反思及其启示
2015-01-21李冠煜
李冠煜
(华中师范大学法学院,湖北武汉,430079)
对积极的一般预防论中量刑基准的反思及其启示
李冠煜
(华中师范大学法学院,湖北武汉,430079)
刑罚目的与量刑基准关系密切,量刑时必须考虑预防犯罪的目的。积极的一般预防论在目的刑论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它试图从提升公民的法律信仰、发扬公众的守法精神、强化一般人的法律忠诚信念的角度正面论证一般预防的积极效果。但是,它所提倡的量刑基准可能不利于实现预防效果,无助于提供清晰的刑罚限度,导致处罚的扩大化和严厉化。通过反思积极的一般预防论中量刑基准的缺陷,可以给我国刑法理论带来深刻的启示。
积极的一般预防;消极的一般预防;特别预防;责任;量刑基准
一、刑罚目的与量刑基准
自欧洲18世纪上半叶的启蒙运动以来,刑罚目的论大致经历了如下变迁:一般预防论→绝对的报应刑论→特别预防论→并合刑论。[1]在这一漫长的过程中,刑法学派由对立趋于融合,刑罚由严厉变得宽和,刑罚理念由一元转向多元。大部分学者主张,刑罚的目的在于预防犯罪,量刑时也必须考虑如何有效地实现这一目的。在此意义上,量刑作为实现刑罚目的的手段,应当以刑罚目的为前提。换言之,要在与刑罚目的一致的方向上进行量刑。因此,刑罚目的制约量刑,包括决定量刑基准。
大陆法系刑法学界普遍认为,量刑基准是指导量刑情节适用的一般性原理或方法,属于量刑论的核心内容。量刑基准的理论就是处理责任和预防关系的理论。例如,德国学者彼得斯(Karl Peters)在20世纪30年代的研究中,揭示了作为分析量刑过程的各种要素:①评价的基础(Bewertungsgrundlagen);②评价的观点(Bewertungsgesichtspunkte);③评价的基准(Bewertungsmaßstäbe)。在此,①意味着刑罚目的,②是发现从各个刑罚目的推导出的量刑情节的观点,③决定同样从各个刑罚目的推导出的量刑情节的评价方向和重要性。[2]
可见,量刑论是刑罚论的一部分,量刑基准的内容取决于刑罚论的基本立场。“原因在于,要说明量刑应当依据的标准,就必须从刑罚的正当化根据出发,即必须说明为什么刑罚是正当的、何种程度的刑罚是正当的这一刑罚学的根本问题。”[3]“换言之,对具体犯罪的量刑以及具体刑罚制度的取舍,都取决于对刑罚功能、本质与目的的认识。”[4]所以,在不同的刑罚目的观下,必然产生不同的量刑基准。如果采取绝对的报应刑论,必将以犯罪的危害性尤其是危害结果作为量刑基准;如果采取一般预防论,就会将犯罪的危害性或犯罪动机作为量刑基准;如果采取特别预防论,就会把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作为量刑基准;如果采取并合刑论,基本上必须同时以犯罪的社会危害性和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作为量刑基准。①而且,由于量刑基准本身就明确了量刑时应当考虑的因素及其评价方法,所以,刑罚目的也不可避免地会影响量刑情节的适用。“在量刑阶段不应考虑与刑罚目的不相容的情况的意义上,刑罚目的限制各个量刑事实的范围,发挥决定量刑事实果然是加重刑罚、还是减轻刑罚的评价方向的作用。”[5]
总之,“所谓刑罚目的,是通过科处刑罚以对行为人或一般人产生预防犯罪的影响的目的。这种刑罚目的,常常被称作‘目的性的量刑事由’。作为目的性量刑事由的刑罚目的,被区别为一般预防目的和特别预防目的”[6]。因此,量刑时必须考虑预防犯罪的目的。“手段对目的从属性决定了量刑必须以服从刑罚目的为要求”[7],这既是预防犯罪的要求,也是量刑公正的要求。
二、积极的一般预防论的兴起
积极的一般预防论,又称为一般预防的积极方面、统合的一般预防或肯定性一般预防。该说认为,适用刑罚是为了唤醒普通公民对犯罪现象的厌恶情绪,以维持、强化公民的规范意识及其对法秩序的信赖。就其本质而言,这是一种刑罚鼓励论,即刑罚的实际效果取决于社会公众是否由于刑罚的适用而自愿遵守法律、更加信赖规范、提高忠于法律的程度。简言之,刑罚的激励作用决定了刑罚的预防效果。
作为目的刑论的重要成员之一,积极的一般预防论的提出有其特定的社会背景和刑事政策理由。科技进步和生产力的发展在大大提高人们生活水平的同时,也使整个社会充斥着各种危险——交通事故、环境污染、食品安全、金融欺诈、有组织犯罪等,这些都可能严重侵害个人法益、社会法益乃至国家法益。对此,德国学者贝克(Ulrich Beck)创立了风险社会理论。那么,在这种危险社会中,刑法应当处于何种地位,直接关系到刑法机能的设计和刑法模式的选择。一般认为,为全面应对风险、充分保护法益,危险社会中的刑法具有处罚的早期化、处罚的严罚化、处罚的扩大化的特征,其机能也从事后处理机能向事前预防机能转移。[8−10]这意味着,刑法模式应当从传统的核心刑法转换为危险减少刑法,一般预防的目标设定要扩张至社会中所有的重要领域。于是,积极的一般预防论在今天的德国刑法学界占据了优势地位[11],并随着消极的一般预防论和特别预防论的衰退,逐渐成为欧洲主流的刑罚目的论之一。[12]
在德国,许多刑法学者支持积极的一般预防论,因而产生了多个版本。例如,哈塞默(Winfried Hassemer)指出,预防刑法与传统的、以对不法和责任的报应为目的的刑法不同,首先应当具有以效果为志向的刑法的特征。以预防为志向的刑法被归纳为,根据刑罚威吓、刑罚宣判和行刑被期待的或者对人的犯罪决定自由产生影响的外部效果。[13]而且,刑法体系的地位处于社会控制的领域之中。刑法体系是其部分领域。所以,刑罚不以对潜在犯罪人的威吓为课题,而以旨在对共同体规范意识的有效帮助为课题。[14](20)这样,科处刑罚是为了有助于提高共同体的规范意识。雅各布斯(Günter Jakobs)则认为,刑罚清楚地并且高度地被使用刑罚后果所归属的行动承受了一种可能性,一种必须普遍地把这种行动作为不值一提的行动选择来学习的可能性。这不是威吓意义上的一般预防,而是学会对法律的忠诚意义上的一般预防。对积极的一般预防的经验性考察总是多少不适当地发生影响,但是,它只涉及到这样一些情况即个人的或社会心理的结果,而不涉及到这个理论的核心:当因为规范被损伤而认真地采取一个程序时,刑法完全在交往的层面不断支撑被搅乱的规范有效性(Normgeltung),并且,这同时意味着,因此而显现社会的不变的同一性。[15]因此,刑法的任务被设为作为“规范妥当的确证(Bestätigung der Normgeltung)”或“规范妥当的承认(Anerkennung von Normgeltung)”的“规范信赖的训练”(Einübung des Normvertrauens)。[14](20−21)那么,按照这种刑法机能化的规范保护主义立场,行为是对规范适用的损害,刑罚是对这种损害的清除。[16]科处刑罚是为了再次确认和证明法规范的有效性,促使公民学会信赖和忠诚于法规范。可是,罗克辛(Claus Roxin)根据刑法机能化的法益保护主义主张,刑法只应当保护具体的法益,不保护政治的、道德的确信、宗教上的教义、关于世界观的意识形态、纯粹的感情等。这是刑法的根本思想。[17]于是,一般预防的积极方面“反映在一般地维护和加强对法律秩序的存在能力和贯彻能力的忠诚上”。由此,刑罚就具有了这样的任务,“在法律共同体中证明法律秩序的牢不可破,并且由此加强人民的法律忠诚感”。[17]这个作为纯粹威慑作用的观点,在今天仍然具有很大的意义。准确地考察,在积极的一般预防中,还可以区分出三个既相互区别又相互交叉的目标和作用:学习效果,即通过刑事司法活动在人民中号召学会法律忠诚的效果;忠诚效果,即国民通过看见法律得到贯彻执行而产生的效果;满足效果,即公众基于对违法行为的惩罚从而使其法律意识得到抚慰,及其与违法行为人的冲突被看作是已得到了结而出现的效果。[18]
由于在基本理念和解释方法上深受德国刑法理论的影响,部分日本学者也赞同积极的一般预防论,特别是在行政刑法学的范畴中。例如,藤木英雄在公害犯罪处罚的领域中强调刑法的社会伦理机能、规制机能,尽管没有明示,但的确在确立加害一方犯罪事实认识的意义上,可以发现积极的一般预防论的开端。山中敬一则在刑事规制的语境中将现代社会理解为“危险社会”,因而作为刑法的课题,举出抽象危险犯这种犯罪构成要件的创设、伦理形成机能的当否、为定立国民行动规范的刑法机能的当否、成否。他认为,今天,即使存在权力滥用危险的国家刑罚,也在一定的范围内操纵,如果对社会形成不起作用,就难以在危险社会中进行犯罪的处置。在环境犯罪、经济犯罪、组织犯罪等许多局面下,不可能预定和谐地获得由神看不见的手造就的市民和平,不能忽视的是,需要特殊的国家保护。为对其予以补充强化,不得不依靠作为必要恶的刑罚,这是不可否定的。对于定立国民的行动规范时刑法应否发挥一定的机能,基于刑事立法的社会意识的形成、尤其是唤醒守法意识的机能在交通道德和环境道德中实际上还是发挥了很大作用。前野育三也指出,在环境犯罪中,逐渐形成基于得失的奖励体系和教育体系,因此,在其形成过程中,刑罚的伦理感觉形成机能比在有关传统犯罪的领域更为明显地表现出来。[14](290−291)
较之于消极的一般预防论,积极的一般预防论以别样的社会心理假设为前提,试图从提升公民的法律信仰、发扬公众的守法精神、强化一般人的法律忠诚信念的角度论证一般预防的有效性。这种心理假设是正面的,而不是负面的;是进取性的,而不是退避性的;是应当予以褒扬的,而不是应当予以贬抑的。正是基于这种假设,积极的一般预防论者描绘了更加富有前景的美好蓝图。消极的一般预防论单纯强调刑罚的威慑效应,而积极的一般预防论主张刑罚具有帮助效果、学习效果、忠诚效果、满足效果等多重功效。仅就理论基础和预期效果而言,消极的一般预防论和积极的一般预防论就表现出了明显的对立。
三、对积极的一般预防论中量刑基准的反思
然而,积极的一般预防论也存在一般预防论的某些通病。例如,刑罚依旧作为实现预防目的的手段,犯罪人无法摆脱预防工具的地位;对于预防效果的有效性,既不能在经验上准确描述,也不能在实践中确切证明,等等。除此之外,积极的一般预防论倡导的量刑基准还有几点软肋,必须给予高度重视。
第一,放弃以他行为可能性为基础的责任构造,直接影响量刑基准和预防效果的创设。关于作为责任论基础的意思自由问题,曾经存在非决定论和决定论的对立。但是在今天,这种对立已经相当缓和,即非决定论也肯定素质、环境对意思自由的制约作用,逐渐变为相对的非决定论;而决定论在承认法则性的同时并不完全否定意思自由,逐渐变为柔和的决定论。无论如何,即使意思自由的有无不能被今天的科学证明,但也不能被否定。既然刑法理论以此为前提,那么它就是假说。在规范责任论中,无论是相对的非决定论,还是柔和的决定论,都以他行为可能性为基准。问题在于,该基准究竟是具体的他行为可能性,还是抽象的他行为可能性。[19]罗克辛、雅各布斯、许内曼(Bernd Schünemann)等德国学者为更直接地发挥积极的一般预防效果,放弃了以他行为可能性为基础的责任范畴,通过在传统的罪责概念中补充预防必要性而创造了新的罪责概念。[20−22]于是,责任内涵的变化引起责任功能的转变。以往的责任概念主要发挥刑罚限定机能,以限制国家刑罚权的任意发动;现在的责任评价本身就要受到预防必要性的影响,显然已不适宜于控制刑事政策的冲动。一方面,如果根据这种责任概念设置量刑基准,量刑就会以一般预防的必要性为基础而不以责任为基础,刑罚的程度将根据一般预防必要性的大小来量定,责任概念似乎是多余的。另一方面,假如根据这种责任概念来预测一般预防效果,作为引发刑事可罚性条件之一的预防必要性与作为刑罚目的之一的一般预防就会自然地站在同一阵线,预防效果将被放大,刑事政策的考量可能突破责任主义的保障底线。
第二,“规范意识”“法律忠诚感”“规范信赖”等概念过于抽象,无助于提供清晰的刑罚限度。由于积极的一般预防论以肯定能够影响社会心理为其预设前提,所以采用了“规范意识”“法律忠诚感”“规范信赖”等横跨刑法学和心理学的术语来诠释预防效果。笔者认为,“规范意识”是指公民自主遵守刑法规范的认知、觉察、感觉等情绪;“法律忠诚感”是指公民不违反、不背叛、不否认法律的诚实、守信、服从等心理;“规范信赖”是指一般人信任法规范的效力,并依靠这种信任而选择行为的态度。这些通过科处刑罚而产生的各种效果,将作为社会心理事实在预防犯罪的意义上被理解,不仅决定刑罚目的的内容,而且提供刑罚适用的界限。但是,无论用哪一个概念来充实积极的一般预防论,都不能推导出相对明确的量刑基准。例如,站在实在法规范的角度,犯罪是对实在法规范的否认,刑罚是对犯罪的实在法规范性报应。在没有否认实在法规范效力的地方不需要刑罚,刑罚的分量是与否认实在法规范效力的程度相适应的。[23]那么,“否认实在法规范效力”的反面就是“规范效力的确证”或“法律忠诚的训练”,即刑罚的轻重要与确证规范效力的努力大小或法律忠诚的训练强度相适应。可是,这样的解释无异于同语反复,还是没有彻底回答如何确定积极的一般预防论的量刑基准。
第三,可能产生积极的责任主义,并回到绝对报应刑论的思维轨迹。在重视以积极的一般预防论作为刑罚目的的场合,可能推导出一种积极的责任主义。[24]理由在于,积极的一般预防论寻求刑罚对社会心理的重塑,只要法官认为能够满足一般预防需要的,就可以对犯罪人科处刑罚;积极的责任主义也认为责任是刑罚的根据,只要有责任,就应当科处刑罚。显然,这里的一般预防的必要性和责任共同构成刑罚适用的条件:在行为人实现了不法之构成要件后,他就是有罪责的。同时,由于不法被实现,通常也就存在一般预防的必要性。最为关键的是,在国家对待一般预防效果的主动期望和针对责任机能的张扬态度方面,二者表现出了内在的一致性。积极的责任主义不利于充分发挥刑罚限定机能和人权保障机能,在追求积极的一般预防效果时应对此保持警惕。但是,积极的一般预防论不仅和积极的责任主义有关,而且和绝对的报应刑论有关。根据雅各布斯的见解,刑罚的功效在于,通过与犯罪的对抗而确证了社会同一性。刑罚不只是一种维持社会同一性的工具,而且已经是这种维持本身。尽管可以把对社会的或个人心理的结果的种种希望与刑罚联系起来,但刑罚已经不依赖于这些结果,而意味着一种自我确认。[15](103)可见,犯罪否定法规范的同一性,刑罚通过否定犯罪来维持法规范的同一性,即刑罚是对犯罪的否定之否定。而且,作为法规范一部分的刑罚的目的在于维持法规范的同一性或有效性,实质上就是维持刑罚本身的效力,即刑罚除了自我确证或自我维持之外不存在任何目的。因此,仅就以上两点而论,积极的一般预防论已经相当接近黑格尔(Friedrich Hegel)的报应理论,以至于实际上建立了一种新的绝对主义。
第四,舍弃传统的责任概念以及同绝对报应刑论的藕断丝连,可能导致处罚的扩大化和严厉化。积极的一般预防论通过创造新的责任概念和预防目的,意图建立与众不同的刑罚目的论。一方面,这与上述第一点不足有关。放弃传统责任概念的结果是失去处罚必要性的外在制约原理[25],可能导致处罚的扩大化。在传统的责任范畴中,责任内部不包括预防目的,责任和预防处于不同等级,责任可以从外部制约预防犯罪来考虑;而在答责性(Verantwortlichkeit)的范畴中,刑法性责任的内部包含着预防必要性,罪责和预防处于同一等级,罪责无法在内部限制预防犯罪的考虑。尽管积极的一般预防论者声称:“罪责原则的法治国保护作用,也不会通过对预防性刑事惩罚必要性的要求而受到损害。……刑罚总是以罪责为条件的,因此,还没有什么预防性刑罚化的需要(Pönalisierungsbedürfnis),能够大得可以对一种与罪责原则相矛盾的刑事惩罚加以正当化。”[18](558)但是,作为刑法性责任中处于相同等级的条件,罪责的刑罚限定机能轻易地被一般预防的刑罚扩张机能所吸收,不能指望罪责可以抗衡一般预防的必要性。另一方面,这与上述第二点、第三点不足有关,没有同绝对报应刑论划清界限的结果是失去处罚相当性的制约原理,可能导致处罚的严厉化。积极的一般预防论旨在通过处罚削弱、撼动规范意识的行为来培养、强化规范意识,那么,刑罚的轻重应该与规范意识的动摇程度相适应。尽管积极的一般预防论的本意是从量刑中排除威吓预防和绝对报应的考虑,但是不太成功。这表现在两种情况下:第一,在许多严重犯罪被冲动实施、不怎么能期待威吓效果的场合,以规范意识的动摇为根据可能科处重刑;第二,认可防止由于过剩威吓而破坏规范意识的意义。在前者中,若将这一主张彻底化,只要发生犯罪,规范意识一定动摇,必须科处刑罚,这就回到绝对报应刑论的思想。的确,虽然在使目的先行这点上,积极的一般预防论能够与绝对的报应刑论相区别,但是,假如这里的目的是对社会心理学上规范的信赖维持的必要性和对法律制度的信赖保持的必要性之类的东西,那么对其难以在经验上确认这一点上,作为实际的现象和绝对的报应没有差异。而且,与报应刑论不同,由于对责任予以机能的定义,基于责任主义的刑罚限定不起作用。这不仅造成必罚化,也有重罚化的可能性。在后者中,过剩威吓的防止是对取代责任这种外在制约的积极一般预防论固有的内在制约。然而,国民的规范意识这一范畴非常暧昧,仅仅具有排除明显与行为不相均衡的威慑的效果。[25](469−470)因此,责任概念的机能化、预防目标的不明确以及未彻底告别绝对理论的摇摆立场,会直接造成处罚的扩大化和严厉化。
四、启示
反思积极的一般预防论中量刑基准的缺陷,可以给我国刑法理论带来如下启示。
首先,尽管预防犯罪是独立的刑罚目的,但量刑时对预防目的的追求不能超出罪刑均衡的范围。量刑时必须在考察责任和预防关系的基础上,分配给双方适当的刑罚。换言之,处理责任和预防的关系,就是处理责任刑和预防刑的关系。所谓责任刑,是指与责任相适应的刑罚。这里的“责任”是广义上的责任即量刑责任,其大小由违法性的程度和有责性的程度共同决定。而违法性和有责性反映了行为的客观危害和行为人的主观恶性,体现的是罪行轻重。社会危害性正是客观危害和主观恶性的有机统一,能够决定罪行的轻重。所以,与责任相适应的刑罚就是与罪行相均衡的刑罚。所谓预防刑,是指预防犯罪所需要的刑罚。这里的“预防”,包括一般预防和特别预防。一般预防刑主要由责任刑决定,特别预防刑主要由人身危险性决定。由于责任刑本身就具有一般预防的效果,所以不能用一般预防刑加重或减轻责任刑。由于特别预防与罪行轻重无关,所以允许在责任刑的范围内用特别预防刑对其进行修正,例外情况下,还可以突破责任刑的下限量刑。总之,根据量刑基准的要求,只有在以行为责任为基础的刑罚幅度内适当地考虑预防必要性,或者在根据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确定的刑罚范围内合理地兼顾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才能进行公正的量刑。
其次,预防犯罪是重要的量刑基准,量刑时必须处理好一般预防和特别预防之间的关系。量刑时仅仅追求积极的一般预防作用,很难得到满意的结果。这是因为,一般预防的必要性和特别预防的必要性经常不一致。对此,我国刑法理论通说历来主张,一般预防和特别预防之间存在着一种对立统一的关系。两种预防的对立性是由对象的差异性决定的,两种预防的统一性是由目的共同性、功能互补性决定的。在刑事法律活动中,要根据不同情况对预防犯罪的两个方面有所侧重。具体到量刑阶段,首先考虑特别预防的要求,即根据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判处刑罚;其次还要兼顾一般预防的要求,即根据刑事立法规定、社会形势、犯罪率等判处刑罚。[26]笔者基本同意上述见解,但认为不宜一概而论。量刑时应结合具体案情来决定是以一般预防为主,还是以特别预防为主。详言之,对人身危险性较小的犯罪人、常见多发性犯罪、社会治安形势恶化期间实施的罪行科处刑罚时,应以侧重一般预防的双面预防,即一般预防为主,特别预防为辅。反之,对人身危险性较大的犯罪人、罕见偶发性犯罪、社会治安形势稳定期间实施的罪行科处刑罚时,应以侧重特别预防的双面预防,即特别预防为主,一般预防为辅。显然,积极的一般预防论不能抹杀特别预防论的合理性。
再次,刑罚消极的一般预防效果是客观存在的,量刑时必须处理好消极的一般预防和积极的一般预防之间的关系。根据机能的不同,一般预防可分为消极的一般预防和积极的一般预防。[27]其实,德国学者费尔巴哈(Paul Johann Anselm Feuerbach)基于“心理强制说”提出的一般预防理论即为消极的一般预防论,又称为一般预防的消极方面、威慑的一般预防论或否定性一般预防。该说认为,适用刑罚会对社会中所有潜在违法者的心理产生威慑作用,警告其远离犯罪,以达到预防犯罪的效果。就其本质而言,这是一种刑罚威胁论,即刑罚的实际效果取决于社会公众是否由于刑罚的适用而抵制犯罪的诱惑、预知受刑的痛苦、体会刑罚的恐怖。简言之,刑罚的威吓作用决定了刑罚的预防效果。借助刑罚的威慑功能实现刑罚一般预防的目的,早已成为我国刑法理论界和实务界的共识。刑罚的一般威慑功效通过立法机关制定刑罚以及司法机关适用、执行刑罚来实现,使意图犯罪者对刑罚产生畏惧心理而不敢犯罪。[28]既然一般预防机能的内部有消极的一般预防和积极的一般预防之分,那么量刑时就必须处理好二者之间的关系:既不能过于重视消极的一般预防,使刑罚的威慑功能完全抵销了刑罚的教育、安抚、鼓励功能;也不能过于强调积极的一般预防,使刑罚的教育、安抚、鼓励功能彻底吸收了刑罚的威慑功能。因此,量刑时不仅要使刑罚与犯罪的客观危害程度或犯罪动机的强弱相适应,也要使刑罚与唤起公民规范意识的难度或教导公民信赖法律的状况相适应。这表明,法官在适用刑罚时应当同时考虑到两种一般预防的效果,在非刑罚处理方法和刑罚之间、在限制自由刑和剥夺自由刑之间、在短期剥夺自由刑和长期剥夺自由刑之间、在生刑和死刑之间、在暂缓执行刑罚和立即执行刑罚之间做出适当的选择。
最后,在迫切追求刑罚积极的一般预防效果时,还要注意由于量刑倒推的“象征性立法”的机能边界。不管是主张刑法的任务在于法益保护,还是认为刑法的任务在于规范保护,都不能完全否定“象征性立法”的存在和刑罚的象征性机能。近年德国刑事立法的特色,可以评价为刑罚积极主义(单独地可将重罚化、保安主义、象征性立法作为关键词举出)划定处罚范围的实体刑法的机能低下。[29]“象征性立法”源自风险社会背景下立法者对刑法机能的反省以及对公民更高的安全保障诉求的回应,因此,安全保障的思想在刑法中被允许,“以预防为导向的刑法”也具有了正当性。“象征性立法”贯彻了安全刑法的理念,在设置刑罚法规时以处罚的早期化和严厉化为主要特征。所以,“象征性立法”主要与法益保护的界限有关,而象征性刑罚法规即指对于保障和平的共同生活不必要的、为追求有权者的感情绥靖和国家的自我演出这种刑法外的目的的刑罚法规。[17](259)具体而言,这里涉及的刑法条文首先不是在详细地说明具体的保护效果,而是应当服务于对特定价值的认识或者服务于反对被看成是卑鄙的政治和信仰组织自我表现的姿态。这经常是以平息选民的情绪为目的的,在这里,通过预先可知无效果的法律,能够使人造成这样的印象:政府在与不受欢迎的行为和状态进行的斗争中,“已经取得了一点成绩”。因为所有的刑法条文,多少都带有一点应当对人民的意识形成发挥作用的象征性特点,所以,“象征性”的立法因素并不是一般不允许的。[18](18)可见,“象征性立法”具有很大的形式价值和宣示意义,象征性刑罚法规只是为了迎合公民的处罚感情,表明国家的政策立场而制定。在危险社会中,积极的一般预防论成为时髦的刑罚理论,但是,有必要通过检讨宣言性的“象征性立法”以及不那么重视实效性的象征性刑罚法规来思考预防效果的作用范围。在刑罚裁量阶段,不能为了满足积极一般预防的需要而在刑罚制定阶段进行“象征性立法”并制定大量的象征性刑罚法规。因此,诸如我国《刑法修正案(八)》增设危险驾驶罪、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的合理性,仍然值得商榷。关于前者,立法者意图通过对危险驾驶行为处罚的早期化,实现预防交通犯罪的目的。然而,由于同传统的入罪标准相隔太远,该条规范要么可能被虚置,要么可能被滥用,其立法效果值得怀疑。关于后者,立法者打算通过对恶意欠薪行为处罚的严厉化,实现预防劳动犯罪的目的。但是,由于新设的构成要件过于复杂,该条规范要么可能使雇主依然游离在刑事制裁的界限之外②,要么可能使劳动者完全丧失获取报酬的机会③,其立法作用令人深思。因此,即使现实中对某些危害行为存在迫切的处罚必要性,也不能过分依赖积极的一般预防效果,有时,这反而有损被害人的利益。所以,应在恪守刑法谦抑原则的前提下,加强有关部门法的配合,确保刑法法益保护机能和人权保障机能的平衡。
注释:
① 具体来说,并合刑论内部还有各种不同的主张,如“分配说”“幅的理论”“位置价值说”等。
② 由于法官对雇主宣告无罪,认定其行为不符合本罪的构成要件,这将迫使劳动者只能通过民事诉讼或行政诉讼维权,劳资双方又回到了纠纷的原点。这也成为许多学者以强化行政执法为由质疑其入罪正当性的主要论据之一。
③ 由于法官对雇主宣告有罪,判处自由刑和财产刑,这会进一步激化劳资双方的对立,劳动者最终也许得不到任何报酬。这也成为部分学者提倡将本罪规定为亲告罪的主要论据之一。
[1] 大谷实. 刑法讲义总论(新版第4版)[M]. 东京: 成文堂, 2012: 43.
[2] 城下裕二. 量刑基准的研究[M]. 东京: 成文堂, 1995: 13−14.
[3] 冯军. 量刑概说[J]. 云南大学学报(法学版), 2002(3): 31.
[4] 张明楷. 新刑法与并合主义[J]. 中国社会科学, 2000(1): 105.
[5] 冈上雅美. 量刑判断的构造——序说[J]. 法研论集, 1988(48): 97.
[6] 川崎一夫. 体系的量刑论[M]. 东京: 成文堂, 1991: 158.
[7] 赵淞. 刑罚目的与量刑[D]. 北京: 中国政法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11: 13.
[8] 乌尔里希·齐白. 全球风险社会与信息社会中的刑法: 二十一世纪刑法模式的转换[M]. 周遵友, 江溯等译. 北京: 中国法制出版社, 2012: 162−272.
[9] 高桥则夫. 刑法保护的早期化与刑法的边界[J]. 法律时报, 2003(2): 15−18.
[10] 马克昌. 危险社会与刑法谦抑原则[J]. 人民检察, 2010(3): 5−9.
[11] 克劳斯·罗克辛.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德国刑事政策与刑法学的发展[J]. 川口浩一, 葛原力三译. 关西大学法学论集, 2000(1): 174−175.
[12] 松宫孝明. 犯罪论与刑罚论——代问题提起[J]. 刑法杂志, 2007(2): 222−223.
[13] 温弗里德·哈塞默. 现代刑法体系的基础理论[M]. 堀内捷三编译. 东京: 成文堂, 1991: 23−39.
[14] 金尚均. 危险社会与刑法——现代社会中刑法的机能与界限[M]. 东京: 成文堂, 2001.
[15] 格吕恩特·雅科布斯.行为责任刑法——机能性描述[M]. 冯军译. 北京: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7: 10, 103−104.
[16] G·雅各布斯. 刑法保护什么: 法益还是规范适用[J].王世洲译. 比较法研究, 2004(1): 107.
[17] 松原芳博. 克劳斯·罗克辛: 作为刑法任务的法益保护[J]. 早稻田法学, 2007(3): 256.
[18] 克劳斯·罗克辛. 德国刑法学总论(第1卷) [M]. 王世洲译.北京: 法律出版社, 2005: 42−43.
[19] 堀内捷三. 责任论的课题[C]// 芝原邦尔, 堀内捷三,町野朔,等. 刑法理论的现代展开——总论Ⅰ. 东京: 日本评论社, 1987: 181−187.
[20] 克劳斯·罗克辛. 刑事政策与刑法体系(第二版)[M]. 蔡桂生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1: 78−79.
[21] 京特·雅各布斯. 责任原理[J]. 松宫孝明译. 立命馆法学, 1993(4): 800−801.
[22] 贝恩德·许内曼. 现代刑法体系的基本问题[M]. 中山研一,浅田和茂监译. 东京: 成文堂, 1990: 195−196.
[23] 冯军. 刑法的规范化诠释[J]. 法商研究, 2005(6): 63−64.
[24] 铃木茂嗣. 犯罪论与量刑论[C]// 前野育三, 齐藤丰治,浅田和茂, 等. 量刑法的综合研究. 东京: 成文堂, 2005: 11.
[25] 本庄武. 从刑罚论所见的量刑基准(2)[J]. 一桥法学, 2002(2): 469.
[26] 高铭暄. 刑法学原理(第三卷)[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5: 68−72.
[27] 阿图尔·考夫曼. 法哲学与刑法学的根本问题[M]. 宫泽浩一监译. 东京: 成文堂, 1986: 157−158.
[28] 高铭暄, 马克昌. 刑法学(第五版)[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1: 220−221.
[29] 井田良. 德国刑法的现状和比较刑法研究的今日意义[J]. 法学家, 2008(1348): 176.
Reflection and revelation of sentencing criterion in the theory of positive general prevention
LI Guanyu
(School of Law,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Wuhan 430079, China)
The criminal purpose has a close relationship with sentencing criterion, so the purpose of preventing the offences needs to be considered in sentencing. The theory of positive general prevention occupies an important position in the theory of punishment ,attempting demonstrate the positive effects of general prevention in enhancing citizens’legal faith, developing public spirit of complying with the law and strengthening the majority’s convictions of law loyalty. However, the sentencing criterion advocated by the theory of positive general prevention may harm attaining preventive effects, may be helpless to provide clear penal limits and may cause expansion as well as severity of punishment. Reflecting the defects of the sentencing criterion will be able to bring some profound revelations to our criminal science.
positive general prevention; negative general prevention; special prevention; liability; sentencing criterion
D924.11
A
1672-3104(2015)01−0059−07
[编辑: 苏慧]
2014−04−10;
2014−05−15
2011年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研究生项目A类奖学金资助(留金发[2011]3005号)
李冠煜(1982−),男,湖北武汉人,华中师范大学法学院讲师,法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刑法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