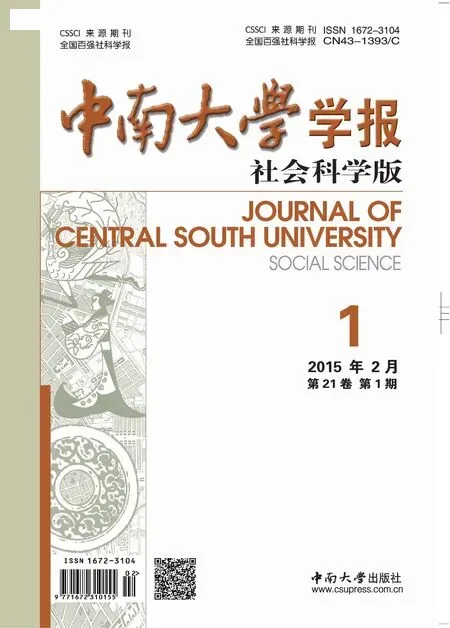情感与理性之间的彷徨
——解析休谟的《趣味的标准》
2015-01-21董志刚
董志刚
(山西大学文学院,山西太原,030006)
情感与理性之间的彷徨
——解析休谟的《趣味的标准》
董志刚
(山西大学文学院,山西太原,030006)
在18世纪的英国,趣味成为美学的一个核心概念,意指审美判断的特殊能力。休谟的美学同样是围绕趣味这一概念展开的,并且在新的哲学体系中,用情感和想象的规律阐述了趣味的内涵。然而,休谟由此也面临着与同时代美学家一样的问题,即趣味判断是否具有客观性。面对这个难题,休谟写出《趣味的标准》一文,其中他既坚持趣味的情感属性,又求助于理性,这导致他把趣味判断转化为理性认识或事实判断,最后把趣味的标准定义为正确的理性认识所需要的一系列品质。这虽然保证了趣味的客观性,但却背离了审美判断的本质。同时,休谟仅关注事实意义上的标准,忽略了价值意义上的标准,因而没有完全说明趣味差异的根源。不过,他的哲学仍然为弥补这些缺憾提供启发,即理性认识可以确定事实意义上的标准,情感可以解释价值意义上的标准。
休谟;《趣味的标准》;趣味;情感;理性
一、“趣味”的难题
“趣味(taste)”作为美学概念最早可以追溯到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但这一概念对整个近代美学发挥影响,并成为其中的核心概念,则要归功于18世纪的英国美学。在英语中,将趣味这个词用于描述对于艺术的审美经验早已有之,可零星见于本·琼森(如From Timber, or Discoveries,作于约1620—1635年)、乔治·查普曼(如Prefaces to the Translation of Homer,作于约1610—1616年)等人的作品中,到17世纪末和18世纪初,这种现象就非常普遍了,成为约翰·丹尼斯、查尔斯·吉尔登、约翰·休斯、乔治·法夸尔等人的批评文章中的常用词。不过,他们都只是经验性地使用这个词,多用来指一个时代或一个民族总体的审美倾向,后来又指个人带有主观性的鉴赏能力和取向,而没有从哲学上定义和解释趣味一词,没有确定它究竟属于何种认知能力,由哪些要素构成。
第一个试图在哲学体系中解释趣味这个概念的作家当属夏夫兹博里。他对趣味的理解与对美的认识有着密切关系。他把美的本质视为自然中神性的创造力,这种力量塑造了人的心灵和事物的外在形式;正如人们称一个行为是善的,乃是指直觉行为主体的性格或动机的善。美和善都带给人一种非功利性的快乐,不以个体的欲望和利益为标准。因而美不是事物的客观属性,既非外在感官可以捕捉,也不可根据外在标准测定,对美的把握必然要依赖一种特殊的能力,夏夫兹博里称之为“内在的眼睛”,亦即趣味。
一旦眼睛看到形象,耳朵听到声音,美就立即产生了,优雅和谐就被人知晓和赞赏。一旦行为被观察到,一旦人的情感和激情能被人觉察到(大多数人感觉到的同时就已经能分辨),一只内在的眼睛(an inward eye)就立即会加以分辨和领会漂亮的和优美的,可亲的和可赞的,否则就是丑陋的、愚蠢的、古怪的或者可鄙的。[1]
之所以将趣味称为“内在的眼睛”,是因为它像外在感官一样是一种直觉能力,可以直接把握到美,但又不是外在感官,而是心灵内部的接受能力,它接受到的不是色彩、声音等感觉观念,而是快乐的情感。
夏夫兹博里的哲学和美学思想带有浓重的新柏拉图主义色彩,这与自培根以来称霸英国的经验主义有些格格不入,但他对美和趣味所作的阐述虽显神秘,却又鞭辟入里。如何用经验主义哲学中的心理学来清晰地阐明夏夫兹博里所描绘的趣味以及美的性质便成为后来美学的重要任务。然而,夏夫兹博里也留下一个难解之谜,即如果美表现为内在的情感,这种情感是否具有客观性和普遍性?
艾迪生在18世纪英国美学中地位显赫,有人称其《想象的快感》为近代第一部英语美学专论。艾迪生重拾培根的想象概念,又援引洛克的观念论,但却为想象和美的观念增添了源于夏夫兹博里的内涵,他说,想象的快感“既不像感官快感这么粗鄙,也不像悟性快感这么雅致”[2](36)。因为想象一方面把外在事物复现为观念,另一方面也把这些观念加以改变和相互联结,所以,“想象所领悟的光与色不过是心灵中的观念,而决不是存在于物质中的性质”[2](43),想象的快感自然不同于感官快感。艾迪生以写随笔闻名,并不在意哲学推理的严密性,他虽然用想象对近代美学中的新奇、伟大和美三大范畴作了生动的描绘,但对于想象从何而来,又如何运作,以引起心灵的神秘反映却不甚明了,对于趣味的难解之谜也未提及。
哈奇生恪守夏夫兹博里的遗训,直接把趣味定义为“内在感官”:内在感官则可以把握具有“寓于多样的一致”这种特征的形式,得到一种内在的快乐。然而,内在感官并不是理性认识能力,因为“首先打动我们的是美的观念,最精确的知识也不会增加美的程度”。[3](22)如果美不依赖于理性认识,那么趣味或内在感官的客观性和普遍性便无法保证,哈奇生的辩解是,要知觉到美,前提是超脱个人的欲望和利益,而趣味则超越了外在感官,自然就是客观的和普遍的。然而,这个辩解最多也只是反证而已。
后来,包括休谟在内的诸多作家接受了想象和内在感官,用内在感官表明趣味的直觉性,用想象来解释其原因。例如亚历山大·杰拉德在《论趣味》中说:“趣味主要由几种能力的发展构成,它们通常被称作想象力,也被现代哲学家认为是内在感官或反省感官,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比外在感官更为精细和雅致的知觉。”[4]趣味所获得的美感主要源于想象在构成美的观念时的运动方式,但凡能使心灵活跃起来的运动都是令人快乐的。即便用生理学原则解释美感的博克也把趣味看做是“心灵的官能,是那些受到想象力与优雅艺术作品感染的官能,或是对这些作品形成判断的官能”[5](13)。
美学家们让趣味不同于外在感觉和理性认识,一方面是为了证明美感不同于肉体的快感,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反驳传统美学中的比例、匀称、适宜等形式原则。艾迪生在“美”之外描述了伟大和新奇,伟大便是崇高,使人感到一种“愉快的惊愕”和“极乐的谧静和惊异”;而新奇则打破了平常事物造成的沉闷,让心灵重获激情。杰拉德列举的七种趣味情感中,除了崇高感、美感、新奇感,还包括模仿感、和谐感、荒诞感和德行感,只字不提比例等概念。博克则明确反驳了传统的比例说和适宜说,所列举崇高和美的对象的各种性质超出了传统美学的范围。此前荷加斯提出“蛇形线”同样是要强调美的多样性和装饰性,这种线条不可能在数学上得到测量,比如由蛇形线构成的人体,“不管某些作者多么费力,要把人体肌肉的真正比例像数学那样准确地用线测量出来是不可能的”[6]。18世纪末的艾利逊甚至把美的根本原因归于形式所指示的“动人或迷人的心灵品质”,求助于理性来把握美无异于缘木求鱼:“研究拉斐尔的设计的画家和计较弥尔顿的韵律的诗人,都丢失了作品给予他们的愉悦。”[7](14)这样,领悟美的趣味这种能力必定是某种仿佛是神秘的直觉,如布莱尔所说:“美丽的风景和雅致的诗歌常常直接打动我们,并造成强烈的印象,此时我们无法指明我们之所以快乐的原因,……因此我们品鉴美的能力看起来更接近于一种感官的感受,而不是理解的过程。”[8]这也是18世纪的美学家常常用法语“je ne sais quoi(我不知道是什么)”来形容趣味的神秘。
二、情感对理性的反抗
当人们发现趣味这种审美能力的独特性并力主其独立性的时候,情感和理性之间的对立在美学领域才显得如此尖锐,却又难舍难分。让情感服从于理性,会让审美判断丧失其独特性,驱逐理性又会让它失去客观性。自笛卡尔以来,理性主义一路凯歌,功勋卓著,文艺也要服膺,以布瓦洛为代表的新古典主义便是明证,在英国也先后有德莱顿和蒲柏为其声张。以数学为典范的理性精神追求永恒不变的先天法则,要求斩断感性世界多变的细枝末节,让情感服从于理智和礼仪,然而这些要求到18世纪却已不再适应新兴的市民文化,尤其让标榜自由传统的英国人难以接受。
排斥理性,保卫趣味是否会让审美领域陷入混乱无序?面对这个难题,休谟显然无意退却,其《趣味的标准》(1756)一文之所以成为18世纪英国美学的经典之作,原因便在于它直面这个难题,并敢于给出一个明确的答案,虽然这个答案至今仍遭受争议。
休谟此文的推论简单而明晰。美是一种情感,而趣味是知觉美的能力,但美的情感毕竟是由某些性质或与之相应的观念引起的,而且相同的性质或观念应该引起相同的情感,所以精致的趣味表现在能够准确地辨析对象中引起美感的性质或观念。在艺术鉴赏中,精致的趣味在细腻的感觉和想象力的基础上,能够准确地观察、分析和比较艺术作品,能够发现其中的艺术法则,因而能够体验到作品中的美。总之,既然引起美感的性质和观念是客观存在的,所以能够发现它们的趣味便也是客观的,必然存在一定的标准。然而,细心的读者马上就会发现,这个结论与休谟之前的说法是矛盾的,他说过:“由同一对象激起的千百种不同的情感,都是正确的,因为所有情感都不再现对象中实际存在的东西。……美不是事物自身里的性质,它只存在于观照事物的心灵中;每一个心灵都知觉到不同的美。”[9](6)这样看来,发现引起美感的性质和观念难道不是一种理性能力吗?而且他也明言理性是好的趣味不可或缺的因素,这是不是重新让趣味服从于理性呢?同时,如果趣味依靠理性,人们又怎么会在现实中表现出那么大的差异呢?
休谟是否果真是重理性而轻情感?问题并不这么简单。在他的推论中隐含着非凡的创造性乃至革命性的思想。之所以说休谟的思想富有革命性,是因为他打破常规,不再让情感屈尊于理性,而是让理性服从情感。《人性论》当中有这样的振聋发聩之言:“理性是并且也应该是情感的奴隶,除了服务和服从情感之外,再不能有任何其他的职务。”[10](453)理性的成功在于它能确定自然世界的规律,而休谟则相信,作为人性之主宰的情感同样富有规律,而且连理性也要遵循这样的规律。在《人性论》开篇他表露雄心,要像牛顿揭示自然世界的规律一样解开人性的谜团:“在人类的行动中,正像在太阳和气候的运行中一样,有一个一般的自然规程。”[10](440−441)当他断言与情感密切相连的趣味存在标准的时候,根基便是情感同样遵循严格的规律。可见《趣味的标准》一文与休谟的整个哲学一脉相承,只要发现情感的规律,趣味的难题也许就迎刃而解了。
毋庸置疑,休谟从艾迪生那里得到很大启发,因为他所描述的情感规律正体现在想象之中。对于任何情感,人们只可直觉不可定义,但这并不代表情感是不可分析和描述的。因为情感并不是抽象的,它们总要附着于观念,与观念相互对应,相伴而行。人最初的知觉是印象,它们饱含情感,情感淡化之后成为观念,而当人想到一个观念时又生成新的情感。心灵中的各个观念总是在空间和时间中相互联结,亦即休谟所谓的想象。这种联结遵循一定的自然法则,即相似、接近和因果关系,但同时又受着情感的推动。情感本身也从不完全静止,而是遵循相似法则相互转化,例如羡慕生嫉妒,嫉妒生愤恨,但这个过程离不开观念的支撑。可以说观念是情感的媒介,情感则是观念联结的动力,两者相互转化,相互促进。这就是休谟所谓的印象和观念的双重关系。
在情感和想象的运行过程中,休谟描述了各种美感生成的机制。首先,美感不是生理反应,而是心灵面对内部观念以及想象在观念间的转移的时候形成的反省印象或间接情感。直白地说,美不在外物上面,而在印象或观念的联结之中。其次,美感也形成于想象过程中。想象总是从一个观念到另一个观念不停运动,不同的运动就产生不同的美感。想象按照自然程式转移,显得平缓顺利,便是优美。然而,想象在陌生的联结中遭遇的困难反而能让心灵获得更大的快乐,困难会激发起心灵克服它的欲望,而克服之后的成功带来更强烈的快乐。这便是崇高或伟大:“任何一种障碍若不是完全挫败我们,使我们丧胆,则反而有一种相反的效果,而一种超乎寻常的伟大豪迈之感灌注于我们心中。在集中精力克服障碍时,我们鼓舞了灵魂,使它发生一种在其他情况下不可能有的昂扬之感。”[10](472)
如果情感具有人人都要遵循的客观规律,作为情感判断的趣味就应该不可能完全脱离这些规律;即使存在各种差异,人们也有望根据这些规律评判谁对谁错,谁高谁低。正如自然界的一类现象可能也形态各异,但人们可以根据一般规律说明这些差异原因,辨别其正常或反常。更重要的是,人们在这个评判过程中,可以维护趣味的独特性,不需要过分依赖通常所谓的理性。对于近代美学而言,休谟对情感规律的阐述功不可没,非此就不会有繁荣兴盛的以心理学为依据的各派美学。
三、趣味标准的双重含义
看起来休谟的情感理论可以为趣味标准问题奠定一个坚实的基础,甚至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然而,这个结论有个前提,亦即情感的规律就等于趣味的标准。不过,这个前提未必完全正确。因为纵然这些规律不可否认,人们的趣味仍然显出巨大的差异性,而这些规律并不能规定一个人必须或应该欣赏什么样的艺术作品,或者什么样的艺术作品引发的美感才是可取的和值得赞赏的。我们也可以说,标准有着双重含义,一指符合客观规律,我们可称之为事实意义上的标准,二指存在价值差异,我们可称之为价值意义上的标准。显而易见,休谟在《趣味的标准》中抓住的是前一种含义,并依此解释趣味的个体差异如何形成,又如何根据某些标准来矫正。
休谟发现,当人们认为“趣味无争辩”的时候,所指的差异性意思并不十分明确。事实上,人们对于美丑的选择是大体一致的:“人们众口称赞优美、适当、质朴、生动,而指摘浮夸、做作、平庸和虚假的粉饰。”[9](3)不过,这些一致仅仅停留在语言层面上,一旦涉及到具体事例就言人人殊了,比如,对于一个具体的对象是否是优美的或是浮夸的,人们可能做出截然不同的判断来。所以,问题不在于人们的情感反应有差异,而在于对对象的认识有差异,换言之,只要人们得到相同的观念,便可以遵照《人性论》描述的情感规律来判定对错,一较高下。
不过,人们怎么可能从同一对象上得到不同的观念呢?这正是《趣味的标准》一文着重论述的问题。回答这个问题也需要参照休谟所继承和发扬的经验主义哲学。这个哲学传统认为认识始于感觉,但感觉到的东西并不等同于外在事物的性质,例如霍布斯发现从外物性质到心灵中的“思想(thought)”实际上经过了一系列转化,最终是“假象或幻象”;我们的听觉接受到的是一些声音,但声音本身却是物体的振动。洛克区分了第一性质和第二性质,前者有如形状、体积等,它们如实反映为心中的观念,后者有颜色、气味、冷热等,人心中关于它们的观念是主观的产物。休谟更进一步,断言人心中除了印象和观念之外别无他物,对外在世界是否存在存而不论。这并不是说休谟否认各人心中的印象和观念存在一致性,因为人类的思维规律是相同的,而是说明它们极容易受到各种因素的干扰,因此产生偏差,例如一条线因与更长的线的比较而显得比原先短,忧愁的情绪使阴雨连绵的天气倍加昏暗。
与此同时,还有一个关键因素影响着人们的判断,那就是因习惯而形成的“通则(general rules)”。习惯使人们相信某些印象或观念之间存在必然联系,致使一个观念或印象的出现总是让人想象到其他的观念或印象,纵然后者实际上并不存在。比如因为我总是在忧郁的时候喝酒,以至于我一看到《将进酒》这个题目就觉得李白也很忧郁,尽管他事实上不忧郁。通则的作用是双重的,它们能使我们作出迅捷的判断,但很多时候却很容易作出错误的判断:
当一个在很多条件方面与任何相类似的对象出现时,想象自然而然地推动我们对于它的通常的结果有一个生动的概念,即使那个对象在最重要、最有效的条件方面和那个原因有所差异。这是通则的第一个影响。但是当我们重新观察这种心理作用,并把它和知性的比较概括、比较可靠的活动互相比较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这种作用的不规则性,发现它破坏一切最确定的推理原则;由于这个原因,我们就把它排斥了。这是通则的第二个影响,并且有排斥第一个影响的含义。随着各人的心情和性格,有时这一种通则占优势,有时另一种通则占优势。一般人通常是受第一种通则的指导,明智的人则受第二种通则的指导。[10](171−172)
简言之,一般人依赖的是习惯性思维,而明智的人却能警惕其中的错觉。所以要获得真实而正确的观念必须抑制想象,运用比较、判断和推理等方法。显而易见,《趣味的标准》一文中所谓的鉴赏家便是“明智的人”,面对艺术作品时,他们表现出五种优秀的品质:“有健全的感觉(sense),与细腻的情绪相结合,因锻炼而得到增进,又通过比较而完善,还能消除一切偏见。”[9](17)这些品质便是趣味的标准了。
依靠这些品质,鉴赏家们可以准确地发现艺术作品的法则,即艺术手法对于其目的的有效性:“每一部艺术作品都有它想要达到的某个目的或目标,并且根据其或多或少适合于达到这一目的,而被看做是或多或少地完美的。雄辩的目的是说服,历史的目的是教导,诗歌的目的是通过情感和想象来给人快感。”[9](16)可是,即使人们根据经验总结出了一些普遍的法则,每一件作品的具体表现也不是千篇一律。因此,对于艺术作品中的事实的鉴别需要更精细的判断力,也需要参照久经考验的典范来做出评定。
这个推论看来不错,但令人生疑的是,如此欣赏艺术作品还是诉诸情感的趣味判断吗?实际上,休谟不知不觉把趣味判断转化为了事实判断或理性认识。鉴赏家的品质中核心是“感觉”,但在英文中这个词还可以指“理智”,而且锻炼、比较和消除偏见的作用不正是增强了其“理智”的含义吗?确实,长期锻炼可以使人不仅知其然,还能知其所以然,比较可以确定不同的美的等级,消除偏见可以恢复理解力的作用。
这样一来,休谟就把《人性论》中驱逐的理性又召了回来,他明确说:“理性即便不是趣味的必需成分,也是趣味这种官能的活动所必要的。”[9](16)他不认为理性判断和情感判断之间存在什么不可调和的矛盾。他在《道德原则研究》中说,人天生就有某种内在感官让人能从任何对象上感受到美丑善恶的情感,在没有这些情感的地方,任何推理都无能为力。但是,“为了为这样一种情感铺平道路、并确切地分辨它的对象,我们发现,事先进行大量的推理,作出精细的区分,引出合理的结论,建立广泛的比较,考查复杂的关系,确定和确断一般的事实,常常是必要的。”[11](24)在《趣味的标准》中,休谟也说:“各种类型的作品,即使是最富于诗意的,也不过是一连串的命题和推理;当然这并不总是最正确和最严格的,但仍然是可信的,看似合理的,无论怎样被想象的色彩掩饰。”[10](16)
可以看到,休谟所谈的趣味标准指的多是第一个标准,即趣味作为一种心理能力是否存在规律,这些规律如何导致人们在鉴赏中的差异,如何可以帮助人们矫正某些错误。而对于何种美感可取和值得赞赏,即价值意义上的标准,休谟只是用一句“人们众口称赞优美、适当、质朴、生动,而指摘浮夸、做作、平庸和虚假的粉饰”轻易打发,如果人们进一步追问,优美、适当、质朴、生动何者更优,休谟可以说“一个人喜欢崇高,另一个人喜欢柔美,第三个人又喜欢谐趣”,[9](20)这些偏好源于个人先天性情和时代环境,一来不可避免,二来也无害,所以“无可指摘”,也就用不着什么标准。问题是为什么“优美、适当、质朴、生动”就高于“浮夸、做作、平庸和虚假的粉饰”,人们又如何辨别这些不同的美,休谟未置一词。
四、趣味标准辨析
休谟只关注事实意义上的标准,导致的结果是让理性认识重又在趣味判断中主持正义,也让趣味判断失去情感判断的本义。休谟的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呢?这里有两个方面需要注意,一是休谟对于构成艺术作品或审美对象的要素没有清晰的判断,二是他混淆了艺术欣赏的两种方式。
首先,休谟认为艺术作品的要素不过是一系列命题和推理,亦即一些观念,这使他认为只要能准确地辨认这些观念,就意味着有更好的趣味。这未必在理。桑科随从的亲戚们能从酒中分辨出皮子和铁的味道,这让他们很得意,但这并不意味他们能从美酒中得到快乐;同理,鉴赏家能看到一首诗歌描写的是什么事物或行动,用了什么韵律和修辞手法,但他未必能得到更多美感。按照哈奇生的理解来说,这样的鉴赏家把一个本来是整体的复杂观念切分成了简单观念,而前者给人的快乐不等于后者分别给人的快乐的相加:“每个人都会承认,他喜爱姣好面容、逼真画像胜过对哪怕是最强烈最鲜艳的任何一种颜色。”[3](3)诗人们也许并不知晓关于一片风景中包含的科学知识,但他们的描写却能令人心驰神往。
我们可以赞成休谟的观点,也就是,在批评或鉴赏中,艺术作品需要被分析,但分析出来的是什么却是另一个重要问题。后来,艾利逊也注意到了这个问题,指明艺术作品中打动人的是哪种性质;比如美第奇的维纳斯和观景殿的阿波罗,“前者的娇弱、质朴和羞怯,后者的优雅、高贵和威严,是表现这些人物的无与伦比的艺术,一般来说,也就是首先给观者的想象力造成印象的性质”,有人“可能观察到它们的尺度,可能研究了它们的比例,也可能关注到了它们的保存状况,以及它们被发现的史实,或者甚至是制作它们的大理石的材质。的确,所有这些都是这些雕塑的性质,正如其威严和优雅,在某个特殊时刻,它们也肯定曾经吸引了有着最精致趣味的人的注意力。但在这种情形中,人们感受不到美的情感,毋庸置疑,在感受到美的情感之前,观者必须停止对这样一些索然无味的性质进行思考”。[7](98−99)
“娇弱、质朴和羞怯,优雅、高贵和威严”这些是印象,即一个对象给我们的情绪或感受,而比例、材质、保存状况等性质则是观念,在艾利逊看来,前者才是构成艺术作品的审美要素,而休谟在《趣味的标准》中却并未做出这种区分。事实上,在休谟的哲学中也有这样的区分,印象和观念只在生动和活泼程度上有别,两者之间仍然可以相互转化。艺术创作的目的(同样也是艺术欣赏的目的)不是给人确定的观念,而在于造成强烈的印象,这需要想象的渲染,而非理性的认识,休谟自己也说:“[理性]按照对象在自然界中的实在情形揭示它们,不增也不减;[趣味]具有一种创造性的能力,当它用借自内在情感的色彩装点或涂抹一切自然对象时,在某种意义上就产生一种新的创造物。”[11](146)但是,在《趣味的标准》当中休谟仿佛放弃了印象这个概念和想象的作用。也许一个关键原因是,休谟认为理性判断与想象和情感的活动没有本质的差别:“判断与想象,也如判断与情感一样,都是互相协助的;不但信念给予想象活力,而且活泼而有力的想象,在一切能力中也是最足以取得信念和权威的。”[10](143)一定程度上说,理性不过是冷静的情感。问题是他在这里没有坚持印象的关键作用,也没有由此发展出一套完整有效的艺术鉴赏理论,至少他没有说明认知推理与艺术推理的区别。
其次的问题是,如何处理理性认识与趣味判断的关系呢?如果理性对于趣味来说必不可少,像休谟所说的那样至少可以作为趣味判断的恰当前提(但不必是趣味判断的本质和目的),“尤其是那些精巧的艺术作品的美,为了感受适当的情感,运用大量的推理却是必不可少的;而且一种不正确的品味往往可以通过论证和反思得到纠正”,[11](24−25),那么理性认识是否可以帮助我们建立趣味的标准呢?
可以肯定地说,经验的积累和理性的运用可以增进美感,能让我们能在对象间建立更精确的秩序,展开更丰富而顺畅的想象,观察到这件作品比另一件作品制作更精致、技艺更复杂、形式更和谐,或者有更明确的主题,以能获得更精致的快感。这里可以有一个标准,即有精致的或粗浅的差别,但谈不上正确与错误。这个时候,休谟忽视了一个重要区别,即,我们是否能正确地感觉到作品中的情感是一回事,我们是否能享受这种情感是另一回事。他一方面说:“虽然可以肯定地说,比起甜和苦来,美和丑更加不是对象的性质,而完全属于内在的或外在的情绪,但人们必定承认,对象中的某些性质是天然地适合于产生这些特定的感受的。”[9](11)另一方面又说:“最粗劣的涂鸦也富有某种光彩和正确的模仿,在这个层次上它们是美的,能打动一个农民或印度人的心,博得他们的最高赞赏。最粗俗的民谣也并非完全缺乏和谐自然,只有熟悉高级的美的人才能指明它们音调刺耳,内容乏味。”[9](14)这两种说法明显是矛盾的,既然民谣能用某些手法实现其目的,欣赏者也能得到“正确的”情感,那就不能说这些音乐不好,或者其欣赏者的趣味有错。
确有人发现休谟混淆了欣赏艺术作品的两种方式:“休谟这篇论文中的趣味概念混合了两个截然不同的东西——喜爱和评价(liking and assessing)。”[12]例如,我可以理解批评家说《红楼梦》内容如何广阔,情节如何绵密,因此也很同情他们从中得到的某种快感,但这并不妨碍我如饥似渴地阅读《还珠格格》,这种清新率真的感觉是在评价《红楼梦》的时候得不到的,别人没有理由谴责我喜爱这种感受。休谟谈到有两种趣味上的偏见或差异是很难消除的,那就是源于个体的不同气质的偏见和源于不同国家和时代的生活方式的偏见,但它们不足以混淆美丑的界限,所以也就没有必要设定什么标准。然而,“民间小调”与“高级的美”的差异属于何种差异呢?为什么前者会让“对最高形式的美有素养的人”斥之为丑呢?其原因多半是出于阶级的偏见吧。
不过,休谟观察到的实例的确不可忽视,把弥尔顿与奥格尔比、艾迪生与班扬等量齐观,让人难以认同;但这样的判断仅仅是源于个体先天性情和时代环境的偏见吗?仅仅是无可指摘的喜爱吗?显然,在多数人看来,弥尔顿崇高,奥格尔比平庸,艾迪生优雅,而班扬做作,纵然选择崇高或优雅可归于个人偏好,但喜爱弥尔顿和艾迪生的读者的趣味还是更高一筹,这自然说明他们的判断是符合某种标准的,这种标准属于我们所谓价值意义上的标准。实际上,休谟说“人们众口称赞优美、适当、质朴、生动,而指摘浮夸、做作、平庸和虚假的粉饰”,所用的也是这种标准;可惜休谟在《趣味的标准》一文中对这种标准的根据讳莫如深,“众口称赞”毕竟无法替代理性论证。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无论如何这种差异无法通过艺术法则来解释。
那么,休谟是否在其他地方给我们的疑问提供答案了呢?我们或许可以在《人性论》的“情感论”这一部分中找到些线索。虽然情感无法定义,但休谟在讨论骄傲和谦卑、爱和恨等情感时提出了新的方法,那就是从情感的对象和原因来加以解释。骄傲和谦卑的对象都是自我,爱和恨的对象都是他人;骄傲和爱的原因是引人快乐的性质,而爱和恨的原因则是令人痛苦的性质。在这里,情感因其原因不同而又快乐和痛苦两个基本类别,以及作为对象的自我有着密切关系。显而易见,外物与自我的所属关系会影响情感的性质和程度,而更重要的是,借外物性质而展开的自我与他人的关系同样发挥着显著作用:“如果在把自己同别人比较起来(这是我们往往时刻都在进行的),我们发现自己丝毫没有突出的地方;而在比较我们所有的对象时,我们仍然发现有同样不幸的情况;那么由于这两种不利的比较,骄傲情感必然会完全消失了。”“别人如果认为我们是幸福的、有德的、美貌的,我们便想像自己更为幸福、更为有德、更为美貌。”[10](327)看来,自我与他人的关系决定了情感更为复杂的类型和价值等级。
我们可以把这些原理运用到艺术鉴赏那里。首先可以确定,优美、质朴、浮夸、平庸本不属于作品自身的客观性质,而是接受者体验到的情感,其次,这些情感也并不是来自直接的感觉,而是源于比较。的确,艺术作品有着基本的一般法则,但完全照搬法则的作品就显得平庸,过于新奇的作品显得浮夸,而在它们之间取得巧妙平衡的作品则是适当、质朴的,这正如一个人处处模仿他人就被视为平庸,过分突出就被认为浮夸,而在两端之间的平衡可谓之得体。他人身上有价值的地方本身是令人快乐的,但模仿却无法使自我(无论是自己的还是他人的自我)“突出”,致使骄傲情感丧失,过度“突出”自我却会使旁人嫉恨,这都使原本的快乐转化为痛苦;同理,艺术典范本身令人愉悦,甚至模仿之作在被识破之时也是如此,但模仿行为本身令人鄙夷,而全然抛弃法则,一味标新立异却又让因循法则的读者无法忍受,这些同样是把原本的快乐转化为痛苦。这个过程必须依赖于比较,比较的参照物是那些艺术典范,其间虽没有量化指标,但却能在面对具体对象时做出大致的价值判断。说到底,对不同类型的美感的选择体现出来的是一个人在社会交往中的态度。这样的推论并非无端揣测,因为后来的博克也根据这些原则来解释崇高和美的人性基础;美的根源是社交性情感,而引发这种情感的原因则有同情和模仿;“我们凭借模仿而非规程学习一切东西,这样的学习不仅更加有效,也更令人愉快”[5](49),但一味地模仿就陷入循环,“为避免这样,上帝在人心中植入一种雄心感,一种源自试图在某些有价值的地方胜过同类的满足感”[5](50)。当然,博克并没有借此而化解趣味标准的问题。
然而,这样一来趣味标准的问题就跨入了社会实践领域,仿佛偏离了审美领域,但其合理之处在于,价值判断与趣味判断同样都遵循情感的运行规则,而且这至少可以填补休谟在价值意义上的趣味标准这一问题上留下的空白。显然,休谟无意将自己的情感论贯彻到《趣味的标准》一文中,或许有一个重要原因是,这样的标准得自于比较,一定程度上是相对的,不太符合严格意义上的标准,这使得休谟放弃了这条思路,但这条思路无疑有助于解开情感与理性之间的错综关系。理性认识可以确定事实意义上的标准,而情感则可以阐明价值意义上的标准。
也许我们这样批评休谟犯了时代性的错误,实际上,情感与理性的矛盾并不单单出现在休谟的美学中,它本身就内含于18世纪英国的美学中。自夏夫兹博里伊始,趣味理论的一大目标就是反对17世纪以来伦理学中流行的功利主义,即善恶取决于一个对象是否有利于个体的欲望和利益,趣味理论则把善恶美丑的根源规定为人先天的社会性情感和对美善的非功利的爱。然而,单纯依赖情感的作用反而会使趣味理论陷入相对主义的困境,由此,包括休谟在内的众多哲学家力图运用想象活动将情感转化为具体的观念,并以此来描述情感的规律。同时,为了进一步保证情感的客观性,他们又试图在情感(尤其是趣味判断中的情感)与理性之间建立有效的联系,最典型的是博克把趣味定义为感觉、想象和理性相结合的能力,虽然这样也使趣味的内涵变得更加模糊。另一方面,在艺术批评中,诚如吉尔伯特和库恩的《美学史》所言:“为什么激进的开端未能产生激进的结果呢?部分原因在于,从布瓦洛时期所形成的法国审美趣味的实际威力,至少在十八世纪上半期还统治着英国。”[13]这就难怪很多作家仍然难以打破新古典主义的藩篱,反而奉古代经典为圭臬。当然,趣味理论在实践领域慢慢发挥着影响,艾迪生反对欧洲传统的园林整齐刻板,赞赏中国园林自然随意,浑然天成;在绘画领域,荷加斯的“蛇形线”学说也强调变化和运动。到了18世纪末,华兹华斯等人倡导返回自然,从田园生活和民间歌谣中汲取素材和语言,开创浪漫主义潮流。在这个过程中,休谟的美学乃至整个哲学依然为化解趣味理论的难题做出了复杂但有益的探索,也为后来西方美学的发展提供了诸多启示,这一切不是《趣味的标准》一文所能完全涵盖的。
[1] Shaftesbury. Characteristics of Men, Manners, Opinions, Times [C]. Lawrence Klei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326−327.
[2] Hutcheson. An Inquiry into the Original of Our Ideas of Beauty and Virtue in Two Treatises [M]. Indianapolis: Liberty Fund, Inc, 2004.
[3] 艾迪生. 想象的快感. 缪灵珠美学译文集·第二卷[C]. 张安祺编订.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87.
[4] Gerard, Alexander. An essay on taste [M]. London: 1759: 1.
[5] Burke. A Philosophical Enquiry into the Origin of Our Ideas of the Sublime and Beautiful [C]. Boulton. London: Routlege and Kegan Paul Limited, 1958.
[6] 荷加斯. 美的分析[M]. 杨成寅译.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 68.
[7] Allison, Archibald. Essays on the Nature and Principles of Taste ·Vol. 1. [M]. Edinburgh: 1811.
[8] Blair. Lectures on rhetoric and belles lettres [M]. London: 1783: 18.
[9] Hume. Of the standard of taste and other essays [C]. John W. Lenz. Indianapolis: The Bobbs-Merrill Company, Inc, 1965.
[10] 休谟. 人性论[M]. 关文运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0.
[11] 休谟. 道德原则研究[M]. 曾小平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1.
[12] Carroll, Noel. Hume’s standard of taste [J]. The Journal of Aesthetics and Art Criticism, 1984(2): 181−194.
[13] 吉尔伯特, 库恩. 美学史·上卷[M]. 夏乾丰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9: 307.
Hesitation between sentiment and rationality: An analysis of Hume’s of The Standard of Taste
DONG Zhigang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Shanxi Normal University, Linfen 041004, China)
In the eighteenth-century Britain, taste became a key concept in Aesthetics, by which it means the specific function of aesthetic judgment, and the special ability of aesthetic judgment. Hume, likewise, built his aesthetics on taste, and expounded in the new philosophic system the connotation of taste with rules of sentiment and imagination. However, Hume was faced with the same problem as his contemporaries, that is, whether taste judgment is objective. In the face of this problem, Hume composed an article Of the Standard of Taste, in which he insisted on emotion quality of taste, without falling short of reason, and this caused him to translate taste judgment into reasoning cognition or fact judgment, and finally to define the standard of taste as a series of qualities of reasoning cognition. Here, Hume ensured the objectivity of taste, but departed from the essence of aesthetic judgment. Meanwhile, Hume merely concentrated on the standard in the sense of the fact, but ignored that of value; as a result, he did not expound the original reasons for differences in taste. However, his philosophy could supply some inspirations for making up these defects, that is, rational cognition can determine the standard in the sense of the fact, and rules of sentiment can explain that of value.
Hume; Of the Standard of Taste; taste; sentiment; rationality
B561.291
A
1672-3104(2015)01−0012−08
[编辑: 颜关明]
2014−03−19;
2014−12−16
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十八世纪英国美学学派研究”(11CZX073);山西省青年学术带头人支持计划(2012)
董志刚(1978−),男,山西平遥人,哲学博士,山西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西方美学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