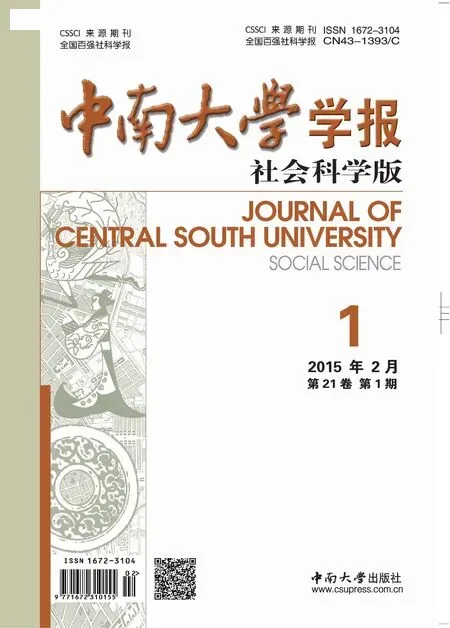马克思实践诠释学的方法论意义及其合理运用
2015-01-21王浩斌
王浩斌
(中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南长沙,410083)
马克思实践诠释学的方法论意义及其合理运用
王浩斌
(中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南长沙,410083)
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及其意识形态学说确立了一种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形成的诠释方法论原则,事实上开创了一种新的诠释学即实践诠释学,从而实现了诠释学领域的重大革命。马克思实践诠释学的方法论意义在于它突破了“理论指导实践”“意义先在”以及“释义学循环”的片面性或局限性,形成了基于“实践选择理论”的实践反思法、基于“意义生成”的理念生成法以及基于“意识形态批判”的经验析取法。要合理运用马克思的实践诠释学,必须正确处理好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理论与实践、逻辑与历史之间的辩证关系,不能分别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实践哲学以及问题哲学等完全等同于实践诠释学。
马克思;实践诠释学;方法论;唯物史观;实践哲学;问题哲学
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乃至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注重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形成是马克思哲学甚至是其唯物史观的一个重要特点。在某种程度上,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及其意识形态学说开创了一种从实践出发诠释文本、认识世界和发现真理的科学方法——在改造世界中认识和诠释世界的方法,我们将这种方法称之为实践诠释学或“实践释义学”[1]。马克思实践诠释学的重要意义并不在于其基本观点表达得如何科学,也并不在于其语言的表述如何生动,而在于它为我们诠释文本、认识真理、发现真理以及检验真理等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思路,蕴涵着较强的方法论意义。当前,我们正处在一个文化价值多元化、思想观念急剧变迁的历史时代,如何从我们面临的实际问题出发,筛选出能够真正引领经济及社会发展的价值观和思想理论体系,这是一个重大的理论课题和实践课题。为此,从时代特点和我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具体实际出发,深入分析马克思实践诠释学的方法论意义,并探讨其合理运用的有效途径,这无论是对于丰富马克思实践诠释学的理论研究,还是对于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持续、快速而健康发展,无疑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积极的现实意义。
一、诠释学的实践转向与马克思的实践诠释学
诠释学或解释学(Hermeneutics)是一门关于理解的学问,它的基本问题就是文本及其意义的理解问题。当然,对文本意义的理解,一直存在着原则上的分歧:“是将文本的意义还原于‘所指’的生活实际,契入现实世界探求真理,还是只停留于它的‘能指’辨析,徜徉在思辨王国里游戏语言?坚持前者,则是解释学的辩证唯物主义态度;若固守于后者,则只能流于肤浅甚至陷进经院哲学的解释学泥淖。”[2]很显然,传统的神学诠释学和法律诠释学坚持的是后者,强调解释或理解的目的在于还原文本或经典的原意,维护上帝的权威性、唯一性以及法典的严肃性。为此,传统诠释学的理解所追求的是对文本字面意义的“准确把握”和“权威解释”,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这种“准确把握”和“权威解释”得来的文本意义与生活实际是否相符,而在于这种诠释的“表演”或“技艺”是否高超,这样,那些专门握有经典及法典解释权的牧师和律师自然在社会上享有崇高的威望,他们也事实上被涂上了一层被马克思所谓的“受人尊崇和令人敬畏的职业的神圣光环”[3]。当然,这种停留于文本意义的“能指”的传统诠释学受到了近代以来一些哲学家如海德格尔、利科尔等的质疑,其质疑的依据在于诠释者永远都生活在“当下”,总是带着“当下”的语境或情境,要达到对文本语境的“准确把握”是不可能的,因为在诠释者语境与文本语境之间有着难以逾越的“间距”。
在海德格尔看来,“把某某东西作为某某东西加以解释,这在本质上是通过先行具有、先行之见与先行掌握来起作用的。解释从来不是对先行给定的东西所作的无前提的把握。”[4]而这个“先行具有、先行之见”的“前提”就是理解的偏见、前见,它指的是理解者存在的种种历史条件,指的是构成理解主体的语言、记忆、动机、经验、知识、情感、世界观以及方法论等一切精神因素的总和,在海德格尔看来,这种偏见不是理解的障碍,而恰恰是理解的前提和条件。当然,这种前见或偏见的存在,表明诠释或理解实质上就是对“此在”的历史性解读,因为理解的偏见乃至人的存在本质上是一种历史的存在,它表征着原始的、本体的深层历史性。现代哲学解释学大师伽达默尔认为,作为理解者或诠释者的个体“隶属于历史。早在我们通过自我反思理解我们之前,我们就以某种明显的方式在我们所生活的家庭、社会和国家中理解了我们自己”[5]。可以看出,现代哲学诠释学不再停留于对文本意义“能指”的层面上,而是将文本的意义还原于我们的生活实际及历史存在,契入现实世界之中去探求、发现、认知真理,这种哲学诠释学认为真正的诠释就是诠释者的当下视域同文本视域之间“视域融合”的过程,它体现为一种“效果历史”。由此可知,现代哲学诠释学实现了诠释过程中文本意义的“能指”向“所指”的革命性转变,这实质上是诠释学的实践转向。
诠释学的实践转向实际上是确立了一条重要的诠释学原则,那就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读或诠释文本的意义,而不是相反。当然,真正使这条原则得以贯彻的是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因为“这种历史观和唯心主义历史观不同,它不是在每个时代中寻找某种范畴,而是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形成”[6](92)。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及其意识形态学说事实上开创了一种从实践出发诠释文本、认识世界和发现真理的科学方法,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将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历史观所确立的这种诠释文本的方法叫做实践诠释学。马克思的实践诠释学就是“把文本意义的理解置于文本作者所处的现实生活环境,从社会实践致使文本作者所求、所为、所思、所言的方面去揭示和理解文本的意义”[2]。历史表明,马克思的实践诠释学在解释世界、认识真理、发现真理和检验真理等方面,发挥了纯粹的哲学解释学所无法发挥的作用,因为现代哲学诠释学尽管将诠释学的出路定位在应用或实践上,也就是实现了诠释学的实践转向,但现代哲学诠释学只是将诠释学视为“实践哲学的近邻”[7],而不是直接立足于实践哲学本身或者从实践出发来重新确立诠释学的原则及方法。由此可知,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及其意识形态学说不仅实现了近代以来的伟大哲学革命,同时也事实上实现了诠释学领域的伟大革命。
二、马克思实践诠释学的方法论意义
如果说现代哲学诠释学突破了传统文本诠释学的局限而开创了本体论的诠释学方法,将诠释学的重点由“文本言说”转到“文本意义”所指向的生活实际,那么,马克思的实践诠释学则突破了现代哲学诠释学的局限而开创了实践论的诠释学,将诠释学的重点不再简单停留于对文本的本体论承诺,而是直接从物质实践出发去解释、还原文本的存在意义或本体价值。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实现了诠释学领域的重大革命,其开创的实践诠释学的重要意义并不在于其基本观点表达得如何科学,也并不在于其语言的表述如何生动,而在于它为我们诠释文本、认识真理、发现真理以及检验真理等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思路,蕴涵着较强的方法论意义。
(一)“理论指导实践”——“实践选择理论”的实践反思法
无论是传统诠释学还是现代哲学诠释学,其诠释的根本目的在于充分揭示文本的意义,从而有效地发挥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不可否认,任何文本的“意义言说”对现实的社会生活及物质实践都有一定的牵引作用,哪怕是被严重幻想化的宗教,都折射着现实生活中的苦难,从而对具有苦难之中的人民具有某种“导引”作用,对此马克思指出,“宗教里的苦难既是现实的苦难的表现,又是对这种现实的苦难的抗议。宗教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是无情世界的心境,正像它是无精神活力的制度的精神一样。宗教是人民的鸦片。”[6](1)也就是说,宗教对实践的牵引主要体现为“欺骗”,是一种“精神鸦片”,沦为被统治阶级利用来征服人民的思想武器。当然,文本的“意义言说”对实践的指导也发挥正面的积极牵引作用,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的,“劳动过程结束时得到的结果,在这个过程开始时就已经在劳动者的想象中存在着,即已经观念地存在着。他不仅使自然物发生形式变化,同时他还在自然物中实现自己的目的,这个目的是他所知道的,是作为规律决定着他的活动的方式和方法的,他必须使他的意志服从这个目的。”[8](178)在这里,马克思指出了观念对于实践的积极牵引作用,而这实质上就是理论指导实践的过程,或者说,它体现着理论对实践的某种指导价值。
当然,在揭示文本的意义从而对实践的牵引问题上,传统诠释学和现代哲学诠释学还是有着重大的区别:传统诠释学完全拘泥于“文本”,把“文本意义”的唯一神圣解释当作“圣条”供大家遵守和膜拜,从而维护上帝的权威性和法典的严肃性;而现代哲学诠释学则强调诠释者的“当下”语境即主体视域在文本诠释中的决定性作用,将文本的意义阐释放在作者与诠释者两种不同视域所形成的“时空通道”中进行揭示,这一方面凸显了诠释者在文本诠释中的主动性和能动性,大大降低了“文本”及其意义言说的权威性和神秘性,从而将文本的意义理解和诠释同人们的现实生活结合起来。与传统诠释学和现代哲学诠释学不同,马克思的实践诠释学在对待文本及其意义的理解问题上,不是一味地追求“理论指导实践”,不是单纯地追求“还原作者原意”,而是强调在实践面前理论或观念平等,都平等地接受实践的选择,任何文本或观念性文本对于实践而言,其诠释的价值以及意义的阐释都要视实践的需要而定。也就是说,马克思的实践诠释学坚持“实践选择理论”的实践反思法,强调文本的意义及其价值取决于它的真理性,而这种真理性能否得到实现则取决于完全实践的需要,即“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6](11)。由此可知,在实践那里文本、观念、理论乃至真理并不神圣也并不权威,“理论指导实践”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实践选择理论”。
(二)“意义先在” ——“意义生成”的理念生成法
马克思的实践诠释学注重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形成,强调实践选择理论,但这并非意味着马克思的实践诠释学只注重实践而不重视理论,只重视现实的物质生活而忽视文本的意义存在。正如前文所述,马克思也十分重视文本的意义及观念对于实践的牵引作用,在马克思看来,“光是思想力求成为现实是不够的,现实本身应当力求趋向思想。”[6](11)而“现实趋向思想”的过程实质上就是文本或观念性文本的意义不断臻于完善的过程,这实际上开创了一种不同于传统诠释学和现代哲学诠释学的新的意义阐释方法——理念生成法。总的来说,无论是传统诠释学还是现代哲学诠释学,都坚持一个基本的观点即“文本意义的先在性”,即任何形式的文本一经形成,其文本背后的意义就先在地存在着。传统诠释学所追求的就是对这种文本的“先在意义”进行准确的还原,“符合作者原意”可以说是传统诠释学的最高境界;而现代哲学诠释学所追求的就是对文本的“先在意义”进行本体论的还原,或者说,从诠释学的当下语境出发去揭示出早就蕴涵在文本中的“先在意义”,在这个意义上,现代哲学诠释学的最高境界在于诠释者与作者“视域融合”的“效果历史”,不管怎样,现代哲学诠释学尽管总体上坚持了文本诠释“意义先在”的立场,但事实上开启了文本诠释由封闭走向开放的思想大门,将文本的意义阐释看作是一个开放式的解释过程。
在马克思的实践诠释学看来,文本意义的开放性来源于其所指涉的现实社会生活的实践性,体现为一个“意义生成”的实现过程。马克思终其一生解读了数以万计的各种思想文献,但马克思不是封闭式地阅读,以获取文本的“先在意义”,相反,马克思将这些思想文献视为一种随着语境变迁而不断生成新的文本意义的流传物。因此,马克思对各种文献采取了一种辩证的阅读或诠释方式,一方面,继承那些蕴涵在文本中仍然能够有效解释现实社会生活的意义表达,但另一方面,他又毫不留情地抛弃那些看起来很合理但事实上不能迎合实践需要的意义阐释。这个过程在马克思的实践诠释学那里就是“扬弃”的过程,也就是批判地继承、丰富、充实和发展理论的过程。譬如,对于黑格尔的文本,马克思继承了那些极具生命力的辩证法阐释,而抛弃了蕴含在黑格尔文本中的唯心主义的意蕴;而对于费尔巴哈的文本,马克思对其唯物主义的合理内核进行了充分的意义阐发,而毫不留情地抛弃了蕴含在朴素唯物主义外衣之下的唯心史观。由此可知,马克思的实践诠释学尽管重视对文本的意义阐释,但将这个文本意义看成是一个不断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生成的过程,强调要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文本的意义,认为这是正确对于文本及其意义解释的重要方法论原则。
(三)“释义学循环” ——“意识形态批判”的经验析取法
马克思的实践诠释学还有一个重要的方法论意义,就是突破了传统诠释学和现代哲学诠释学所无法突破的“释义学循环”,在强调“意识形态批判”的基础上形成了一种重要的介入并突破“释义学循环”困境的途径及方法——经验析取法。众所周知,“释义学循环”又称之为“解释学循环”,它是诠释学领域中的一个极为重要的理论概念,它强调文本的整体只有通过它的部分才能得到理解,而对部分的理解又只能通过对整体的理解。事实上,在传统诠释学和现代哲学诠释学那里,对待“释义学循环”存在两种不同的态度,“古典解释学认为解释学循环是可以消解的,人们可以达到对作者作品原意的全面理解;当代解释学认为解释循环是不可以消解的,每个人对同一文本有不同的理解,文本的意义只有在解释者的自我理解中方可实现。”[9]值得指出的是,这两种诠释学都没有突破“释义学循环”所带来的困境,传统诠释学事实上回避了问题的存在,它试图绕开“释义学循环”而直接达到对“文本意义”的先在性把握实际上是不可能实现的,因为诠释者永远活在“当下”,有着当下的语境和偏见;但现代哲学诠释学则是夸大了“释义学循环”的矛盾性和困境存在的绝对性,对走出“释义学循环”表现出了一种极强的悲观论调和宿命论的价值取向,陷入了一种“整体——部分”的释义学循环的泥潭之中不能自拔。
在马克思的实践诠释学看来,正确地进入“释义学循环”的重要途径就是“意识形态批判”。关于这一点,俞吾金教授也指出,“意识形态批判是正确地进人释义学循环的道路……一定历史时期的意识形态构成该时期的理解和解释活动的总体背景,换言之,构成了理解者和解释者的先入之见的基础和源泉。因此,当理解者和解释者对自己置身于其中的意识形态缺乏反思和批判的理解时,是不可能正确地进入释义学循环的。”[1]这在马克思的经典文本中也可以明显地看出来,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强调“对宗教的批判是其他一切批判的前提”[6](1)。因为宗教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对它的批判是理解宗教本身及其精神实质的重要前提和根本途径,马克思进而认为,“当我们不去批判我们现实历史的未完成的著作,而来批判我们观念历史的遗著——哲学的时候,我们的批判恰恰接触到了当代所谓的问题之所在的那些问题的中心。”[6](7)在这里,马克思将对哲学、宗教等意识形态的批判看成是理解观念即“当代所谓的问题”或“当代所言说的问题”的重要途径。当然,尽管马克思认为意识形态批判是正确进入解释学循环的重要途径,但真正要跳出解释学循环只能求助于现实的社会实践,求助现实的生活实践经验,正如马克思所言,“不使哲学成为现实,就不能够消灭哲学。”[6](8)为此,在诠释者立足于实践的基础上不断对观念及文本的意识形态批判过程中,通过对这种批判经验的有效析取,达到发现真理、认识真理的目的,而这个过程实质上就是实践诠释的过程。
综上所述,马克思实践诠释学的方法论意义在于它突破了“理论指导实践”“意义先在”以及“释义学循环”的片面性或局限性,形成了基于“实践选择理论”的实践反思法、基于“意义生成”的理念生成法以及基于“意识形态批判”的经验析取法。
三、马克思实践诠释学的合理运用
马克思的实践诠释学毫无疑问地实现了诠释学领域中的重大革命,但作为一种新的“诠释学”方法,能否将其合理运用则是问题的关键。我们认为,要合理运用马克思的实践诠释学,必须注意做到以下几个方面。
(一) 不能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完全等同于实践诠释学
尽管我们认为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开创了一种新的从实践出发诠释文本、认识世界和发现真理的科学方法,我们将这种方法称之为实践诠释学,但是,这并非意味着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完全等同于实践诠释学。这是因为,马克思毕其一生的精力都花在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上,尽管马克思深知改造世界比解释世界或认识世界更为重要,但从马克思一生中所撰写的著作来看,他的著作主要集中在认识世界的层面上,他花了近四十年的时间但尚未完成的《资本论》实质上就是在解释是资本什么,属于认识世界的范畴。在这个意义上,布洛赫说的有一定道理,也就是认为马克思主义接近于“纯粹理性批判”,而“实践理性批判”还没有写出来。正是因为这个缘故,马克思的墓碑上出现的恰恰就是《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的一句名言,“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6](51)马克思这句话的言外之意就在于,尽管我做的主要工作停留于解释世界或认识世界的层面,但问题的关键在于改变世界,而现在“改革世界”的任务远未完成,无产阶级还需继续努力去完成这项工作。在这个意义上,这句话实际上执行着马克思“遗嘱”的作用,它同时也充分表明了马克思唯物史观及其意识形态学说的重点在于改变世界(尽管认识世界是极为重要的前提)。因此,如果我们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完全等同于实践诠释学,既降低了马克思唯物史观的革命性,容易导致将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哲学化甚至唯心主义化,也不符合马克思实践诠释学的基本精神——“解释世界是为了改变世界”。为此,要合理运用马克思的实践诠释学,必须正确处理好解释世界和改变世界的辩证关系,不能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完全等同于实践诠释学。
(二) 不能将马克思的实践哲学完全等同于实践诠释学
马克思的实践诠释学尽管突出地强调实践活动在文本诠释、认识真理、认识世界中的极端重要性,甚至可以说,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乃至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首要的和最基本的观点,但这并非意味着马克思的实践哲学完全等同于实践诠释学。这是因为,实践的过程确实在某种程度上打通了进入诠释学循环的通道,更好地达到了对文本、观念的真理性认识,但必须明确两点:其一,实践是有其历史前提的,除了物质性的条件之外,还必须有意识形态上的积淀,也就是说,排除任何精神、意识先在的实践是不存在的,实践是对某种知识性真理的意义诠释的基础上进行的;其二,实践作为检验文本诠释、认识真理性的标准既具有确定性,同时也具有不确定性,在这个问题上,列宁指出:“生活、实践的观点,应该是认识论的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这种观点必然会导致唯物主义,而把教授的经院哲学的无数臆说一脚踢开。当然,在这里不要忘记:实践标准实质上决不能完全地证实或驳倒人类的任何表象。这个标准也是这样的‘不确定’,以便不让人的知识变成‘绝对’,同时它又是这样的确定,以便同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论的一切变种进行无情的斗争。”[10]可以看出,马克思的实践哲学尽管也突出实践在诠释文本、认识真理中的积极作用,但严格地讲,这种实践哲学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诠释学,其作为诠释学有一定的缺陷,即只注重实践对认识真理、诠释文本的确定性方面,只注重实践反思,而没有注重到其不确定性的方面;而马克思的实践诠释学则不同,尽管它也强调实践的重要性,但实践只是一种重要的突破口,它只是一个修饰语,可以理解为实践的诠释学,其重点在于后者即诠释,它试图在实践反思、理念生成以及经验析取之间逻辑互动的基础上,形成对文本意义及其真理性的认知与把握,而不只是注重实践反思。为此,要合理运用马克思的实践诠释学,必须正确处理好理论和实践的辩证关系,不能将马克思的实践哲学完全等同于实践诠释学。
(三) 不能将马克思的问题哲学完全等同于实践诠释学
马克思的实践诠释学强调问题的重要性,主张从我们面临的实际问题出发去选择理论、解释文本和理解观念,问题意识可以说是马克思实践诠释学的重要特点,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而将马克思的实践诠释学理解为问题哲学,甚至将马克思的问题哲学完全等同于实践诠释学。这是因为,马克思的问题哲学实质上指的就是以问题为立场和基本出发点,在积极分析问题精神实质、寻求问题解决方法及途径的哲学方法,当然,这种方法主要是逻辑思维的方法,或者说就是唯物辩证法。马克思的问题哲学主要通过运用三大规律来对事物的发展、状态及其趋势进行辨证分析和把握,其中对立统一规律揭示事物发展的原因及动力,它所指涉的是“为什么”(Why)的问题,也就是事物为什么会发展的问题;质量互变规律则揭示事物的发展状态,它所指涉的是“怎么样”(How)的问题,也就是事物处于怎样的发展阶段的问题;而辩证的否定观则揭示了事物发展的趋势和道路问题,它所指涉的是“在哪里”(Where)的问题,也就是事物发展的方向、趋势和道路的问题。马克思的实践诠释学尽管也从现实的问题出发去解释观念的形成,但问题哲学的那种辩证思维却不是它的精神实质,而尊重历史的发展要求则是马克思实践诠释学的重要特点,在某种程度上,马克思的实践诠释学是一种历史诠释学,具有浓厚的历史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对此,恩格斯指出,“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这种反映是经过修正的,然而是按照现实的历史过程本身的规律修正的,这时,每一个要素可以在它完全成熟而具有典型性的发展点上加以考察。”[8](43)可以看出,对思想进程的诠释和理解必须尊重历史事实,尽管逻辑的分析可以实现对“历史进程”的某种“修正”,在逻辑上可以作出新的“理解”和“解释”,但必须在遵循“现实的历史过程本身的规律”的基础上进行诠释。可以看出,要合理运用马克思的实践诠释学,要正确处理好逻辑与历史的辩证关系,不能将马克思的问题哲学完全等同于实践诠释学。
[1] 俞吾金. 马克思的实践释义学初探[J]. 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 1995(3): 96−103.
[2] 胡潇. “从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马克思解释学思想片论[J]. 马克思主义研究, 2006(8): 53−57.
[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34.
[4] 海德格尔. 存在与时间[M]. 北京: 三联书店, 1999: 184.
[5] 汉斯−格奥尔格•加达默尔. 真理与方法—哲学诠释学的基本特征·上[M].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4: 357.
[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7] 加达默尔. 科学时代的理性[M]. 上海: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1998: 85.
[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9] 张树业. 从“解释学循环”看解释学真理观的“古今之争”[J]. 广西社会科学, 2008(3): 55−58.
[10] 列宁选集·第2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103.
The methodology meaning and the reasonable application of Karl Marx’s practical hermeneutics
WANG Haobin
(School of Marxism,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3, China)
Karl Marx’s Historical Materialism and Ideology Theory has established a kind of hermeneutics methodology principle that sets out to explain the notional formation from material practices. The principle has in fact founded a new kind of practical hermeneutics, namely, an important revolution in the fields of hermeneutics. The methodology meaning of Karl Marx’s practical hermeneutics is that it breaks through the partiality or limitation of the unilateral or localization of “theories guiding practice”, “meaning to release in the first” and “hermeneutics circulation”, and has created practice examination methodology according to “practice choosing theories”, theory born methodology according to “meaning born” and experience choice methodology according to “ideology theory judgment”. To apply Karl Marx’s practical hermeneutics reasonably, we need to handle dialectical relations of the recognition and reformation of the world, theory and practice, logic and history, and we cannot eguate Karl Marx’s Historical Materialism, practice philosophy and problem philosophy with Karl Marx’s practical hermeneutics.
Karl Marx; practical hermeneutics; methodology; materialism; practical philosophy; problem philosophy
A81
A
1672-3104(2015)01−0006−06
[编辑: 颜关明]
2014−03−19;
2014−12−16
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马克思社会理想视域中的中国梦研究”(14YBA329)
王浩斌(1976−),男,湖南双峰人,法学博士,中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中南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博士后流动站博士后,湖南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研究会常务理事,主要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