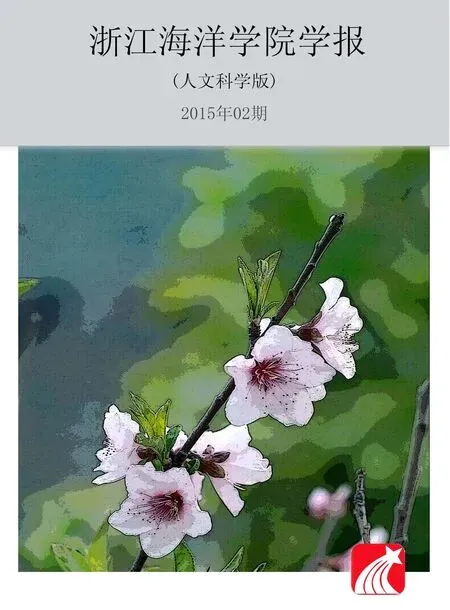《图书馆里的贼》与《超杀人事件》的“侦探元小说”性探析
2015-01-20夏寒
夏寒
(浙江海洋学院外语学院,浙江舟山316022)
《图书馆里的贼》与《超杀人事件》的“侦探元小说”性探析
夏寒
(浙江海洋学院外语学院,浙江舟山316022)
侦探小说经历两个世纪的发展,从未停止过小说内部与外部的各种探索与创新。美国冷硬派代表人物劳伦斯。布洛克和日本新本格派中坚力量东野圭吾的作品呈现出一个共同点,在其前期个人化风格浓重的作品分别奠定了他们冷硬派与本格派大师地位后,后期的作品又呈现出作者新的文学尝试,其中《图书馆里的贼》和《超杀人事件》就是这类作品的典型。这两部小说皆在侦探小说内部探讨侦探小说,因此有了“侦探元小说”性。
侦探元小说;劳伦斯·布洛克;东野圭吾;《图书馆里的贼》;《超杀人事件》
自爱伦。坡1841年发表史上第一部侦探小说《莫格街凶杀案》算起,侦探小说经历了近两百年的发展历史。从以福尔摩斯系列为典型代表的短篇小说时期,到以阿加莎·克里斯蒂引领的长篇小说的黄金时代,再衍生发展出日本的推理小说,美国的硬汉侦探小说,乃至警察小说、犯罪小说等等,作家们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对于侦探小说内部与外部的各种探索与创新。侦探小说已经形成一个脉络复杂、体系完整的小说派别。
以当前在中国比较流行的两位高产的侦探小说家美国的劳伦斯。布洛克和日本的东野圭吾为例,纵观其各自的创作年表,不难发现他们的创作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早期作品是极具风格化的典型“本格派”推理与“冷硬派”侦探小说,奠定了他们在各自领域的大师地位;而在中后期的创作中,他们均进行了风格更加多样的文学尝试。东野圭吾在《名侦探守则》、“三笑小说”和《超杀人事件》等作品中用各种后现代文学的手法极致调侃推理小说这个行业中的黑色与畸态,而劳伦斯。布洛克则干脆让主人公的身份从侦探摇身一变,成为从各方面都很有文艺品味的雅贼和经常身陷各种无厘头状况之中的杀手。在这些尝试中,他们不仅是在写作侦探小说,更是借作品讨论侦探小说,具备了明显的“侦探元小说”特点,《图书馆里的贼》和《超杀人事件》便是两位作家试图超越传统侦探小说模式的代表性尝试。
一、从侦探小说到“侦探元小说”
自《唐吉诃德》开始,西方小说经历了从古典主义到现代主义再到后现代主义的纵向发展,宏大叙事逐渐消解,线性模式慢慢断裂;而在横向方面,各种文类(genre)与子文类(sub-genre)不断产生交汇,衍生和变异,呈现出不断解构外部世界和关照自我的写作历史。
朱莉娅。克里期蒂娃和罗兰(巴特较早地提出了“互文性”(intertexuality)的概念[1]127,是指所有的文本都不可能脱离其它文本的影响而独立存在,它与早前的文本、他人的文本甚至作者自己的文本相互联系和折射。作品被不断地戏仿、拼贴和反复改写,这种刻意引用他人和自身的过程让其产生了强烈的自我指涉意识,使后现代小说常常成为元小说。元小说的英文是metafiction,也有人称之为“自我意识小说”(self-conscious fiction)或“内向小说”(introverted novel),meta一词源于希腊文,意为“伴随着……”,“超越……”等抽象的关系,过去通常被译为“形而上”和“玄学”,其关键点是它对于自身的反省、解构和分析,简言之,“元小说是在小说本身内部探讨小说的理论”。[2]31具有三个比较显著的特点,“1.玩弄文字游戏;2.小说文本直接引入作者”;3.浓厚的自我意识”。[2]36而“侦探元小说”(metaphysical detective story),也称为“玄学侦探小说”或“反侦探小说”(anti-detective story),这个概念是著名的侦探小说理论家,《为了娱乐而杀人》的作者霍华德。海格拉夫提出的,它既是“元小说”的次文类,又是侦探小说的次文类。
侦探小说在文学门类中一直是被界定为通俗小说而存在的,因为侦探小说具有清晰可辨的模式,契合通俗小说的一般定义:“通俗小说是模式小说。每类通俗小说都必段遵循一定的情节、人物创作规则和避免犯一些禁忌。这些规则和禁忌既为作者所承认,又为出版商所要求。”[3]3对于侦探小说的模式,W(H(奥登这样归纳道:“侦探小说的基本模式是:谋杀发生;许多人有嫌疑;除凶手之外所有人的嫌疑一一洗清;凶手被逮捕或死去。”[4]
侦探小说诞生于十九世纪的英美,工业革命、启蒙运动、期刊杂志的流行等因素的作用在市民阶层中培养出了一大批的读者,侦探小说的模式刺激而易读,恰到好处地迎合了这一些读者的口味。《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有这样的评论:“时人有看不起西方言情小说、社会小说及政治小说的,可没有人不称赞西方的侦探小说”。[3]182侦探小说封闭的结构让它成为给予读者游戏般体验的“避世文学”,比起其它文类,理论家们也更容易剖析它的规律,比如在S.S.范达因的《写作侦探小说的20条准则》和诺克斯的《侦探小说十诫》等作品中,侦探小说的一整套模式一览无遗。二十世纪后现代文学中,互文、拼贴等文学游戏随处可见,侦探小说这一在形式上高度程式化的文类恰好满足了作家们进行文学实验的需求,“侦探元小说”应运而生,较为典型的有博尔赫斯的《小径分岔的花园》,艾柯的《玫瑰之名》,罗伯特-格里耶的《橡皮》、《偷窥者》,保罗。奥斯特的《纽约三部曲》等等。这些作家不约而同地借用侦探小说这一形式,却又颠覆了传统侦探小说的写法,原本通俗的故事常常消解在松散的叙事中不了了之。
国内著名的侦探小说研究家袁洪庚这样分析:“玄学侦探小说的写作完全建立在对传统或主流侦探小说的陈规俗套的颠覆与反叛上。它所关注的不再是具体的虚构的外部世界,而是小说写作本身,也即批评家们常说的、具有自我观照性质(self-reflexive nature)的实验。传统侦探小说致力于从认识论的层面上考察外部世界,它的情节是为寻觅知识中隐匿、欠缺的那些环节而设置。它要解决的是如何解释世界的问题,具体地说不外乎‘发生了什么事’、‘怎么会这样’,以及‘这是谁干的’这类问题。”[1]128也就是说,侦探元小说是借由侦探小说的外衣对传统叙事结构进行解构,它们其实并不真正关心侦探小说的那个核心问题——凶手是谁。虽然这些小说中也会存在案件,但是案件的最终走向往往在作者心存旁骛的叙述中慢慢模糊在读者的视野中。侦探小说从情节叙事上是历时性的,封闭式的,它一定会提供一个侦探,一个案件和这个案件的答案;而侦探元小说也提供侦探和案件,却对于那个答案缺乏真正的兴趣,也无心通过层层的推理来论证,它将读者置于一个不再关心时间顺序的世界,是共时性的,因此它是开放式的。正如保罗。奥斯特在区别他的小说与侦探小说时说,侦探小说是给答案的,《纽约三部曲》是提问题的。所以侦探元小说虽以侦探小说为形式,却不以侦探小说的目的为目的。在阅读这类小说时,读者的期待也随之改变,对于作品的思考超越了案件本身,读者与作品之间的关系也自然而然地改变了。
文学的门类从来都是相互影响的,侦探小说家们不愿永远只和读者玩猜谜和解谜的游戏,于是产生了达许尔(哈米特和雷蒙(钱德勒领军的美国冷硬派侦探小说革命,他们的宗旨是侦探小说要“把谋杀案还给他有杀人理由的人,不仅仅是提供一具尸体而已”。[5]二十世纪后半叶之后,侦探小说除了内部结构革新外,也开始慢慢尝试挣脱其通俗文学模式的束缚。大量采用戏仿、互文等后现代技巧,刻意将作者的话语权代入人物,具有强烈的自我指涉意识,从而使侦探小说具备了元小说的特质。
二、《图书馆里的贼》的“侦探元小说”性
《图书馆里的贼》是布洛克雅贼系列小说的第八本,在这本小说之前,主人公(人前的身份是二手书店的老板,人后的身份是偷窃成癖的梁上君子的伯尼)已经一次次地撬开别人的门并且因此卷入一起又一起的谋杀案,于是不得不充当侦探的角色寻找真凶,以摆脱自己的犯罪嫌疑。《图书馆里的贼》也遵循了偷窃-陷入麻烦-寻找真凶的模式,只不过从第一个章节起,作者就有意将浓重的英式氛围引入书中。故事场景设置在加特福旅舍,那是距纽约只有三小时路程的“地道的英国乡村宅院”,那正是符合熟读阿加莎。克里斯蒂和多萝西。塞耶斯的英伦迷胃口的乡间;而伯尼带着他的女同性恋闺蜜卡洛琳造访该地的真正目的却是偷一本雷蒙。钱德勒签名题语献给达希尔。哈米特的《长眠不醒》。这两个元素的设置让侦探小说史上两大流派产生碰撞,作为冷硬派代表钱德勒的传承者,布洛克在此却似乎要一反其创作常规,欲向读者展示一个英式谋杀的画卷。当然,他绝不会仅仅按部就班地贡献一篇阿加莎式的小说,纵观全书,它更像是一篇以冷硬派的视角所剖析的关于古典派的论文,这才使其有了侦探元小说的实验感。
在小说开篇,作者就借主人公之口说:“你甚至不必是个侦探小说迷,也会喜欢钱德勒。你会听到有人说:‘我从来不读侦探小说,当然雷蒙。钱德勒除外。我崇拜钱德勒。’”[6]25于是整部作品有了向钱德勒致敬的基调,接着,他用了整整四个章节来铺垫小说的理论背景,冷硬派侦探小说的两大先驱哈米特与钱德勒的作品、生平与互相之间的交集,他甚至直接引用了钱德勒在《简单的谋杀艺术》对哈米特的评价,而这句话正是道破冷硬派较之古典侦探小说革命性意义的经典论述。
小说按照读者可以预料的节奏进行下去,加特福旅舍如约迎来了身份各异、各怀心事的客人,作者时不时地加入“不仅加特福旅舍好像是英国侦探小说场景重现,连客人也好像是直接从书里走出来的”,“如果这是部英国侦探小说,而不是真实生活的话……”这样的句子,似乎是提醒感觉比较不敏锐的读者,本书正在英式谋杀的轨道上徐徐前行。如果读者还不够敏锐的话,主人公伯尼和卡洛琳却似乎非常清楚自己身处的故事的行进方向——有人会被杀,然后他们找出答案,就像那些侦探书里写的那样。
伯尼在谜宫般的加特福大宅潜入图书馆偷书后,第二天早晨就出现了一具尸体,在这种状况下,暴风雪是必不可少的,电话线也恰到好处地断了——一切与外界的联系都失去了,于是密室出现了,凶杀案就发生在这个密室,幸存的房客面面相觑,因为他们当中有一个人是凶手。凶手出现了,侦探也自然应该登场了,所以卡洛琳认为伯尼应该尽快出击,不然第二具尸体就会出现——就像侦探小说里的那样。而剧情被她全部言中,不但出现第二个受害者,还出现了第三个——那个没人知道姓名的厨师,死得干干净净,悄无生息,而这些情节都让人那么熟悉:“这完全是出自阿加莎。克里斯蒂,大概是《捕鼠器》和《无人生还》的混合版。我们孤立无援,既无法离开也没有人能够来救我们。而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凶手的企图。”[6]159故事中的人物完全清楚自己所处于一个故事中,并了解它的走向,对于小说中的一个“人物”来说,他们似乎知道得太多了,因为作者赋予了他们额外的权力,让他们从某种意义上扮演了叙述者的角色。
胡全生在《英美后现代主义小说叙述结构研究》里对于人物与叙述者之间的关系有这样的阐述:“一般而言,叙述者可分为三类:1.叙述者>人物;2.叙述者=人物;3.叙述者<人物。第一类多为现实主义小说所采用,后两类多为现代主义小说所采用。但在后现代主义小说中,往往还见另一种超然于上述三类叙述者之上的一种叙述者。有人称他为‘不速客叙述者’(intruder)。这种叙述者就是真正的作者,但他不讲故事;他只评论故事的叙述(故有人称此为元叙述),而评论的要旨,往往就是对读者明言‘我讲的故事是虚构的’。”[2]67主人公伯尼和卡洛琳不时地打破文本的束缚,像一个不请自来的叙述者,一面作为参与者存在于故事中,一面又会选择时机突然停下来讨论故事的行进方向,这就是典型的“元叙述”。而读者也被他们带动着,从故事外部的旁观者不时地参与到作者的解构游戏之中。可见,与其说这是布洛克的一次单纯的英式模仿,不如说这是借着对阿加莎式侦探小说的自我戏拟,当小说自身成为作者和读者的关注点时,大家也就不十分介意“谁是凶手”这个阿加莎式小说的经典问题了。
在结尾处,布洛克还任性地给小说留了个尾巴——那个无名的厨师死到最后还是不明不白。这是传统侦探小说不可能出现的,因为凶手不交代,小说就失去了意义。钱德勒《长眠不醒》故意略去了司机的死因,以示与古典侦探小说的区别,所以布洛克这个结尾的处理一方面是向钱德勒致敬,另一方面也表明了“侦探元小说”的写作动机。“反阿加莎”设置加重了叙述者在小说中的呼吸声,布洛克解释道:“不能因为他写了书,就表示他知道谁杀了司机。我们也永远也不知道谁杀了厨师,就和雷蒙德。钱德勒一样。”[6]318
三、《超杀人事件》的“侦探元小说”性
日本是侦探小说产业极为发达的国家,“推理小说”这个概念就是其发明并习惯使用的,并且衍生出本格派、变格派、社会派等分枝。作为日本当今侦探推理小说最畅销的作家之一东野圭吾,电气工学毕业的他以获得江户川乱步奖的《放学后》打入推理小说界,从此开始了他产量极高,形式多样的小说生涯。东野的视野从来不局限于推理,他的作品折射了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日本社会的方方面面,被称为本格写实主义。他认为,好的小说首先应该是个好的故事,因此他非常重视叙事的多样化,在他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多重视角叙事(多位嫌疑人对于同一事件的不同描述),多线结构(查案线和主人公的成长线时而平行时而交叉进行),内外聚焦并置(案件当事人的感受和旁观者的观察并置,并附以大量的日记、书信等形式辅助故事的进行)等等多种技巧。在日本推理小说高度产业化的环境下,作者完全打破了侦探小说的叙事结构,用无厘头的方式揶揄侦探小说行业内部的乱象,手法荒诞,充满黑色幽默。“名侦探”系列、“三笑”系列等短篇集均是这类作品,《超杀人事件》则将这个功力表现到了极致。
作品中的八个短篇是作者拿着手术刀对侦探小说的一次全方位剖析,完全支解了它的固有模式,文体本身成了写作对象,该书的副标题《推理作家的烦恼》所传达的信息表明,这本小说讨论的是侦探小说业界现象、侦探作家的写作困境等等侦探小说的内部问题。
这八个短篇用夸张荒诞的手法展示了日本推理小说界的一系列怪现象,有的作家为了逃税,不得不生硬设置人物场景,在小说中罗列一大堆可以报销发票的生活用品;有的作家猜不出自己小说的结局,不得不骗来一堆编辑来猜小说中的凶手;有的作家为了迎合出版界的趋势,不得不把八百页的小说撑成两千页的“超级巨作”,结果破了最重推理小说的纪录;有的评论家为了应付阅之不尽的小说稿,不得不买了书评机,于是可以随意选择“盛赞”或“恶评”模式瞬间完成评论……虽是荒诞,却映射现实,在推理小说产业化高度发达的背景下,写作者和文本都成为了产业链中的一环,似乎早已被异化,作者选择了以退为进的夸张、扭曲的游戏式写法,倒也符合后现代主义的精神。
在大部分的故事中主人公都是推理作家,因此既是故事的参与者与叙述者,又是小说的创作者,而他所处的故事与他所创作的故事就形成了文本套文本的结构,在后现代语境下,不管是故事的文本,还是故事中的文本,成为了推理机器中的一枚螺丝,或是作者写作游戏中的一颗棋子,人物承认了自己的虚构性,失去了血肉的特性,成为了推理小说中的符号。作者如外科医生般将推理小说放在手术台上一层层剖开,于是情节失去了连贯的意义,文本与文本间组成了断裂的拼贴。主人公的推理作家身份又与作者产生了相互作用力,二者之间形成了巴赫金所说的“复调”,于是无意识间让他产生了高于故事人物又区别于作者的叙事能力,从某种程度上达到了“不速客”叙述者的效果,整个小说也形成了更加立体的叙事结构。
以《超猜凶手杀人事件》为例,读者先看到了这样一个故事:四位不同出版社的编辑被推理作家约到一起要求参与猜作家新小说凶手的游戏,猜到凶手并能够为自己的推测做出合理论证的编辑可以为他的出版社获得该新书的版权,当大家正冥思苦想时,隔壁传来尖叫声,随后大家便发现了作家的尸体。随后读者就发现,原来这个故事是作家以自己与现实中的编辑为原型所写,书中所写的正是他所处的现实中发生的一切,他也要求编辑们猜凶手,而猜的正是杀害他写的故事中的作家的凶手。当其中的一位编辑了解到作家自己其实根本也没有答案,只是想借助编辑提供的答案来完结自己的故事后,不由心生杀死作家的冲动——就如作家给他们的故事里的情节那样。于是这则小说的故事与故事中的故事互相呼应,形成自我互文。
比如《超理科杀人事件》和《超长篇小说杀人事件》,故事中的作家分别为了逃税和拼凑字数的需要,将自己的作品不断地推翻重建,最后形成了两本超烂和超重的小说。如果说作者是在以手术的方式剖析推理小说的话,那么他让主人公自己持起了手术刀,并向读者作术前阐述:“以下的两段文字纯属作者专业知识的炫耀,无相关专业背景的读者可以略过”,“为了应付出版社的要求,作者将在以下了两页拼凑字数,望读者理解和见谅”。这样的戏谑味十足的自我指涉就是典型的元小说技巧,在整本小说里比比皆是。小说中的作家胡乱拼凑的一个个片段就像割裂式的碎片,意义已经流失在文字游戏中,情节无需要再找出路,强烈的荒诞感之下,是作者对于侦探小说这个文体本身的思考。副标题中《推理作家的苦恼》中“苦恼”一词既暗示了本书所刻画的一切让人啼笑皆非,又隐含了作者在嬉笑怒骂背后的忧虑,因其尚存忧虑之心,读者仍然能够期待侦探小说未来更大的可能性。
布洛克的《图书馆里的贼》和东野的《超杀人事件》都是对于侦探小说的戏仿,前者以英式古典侦探的外衣解构了古典侦探本身,并向冷硬派侦探致敬;后者则以侦探小说从业人员的身份以文本游戏的方式将侦探小说业内的炎凉世态一一呈现。或戏谑,或夸张,指向的都是侦探小说自身问题。脱下后现代嬉笑怒骂的外衣,我们可以看到两位作家对于侦探小说在文学意义上的思考与摸索。尽管侦探小说已经发展得非常成熟,然而模式化的叙述结构也容易使其陷入自身发展的僵局,布洛克和东野圭吾让我们看到了它与后现代文学结合后进一步发展的可能性。
[1]袁洪庚.旧瓶中的新酒:玄学侦探小说论[J].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8,26(1):127-134.
[2]胡全生.英美后现代主义小说叙述结构研究[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
[3]黄永林.中西通俗小说叙事:比较与阐释[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4]袁洪庚,魏晓旭,冯立丽.侦探小说:作品与评论[M].北京:外语教育与研究出版社,2011:397.
[5]雷蒙·钱德勒.简单的谋杀艺术[M].董乐山,石蓝,译.北京:新星出版社,2008:19.
[6]劳伦斯·布洛克.图书馆里的贼[M].王志弘,译.北京:新星出版社,2012.
An Analysis of Meta-detective Stories’Features of Burglar in the Library and Super Murder Stories
XIA Han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Zhejiang Ocean University,Zhoushan 316022,China)
As a distinct genre of popular novels,detective stories have gone through a history of two centuries,many schools of detective stories have formed,and also,they have influenced and been influenced by other genres of literature.American hard-boiled detective novelist Lawrence Block and Japanese detective novelist Higashino Keigo have one thing in common in their works:besides the typical detective stories,they have tried their hands in post-modernism in their later works.Burglar in the Library and Super Murder Stories are typical among those works.Both of the two novels discuss detective stories within themselves,so that both of them are with the features of meta-detective stories.
meta-detective stories;Lawrence Block;Higashino Keigo;Burglar in the Library;Super Murder Stories
I106.4
A
1008-8318(2015)04-0047-05
2015-02-17
夏寒(1982-),女,浙江舟山人,讲师,硕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