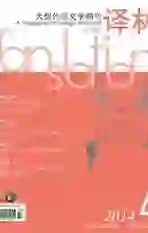马雅岭:茜茜公主永远的心痛
2015-01-13
1889年1月30日,奥匈帝国31岁的皇太子鲁道夫,茜茜公主和弗朗茨·约瑟夫皇帝的独子,在位于维也纳西南郊的马雅岭自杀身亡。同赴黄泉的,还有他年仅17岁的小情人玛丽·维切拉。
鲁道夫自杀后,奥匈帝国皇室旋即将所有关键文件销毁,并勒令所有相关人员一律三缄其口,不得对此事件提供任何信息,作任何表示或评判。此事遂成百年悬案。
马雅岭的呼唤
125年来,马雅岭那座卡麦尔修女院肃立于尘世。去春,细雨潇潇间,我造访了她,见四周旷野沉寂,山色黛绿,松柏常青。通向修女院的僻静小路上,几个行人踯躅着,沉默无语,仿佛也在寻觅、感知、冥思,思量百年前扑朔迷离的皇家血案。今春,我重返马雅岭,为的是再次回顾那段历史,寻觅事件的蛛丝马迹。修女院依旧,院前的迎春花盛放,两棵老朽垂柳,蹲在小小的芦苇池边,粗壮而古旧的树干上,抽出无数鲜嫩而曼妙的枝条。
马雅岭早在公元900年左右,便得其名,地属两位贵族。马雅岭的修女院,史上曾是隶属于圣十字架修道院的一座教堂。1412年,圣十字架修道院首次修建此座哥特式教堂,并命名为圣劳伦斯教堂。1529年,教堂被土耳其侵略军夷为平地。1642年,圣劳伦斯教堂复建,重见天日,并成为周边天主教徒的朝圣之地。未料它灾难深重,1683年,土耳其人第二次入侵,再次将之摧毁。但教堂很快又被重建,成为更多教徒的圣地。
1886年,哈布斯堡皇太子鲁道夫对马雅岭一见钟情,将这座教堂买断,改建成皇家狩猎场。此后三年,这里成为奥匈帝国的一座狩猎城堡,鲁道夫出入频繁,视马雅岭为远离尘嚣、忘却烦恼的好去处。因鲁道夫性情恭谦,温文尔雅,和蔼可亲,毫无皇族傲慢之气,故当地村民与之交往甚多。当时一位马车夫很自豪,因为鲁道夫常坐他的马车,还称他为“亲爱的邻居”;一位女邮递员回忆道,她曾因为不顾天色已晚,将一份电报急送至马雅岭,获得了鲁道夫赠送的一座金钟,让她欣喜若狂。可见,鲁道夫极有亲和力,在当地臣民中口碑良好,颇受爱戴。
然而,骨子里具有亲民思想,甚至民主意识的鲁道夫,与其父,即堂堂奥匈大帝弗朗茨皇帝时有争执。政见的不同,使得这对父子琴瑟难和,常常针锋相对。鲁道夫年轻气盛,难免言语不逊,这让弗朗茨十分不安,对皇权使命在身的皇太子产生了怨怼和提防。而弗朗茨的独裁和强权,也让鲁道夫感到社会不公,身不由己,前途渺茫。父子俩彼此不理解,随着时间的推移,隔阂渐深。鲁道夫那颗孤独而善感的心,急需安抚,他深爱的母亲茜茜公主,却又经常出远门,不在身边。
一个公认不讳的事实为,鲁道夫自幼聪慧好学,但性格内敛,天生敏感,是个需要呵护和耐心对待的孩子。然而,仿佛天意捉弄,鲁道夫儿时的首位启蒙老师竟是铁掌大将军,法国人贡德勒库伯爵。这个“铁面无私”的强势人物对鲁道夫实施的教育,是充满险道和恐怖的军事化模式。贡德勒库伯爵的粗暴和不顾后果,给鲁道夫细腻而敏觉的幼小心灵,留下了不少阴影。长大后,鲁道夫虽有心仪之人,却在父母包办下,不得不与门当户对,却毫无感情的皇族女子成婚。加上因挑战皇权,常年与父皇唇枪舌剑,欲罢不能,皇太子烦恼无数,情志抑郁。
可以说,不得意的鲁道夫短短一生,心灵的土地上千疮百孔,坎坷不平。自杀,是不是他得以最终超脱的抉择?然而,在过去的125年里,被人为销毁或掩饰的证据时而显山露水,又似乎暗示着这位并非没有自杀倾向的皇太子,未尝不是一个时代阴谋的牺牲品。
一个时代的悲剧
走进卡麦尔修女院,便见曾经搁置鲁道夫卧床的地方,已上下两层打通,改成偌大的祭坛。坛顶的彩绘图上,众天使在柔和的圣光里飞翔。祭坛左边的侧室里,有个罩在镶金拱形门内的圣母石像,高约170厘米,精工细雕。雕像的胸口,插着一把匕首。当年茜茜公主获悉儿子自杀后,身心俱裂,斥资建成这座雕像,喻义自己如被匕首穿胸,生不如死。

茜茜公主绝没有料到的是,九年后,即1898年,她自己厄运降身,在瑞士旅行时,遭意大利无政府主义分子暗杀。而暗杀者的武器,竟也是一把匕首!
这是一个时代的悲剧。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欧洲,平民阶层的自主意识,民族独立的强烈呼声,已如汹涌波涛,铺天盖地,席卷而来,令帝国皇权招架不住。王储、贵族阶层岌岌可危,正被社会大潮逐步淘汰,其代表人物,自然成为矛头所向。鲁道夫自杀后,弗朗茨皇帝之弟卡尔·路德维希的长子弗朗茨·斐迪南大公,成为皇室继承人。斐迪南与鲁道夫性格迥异,社会主张相去甚远。斐迪南虽然自己娶了庶妻,但心中无民主意识,反而,更多的是称霸世界的帝国野心。他认为,由奥地利和匈牙利组合而成的二元奥匈帝国要想更加强大,就应该吃下南斯拉夫,与之组成三元帝国。然而,20世纪初的塞尔维亚王国,其民族主义运动已初见端倪。1914年,斐迪南大公携妻视察奥匈帝国波黑省首府萨拉热窝时,遇刺身亡。这个事件,成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索,同时也埋葬了奥匈帝国。
1916年,弗朗茨·约瑟夫皇帝驾崩。1918年,奥地利成立第一共和国。哈布斯堡王朝在一战的滚滚硝烟里,寿终正寝。
自杀?他杀?云谲波诡
鲁道夫死在这样一个特别的历史时期,自杀他杀,众说纷纭,并不奇怪。毕竟,当时社会动荡,各种势力林立,阴谋迭出。笔者在翻阅了一些资料后发现,1989年,德国《明镜》周刊在哀悼哈布斯堡王朝的没落女皇琪塔谢世的文章里,曾提及女皇对她儿子奥托所言,即鲁道夫和玛丽的马雅岭之死,非鲁道夫所为,他们是“政治阴谋的牺牲品”。同年,女历史学家布丽吉塔·哈曼在接受奥地利杂志《侧影》的采访中也说,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当年鲁道夫之死与共济会组织有关,是“掩人耳目之举”。共济会打着博爱的旗帜,其成员却大都是政治家和社会名人,权贵意识浓厚,其秘密宗旨是统治世界,建立世界新秩序。endprint
后来,笔者发现早在1983年,德国《时代》周报便惊爆女皇琪塔的回忆。这位在世98年的老人,成为一个逝去时代的活化石。她无数的回忆,虽有些自相矛盾,但毕竟提供给了世人一个窥探皇室内幕的重要棱镜。琪塔对周报说,鲁道夫是一个国外地下组织的政治阴谋牺牲品,这个组织在获悉鲁道夫与其父不和后,多次派人怂恿他,协助刺杀弗朗茨·约瑟夫皇帝。而他,不予以配合,还暗中保护其父。这引起那个地下组织的不满和恐慌,最终,他们派遣法国人克莱门梭前往马雅岭,刺杀了鲁道夫及其小情人。
但是,根据鲁道夫的多年情人米琪提供的消息,鲁道夫因为思想激进,极不得志,故早有自杀之心。为此,她还通知过警方,却从未被人重视。1889年1月27日,即马雅岭自杀事件的三天前,皇太子鲁道夫去维也纳与米琪度过了最后一夜,翌晨返回马雅岭。见她时,鲁道夫请求她陪自己共同完成赴死计划,遭她婉拒。

鲁道夫的自杀迹象不止于此。鲁道夫在1887年便写下遗嘱,交给其父皇。遗嘱将所有财产留给自己的女儿伊丽莎白·玛丽,给情人米琪也留下了3万古尔盾银币。可惜,鲁道夫死后,米琪拒绝任何采访,完全低调生活,直至43岁时去世。死后,她未留下任何笔记、信件或回忆录。一条线索就此断掉。
再有的一个自杀证据,是鲁道夫在死前留给妻子,比利时列奥波德二世之女史蒂芬妮公主的一封信。信中说:“亲爱的史蒂芬妮,你将从我的存在和折磨里解脱,幸福地我行我素了!……我安静地走向死亡,唯有死亡,才能挽救我的善名。”
玛丽·维切拉
与史蒂芬妮的包办婚姻,是鲁道夫心头的痛。两人虽然有了女儿,但他们的婚姻从来不是夫唱妇随的金玉良缘。
鲁道夫婚前曾经有过一场轰轰烈烈的爱情。1878年,鲁道夫完成学业后,奉命前往布拉格服役。在布拉格逗留期间,他邂逅一位年轻貌美的犹太女孩,陷入热恋。据他的外孙女回忆,那是他一生中唯一的一场真正爱情。这个犹太女孩与他成双成对,出入于社交场合。维也纳警署的秘密档案文件中记载道,这个女孩甚至陪同他前往过布鲁塞尔,在皇宫参加新娘选秀活动。犹太女孩命运多舛,不久被流放,并客死他乡。
伤心的鲁道夫巡走欧洲和其他大陆,时而隐名匿姓。他走遍奥匈帝国的疆土,并动员专家,把各处的风俗文化地志历史等,记载在案。他也亲手捉笔,撰写文稿。这些旅行让他眼界大开,他开始陶醉于大自然,成了鸟类专家。
鲁道夫婚后与史蒂芬妮在布拉格居住了几年,并有了女儿,即伊丽莎白·玛丽女大公。但事实上,新婚伊始,两人已冷语相向,不依不饶,难享琴瑟和鸣之乐。回到维也纳后,鲁道夫秘密情人不断。但,似乎这也无法给他带来真正的心灵慰藉。我想,他心中最大的结,该是政治上的激进主义,无法与皇室的清规戒律合拍。他远走天涯的那些旅行,使他无可遏制地拥抱自由和民主。他对德国自由主义和匈牙利民族运动的同情和支持,让他在皇室倍遭孤立和冷遇。
马雅岭的皇家狩猎场,给了他反思的空间。可惜,或许这个空间让他愈发地仇视人间。可以说,他的绝望,也建立在不可思议的孤独之上。他决意弃绝尘寰时,竟然希望有人同行。这,对于一个温良开明的皇家绅士来说,是怎样的人性悖论!
在多年情人米琪拒绝了他的殉情要求后,鲁道夫的目光,转向了不久前刚刚结识的年轻女子,男爵夫人玛丽·维切拉。
1871年出生于维也纳的玛丽·维切拉,如许多年轻姑娘一般,痴情于皇太子鲁道夫。1888年10月中旬,年仅17岁的玛丽给鲁道夫写了封情书。两人一见面,遂成情人。这离两人共赴黄泉,仅有三个月的光景。1889年1月29日,鲁道夫派人叫来玛丽,与他共进晚餐。对于可能发生的事件,玛丽毫无察觉。她欢天喜地,梳妆打扮,盛装赴约,准备与鲁道夫共度良宵。站在早已改为祭坛的台前,我问修女院里的接待员,两人翌日如何被发现。这位上了年纪,慈眉善目、笑意盈盈的修女说,鲁道夫的侍从一般在早晨10点左右会敲门,服伺他起床。但那晚,他们知道玛丽在内,不便打扰,就一直恭候到午后。 然而,太阳西斜了,室内依旧没有动静。这时,人们才警觉起来,开始叩门,却不见应答,无奈,破门而入,眼前,惊现惨不忍睹的一幕:血流满床,鲁道夫和玛丽双双中弹身亡。
经法医鉴定,鲁道夫先执枪,对着玛丽头颅开了火,之后举枪对准自己脑门,饮弹自尽。当晚,茜茜公主和弗朗茨·约瑟夫皇帝赶到马雅岭,肝肠寸断。之前,玛丽的尸体已被藏匿,留下鲁道夫,独自瞑目在床。有人就此图景画了素描。参观劳伦斯教堂,人们可以在墙壁上悬挂的图文资料里,找到这幅触目惊心的图画。
因为身份不同,玛丽被葬进马雅岭当地的墓园,鲁道夫的遗体,则在当晚被运回维也纳霍夫堡皇宫,后安葬进哈布斯堡皇室位于市中心的皇家墓室。
雨中,我站在玛丽的墓前,看那个如花似玉的年轻生命,天真无邪,痴情纯洁,却转瞬即逝,灿若缤纷落英。玛丽生前死于非命,死后,还几度遭遇不测。她30日死亡,31日便被装进当地木匠用松木制成的棺木里,匆匆下葬。同年5月,玛丽的母亲托人造了一口华丽高档的铜棺,给女儿举办葬礼。可这口铜棺在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烧杀抢掠的混乱局面里,被盗墓者肆意破坏,面目全非。1959年,一位名叫特蕾西亚的女子(她祖父辈曾是弗朗茨·约瑟夫皇帝的猎友)让人给玛丽重修了一口锡棺。然而,这口棺材又在1991年被一个家具商盗走,连同玛丽的遗骨。一年后被发现追回时,家具商当下表示,他只是对玛丽其人其事感兴趣,花钱聘请了医学专家,对玛丽的头盖骨和毛发进行DNA鉴定。但鉴定结果并未公开。1993年,玛丽的遗骨被安放进一口金属棺材,她的第四口棺材,并葬于圣十字架村墓。

拆不掉的心痛
鲁道夫和玛丽死后不久,弗朗茨·约瑟夫皇帝即在年内下令,将马雅岭狩猎城堡全盘改建。鲁道夫的卧室内部完全拆除,修成祭坛教堂,教堂内放置鲁道夫生前的一些图文资料,供人追悼。1891年,改建后的城堡交付给卡麦尔教会,只接受修女,成为眼下宁静柔和、肃穆安详的卡麦尔修女院。修女院的修女们每日早晚诵读经书,粗茶淡饭,守护着这充满悲剧色彩的方圆之地。维持日常开销的,只是时而慕名而来,回顾历史的人士给予的微薄施供。
房屋好拆,心痛难补。虽然鲁道夫的卧室被就地拆毁,修成了一间纪念他的教堂,卧床位置,也成为天光与灯火交辉,众神起舞,通明永昼的华美祭坛,然而丧子之痛,成为茜茜公主一生最大的悲哀。这位曾经与弗朗茨·约瑟夫皇帝相亲相爱的巴伐利亚公主,一直对皇室的森严等级颇有微词,对民主政体充满遐想。她曾在诗化的文字里表示:“我触摸我的发,它的存在,却像我头上的异物。”这句话,在独子鲁道夫离世后,该是她绝望心态的最好写照。所有的荣耀繁华,都是过眼烟云,不值一提,而自己唯一的血肉,竟如此决绝离去!
历史学家布丽吉塔·哈曼曾评论道:“茜茜是个聪慧而具反叛精神的女性。”作为母亲,茜茜想必是了解儿子的,鲁道夫的寂寞无奈,又何尝不是她的心事?然而,即便茜茜伶牙俐齿,在封建皇权的时代,她为儿子所说的话,想必如沧海一粟,不为人觉,亦不为人解,甚至,是要遭皇室唾弃的。何况她多年与弗朗茨貌合神离,影响力大约荡然无存。母亲无力回天,无力阻挡儿子匆匆离世的脚步。千年古地,百年悬案。马雅岭,终成茜茜公主永远的心痛!endprint